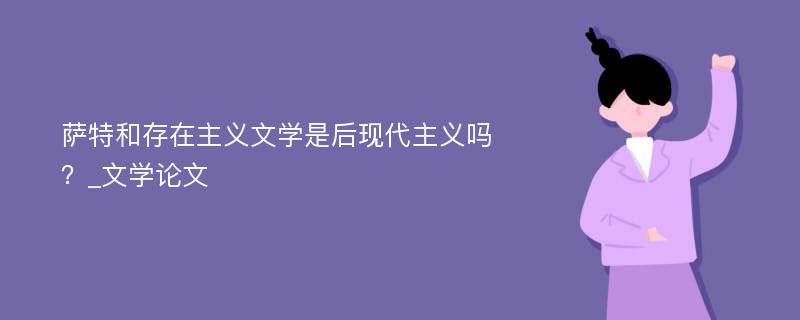
萨特与存在主义文学是后现代主义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存在主义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郑克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史》修订版(下),是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校使用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遗憾的是,该书出现了不该出现的错误,在第四章居然把西方现代主义重要流派——存在主义,划入了后现代主义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西方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如弗·詹姆逊、伊哈布·哈桑等为后现代主义制作的家族谱系中,还是在中国专治后现代主义的著名学者如高宣扬、王岳川等的专著中,从不见著一个字的萨特和存在主义文学,而在郑本《外国文学史》修订版(下)中萨特和存在主义文学却被列入了后现代主义文学。我们认为,这是理论与批评的双重错误。
一、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毫不相干
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西方文化思潮呢?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对此作过许多描述和概括,有很多很有影响的说法。而且,几乎所有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都是在与现代主义的比较中进行的。但我们正是从那些出自不同学者之口的描述性话语中,获得了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詹姆逊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是“对高级现代主义的既有形式的刻意反动”[2](P2)。詹姆逊的结论,完全可以参之以哈桑的《走向后现代文学》,因为在那里哈桑给出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33条对立。[3](P112)尽管哈桑的对比研究十分深刻,极具权威性,但限于篇幅,我们不能照搬哈桑。我们只从众多思想家共同关注的几个主要方面看后现代主义怎样“刻意反动”了现代主义。
第一,现代主义是以进行“宏大叙事”为己任的。现代主义宏大叙事有两大类,即政治叙事和哲学叙事,“包括诸如辩证法的精神,解释学的意义,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者财富的创造等等话题”[4](P251)。以人的生存的名义彻底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全面揭示西方社会的异化状况,宣示人的自由本质及其与异化的抗争,乃是现代主义文化生产的基本目的。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则完全相反。正如利奥塔明确宣布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在后现代主义叙事中,“那种能够产生原动力的伟大英雄、巨大灾难、伟大航行和崇高目标都已烟消云散”。[4](P252)后现代理论家吉尔·德勒兹则宣称,后现代社会“主体”就是一架“欲望机器”,后现代文化就是“欲望的生产”,但这欲望“本质上是非中心的、片段的、动态的”,欲望仅仅是日常欲望而非“人类解放的欲望”,为实现这些日常欲望的“欲望政治”,就是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微观政治”。[5](P122)迈克·费瑟斯通则提出,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呈现”[6](P95)。后现代主义倡导的是所谓“小叙事”,即没有总体性理论指引的叙事,差异的叙事,个别的叙事,日常生活的叙事。显然,仅在“叙事”理想方面,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就表现出一种坚定的断裂关系。
第二,现代主义是追求深度的文化。这是由其宏大叙事特征决定了的。因此,关于人类命运、人的存在状况、全面异化的程度,成了一切现代主义文化的“主旋律”。而后现代主义则恰恰相反,它否定意义,消解“真理”,因而公开倡导“去除深度”。后现代主义“大祭司”波德里亚就声称他“赞成另一场革命,一场20世纪的后现代性的革命。这场革命乃是对意义的广泛的解构。凡生于意义者必将死于意义”。因为“意义需要深度,一个隐藏的维度,一个看不见的底层,一个稳固的基础;然而在后现代社会里,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可见的、外显的、透明的,而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5](P164)而齐格蒙特·鲍曼则更直接揭示:“后现代主义者宁愿生活在无真理的状态之中。”[7](P218)为了“去深度”,后现代主义大力推广平面视像文化,把后现代社会变成“读图时代”。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观察到的:“目前据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图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当代文化正在变成视觉文化。”[8](P154-156)詹姆逊也发现:“现代社会空间完全浸透了影像文化,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统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2](P20)波德里亚对这种视像文化作如此评价:“艺术就已经在日常生活的普遍美学中被分解了,并让位于一种形象的纯流通,一种平庸的超美学。”“我们创造了大量的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没什么可看的……它们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没有投下任何影子,也没有任何结果。”[9](P305)
第三,现代主义是精英知识分子创造的文化,是如贝尔所说的坚持“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的“个性原则”的文化,“一种典型的唯我独尊的文化,其中心就是‘我’”。[8](P182)作为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现代主义是要求“艺术自律”、追求高雅理想的文化,它特别强调艺术的“个性化”和“独创性”,并以此自觉抵制文化商品化,或者说抵制艺术大众化。但布尔迪厄、贝尔以及詹姆逊却都发现后现代主义文化最主要特征是“消弭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界限”,因为后现代主义更愿意接受流行的商业的大众消费的市场,不屑于独创,更热衷于模拟、仿制、拼贴等手段,以满足大众消费的需要。波德里亚指出,后现代主义就是“仿真时代全面开始”,“到处都是‘拟像的创世纪’”。[4](P310)这种模拟的形象“与任何形式的现实都没有关系:它是其自身的纯粹拟像”[10](P77)。伊格尔顿说后现代主义的“典型文化风格是游戏的,自我戏仿的,混合的,兼收并蓄的和反讽的。它代表了在一个发达的和变形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一般文化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最终结合:它不喜欢现代主义那种‘纯粹的’自律的风格和语气”[11](P1)。显然,一是精英文化,一是“大众”文化,这是创作主体趣味和理想都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
第四,现代主义审美上追求“崇高”,或者说,现代主义与“崇高”认同。现代主义不注重再现美而致力表现丑,于是人们从现代主义笔下看到的只是丑的形象,然而透过这丑却能读出那“崇高”——“体积和力的无限大”(康德语)。这种体验无论是从蒙克的《呐喊》还是从奥尼尔的《毛猿》或者卡夫卡的《城堡》,无论是从达利的《内战的预感》还是艾略特的《荒原》或者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都能深刻地获得。人们说后现代主义终结了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被终结的实际上就是崇高。而终结现代主义“崇高”理想的武器之一,就是后现代主义“美的回归”的诉求。“美的回归”是后现代主义要求“去深度”、要求“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必然结果。正如德国后现代美学理论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言:“毫无疑问,当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美学的勃兴。它从个人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现实中,越来越多的要素正在披上美学的外衣,现实作为一个整体,也越益被我们视为一种美学的建构。”[12](P4)当然,这种“美的回归”并非回归传统美学。因为它有四个特点:其一,取消了审美距离,审美变成了“直观”,“这种审美方式表明了与客体的直接融合”[6](P104),主体性消解了。其二,把美仅仅视做外在形象的“漂亮”和视觉的“快感”。正如詹姆逊所总结的:“这就是后现代性的另一面,在原有的现代的崇高的位置上,出现了美的回归和装饰,它抛弃了被艺术所声称的对‘绝对’或真理的追求,重新被定义为快感与满足。”[2](P84)因而“今天所有的美都虚有其表”[2](P131)。其三,超真实。审美对象不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仿真”产品。“仿真的特点是模型先行——模型先出现”,“仿真……是一种无源泉的真实或一种实体的模式产物:一种超真实”。[9](P293)其四,超美学。审美判断已经不再可能,因为没有了审美理想、审美尺度或者称为价值标准。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在艺术问题上我们都是一些不可知论者,我们不再有任何美学信仰,不再信奉任何美学信条,要不然就信奉所有的美学信条。”[5](P175)
第五,现代主义是坚持总体论、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则是反总体论、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维尔施反复强调:“多元性是后现代的关键性概念”[13](P10),“后现代应被称作‘彻底的多元性’”[13](P7),“准确的后现代主义是名副其实的和有效力的后现代主义,它是真正支持多元性,维护和发展这种多元性”[13](P5)。德勒兹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客体支离破碎的时代,我们不再相信有什么曾经一度存在过的原始总体性,也不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有一种终极总体性在等待着我们。”[5](P98)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所有诸如绝对理念论、人的类本质、人的阶级属性、人的自由本质、英雄史观或者阶级斗争史观,以及历史必然性等等现代主义的观念,其实都是总体论的。同样,诸如欧洲中心论、白人中心论乃至于人中心论、自我中心论等等现代主义的观念,其实也都是总体论的。而总体论是后现代主义第一个绝对拒斥的理论。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和个体欲望的合法性,强调身体及快感的异质性,强调主体间性,强调对话性,从而把后现代主义从哲学上与现代主义彻底划割开来,两者泾渭分明,混淆不得。
因此,从文学研究后来“转向”到后现代文化研究的伊格尔顿才能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下这样一个很有综合意味的“定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中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性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糊了高雅和大众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11](P1)
存在主义文学是这样的文学或文化风格吗?显然不是。不仅不是,而且毫不相干;不仅不相干,而且是对头,或者反过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存在主义的对头。
二、萨特和存在主义文学是清晰至极的“高级现代主义”
联系上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分域,来审视萨特的存在主义及其文学,一切应一目了然。
第一,存在主义文学是典型的宏大叙事。这宏大叙事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或谓“人学”。因为萨特说自己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唯一给人以尊严的理论”。[14](P125)萨特最有影响的“人学”观念,就是他坚定地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他说:“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14](P117)但是,正如乔治·瑞泽尔所说:“正是出于反对这种人道主义,尤其是呈现在萨特著作中的这种人道主义,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举行了他们的反叛。他们试图对社会思想‘去中心化’,将它从‘人’这个焦点上移开。”[7](P38)萨特当然是不可预知这之后会发生什么“后”学的。他从这种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出发思考文学,把文学的本质与自由、存在联系在一起,提出:“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15](P116)“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15](P115)“作家为诉诸读者的自由而写作,他只有得到这个自由才能使他的作品存在。但是他不能局限于此,他还要求读者们把他给予他们的信任再归还给他,要求他们承认他的创造自由,要求他们通过一项对称的、方向相反的召唤来吁请他的自由。”[15](P105)萨特的全部文学创作也因此成了一种关于自由的叙事。用他的话说:“每幅画、每一本书都是对整个存在的复原,每一个作品都向观众的自由展现着整个存在。”“穿过作品现象的符合因果性,我们的目光达到作为对象的深部结构的符合目的性,而穿过这一符合目的性,我们的目光达到作为对象的源泉乃是其原始基础的人的自由。”[15](P109)
第二,存在主义文学是最自觉追求深度的文学。这深度就是通过文学艺术追问存在的真理。这源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通过解读梵高《农妇的鞋》,得出“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已经自行设置入作品中”,“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16](P21),“在作品中发生着这样一种开启,也即解蔽,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了。艺术就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16](P22)的重要结论,这就确立了存在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最典型的深度文化的理论基础。萨特很早就自许为思考真理并准备献身真理的“孤独者”[15](P9),毕生都在为他所思考的真理——人的自由而斗争。因此,他反对一切“唯艺术论”,最自觉地追求艺术的意义深度。他强调:“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15](P74)“这是艺术的最终目的:在依照其本来面目把这个世界展示给人家看的时候挽回这个世界,但是要做得好像世界的根源便是人的自由。”[15](P110)“作家可以引导你。如果他描写一所陋屋,他可以让你从中看到社会的不公正的象征,激发你的想象。”[15](P72)为了艺术的深度,萨特提出文学就是一种“介入”的重要思想。萨特认为,文学的本质是自由,为了实现它的自由本质,文学必须“介入”现实,介入就是为自由说话,就是争取自由。所以,“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15](P116)
第三,存在主义文学是精英文化的典范。可以说,西方文学在浪漫主义之外,很少有存在主义作家那么自我精英化的。请看这种萨特式精英“自我”:“当我欣赏一处风景的时候,我很明白不是我创造出这处风景来的,但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我,树木、绿叶、土地、芳草之间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就完全不能够存在。”[15](P105)“我的自由任意行事;我越是确立新的关系,我就越是远离那个对我发生召唤的幻觉的客观现实。”[15](P106)正因为这个审美主体、这个“我”在审美活动中处处强烈地表现自我的自由,于是,文学创作并不必要尊重客观真实,作家主观“创造”才是决定性的。萨特自豪地说:“作品也必须有一种豪情,……如果人们把这个世界连同它的非正义行为一起给了我,这不是为了让我冷漠地端详这些非正义行为,而是为了让我用自己的愤怒使它们活跃起来,让我去揭露它们,创造它们,让我连同它们作为非正义行为,即作为应被取缔的弊端的本性一块儿去揭露并创造它们。因此,作家的世界只有当读者予以审查,对之表示赞赏、愤怒的时候才能显示它的全部深度。”[15](P114)“现在是我们俩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责任。”[15](P113)什么是精英?这种自视为高于一切客观存在,自视为能改变或者创造世界的人,自视为救世者的知识分子就是精英。萨特的文学主人公都是这类精英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
第四,存在主义文学是“崇高”美学的顶礼者。存在主义文学中不见美。我们只见理念与情境的冲突。或者用海德格尔的概念,只见“在的真理”。如果说存在主义有“美论”,那么美也是决定于“真理”的。美只是真理的通道,只是为了显现真理而服务。海德格尔为“美”这样反复下定义:“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显现方式。”[16](P25)又说:“美与真理并非比肩而立的。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作为在作品中有真理的这一存在和作为作品——也就是美。因此,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16](P69)在萨特,便把审美快感与“自由”紧密联系起来。他说:“人们习惯称之为审美快感的感情,我宁可把它叫做审美喜悦。……自由辨认出自身便是喜悦。”[15](P110)说到底,这就是一种崇高美。我们从存在主义文学中处处可见这种“崇高”美。因为无论是从《恶心》、《苍蝇》、《自由之路》还是从《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和《鼠疫》,我们都能在那里感受到强烈的悲剧意识,即人的自由本质与荒诞现实的悲剧性冲突。而悲剧是与崇高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朱光潜先生早年所深入研究的:“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形式。”“因此要给悲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崇高的一种,与其他各种崇高一样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奋鼓舞的力量,它与其他各类崇高不同之处在于它用怜悯来缓和恐惧。”[17](P92)
第五,存在主义文学是以人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的集中体现。萨特坚信人是主体,人是中心,人的存在先于万物的存在。他说:“由于人的实在,才‘有’万物的存在。或者说人是万物借以显示自己的手段。是我们使这一棵树与这一角天空发生关联;多亏我们,这颗灭绝了几千年的星,这一弯新月和这条阴沉的河流得以在一个统一的风景中显示出来;是我们的汽车和我们的飞机的速度把地球的庞大体积组织起来;我们每有所举动,世界便披示出一种新的面貌。”[15](P94)萨特认为,人之所以要写作,就是为了彰显人,彰显人的主体性。萨特说:“如果我们自己决定生产规则、衡量尺度和标准,如果我们的创造冲动来自我们内心最深处,那么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作品中所能找到的永远只是我们自己。”[15](P96)萨特的戏剧杰作《禁闭》实际上就是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观念的集中表达。三个鬼魂个个要以自己为中心,人人都欲望着实现自己的自由,因而都视他人为敌。“他人就是地狱”,这是西方现代性形成的典型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使西方人几百年间一直进行着树立他者并征服他者的“宏大叙事”。事实上,“他人就是地狱”成为了西方现代人的悲剧性宿命,也是一个诅咒。要摆脱这种宿命和诅咒,是作为现代主义者的萨特式精英们无法胜任的。只有后现代主义出现,悲剧命运才能改观,因为只有后现代主义才废黜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确立了“主体间性”价值论,才能真正以平等对话的交往方式对待“他人”,萨特揭示的这种悲剧才能真正避免。
显然,存在主义只能是现代主义,而且与其他现代主义主流派相比较,它还更是一种詹姆逊所说的“高级现代主义”。
三、“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建设是严肃的事业
“面向21世纪教材”建设应该是一项严肃的事业。这严肃主要指的就是教材的权威性、科学性和学术创新性。首先,它是上世纪90年代由国家教委(教育部)直接组织领导的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宏图大业”,有着鲜明的国家事业规划色彩,而不是一个或者几个专家学者个人学术成就的展示,因此它应具有权威性。其次,这权威性应是建筑在科学性和创新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筑在权力话语基础之上的。不能设想一本缺乏科学性的大学教科书能具有权威性。我们即使并不希求一本教材通用一个世纪,“经得起世纪检验”,但它也不能出现明显的学术问题,乃至常识性错误。那是会损坏国家高等教育形象的。再次,面向一个世纪的教材,应该具有学术创新性。所谓创新,当然是在前人成果之上而不是弄些忽发奇想的东西,学术有所进步而不是倒退,形式更加精致而不是粗制滥造。
郑本《外国文学史》(下)虽然被封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却令人遗憾地未能达到这个基本要求。这并不仅仅因为上述把存在主义错划为后现代主义这一个事实。众所周知,该书曾经把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流派魔幻现实主义轻易地划归到“现实主义文学”中去,后来经学者严肃批评才在“修订版”中让其回归正位。但这个纠正亦未能彻底,因为在“修订版”2007年第12次印刷中还有“本书是将这一流派(即魔幻现实主义)列入现实主义去分析的”表述。[1](P181)这是其不严肃的一个证据。此外,本书还有其他常识性错误。例如:写出了“但泽三部曲”这样极富荒诞派色彩小说的君特·格拉斯和写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这样典型后现代主义风格小说的米兰·昆德拉,以及纳博科夫、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这样举世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作家,都被随意划到了“20世纪现实主义”中;而在“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被列举过的索尔·贝娄和威廉·戈尔丁,后来又被列入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流派和作家”中[1](P179)。同样,这张现实主义榜单上出现过的艾吕雅和阿拉贡,在本书下一章却成为了现代主义重要流派“超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亨利希·曼写于1914年前的《臣仆》不知根据怎样的“法西斯史”被说成“描绘了德国法西斯的狰狞面目”,而以“嚎叫”“我这一代精英”的痛苦为主题的美国存在主义小派别“垮掉的一代”,被三言两语介绍了一下就划进了“后现代主义重要流派”,却没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些当然也是不够严肃的证据。至于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说成是“主要受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影响”,就更令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人们熟知,后现代哲学的“话语者”无非就是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哈贝马斯等。
至于解读作品,那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乎不必强求。尽管作为全国通用教材,能“非个性化”一些更易于为大家所接受,而且那样也能使全书风格能尽量统一一些。但是这本书不是这样。例如有的作者可能为了表现其学识渊博,根本不顾及该书是大学教材而不是研究资料,只管展示下去,一节“20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简介,就一口气提到近120位作家。这不仅不符合大学教材的基本要求,而且容易给人以错觉,似乎20世纪欧美文学的主流仍是现实主义而不是现代主义。如果我们稍稍认真读一下全书起首那个对20世纪文学的“导论”,就会感到过分“个性化”对一本全国通用教材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一,整个导论近6,000字,集中谈了一个问题,即“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对20世纪西方文学的影响。这给人一个深刻印象,好像20世纪西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成就和特点,就只与非理性主义相关。事实上,即使只指涉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仅仅关注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也是远不够全面的。而且,作为20世纪文学导论,作者似乎完全忘了它统帅下的本书第一章“欧美现实主义”和第二章“俄苏文学”,那是绝对不能用非理性主义来解释的。第二,导论似乎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西方“理性”与“非理性”两个哲学概念的内涵及其文学表现,于是得出下面这样匪夷所思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欧美文学,这种追求理性的倾向更为明显。……西方文学中的理性也就在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后进入到新的文化境界。存在主义文学中的‘自由选择’和西西弗斯式的行动原则,表现了人在非理性的荒诞现实面前的高度的理性意识;荒诞派戏剧中对‘戈多’的等待,正是对新的‘上帝’重临的期待,也即对新的理性的期待;……可见,在经过否定之否定后,20世纪欧美文学出现了对‘上帝’与‘理性’的崇敬与追寻的趋向。”“在20世纪文学中,‘理性’拥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如卡夫卡小说中将人变成甲虫,使人无法到达‘城堡’的神秘力量,海勒笔下的不讲理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萨特小说中导致人‘恶心’又难以将其摆脱的现实存在,等等,都是‘理性’力量的表现形态”。第三,导论中莫名其妙的说法有多处,如:“传统文学那种崇高美”;“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把浪漫主义的‘返回自然’推向返回原始的蛮荒时代”;“在艾略特的《荒原》中,……人要找回自己就必须返回远古的神话时代”;“他们真切地体察到了人的非理性内容并视其为人的生命本体,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忧虑的”,等等。这些说法明显经不起追问。一本以教育部名义要求中国高校必须采用的权威教材,一开头就写成这样,实在令人痛心。我们想问:该书已经印了12次了,还准备这样子走完21世纪吗?
标签:文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萨特论文; 后现代风格论文; 外国文学史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