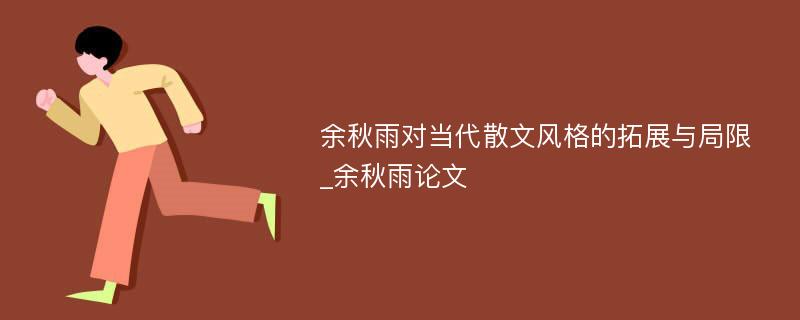
余秋雨对当代散文文体的拓展及其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秋雨论文,文体论文,散文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为代表的余秋雨文化散文,屡屡在华文阅读中掀起一阵阵的阅读狂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五四”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散文作家的创作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与反响。在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余秋雨的散文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哪些贡献?它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特殊贡献表现在哪里?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如此众多的喜爱余秋雨散文的读者群体?乃至,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又有哪些局限与不足?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值得关注与深思的问题。
一
散文,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是与韵文、骈文相对的散行文体。从广义来说,它包含有小说、戏剧、历史、哲学、传记等一切无韵的文体样式;从狭义来说,它是与诗词、歌赋等韵文相对的一种特殊文学体裁。从先秦两汉的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到唐宋韩愈、柳宗元的古文,都属于这一文体范畴。而在这其中,在那个漫长的一直以诗文为正宗的古代社会中,“散文”长期以来被赋予了作训垂范、载道明理的教化作用,成为统治者经天纬地事业中的有用工具。
真正使我国传统的散文观念出现根本性转折的是在“五四”时期。1925年,鲁迅先生翻译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厨氏在书中对Eassy(随笔)的论述,成了当时作家和评论家所信奉的散文创作准则。
然而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他竟然又以闲适散淡的趣意营造着自己的作品,似乎将“散文”摒弃于启蒙主义的功利文学观念之外。《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乃至《阿长与山海经》、《五倡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等等,均写得挥洒自如。
与鲁迅先生散文观念极为类似的是周作人。他于1921年6月8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美文》一文,几乎成为“五四”作家谈论现代散文的艺术标尺。他认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论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为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有很多两者夹杂的……中国古文里的序、记和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由此出发,他将中国美文的传统追溯到晚明小品,从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中寻找现代散文的理论资源。同时,他又眼光向外,认为英式随笔应该成为国人学习与借鉴的榜样。在他的散文创作中,《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谈虎集》等作品,文笔舒徐自如、信笔直书,是自己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主要是在周氏兄弟文学主张的影响下,实现了一次对传统散文观念的根本性裂变与转型。著名散文作家朱自清在1928年所写《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一文中这样认为:“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实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有中国的土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表现上是如此。”这篇文章后来作为附录,收入1936年5月出版的朱自清散文集《背景》中,长期以来几乎一直成为人们评价“五四”时期散文繁盛状况的经典性论断。
不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社会安康、风花雪月的和平年代,而是一个充满着挣扎与战争,徘徊于生与死之间的风沙扑面的动荡时期。在一段时间的新鲜与探索之后,许多作家纷纷寻找战斗的艺术,认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和投枪,是社会感应的神经,是人民苦难的代言人。因而,尽管当1924年语丝社力图倡导“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战斗特色时,并没有能形成文坛步调一致的行动口号。但到1934年4月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创作时,则几乎受到了当时文坛众口一词的批判与嘲讽。林语堂在《人间世》的“发刊词”中说,“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善治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这段“宣言”在内容上与1925年鲁迅翻译与倡导的厨氏的散文观并无二致,然而,它们在散文作家心目中的分量已经截然不同。
启蒙与救亡,是20世纪大半个阶段横亘于中国文学的两大主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义的中国人,都不可能赞同弃启蒙与救亡而不顾,只是一味追求所谓的散文观念新思潮。时代从根本上决定了当时作家的最终选择。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朱光潜、沈从文、何其芳、陆蠡、丽尼、缪崇群、李广田、柯灵、芦焚等一大批散文作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不同文学追求,诸如或固守、或转型、或改行等等,都映现出了在民族命运危亡关头对散文文学观念的矫正与定型。闲适已离人们远去,读者需要的是血与火的艺术。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散文创作中,其主要创作倾向仍然是为政治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并呈愈演愈烈之势。且看其间公认的杨朔、刘白羽、秦牧“散文三大家”,他们的散文观已不复“五四”时的闲适、优雅与有趣了。
“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国当代散文的创作呈现为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一方面,许多作家继续关注现实、讴歌时代,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精神内涵。你看巴金,他在“文革”后写下了五集共150篇的《随想录》,真实地记录下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劫难以及在“文革”后的自省。他在《随想录》的“总序”中说:“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又不高明。但它们都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这里“随时随地”的感想,其实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琐事的随意回忆或者对往事的简单追忆,而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此外,如陈白尘的《云梦断忆》、丁玲的《“牛棚”小品》、杜宣的《狱中生态》、王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等等,都以其深重的政治历史内容与真切感人的艺术方式吸引着读者的注意,成为新时期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收获。同时另一方面,随着长期极左路线所造成伤害的渐渐平复,随着日益宽松的文化气氛的渐渐形成,许多散文作家似乎又重新接续上了“五四”时“美文”的创作传统,以冲淡而平和的笔触写出自己不同的心境。例如汪曾祺在《葡萄月令》、《故乡的食物》、《午门》等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冲淡风格与士大夫情趣,贾平凹在《静虚村记》、《一棵小桃树》、《冬花》、《静》、《落叶》等作品中追求的空灵、浑朴和秀美,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现代散文作家的影响。又如那位以《负暄琐话》、《负暄续话》散文集引起文坛关注的张中行,其散文观念几乎与“五四”美文别无二致。
新时期散文在多元共生中滋生着、繁荣着,并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肯定与充分赞誉。既有着如巴金《随想录》那样充满现实战斗精神的饱满力作,又有着如张中行这般亲切有味、舒徐自在的美文经典,新时期散文似乎到了一个成熟与收获的季节。
而在此时,余秋雨散文的出现,《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狂销,则又将人们带入到了一个柳暗花明的境界。
相对于自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日益强化的为现实服务的现当代散文,余秋雨突出的是传统,强调的是在传统中寻找与现实的共通点;相对于现当代散文中热切的为政治服务的热情,余秋雨探讨的是文化,着意在文化中搜寻影响政治的因素。而同时,有着数千年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读者,则又从根本上决定了那种咀嚼身边小小悲欢的“美文”不可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与强烈反响。他们竭力想摒弃过于急功近利的为政治服务的应景之作,但是他们却愿意透过一段距离,通过一个中介,在“传统”与“文化”中思考祖国的命运与民族的未来。他们不愿意接受扳起面孔的文化教训形式,但是他们却愿意与作者一起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共同探索与沉思祖国的传统与文化的命运,乃至在新形势下的转型与生机。你看他在创作《山居笔记》时的心态:
中国文化从来离不开社会灾难。我借清初和清末的民族主义激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思维灾难,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
正因为灾难,文化更具备了寻找精神归宿的迫切性。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侠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
…………
整整两年,天天精神恍惚,如痴如呆,彻底沉陷在一个个如此重大的话题中。几乎断绝社会交往,连写作过程中的考察也蹑手蹑脚,不事声张。①
余秋雨带给人们一种新的阅读经历,一种新的关注政治与现实的途径。人们愿意,甚至毫不勉强地与作者一起思索祖国、民族、政治、传统和现实等一系列宏大的社会与文化命题。
这,应该是余秋雨对现当代散文创作的一次重大拓展。
二
将传统与文化作为主要叙述点自然是余秋雨散文取得极大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艺术上的精心营造与构思也是不可或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传统与文化出发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使余秋雨的散文显得大气,充满张力,使它不可能流于小小的文人圈子中的阅读;另一方面,余秋雨在艺术上的苦心孤诣与自觉追求,则使他的文化散文散发出魅力,充满着韵味,获得了广大读者喜爱与好评。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其实,艺术形式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制于思想内容,并最终为思想内容服务的。余秋雨在文化散文中的精雕细琢、殚精竭虑,也正应该由此加以理解。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抑文欲其奥,扬文欲其明,疏之欲其通,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作为强烈主张“文者以明道”的散文家,柳宗元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认为文章应该要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从这一创作主张出发,柳宗元认为创作时应该注意情感的合理表达与节制,不能不加掩饰地随意宣泄,因而,使得他的创作呈现出隽永、含蓄和深沉的特点。
这种想法与当代散文家秦牧有相似之处。他在发表于1989年第6期上的《散文漫想录》一文中说道:“如果把散文的散,理解为描述事务向纵深发展,有所发挥,而所谈的东西,尽管纵横捭阖,又是和主题密切关联的,应该承认:‘散文贵散’,有理!如果把‘散’理解为乱跑野马,没有中心,杂乱无章,语无伦次,那么,自然‘散文忌散’”。作为一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重要影响的散文大家,秦牧十分坚信文学的革命功利主义的,因而尽管他试图在《古战场春晓》、《土地》、《社稷坛抒情》、《花城》等篇章中创作出一种闲话趣谈式的氛围,但从总体效果来看,其实是相差甚远——似乎是想营造一种舒徐自如的结构形态,但在深层的意义方面仍处处显示出局促与紧张。
与之相反的,是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散文主张。梁实秋在《谈散文》一文中,表述了他对散文文体的理解:“散文的文调应该是活泼的,而不是堆砌的——应该是像一泓流水那样的活泼流动,要免除堆砌的毛病,相当的自然是必须要保持的。”同时,他又指出:“用字用典要求其美,但是要忌其僻。文字要装潢,而这种装潢要成为有生机的整体之一部。不要成为从外面粉上去的附属品。散文若能保持相当的自然,同时也必能显示作家个人的心情。散文要写的亲切,即是要写的自然”。②在梁实秋的散文观中,“自然”是作品能否成功的生命线,而“自然”与否的判断依据,则在于是否顺应了“个人的心情”。由此出发,梁实秋在他的《雅舍小品》等散文集中,不仅把生活艺术化了,而且也把艺术生活化,从而形成了明净、淡远的艺术风格,成为继周作人之后的闲适派散文大家。
回到余秋雨这里,他自然不是一位闲适派散文作家;同时,他又不是一位直接描写与反映现实与政治的文人斗士。他将着眼点放在传统与文化,并试图通过对传统与文化的剖析与反思来作用于现实与政治。在这里,其实是对余秋雨散文艺术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他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这样表述自己的创作缘由:“……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又说:“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然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并希望自己的散文创作“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同样的思想也表达在他为《山居笔记》写的“台湾版后记”中。他说:“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间居舍里开始这本书的写作的。我显然已经不在乎写出来的东西算不算散文,只想借着《文化苦旅》已经开始的对话方式,把内容引向更巨大、更让人气闷的历史难题”。显而易见的是,余秋雨在创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对“历史难题”的演算与解答,同时并强烈地希望他演算与解答的结论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和共鸣,至于“算不算散文”在他已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在这里,余秋雨找到并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是戏剧化的手法。在散文中演绎剧情,这是余秋雨对当代散文艺术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抱愧山西》是《山居笔记》中的一个名篇。作者开首第一句便设置悬念:“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
为什么会惭愧呢?作者先不说明原因,而是拓开一笔,叙述了对山西的三次误听误信:一是那首凄婉的离开家乡的民歌《走西口》,二是描写穷人革命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三是“文革”中在贫瘠的山顶上人造梯田的大寨大队。因而,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将山西视为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直到有一天,作者在翻阅一堆史料时才发现: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山西竟是中国的首富省份,直到上世纪“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于是作者有了好奇,有了惭愧,进而也有了强烈的进一步探寻的愿望。接着,作者开始了对山西的考察,以及考察时超出预料的震惊,并由此展开了对山西商人和山西文化的探源与考辨。作者推导出的结论是:
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能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
在结论之后,作者回到现实,回到如今改革开放的新型经济政策,最后一句:“今天,连大寨的农民也已开始经商”。张弛有致,前后呼应,一气呵成。
是散文,而又不是惯常的“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作法。与其说是文学创作,倒不如认为是作者驾轻就熟的戏剧编排。
对于历史和文化的介绍与反思,如果抱有了强烈的现实和政治的目的,那么极有可能写成如台湾作家柏杨那样的《丑陋的中国人》,言辞偏激,而辞气浮露;如果抱持了闲适与自由的心情,那么又极有可能写成如现代散文家曹聚仁在《弥正平之死》、《叶名琛》、《并州士人》等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钩沉稽玄、客观描写的历史小品。
余秋雨与上述两者都不一样。他有着较为强烈的现实和政治的文学功利要求,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参与到民族文化的重构和建设中来,希望能有广大的读者阅读并喜欢他的作品。同时,他又保持了一份耐心,保持了和现实与政治一定的距离,只是希望在对传统与文化思考的层面上发表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在这里,戏剧化的文学处理方法是他寻找到的一条有用的途径,也是他的文化散文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
三
在余秋雨文化散文极度畅销的原因中,如果说他得心应手的戏剧化处理方法是“人和”;那么他在“文革”后期所阅读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乃至在戏剧研究过程中对中外传统文化、典籍的广泛涉猎与关注,便是“地利”;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传统文化反思与清理的热潮,则是“天时”。
1985年前后,我国新时期文学在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潮流以后,开始了一股“寻根主义”的文学热潮:例如阿城的《棋王》、李杭育的“葛江川系列”小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贾平凹的《商州纪事》、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红高粱》等等小说。这些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和地域性历史画卷意味,它们寻找民族中带有生命力的根须或病态的根须。不过,它们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重铸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这是我们作家自觉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入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变革中来的可贵追求。同时,也是我们这么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古国在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途中对于作家们的必然要求。尽管余秋雨创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比之要迟了几年,但作者的创作动机却是与“寻根文学”的文化小说一脉相承的。这是余秋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同时也是众多关注中国改革、关注民族命运的广大读者对其作品极其热爱的根本原因。
不过,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尽管传统与文化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并对社会起着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却是有限度的,并且是以极其错综复杂的面貌呈现出来的。因此,如果将传统与文化的作用夸大到极致,认为是社会变革无可更替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也就有可能把握失当,并影响到其对社会和历史的正确判断。这种偏颇,在“寻根小说”家那里有所表露。同样,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中也常常带有这样的缺陷。
例如《山居笔记》中《苏东坡突围》一文。对于身世坎坷、命运多舛的大诗人苏东坡,作者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斥他,糟践他,毁坏他。”在他看来,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在湖州,当苏东坡被差役押解着时,作者认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在作者充满感情的叙述中,读者对苏东坡的遭遇极其同情。不过,问题还在于:真的存在一个小人与大师两相对立的社会格局吗?或者说,文化名人越优秀就真的越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吗?答案其实应该是否定的。且不说苏轼与王安石在对待那场如何变革社会现状的政治风波中谁对谁错,就是所谓“小人”真的会对大师群起而攻之吗?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就是由英雄主义造成的了,而我们现代所倡导的民主政体也就失去了其公正性和合理性。显然,余秋雨在这里过于夸大了“次师”的作用,也过于夸大了所谓“独特国情”对大师与名人的摧残与毁坏。
这种突出一点、不及其余的偏颇,在《十万进士》、《遥远的绝响》、《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作品中也都有所显现;尤其是在《霜冷长河》集中讨论有关名誉、谣言、嫉妒、善良、年龄等等有关具体文化的作品,更为明显。我们觉得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在带给读者许多有益启发的同时,有些篇章也显得不够辩证与全面。在艺术上,他的戏剧化叙述方法也带有一定的缺陷。
因此,他的这种写作技巧与表现手法能够抓住读者的心弦,能够使许多读者读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不过,当这种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运用时,读者也会失去新鲜感,失去亲切感。而且,有时为了叙述与表达的需要,也可能会删减掉许多真实、可信的材料,从而使表述的内容变得干枯与单调。自然,最重要的是,当一些本身并不具备传奇性与戏剧性的材料硬是按照戏剧化的叙述方法处理时,可能就会有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之感。这种缺陷在《借我一生》中的《旧屋与旗袍》、《文化苦旅》中的《风雨天一阁》、《行者无疆》中的《古本江先生》等篇章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不过,从总体来看,上述缺陷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并非明显到足以掩盖其艺术光芒的程度。他在叙述内容与叙述手法上的开拓之功,他对于推动我国当代散文文体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应该值得我们好好总结,认真汲取。
注释:
①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395页。
②梁实秋:《现代作家谈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标签:余秋雨论文; 散文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苦旅论文; 艺术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读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随想录论文; 山居笔记论文; 梁实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