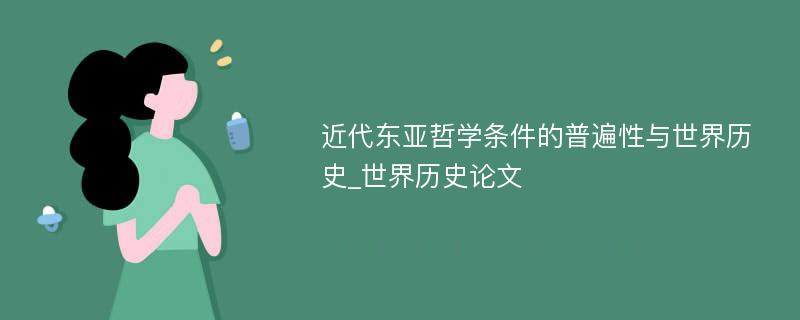
近代東亞哲學話語中被附加了條件的普遍性與世界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普遍性论文,近代论文,東亞哲學話語中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倡“概念史”的瑞哈德·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過去的未來——通向歷史時間的意義論》(1979年)中講到,西塞羅的名言“歷史是人生的導師”(Historia magistra vitae)代表了將“歷史”視為行為之鑑的觀念,而這種歷史認識在18世紀發生了巨大變化,衍生出新的“歷史”觀念。其根源在於像法國革命、美國革命那樣迥異於過去的歷史事件的出現使得聯繫著過去與未來的連續性紐帶的崩潰。這種趨勢的最直接體現即是德語中有關歷史的表達方式的變化: 德語中作為外來語的Historie,其基本意義原指“就發生的事件進行報告或說明”,而另一種較特殊的意義則趨近於“歷史學”。該詞在18世紀的歷史進程中急速地被Geschichte一詞代替。1750年左右,出現了Historie向Geschichte的轉換,這一過程可以通過對文本進行統計學的計算加以驗證。然而,Geschichte主要意味著某事件,即“自身參與的事件、來自外部的事件、行為的結果”。這個詞表達的與其說是“說明事件”,更偏重於“參照事件”之意。① 近代發生的是個別事件,而德語的die Geschichte就是表達這種個別事件的複數形式(50/34)。但是,複數形式的die Geschichte被壓縮成“集合的單數形式”了(51/34)。科塞雷克提及康德的《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的理念》(1784年),同時就此變化作如下說明: 由作為個別事件的歷史(Singulargeschichten)的總和構成的普遍史(Universalhistorie)演變成“世界史(Weltgeschichte)”之時,康德在尋找將散亂的行為的“拼湊”置換成理性的“體系”的手段。顯然,正是集合的單數形的歷史(Geschichte)使這種思考成為可能,這與它是世界史,或個人史無關。(53/34-35) 追求“複數的各別事件的總和”,換言之即是擺脫無序狀態的“拼湊”而最終形成富有理性意味的“集合的單數形”之歷史才是康德的目標。而這個超越了“個體史”的“世界史”究竟是怎樣的呢?康德如是說: 我們從希臘史開始追尋歷史——希臘以前的其他歷史及同時代的歷史並不消失,至少必須確認——吞併希臘國家的羅馬民族的國家組織體的形成及其失敗都受到了來自希臘的影響,而且進一步追尋羅馬民族給予摧毁羅馬國家組織的野蠻人的影響直至現在。在此過程中,如果我們將其他民族國家的歷史像插曲一樣添加進來,如同其後受到希臘和羅馬民族啟蒙的民族所逐漸認識一樣,那麼,我們或許會發現該大陸(有朝一日或許該大陸會將規則帶給所有的大陸)國家體制有規則地得到改善的過程。 康德所說的“世界史”,指向了“人類完全之公民聯合”②這一理性目的。惟其如此,它不是“拼湊”,而必須是理性的“體系”。科塞雷克認為“當作為集合的單數形的歷史確立時(1760年至1770年間),歷史哲學這一概念也就登場了。”③康德式的“世界史”其理性與啟蒙哲學表裡一體。 但是,這種康德式的“世界史”,是否便是羽田正所批判的“歐洲中心史觀”呢?因為它把不過是“插曲”的其他民族國家的歷史不斷地組合進來,希冀有朝一日歐洲大陸將給予所有大陸以法則。而羽田正對“歐洲中心史觀”的批判正是如此: 歐洲中心史觀的立場是,將歐洲置於中心(前者),認為是歐洲領導了世界史(後者)。 在世界史的理解與敘述中,尤其被當做問题的是後者。因為若站在這一立場,那麼創造世界史基本骨架的就只是地球上的一部分人而已,也就必然要接受中心與邊緣這種二分法的世界觀了。④ 在羽田看來,“領導世界史”的“歐洲中心史觀”在近年的全球史中仍有濃重的殘餘。⑤那麼,脫離了“歐洲中心史觀”的所謂“新世界史”是什麼呢?其哲學基礎是什麼呢? 首先,它不追求目的論。“我不認為,根據某種理論對世界的過去進行統一地整理和揭示,作為其結果,能實現大家都認可的唯一的世界史敍述。”⑥以此表述,規避了科塞雷克眼中的基於某種理念將複數的事件捆綁在一起的“集合的單數形”的“世界史”。這也許可以稱之為複數形的Geschichte的復活吧。 因此,為了將複數的事件作為整體來看,就要將其看作是水平的相互聯繫的系列,而非垂直的形而上的敍述。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將其表述為:歷史是如同沒有中心的塊莖(rhizome)般的多重複合體,將時間軸水平切片,則會獲得獨立的內在性平面。而羽田正將之歸納為“描繪世界映射”、“不拘於時間系列史”、“意識橫向聯繫的歷史”。⑦ 這讓我想起武田泰淳的嘗試。泰淳在其《司馬遷——史記的世界》(1943年)中認為司馬遷的《史記》描繪了“世界並立現象的卓異”: 並非只有《本紀》充實了史記世界,這一事實只要讀讀《本紀》就能很好地理解,而隨著進入《世家》,就會感同身受地瞭解世界並立現象的卓異。此處存在著與“本紀”統一現象的卓異度全然不同的又一個卓異: 既然世界中心並非一個,而且不是靜止的,那麼在這個世界上並立狀態就不可避免。願意向單一事物歸一,同時又希望不斷向四面擴散,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痼習。擴散就會多中心並立,每個中心的內容就會變得不確定,甚至連形體也扭曲易於崩潰。因此,《世家》將《世家》們組合編織起來,相互地在其他《世家》內部出入、增減、升降,而不知其所止。⑧ 世界的中心並非唯一,《世家》中這些被邊緣化的人們(世家只存在於《史記》的範疇,為後來的正史所排除)也構成又一個並立。司馬遷之所以“立三十世家”來敍述,正可證明他認為這個世界是“並立現象”或者複數性是不可缺的。而且,泰淳認為這些世家的並立,讓人“聯想到E.A.鮑維的‘發現Eureka’”。⑨ 對於泰淳的這種“新世界史”理解,即描寫世界之並立即為歷史的觀點,竹內好是這樣評論的: 歷史有時看似停滯,循環的軌跡看似不動,但是內部或許蓄積著不測的爆發力。若著眼於此,不僅是持續,革命也或許被添加更多的分量。假設司馬遷書寫的同時,設想著背後存在與持續世界相對抗的默示錄世界,那麼,我推測其作品或許會完成得更加厚重,應該不會不妥。當然,這是得隴望蜀。以其書寫的時期來說,為了對抗流行的流動史觀,或者萬世一系的史觀,已經是竭盡全力了吧。⑩ 在竹內好看來,描繪“持續的世界”的泰淳的“新世界史”所抗拒的乃是“流動史觀”、“萬世一系史觀”。後者肯定現狀,按照時間系列講述過去,並在其中發現類似法則的“循環軌跡”,以此而論則終落“歐洲中心論”的窠臼。泰淳的“新世界史”則關注“內部”的“不測的爆發力”,強調歷史中尚存別一種可能性。不過,它還沒有達到竹內好所希望的“革命”或者“默示錄世界”。然而,正因為沒有導入“革命”或“默示錄世界”,才可以說泰淳的“新世界史”徹底地擺脫了目的論。 在設想“新世界史”時,最迫切的問題之一便是其與普遍性的關係。前文說過,康德自詡為普遍的“世界史”即“世界市民觀點下的普遍史”是“集合單數形”的Geschichte。但是,“新世界史”要回歸複數形的Geschichte,應該排除目的論。若如此,“新世界史”豈非是相對主義的,要放棄普遍性的嗎?然而,羽田所說的“新世界史”也被定義為“為了地球公民的構想”,這與康德的用語幾乎相同。羽田如是說: 新世界不需要“決定版”,如果歷史敘述使人們能持有一種地球公民意識,即理解世界是一個,自己屬於這個世界,那麼這些都是新世界史。(11) 即,“新世界史”容許複數的敍述,同時也主張“世界是一個”,以此來擺脫相對主義的歷史敍述。換言之,“新世界史”是對某種普遍性開放的。問题是,它是一種被附加了條件的普遍性,還是無條件的普遍性? 這裡稱之為“被附加了條件”的情況,是指普遍性與某種特殊性維繫在一起。在康德那裡,其特殊性就是歐洲。在東亞哲學中也一樣,普遍性是與日本或中國這樣的特殊性捆綁在一起的。 武田泰淳撰寫《司馬遷——史記的世界》的時期,正是世界史哲學喧嚣一時的時期,處於其中心的高山岩男也在《世界史的哲學》(1942年)中提倡“新世界史”: 新的世界史的理念需要從歷史世界的多元性出發,將歷史世界看成一元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將自己的特殊世界直接等同於普遍世界的不自覺乃至獨斷。歐洲的世界史觀念中大多充溢著這樣的主觀見解。(12)高山指出“歐洲中心史觀”存在的問題是認為“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史即為世界史”的觀念。(13)為了超越這種觀點,“新世界史”必須在承認“歷史世界的多元性”的基礎上,到達“絕對的普遍性”。(14)高山特別警惕的是把特定的條件看作普遍的“不自覺乃至獨斷”,那將陷入“歐洲的世界史觀念”中。相反,他主張應該通過多元論與一元論的結合,自覺地整理特殊與普遍的關係。 如同不以某種形式設想一元論的多元論,在邏輯上是沒有存在餘地的。但是,以世界的多元論自覺為媒介之一元論,已如過去的不自覺的世界一元論,不再是將自己的特殊歷史世界的原理當作普遍原理似地一仍其舊地、連續地延長擴大的一元論。(15) 高山尋求於“新世界史”的是:不陷入相對主義的、而且不使特定的特殊性擁有普遍性的、“自覺”的歷史敍述。僅在這一點上,高山與泰淳還有羽田的主張似無懸隔。 但是,問题在於高山將日本特權地導入這種“自覺”中: 我們必須從歷史世界的多元性出發,走向考察其世界史關聯的立場。但是這種情況下,如前所述,重視各歷史世界尚存的基於各自地域與民族差異的完成與未完成,必須深刻認識世界史在其交錯關聯中的發展與建設。認為各民族文化的趨同,是因為認為各民族有同等的集體能力,它將等質發展,最終必將回歸不自覺的世界一元論。(16) 高山的多元論,悄悄地導入了“歷史中的完成”(17)這一目的論,以此將“各歷史世界”作為“完成與未完成”的差異來定位。而且其結論歸結為強調建設各民族國家各得其所的“世界新秩序”中日本的道義職責。 因歷史傳統與地域特殊性而聯繫在一起的各民族國家,應以各得其所為建設新世界秩序的道義上的原理,我國正向國內外宣傳這一點。(18) 對於高山而言,日本“是在現代世界史的轉換中扮演著主導性作用的最大的國家”。從而,“現代世界史的成立,無法脫離我日本的行動。事實上,現代世界史脫離我日本的國史是不存在的。”(19)果若如此,這不正是高山自己所批判的、將特定的特殊看作普遍的陷阱嗎? 這必將招致對高山的“絕對普遍性”的質疑,高山如是說: 普遍世界的世界史,畢竟無法脫離一種特殊性。那麼,將現代的普遍世界也作為一個特殊,使歷史世界一般成為相對的、特殊的絕對普遍性是什麼呢?……所謂超越歷史世界性的絕對普遍性,不應賦予限定性的命名,它是絕對無。(20) 作為“絕對普遍性”的“絕對無”構成京都學派的否定神學或否定政治學的核心。(21)問題是,“絕對無”被認為是作為特定的世界觀,即在“差別作為差別而存在,並貫穿全體構架協調的組織秩序”和“相即相入的世界秩序中新的普遍姿態”(22)中顯現。其結局是,無論其做否定神學的表述,抑或是否定政治學的表述,都不過是被附加了條件的普遍性。因此,高山的“新世界史”就成為一邊批判帝國主義,一邊擁護帝國主義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形態。(23)這是因為,日本在批判帝國主義的歐洲的同時,重新定義了特殊與普遍,“自覺”地起到了將二者重新綁定的作用,從而虛構出能使各民族各國家各得其所的“相即相入的世界秩序”。 果若如此,我們構想的未來的“新世界史”與普遍性的關係就產生了兩種可能。其一是面向無條件的普遍性敞開,另一個則是重新考量被附加了條件的普遍性。 無論何種情況,大前提是,因其方法不是“得所”這種差異,多元性受到尊重,不主張特定的特殊歷史世界(歐洲、日本、中國等)擁有通往普遍性的特權。與此同時,不能墮入相對主義,必須意識到“世界是一個”。 筆者認為,近年依據中國哲學中“天下”的概念,將“天下”作為中國式的普遍性予以重新肯定的動向隨處可見。(24)他們將“普遍”與“特殊”適度地融合,不放棄對普遍性的要求,但是同時恢復文化的主體性。若真如此,如何使其成為可能,則是必須謹慎而深入探討的。近代以來,看似被塞進一種特殊之中的中國文化,如果能在接受了近代的基礎上再次擔負起普世性的職責,其意義將是無比深遠的。這種對天下概念的重新思考,與高山所說意義上的“新世界史”的關係,是極其重要的問題。它是否得以重新定義被附加了條件的普遍性條件,抑或陷入了異曲同工的結構中。對此一問題的回答,或有待今後討論的進展。 我們必須在充分把握近代光與影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普遍性。通過重新思考,如果確能構建出不依存於條件限制的普遍性,那麼即將到來的“新世界史”就會牢牢地立足於斯。 註釋: ①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9,pp.47-48; 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32. ②康德:《世界公民觀點下的普遍歷史的理念》,《康德全集》,第14卷,福田喜一郎譯,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第19~20頁。 ③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9,p.56; 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p.36. ④⑤⑥⑦(11)羽田正:《通往新世界史——為了地球公民的構想》,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第103、101~102、161、166~167、150頁。 ⑧⑨武田泰淳:《司馬遷——史記的世界》,東京:講談社,1972年,第99~100、104頁。 ⑩竹內好:《〈武田泰淳全集〉第九卷解說》,《竹內好全集》,第12卷,東京:築摩書房,1981年,第161頁。 (12)(13)(14)(15)(16)(17)(18)(19)(20)高山岩男:《世界史的哲學》,东京:こぶし书房,2001年,第89、87、447、35、94~95、94、387、389、 447~448頁。 (21)西谷啟治亦將“絕對無”適用於自己的“世界史的哲學”。請參看西谷啟治:《世界史的哲學》,上田閑照監修:《世界史的理論》,京都:燈影舍,2000年(尤其是第57頁)。關於京都學派的否定政治學,請參看拙著:《否定政治學與公生哲學》,中島隆博、小林康夫編:《為了公生哲學》,東京:UTCP,2009年。 (22)參見中島隆博、小林康夫編:《為了公生哲學》,第456頁。 (23)對此種理論的批評,參看高橋哲哉:《記憶的倫理學——戰爭·哲學·奥斯維辛》,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米谷匡史:《殖民地·帝國的〈世界史的哲學〉》,《日本思想史學》,第37號,仙台:日本思想史學會,2005年;米谷匡史:《〈世界史的哲學〉的結局》,《現代思想》,第23卷第1號,東京:青土社,1995年。 (24)參看趙汀陽:《天下體系的一個簡要表述》,北京:《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10期;許紀霖:《天下主義/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變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