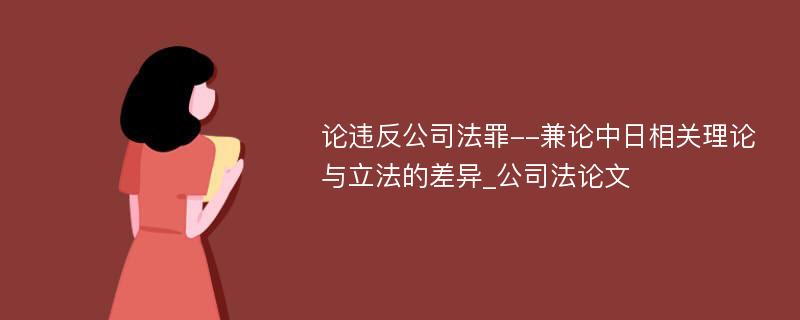
论违反公司法犯罪——兼论中日有关理论及立法之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公司法论文,中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违反公司法犯罪,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公司形态高度发达、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的基础上,而发生的一类新型犯罪。在我国,违反公司法犯罪尚属初露端睨;而在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例如日本,违反公司法犯罪早已出现,并成为人们密切关注与深入研究、司法机关严密注视并严格取缔的一类犯罪。本文拟就我国违反公司法犯罪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对我国与日本有关理论及立法之异同,做简要的比较分析,以求对此问题有较深入的理解。
一、违反公司法犯罪的概念
在我国《刑法》上,并无违反公司法犯罪的专门规定。在我国的《公司法》颁布实施之后,与《公司法》中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相应,作为对刑法的补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可以说,正是这一决定,首次提出了违反公司法犯罪的概念,并引发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研究。
违反公司法犯罪是指违反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危害公司业务正常运行,损害公司及其他人的利益,使社会经济秩序遭受严重损害,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概念表明,违反公司法犯罪的成立,至少应具备五个条件,即:违反公司法规定、妨害公司业务、损害公司及其他人利益、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
在讨论违反公司法犯罪的概念时,有必要将其与其他一些概念的区别进行比较分析,以使其得到确切的界定。
违反公司法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就违反公司法犯罪而言,首先应该确认其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同时也需要确认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其应受刑罚处罚,否则就不能成立违反公司法的犯罪;而一般刑事犯罪则属于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对于违反公司法而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及其刑罚,日本规定在《商法》的公司编罚则部分中,因而,日本有的学者将前者称为“商法上犯罪”,而将后者称为“刑法上犯罪”[1]。我国在公司法上虽然并未直接对违反公司法的行为,规定具体的刑罚,但已经规定了若干行为可以构成犯罪,并以《决定》作为刑罚适用的依据,因而,也可以认为,违反公司法犯罪为商法上犯罪,而一般刑事犯罪为刑法上犯罪。
违反公司法犯罪与公司犯罪。目前我国并无通行的公司犯罪的概念,国内有人在研究国外有关公司的法律责任规定时,提出在国外立法中,对于利用公司进行犯罪或者利用公司制度进行违法犯罪的,作为公司犯罪而追究刑事责任[2]。从前述的对于公司犯罪的一般表述来看,国外的公司犯罪,与我国法律规定的违反公司法犯罪基本上是一致的。日本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公司犯罪,是指与公司相关联而发生的、应处以刑罚的行为”[3];也有的学者认为,公司犯罪“是围绕着股份有限公司所发生的各种犯罪的总称”,并认为公司犯罪通常应包括四类,第一类是“相当于商法第二编第七章规定的‘商法罚则’所涉及的事件”,第二类是“以公司为嫌疑人或者以公司为犯罪舞台(手段)的事件”,第三类是“以公司干部职员为嫌疑人的事件”,第四类是“有关帐簿记载、交易内容等与公司相关联的事件”[4]。在通常情况下,一般将日本商法有关公司的罚则规定所涉及的犯罪,称为公司犯罪(“会社犯罪”)[5]。由此可以认为,我国的违反公司法犯罪与日本的公司法犯罪,大体上为同一概念,不能仅凭字面理解,认为公司犯罪是以公司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因而与违反公司法犯罪有所不同。至于我国是否应该采用公司犯罪这一表述,来概括违反公司法犯罪,则另当别论。
违反公司法犯罪与法人犯罪、企业犯罪。对于法人犯罪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颇多,对法人犯罪概念的界定也渐趋一致。有人提出,“所谓法人犯罪,是指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出于自己的意识和意志,为了其整体利益,通过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行为”[6]。这一法人犯罪概念的界定,虽然把非法人团体犯罪也包含在法人犯罪之中,但其实质已经表明所谓法人犯罪,归根结底是以法人为犯罪主体的犯罪。由此可以看出,违反公司法犯罪与法人犯罪的联结点,仅在于犯罪主体。也就是说,在法人犯罪中,可能有属于违反公司法的犯罪;而在违反公司法犯罪中,也可能有以法人为主体而进行的犯罪。企业犯罪则是日本法学界对于以企业组织为犯罪主体的一类特别犯罪的概括,也称为“组织体犯罪”,其特征表现在该犯罪“是由企业等合法组织体所进行的”这一点上[7]。因而,可以说,日本的企业犯罪,与我国目前学者所主张的法人犯罪,大体上相同,因而,在与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关系上,也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
二、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应受惩罚性
就一般认识而言,公司法属于商法的组成部分,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认为,民法及商法均属于“私法”范畴,而解决犯罪及刑罚问题的刑法,则属于“公法”范畴,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因而,违反公司法的行为,是否即为犯罪行为,仍有相当的疑问。在日本,人们对于违反公司法的犯罪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那之前,虽然客观存在着违反公司法犯罪,但真正作为违反公司法犯罪而受到刑罚处罚的,几乎一件也没有[8]。其中的关键在于,对于违反公司法的行为,是否具有犯罪行为所应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并应受到刑罚惩罚,在认识上有相当的偏颇。
违反公司法犯罪,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后出现的新的犯罪种类。同传统的犯罪种类,例如故意杀人、盗窃、诈骗等犯罪相比,违反公司法犯罪有着相当的区别。按照通常的社会理念,传统的犯罪行为显然有着严重危害社会的性质,因而,足以构成犯罪并应受到刑罚处罚。但违反公司法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并不那么直接,因而也就不易于为人们所认识。特别是当某些违反公司法的行为,其后果并未明显表现出来的时候,与传统的犯罪行为相比较时,社会危害性就更不易认识。例如,对于诈骗犯罪,包括假借设立公司而集资的名义进行的诈骗、以签订假合同的方式进行的诈骗,认定其为犯罪行为并无异议,但对于在设立公司时进行虚假出资的行为,认定其为犯罪行为,则有相当的障碍,因为虚假出资并未使他人在财产上受到直接侵害,因而也就不具有诈骗犯罪那样的社会危害性。有鉴于此,日本学者提出,违反公司法犯罪是“现代社会型犯罪”,因而,在认识该种犯罪及其社会危害性时,就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样一个大前提。[9]
实际上,违反公司法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与公司这一现代经济组织形态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分不开的。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公司自身的地位来说,它处于出资人和社会大众之间,因而,公司的全部活动,包括其设立、组织、运营,无不与出资人和社会大众密切相关。但是,基于公司在组织运营上的特别需要而确立的相应制度,又决定了作为股东的出资人与公司经营发生一定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经营者或者其他相关人,就可能利用公司制度上的特点,为不法行为,从而危害公司,使出资人、公司交易上的相对方以及一般社会大众受到损害,并进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障碍。前一段时期,我国在试行公司制度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波及面极大的若干公司案件,即为明显的例证。可以说,违反公司法的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在一段时间可能表现为潜在的,但是,一旦发生危害,其危害后果则是巨大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为避免该种危害的发生,在立法上,一般均将有关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规则,作为强行法规规定在公司法上,同时设立相应的罚则,在对违反公司法行为规定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同时,也将若干违反公司法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给予刑事制裁。
三、违反公司法犯罪的立法体例
由于违反公司法犯罪是一类特殊的犯罪,在已有的刑法规定中不能完全包括或者并无相应规定,因而,需要以特别法加以规定,通常在公司法或者商法的公司规则部分,列入有关违反公司法犯罪的规定。我国有关立法和日本有关立法,总体上说来,均采用此种立法体例。但我国有关违反公司法犯罪的立法,与日本有关违反公司法犯罪的立法,在具体的立法体例上,有两点主要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规范结构上的不同。从我国有关违反公司法犯罪的立法来看,在规范上表现为犯罪行为的规定与具体刑罚的规定分离,前者规定在《公司法》的法律责任部分,而后者则单独规定在《决定》中。在《公司法》中,规定对若干违反公司法的行为,在其构成犯罪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未明确规定具体的刑罚;而在《决定》中,则对该犯罪行为规定了具体的刑罚。这种立法体例,是我国在立法上所遵循的一个原则。日本在立法上则遵循与此不同的原则,即在刑法以外的实体法中,既规定某种犯罪行为,同时也直接规定相应的刑罚标准。在日本《商法》的公司编中,专门规定罚则一章,规定了违反公司法的犯罪行为,同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与日本立法相比,我国所采用的上述立法体例,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对犯罪行为的刑事处罚规定在一起,且与刑罚的规定分离,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有关违反公司法犯罪处罚规定的预防性效力。在我国《公司法》的法律责任规定中,有二十一条条文规定,对违反公司法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而其中有十七条在末尾附加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而日本《商法》的公司罚则规定,首先用十三条条文直接规定了违反公司法的犯罪行为及其刑罚标准,然后用一条条文专门规定应处以罚款的二十九种违法行为。应该说,日本的这种立法体例,是明晰而确切的。第二,由于对违反公司法犯罪行为的规定和具体刑罚标准的规定分离,一方面造成罪状表述上的差异,同时也发生内容上的不对应乃至遗漏,造成适用上的困难。在我国的《公司法》中规定的、可以构成违反公司法犯罪的行为有十七项之多,但在《决定》中仅概括为十一项。其结果是,在《公司法》中分别表述的罪状,有相当一部分被合并为一项,例如,《公司法》第208条规定的是虚假出资犯罪,第209条规定的是抽逃出资犯罪,而在《决定》中则合并为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一项。也有个别已在《公司法》中规定的罪状,未在《决定》中规定相应的刑罚,例如,《公司法》第211条规定的另立会计帐册的犯罪、将公司资产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的犯罪,第213条规定的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配的犯罪,第218条规定的清算组成员徇私舞弊、谋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犯罪,均未在《决定》上规定相应的刑罚,亦未表明可以适用刑法的相关规定。
其次是规范体系上的不同。我国《公司法》首先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在其后规定了违反公司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这就表明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特别是刑事责任的规定,同时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在《决定》中亦未区分两种公司形式,而规定了统一的刑罚标准。在日本立法中,在《商法》的公司编中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其后规定了公司罚则;而在单独制定的《有限公司法》中,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其后也规定了公司罚则。将两种公司形式分别规定在两个法律中,固然是日本特有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立法处理上的特别考虑使然,而非理论上的或者某种逻辑上的原因;但是,由于两种公司形式在客观上存在着制度方面的以及社会影响及社会作用上的差异,在日本的两个法律中分别规定的公司罚则,在内容上也有所不同。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的社会影响,明显小于股份有限公司,因而,在违反公司法犯罪的法律责任上,也有显著的减轻。例如,同属于危害公司财产罪,股份有限公司适用的罚则规定处五年以下惩役或者200万日元以下罚金;而有限责任公司适用的罚则规定处三年以下惩役或者100万日元以下罚金。对于其他同类犯罪的刑罚,也均有轻重的区别。对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种不同形式的公司,分别制定不同的罚则规定,应该说不无道理。
四、违反公司法犯罪的罪名
根据罪状确定罪名,是罪名确定的一般原则。对于违反公司法犯罪,其罪名的确定也应遵循这一原则。违反公司法犯罪是一类特别的犯罪,其中包括具体罪状不同的若干个犯罪,因而,其罪名并非单一的一个罪名。这在日本有关立法上是如此,在我国有关立法上也应该是如此。
日本对于违反公司法犯罪的罪名,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罪名体系,在日本《商法》公司编的罚则中,对于违反公司法犯罪,设立了九个不同的罪名,这就是:特别背任罪、危害公司财产罪、虚假文书使用罪、伪装缴纳股款罪、股份超额发行罪、渎职罪、对胁迫公司者行贿受贿罪、逃脱股款缴纳责任罪、与股东权利行使相关的财产利益提供罪。对此,需要特别说明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特别背任罪。特别背任罪是相对于日本《刑法》中的背任罪(即一般背任罪),作为违反公司法的特别犯罪而设定的罪名。日本《刑法》第247条规定,为他人处理其事务者,以谋取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或者以加害于本人为目的,为违背其任务的行为,对本人财产造成损害,即构成背任罪,得处五年以下惩役或者二十万日元以下罚金。相对于刑法规定的一般背任罪,在公司罚则上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董事、监查人、职务代行人、经理人、就有关营业事项接受委托的使用人,以谋取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或者以加害于公司为目的,违背其任务,对公司财产造成损害,即构成特别背任罪,得处七年以下惩役或者三百万日元以下罚金。可以看出,特别背任罪的刑罚要较一般背任罪的刑罚为重。
第二,危害公司财产罪。实际上,危害公司财产罪仍然是一个类罪名,其中包括着四个具体的罪名,即:虚假股份(日本称为“幽灵股”)发行罪、违法取得自有股份罪、违法分配罪、营业范围外投机处分公司财产罪。
第三,渎职罪、对胁迫公司者[10]行贿受贿罪、与股东权利行使相关的财产利益提供罪。这三个罪具有大体上相似的性质,即属于行贿和受贿犯罪。渎职罪是对公司发起人、董事、监查人等具有特定身份地位者行贿及其受贿罪,而对胁迫公司者行贿受贿罪、与股东权利行使相关的财产利益提供罪,则是对某些股东、公司债权人行贿及其受贿罪。后二种罪的区别,主要在于用于行贿或受贿的财产利益的来源不同,与股东权利行使相关的财产利益提供罪,其所涉及的财产利益来源于公司。
在日本违反公司法犯罪中的其他几种罪,则比较易于理解。虚假文书使用罪,主要涉及股份公司债募集时,使用就有关重要事项有虚假记载的股份认购证、公司债认购证、招股说明书、有关募集的广告或其他文书的犯罪。伪装股份缴款罪,是在公司设立或者新股发行时,发起人或者董事未将股款缴存收款银行,但伪装已缴存收款银行的犯罪。股份超额发行罪,是公司发起人、董事等,超过公司得发行股份总额(授权资本总额)而发行股份的犯罪。逃脱股款缴纳责任犯罪,则是以逃脱股款缴纳责任为目的,使用他人的名义或者虚构人的名义认购股份的犯罪。
从我国《公司法》和《决定》的规定来看,在我国的违反公司法犯罪的罪名体系中,已经包括了以下七种罪,即:虚假登记罪、危害公司财产罪、虚假文书制作使用罪、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公司有关人员受贿罪、侵害公司财物罪、违法批准登记罪。其中的危害公司财产罪、侵占公司财物罪和虚假文书制作使用罪,各自又包括若干具体的罪。在危害公司财产罪中,包括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在侵害公司财物罪中,包括侵占公司财产罪、挪用公司资金罪、隐匿私分公司财产罪。在虚假文书制作使用罪中,包括虚假文书制作罪和虚假文书使用罪。在这里所说的危害公司财产罪和侵害公司财物罪,是两种不同的罪,二者虽然同属于对公司财产的侵害,但其侵害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的侵害是以特殊的行为方式(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进行的,因而带有一定的间接性,故称之为危害公司财产;后者的侵害则是以通常的行为方式(侵占、挪用、隐匿、私分)进行的,因而是一种直接的侵害,故称之为侵害公司财物。
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中的违反公司法犯罪的罪名体系,与日本的罪名体系相比,存在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国法律中和日本法律中均有规定的罪名,主要为:危害公司财产罪,但日本规定的具体罪名,多于我国的规定;虚假文书使用罪,但我国规定的具体罪名,多于日本的规定;行贿受贿罪,但日本规定了三种不同主体、不同性质的罪,我国则只规定了公司有关人员的犯罪,且未同时规定行贿罪;此外,从具体罪状来看,我国法律中规定的侵害公司财物罪,实际上大体相当于日本法律中规定的特别背任罪。第二种情况,我国法律中有规定而日本法律中无规定的罪名,主要为:虚假登记罪、擅自发行罪、违法批准登记罪。其中的擅自发行罪,与日本的股份超额发行罪具有同一性质,但具体的罪状成立上有所不同,而违法批准登记罪,其主体为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这在日本的规定中是完全没有的。这些特有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前在实行公司制度过程中的特别需要。第三种情况,我国法律中无规定而日本法律中有规定的罪名,主要为:伪装缴纳股款罪、股份超额发行罪、逃脱股款缴纳责任罪,其中的伪装缴纳股款罪,与我国法律中规定的虚假出资罪大体上相似,但就具体罪状来看,日本法律规定所强调的,主要是在向承办收款银行缴款过程中,所发生的伪装缴款行为。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现有的违反公司法犯罪的罪名体系,大体上是完备的,日本一般认为属于公司犯罪中的“四大罪”—特别背任罪、危害公司财产罪、受贿罪、虚假文书使用罪[11],在我国的罪名体系中,已经基本包括。但就某些具体的罪名来说,我国在立法中尚需进行必要的补充,例如与公司相关的行贿罪、违法分配罪,以使我国违反公司法犯罪的罪名体系更趋成熟和完备,从而切实保障我国《公司法》的顺利实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注释:
[1]参见〔日〕麻生利胜著:《企业犯罪》,株式会社泉文堂1980年版,第110页。
[2]参见徐杰、徐晓松著:《中国公司法与公司实务》,中国致公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289页。
[3]〔日〕西原春夫著:《犯罪各论》,筑摩书房1979年版,第285页。
[4]转引自〔日〕麻生利胜著:《企业犯罪》,株式会社泉文堂1980年版,第110页。
[5]参见〔日〕藤木英雄等编:《法律学小辞典》,有斐阁1979年版,第68页。
[6]李希慧:《关于法人犯罪的几个问题》,《法学评论》1996年第1期,第13页。
[7]参见〔日〕前野育三著:《刑事政策论》,法律文化社1994年版,第300页。
[8]〔日〕佐贺潜著:《商法入门》,光文社1975年版,第198页。
[9]〔日〕板仓宏著:《企业犯罪的理论与现实》,有斐图1975年版,第169页。
[10]胁迫公司者在日本称为“会社荒”,系指滥用其权利,意图从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股东、公司债债权人或者一般债权人。参见〔日〕八木宏编著:《商法小辞典》,中央经济社1979年版,第36页。
[11]参见〔日〕佐贺潜著:《商法入门》,光文社1975年版,第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