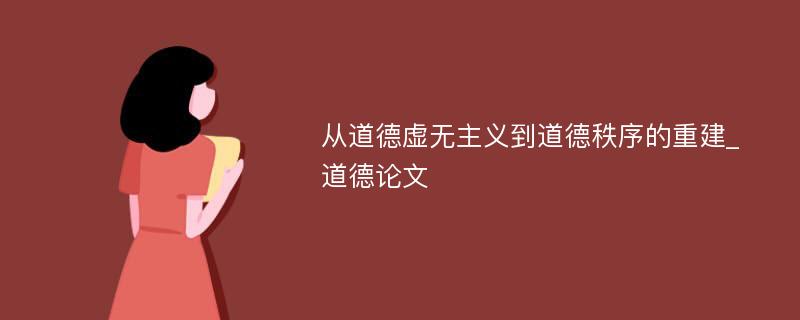
从道德虚无主义走向道德秩序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虚无主义论文,秩序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道德虚无主义与道德重建主义
纵观人类思想史,尽管古今中外各派伦理思想众说纷纭,然而根据其面对社会危机或历史转折所采取的态度可以将历史上的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类人从当时社会上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事实中,推论出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或只能是背信弃义、以强凌弱、相互敌视的冲突,而不可能或不应该建立人人平等的道德秩序,从而得出道德无用或取消道德的结论,这就是道德虚无主义。另一类人则由对道德沦丧的现实痛心疾首而走向重建道德理想和道德秩序,这种主张可以称作道德理想主义或道德重建主义。属于前者的如韩非、马基雅维里、尼采、萨特,以及各色各样的非道德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属于后者的如孔子、墨子、乔答摩、耶稣、卢梭、康德、马克思、孙中山等。
在道德虚无主义者中,韩非从人人都有“自为心”的性恶论出发,否认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的作用,主张用专制主义的严刑峻法统治人民。马基雅维里指出,现实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人是恶的,君王仅凭法律和守信很难长久保持自己的地位,因此一旦遵守道德和法律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他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毁弃条约和诺言,采取兽性的残暴和欺骗的手段击败对手,但他要尽量伪装成仁慈、忠信、人道、正直和虔信宗教的。
尼采公开宣称自己是非道德论者并以此为荣,他认为人是野兽,其天性是邪恶的,因而激烈攻击包括基督教和中国道德在内的一切主张仁爱和利他的非我化道德都是伪善和吸血鬼,是弱者和奴隶的道德,他指责这种所谓颓废堕落的道德摧残肉体、毁灭生命、否定自我、阉割人类、诋毁现实、压抑强者和权力意志,相反他赞美肉体的本能欲望和生命的强力,美化战争和暴力,推崇出类拔萃的超人和有实力有创造力的强者,主张高等种族应铲除无权生存的衰退种族,专制暴君和铁腕人物要无所顾忌地征服并统治一切群畜般的弱者、平庸者、穷人、女人和民众,建立高等种族优越于劣等种族的贵族等级制度,因此他反对劳动、博爱、人人平等、廉洁奉公、社会主义、普选权和民主政治。这就是尼采所谓的“重估”一切价值,其实质乃是对善恶价值的颠倒!尼采可以说是古今最彻底的和最不掩饰的性恶论者和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之为法西斯德国所利用决非偶然,我们可以赞成他高扬自强、肯定合理欲望的精神,但决不能同意他否定平等道德和民主政治的观点。有人说尼采的偏激观点是由于其妹的歪曲和滥用而造成的误解,然而经考证,尼采原稿俱在,白纸黑字岂可否认?他把马基雅维里辈认为需加掩饰和李宗吾辈以为“做得说不得”的东西坦白说出来了,还以为这是在改良人类,君不见“克服了”道德“同情心和正义感”的“高等种族”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是改良人类乎,毁灭人类乎?
萨特提出过“他人就是地狱”的命题,认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类似性虐狂或受虐狂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即一方(主体)奴役另一方(对象)的关系,不是你把他(她)变成对象,就是他(她)把你变成对象,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不是各个主体的平等共存而是永不停息的冲突。然而萨特并不是性恶论者,他否认存在一个先天的人的本质,因此他并没有完全排除道德的可能性,在其早期他将人类关系的改善寄托于一种道德的改宗,而在晚期则寄希望于在人民群众革命集团内产生的兄弟之爱(博爱),不过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写出一部伦理学,而且兄弟之爱也要以革命集团与敌人的冲突为前提,所以他基本上还是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然而,萨特的道德虚无主义不同于尼采,后者把摧毁道德、建立非道德的强者统治作为他的理想目标来追求;而前者只把非道德状态作为一种我们对之无可奈何的罪恶现实来描述(《存在与虚无》首先是一部本体论著作,而不是一部伦理学),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其根源在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人际冲突,因此在匮乏消灭之前不可能建立一种人的道德。不过,萨特的这种修正过的观点仍然有问题,这等于将建立和实施道德的可能性推到无限远的将来,在目前尚存在人际冲突的社会中道德依然讨诸阙如,而道德以及法律的一个最大的功能就在于调节利益冲突。
道德虚无主义最大的谬误就在于混淆了事实与价值,混淆了“是什么”和“应该”,进而从现实的腐败中得出屈服于流俗甚至同流合污的顺世主义。然而历史表明,每当社会上出现罪恶和腐败时,往往就是历史行将发生转折、社会行将改革、道德行将重建之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有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感受到改革的不可避免和重建道德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力挽狂澜,筚路蓝缕,树立一种新价值,造就一种新道德,努力建立一个新秩序。这些人不仅是愤世疾俗的批判者,而且是道德理想和道德秩序的重建者。
孔子倡仁义忠恕,墨子主兼相爱交相利,乔答摩说众生平等,耶稣讲爱人如己,这些都是古代各民族杰出的道德重建主义者。近代以来,面对现实中被解放出来的人的贪欲及其所造成的冲突,西方思想家都或多或少企图通过建立新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秩序来调节人与人、统治者与被治者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其成果就是近代西方的民法、宪法、国际法以及调整个人利益之间和个人与公共利益之间冲突的道德原则。卢梭提出为了对付毫无道德的互相残杀和专制暴君,必须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民主共和制以保障人人自由平等的权利。爱尔维修认为任何一个人只有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他的品行才是明智的和善的,而人们的善则是法律的产物,良好的法律可以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康德则确立了一个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每个人在其行为中应该使他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这条表面上是形式的原则,其实质乃是人人在权利和义务上的平等,与孔子提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儒家的“爱有差等”对其实现有所妨害,而墨子的“爱无差等”则更能切中其意。马克思终生致力于把几千年来人类的道德理想变为现实社会经济制度,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道德原则。
我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元勋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位继往开来、重建中国伦理道德的积极倡导者。他一生坚守高尚的道德节操,不争一己之权,不争一己之利,对争做皇帝的帝王思想和官僚军阀的贪污聚敛深恶痛绝,经常劝勉革命党人“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做大官”(《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3页),鼓励青年造就高尚的道德人格,实行人格救国。为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并建立一个平等团结的新社会,他力辟鼓吹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指出:“至达尔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196页)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和法制建设的方针,孙中山先生提出“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他认为三民主义就是世界潮流与中国情状的结合,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约略相当于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原则,而五权宪法则是孟德斯鸠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加以中国的考试、监察二权的合璧。为了维护民族的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孙中山先生认为必须树立优良的道德,而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他不同意一概排斥,而主张择优汰劣、加以改造并赋予新的涵意:“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他把忠君改造为忠于国家和人民,把仁爱和墨子的“兼爱”说成博爱,把对朋友的信义解释为商业交易上的信用和忠实履行国际条约,而中国人酷爱和平的美德则被用来反对帝国主义强盗战争,进而通过联合爱好和平之各弱小民族共同用公理战胜强权,实现世界和平。孙中山先生的伦理思想是为了拯救中国和建立新的道德秩序有感而发的,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二、新时期道德重建的初步构想
我国五十年代曾大力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伦理原则,这本是在承认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保障并协调个人与他人、社会各方利益的一个最现实最合理的伦理原则,也是对古今中外主张人人在权利与义务上相互平等的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与光大。遗憾的是,随着极左思潮的逐渐泛滥,这一健全的伦理原则受到了错误的批判,个人的合理权益被践踏,权利与义务的平等被破坏殆尽,迨至“文革”时,道德空想主义盛行,一方面在大公无私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美名下对普通人民大行禁欲主义之实,另一方面却为某些人乘机化公为私、大私无公、骄奢淫逸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道德空想主义的主要特征,第一是禁欲主义,第二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若把它与道德虚无主义相比较则可以看出,虽然后者的第一个特征是纵欲主义,而其第二个特征却恰恰也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而且,双方的第一个特征虽然貌似截然相反,但是道德空想主义公开赞美的禁欲只是对人民大众的要求,由于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其暗中实行的却是某些人自己的挥霍纵欲;而道德虚无主义的纵欲也由于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只能成为统治者或上等人的特权,人民大众仍然不得不实行禁欲。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出,道德空想主义的自我牺牲与道德虚无主义的损人利己之间的那种夸张的对立完全是一种骗人的假象,二者的实质竟然毫无差别!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证明,这两个貌似水火不相容的极端学说在实践中却互为前提、互相转化:若没有一方的禁欲就无以支撑另一方的纵欲,而没有一方的纵欲也不至迫使另一方禁欲;正是由于“文革”中道德空想主义的压抑导致了现在道德虚无主义的反弹。两极相通,莫此为甚。
应该肯定,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有了极大的进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民主与法制不断健全,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禁欲的道德空想主义的批判也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然而,被解放出来的追求个人致富的盲目冲动却导致了目前社会上的道德沦丧,以致假冒伪劣、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甚至杀人越货的罪恶现象相当严重。在体制转换时期出现的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旧体制下的某些监督机制(严刑峻法的吓阻和意识形态的约束)的废驰以及新体制监督制约机制(市场的成熟、法制的完善、传媒的监督)尚未真正建立并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因为由厌恶道德空想主义而导致的道德虚无主义的泛滥。很多人由批判道德空想主义的虚伪性而走向抛弃一切道德的虚无主义,把对伪君子的愤慨迁怒于道德本身,从某些人伪善的事实中推论出道德本身是虚伪的而应该抛弃的价值判断,结果虚伪的道德变成了真诚的不道德,自己则从厌恶伪君子变为甘当真恶棍。我们应该自我警醒并且提醒世人,不要被腐败的一时猖獗和恶人的暂时得利迷昏了心窍或气昏了头脑,自觉抗拒道德虚无主义的诱惑,同时抵制道德空想主义的无力说教。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法制不健全和道德虚无主义的泛滥所造成的道德水准的下降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障碍,因此,重建道德规范体系以便把个人追求幸福和富裕的巨大能量纳入法律和道德的轨道,使个人利益与他人、社会的利益重新协调起来,是一项极为必要而紧迫的任务。
然而,关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伦理道德体系的问题,社会上和理论界仍然存在着思想混乱。面对当前道德沦丧的现实,持道德空想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观点的人要么势不两立地争论不已,要么不断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要想真正摆脱这种两极对立的恶性循环,必须抛弃极端主义的思想方式,不被这两种学说表面上的对立所迷惑,抓住二者共同的要害——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加以彻底清算,批判地吸收历史上道德重建主义的有价值的成分,以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原则为主导建立起适应现代社会和我国国情的新型道德体系。这个主导原则就是——权利与义务平等的相互性。
道德的功能是处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其本质特征首先应该是权利与义务的相互性,而任何鼓吹人与人关系的单向性的观点都是非道德的,无论是道德空想主义的单方面禁欲还是道德虚无主义的弱肉强食都是一方宰制另一方的单向性关系,其权利与义务都是分裂的,尤其后者的弱肉强食乃是“丛林法则”(jungle law)、野兽的法则,而不是人的道德法则。一般说来,历史上的道德重建主义大都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相互性,而且向着越来越平等的方向发展。儒家的“三纲”固然是一方统治另一方,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摒弃的,然而儒家并不主张人伦关系的绝对单方面性,而是强调上下关系的相互维系,即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孔子的忠恕之道对这种相互性原则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当然,儒家的礼制是上下有序、亲疏有别的,因此这种相互性还不能说是平等的,惟有五伦中的朋友一伦比较具有平等精神和现代性,孔子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孟子云:“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都是平等的朋友之间相互守信。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原则提倡视人若己、平等互爱和互助互利的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古代所能达到的最富于平等相互性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属于应该继承的民主性的精华之列,经改造后基本上可以运用于现代社会。佛教与基督教分别倡导的众生平等和博爱也是以平等的相互性为其原则,但是我们必须拒斥其禁欲主义的说教。因为禁欲主义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抵牾,而且经济发展是道德重建的基础,中国人自古就已见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的道理。康德提出的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则可以说是对于平等的相互性的经典表述。孙中山先生主张,民族主义包括中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中国与外国的平等,民权主义则是指中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与团体均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民生主义则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120页),可见其三民主义中处处贯穿着平等的相互性原则。我们在重建现代中国的道德理想与道德秩序时应该继承这些宝贵的遗产,发扬光大五十年代倡导过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把平等的相互性真正确立为新时期道德体系的主导原则。
以这个主导原则为标准来检讨古今中外各种道德规范,发现我国传统道德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的“信”和东西方共有的“契约”观念最接近于平等的相互性原则,也最适应我国目前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现代化的时代需要。契约是自由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信则保证了契约的忠实履行。战国时代的慎到就曾说过:“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慎子·威德》),“五常”中的信则是处理朋友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在西方最早提出,社会秩序是人们为了保证公正与幸福、防范彼此伤害而相互约定的结果。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则是神与人的约。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大都主张通过人与人订立契约、制定法律来建立国家与社会秩序。孙中山先生吸收并融汇西方的法制思想和中国传统道德的信义观念,把它们运用于新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在现代西方社会里,契约关系高度发达,渗透于国家、社会、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支配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领域中人与人关系的主要原则,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环节越来越多,各个环节在时间和空间上越来越分离,而各个环节相互联系的整体化要求也越来越迫切,真正能将这个囊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庞大复杂的经济机器连接整合并使之运转起来的有效手段主要是法律上的契约和道德上的信用。假如没有契约和信用,人们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并且带着刀剑随时准备在对方不履约时进行战斗以讨回公道,这类现象在现代社会的那些法外领域(违法或不受法律保护的领域)中至今仍屡见不鲜(如毒品交易、黑市买卖、走私)。我国目前有法不依和不讲信用的现象(假冒伪劣、盗版侵权、拖欠货款、商业诈骗)也相当严重,其后果与上述情形相差无几。这些前现代的交往方式都是现代社会的破坏者和现代化的阻力,必须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和有效的伦理道德加以打击和约束。鉴于契约和信用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将其置于新时期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体系的首要地位。其他道德规范可以根据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作用的重要程度依次论列,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经过无数怀抱崇高道德理想的仁人志士筚路蓝缕、前仆后继的艰苦奋斗,人类文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在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法律与道德之外的领域,如犯罪和黑社会的领域、权大于法的领域、国际关系的领域等等,这些领域至今仍由非理性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统治。人类的理想应该是最终把法律和道德的正义的阳光普照到这些黑暗的王国,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憧憬的“用公理去打破强权”,“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0、253页)的崇高理想。致力于道德重建的志士仁人仍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