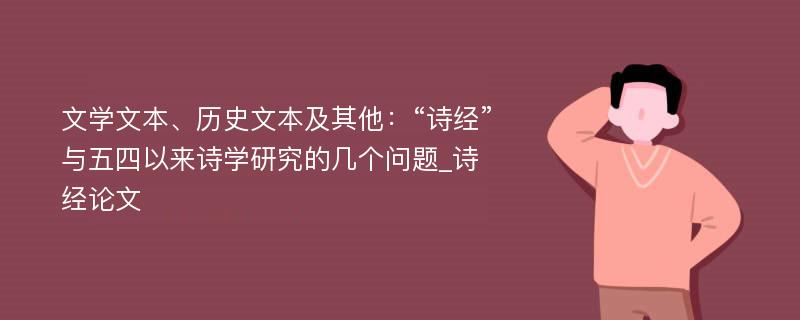
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及其他——“五四”以来《诗经》与诗学研究的几点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诗学论文,诗经论文,几点论文,及其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诗学日子一直不太好过。诗教说、言志说、无邪说、温柔敦厚说、乐淫怨刺说几乎无不遮蔽在愈演愈烈的新思潮批判的阴影之下。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文坛掀起的以“新方法论热”和“河殇热”为标志的文化反思运动,也是伴随着对传统诗学的批判进行的。然而,其中一个颇为令人疑惑却长期为学界所忽略的现象是,历来批判矛头的指向仅止于孔夫子,特别是汉儒、宋明经生等,却无涉《诗经》文本。脱离《诗经》文本而侈谈诗学,批判孔教诗论而宝爱《诗经》,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新诗学的一个偏颇,也是影响诗学研究得以纵向深入的主要障碍。
实际上,透过纷纷扬扬,林林总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诗经》文本,我们就会看到理论分歧的实质和前提在于:诗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是贵族的还是民间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本文拟从《诗经》文本入手,重新审视诗教说、言志说及《诗序》和孔子“删诗”等诗学理论问题。
一、《诗经》文本:民族先期史
在我们一代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地生长着一个坚不可摧的理论观念:文艺源于劳动,源于普通劳动者的生产实践活动。“五四”以来的诗学研究几乎都被这一具有“唯物史观”色彩的理论观念支配着。于是《诗经》被解释为采自民间的文学,亦即民间文学性。特别是“国风”部分似乎更是无容争辩。对于“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孔教遗说的批判正是建立在这一理论支点上。具体地说,民间文学性是由两个概念构成的:一是民间性,二是文学性。民间性是相对于贵族性而言的,文学性是相对于历史性而言的。这也正是“五四”以来新旧诗学理论分歧的基本生长点。对传统诗学持批判立场的新学代表们,认为所谓的“后妃之德”、“代圣贤立言”等诗教说、言志说皆为无稽之谈。胡适就曾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诗经》并非古代圣贤垂训后世的“经书”,而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一部古代歌谣总集”[①]。另外两位新学代表闻一多和郑振铎也持有大致相同的见解,郑氏认为《诗经》并非贵族的专有品,诗经所以被解释成这个样子(即圣贤垂训后世之作——引者),是因其“久已为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把它的真相掩盖住了”。他对于阐释《诗经》,也是传统诗学的重要文献《毛诗序》大加挞伐,指责它对诗的解释充斥着“附会诗意,穿凿不通”之处,他说道:“明明是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②]闻一多在注释《候人》时靠“直觉”断言这首诗的真义是写一个少女派人迎接她所私恋的人,批评《诗序》关于这首诗是“刺近小人也”的解释,完全是“谎言与废话”[③]。
判断《诗经》究竟是历史还是文学,是贵族的还是民间的这个问题时,应建立起一种历史意识,即在阐释现存《诗经》的文本时,首先应意识到这一文本形态经历了大约五百多年的收集、整理、润色、刊定而集结成书的,其中某些篇章口口相传的时间可能还要古远。可以推断,《诗经》是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悠然岁月,经历了一道道不同观念,不同需要,不同目的的工序方成我们今天所见的样子。其次应意识到我们距现存《诗经》已有两千年之久。这是我们解读《诗》文本的两个历史前提。解读《诗经》至少要做两件事:一是要检视《诗经》文本生成、嬗变的历史过程,二是要反省我们20世纪思维和文化背景与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差距。应看到,今人解读《诗经》时,往往因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为《诗经》披上一层我们意识到的历史面纱;也往往以为,今天不可能发生的事,在历史上也不会发生,甚至用今天发生过的或可能发生的事去印证、演绎《诗经》。
基于上述观点,可以认为《诗经》的背后可能隐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民俗学告诉我们,远古时期图腾崇拜、祖先祭祀、巫术仪式、生活禁忌、历史与现实、人神世界,都是混沌未开的。因而,人类早期的诗文大都具有历史性。但因历史不断发展,俗制巫法、人神文史渐渐分道扬镳,这部先期史也不断被修改,愈来愈文学化或虚拟化而变成后来的样子。《诗经》也大抵经历了这一过程。其中的《商颂·玄鸟》、《大雅·生民》皆为殷、周部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公刘》、《绵》、《皇矣》、《大明》则是对周人英雄祖先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记载与讴歌。这些《诗经》早期形态的历史遗篇虽然早已为学界所确证无疑了,但却极少有人承认其为历史而视之为文学。对此,《诗序》的作者和汉儒们或许因为较之我们距离《诗经》时代更近,因而也更易于接受这一“历史”事实。他们的所谓“代圣贤立言”、“美盛德之形容”也许并非如新学代表所言是“荒谬绝伦”的了。《诗序》几乎把《诗经》的每一篇章都与圣人后妃、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显然不完全是什么“牵强附会”的“凿说”,因为《诗经》的作者是在“记载”而不是在“创造”。人类有个最大的共通的弱点,总是愿意把过去的日子(历史)想象为富有诗意的而予以诗化。《诗经》文本被误读为文学而非历史,这种潜在心理也许是动因之一。《诗经》很有可能是湮灭久远的上古史。早期社会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及其记载早已淹没在厚重的历史尘埃之中了,《诗经》则是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之一。但不幸的是,它们已为无情的历史所严重风化而变异而面目皆非了,成为一种残存的变异或变异的残存。
《诗经》的分类原则也透露了其历史性的信息。众所周知,《诗经》由风、雅、颂三大部分组成,对于雅、颂的历史性学界异义不大,主要的问题在于风。因为雅、颂里面的许多篇章很近于我们今天所认可的“历史”形式。即那种记叙的、类似编年的时间性质的。而“风”中的作品则更富有空间性、地域性和抒情性而缺少时间性。西方一些学者也据此认为中国无史诗。然而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古人所理解的“历史”形式,也许并非如今人一样。甚至可以认为,这种空间性和抒情性正是中国史诗不同于西方史诗的一个特点。
因而,就风、雅、颂整体而言,似乎也可认为是一种史的分类或说隐含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跨度。对于风、雅、颂,历来学者或以诗之内容划分,或以诗之用途、功能划分,或以诗之音乐划分,彼此驳难不已,也从不同角度昭示了《诗经》的不同侧面。但可否作一大胆假设,风、雅、颂是一种史的分类呢?陆侃如在《中国诗史》中推测三百篇中“颂”是原始的舞曲祭歌,“雅”是西周土乐,“风”是黄河流域的土乐,“南”是长江流域的土乐,“雅颂起源较早,至少在西周中叶已存在,风是较晚出的新声……,南的起来大约在东迁以后……”[④]。另一学者孙作云也认为,风、雅、颂的区别“大体上是以时代和地域为准则的”[⑤]。这对于解读《诗经》文本的历史性都是颇有价值的见解。但他们没有继续深究下去,编集《诗经》的人为什么要从时代和地域为标准来分集编纂风、雅、颂(或南、风、雅、颂)呢?而且,这些制作和编集《诗经》的人又多是祝巫之史官或宫廷乐士。似乎可以认为:这些祝巫史官是作为历史或史鉴编集和制作风雅颂的。我们所见到的风雅颂的形式也就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形式。当然这一历史形式又伴随着“乐”的形式,甚至“舞”的形式,构成了史(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原始“诗歌”的典型形态。
关于“诗经”的历史性,清代学者章学诚有一个为学界瞩目的说法,即所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⑥]“六经皆史”之说并非始于章氏,而是代有人在。隋代思想家王通(584—618)也曾把“诗”视为史之一体,他说:“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然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其后宋、元、明、清历代学者如陈傅良、宋濂、王守仁、王世贞、袁枚,逮至章学诚,对于此论无不信而不疑,决不是一无缘由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古人不会无端地著书立说,吟诗作赋的。在一般意义上说,那时还不具有为“艺术消费”而进行“消费”生产的需要与条件。《诗经》在那时的主要用途是政治(宗教)与道德教育,或祈祷上天,或祭祀祖先,以先行者的行为作为垂训后世的典范。在《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父终子及的世袭制(《大雅·文王》、《大雅·崧高》),祭祀妣祖的母权遗俗、图腾崇拜(《鲁颂·宫》、《风·桑中》)、君死臣殉的殉葬制(《秦风·黄鸟》)等异常丰富的历史内容。
在某种意义上说,《诗经》对于那个时代是一部历史教科书,而不是文学读本。当然《诗经》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而是被赋予了被我们今人称之为“艺术”形式的历史教科书。它讲究辞藻、格式、韵律。准确地说,是一部先民史诗。由此可看出,学界谓中华民族“无史诗”论是没有根据的。
对于《诗经》的历史性,现代语言学似乎也可以从理论上提供有力的索解。诗的早期形态,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其能指与所指是同一的,指称与意义(内涵)并未完全分离。这些祖述功德的诗章,大多是“记录”而不是表征。《诗序》概括的诗之“六义”(风、赋、比、兴、雅、颂),主要谈的是教化而不是“艺术”,大约反映了那个时代对“诗”的理解。包括《诗经》中的那些充满神异色彩的《商颂·玄鸟》、《大雅·生民》,也不是作为“神话”或“传说”,而是作为“史实”被“认可”在雅、颂里面。契、姜、后稷等殷、周先祖的奇异经历应说是毫无史实依据的,甚至可说是荒诞不经的。但是当他们在口口相传乃至“记录”在“案”时都是深信不疑的。象《公刘》、《绵》、《大明》更是被作为“史”流传下来,而不是作为文学流传下来的。当我们指出(亦即意识到)这是神话传说时,这一原符号系统已渐崩溃,抽象的能指与具体的所指已渐分离,“史”的内涵也渐次消亡而代之以“文学”,具有更宽泛的所指与外延,亦可说是转化为艺术符号系统了。《诗经》文本的虚拟化的历史变迁,使解读带来了歧义纷呈的局面。
所以,似乎可以这样认识,愈是把《诗经》视为“史”,愈接近于它的原始文本内涵,而愈是把《诗经》视为文学,则愈是远离它的原始文本内涵。
二、文本历史性与贵族性的同一与统一
其实,当我们指出《诗经》文本主要是“历史”而非“文学”时,关于它的“贵族”性质与“民间”性质的分歧应当已见分晓。因为任何史书都出自庙堂(或曰反映庙堂的意志)而非民间。但这不妨碍——准确地说,尚需我们详论的。
考察《诗经》的贵族性质,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诗经》的作者问题,即是出自贵族阶层之手,还是出自民间百姓或普通劳动者之手;二是《诗经》特别是“国风”部分所反映的生活内容问题,即是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喜怒哀乐、理想追求,还是上层社会的需要、情感世界。我们知道,《诗经》在流传、收集、整理直至编订成集,经历了相当漫长而严酷的历史过程,致使它的绝大多数作者已经湮灭无考了,于是其作者或曰著作权问题成了诗学研究中一个众讼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诗经》的著作权问题被提高到历史观与文学史观的层面上来,从而使其成为一个颇为重要而严肃的问题。当然,遭到批评最厉的还是《诗序》的作者。《诗序》问世之前,《诗经》中除五、六篇作品标明作者外,其他作者都是不得而知的。而《诗序》在对《诗经》篇章进行题解时,常把一些作品冠以某王、某公或与其相关的大人物所作,例如:把《关雎》、《葛覃》、《卷耳》归于周文王后妃之手笔,把《七月》、《鸱鸮》、《东山》归于周公旦名下,等等。对于这些说法在过去的诗学研究中也曾出现过异议,但真正受到激烈的殂击是“五四”运动之后。因为在一些人看来这不仅无形中剥夺了人民群众的著作权,也是有违于所谓的唯物史观的。
然而,我们讨论问题一个重要前提是应当尊重历史,回避不能以论代史,以观代史,回避坚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诚然,《诗经》的多数具体作者已无从考起,《诗序》的裁定也未尽可信然。但至少有一点事实可以确定:《诗经》毕竟有过作者,而且它的作者在创作时是负有神圣使命并具有肩负这一使命的地位、能力与条件的。这一点从已标明作者的五篇作品中是可以印证的,如次: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汹。”
《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
《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鲁颂·閟官》:“新庙奕奕,奚斯所作。”
诗中自道之“家父”、“孟子”、“吉甫”、“奚斯”即为各篇之作者。这些人的具体身份虽然大多缺少可供查询的文献资料,但作品本身所提供的内容已经足以证明作者多为社会上层之贵族人士。
此外,通过参校史书从先秦文献里考据到的少数作者,查明他们的身份也均为贵族阶层人,如《卫风·硕人》的作者为卫国大夫(见《左传·隐公三年》),《郑风·清人》的作者郑国大夫(见《左传·闵公二年》),《鄘风·载驰》的作者为许穆夫人(见《左传·闵公二年》),《秦风·黄鸟》的作者为秦国大夫(见《左传·文公六年》),《秦风·无衣》的作者为秦哀公(见《左传·定公四年》)。
对于绝大多数目前无法知其作者姓名和身份的作品,则可通过对作品文本的阐释得到某些索解。由于《诗经》流传的极为古远,语言逻辑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因此,对它的阐释我想应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面进行。表层结构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深层结构是我们难以理喻的意义世界。下面我们从《关雎》、《葛覃》和《卷耳》三篇入手分析,这是诗家所论颇多的几篇作品。从表层结构意义上看,《关雎》可以是“后妃之德也”(《诗序》),也可以是“周邑之咏初婚者”(方玉润语)。或依现代诗解,是描写青年男女恋爱婚姻的。但有一点,即似乎很难视为普通劳动者的婚恋歌谣。诗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在当时都不是普通百姓的称谓,庆典所用之“琴瑟”、“钟鼓”等也非寻常百姓之器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所表达的情致、心态可说是“极其哀乐而不过则”,温良恭俭、平和节制之极。概言之,诗中的这对男女都很有教养且符合特定道德规范的贵族青年。《葛覃》的教化色彩颇浓,诗中“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叙述的也是对贵族妇女的品德要求:躬俭节用、服澣濯衣、尊敬师傅、志在女功等。《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聩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吁矣,云何吁矣!”据许慎考:“金罍,大器也。天子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⑦]“兕觥”亦属同类器物。诗之主人有仆有马,有兕觥,有金罍,显然是大夫以上阶层之人物。现代诗家多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把《关雎》解释成一般青年男女恋爱的作品,把《葛覃》、《卷耳》分别解释为女仆告假和士兵之妻思夫、反对兵役之作,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从《诗经》的深层结构看,所展示与表达的应说是一个我们今人很难理喻、意识不到意义世界。这一世界的具体内容、意义早已淹没在厚重的历史尘埃中了。但我们或许可以从其他方面——个别词语或形式结构等因素上去探赜索隐,求证出某些可资参悟的索解。
首先,从形式结构论,《诗经》的文体框架很可能保留了上古时期的祝祭辞体结构,即词语、句式或篇章的反复咏叹与重叠。这种独特的语言结构形式与处于混沌未开的早期先祖进行祝祭活动的原始宗教行为和宗教心理有着密切联系。祭天、祭地、祭祖先、祭鬼神,求福避祸,要反反复复、重重叠叠,以惊天地,泣鬼神,感动神灵。这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文化现象。《诗经》中这样的章法句式比比皆是。《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出现了四次,“参差荇菜”出现了三次;《葛覃》中的“我”、“彼”反复出现各有六、七次之多,最后一章: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吁矣!云何吁矣!”几乎全为感叹句。
祝祭辞体在形式结构(或曰修辞)上的另一突出特征是比喻——在严格意义上说是隐喻。这与人类早期的“前逻辑”思维有关。“前逻辑”思维表现为思维载体不是抽象的概念符号,而是感性的形象符号。原始先民把外部世界的许多事物、现象都视作亦即赋予了富有神幻意义的“物象”。在他们眼里这些“物象”已超出了其自身固有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出现了语言学意义上的“隐喻”或“转喻”。后人所谓《诗经》在修辞上的“比、兴”手法,很可能与祝祭的“隐喻”或“转喻”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比《诗经》更为古老的文献《卦爻辞》中找到可资参照的例证。《卦爻辞》是由古代巫师(同时也是部落领袖)占卜吉凶福祸的记录编辑而成的,保留着比较浓郁的上古时期之神幻色彩,其中一些篇章的修辞形式与《诗经》中的作品已经颇为接近。例证如下:
《明夷》初九: 《邶·燕燕》:
明夷于飞, 燕燕于飞:
垂具翼;差池其羽;
君子于行, 之子于归,
三日不食。 远送于野。
《渐》九三:《豳·九罭》:
鸿渐于陆, 鸿飞遵陆,
夫征不复, 公归不复,
妇孕不育。 于女信宿。
从以上两组对比中我们看到,《诗经》中的《比兴》手法与《卦父辞》中的隐喻尽管有着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重大差异(一个是宗教的、神秘世界的载体,一个是现实的、人的世界载体),但语言逻辑内在结构的一致性是十分明显的。这种一致性就是:借助某一物象象征或表达某一特定的意义世界。后人所谓:“比者,比方于物也。”(郑玄)“兴者,起也。取譬引类,发起己心。”(孔颖达)或“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在上文中我们提出《诗经》文本的背后可能隐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现在,我们通过对《诗经》深层结构的分析,似乎同样可以说,《诗经》中绝大多数篇章的“原型”有可能是上古时期的祝祭之辞。因为处于魔法神幻时代的原始先民,人神巫史是混沌不分的。换言之,人的世界充满了神幻内容,巫即是史,史即是巫。《诗经》中的许多篇章或许与人类早期巫法咒祝等宗教活动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深层联系。“诗”的早期形态不仅是与舞、乐三位一体的,更核心的意义在于它是巫史、人神合一时代法师所歌所诵之言,是具有巫史合一性质的占卜纪载、祝祭之辞。有的研究者从文化学角度提出《关雎》、《卷耳》、《芣苢》皆有“爱情咒”的意义,[⑧]对于这三篇确否属于“爱情”这一特定含义之咒语,笔者尚不敢完全认同,但在原始宗教意义上作出的祝辞、咒语之索解,我想是颇富启示意义的。其实,不仅《关雎》、《卷耳》、《芣苢》等篇章,包括象《伐檀》、《硕鼠》这样的被现代诗家解释为劳动者之歌或劳动者控诉剥削阶级之歌的篇章,最初也许只是有关神木的祭辞或动物图腾的咒语。这些负载着原始先民混沌未明、野性激情的篇章,伴随着文明与进化,变得愈来愈纤细而精致,并且一度曾经演化为统治阶级教化的工具,如《诗序》所理解的,后来又成了被人们视为楷模的文学典范。
支持“民间文学”说立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所谓“采诗”说。认为上古至周代统治阶级为了解民情,而实行了一种“采诗”制度。采诗之官或“遒人”,或“使者”,或“行人”,或年老无子的男女遍访民间歌谣,使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但“采诗”之说主要见诸汉代文献,先秦文献中则颇为罕见。所以怀疑者颇众。先秦文献中记载较多的是“献诗”之说。即古代王者为考察时政而令大小官员进献诗章。《国语·周语》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国语·晋语》言:“古之王者,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左传·襄公十四年》言:“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另,《左传·昭公十二年》还记载了祭公谋父献诗劝谏周穆王不要周游天下的事件,可为“献诗”之佐证。足见,《诗经》之产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政府”、“庙堂”行为,而非民间百姓行为。包括“采诗”之举即或可备一说,也基本上是“政府”行为。关于这一点,刘师培的一篇短文《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分析得颇为透辟。他通过对“词”、“祝”两字的考据,得出结论:古代文词,主要用于祈祀,所以巫祝史官,文笔都特别的精彩,“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⑨]作为以功烈扬祖先,以成功告神明的史著,很难说是民间作品。事实上,从春秋到战国及秦汉唐宋,众多的文献史籍把《诗经》是作为贵族的专有品来对待的。春秋时代的申叔时就指出《诗》与《春秋》、《礼》、《乐》同为贵族子弟的教科书:“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韦昭注曰:“导,开也。显德,为若成汤、文、武、周、邵、僖公之属,诸诗所美者也。”[⑩]。到了孔子时代,诗已成为贵族子弟修身立业的根本了,所谓“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与”[(11)]。史官司马迁则认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国十五世纪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对《诗经》及《诗序》推崇备致,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是:“诗礼足以相解。”《诗经》集结大约在西周春秋之际,还是以礼为法度的“礼治”时代,王安石认为诗礼足以相解,就是:“以其理同故也”[(12)],诗与礼的性质是相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也不可能是民间的。退一步说,即或它是文学或具有文学性质的话,也不大可能是民间的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虽然有可能为他们提供艺术活动的条件、物质基础,然而他们却是艺术活动权力的被剥夺者。即或有少量的民间文学创作,也很难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学。
前述对风雅颂的分类方法有许多学者倾向于是音乐的划分。即所谓雅、颂是天子之乐,风是地方诸侯土乐。但“土乐”不是“民间”之意,而是“地方”之意。足见,即或从音乐曲调上也很难找到《诗经》的民间性质。
诚然,也不能否认,在如此广泛而漫长的采集、搜求过程中,难免有少量的民间歌谣渗入《诗经》之中。但应看到在它们被搜求、筛选、整理的过程中,早已为神庙巫祝或宫廷乐官所贵族化、宫廷化了。那一时代礼、俗(制)权威的不可侵犯性,使《诗经》的收集、编纂者们废其不合“礼”者而存其合“礼”者,改其不合“礼”之俗,而沿其合“礼”之俗,发挥诗之“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功能。孔子删诗也好,正乐也好,也说明它是经过一道加工的。
三、孔子“删诗”与《诗经》文本的变迁及汉儒的功过
孔子“删诗”之说,最早见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此,历来有信、疑两派学者,彼此驳难不已,我想,仅就孔子“删诗”的真伪问题耗时费力,也许意义不大。重要的是判断孔子“删诗”之举对于认识《诗经》文本的变迁也许是具有重大价值的。并且这里还包含有文化学方法论意义上的东西。
近人几乎一致认定孔子“删诗”是不可信的。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即或是怀疑派,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孔子虽未“删诗”,却对《诗经》做过一番“正乐”工作,即所谓“纠正流传中被唱错了音调音节,清除混入雅颂中的乡土小调”。证据是《论语·子罕》里曾记载孔子的一句话:“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但是,如果承认孔子“正乐”就应承认孔子“删诗”。因为在孔子及其以前的时代,正“乐”与正“诗”应当是一回事。那时的正乐,决不仅仅是与诗文无干的,用琴弦调调调子而已,并非象方玉润所说的那样,什么“夫曰‘正乐’,必雅、颂之乐各有所在,不幸岁久年湮,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减于其际也。”[(13)]事实上,在先秦时代,诗与乐是分不开的。是否可以认为,那时的乐师,在调音的同时,就把诗文也改了呢。音节和音调的要求,也就是文字的要求。音节、音调与文字是同一的。甚至可以认为,其时所唱的,也就是今之所念的。所以《诗经》中的文字那么整齐、和谐,读之朗朗上口,其高度统一之程度,为今之大诗人、大文豪郭沫若所慨叹。这种“统一”或曰“由太师叶律合乐”也可说是作为史的“诗”之文学(艺术)化过程。《史记》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并不是说给它谱曲,而是说为之配器伴奏。诗的存在形态是诗乐合一的。许多怀疑派责备司马迁把孔子“正乐”,误为“删诗”,孰不知,恰恰是这些怀疑派们没有搞清《诗经》是诗、乐合一的文本形态。
古代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据考,“诗”的古字为象形文,摹拟顿足击节之状,古人训“颂”有舞容者之说,《宛丘》、《东门之(13)》、《伐木》、《宾之初筵》都表现出舞、乐、诗三位一体[(14)]。《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也都说明古代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结构形式。写到这,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探究,孔子所谓的“正乐”正的是什么?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现实痛心疾首,这种礼崩乐坏反映在诗上,就是代表天子之乐的雅颂之音已不那么纯正了,为地方诸侯各国曲调冲击、渗入,失去了天子之乐的威仪。但是乐,在先秦没有独立出来,“六经无乐”即为旁证。为什么独独缺乐呢,因为乐附于诗上,所以中和之美,温柔敦厚,思无邪,既是诗的要求,也是乐的神髓,况且先秦史籍根本就没有乐谱留下,乐谱也许是汉代以后才有的。准确地说,彼时之正乐也就是选定适合音韵的字词,所以,孔子的正乐,实质也就是正诗,也就是改定文字的音韵,于是,在正乐的同时,诗文也就被删定,足见正乐与删诗是同时进行、并行不悖的。关于孔子删诗我们还能找到另一佐证,即未收入《诗经》的散见于先秦典籍中的逸诗,绝大多数的句式是参差不齐的长短句,而《诗经》中诗的形式主要是四言,音韵又差不多是一律的。据此郭沫若指出:“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的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却呈现着一个统一性”,并由此推测:“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的。”[(15)]诚然,孔子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删诗者,因为几千首诗删定为305首,如此浩大的工程不可能出自一个人之手。但他极有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即进行最后一道加工的那个人。而这一道加工绝非无足轻重的小事,是“诗”由历史文本转变为“文学”文本(准确地说被赋予文学文本形式)的根本性变革,是“诗”的文学化的一次革命。甚至可以推测,未经删去的原始文本可能是叙述诗(史),或叙述成份较多的诗(史)。我们手中能够有如此感叹心灵优美动人的伟大诗篇,应当感谢孔子,当然也为失去那么多丰富的历史篇章而遗憾不已。“五四”以后的新学几乎舆论一律地认定是重重叠叠的注疏、题解掩盖了《诗经》的“文学”本貌,殊不知,恰恰是“诗”的文学化过程掩盖了其“史”的本貌。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汉儒的功与过。所有诗论中受批评最厉的是汉儒,而遍翻史论汉儒最大的错误是立诗为经。那么,立诗为经的功过究竟如何呢?换言之,在汉儒的努力下,把诗立为“经”是好事还是坏事?判断一件事的好与坏的标准主要应是看其损益程度。诗到了汉代被尊为五经之一,第一,提高了诗的地位,这一点类似于亚里斯多德的诗界革命,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学是一等公民,战士是二等公民,农工商是三等公民,诗人则是不入流的六等公民,诗的地位之悲惨也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亚氏那里,一反他老师的成见,把诗提高到哲学的地位,诗人也跃踞为头等公民,与哲学王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在我国先秦时期诗虽然还没有悲惨到六等公民的地位(在秦时也遭到焚灭之灾),但与汉代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汉时,统治阶级专门为之立学官置博士,奉为“显学”。并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学科“诗经学”。
第二,立诗为经,对于作为文学的诗固然是种禁锢,但另一方面对于诗歌的发展繁荣也不能说不是一件幸事。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中,诗的崇高地位被一代又一代的延续着,使中国成为世所公认的诗的国度,如果没有儒家的努力,没有“诗经”的地位,没有统治阶级的重视,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信仰和学说四方奔走游说、矢志不渝、皓首穷经的孔氏门徒们。
注释:
① 胡适:《谈谈诗经》。
② 参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③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
④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上)第85页。
⑤ 孙作云:《诗经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423页。
⑥ 《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上》。
⑦ 《五经异义·六》。
⑧ 参见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⑨ 《左畲集》卷八,《近代文论选》。
⑩ 《国语·楚语》。
(11) 《论语·阳货》。
(12) 《诗义钩沉》第10页。
(13) 《诗经原始·诗旨》。
(14) 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和研究》,《文学评论》1993.6。
(15) 郭沫若:《简单地说说〈诗经〉》。
标签:诗经论文; 儒家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卷耳论文; 葛覃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