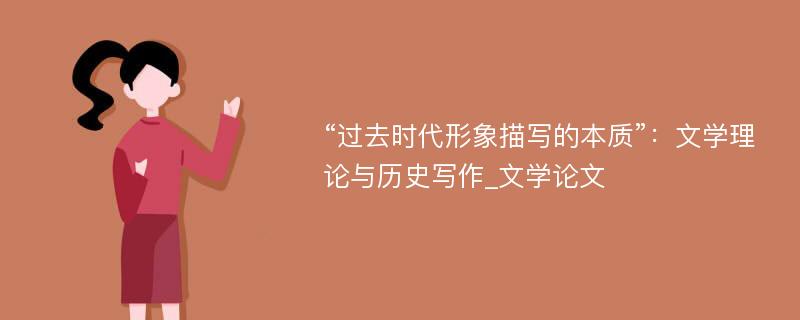
“形象描写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和历史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质论文,形象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雅各·巴曾把自己描写为“一位学历史的学生……以前曾投身于教历史的奇怪仪式”,然后,他又在括弧中说,“所谓奇怪,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历史只能被阅读”。(注:Jacques Barzun,"The Critic,the Public,the Past,"Salmagundi,68-69(Fall,1985-Winter,1986),p.206.)当然,巴曾所说的“历史”并不是指过去的实际事件、结构和过程,而是指职业上积累的学问。然而,在这个简短的旁白中,巴曾使我们想起了现代历史理论不断有意让我们忘记的一些真理:即作为所有这些学问的主题的“历史”只有通过语言才接触得到,我们的历史经验与我们的历史话语是分不开的,这种话语在作为“历史”被消化之前必须书写出来,因此,历史书写本身有多少种不同的话语,就有多少种历史经验。
如是观之,“历史”不仅是我们可以研究和进行研究的一个客体,而且,甚至从根本上是由一种独特的书写话语与过去相协调的一种关系。事实上,历史话语是据结构上具有意义的形式发挥作用的,是一种特殊的书写,在历史修撰的理论和实践上允许我们考虑与文学理论的相关性。
首先,只有假定“过去”的存在具有可言说的意义,历史话语才是可能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不关心过去是否真正存在这一形而上学问题,或者,如果它确实存在,我们是否可以真正认识它这一认识论问题,原因就在于此。过去的经验是历史话语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我们实际上可以书写历史,这个事实是我们可以认识历史的一个充足理由。
其次,与科学话语不同,历史话语并不事先假定我们的历史知识研究是衍生于“过去”而非“现在”的事物的一种独特方法。过去的事件、人物、结构和过程可以看作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中任何或全部学科的研究客体,甚至是许多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当然,仅仅因为它们是过去,或实际上被当作过去,这些实体才能得到历史地研究,但使它们成为历史的并不是它们的过去性。它们之所以是历史的,仅仅因为它们被再现为特定历史书写的主题。巴曾正确地谈到“历史只能被阅读”,但它必须首先被书写才能被阅读。而且正是因为历史首先必须被书写然后才能被阅读(或被言说、歌唱、舞蹈、表演甚至拍成影片),文学理论才不仅与历史修撰、而且特别与历史哲学相关。
历史话语的这一特征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事件、人物、制度和过程从未真正存在过,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得到关于这些过去实体的比较准确的信息,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通过应用包括一个时代或文化的“科学”在内的不同学科的不同方法把这个信息改造成知识。相反,它旨在突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关于过去的信息本身并不是那种特定的历史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的知识本身并不是那种特定的历史知识。这种知识最好被看作“档案”,因为它可以成为任何学科的客体,成为那个学科的独特话语实践的主题。因此,只有在成为历史话语的主题时,我们关于过去的信息和知识才可以说是“历史的”。
因此,历史话语并不生产关于过去的新的信息,因为占有关于过去的新旧信息是建构这样一种话语的先决条件。仅就知识是一种独特探究方法的产物而言,也不能说历史话语提供了关于过去的新知识。(注:Paul Veyne,Writing History:Essay on Epistemology,trans,Mina Moore-Rinvolucri(Middletown,1984),p.12.)历史话语所生产的东西是对历史学家掌握的关于过去的任何信息和知识的阐释。这些阐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简单的编年史或事实的罗列一直到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但它们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把一种再现的叙事模式当作理解作为独特“历史”现象的指涉物的根本。用克罗奇的一句名言来说,没有叙事,就没有独特的历史话语。(注:Benedetto Croce,Primi Saggi,3rd ed.(Bari,1951),p.38.)
在把历史话语当作阐释、把历史阐释当作叙事化时,我认识到我参与了一场关于历史知识性质的争论,并采取了一种立场。这场争论把“叙事”与“理论”对立起来,就如同把一种大部分属于“文学的”甚至“神话的”思想与已经成为或渴望成为科学的思想相对立一样。(注:Cfr.Christopher Norris,"Narrative Theory or Theory-as-Narrative: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Reason,"in The Contest of Faculties:Philosophyand Theory after Deconstr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1985),Ch.1.)但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此考虑的问题不是应该用来探讨过去的研究方法,而是历史书写的方法,即在历史作为一门学科而成长的漫漫长河中历史学家所实际生产的那种话语。事实上,叙事始终是、而且仍然是历史书写的主导模式。因此,任何历史书写理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用科学方法研究过去之可能或不可能的问题,而是解释历史修撰中叙事何以持续的问题。关于历史话语的理论必须涉及在历史文本的生产中叙事性的功能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从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开始,即独特的历史话语必定生产关于其题材的叙事性阐释。把这些话语翻译成一种书面形式将产生一个独特的客体,即历史文本,历史文本反过来又成为哲学或批评反思的主题。于是就有了现代历史理论中约定俗成的区别,一方面是过去的现实,即历史学家研究的客体,以及历史修撰,即历史学家关于这个客体的书面话语;另一方面是历史哲学,即对这个客体与这个话语之间可能有的关系进行研究。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文学理论之于历史书写的实践和理论的各种关系,那就必须记住这些区别。
Ⅰ
目前流行的文学理论对理解历史书写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所谓直接影响是说文学理论是在现代语言理论的基础上提练出来的一些一般话语理论,用以分析历史书写,识别历史书写特有的“文学”(即诗歌和修辞的)方面。在用话语结构的观念替代旧的、在19世纪被认为是“优秀书写”之秘诀的“文体”概念时,现代文学理论提供了关于文学性本身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比以前更精细地区别了历史话语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按照以前的观念,事实构成了历史话语的“主体”,文体或多或少是迷人的,但决不意味着本质上的“掩盖”。(注:Hayden White,"The Problem of Style in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Marx and Flaubert,"in The Concept of Style,ed.Berel Lang(Philadelphia,1979),pp.213-229.See Stephen Bann,The Clothing of Clio:A Study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n Nineteen-Century Britain and France(Cambridge,1984),and Linda Orr's superb review of it in History and Theory,XXIV,3(1985),pp.307-325.)在现实主义话语如同在想象话语中一样,语言既是形式又是内容,这种语言内容必须被看作与其他的(事实的、概念的、类属的)内容一样,构成了整个话语的总体内容。这一认识把历史批评从对一种不可能的“直义主义”的忠实中解放出来,使历史话语的分析者认识到历史话语在何种程度上在言说题材的过程中建构了题材。有关语言形式的内容的观念淡漠了直义与比喻话语之间的区别,使人们能够在历史散文如同在虚构散文中一样探讨和分析比喻成分的功能。
现代文学理论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之所以是间接的,是因为文学理论中充斥的关于语言、言语、书写、话语和文本性等概念为传统上由历史哲学提出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洞见,这些问题包括历史话语样式的分类,历史再现与其指涉物的关系,历史解释的认识论地位,以及历史学家的话语中阐释、描述与解释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把注意力引向了历史话语的最明显问题,但这些问题直到最近仍未得到系统考虑,即是说,每一种历史首先都是一个词语制品,一种特殊语言应用的产物。而这意味着,如果人们认为历史话语能够生产一种特定的知识,那就首先必须将其作为一种语言结构加以分析。
令人惊奇的是,历史哲学家早已经认识到,尤其是自现代哲学在检验其他科学部门时普遍把语言作为中心客体以来,就已认识到语言对于理解历史话语的重要性。这种重心转移部分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历史学家本身已把他们自己的语言看作毫无问题的、透明的中介,既用来再现过去的事件,又表达他们关于这些事件的想法。但也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哲学家把历史话语当作特定的分析客体,他们认为可以把一个话语的实际和概念内容与其“文学的”和语言的形式区别开来,以便评价其真实价值及其与现实的关系的性质。比如,近来的历史哲学家都典型地把叙事当作一种以讲故事为手法的解释而非词语结构,把特定历史中所讲的故事当作由论证概念组成的一个结构,其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是逻辑的(尤其是三段论的),而非语言的。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个历史话语的内容可以从其语言形式中抽取出来,在一种凝缩的复述中清除一切比喻和转义成分,作为论证经受逻辑一致性的考验,并作为整体事实而接受能否充分预示未来的检验。但这将忽视一种“内容”,没有它,历史话语就永远不会存在,这就是语言。
在这一论证模式主导历史话语分析的时期里,诸如奎因、瑟尔、古德曼和罗蒂等哲学家都表明很难把自然科学的话语中所说的内容与说话的方式区别开来,更不用说像历史这样非规范化的话语了。(注:F.R.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Theory,Beiheft 25(1986).)他们的著作证实了现代语言学的奠基前提,即语言决不是等待着填充事实或概念内容的空洞“形式”,或附属于世界的先存的指涉物,其本身作为许多事物之一而存在于世界之上,已经充满了比喻的、转义的和类属的内容,而后才在特定言语中实际表达出来。这意味着,想象书写和现实主义书写之间、虚构话语和真实话语之间的区别必须加以重新评价和重新概念化,自17世纪初历史修撰与修辞分道扬镳以来,人们就以这种区别为基础分析历史的书写了。(注:Hayden White,"Rhetoric and History,"in Hayden White and Frank E.Manuel,Theories of History:Clark Memorial Library Papers(Los Angeles,1978).)
事实上,对实际历史著述的语言进行最简捷的检验也会揭示出历史话语的内容是与其话语形式不可分割的。这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验证,即经典历史著作在其信息早已过时、其解释在形成书面语言的文化时刻已成常识之后很久,却仍然由于其“文学性”而受到重视。的确,在谈到希罗多德、塔西陀、圭恰尔迪尼、吉本、米什莱、托克维尔、布克哈特、蒙森、休津伊哈、费布弗尔或托尼等人的经典历史著述的“文学”性时,我们往往把他们当作思想“阐释”和文风得体的典范。但是,通过把他们的著述看作“文学”,我们并没有让历史脱离知识生产的领域,而不过表明文学本身是在何等程度上也寓于那个领域之中,并为我们提供了类似的阐释思想的模式。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区别在于其基本的指涉物,即所谓“想象的”而非“真正的”事件,但这两种话语之间事实上共性多于差异,它们运作语言的方式仍不可能清晰地将其话语形式与阐释内容区别开来。
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们才必须拒绝、修改或增强关于历史话语的旧的模仿论和模式论。如安克斯密特所说,一种历史与其说是有意描摹它所言说的客体的一幅图画,或“由一些翻译规则而与过去绑缚在一起”的一个模式,毋宁说是“为表明过去的某一部分而特别建构的一个复杂的语言结构”。(注:F.R.Ankersmit,"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History,"MS.)由此看来,不能把历史话语比作一幅图画:图画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客体,没有图画,它就是模糊的,得不到准确的理解。它也不是对一个解释程序的再现,最终只是为了回答在某一特定领域的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的问题。相反,用E.H.冈布里奇在研究西方现实主义绘画时推广的一个表述来说,历史话语并不就是把某一形象或模式与某一外在“现实”相匹配,而是制造一个语言意象,一个话语的“物”,它甚至在把我们的注意力固定在假定的指涉物之上时,也在干扰我们对这个指涉物的认识。(注:E.H.Gombrich,Art and Illusion: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ictorialRepresentation(London and New York,1960).)
保罗·利科曾指出,一个历史文本与其指涉物的关联就如同隐喻作为工具与其要义相关联一样。在他看来,一个历史话语是一个扩展的隐喻——寓言的传统定义——因此,必须被看作既属于直义和技术言语的范畴,又属于比喻的范畴。(注:Hayden White,"The Rule of Narrativity:Symlolic Discourse and theExperiences of Time in Ricoeur's Thought,"in A La recherche du sens/InSearch of Meaning,ed.Theodore-F.Geraets(Ottawa,1985),pp.287-299.)历史话语之所以与文学话语或一般的比喻语言一样,如安克斯密特所说是“浓浊和模糊”的而非稀薄和透明的,抵制仅仅用逻辑概念进行复述和分析,原因就在于此。(注:Ankersmit,loc.Cit.)
与雅各布森描述的诗歌话语一样,历史话语是“意图性的”,即是说,始终既是外指涉的又是内指涉的。这种意图性赋予历史话语以一种“物性”,它相似于诗歌表达,因此,试图理解历史话语何以能产生认识效果的努力都不能依据一种认识论的分析,即对历史学家的“精神”与一个“过去世界”的关系的分析,而必须依据一种科学研究,即对由语言所生产的并在语言中生产的事物与构成普通现实的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简言之,不应该把历史话语基本上看作“我们的精神机制”努力认识现实或描述现实的一种特殊情况,而应看作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如隐喻的言语,象征性语言和寓言的再现,总是意义多于字面的言说,它们总是言说不同于意味,而且,只能以掩盖世界为代价揭示世界。
伟大的历史经典之所以从来不明确“解决”某一历史问题,而总是向过去“敞开”以激发更多的研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比喻性。正是这个事实允许我们基本上把历史话语当作阐释,而非解释或描写,而最重要的则是将其当作一种书写,不是为平息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意志,而是刺激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生产更多的话语,更多的书写。如安克斯密特所说:
历史修撰领域中伟大的历史著作,如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休津伊哈、迈内克或布罗岱尔等人的著作,都没有终结历史争论,没有让我们感到我们终于知道了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切终于澈如明镜了。相反,这些著作证明是最有力的刺激物,促成了更多书写的生产——其效果是非但不能将过去置于历史博物馆的支架上,以便从各个角度审视,反而使我们疏远了过去。(注:Ankersmit,loc.Cit.)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应该把历史研究活动(历史学家对包含着过去的信息的档案的研究)与历史书写(历史学家建构的话语并把它转译成一种书写形式)区别开来。历史学家力主发现关于过去的真理,恢复已经忘记的、被压抑的或被掩盖的信息,当然,要尽可能从中获得意义。但这个研究方面实际上与记者或侦探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在完成一部书面历史之前,还要经过一些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思想的比喻方面得到了强化而非减弱。
从研究档案到建构话语,再到把话语转译成一种书写形式,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历史学家必须采用想象作家所采用的那种语言比喻的策略,赋予其话语以隐在的、二级的或内涵的意义,这要求不仅要把他们的著作当作信息来接受,而且作为象征结构来阅读。(注:Roland Barthes,The Fashion System,trans.Matthew Ward and Richard Howard (New York,1983),pp.230-232.)历史话语中包含的隐在的、二级的、内涵的意义是对构成其显在内容的事件的阐释。由历史话语产生的这种阐释赋予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序列事件以形式的连贯性,也就是虚构小说中情节结构的那种连贯性。给编年史的事件以一种情节结构,也就是我所说的情节编排的运作,是通过话语技术进行的,这些语话技术在性质上是比喻的而非逻辑的。
倘如是,如果我们要为理解历史话语如何产生其特有的认识效果,那就必须给逻辑分析加上比喻的分析。从逻辑学家的视角来看,如果典型的历史话语必须具有三段论省略式而非真正的三段论的结构,那是因为给序列事件以情节—形式的结构连贯性,和给一组事实以它所应具有的任何意义,都是由转义而非由逻辑主宰的。实际上,只有通过转义行为,而非逻辑还原,我们愿意称作“历史”的任何特定的过去事件才能(首先)被再现为拥有编年史的序列;(其次)由情节编排改造成具有可识别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一个故事;然后(第三)被建构成任何形式论证为确定“意义”——视情况可以是认知的、伦理的或审美的意义——而引证的主题。这三种比喻的不明推论式发生于每一个历史话语的写作之中,甚至回避故事讲述、仅限于对制度、对长期的、具有共时效果的、生态和族群的发展过程进行统计分析的现代结构主义的历史修撰,也离不开这3种推论。
为什么把这3种不明推论式说成是转义的呢?
首先,虽然事件可能发生于时间之中,但把事件编成特定时间单位的编年规则却具有文化特性,而不是自然的;此外,如果历史学家想要把它们建构成一个连续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他还必须为其填充特定的内容。把编年史建构成能够提供故事成分的一组事件,这在性质上是较具诗意而非科学性的一种运作。事件可能是“给予”的,但其作为故事成分的功能却是强加给它们的——而且是由性质上属于比喻的而非逻辑的话语技术强加的。
其次,把编年史的事件改造成一个故事(故事群)要求在许多情节结构中做出选择,这些结构是由历史学家的文化传统提供的。虽然常规会把这个选择限制在特定情节结构的范围之内,但这种选择至少是相对自由的。无论从逻辑的还是从自然的角度看,都没有必要控制给特定序列事件编排情节的决定,如编排成悲剧而非喜剧或罗曼司的决定。悲剧事件本来就是悲剧的吗?还是透过看待这些事件的视角而定?把真实事件编排成特种故事(或特种故事的混合)就是以转义描写这些事件。这是因为故事并不是生活中经历的;“真正的”(real)故事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故事是讲出来的或写出来的,不是发现的。至于“真实的”(true)故事的观念,这实际上是术语上的一个矛盾。所有故事都是虚构。当然,这意味着它们只能在隐喻的意义上是“真实的”,而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比喻可以是真实的。这够真实吗?
第三,历史学家不管提出怎样清楚的论证来解释编年史中事件的意义,这种论证都将是论述把编年史建构成一种特殊故事的情节的,就如同论证事件本身一样。这意味着一个历史话语的论证最终是二级虚构,即虚构的虚构,对虚构创造的虚构,它与情节的关系就如同情节与编年史的关系一样。毫无疑问,“解释”将成为关于被漏掉的事件的故事,只有概念内容(一方面是“事实”,另一方面是情节“关联”)才是逻辑处理的材料(或用技术术语来说,是自然规律推理的材料)。
结构主义的历史话语达到产生“科学”叙述的效果,更多的是依靠对以前编排成固定情节的历史事件进行比喻的情节剖析,而不是依靠像自然科学理解自然那样提供对历史的理解。保罗·利科在最近发表的《时间与叙事》中已经表明,“年鉴派”的历史学家们首先要把叙事性话语结构建构成对过去的叙述,以便使其成为特殊的历史叙述,然后再除去这种叙事性,使其成为“科学”分析。(注: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trans.Kathi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Chicago,1984),II,pp.208-225.)在历史反思中,科学地处理历史材料只能在比喻地转向既不多于也不少于可证实的认知基础时才是可能的。
历史研究从没有发生过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哥白尼革命。自然科学成功地为现代人提供了以前只是梦想的控制自然的方法,恰恰是自然科学以此为基础的声誉激发人们把自然科学的描写、分析和解释原则应用到历史上来。但是,在这样一场哥白尼革命发生之前,历史研究仍然是一个探究的领域,所选择的探讨过去的方法和书写过去的话语模式都将是自由的而不是受限制的。在历史修撰中,话语始终是、而且将依然既是受制于规则的,又是发明规则的。在任何科学领域中,只有通过转义行为背离旧规则才能制定新规则,但在历史修撰中,只能通过转义策略才能使用旧规则。这并不是说传统的历史修撰本来就不是真实的,而只是说它有两种真实:实际的真实和比喻的真实。
Ⅱ
当然,比喻的应用并不是一种语言理论,而是或多或少系统化了的衍生于新古典主义修辞学的关于比喻语言的一连串观念。(注:See Paolo Valesio,Novantiqua:Rhetorics as aContemporary Theory(Bloomington,1980),Ch.1.)因此,它提供透视语言的一个视角,由此可以对非形式化了的、尤其是实用的话语的成分、层面和综合程序进行分析。比喻的应用把注意力集中在话语的“转向”上:从一个组织层面向另一个组织层面的转向,从序列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向,从描述向分析或从分析向描述的转向,从比喻向原由或从事件向事件的环境的转向,在同一话语内部从一种体裁的常规向另一种的转向,等等。这些转向可能由逻辑证明、数学推算、统计推理、(讲故事、法律争端、政治争论等的)通用或演说规则所控制,但往往包括对这些规则的违背。一种形式化了的话语明显受控于选择和综合规则,其中的转换是可以预见的;与此不同,任何特定的非形式化了的话语,其事件发生的顺序和转向在它们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之前是不可预测的。因此,要建构叙事的逻辑甚至语法的尝试无一成功。但这些转向是可以识别的,可以据特定话语中典型的发生顺序而将其分类。
对语言、言语和话语的转义的分类是格语言学(figurative linguistics)、符号学、新修辞学和解构主义批评的一项未完成的(原则上是不可能完成的)规划。然而,新古典修辞理论识别出来的四种普通转义似乎是基本的分类:隐喻(以相似性原则为基础),换喻(以临近性原则为基础),提喻(以作为整体的一事物的各部分之间的同一性为基础)和反讽(以对抗性为基础)。这4种转义作为比喻的基础结构为我们提供了识别关联模式的范畴。在表达的范式轴上,这些关联模式把词语的秩序与思想的秩序联系起来(如“苹果”与“诱惑”),而在句法轴上则把话语的一个阶段与以前和后续的各个阶段联系起来(如“过渡的”段落或章节)。在整个话语中把词语与思想相互关联的主导模式使我们能以转义的术语描写整个话语结构。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以及与其相对应的按弗莱划分的情节类型:罗曼司,悲剧,喜剧和讽刺)为我们提供了历史话语的分类,这比就历史进程的“线性”和“循环”再现所做的传统划分要精确得多。它们还使我们看到历史话语与虚构叙事的相近性和聚敛性,这既体现在它用来赋予事件以意义的策略上,又体现在它所涉及的那种真理上。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问:那又如何呢?如阿纳尔多·莫米格连诺所说:
我为什么要关心一个历史学家是否用部分代替整体而非用整体代替部分呢?不管怎么说,我不在乎一个历史学家是否选择了史诗风格,或在叙述中引入了演讲。我没有任何理由喜欢提喻式历史学家而不喜欢反讽式历史学家,或相反。(注:Arnaldo Momgliano,"La retorica della storiadella retorica,"Sui fondamenti della storiaantica(Torino,1984),p.466.)
在莫米格连诺看来,对历史学家的唯一要求是发现真实,提出新事实,并为事实提供新的阐释。“当然,”他承认说,“为了被称作历史学家,他们必须把研究变成某种形式的故事。但他们的故事必须是真实的故事。”(注:Ibid.)最重要的只有真实的事实和阐释的合理性。用来进行阐释的语言形式和分类模式,话语的措辞和修辞,都不具有什么重要性。
但事件是否作为一个整体的任何部分以柏拉图的现实主义方式表现出来(任何一个部分如果个别看待,其意义就是不可理解的),或效仿唯名论者而把整体作为若干构成成分的总合表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从对特定组合的事件的研究中获得的那种真实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甚至莫米格连诺教授也会承认,选择笑剧风格再现一些历史事件不仅是鉴赏力的错误,而且也是对事件真实性的曲解。反讽的再现模式也同样。像反讽这样的再现模式是话语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形式——针对形式和内容发表反讽言论的人都非常了解这一点。当我以反讽模式提及或谈论某人或某物时,我不仅仅是以机智的文体掩盖我的观察。我所说的不仅仅是我的话的字面意义。以反讽为主导模式的历史话语是如此,我以其他话语方式谈论任何话题时也是如此。
同样,有些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拒绝对历史文本进行修辞分析,理由是历史文本避开了政治或社会批评所关心的更加严肃的问题。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位在历史上自觉的拉丁美洲文学批评家热内·贝尔-维拉达写道:
同时,面对国内的社会政治全景开始模糊,不那么清楚地显示“拉丁美洲”特点时,再加上一些南美的“友好政权”越来越像纳粹,美国的“批评制度”所能做出的唯一反应就是详细拟定的超文学计划,就“历史是虚构、转义和话语”的指涉性和说教性展开争论。数千名萨尔瓦多杀人小组的受害家庭可能愿意听听关于历史的其他想法。(注:Gene H.Bell-Villada,"Criticism and the State(Political and Otherwise)of the Ameircas,"inCriticism in the University:TriquarterlySeries on Criticism and Culture,no.1(Evanston,1985),p.143.)
这段话中暗指的那些家庭的确有“关于历史的其他想法”,而不认为历史包括“虚构、转义和话语”——如果他们不嫌麻烦考虑过历史的话。贝尔-维拉达教授认为他们和我一样愚蠢,如果他们有过这些想法的话。但那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所讨论的“历史”以语言、情感、思想和话语为形态,试图理解那些家庭所忍受的那种经历。在他所举的例子中,首先是政治经历,而理解这些经历的方法之一就是“历史地”思考之。但是,这种想法完全可能是转义的、话语的和虚构的(即“想象的”),甚至成为政治上的承诺或意识形态上的动机。“战斗之外”的任何立场,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都不能不同样是转义的、话语的和虚构的。忘记了那种“历史”,历史意识就将失败,在这个意义上,事件和对事件的叙述并不是发生的,而是制造的。还应该提到的是,它是由战斗的双方制造的,对于一方如对于另一方同样有效。
贝尔-维拉达关于历史意义的评论充斥于现代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之中,这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会说他们的作品由于是虚构的而不会使我们了解到真正的历史吗?或者,由于是关于历史的虚构,所以就缺乏转义和话语性吗?他们的小说由于是虚构的而不那么真实吗?由于是历史的而不具有那么多的虚构性吗?任何历史如果不利用在巴尔加斯·略萨、卡彭铁尔、多诺索和科塔萨尔的作品中发现的诗歌转义的话,也能和那些小说一样真实吗?
Ⅲ
我曾在别处提出一些论点支持上面概述的立场,以便引申地解释特定历史文本的形式说明了这些解释可能有利于理解历史话语的构成。(注:See Croce,Primi saggi.)在此,由于篇幅有限,我不再详述这些论证的细节,但概述一下批评家对此处提出的立场发表的一些反对意见将是有益的。普遍的反对意见共有4点。
对这个理论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是,它似乎使我们致力于语言决定论,或相当于一些批评家所说的语言相对主义。这种反对意见认为,信奉这种理论的历史学家似乎是语言模式的囚徒,他能动地用这种语言模式描写他的研究客体:他只能看到他的语言允许他加以概念化的东西。这种状况似乎为在研究证据的过程中可能了解到的东西设定了界限,而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学家的确不可否认地在研究的过程中改变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并在反思证据时修正对事物意义的理解。
根据相同的一般理由提出的一个类似论点是关于历史学家就他的发现所做的书面叙述问题。历史话语的比喻理论似乎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部历史著作是关于事实的报告,也就是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发现的事实,他对这些事实的真实性的看法,以及他就这些事实的原因、意义、意指或对于理解他所研究的发生领域的重要性所能提出的最好论点。历史话语意在说明,使得论点从中提出的话语的各个因素、层面和维度之间的关联是比喻的,而不是逻辑的或经过审慎的理性思考的。由于说明了这一点,历史话语便被剥夺了主张真实性的权利,被贬降到虚构的想象领域。这两种论点常常结合起来,更加简捷地宣布,话语理论不过使历史修撰成为一种修辞练习,因此削弱了历史试图提供关于其研究客体的真实性和知识的主张。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针对关于语言的比喻性质的理论以及这种理论对历史话语理论的意义的。语言的比喻理论似乎消解了比喻言语与直义言语之间的区别,把后者变成了前者的一个特例。这种理论把直义的语言看作一套比喻用法,这些比喻用法碰巧被规范化,由于约定俗成才被确立为直义的言语。因此,在某一时刻是直义的东西,在另一个时刻可能成为比喻的,反之亦然。于是,特定话语的意义便随着规则的变化而变化,这些规则是用来确定何为直义言语、何为隐喻言语的。这似乎没有把确定话语意义的权力赋予作者的意图之中,也没有给予公开表达的书面文本。而给予读者或阅读群体,允许他们随意或根据常规来理解话语的意义,这里指的是控制直义言语与比喻言语之间区别的当下常规。因此,按照语言的比喻理论,我们似乎不再诉诸于“事实”来证明或批判对现实的任何特定阐释。被看作事实的东西可能是可以无限修改的,正如被看作直义陈述的东西和被看作隐喻陈述的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一样。总之,语言和话语的比喻理论击中了事实性的要害,尤其击中了历史学家就事实的真实性提出的主张,不仅包括他们就特殊事件的陈述的真实性,而且包括整个话语的真实性。如果一个事实陈述不仅仅是以直义语言表达的个别存在的命题,而且加上为确定那个命题中何为直义、何为比喻所需的隐含常规,那么,对这种陈述就不要再取其表面价值了。如同印刷的钞票,它们只能以现行的直接价率兑换。由于这样的兑换率总是浮动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与“现实的事实”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因此,语言的比喻理论对历史数百年来声称处理事实的主张和作为一门经验学科的地位构成了威胁。
就与历史话语相关的语言和话语比喻理论提出的第三个反对意见是针对历史学家研究客体的性质的。这种理论似乎意味着,这些客体不是在现实世界上发现的(即使这个现实世界是一个过去的世界),而是语言的建构,是诗意地或修辞地“发明”出来的幽灵般的、非现实的客体,它只存在于书本之中。一句话,这种理论强调历史话语的诗歌(自我指涉)功能,意动(情感)功能,而最重要的是元语言的(编码)功能,而牺牲其指涉性(述谓)、交际性(交流)和表达(作者的)功能。(注:See Roman Jakobson,"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s,"in Style inLanguage,ed.Thomas A.Sebeok(Cambridge,1978),pp.350-358.)由于历史话语从根本上说是指涉的、表达的(表达作者就话语之指涉物的理性思考)和交流的,所以,话语的比喻理论把历史仅仅看作虚构就是不正当的。这种做法否认了话语指涉物的“现实”,用巴特蔑视地称之为“现实—效果”的东西取代之,(注:Roland Barthes,"Le discours de l'histoire"and"L'effect de reel,"in Le bruissement de lalangue(Paris,1984),pp.153-174.)而这个“现实—效果”却是一个纯粹的修辞建构。但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客体现在是(或过去是)真正的客体,历史学家有意准确地援指它们以及关于它们的真实陈述,把话语的指涉功能与其他功能之间的差异略掉,都将对现实本身的存在以及对现实进行“现实主义”再现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
如果语言和话语的比喻理论似乎削弱了历史学家关于涉及特殊的、真正的客体之事实的主张,那么,对于涉及比较一般的、集体的或程序性质的事实的主张就具有更大的威胁了。这种情况尤其与这样一个观念有关,即叙事性历史学家所讲的故事是“真实的”而非“发明的”故事。这里的“真实”是指与“真正发生的事情”相一致,而“真正发生的事情”则是一种人类生活形式,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都具有故事的轮廓和结构。比喻理论,在暗示一个故事只能是语言建构和话语事实之时,似乎削弱了关于传统历史话语模式之真实性的合法主张,这个传统的历史话语模式就是叙事。因此,在表面上削弱科学性历史学家关于科学性的主张的同时,历史话语的比喻理论也消解了传统叙事性历史学家关于提供真实而非想象的故事的主张。
最后,反对用语言的比喻理论分析历史话语的第四个意见转向了历史批评家自身话语的认识论地位问题。如比喻理论所暗示的,如果所有话语都是虚构的、比喻的、想象的、诗歌—修辞的,如果话语发明了主题而非在现实世界上发现了主题,如果只能比喻地看待话语,如此等等,那么,这难道不也适于比喻批评家自己的话语吗?比喻批评家怎样才能严肃对待自己的话语呢?或怎样希望别人严肃对待他的话语呢?比喻本身难道不是虚构吗?依据比喻所做的任何陈述难道不只是它刻意在别处发现的对虚构的虚构吗?简言之,语言的比喻理论似乎不可能成为认知上负责任的批评,惟其如此,也就破坏了批评活动本身。
Ⅳ
对于信奉直义言语与比喻言语、指涉性话语与非指涉性话语、事实性散文与虚构性散文、特定类型的话语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约定俗成的差别的人来说,这些反对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咄咄逼人的。在对上述差别坚信不移的地方,现代语言和文学理论提供的关于这些差别的可选表述就似乎是不必要的,对于历史话语的理解也不会行之有效。然而,应该强调指出,话语的比喻理论与其说消解了这些差别,毋宁说对这些差别进行了重新概念化。传统批评理论视语言的直义与比喻、虚构与事实、指涉与意图等范畴为对抗的,对一切严肃话语来说甚至是相互排除的选项,而现代语言和文学理论则视其为一个语言连续的两极,言语以任何话语的表达形式,无论是严肃的还是轻浮的,运动于这两极之间。由于话语内部的这种运动本身在性质上是比喻的,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比喻理论来引导对它的分析。
至于上述的反对意见,可做如下答复:
首先,比喻理论中并没有任何语言决定论或相对论的暗示。比喻是一门话语理论,不是关于精神或意识的理论。尽管它认为话语中难免有比喻,但这种理论试图为在不同比喻策略之间做出一种自由选择而提供必要的知识,决不是暗示什么语言决定论。它也不是像沃夫那样,认为认知是由语言决定的,话语的真实性相对于用来书写话语的语言。作为话语理论,比喻侈谈再现,但就认知却无话可说。
其次,比喻并不否认“外话语”实体的存在,不否认我们以言语援指和再现这些实体的能力。它并不认为“一切”都是语言、言语、话语或文本,而只认为语言的指涉和再现比陈旧的、直义的语言和话语观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比喻强调话语的元语言功能,将其置于指涉功能之上,因为它更关心语码,而非通过语码的特殊使用而传达的信息。由于语码本身就是自成体系的信息—内容,所以,它扩展了信息观念自身,使我们注意到话语的述行和交流方面。
第三,一切话语在政治结构上都是比喻的,这个命题说明这对比喻批评家自己的话语也是真实的。但是,这只意味着,比喻分析必须在意识到自身的比喻方面时才能具体运作。比喻理论决非暗示比喻分析是轻浮的游戏,而意在说明,我们应重新思考严肃与轻浮话语之间的区别。当比喻批评家分析文本的比喻结构时,他们谈论事实——语言、话语和文本性的事实,即便他们知道他们所用的语言既是直义的又是比喻的。他们所指的事物都是他们看到或以为在文本中看到的东西,即便他们用以指涉的语言既是直接的直义言语同时又是间接的比喻言语。那么,是否应严肃对待他们的话语,认为他们“真的意在”所言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只是因为“严肃”并不等于狭隘的缺乏想象力,“意在”并不等于只强调字面意义,而“真的”也不能解作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排除,即修辞格能以自己的方式与直义言语一样真实。
第四,比喻理论并不抹除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差异,但在任何特定话语的范围内重新定义二者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原始事实”这种东西,而只有受不同描写的事件,那么,事实性就变成了把事件改造成事实的描写方案的问题了。对真正事件的比喻描写与直义描写一样“讲究事实”,它们只不过是以不同方式——或我所说的“事实学”——讲究事实。比喻理论暗示我们不能把“事实”与“事件”混淆起来。事件是真实发生的,事实是由语言描写建构的。用来建构事实的语言模式可以是形式化了的,受制于规则的,如在科学和传统话语中的情形;它可能是相对自由的,如在每一种“现代主义”文学话语中的情形;它或是形式化和自由话语实践的综合。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比之话语的逻辑和语法模式,比喻为话语发明理论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前景。而由于历史修撰就大部分来说一直是、而且完全可能仍然是受制于规则的和自由的话语实践的综合,因此,比喻就对于理解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
比喻对分析叙事性历史尤其有用,因为叙事性历史是一种话语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种特定文化视为直义真实的东西与其典型虚构中表达的比喻真实之间的关系,它讲述的关于自身和关于别人的故事,都能得到检验。在历史叙事中,一种文化用来“想象”一种独特的人类生活形式可能具有的各种意义(悲剧的,喜剧的,史诗的,笑剧的,等等)的主导情节—形式,也依据特定的人类生活形式在过去所有过的信息和知识得到了检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过去的人类生活形式被赋予了意义,即在特定文化所生产的虚构形式中见到的那种意义,而且,这些虚构形式之于历史现实、之于我们认识历史现实的事实的“真实”和“现实”程度,也可以得到验证。历史阐释与文学再现之间的关系不仅适用于它们相互对类属情节—结构的兴趣,而且适用于它们相互共享的话语的叙事模式。
Ⅴ
正是由于历史话语运用了在纯文学虚构形式中发现的意义—生产结构,现代文学理论,尤其是以语言、话语和文本性为指向的现代文学理论的那些翻版,才直接相关于当代的历史书写理论。它相关于当代历史理论中最重要的争论之一,这就是关于叙事性的认识论地位的争论。
这次争论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持续达40年之久的一次讨论为背景,其中心议题是历史能否成为一门科学的问题。这次讨论提出了叙事的问题,但基本上是依据它是否适于科学话语的目标和目的问题提出的。争论的一方认为,如果要把历史研究改造成一门科学,那么,话语的叙事模式,由于显然在性质上是“文学的”,对于历史的研究和书写就无足轻重了。另一方认为叙事不仅是一种话语模式,而且,最重要的,也是一种特殊的解释模式。虽然叙事性解释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盛行的那种(自然规律推理的)解释模式,但却不能认为前者比后者低贱,不能认为前者特别适合与自然事件相对立的历史事件的再现,因而可以非常得体地用来解释特别具有历史性的事件。这次特殊的争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以妥协告终,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一次哲学争论终归要有个结局。它最后得出的一致见解是,叙事可以正当地用于历史修撰的一些目的,但不能用于另一些目的。
但是,这里的问题似乎刚刚解决,批评界的另一场争论便又轰然炸响,它已在另一个角落里酝酿良久,现又重新提出了一般叙事话语的隐含“内容”问题。旧的争论聚焦于叙事话语与科学知识的关系,而新的争论则强调叙事与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比如,巴特认为叙事性本身就是“现代神话”的有效内容(这里的“神话”指“意识形态”)。克里斯蒂娃(追随阿尔都塞)谴责叙事性是社会把原本自治的“个体”生产成自我压抑的、顺从的“主体”的工具。德里达把叙事作为“法律”的特权“样式”。利奥塔把“后现代状况”归咎于在性质上纯属“习惯”的“叙事知识”的垮台。最近,桑德·科恩把叙事意识作为纯粹“反动的”和“缺乏理智的”一种思维模式的化身,是人文科学中“批判”和“理论”思想的一大障碍。
然而,与此同时,叙事性的辩护者也不乏其人。诸如劳伦斯·斯通、多米尼克·拉卡普拉、詹姆斯·享利塔和伯纳德·贝林等顶尖历史学家最近都强调叙事的可用性,即便不是必然性,其理由是:“技术”历史的抽象性和缺乏亲密感把“门外汉”读者拒于咫尺之外,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是叙事。年鉴派的一些死硬分子,最突出的是勒鲁瓦·拉杜里和勒高夫,不仅开始承认用叙事再现一些历史现象的可行性,而且实际上已经公开投身于叙事性历史修撰的行动了。在文学理论家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试图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不过不是通过强调它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而是将其视作历史的“宏大叙事”,既能提供对过去的一种理解,又能为超越历史的“必然异化”提供必要的基础,而这里的历史是作为阶级压迫的故事所经历过的历史。最后,是来自哲学解释学阵营的保罗·利科,在试图综合现代西方历史思想的最具包容性的著作《时间与叙事》中,利科确立了可证实的叙事性的形而上学,证明叙事不仅可以充分地再现历史,而且能充分地再现基本的“时间结构”。
显然,这次争论涉及的不是“文学形式”的问题。职业历史学家都把叙事看作知识的门面,太枯燥致使门外汉难以直接接受。除此之外,其他人都认为叙事不仅仅是传达信息的媒介,信息完全可以用其他话语技术来传达。相反,叙事仿佛被当作了自成体系的一个信息,有自己的指涉物和完全不同于它表面上看来只是“包含的”意义。比如,詹姆逊说叙事是“人类精神的主要事例,是完全与抽象思想一样合法的一种思维方式”。(注:See Fredric Jameson,"Forward to Lyotard",The PostmodernCondition,trans.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Massumi(Minneapolis,1984).)利奥塔和麦金太尔尽管持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视角,但都把叙事的社会功能看作是知识的有效“合法化”和伦理—政治权威的主要资源。利科则认为叙事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用语言显示人类特有的时间经历。所有这些都与对叙事性抱有敌意的解构主义者相对立,巴特、克里斯蒂娃、德里达和科恩等都认为叙事是现代思想中仍未消解的神话意识的残余。一句话,叙事决不仅仅被看作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话语模式,它的内容就是它的形式,这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
从传统文学理论的角度看,话语的形式可能就是它的内容这一观点必然被看作一个悖论,要么就是一个秘密。然而,从比喻理论提供的视角看,这样一种观念根本没有什么悖论或秘密可言。一种话语形式的内容在性质上可能是语言的,将包括其主要转义的结构,这个转义被用作语言的范式,用以把事物再现为可辨认的整体的部分。根据这种事物观,可以把叙事描写为一种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提喻是主导转义,把一个总体的各个部分“牢牢掌握在一起”(希腊文:提喻;拉丁文:知识),这个暂时分散的总体要以同一性为模式越过一个时间序列,然后再次形成一个整体。这种话语模式有别于另一些模式,即一个明显整体的各个部分是由相似性(隐喻)、临近性(提喻)或对抗性(反讽或词语误用)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再现分散的事物,不管是个体的人,社会制度,还是组合事件,作为统一体的各个方面都是由它们所构成的整体的属性,因此,没有什么特别形而上的东西。我们在普通言语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种再现(不管这种普通言语是什么)。我们在哲学语言中进行这种再现,希望步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黑格尔、詹姆斯、怀海德和杜威的后尘,显示和反映现实的那些方面,这些方面就发展和表达的结构和模式来看是有机的而非机械的。我们在历史语言中进行这种再现,希望谈论连续、过渡和整合。而且,我们也在文学语言中进行这种再现,希望写出叙事性小说、诗歌或戏剧。
叙事与其说是对认知给予我们的那个“现实”(巴特的“神话”)的曲解,或存在的某一形而上理由的顿时显现(利科的“时间结构”),毋宁说是语言的多种比喻用法中一种话语形式的表象。如是观之,我们就能理解把叙事性从“严肃”话语中排除出去,或将其提高到存在、或时间、或历史性的表现高度,如此从事的项目都同样是误导的。叙事是文化的一般,因为语言是人类的一般。我们把它从话语中清除出去,就等于在法律上承认叙事本身并不存在。叙事也许是神话的灵魂,但这是因为神话是一种语言的话语形式,不是因为叙事原本就是神话。叙事与文学虚构的关系也属同理。一些文学虚构采取叙事模式,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叙事都是文学虚构。这意味着神话和文学叙事都是语言的比喻用法。
叙事与历史(以及引申意义上的一切“现实主义的”)话语的关系也属同理。一个历史再现可以采取叙事模式,因为语言的比喻性质提供了那种可能性。因此,由于历史话语采取了叙事模式,就假定它必须是神话的、虚构的、本质上想象的,或否则便“非现实”地讲述这个世界的故事。假定这一点就等于沉溺于通过联想而信奉蔓延的魔法或内疚的那种思维方式。如果神话、文学虚构和传统的历史修撰运用话语的叙事模式,这是因为它们都是语言运用的形式。这本身并不说明它们的真实性——更不说明它们的“现实主义”,因为这个观念总是具有文化的决定因素,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真的有人以为神话和文学虚构并不指代现实世界、不讲述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不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有用的知识吗?
叙事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近来的文学理论界受到特别注意,因为这是有关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问题的核心,即文学的现代主义与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对许多阐释者来说已经促成了对叙事形式和再现“历史现实”的拒绝。尤其对马克思主义阐释者来说,对一种的拒绝似乎是另一种的功能。因此,人们认为,19世纪经典小说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发现的结果,即“社会现实”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发现了社会现实的历史本质就等于发现了“社会”从根本上说不仅仅是传统、舆论和连续,而且还是冲突、革命和变化。现实主义小说是这一发现在文学中的必然表达,不仅因为它把“历史现实”当作“内容”,也因为它发展了叙事形式本来就有的“辩证”能力,以便再现特别具有“历史”性质的任何现实。因此,现代主义作家抛弃正常的叙事性就等于在形式的层面上拒绝内容层面的“历史现实”。而由于法西斯主义是以对历史现实的类似拒绝为基础的,并诉诸于纯粹“形式主义”的政治解决“现实的”社会矛盾,所以,现代主义可以是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在文学中的表达。
现在,现代文学理论内部就文学现代主义的性质的这场争论——甚至波及到后现代主义的这场争论——重新提出了人文科学中以前那场争论所提出的许多论点,这里所说的是由“历史主义的危机”所加剧的那场争论。这次危机体现为一种普遍的绝望,19世纪追求的那种“客观的历史科学”并没有作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破除意识形态的解毒剂而实现。它标志着人文科学中道德和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方法上的折衷主义的开端。在许多方面,传统的兰克式历史研究的成功都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这种研究不仅给一般的人类历史,而且给那些被认为使人性区别于“动物”本性的伦理价值、审美理想和认知结构,绘制了政治、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地图。历史知识似乎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文化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文化形式就是可以无限变化的,知识和价值就是具有文化特性的,而非“普遍的”。此外,历史知识本身决不是理解人性的关键,可能仅仅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特殊偏见。于是,人们就感到有必要建立关于社会和文化的新科学,这些新科学在规模和取向上一定是普遍的,摆脱与任何特定文化的价值的联系,而在研究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方法上也必须始终是非历史的。
这些预想的新科学所采取的形式就是新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它们是用来替代一般人文科学中陈旧的“历史主义”、尤其是替代传统历史研究的选项。历史研究中尤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能否开创一种研究方法,完全摆脱19世纪“现实主义”的幻觉,包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和历史修撰等一切形式的幻觉。
因此,在许多方面,当代人文科学内部就传统历史修撰之于“科学的”历史修撰的关系的争论相似于当下文学研究领域内流行的就文学现实主义与文学现代主义的关系的争论——而且,无独有偶,由于这两场争论中的关键问题是特定的话语形式即叙事能否充分再现特定内容的问题,这个特定内容就是“历史现实”。如果这两场争论似乎极少聚敛或融合,那是因为每一场都当然地把被另一场视为待解释的事物(explanandum)看作解释的要素(explanans)。
比如,文学研究内部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论是在这样一个观念的保护之下展开的,而且是现代主义者和反现代主义者们所共享的一个观念,即“历史”提供了一个中立的“事实”场,可以用来描写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它究竟具有哪些真正的社会或文化意义,其真正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什么。这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尤其有用,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发展的一门历史科学,旨在揭示被视为一种时代风格的现代主义的真正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历史意义。同样,历史理论内部关于传统叙事性历史的地位问题的争论也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也是叙事的支持者和反对派所共享的一个前提,即叙事是一种“文学”话语形式,文学涉及“想象的”而非“真正的”事件,因此,历史研究要么必须清除叙事,要么只用叙事制造历史现实的“细节”,以便使困惑的读者对历史发生兴趣。文学批评家把历史作为毫无问题的事实,以解决文学理论问题,而历史理论家则诉诸于他们以为毫无问题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概念,把叙事功能的问题置于历史话语之中。任何特定的知识领域都必须以至少另一个其他领域的充分实践为前提才能开展自己的事业。
但是,现代文学理论提供的历史书写的视角,比起关于叙事话语性质的争论者们提出的视角,或关于历史知识的性质的争论者们提出的视角,都更具包容性。历史话语(与历史探讨相对立)是一般话语的一个特例。因此,历史话语的理论家都不可能忽视现代文学理论内部发展的一般话语理论,这种话语理论的基本概念是语言、言语和文本性,它们就文学性、指涉、作者、读者和语码等传统观念进行了重新表述。这不是因为现代文学理论为语言、言语和文本性等新概念提出的问题提供了明确的回答,相反,恰恰因为它重新给探究领域提出了问题,而在这样的探究领域里,至少在历史理论方面,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以为没有什么问题可言了。
在1972年发表的题为《交流》的一篇文章中,巴特指出,现代人文科学需要的那种跨学科研究与其说要求一些既定学科以便分析传统上定义的研究客体,毋宁说发明一个不属于任何既定学科的新客体。巴特主动提出把现代经过语言—符号概念化了的“文本”作为这种新客体。如果领会了这一建议的含义,我们就能掌握现代文学理论,从而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对历史书写加以理论化。其最重要的含义之一是,我们再不能把历史文本当作毫无问题的、中立的容器了,再不能认为这个容器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是由位于其限域之外的一个“现实”给予的。我们不必像巴特当时走得那样远,把文本分成“读者的”和“作者的”两种,然后提出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特殊的、伪装的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启示用法恰恰产生于它对新的研究问题的标识功能,而非作为对旧问题的解决。然而,我们或许希望探讨历史书写在何种程度上用作“读者的”文本的特权场所,并为所有推论的“现实主义”话语提供一个范式。
巴特本人在一篇题为《历史的话语》(1970)的文章中也提出过相同的建议。他在文中指出,当代科学的历史修撰已经放弃了对“真实”的探求,而热衷于更谦虚的、最终是更“现实”的任务,即把历史表现为“可理解的”。在发展他自己的话语理论的这个阶段,巴特认为,这导致了对“叙事结构”的抛弃。他认为,由于叙事是在“虚构的坩埚(神话和早期的史诗)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它本来就不适于作为“现实的符号和证据”,无论在什么话语里。
在巴特看来,现代科学的历史,也就是“年鉴派”的结构主义的历史修撰,在对“可理解性”而非“真实性”的兴趣上相似于文学的现代主义。但是,如果情况确乎如此,那么,不言而喻,“结构主义”历史就与传统历史一样是“现实主义的”。此外,如果问题在于“可理解性”而非“真实性”,那么,叙事在生产话语工具性方面就如同每一种科学的历史修撰所热衷的论证模式一样有效。
然而,巴特所说的结构主义历史与文学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的确对我们理解它们对叙事话语抱有的表面上的共同敌意具有深远意义。我说“表面上的”,是因为现在已经能够认识到文学现代主义并非真的那么拒绝叙事性、历史性甚或“现实主义”,而恰恰探讨其在19世纪的特殊形式的局限性,揭露这些形式在高雅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主导话语实践中的相互共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现代主义揭示了叙事话语本身新的或被忘却了的潜力,即把现代特有的时间经验、历史意识和社会现实表现为“可理解的”。文学现代主义并不拒绝叙事话语,但在叙事话语中发现了一个语言的和比喻的内容,它足以再现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只是19世纪文学和历史的现实主义所隐含地看到的。文学现代主义的“形式的内容”足以再现我们希望称之为“现代”的那种历史生活的形式和内容,这说明了文学现代主义对于现代历史话语的重要性。
我认为,这还说明了现代文学理论对我们理解从事历史思想、研究和撰写的理论家们所争论的问题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现代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是出于理解文学现代主义,确定其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的历史特殊性和意义,开展一种适于研究客体的批评实践的需要而被建构的,还由于一个根本原因,即现代文学理论有必要成为关于历史、历史意识、历史话语和历史书写的一门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