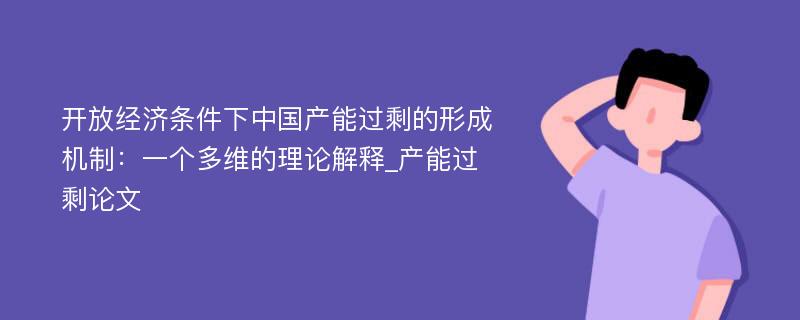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产能过剩的生成机理:多维视角的理论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条件下论文,机理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4-0020-05
一、问题的提出
产能过剩是指一定时期内某一区域(产业或产品)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能力超越了市场有效吸纳水平的一种经济现象。国际上通常以产能利用率指标来加以衡量,如美日都将产能利用率较长时间低于78%界定为产能过剩,我国则通常在考量综合产品库存、产销比率、产品价格回落、行业亏损面、企业破产数量、贸易受阻和摩擦六个指标变化的基础上加以鉴定。产能过剩与生产过剩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前者的度量侧重于生产潜能,后者的评价侧重于生产结果(李江涛,2006);前者往往是导致后者出现的直接原因,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市场反映。
从辩证和动态的角度看,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都是一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常态,并成为该国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尽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分析认为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产能过剩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即适度的过剩能够促进竞争,强化企业的创新动机,并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利,但从经济运行的实践来看,产能过剩不仅加大了资源耗费和环境成本,而且也会进一步诱发市场秩序和产业链的紊乱,甚至还会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格局。因此,着眼于当今开放型经济的运行实践,系统地剖析产能过剩的生成机理就显得格外必要和迫切。
二、中国产能过剩生成机理的相关研究
早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蔓延期间,因前期投资的累积效应和需求的突然萎缩,我国以消费资料制造为代表的部分行业就呈现出生产过剩的现象。而自2003年步入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之后,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更趋突出,并于2008年起渐次达到高峰。由于此后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造成我国出口的大幅下滑,产能过剩的矛盾变得进一步突出。
产能过剩现象的陆续蔓延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受到了国内许多专家学者的认真关注,他们在相关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对于我国产能过剩生成机理或原因的相关研究来看,除了少量成果立足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尚鸣,2006)、厂商的窖藏行为(何彬,2008)、需求抑制(赵健,2008)、市场供求失衡(田娟等,2008)、企业认知偏差(张新海等,2009)、信息不对称引致的预期偏差和失误(周劲等,2010)、经济危机(兰日旭,2010)等因素外,大多数研究都建立在政府主导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这一前提下,并将投资膨胀与政府过度干预作为中国式产能过剩生成的直接原因。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以下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了国民经济的过剩运行(刘诗白,1999);重复建设与体制转变、市场有效需求和资本积累共同酿成了产能过剩(汪同三等,2001);行业投资过度、有效供给不足和即期消费乏力是造成我国主要行业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梁金修,2006);投资持续过快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的严重失衡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王小广,2006;闻潜,2006);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由民间投资需求和热情的释放而引发的(袁钢明,2006);进退机制的不对称致使投资不断累积是造成严重产能过剩的原因(周其仁,2005);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所引发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盲目投资是产能过剩的主要诱因(罗蓉,2006);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过度干预与粗放式增长、外资进入共同构成了产能过剩的原因(国经文,2006);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缺乏必要与恰当的调控引导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易培强,2010);地方政府的传统思维、信息指导缺乏与宏观调控失当以及产业结构失衡、逐利竞争与业绩攀比机制、经济危机推动了产能过剩的出现(王志伟,2010);等等。
尽管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为剖析中国产能过剩的生成机理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与思路,但理论解释的路径还显得较为狭窄,而且大多数分析论证仅局限于国内变量的引入,与开放型经济的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从多维视角对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的生成机理进行更为系统的思考,不仅是进一步丰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需要,而且对于深化产能过剩问题的认识并寻求有效的防治策略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诠释产能过剩生成机理的多维视角
(一)基于国民收入均衡理论的解释
根据凯恩斯主义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均衡条件理论,无论是一国经济总体还是一个特定的产业部门,外在表现为供求失衡的产能过剩现象或在内部有效需求(消费性需求、投资性需求、政府公共需求)抑制、出口减少的情况下产生,或在投资(政府投资、私人投资)膨胀、进口供给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也可能是在二者合力共振之下生成。
1.开放条件下的投资规模膨胀
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经济运行轨迹表明,具有刚性特征的投资是产能扩张中最为重要、最具功效的驱动力量(张新海,2010)。投资对产能扩张的驱动作用不仅直接表现在其投向的产业领域,也会通过示范效应和产业链的传递效应引发其他产业部门的投资扩张,由此极易诱发轮番追逐下的投资“大跃进”和产能急速扩张后的过剩。在开放型经济中,投资对产能扩张的驱动作用还来自于外来资本输入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产业转移,尤其在东道国内部市场分割、各自为政的盲目无序引资和低水平产业重复引进的条件之下,内外产能的叠加致使过剩现象更容易滋生。同时,内外资的投入还会产生相互“激励”效应:一方面,东道国为了增强利用外资的区位优势,往往会在基础设施以及相关产业综合配套能力的建设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并通过市场信号与产业链的传递,刺激内资追加,吸引外资介入,二者的联动加速了经济总体或特定产业的产能扩张;另一方面,在投资冲动和“崇洋”心理的惯性作用下,外资的进入也会引诱国内投资者的非理性跟风,从而进一步助推了更广范围的产能膨胀和更高程度的产能过剩。
2.开放条件下的消费抑制或转型
市场需求是厂商进行生产经营决策和资源调配的风向标,实际产能利用率的高低将首先取决于市场需求能量的变动状况。由收入水平、相对价格、消费观念等因素引发的需求变化既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产能显现不足,也可能酿成另一部分产能的过剩。当需求趋向萎缩时,即便先前处于正常状态下的产能也会变得相对过剩;需求萎缩持续的时间与幅度将决定产能过剩的周期与程度。当需求呈现转型升级时,一方面会出现面向高端需求的产能不足,另一方面则会出现面向低端需求的产能过剩。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进出口贸易分别构成了一国总需求的抵扣和增加部分。鉴于外部市场需求更具多样性、易变性以及易受各种贸易壁垒的干扰,出口导向型经济中产能利用的波动性会更加突出。当外部市场消费者预期改善、偏好相对稳定、需求趋盛引致本国出口扩张而进口平稳或缩减时,国内产能过剩现象可变得弱化,甚至会消失;反之,产能过剩现象必将凸显。此外,开放条件下的消费文化交融和消费行为模仿使消费者偏好也具有国际传导性。外国高消费或超前消费的示范作用不仅会使国内产业结构相对滞后于消费结构,而且还会驱使进口需求的增加,从而诱发国内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出现。
(二)基于产品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解释
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Gort等(1982)的产业生命周期“G-K模型”尽管在研究对象、目标及应用领域等方面存有差异,但它们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及相似的阶段划分和曲线形状,从中也清晰地描绘出现实经济生活中产能过剩生成的轨迹。
在产业引入期和产品导入期,供求均处于较小规模状态,呈现出卖方市场的特征。在产业大量进入期和产品成长期,企业的大量涌入使产业总体规模扩张较快,但处于总体均衡状态,产能利用率逐步上行。当进入产业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后,产业扩张趋于平缓(后期转向下降),处于相对稳定阶段,产品供求规模逐步攀升至顶峰,且呈现买方市场特征,产能利用效率经峰值后开始下滑,产能过剩现象逐步显现。一旦进入产业衰退期后,市场需求出现明显萎缩,产能利用效率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程度更趋严重(张会恒,2004)。
开放型经济中,全球资源流动性的加强打破了传统的要素禀赋边界,要素瓶颈制约相对弱化,企业的新建或扩建更趋容易。无论是来自利益的诱惑还是出于竞争战略考虑,产业外部的各类主体随时都会蜂拥而入,产业内的已有主体也会伺机竞相扩张。而且,受多边制度安排与本国开放承诺的约束,原有的各种准入门槛大大削减,国际资本流动及其相伴随的产业转移也更加活跃,外资的不断涌入和国际转移产业的大规模承接为国内产业的成长进程又添加了外部力量的助推,产能膨胀的速度和程度势必得以明显提升。因此,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大量进入期不仅较封闭条件下前移,而且进入期的时间跨度也将会大大缩短,从而导致整个产业生命周期演进速度的进一步加快,产能过剩也势必更容易提前和频繁显现。
(三)基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
Schumpeter(1934)指出,创新或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带动了投资的大规模进行。Solow(1957)则把技术进步视为独立因素和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变量。Romer(1990)、Lucas(1988)等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保持增长的决定因素,知识、技术进步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综合运用能够突破增长的极限。Nelson等(1997)认为,新技术的改进和扩散使整个产业的生产率上升,产业结构变迁是技术进步推动的直接结果。上述经典理论系统解析了技术进步导致产出规模扩大和产出效率提高的内在机制,对产能的扩张与过剩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伴随着技术的引进、学习、应用以及对生产方式、工艺流程等的革新改造,既定要素效率的提高也将会激发产能扩张(宋晓舒,2009)。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还会衍生出新的替代行业与产品,或催生出延伸性行业与产品,从而进一步驱动产能总体规模的扩张。在开放型经济中,技术进步的渠道更为广泛。虽然以合同交易标的进行的技术转让还时常会受到更为严格的管制,但通过技术许可方式以及在国际资本流动、国际产业转移、进口贸易、合作研发等活动中产生的技术溢出则愈加频繁和广泛。而且,跨国公司的创新理念传播、当地科技人员培训以及研发活动示范等也将促进东道国自主创新活力的激发与科技成果的诞生。开放条件下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使既有投入的产出效率提高以及产业产品的快速更新延伸成为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产能过剩显现的机率与频次也会由此提高。
(四)基于市场外部干扰的补充性解释
外部干扰性事件不仅会直接诱发市场供求的过度失衡并导致产能过剩的形成,由其产生的刺激与助推作用也会使产能过剩的出现在时间上更加提前、在范围上更为广泛、在程度上更趋严重。从实践来看,外部干扰性事件大体上可归纳为灾难性事件和政策性事件两类。
1.灾难性事件影响
自然灾害、战争、经济危机等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经济系统原有的正常运行秩序,导致生产供给与需求吸收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由于此类事件固有的突发性,各类主体的非理性行为表现得较为突出和普遍。特别是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减少甚至缺失的情况下,收入预期及消费倾向都会产生重大改变。伴随着由此引发的需求吸收能力的萎缩,产能利用率快速趋向下降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之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间经济关联性的增强和市场融合度的提高使风险传递的机率和速度大大提升。一旦有影响力的主要经济体或主要目标市场国发生经济危机等灾难性事件,就会通过投资、贸易、金融等渠道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传导,并在各类主体悲观预期的影响下,引发国内外需求吸收能力和本国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丁世勋等,2010)。
2.政策性杠杆作用
政策调控对产能变动的影响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种情形:(1)通过政策作用于市场并形成市场信号,使市场行为主体改变现状认识和未来预期,进而对投资与消费决策以及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2)通过投资、信贷、外资利用、对外投资等政策调节资本形成,并配之以产业、贸易政策对资本的注入规模、结构加以导向和助推,从而影响产能变动的轨迹;(3)在以价格、税收等收入再分配政策影响国内消费需求总量和消费倾向的同时,以外贸、外汇政策干预进出口贸易,通过调节国内外市场的吸收水平来影响国内产能利用率。实践表明,当施行的政策总体具有激励性倾向时,产能扩张即会呈现加速态势,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反之,则相对较低。而当面向产能供给的政策激励过多,产能吸收缺乏政策刺激时,就会形成产能的单方面扩张,最终导致产能过剩的出现。由于外部市场需求更具波动性,海外投资环境更具不确定性,并且往往还受制于目标市场国的政策干预,因此,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产能调控的精确性、成效性目标更难以实现。一旦国内政策调控偏向或滞后,或受外部抗衡而政策失灵,产能过剩将会随之出现。
以上分析表明,产能变动受制于产业、贸易、技术、资本、需求和突发性事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或交替影响,我们不能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某一经济变量,而应立足于不同发展背景下多维变量系统效应的观察与评估。
四、对防治产能过剩的重要启示
(一)产能的监测调节应立足于多维面向
产能过剩生成原因的多维性、复杂性特征决定了产能监测调节的系统性、动态性要求,也指明了产能预警监测窗口和产能调节的切入点所在。惟有真正破除部门利益界限和信息流动限制,才能确保产能监测的连贯性、整体性和产能调节的协同性、效率性。若仅局限于关注某一时点上特定产业领域的投入产出、生产销售、市场供求等表观,就容易陷入重标轻本、顾此失彼的困境之中。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孤立狭隘思路与做法不仅不能真实地反映和有效地调节产能变动,反而可能因片面的信息与静态的表象错失调节的有利时机,或偏离调节的重点和着力点。而扭曲无效的监测调节将致使产能在不断延续的膨胀与累积之后呈现出过剩,这也是产能过剩现象经常循环往复甚至成为顽疾的主因之一。
(二)防止产能过剩需内外协调、双管齐下
开放条件下,引发产能变动的各种变量在国际间的传导更加频繁,其效应的发挥往往也是在国内外交错互动过程中进行的,因此,防止产能过剩既要建立在对内部变量有效调控的基础上,也有赖于对外部变量影响的积极干预。在遏制投资膨胀方面,要借助投资管理信息化系统和项目论证审核制度,加强对国内新增资本投入和外资引进项目在产能增长与市场吸收方面的评估,在保持国内投资适度规模和扩张节奏的同时,严格控制低水平、重复性外资利用项目的进入和产业承接;积极推进对外投资,输出膨胀产能,使国内产业成长和产能扩张保持在有序适度的状态之中。在提高产能消化吸收水平方面,既要不断激发内需潜力,并减少内需的外向化转移,还要不遗余力地开拓外部市场需求。此外,还应密切关注国外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变化、政策动态、发展趋向等,加强风险预警系统和应对预案研究,提升抗御外部干扰性事件影响的能力。
(三)治理产能过剩需兼顾市场修复和政策推进
产能过剩的生成不仅与各类主体的行为直接相关,也与一定时期内的政策导向(包括误读、偏离、失效等)密不可分。尽管市场在其内在规律的作用下亦可逐步实现自我修复,但或多或少都会遭遇一些利益主体或相关利益集团(如生产者、产业部门、地方政府)的抵抗,由此可能会引发更高的时间成本与效率损失。况且,产能过剩的治理有对外转移、转型升级和淘汰落后等诸多路径,为避免冲动惯性下的盲目跟风和市场的剧烈波动,维护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的正常秩序,产能过剩治理也需要统筹决策、有序部署、稳步推进。可见,无论从生成原因、实现效率,还是从治理路径的选择与组合来看,基于市场与政府的合力是加快产能过剩治理进程的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