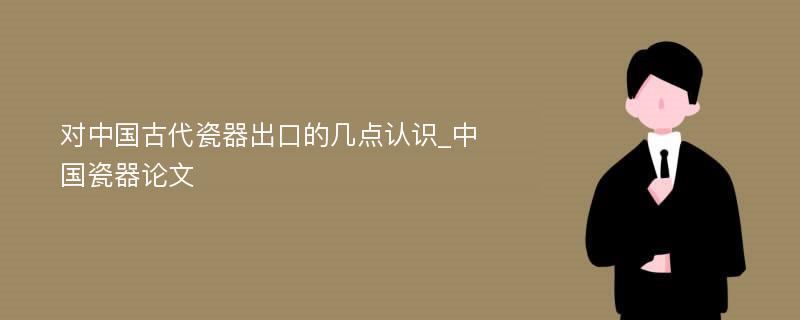
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瓷器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上半年,笔者应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林业强教授邀请在该馆作访问研究,主要考察对象是郑德坤先生捐赠的瓷器。郑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开始关注邛窑瓷器并力图建立四川地区古代陶瓷发展史纲①,为我国现代瓷器研究主要的学科奠基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郑先生先后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因教学之需,郑先生在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地收购了大量中国古代陶瓷器,为进行比较,还收购一些越南、泰国、柬埔寨、伊朗等国家生产的陶瓷器,并把这些陶瓷器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现以郑先生的堂号命名为“木扉瓷器”。
由于木扉堂收藏的中国瓷器均购自海外,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称长期保存在中国境外或在中国境外出土的瓷器为“外销瓷器”,所以我们的研究自然以中国古代瓷器输出、中外瓷器文化交流为出发点,从世界瓷器文化史的高度来审视中国古代输出瓷器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木扉瓷器之个体,并体会其价值②,这也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看重和想让学生了解的知识③。
以往对中国输出瓷器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输出瓷器的类别和年谱、输出区域,以及输出瓷器对世界青花瓷器和青花陶器生产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中国输出瓷器产生的文化影响等诸方面的研究,无疑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④。近年来更有学者把中国明清时期输出的丝绸、瓷器、家具、绘画等所有商品,视作当时中国输出之艺术的载体⑤,使研究走向深入。但是,回顾研究的历程,还有诸多问题尚需探讨。如以“外销瓷器”通称在当代中国行政版图以外出土或传世的中国瓷器是否恰当;中国古代瓷器输出的范围,是否是以中国人航海能力发展的进程而逐步扩大,抑或是另外一种情形;除从事生产外,中国人在瓷器输出中还起到了什么重要的作用;中国输出瓷器是否一直以中国文化为主导,还是有阶段性变化;再如,当我们从物质文化交流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输出的瓷器时,发现过去的研究重点只是放在输出或输入,而没有视之为古代世界瓷器发展史的内涵,并在通史的范畴内探讨中国输出瓷器的意义。同时,如何从物的层面探讨输出者行为的动机和执行者所带来的变化,并在当时的语境中界定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关系,都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所在。
一 关于研究对象及其概念之厘定
输出瓷器以往被中国学者称为外销瓷器,日本学界称为“贸易瓷器”,西方学者则习用export Porcelain⑥ 和Chinese Trade porcelain⑦ 两种说法。但是,这些概念是否准确或者全面,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分析。
第一,由于古今世界的政区格局不同,中国的疆界也有很大的变化,历史上瓷器输出与内销是以各时代之疆界而论,所以,以当代中国版图为界论定在当代中国境外发现的瓷器并称之为外销瓷器便不确切。如在唐朝以前和明代早期一段时间内,今越南北部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上述两个特定历史时期内输往该地的瓷器显然和输往中国各地的瓷器具有同一性质。同样,元代瓷器输出情况也很复杂,蒙古喀喇和林遗址出土大量元代瓷器,和林是蒙古人在漠北时期的王廷,这些瓷器大多是元朝统一中国后从内地带到和林,属当年元朝宫殿用器之一部分⑧,现该地虽不隶属中国,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些瓷器为元朝宫廷用瓷的属性;当时输往伊儿汗国的瓷器,一直被称学术界视为研究中国外销瓷器的重要标本,这其实也是以现代人的国家概念错误地界定古物。新疆伊犁霍城阿力麻里出土有元代青花、龙泉窑、磁州窑、青白釉、钧窑瓷器⑨,阿力麻里是察合台汗国东部汗王廷所在地,所以这批元代瓷器当与察合台汗国有关,于古于今显然都不能称为外销瓷器。同理可推,与其性质相同的、当年从元廷输往伊儿汗国的瓷器也不是外销瓷器。从古今行政版图变化和以上例证可知,以外销瓷器的概念称长期保存或出土于当代中国版图以外的瓷器并不合适。
第二,在古代中国人的概念和记载中,输出瓷器的性质和目的是多样的。纯粹作为外销商品输出的瓷器,当然可以称为外销瓷器,但只是不同性质的输出瓷器中的一种;中国皇帝或中央对外国君臣的赏赐用瓷器,这部分被称为“赏赉瓷器”(其细微差异,下文再予评述)⑩;还有中国政府为获取对方的物产而把瓷器作为交换物之一的以物易物性质下的交换瓷器,这部分瓷器虽然以商业为目的,但具有政府控制下的输出性质,也不能简单地称为外销瓷器。
第三,对比当代中国版图以外与中国内地所见同一历史时期的瓷器,大多数情况下看不到明显的不同。如近在咫尺的菲律宾和远在天际的非洲肯尼亚东海岸所见中国瓷器,包括了从唐代以来至明清的各种名瓷,如越窑、长沙窑、邢窑、定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元明青花、明清彩瓷等,和内地考古发现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器物类型上看不出内销和外销的差别。倘若一定要按行政或地理区域划分或定名,则必然会有与外销瓷器对应的内销瓷器的概念,和次一等级的江北瓷器、江南瓷器等以地域命名或以省区命名的多重瓷器概念,显然没有必要。
第四,由于疆界变化,当代中国的部分地区在历史上只是中央王朝的藩属甚至是敌对政权,流传到这些地区的瓷器对古代中央王朝是输出,但在今天则不能称为输出。在南北对峙时期,瓷器等商品在敌对或友好王朝间的交流也很常见,对这些王朝或王国来说,这种情况和与中国以外地区的交流与输出并无不同,如在北朝区域内发现的南朝青瓷、在辽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宋瓷、在金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南宋瓷器和在南宋临安城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等,都是当时各政权间交流与输出的结果。这一类瓷器显然和各个政权行政区域内的瓷器流通性质和方式有所不同,也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第五,历史上纯粹以商业为目的输出瓷器,可以使用外销瓷器的概念。但其情况也相当复杂:有品种、质量及产地都和内地市场销售的瓷器完全相同的;有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窑场模仿内地各名窑场生产多用于销往海外市场的,在质量上与内地的产品有明显的差别,但这种差别是商品价格决定的还是由销售地文化决定的,也值得研究。上述的这些外销瓷器和再后来西方商人的订货和中国窑场照来样加工并销往海外的瓷器,性质并不完全相同。
虽有上述的不同,但输出的性质则是共有的。为了能全面地概括中国古代因不同需要输出之瓷器,改变并弥补过去所用的外销瓷器、贸易瓷器等概念的缺陷,本文称在历史上输出到中国行政版图以外地区和国家的中国瓷器为“输出瓷器”。也可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已有学者在研究16世纪~20世纪东南亚地区所见瓷器时已开始不使用传统的概念,只是注重其生产地和瓷器风格(11)。
二 从中国角度看瓷器输出
以中国为本位看各历史时期的输出瓷器,在性质上大致可以把这些瓷器分为以下几类:
1.政府外交用瓷器
政府外交用瓷器即中国文献所说的赏赐瓷器,现称之为“赏赉瓷器”。出土于境外最早的瓷器是韩国武宁王陵随葬的南朝青瓷器,有可能是中国南朝皇帝赏赐给武宁王的。但对外赏赐瓷器多发生在元明清时期,正是中国瓷器普遍为外国赏识、认同或渴求的时段。赏赐对象有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各古国,以及后来的欧洲各国。
根据霍布逊的研究,伊朗阿德比尔神殿旧藏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皇宫旧藏明代早中期的官式青花瓷器,是万历以前诸帝赏赐给伊尔汗国或萨发维王朝的,万历皇帝也赏赐瓷器给莫卧儿帝国(12),而这些赏给伊朗的瓷器在后来又被奥斯曼帝国掠夺为战利品(13)。
据载,明代得到赏赐瓷器的国家有朝鲜(14)、琉球(15)、占城(16)、真腊(17)、暹罗(18)、撒马儿罕、失刺思、哈蜜(19)、失剌思(20)、日落国(21)等,清代受赏赐的外国有朝鲜(22)、琉球(23)、暹罗(24)、廓尔喀(25)、俄国(26)、西洋国教王(27)、葡萄牙(28)、英国(29)、荷兰(30)等。光绪二十四年传旨九江关监督烧造“赏用外国王饭食应用白地五彩西莲”海碗、大碗、中碗、小碗、九寸盘、七寸盘、五寸碟、三寸碟、酒盅共七百二十件(31);光绪二十五年共“预备上传赏用外国王饭食应用白地五彩西莲”海碗、大碗、中碗、小碗、九寸盘、七寸盘、五寸碟、三寸碟、酒盅共二百六十件(32);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皇太后致赠日本国皇帝、皇后五彩瓷瓶一对……皇帝致赠日本国皇帝青花白地瓷瓶一对”(33)。从光绪的外事活动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皇帝所谓的“赏赐”,也就是外交中的“致赠”。
2.官府贸易瓷器
官府贸易瓷器,是对外贸易瓷器中的极小一部分,主要见于元代和明代早期。元代的官府贸易,是以官府资本为主进行的,用官船和官府资金并派遣官员进行海外贸易(34)。明早期,对外贸易以中国皇室垄断为特点,外国人来华以朝贡贸易为主。洪武七年冬,刑部侍郎李浩以陶器七万、铁器千至琉球买马,得马四十匹。洪武十六年赏赐占城、真腊瓷器各一万九千件,数量之巨为历代赏赐所无,恐怕也是以物物交换为目的。永乐二十三年仁宗皇帝即位诏书载:“往迤西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买马等项,及哈密取马者,悉皆停止。将去给赐缎疋、磁器等件,就于所在官司明白照数入库”,说明到永乐时期以瓷器为交换物从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换买马匹的做法仍然存在。这种以瓷器和丝绸进行的物物交换,极可能是明代早期官方对外贸易的常态。缘此,就不难理解以郑和为代表的庞大官方贸易使团出现与出海的历史及社会原因。
以郑和船队为代表的官府贸易使团到了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地区,和非洲东海岸的埃及、索马里、肯尼亚、莫桑比克甚至是南非等地(35),船队下海前准备的物资中就有瓷器、铁锅等(36)。当时,通过瓷器及其他物品的出口为国家换取了大量的珍贵木材、香料、西洋布等国外产品(37) 和马匹(38),国家也收到了极大有经济效益(39)。
3.民间对外瓷器贸易:合法与走私双重形态
历史对外贸易是以民间贸易为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因国家政策的变化,民间贸易分为公开的、受政府鼓励的正当贸易和政府禁止的走私贸易两种。
唐代是中国瓷器最早大量输出的时期,在今天的日本、朝鲜、菲律宾、伊拉克、埃及、肯尼亚等地区都出土有唐代瓷器。当时输出的瓷器有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瓷器、巩县窑白瓷、唐青花、巩县窑和邢窑的白釉绿彩、唐三彩器物等。
观察菲律宾(40) 和肯尼亚各遗址所见情况,唐代以后中国输出的瓷器有定窑、耀州窑青瓷及仿耀州青瓷、青白瓷及仿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及仿龙泉窑青瓷、元青花、明清青花、明清彩瓷等,说明从唐代开始瓷器输出一直不曾中断。由于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不曾有如此长时间、广泛的赏赐瓷器的可能,再加上唐、五代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比较频繁、且南宋和元代又都实行鼓励自由贸易的政策,所以推定这些输出瓷器是以民间自由贸易的形式实现的。
明代海禁时间虽长,但在隆庆元年月港对外贸易合法化(41) 后,福建地区的对外贸易得以急剧发展(42),从月港输入中国的外国产品多达一百余种(43),大致可以分为名贵木材、香料、药材、装饰用物、粮食和奇异食品,也有钱铜、黄铜、乌铅、皮革等国家军事物资,以及交趾绢、土丝布、粗丝布、西洋布、东京乌布、白琉璃盏、琉璃瓶等外国名品。那么,中国是用什么物资从外国换回如此利润呢?明人的记载是:“民间醵金发舣艎,与诸夷相贸易,以我之绮纨、瓷,饵易彼之玳、香椒,射利甚捷,是以人争趋之。”可知当时中国输出的主要是丝织品和瓷器。
该时期走私方式的瓷器贸易虽为中国禁止,但在其他国家看来,走私的性质并不存在。瓷器走私在洪武时期已经开始,政府虽屡有禁令(44),但走私贸易却有增无减(45)。见于西方文献,1515年(正德九年)“中国商人亦涉大海湾,载运麝香、大黄、珍珠、锡、磁器、生丝及各种纺织品如花绫、绸缎、绵襕等甚多,至满剌加贸易”(46),走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同时,有条件来华的外国人也不惜违禁购买瓷器。永乐二年五月,琉球国山南王使臣曾违法至处州购买磁器(47);正统六年闰十一月,又有琉球国官方走私瓷器往爪哇国的事件(48),由于琉球并无烧造瓷器的能力,其载往爪哇国的瓷器必然是来自中国的走私品。
三 瓷器文化的交流与普及——看待输出瓷器的新视角
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瓷器交流,所以便不可避免的用现代国家的观念来理解这些中国瓷器,对原产国来说就有了输出的概念。但是,当我们把中国输出瓷器放在世界范围内看,不再以中国为中心发言时,就发现输出或外销的概念并不强烈。如果不考虑行政疆域,仅以陶瓷作为一种工艺品的传播形式,又会发现中国瓷器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存在如上古同一类型的陶器分布一样,代表了文化的流布及影响所及。所谓的输出,只不过是瓷器使用地域的扩大,是人类陶瓷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下面从瓷器输出的时间、空间及交流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瓷器的输出区域
从已知情况看,在南朝时期瓷器已输出到朝鲜半岛。唐代中国瓷器输出空前发展,输出地区也大大增加,在东亚、东南亚、西亚、东非海岸和北非的古代遗址都有中国唐代瓷器出土。但是,直到明代中期西方人开辟新航路并成为海上主导力量以前,中国瓷器输出的地域基本再没有向更大的地域扩展。
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相继东来,除了他们在东南亚、东亚各地从事的转口贸易加大和促成了中国瓷器在各地的影响和广泛使用外,中国瓷器也被他们运到了南非、西非和欧洲、美洲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是此前中国瓷器不可能到达的新市场。
(二)中国参与世界陶瓷文化交流的内容
中国参与世界陶瓷器文化交流的努力自古以来就存在,且这种交流并非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具有双向交流的特点。
据研究,在中国南方各地、东西伯利亚、日本列岛发现的上古制陶技术,大约是在中国江南地区出现以后渐次向周边传播的,而并非各地各有源头(49),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陶瓷生产技术自创始之日起已处在一个对外交流的进程之中。
和陶瓷器相关的从西亚经印度、中亚地区不断输入中国的有玻璃与玻璃生产技术、琉璃与琉璃生产技术、低温彩釉生产技术等。尤其是经大月氏人、粟特人持续传入中国的低温彩釉技术,更是影响到了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先后发展出北朝的白釉绿彩、唐三彩、唐青花等瓷器品种(50)。元代青花瓷器的出现虽不是唐青花直接发展的结果,但如唐青花是受中西亚技术和绘画原理影响而产生一样,元青花也是中国制瓷技术和中东地区的青花陶器技术的结晶(51)、是使用中东所产的钴为绘画颜料(52) 的结果。
元代珐琅器已传入中国,明代珐琅器是御用监的主要生产品种之一,而在清代康熙、雍正二帝的追求下,又从欧洲引进珐琅彩原料并在瓷器上绘画,这类瓷质的珐琅器被称为“珐琅彩瓷器”。事实上,约在同时或稍早,西方先进的珐琅彩技术也在广东地区落地生根,这或与十三行在广州的生产、销售有关(53)。在清宫的努力下,珐琅彩技术和原料被推广到景德镇地区窑场,产品即文献所说的“洋彩”瓷器,到光绪时期这种洋彩开始被称为“粉彩”,最终完成了珐琅彩技术从引进到消化、再到本土化的全部进程(54)。
至于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向外传播,当晚于瓷器之输出。瓷器输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瓷器文化和制瓷技术的传播,所以最早试图学习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地区也是最早接触到中国瓷器的地区。从唐代开始越窑青瓷生产技术和三彩生产技术已传播到高丽和日本,在长时间内中国的制瓷技术更是不间断地向朝鲜半岛传播。约在五代时期,伊拉克地区已开始用其传统的锡白釉陶器仿烧中国邢窑的瓷器。明代,龙泉窑青瓷、青花、五彩瓷器生产技术的已传至日本、越南、泰国、波斯等地区,越南在明朝早期已能仿烧高水准的青花瓷器、泰国在仿烧龙泉窑瓷器的同时,把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发展成釉下褐彩;而日本在明朝晚期从中国学得了青花、五彩瓷器的先进工艺,部分地改变了中国瓷器独领风骚的局面。当波斯地区学得青花瓷器的生产技术后,通过产品的传播影响到土耳其、叙利亚地区的瓷器生产,余绪波及欧洲,更使得中国瓷器生产技术和瓷器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可能。故而,在《帖木儿的餐具》(55) 一书中,作者直接把15世纪、16世纪波斯地区生产的仿中国青花瓷器称为中国风格,并视之为18世纪中国风的源头。
(三)古代中外陶瓷器技术交流的层次
瓷器输出势必会影响到输入地的审美,导致其日用器物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进而带动文化变迁。但模仿不等于技术的直接传播,真正的技术传播往往是通过人群的流动,带动原料选择、成型工艺、窑炉形态、装烧方法等方面的技术交流而实现的。中国古代瓷器输出和制瓷技术向外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单纯的瓷器输出。对输入地来说虽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停留在表面,作为一种外来物品在最初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第二个层次是制瓷技术的外传和输入地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如韩国仿越窑、耀州窑、汝窑青瓷;日本仿唐三彩、龙泉青瓷、青花瓷器、五彩瓷器等;伊拉克在10世纪用锡釉白陶器仿邢窑瓷器;越南仿烧中国的龙泉青瓷、青花、五彩瓷器等;泰国仿烧龙泉青瓷和磁州窑瓷器。但各地的模仿生产应是以当地技术为主体,由中国直接输出的制瓷技术所占比例甚小。
第三个层次是以人为媒介的技术交流,这是技术传播中的最高境界。在西方把瓷器生产技术纳入科学研究之前,世界各地的制瓷技术之交流,只有当人员流动并发现合适的原料后,才能实现真正的异地生产。正如中国古代仿烧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玻璃器一样,虽然也明白波斯、阿拉伯玻璃器的生产原料和工艺,但产品却一直不能像进口玻璃器一样耐高温(56)。制瓷技术的交流也是这样,熟练工匠的流动在技术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越窑青瓷生产技术传往高丽,据传是占据今济州岛的军阀张宝皋从越州掠取窑工的结果(57)。而日本为获取瓷器甚至不惜对朝鲜发动战争,从朝鲜带回窑工李三平后,才有了制瓷业。通过对中日窑炉技术的比较研究,发现万历以后日本从中国学得的瓷器生产技术主要是以横室阶级窑为代表的福建地区民间窑场的技术,这可能来自中国江南的技术人员直接参与其中有关(58)。民族学材料表明,菲律宾的陶瓷生产技术是由福建窑工直接带到菲律宾的;而在泰国的传说中,嫁到泰国的一位中国公主从磁州窑带来的工人在当地生产开创了泰国的制瓷业(59)。至于制瓷技术向欧洲传播,传教士殷宏绪从景德镇获取生产技术情报是大家熟知的,但从当时传到西方的不同版本的《陶冶图》可知,在18世纪从中国获得制瓷技术的西方人并不只殷宏绪一人,且技术也不只来自景德镇一地。英东印度公司的约翰·布莱克不仅把中国的高岭土和白瓷土标本寄给伟奇伍德,而且于1770年把中国人黄亚东带到伦敦,由黄亚东直接向伟奇伍德传授瓷器的生产流程和方法(60)。
四 对传播人群的观察
瓷器输出从唐代以来几乎不曾间断,并流布世界各地。但是当我们观察各历史时期、各国输入的中国瓷器时,又会发现不仅其输入目的不单一,而且行为的执行者和完成者也是多种多样,有中国人与消费地人民的直接交流,也有借第三方甚至更多方的力量才完成的间接交流。为了解当时传播瓷器的人群的动态,现仅就直接交流和间接交流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而加以讨论。
(一)直接交流
直接交流是由瓷器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人群直接完成的。
瓷器输出在本质上是古代中国人对海外商业市场占有的结果,和航海能力及制海权相关。但就远洋航海能力看,中国人中并不占优势:西方人经由红海进入印度洋时间远比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人进入印度洋的时间要早,东汉时期大秦使臣就经南海北上入华。唐五代时期,往来于中国与中东之间、有制海权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南宋时期,中国人的远洋船队似仍不出南洋的范围,在中国和中东之间往来的主要是阿拉伯人。郑和下西洋前,中国人对外的直接交流、贸易,基本不出东亚和东南亚。新航线开通以后,制海权归西方各国。从航海能力可以看出,东亚、东南亚各国和中国的瓷器交流主要是中国与各国人民直接交流的结果,琉球人甚至亲自到龙泉青瓷产地购买瓷器,明代晚期还有日本人在景德镇订烧瓷器之事。南亚、西亚和东非、北非等地的情况就相对复杂,郑和下西洋时期在当地的活动是中国和这些地区直接交流,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从中国运瓷器回本国也属直接贸易。西方人主导世界贸易和航海权后,从中国订货并运回欧洲的瓷器,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直接贸易表现。
(二)产地与消费地的间接贸易
此处所说的间接贸易,是指经由第三国或更多中介而完成的瓷器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供需交流。
唐代和宋元时期,当波斯人、阿拉伯人独专东西海上贸易之利时,他们从中国运出的瓷器除供应其本国外,有相当的部分是转口销往其他国家。东非中国商船的“黑石号”出水瓷器表明,中东商人在唐代已开始从事中国和东南亚各地间的转口贸易;在肯尼亚MALP遗址同时出土有五代时期邢窑白瓷碗和伊拉克仿烧的同型锡白釉陶碗,或可说明非洲各地出土的明早期以前的中国瓷器,是中东商人转口贸易的结果。
前引《英宗睿皇帝实录废帝附》载正统六年闰十一月琉球国通沈志良等人载瓷器往爪哇国买胡椒、苏木等物,当时琉球并不生产瓷器,其商人所载往南洋的瓷器应是中国产品,这说明在明代早期中国瓷器输入爪哇等东南亚国家至少有一部分是间接贸易的结果。
在欧洲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内,大量的中国明代晚期青花瓷器又分别被西班牙人输往东南亚、美洲至欧洲:由葡萄牙人、荷兰人输往东南亚、南亚、中西亚、非洲至欧洲,除运回欧洲的瓷器外,由他们销往各地的中国瓷器均属生产地与消费地间的间接贸易。
唐代中国的越窑、长沙窑、邢窑瓷器中已出现在东非沿岸,当时中国显然没有如此的远航能力,这些瓷器被运销往东非地区肯定是藉由中间媒介完成,明以后的大量出口并销往世界各地更是由西方人主导。就输出区域看,既无法证明瓷器输出中中国人一步步由近及远的推销轨迹,也看不出中国人独自控制瓷器输出的迹象。输出之盛世固然与政府之鼓励有关,但在中国禁止出口时,同样也有大量的瓷器输出。而几次输出势头之衰微都和波斯、阿拉伯人海外经营力下降有关。均表明中国古代瓷器输出并非一国或一族人所独控,而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协作的结果。另外,根据对海外各遗址出土的中国古代瓷器的断代研究,几次输出高峰时都恰当海上霸权存在之时,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远洋运输能力及海上交通安全与否是制约远洋贸易和瓷器输出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人虽然发明和生产了瓷器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独霸世界瓷器市场,但是在把瓷器输往世界各消费地的过程中中国人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
五 瓷器输出过程中文化主导因素之变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输出瓷器和国内各遗址出土的同时期的瓷器完全相同。到明代晚期克拉克瓷器出现以后,窑场始按照西方人的要求生产瓷器,及至再后来的广彩瓷器是以景德镇生产的白瓷胎为原料,由广州窑工根据西方商人的需求而随时加工。在考古学或社会学的范畴内,可以根据主体文化因素之变迁归纳为文化演进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以中国为本体看待这个变化,可视之为瓷器输出过程中中国文化从占主导地位到主导地位逐渐丧失的过程。
(一)中国文化居主导的时期
从六朝时期中国瓷器见于武宁王陵开始,直到明代早中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输出的瓷器和国内使用的瓷器完全相同。输出的产品有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白釉绿彩瓷器、巩县窑白瓷、青花、三彩及白釉绿彩器、长沙窑瓷器、耀州窑瓷器、青白瓷、龙泉青瓷、元明青花、仿耀州青瓷、仿青白釉、仿龙泉青瓷等多种。过去有论者以为唐代长沙窑瓷器和唐青花是专门为中东市场生产,但通过对“黑石号”沉船瓷器的总体观察发现,在“黑石号”所载大量长沙窑瓷器中,带汉字诗文的只有少数几件,表明在窑场所见的大量有诗文瓷器仍是为认识汉字的消费者生产而并非供应海外市场,可见长沙窑瓷器不分海内外市场(61)。随着内地各唐代遗址的发现,尤其是上街唐墓出土的唐青花塔式罐(62),从使用地点和器物的属性均说明唐青花在国内同样有消费市场,否定了过去认为的唐青花和长沙窑瓷器是专为外销生产的说法,说明唐代并无专门供应海外市场的瓷器品种。同时,该时期输出的绝大部分瓷器并不因国外与国内市场不同而产生变化,生产这些输出瓷器时仍是由中国各窑场自己的传统文化决定,虽然唐青花、蓝彩三彩器和长沙窑瓷器从生产技术到原料、纹样等方面都有不少外来文化因素,但这些主要是生产者的主动吸纳,并非专门为输出而有的结果,该期是中国文化为主导的瓷器输出时期。
(二)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影响时期
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之相互影响,是指输出瓷器在器类、造型、纹样等方面受产地和消费地的双重文化主导。这一过程最迟在元到明早期已经存在,当时销往东南亚各国的福建窑场所产瓷器中的军持、小盖盒等,在体量大小乃至造型上有些改变。由于尚没有发现当时东南亚人要求改变中国输出瓷器造型的记载,所以在这一改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有可能是中国商人为适应市场扩大销售的结果。
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出土瓷器上的“天文年制”日本款(63),和明代晚期青花瓷器上的欧洲徽章(64),并没有影响瓷器的整体风格,器物的造型、纹样仍是景德镇窑场习见的内容。克拉克瓷器的最初造型,也是以中国传统装饰为特征,只是在图案布局上作了些许调整。
上述现象是生产者为了适应消费市场的要求而作出的调整,该时期输出瓷器是产地传统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可称之为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影响时期。在这些瓷器上虽已附加有消费地的文化因素,但瓷器之整体生产仍以中国文化为主导。
(三)西方文化主导时期
西方文化为主导时期,即大家熟知和常说的来样加工时期,此时中国输出瓷器的生产已完全受西方文化左右。
接受西方人的订单并进行加工始自16世纪早期葡萄牙与中国的交流,但完全受西方的订单和要求控制,使生产处于来样加工的地位,则始自荷兰人订烧的克拉克瓷器。在典型的克拉克瓷器上,虽保存有少量的中国文化因素,但在器物类别、造型、组合等方面,外来文化已占主导地位,中国的窑场完全沦为西方需求瓷器的加工地,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一种生产模式。在景德镇烧造克拉克瓷器的同时,闽南各窑也烧造同样风格的瓷器出口,由于无法从生产技术上或产品演进序列上找到景德镇产品影响闽南窑场的证据,所以这极可能是洋人或代理商持样到闽南各窑场订货的结果。在同一时期或稍后,日本、波斯等地区也生产克拉克风格瓷器,同样不是对中国产品模仿,而是西方人持样订烧的结果。就克拉克瓷器的烧造地点的扩展可以看出,是西洋人的意图与文化需求导致了景德镇和闽南窑场产品风格趋同,以及中外主要瓷器产地产品风格的趋同,这是西洋文化居主导地位并影响世界瓷器生产的表现。
其后,销往欧洲的瓷器更是出现了中国传统所没有的器物,根据西方的需要在广州加工广彩瓷器,景德镇所产白瓷器只是广州窑场加工广彩的原料,更说明中国已沦为西方市场的瓷器加工厂,千年来中国文化主导输出瓷器生产的现象已成为历史。欧洲生产的瓷器和瓷器生产技术在清代晚期开始引领世界瓷器文化的发展方向,产品大举占领中国市场,世界瓷器文化的中心已不在中国。
六 输出瓷器的用途和文化内涵的转变
观察海外各地区所使用的中国瓷器,除日用器的性质外,其功用和文化内涵亦有转变。就已知情况,既有继续做日用器者,也有被用为装饰品,更有用为葬具等,甚至赋之以货币的功用或以中国瓷器为贸易媒介。
1.日用器性质之继续
中国大量输出到世界各地的瓷器以日用器类的碗、盘、瓶等为主,其性质在各地也基本得到保留。对中国瓷器的使用不仅改变了东南亚地区古代民族的生活习俗,当瓷器和制瓷技术输入欧洲并得以普及后,欧洲日常用器面貌也为之一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把输往东南亚等处的炉瓶类供器、军持类伊斯兰教用器,均视为日常宗教生活的器物而归入日用器的行列,不再单独列为宗教用器。
2.财富和财富性质之扩展
任何具价之物均可被视作财富。中国输出的瓷器在东南亚各地除被视作传统意义上的财富外,还在此性质上被扩展成为当地人民进行商业贸易的媒介,部分地充当了货币的作用。
据郑和使团成员记载(65),在南洋和西洋各地习见青瓷器、青花瓷器、青白花瓷器几种,是龙泉窑、景德镇窑和福建等地的窑场的产品。在使用中国瓷器的26个国家中,有24个国家把中国瓷器作“货用”媒介(66)。锡兰国对中国瓷器的态度是:《星槎胜览》卷三记为“货用”、《西洋番国志》记为“甚爱”、《瀛涯胜览》记为“重”,可见瓷器之所以被作为“货用”之媒介,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瓷器受到当地人的“重”与“甚爱”,首先是被视为极珍贵的财富,次之在此基础上产生近似货币的作用。
3.装饰品
以中国瓷器为装饰品的例证较多,从伊朗阿德比尔陵神殿内装饰的中国瓷器,到欧洲各国王宫内装饰的瓷器,都是把中国的瓷盘镶嵌到墙或天花上,在墨西哥西班牙殖民者把瓷器装饰到花园内的水池上(67),纯粹以中国瓷器为装饰品。
在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等地,习见把中国出产的龙泉窑青瓷罐、碗、盘和青花碗、盘镶嵌到柱墓的柱子或丘墓的墓表,这在表象上虽是装饰,但其深层是否另有含意尚为未知的内容。
对肯尼亚东海岸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古代当地人民还把破碎的中国瓷片进行加工,使之成为装饰性质的瓷珠,和玻璃珠一起使用。这既可能是对中国瓷器之装饰性质的延伸,也可能是以中国瓷器为财富之延伸的表现。
4.葬具——通神器?
以中国瓷器为葬具的明确记载并不多,《东西洋考》卷四“西洋列国考·文郎马神国”条载,该国风俗“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磁器。又好市华人磁瓮,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葬”。可知,中国瓷器的传入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首先是以中国瓷器代替传统的以蕉叶为盘盛食的习惯,其次是用中国产磁瓮作为葬具。为什么用瓷瓮为葬具并无记载,如果是作为财富炫耀他人则不应该葬于地下,而作为人死后归宿之具,是否是通过在这些瓷瓮上画的龙纹并赋予它们神通之灵异,则不可得知。
七 瓷器在中国古代输出商品中的比例和地位
如何正确界定瓷器在中国古代输出商品中的地位,以及景德镇窑场的产品在整个输出瓷器应有的地位,虽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作为不可忽视的商品输出问题之外延,还是要加以说明的。在中国古代输出商品中,丝绸向来都占最大比例。尽管我们无法统计各历史时期内丝绸、瓷器等商品的绝对比例,但却可以选择文献记载详尽、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的明代晚期的情况为例加以说明。
(一)瓷器在输出贸易中所占份额
瓷器在当时输出商品中所占的比例,据前引正德《饶州府志》和嘉靖《漳州府志》的记载,饶州府和漳州府两地当时每年的窑冶课钞总数为3861贯397文。据明代税钞折算标准,饶州景德镇和漳州府生产的瓷器全部用于出口,在国内市场的商品价值也不过值银1320两。明代中晚期对外贸易利润在400%~1000%之间(68),如果饶州景德镇和漳州府生产的瓷器全部出口,当可以换回白银5280两~13200两。初看数量并不算小。
在明代晚期中国向菲律宾输出的商品大致包括各种纺织品、食品、日用品、农产品、家禽畜类、奢侈品和军需用品等多种(69),瓷器只是其中之一类。据研究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在1570~1799年间每年约在63000公斤~94000公斤(二百万比索到三百万比索)之间,再加上同一时期内从日本、阿姆斯特丹—巴达维亚、果阿—澳门、伦敦—印度等不同贸易线路,中国通过外贸易每年平均可得白银约250吨、最多时达400吨(70)。每吨白银为32000两,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每年正常的白银收入为8000000两,最多时则高达12800000两。通过这种绝对数的比较,可以看出瓷器在当时输出商品中所占份额并不高。
(二)景德镇产品在古代输出瓷器中所占的比例
根据菲律宾和肯尼亚各遗址所见情况,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在该地的使用几乎不曾中断,唐代以后中国输出的瓷器有定窑、耀州窑青瓷、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元青花、明清青花、明清时期的彩瓷,福建地区的仿青白瓷和仿龙泉窑青瓷、广东各窑场生产的青釉瓷、褐釉瓷器,两广地区的仿烧的耀州窑青瓷和仿青白瓷等。而这些输出瓷器的产地就省区论,有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江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处,窑场则有越窑、邢窑、巩县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繁昌窑、景德镇窑、福建各窑、两广各地的窑场,景德镇只是产地之一。而就瓷器的输出时代论,景德镇的产品输出也只见于南宋到清。就海外各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看,在南宋到明早期,在输出瓷器中居第一位的是龙泉窑青瓷和福建等地的仿龙泉窑瓷器,景德镇的产品在这一时期并不占主要地位。
至于景德镇窑场瓷器的输出最盛时,可以从官方志书的相关记载对其输出数量在全国总输出额中所占比例加以推测。据正德《饶州府志》记载,该州“土产”之“瓷器,浮梁出”,岁办“窑冶课钞二千二百四十一贯”(71),而据嘉靖《漳州府志》记载“本府税课局岁办各色课钞七千一百四十三锭三贯七百五十文,内……窑冶钞四十锭一贯四百文”,“有闰月……窑冶钞加三锭一贯七百文,正德、嘉靖志俱”(72),当时漳州府的税局除本府税课司和龙溪县税课司外,其余均为各县代办,综合嘉靖《漳州府志》及附各县志所载,当时每年平常情况下可征办的窑冶课高达三百二十四锭三百九十七文(73)。嘉靖时期以锭计钱、每五贯为一锭(74),则漳州府全府平常情况下每年窑冶课钞为1620贯397文,而同一个时期或稍早景德镇岁办“窑冶课钞二千二百四十一贯”(75),也就是说正德、嘉靖时期景德镇的瓷器生产量只是漳州府各地的瓷器总生产量的1.4倍左右。如果再把泉州和潮州考虑进来,可以推想明代中期以后以海外为市场的瓷器生产在闽南、粤东的普及程度。所以在谈论明代中晚期到清初的外销瓷器的数量时,不能只是片面地强调景德镇的产品,而低估了闽南、粤东地区。
八 瓷器输出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瓷器外销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是经济上的影响,瓷器外销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南宋时期在政府的鼓励与推动下,市舶司之入号为“天子南库”,而据元人记载南宋王朝以磁器、铁锅、摩合罗等无用之物出口为国家换回利润。元朝学习南宋时期鼓励对外贸易的方法,瓷器得以继续大量出口。明代初年的官方贸易给国家带来巨大收入,即便晚明月港一地之入,也是“公私颇赖之”。其次,瓷器输出给国家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瓷器生产格局、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诸方面产生了如下深远的影响。
(一)瓷器输出对我国瓷器生产格局的影响
两广和福建沿海地区并不是中国瓷器的传统生产地,在唐、五代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时,输出的瓷器也是产自内地的各名窑场,主要有邢窑、定窑、巩县窑、长沙窑、耀州窑、越窑等,且销往海外的产品和供应内地的产品并无不同。
随着对外贸易量的增加,中国瓷器生产格局发生了变化,两广和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以海外市场为供应对象的窑场,这些窑场以模仿不同历史时期著名窑场的产品为主,随不同历史时期的潮流而变化,模仿的对象先后有耀州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场的青花瓷器和五彩瓷器等。
两广、福建沿海地区的窑场虽以生产外销瓷器为目的,但对内地名窑场的模仿,无疑是生产技术在这两地的普及、发展的表现。内地的瓷器生产技术是如何向两广、福建沿海地区传播的?明代方志的记载或许有提示作用。据嘉靖《安溪县志》载,安溪瓷业“皆为外县人氏作业”;乾隆《德化县志》卷三“疆域志·风俗”条亦云,“百工艺事,多藉外人”。明代早期,瓷器主要从景德镇经闽江运至福州出海,销售景德镇瓷器的过程和行为,促成了在当地开窑自造。极有可能是参与走私外贸的巨户、大室人家从江西请来窑工,从而形成了明中晚期以来闽南、粤东地区出现的仿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生产区,形成专门的区域化外销瓷器生产基地。因外销影响中国手工艺生产地域格局变化,当无复如斯之大者。
(二)对瓷器生产方式的影响
瓷器大量输出的需求,生产者或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提高产量,常导致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不高。为在短期内获得大量的产品,模具化生产成为外销瓷器窑场的生产方式之一,生产各种瓷器的内、外模具在福建各窑场随处可见,而输出的瓷器或窑场保留下来的残次品也可以看到模具成型的痕迹,而这种现象在同一时期供应国内市场的各窑场并不常见。
明代晚期以后,外商在华订烧瓷器的生产机制,据《陶说》记载当时称西方市场需要的瓷器为“鬼器”,由粤东商人持样到景德镇订货,景德镇的生产者看样生产。洋人只在广东和粤东商人打交道,并不深入到瓷器产区。
那么,在景德镇是由谁和粤东商人打交道、谁来接瓷样和订单呢?受御窑分工流水式生产的影响,明朝中期以后景德镇窑场有窑户、坯户等,生产分工极细,每日所需佣工达数万人(76),比邻而居者皆为瓷器匠人,甚者夫妇二人分别从事拉坯和画青(77),各色匠人只是流水作业中的一员,无力独自完成瓷器生产。再考虑到明代瓷器生产税——窑冶课的征收是以窑场为对象并具体到产品(78),组织生产的也是窑户(79)。且景德镇瓷器销与外来商客向由牙行把持,所以,粤东商人极有可能是经过牙行和窑户联系,最终形成了洋人持样到广东,把瓷样交给粤东商人,粤东商人带样到景德镇通过牙行和窑户组织所需瓷器的模式。
至于景德镇烧造克拉克瓷器的情况,2007年对景德镇观音阁窑址的发掘(80) 表明,该窑场规模很大,但在这里发现的典型克拉克瓷器只有数十片,和该窑场同一时期的瓷器相比,克拉克瓷器绝对不是产品的主流。而历年对景德镇各地窑场的调查得知,当时生产瓷器的各窑场均出土克拉克瓷器,说明在景德镇并不存专门的克拉克瓷器窑场。这种现象正可以表明,当粤东的商人持样到景德镇后,是在短时期内,在众多窑场获取所需要的商品,对生产者来说照样烧造克拉克瓷器只不过是其生产的内容之一。
明末清初中国瓷器出口受到影响时,荷兰等西方商人一方面到日本寻求替代品(81),另一方面把大量的波斯产青花瓷器运往欧洲冒充中国瓷器,而荷兰和英国商人以波斯青花冒充中国青花的做法甚至到18世纪中期还有发生(82)。这也说明西洋商人订货时并不以景德镇窑场为唯一目标,所以当清初中国瓷器外销停滞时他们很容易转向日本窑场订货,从而使得日本瓷器迅速占据欧洲市场(83)。
(三)中国垄断世界瓷器市场时代的终结
瓷器作为古代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文明内容之一,在其向外输出的同时也激起了各国人民对瓷器的渴求和仿烧,促成制瓷技术的输出和交流。仿烧的成功,就是中国对这些地区或国家瓷器市场的丧失。
各国成功地仿烧瓷器后,在供应其本国市场同时也开始向外输出。唐代伊拉克地区仿烧的锡白釉陶器碗已和同形的邢窑碗一起输出到肯尼亚;南宋至元代高丽青瓷也出口日本并输出到中国。明初的海禁和官方垄断的贸易政策使瓷器外销受到限制,这在世界陶瓷贸易史上被称为中国瓷器外销的“明代断档时期”(Ming gap period),在南洋各国对瓷器的需求下,越南、泰国所产劣质瓷器开始在东南亚、中东地区销售并填补空白(84),市场的需求又促成了这两个国家瓷器质量的提高,越南、泰国瓷器开始在东南亚盛行,缅甸的产品甚至远销到肯尼亚。葡萄牙商人最初得到中国瓷器时,是以二倍于白银的价格成交的(85),并被作为极为珍贵的物品销往欧洲和世界各地,从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仿烧中国青花瓷器的浪潮。在欧洲各国仿烧的同时,远在新大陆的墨西哥也掌握了青花技术,从而形成世界青花文化(86)。
在欧洲市场被大量的日本和波斯产品替代的同时,波斯青花瓷器和卡曼碟甚至还被荷兰人运到东南亚的锡兰、巴达维亚、孟加拉等传统的中国瓷器市场(87)。至清代晚期,欧洲各国、日本、美国出产的瓷器反而大量销往中国内地,严重冲击了中国本土瓷器的市场并造成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进一步衰落。
九 余论
作为一篇研究报告,本文所述只是自己关于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看法,其准确与否尚需进一步的讨论。尽管有些提法为以往研究者忽略,有的内容涉及对这类瓷器命名方法的更定,但本文之目的并不是对过去的研究工作和已取得成果的否定,而是想更客观地还原到历史的真实情况来研究中国古代输出的瓷器。
中国古代输出瓷器,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内容外,还有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以中国为中心输出瓷器的性质并不同,但各国获取中国瓷器之目的是否存在差别;在瓷器输出过程中,除了中国人的努力,其他外国人参与其中除商业目的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输出瓷器功能的转变?而从输出瓷器在世界分布区域看,从唐到明代中期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局限在中国古代所认识的东洋、南洋、西洋的范围而没有扩大,瓷器在北非的福斯塔特等地大行其道时为什么欧洲人会视而不见?在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内瓷器空前流行且中国与欧洲已发生了直接交往时,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瓷器没有进入欧洲市场?同时,东亚、东南亚和西亚各国虽然早就有仿烧中国瓷器的努力且不乏有成功之作,但为什么直到欧洲人获取瓷器后才最终形成真正完整的世界瓷器文化,这里面除了欧洲人加入的科学的成分外是否还有文化传统的原因?诸如这些内容都应是研究输出瓷器时应该想到的。
瓷器之输出与输入都是根据狭义的国族地域观而有的看法,置之于世界人类文明史的大范畴内,则是制瓷技术的传播与以瓷器代表的物质文明的普及等内容在实物方面的表现。所以,我们的研究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应该在世界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而不仅仅局限在瓷器或输出瓷器本身。
注释:
① 参见Cheng Te-k'un,Studies in Chinese Ceramics,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4.
② 该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是与林业强教授一起观摩实物、交流后所确定的。
③ 作者就该研究项目及相关问题与香港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苏芳淑教授交流时苏教授所谈想法。
④ 中外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多,此不一一注出。
⑤ Amanda E.Lange,Chinese Export Art at Historic Deerfield,Deerfield,Massachusette:Historic Deerfield,Inc.,2005.
⑥ 西方学者常用该概念:如,D.F.Lunsingh Scheurleer,Chinese Export Porcelain,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74.香港艺术馆分馆茶具文物馆:《中国外销瓷: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史博物馆藏品展》,1989年。
⑦ Michel Beurdeley,Chinese Trade porcelain,Rutland:Charles E.Turtle Company of Rutland,2002.Monique Crick,Chinese Trade Ceramics for South-East Asia:Collection of Ambassador and Mrs Charles Muller,Geneve:Fondation Baur,2010.
⑧ Kamei Meitoku,Ceramics from Kharkhorum site,Mongolia.Fukuoka-shi:Tōka Shobō,2007。林梅村:《和林访古(上、下)》《紫禁城》2007年第7期,页212~219;第8期,页208~217。
⑨ 新疆博物馆:《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器等文物》,《文物》1979年第8期,页26~29。
⑩ 余城:《明代青花瓷器的发展与艺术之研究》页83,台北:文史出版社,1986年。
(11) Barbara Harrisson,Later Ceramics in South -East Asia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2) John Alexander Pope,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1956.pp17.
(13) Julian Raby and Unsal Yucel,Chinese Porcelain at the Ottoman Court: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London: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1986,pp27-54.
(14) 吴昭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页342,中华书局,1980年。
(15) 《明史》卷三二三《外国四·琉球传》。
(16) 《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五·占城传》。
(17) 《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五·真腊传》。
(18) 《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五·暹罗传》。
(19) 刘海年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三册《皇明诏令》卷七“仁宗皇帝·即位诏”,科学出版社,1994年。
(20)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四·失剌思传》。
(21)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四·日落国传》。
(22) 《清史稿》卷五百二六《属国一·朝鲜传》。
(23) 《清史稿》卷五二六《属国一·琉球传》。
(24) 《清史稿》卷五二八《属国三·暹罗传》。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四五,页48,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下同)。
(26) 宋伯胤:《从刘源到唐英》,《清瓷萃珍》页11,南京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博物馆,1995年。
(27) 《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一,页32~34。
(28) 《清史稿》卷一六○《邦交志八·葡萄牙志》。
(29) 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页78,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下同)。
(30) 《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页78。
(31) 《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四五,页172。
(32) 《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四五,页434。
(33) 《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四八,页24。
(34) 《元史》卷九四“食货二·市舶”,页2043;卷二五○“铁木迭儿传”,页4576。
(35) 郑一钧:《郑和下西洋》,页202、21O~211,海洋出版社,2005年(下同)。
(36) (明)巩珍:《西洋番国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42册,页373。
(37) 可综合参考《明会典》、《明史》等书关于南洋、西洋各国贡物之记载。
(38) 《明史》卷三三二“列传第二百二十·西域四”:“时车驾频岁北征,乏马。遣官多赍彩币、磁器市之实喇苏及赛玛尔堪诸国,其酋即遣使贡马。”
(39) 《郑和下西洋》页406~409。
(40) 菲律宾10世纪以来出土中国瓷器情况,见Leandro and Cecilia Locsin,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Tokyo:Charles E.Tuttle Company,1970.
(41)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页131,中华书局,1981年(下同)。
(42) (明)周起元《东西洋考序》,《东西洋考》页17,中华书局,1981年。
(43) 《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页141~147。
(44) 参见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页13、14,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8年(下同)。
(45) 《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页131。
(46)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明中中欧交通之恢复第一百五十一节”引Henri Cordier,L' Arrivee Portugis,H.Yule,Cathay,Vol.I.P.180.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北平:京在书局,页385~386。另,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页198~199也引有此文,但译释略有不同。
(47)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载永乐二年五月甲辰;《礼部志稿》卷二“怀远人之训”、卷九二“不罪赍金市磁器”诸条。《明史》卷三二三《列传第二百一十一·琉球传》。
(48) 《英宗睿皇帝实录废帝附》卷八六,正统六年闰十一月己丑条。
(49) 张弛:《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古代文明》第5卷,页16,文物出版社,2006年。
(50) 王光尧:《关于青花起源的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5期。
(51)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九“马合马沙碑文”载:“西域有国,大食故壤,地产异珍,户饶良匠。匠给将作,以实内帑。”
(52) 《大元塑画记》卷九“御用”条载,大德十一年已开始引进回回青料。
(53) 许晓东:《康熙、雍正时期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宫廷与地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技术交流》,页320-325,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54) 王光尧:《雍正时期御窑制度的建设》,《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年。
(55) Lisa Golombek,Tamerlane's Tableware:A New Approach to the Chinoiserie Ceramics of Fifteenth-And Sixteenth-Century Iran,pp57-60,Mazda Publisher,Costa Mesa,1996.
(56) (宋)赵汝适:《诸番志》卷下:“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添入南鹏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
(57) [韩]郑良谟(金英美译):《高丽青瓷》页2,文物出版社,2000年。
(58) 2008~2009年,作者参加日本国立爱知县陶磁资料馆组织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参加的《东亚窑业技术交流课题》研究时,在日本调查锅岛藩官窑时得知,为锅岛藩烧造瓷器的最优秀的技术工人金武氏,原本是来自中国江南的武氏人家,因技术优异被赐日本姓。
(59)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Thai Ceramics The James and Elaine Connell Collection,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6.
(60) 故宫博物院编:《英国与世界:1714—1830》页230,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61) 作者在2009年3月份在新加坡观摩“黑石号”沉船后的认识,此次观摩得到亚洲文明博物馆郭逊勤先生和谢建平先生的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6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上街峡窝唐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期,页22-26。
(63)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页54。
(64) John Carswell,Blue and white: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0.pp135.
(65) (明)马欢:《瀛涯胜览》,(明)费信:《星槎胜览》,(明)巩珍:《西洋番国志》,均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42册。
(66) 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表七:郑和下西洋时期使团在各地所见瓷器之情况”,页205,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67) Jean McClure Mudge,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In North America,New York:Riverside Book Company,Inc.1986.p84.
(68) 2010年4月29日,钱江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克拉克瓷器与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研讨会》上的发言。
(69) 钱江:《1570—1760年中国与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页71。
(70) 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的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南洋问题研究》1988年第2期,页85~88。
(71) (明)陈策:《饶州府志》卷一“土产”、“税课”条,页124,正德辛未年(正德六年,1511年)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44)》,上海书店出版社(下同)。
(72) (明)罗青霄:《漳州府志》(万历元年刻本)卷五“赋役志·财赋·税课”,页100~101,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
(73) 王光尧:《明代宫廷陶瓷史》“表九:嘉靖《漳州府志》载瓷器生产及税课情况”,页237。
(74)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钱钞”。
(75) (明)陈策:《饶州府志》卷一“土产”、“税课”条,页124。
(76) 光绪《江西通志》卷四九《萧近高参内监疏》。
(77) (明)冯梦龙:《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醒世恒言》页449,岳麓书社,1989年。
(78) 万历《明会典》卷九《关给须知》条“授职到任须知条目录:十七窑冶”。
(79) (明)王宗沐:《江西大志》卷七“陶书·窑制”。
(80)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页39~58。
(81) Yolande Crowe,Persia and China:Safavid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501-1738,London:Thames and Hudson,2002.pp23.
(82) Yolande Crowe,Persia and China:Safavid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501-1738,London:Thames and Hudson,2002.pp21.
(83) Oliver Impey,Japanese export porcelain,Amsterdam:Hotei Publishing,2002.
(84) 该情况可参看菲律宾10世纪以来出土中国瓷器变化情况与明代中国瓷器和越南、泰国瓷器的对比,见Leandro and Cecilia Locsin,Oriental Ceramics Discovered in the Philippines,Tokyo:Charles E.Tuttle Company,1970.John Stevenson and John Guy,Vietnamese Ceramics:A Separate Tradition,Chicago:Art Media Resources with Avery Press,1997.pp47-60.
(85) Nuno de Castro,Chinese Porcelain and the Heraldry of the Empire,Barcelos:Livraria editora Civilizacao,1988.pp X I X.
(86) John Carswell,Blue and White:Chinese 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2000.
(87) Yolande Crowe,Persia and China:Safavid Blue and White Ceramics In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501-1738 London:Thames and Hudson,2002.pp21-22.
标签:中国瓷器论文; 唐代瓷器论文; 定窑白瓷论文; 清代瓷器论文; 陶瓷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青花瓷论文; 青瓷论文; 定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