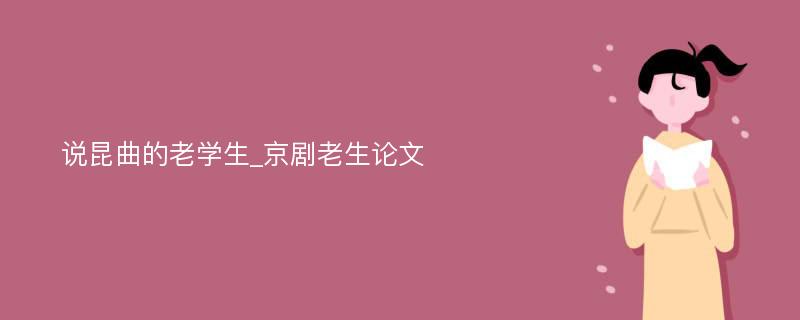
话说昆剧老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昆剧论文,老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宋元南戏没有独立的老生行当,统一归入生行,明徐渭《南词叙录》云:生“即男子之称”,年老男子的角色也归属于此行。但在明传奇中,有不少剧本已分正生、贴生,正生即老生为中老年男子的称谓(与清中叶的正生为小生的概念不同),贴生即小生,为青少年男子的称谓。明王骥德《曲律》将正生列于各行之首,受到重视,明末清初的昆山腔剧本中,开始出现老生的称呼,剧中中老年男子即由老生应工,《缀白裘》所辑昆剧折子戏,有的将老生写成生,类似《南词叙录》,但另有小生一行,以示两个行当的区别。至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正式确立以老生为名称的行当,正生为小生的别名。当时的老生与副末、老外均独立成行,不能混淆。[1]近代以降,老生行包括副末、老外。
经历长期艺术实践,老生行当的概念渐趋完整,并在昆剧脚色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与京剧不同,没有安工老生、做功老生、靠把老生的区分,其在剧种和戏中的位置也不像京剧老生那样显要,但也有不少重头戏和骨子戏,特别是在串本戏和建国后的新编历史剧中,成为主角,重要性不亚于长期在昆剧中占主力的小生与花旦。昆剧老生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身材略魁梧,扮相要好,脸要丰满,适合戴纱帽和口面,口面以黑三绺为主。所扮演的中老年人物中大多为正面人物,或忠臣、或良相、或慈父、或严师,忠贞耿直,刚毅不阿,善良谦和,为人楷模。如《鸣凤记》中杨继盛,《精忠记》中岳飞,《寻亲记》中周羽,《琵琶记》中张大公等。
二、嗓音宽厚而响亮,以衬托忠臣良相的宽大胸怀的气质。有的演员嗓音响亮程度不足,则以宽厚为主,质朴中见功力。更有嗓音沙哑者,则讲究丹田运气,在发音、运腔上严格要求,做到字正腔圆,发挥昆剧唱曲的特点。
三、讲究工架。工架是指人物造型动作,包括眼神、手势、脚步等,它与武技不同,不以跟斗、跌扑取胜,而是在亮相或动作架式上下功夫。昆剧老生工架要端庄、严肃、大方。[2]端庄即端正、庄重、不浮躁;严肃即执着、规矩、不轻视小节;大方即磊落、光明、有棱有角。扮演老年的虽有老态,但不龙钟,要有精神,没有迟暮的感觉。
四、苏昆没有武戏,但要有武功基础,北方昆曲及宁波昆弋班有文武老生,要见武生功夫。北方昆曲艺人陶显庭即为文武老生佼佼者。老生也有特技。《邯郸梦·云阳法场》中卢生。当听到“斩”字,必须向左中右三个方向连甩三次排发,每次头发都直竖起来,在排发的一端,用弦线扎紧约二寸长,另一端的头发必须崭齐,不能有长短,平时倒挂,直垂不乱,不能甩发用力过度,否则排发倒向脑后;也不宜太轻,轻则不能竖直。
昆剧老生戏分头榜、二榜、三榜。头榜即正牌,须嗓音高而宽,所演剧目注重唱工,如三法场戏:《鸣凤记·写本、斩杨》中的杨继盛,《寻亲记·出鼎、府场》中的周羽,《邯郸梦·云阳、法场》中的卢生。这些戏通过矛盾冲突,表现人物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的品质。为了反映人物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演员们设计了大段唱腔,通过曲文体现人物心理活动,达到塑造艺术形象的目的。二榜即二牌,所演剧目唱做并重,但是讲究做工,如《琵琶记·扫松》中的张广才,《牧羊记·望乡》中的苏武,《千钟禄·搜山打车》中的程济,《水浒记·杀猪》中的宋江,《四声猿·打鼓骂曹》中的祢衡。因注重做工,所以对嗓子的要求比较低,其不足部分用身段动作弥补。对甩发、水袖、台步均有一定程式,且因戏而异,因人而异,富有变化。宁波昆弋班的二榜老生实际上是武老生,主要演武戏,不论长靠短靠,都要擅长。清末梨园盛行武戏,因而二榜老生成为宁波昆弋班中的台柱,他们的武技好坏,决定戏班的名誉和营业。尽管二榜老生的地位不及头榜老生,但武技高超者的包银往往优于头榜老生。有的艺人为了声誉,宁愿放弃优厚的包银,由二榜老生升为头榜老生,就此不再演出武戏,但就班主来说,并不主张这样做,因为这将减少观众,因此宁愿提高包银及待遇,也不图艺人升迁。[3]三榜即扫边,被称为老生行的戏抹布,除三法场(为头榜老生的戏)不演外,其他老生戏都要会唱,起替补作用。这个分工在全福班时期尚还讲究,但至新乐府、仙霓社已不起作用,传字辈中的老生行演员如施传镇、郑传鉴,凡头榜、二榜、三榜老生戏都要兼演。
现在我们所说的老生戏,实际上融合了老外、副末两个行当,在清中叶,这三个行当不可串扮及兼演。清末民初的全福班及后来的传字辈虽可串扮兼演,如有的小生兼副末,或老生兼老外,或三者皆兼,但在归属上还是有规定的,以老生为主的戏称老生戏,以副末为主的称副末戏,以老外为主的称老外戏,不能将副末戏、老外戏混入老生戏中统称为老生戏。建国后,在培养新一代的昆剧老生演员中,已不再分老生、副末、老外,三个行当已合并为一,演出的戏统称为老生戏。发展至八、九十年代,江浙沪一带的昆剧院团就只有老生一行,而没有副末、老外的行当名称。与历史恰好相反,宋元南戏及明初传奇,只有副末、老外的称谓,而无老生一行。这一艺术发展现象值得深思,至少可以启迪我们,行当与其他表演艺术一样,发展才是硬道理,老生行当是在不断改革中求得生存的,而副末、老外因其固步自封而渐渐消亡。
历史上老生与副末、老外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老外,在宋元南戏中为老年男子及老年妇女的称呼,如《张协状元》中的张协父亲、王夫人均由老外扮演。至元末明初“荆、刘、拜、杀”及《琵琶记》流行时期,老外成为专演老年男子的行当。明中叶;徐渭《南词叙录》中称外为“生之外又一生也,或谓之小生。”似乎还包括小生角色,但此小生与后世的小生概念不尽相同,也扮演老年人物。后又有外旦之称,外旦即小旦。清中叶,老外成为专演耄耋之年的老人,即挂白胡子者。扬州昆班中,演老外的艺人比副末多。其表演要比老生及副末更为气局老苍。声音带沙哑,讲究念白。属老外的戏有《琵琶记》中牛丞相,《风云会》中赵普,《浣纱记》中伍员,《精忠记》中宗泽,《寻亲记》中范仲淹,《牡丹亭》中杜宝,《狮吼记》中苏东坡,《千钟禄》中方孝孺等。老生与老外的最大差别,前者扮演的是老年中年轻一属,按年龄分,约为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中老年,挂黑胡子、声音宏亮,台步矫键,所扮人物多为有地位但经历坎坷的的人物。后者饰演的是老年中年迈一属,按年龄分,约为七八十岁的垂暮老人,挂白胡子,声音沙哑,台步蹒跚,所扮人物地位高低均有,以儒人为主。副末,在早期南戏中为杂角,与同样演杂角的净丑不同,它专扮男子角色,如《张协状元》中帮闲、李公、当值、土地、判官、秀才、门子、干办等。《南词叙录》称末为“优中之少者为之,故居其末。”意思此角为年少初涉舞台的演员充任,其地位低下,故益其名为末。清李斗《扬州画舫录》称“梨园以副末开场,为领班”。它是行当之首,其它行当均在其之下,这一说法与元杂剧中的末概念相近。元杂剧中的末名正末、冲末,为剧中男主角,主要饰演中壮年男性,在所有行当中地位最高。但在明清传奇中,末的地位渐退居次要,成为生的配角,甚至受南戏的影响,演一些零碎角色,《扬州画舫录》中称末为领班,主开场,表明它的地位在清中叶有所提高。不惟如此,在扬州昆班中,副末行当尚有正副席之分,如老徐班,余维琛为正席,王九泉为副席,相当于后来的头榜、二榜。班社的管理及戏中表演当然以正席为主。至清末民初,副末的领班兼开场报台之职发生变化,领班不再是副末的专利,生、旦行当的演员亦可任领班,开场报台老生、老外也可承应,传字辈的演出多为老生报台。副末沦为一般行当,专演穷苦老人,即老生行中的苦生,所饰人物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穷窘迫,且多为悲剧人物,有“卑小处如副末”的说法。表演上唱做并重,并要有掼跌功夫。所演剧目有《千钟禄·搜山打车》中的严震直,《琵琶记·称庆、吃糖》中的蔡公,《一捧雪·换监、代戮》中的莫成,《牡丹亭·学堂》中的陈最良,《渔家乐·卖书、纳姻》中的简人同,《单刀会》中的鲁肃等。与老生相比,副末的角色多变为里子,虽为配角,但却不能或缺。它所饰人物大多为迂腐、酸穷的角色,身份较低,与老生形成鲜明对照。正因为有区别才形成三个行当的不同特点。
(二)
历代皆有一批著称于时的老生演员。明末清初周铁墩工老生兼净脚,曾为明万历年间宰相申时行家乐艺人,年八十还在演戏,且极有精神。饰《鸣凤记·写本》中杨继盛、《钗钏记·观凤》中李若水,庄严中含诙谐,别具一格。[4]“观者如入云雾中。啼笑悲欢,动心失常”。[5]
清中叶,盛名梨园的老生演员较多,扬州昆班中有老徐班的山昆璧、张德容,老张班的程(陈)元凯、刘天禄、任颖士、老程班的王采章,大洪班的周新(星)如、陈应如、刘亮彩、王明山,德音班的朱文元等。一时人才济济,名家辈出。山昆璧,身长七尺,声如镈钟,演《鸣凤记·写本》一出,观者目为天神。自言袍袖一遮,可容张德容数辈。张德容,本小生,声音不高,工于巾戏。演《寻亲记》周官人,酸态如画,程(陈)元凯,为朱文元高弟子,《写本》诸出,得其真传。刘天禄,小唱出身,后师余维琛,为名老生,兼工琵琶,其《弹词》一出称最。任颖士,本海府班串客,后为教师,于《邯郸梦·云阳》、《渔家乐·羞父》最精,善相术,间于茶肆中为人相面。王采章,即张德容一派,擅做工。陈应如,本织造府书吏,为海府班串客。周新(星)如,以《四声猿·狂鼓吏》得名。刘亮彩,刘君美子,小名小和尚,吃字如书家渴笔,自成机杼,工《烂柯山》朱买臣,并以《醉菩提》全本得名。王明山,待考。朱文元,小名巧福,为程伊先徒,演《邯郸梦》全本,始终不懈。在徐班时,以年未至五十,故无所表现,后至洪班,名声大振,班中人称“戏忠臣”。后拘府班十年,因家贫遂归德音班,时年六十有余。江鹤亭见其入班甚喜,及舟甫抵岸,竟暴卒。以上扬州昆班中的老生演员有以下几个令人感兴趣的焦点:一、大多年龄偏老,五十岁尚未出名,因为年资不高,六、七十岁才是盛名天下的最佳时机,与后世追棒青少年演员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二、老生与副末、老外行当已有明确分工,演员各司其职,不串扮,各有其擅演剧目,互不抢戏,有严密的行规。三、老生行当中分诸种艺术流派,各有所宗,互相竞争,如王采章为张德容派,与山昆璧派风格相异。四、有的出身串客(半职业班演员,以清唱为主,与业余演唱的清客有所不同)在串班中打下扎实基础,然后下海成为职业昆班艺人。以上四点也体现了扬州昆班老生的独特风格。
近代以降,在上海、苏州一带演出的昆剧老生演员不少,但由于资料的匮乏湮没,已无法知道鸿福、大章、保和诸班的名单,即使集秀班也无留存老生资料。今知近代老生演员,仅有咸丰末、同治初在上海三雅园演出的大雅班中的张南、夏双寿,两人生平不详,但据当时大雅班行当整齐,名角荟萃的情况来看,张、夏的身手一定不俗,否则难以与声誉卓著的葛芷香(旦),姜善珍(丑)、王松(净)等人并列。
全福班老生演员,光绪前期有李桂泉,李根泉、沈顺福。李桂泉,一名少美、李子美子。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后,受上海天仙茶园之邀,与姜善珍合演《议剑》、《吃茶》、《弹词》;与陆阿全合演《酒楼》、《当酒》、《大话上山》;与周钊泉、小桂香合演《小宴》等,陆萼庭在《昆剧演出史稿》中引著名曲家徐凌云的话说:“他戏路很宽。”[6]徐凌云在他幼年时可能看过他的戏。李除了演老生,还兼演老外、副末,如《弹词》原为老外应工(后改为老生扮演)。周传瑛称他的嗓子能达三条田岸,为光绪中叶后文老生第一。[7]全福班分坐城班与江湖班,坐城班主要唱文戏,李桂泉为坐城班艺人,只唱文戏,不会武戏,所以人称文老生。文老生的特点是嗓音佳、做工好,唯此才能卖座,周传瑛既称他为文老生第一,想来当时的昆剧老生演员中,无人能与他抗衡。李根泉不详,或为李桂泉弟。沈顺福,老生兼副末,出身昆剧世家,沈月泉弟,曾搭过聚福班。
光绪后期全福班涌现的老生新秀有沈锡卿,沈桂生、范荣生、柴根等人。沈锡卿(约1867—1937),又名金钩(或作金戈),李桂泉(少美)徒,苏州人,为全福班后期台柱演员。据徐凌云说,他的艺技较李桂泉更有发展,演戏“身段优美,念白传神,感情充沛。”[8]擅演剧目有《千钟禄·搜山、打车》,《铁冠图·别母、乱箭》,《邯郸记·云阳》,《水浒记·杀惜》,《义侠记·诱叔、别兄》,《连环记·大宴、小宴》,《鸣凤记·吃茶、写本》,《一捧雪·换监、代戮》,《四声猿·骂曹》,《西楼记·侠试、赠马》,《琵琶记·扫松》,《长生殿·酒楼》,《寻亲记·出罪府场》,《烂柯山·前逼、泼水》,《描金凤》(全本),《蝴蝶梦》(全本)。民国10年(1921)11月,全福班来上海演出,与陆寿卿合演《醉菩提·当酒》,与沈盘生合演《长生殿·弹词》,演出时“大卖其力”,“不肯苟且”。[9]全福班解散前夕,于民国12年(1923年)秋,在苏州长春巷剧场作最后一次演出,沈锡卿在《千钟禄》中饰程济,《寻亲记》中饰周羽,《西楼记》中饰胥表,《四声猿》中饰祢衡,《烂柯山》中饰朱买臣,《蝴蝶梦》中饰庄子,这些戏反映了他习艺以来的最终成就。可惜其时年事已高,不再当年风采,戏虽精,但中气不足。此后他在苏州昆剧传习所教戏,施传镇、郑传鉴等的老生戏受其调教。由于他的精心教练,施传镇所演《铁冠图》等老生戏盛名于时。传字辈演员出科后,他来上海拍曲谋生,徐凌云等曲家曾得益于他。民国20年(1931年)新乐府散班,他北上京津,先后在北京音乐会,天津同咏社教授南昆,任拍先(拍曲先生),终老北京。近代老生演员通常兼演老外、副末,而沈只演老生,不及其他,遵从清中叶昆班老生、老外、副末三脚不串、兼扮的做法。但他偶而串演小生戏,在上海小世界演出时,反串《金印记》中苏秦(前为穷生,后为官生),也演武生,如《义侠记》中武松,甚而排演其他武戏。沈是一位文老生演员,为了挽救日趋没落的昆剧,满足各种层次的观众需要,一改原来戏路,排演武戏,就他个人来说,有得有失。得者拓宽戏路,失者他原来专工的文老生剧目得不到提高,难以精益求精,并且他改演武戏时,又是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六十岁学吹打,”真难为他了。全福班后期老生中,就数沈锡卿最有成就,虽然他对于老生行当艺术没有显著的改革业绩,但他在光绪后期至民国初期中,为演出老生戏最多且技艺精湛的一位演员,尚无其他演员可以与他决一雌雄;后来的传字辈老生戏,有一些是他授受的,他对于昆剧老生的保存与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
沈桂生、沈海珊子,沈盘生弟,老生兼副末。民国12年秋,在苏州长春巷剧场演出,沈演《千钟禄·奏朝、草诏》中永乐帝。后因年老演不动戏,在新乐府、仙霓社中充任场面,仙霓社解散后,与沈盘生一起在南京谋生。其演技平平,没有留下什么戏。传字辈的老生戏,《奏朝》、《草诏》由吴义生教习,没有请沈出场,可见一斑。范荣生,全福班后期中的二榜老生,兼副末。因搭班时间较晚,通常在介绍全福班演员时没有他的名字,诨号小广东,但非广东人,人生得矮小,且皮肤黝黑。拿手戏有《追信》、《拜将》、《十面埋伏》、《访普》、《酒楼》等,以唱工见长。民国12年秋,在苏州长春巷剧场演出,老生戏为《麒麟阁·三挡》,饰秦琼,后来仙霓社在大新游乐场演出时加入该班,改名传钟,但演戏不多,所扮多全为里子脚色。其余曾传铨、周传溶、高传潼虽也以“传”字命名,但因非苏州昆剧传习所出身,所以不将他们列入传字辈演员名单。据说范曾教过周信芳昆剧老生戏。[10]柴根,生平不详,仅悉民国12年,在苏州长春巷剧场演出中,饰《醉菩提·伏虎》中道济。
在全福班后期老生演员中,吴义生不可不提,他虽然主工老外,但也兼演老生,更为重要的是,传字辈中的老生戏主要由他教习,培养了施传镇、郑传鉴等技艺高超、鼎盛昆坛的艺术大师,他所教授的老生戏达二、三十出之多,超过了他后期常演的老外戏。对昆剧老生的发展,功不可没。吴义生(1880?——1931),又名炳祥,苏州人,大雅班著名老外演员吴庆寿子。擅演老生戏有《琵琶记》中张大公,《南柯记》中卢生,《西川图》中孔明,《连环记》中王允,《牧羊记》中苏武等。这些戏都授受给传字辈中的老生演员。吴所演的老生带有老外特点,唱曲咬字铿锵有力,念白苍劲沉着,独树一帜。
近代昆剧老生演员与清中叶相比,有着许多差异:一、全福诸班中的老生演员可以兼扮,串演,即在主工老生行当的同时,可以兼演老外、副末,甚至其他行当。老外、副末行当的演员也可串扮老生。由于兼扮拓宽了演员的戏路,丰富了老生的表演艺术,同时也给营业日趋清淡的戏班精简人员,节约开支。但兼演也表明了老生行当萎缩,需要从其他行当补充养料,不断创新,不然将难以为继。二、近代观众的审美情趣发生变化,崇尚小生、小旦演员,老生演员的地位逐渐下降,不再像清中叶那样有辉煌的业绩,老生戏观众寥寥,以生旦丑为主的三小戏趋之若鹜。因此老生演员大大减少,除全福班外,集秀、大章、保和等班竟不知道老生演员是谁,这不能不说是老生行当的悲哀。三、晚清昆剧舞台为与徽、京诸班竞争,上演新编小本戏、时剧,过去流行的全本传奇大戏。一般不照原本演出,故而清中叶扬州昆班演出的全本戏如《醉菩提》、《邯郸梦》、《烂柯山》等已不再从头至尾搬演,而是上演串折戏(将剧中主要的折子戏串起来演出)和折子戏。倘要演出有头有尾的本戏,则为新编的小本戏,如《南楼传》、《蝴蝶梦》、《文武香球》等,这些剧目的出现,使昆剧行当的兼容性得到加强,以老生为中心的老生行(含老外副末)得到确认,老外、副末的作用渐渐消退,融入老生行当之中。如《南楼传》中刁南楼就是有三位合一体的感觉。这一变化,为今天老生行当的改革开创了先河。四、演员年轻化,大多在十余岁习戏,二十几岁已活跃在艺术舞台上,沈锡卿,吴义生戏出名时,都在青年时期,待到了四、五十岁,观众感觉年老了,嫌演出时中气不足,常有非议。而清中叶的朱文元在老徐班因年未至五十而未成名。时代不同,世风也相异。青年演员年富力壮有创新精神,演出有朝气,能吸引观众。同时求新求异也是时代的需要,是一种进步的现象。
民国年间苏州昆剧传习所培养了一批老生演员,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专工的有施传镇,郑传鉴、屈传钟、华传铨,兼演的有倪传铖,包传铎,汪传钤,后改习小生的赵传钧原也学唱老生,周传瑛倒嗓后也兼唱老生。其中施、郑在老生行当中的成就最高,获得行家赞誉。
(三)
老生行当的产生及其发展,与社会历史背景及戏曲艺术发展规律有着密切关系。明中叶,饱受元末明初战争创伤的人民开始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促使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腐败、无能的皇权统治及贪官污吏的盛行,使百姓的生活改善无望,有的更加困苦。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斥逐忠臣,镇压异已,造成大批冤狱;嘉靖年间的权奸严嵩、严世蕃父子,诛杀大臣夏言、将领曾铣、总督张经、谏官杨继盛,卖官鬻爵、胡作非为,万历时期的阉党魏忠贤,结党营私,专断国政,迫害东林党人,使朝政颓败。在此情景下,广大民众希望有明君清官出现,为民请命,平反冤狱,革新朝政。于是出现了《四声猿》祢衡、《水浒记》宋江、《鸣凤记》杨继盛、《邯郸梦》卢生等老生形象,他们之中有敢于辱骂奸雄的儒生,有不畏强暴的朝廷命官,有农民起义的领袖,有被逐边境建功立业的辅丞,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正义力量,激励人们向那种邪恶势力作斗争。
明末清初,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由于明王室的昏庸无能,导致清军入关,政权丧失,此时人们希望屹立一位明君,杀尽朝廷中的奸臣败将,叛徒逆贼,挑起抗清大旗,维护大明江山;或出现一些明大义、识大体的忠臣良将挽回狂澜,抵御清军入侵。象《千钟禄》程济、《牧羊记》苏武、《铁冠图》周遇吉等有爱国主义意识的老生形象也就应运而生。
至清中叶,“乾嘉盛世”,那位号称十全老人的弘历皇帝,到处树碑立传,宣扬他的政绩。清昭棱《啸亭杂录》记载:“纯庙即位,承宪庙严肃之后,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一时辅臣如鄂文端、杨文定、朱文瑞、赵泰安,皆醇儒也。”[11]明明是王室成员的喝采,却说是吴中民谣的歌颂。在一片吹捧声中,出现了为帝王颂扬功德的御命宫廷剧,那些追随乾隆征战南北的大臣、将领也得到了褒封,在千叟宴上受到奖励,皇帝大臣共庆天下太平。以前流行的老生戏如《鸣凤记》、《千钟禄》、《铁冠图》等继续得到青睐外,又诞生了一批新的老生戏,如《满床笏》中的唐肃宗、《长生殿》中的郭子仪、李龟年,《慈悲愿》中的殷开山等,老生演员名家迭出,成为戏班的台柱,受到人们的尊敬,享受丰厚的报酬。
清季,由于清政府的没落,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矛盾再次激化,广大民众反清意识强烈,推翻封建主义统治成为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传统的老生戏仍受到一定的欢迎。但由于权贵富豪追求奢糜的生活,道德沦丧,精神颓化,追求声色,一些以年轻漂亮少男少女演出的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主演)纷纷登场,成为剧坛主流,使老生戏演出受到影响。民国年间,京剧风靡大江南北,昆剧无法与其抗衡而退居一隅。京剧行当首推老生与花旦,老生自三鼎甲的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起,至谭鑫培,再至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等,形成一套完整的老生表演艺术剧目。演唱老生的演员成为班中主角,声誉日隆一日,衰落中的昆剧受此启发,加强对老生演员的培养及剧目的开拓,一批传字辈老生演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茁长,为现代昆剧老生艺术发展打下了基础。
注释:
[1]清乾隆年间,扬州昆班中老生的地位仅次于副末,高于老外及其他生、旦诸角,甚而在所演剧目中的角色位置还显于副末。
[2]参见白云生《生旦净丑的表演艺术》,5——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3月版。
[3]参见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编印《宁波昆剧老艺人回忆录》151页,1963年1月版。
[4]参见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145——14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版。
[5]见褚人获《周铁墩传》,转引自孙崇涛、徐宏图《戏曲优伶史》18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5月版。
[6]见该书318页。
[7]见《曲坛前辈话当年》。
[8]引文见《昆剧演出史稿》319页。
[9]见继贤女士《小世界昆曲杂志》,载《戏杂志》尝试号。
[10]见顾笃璜《昆剧史补论》,22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11]见该书卷一《高宗初政》。载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第35册,1983年4月版。
标签:京剧老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