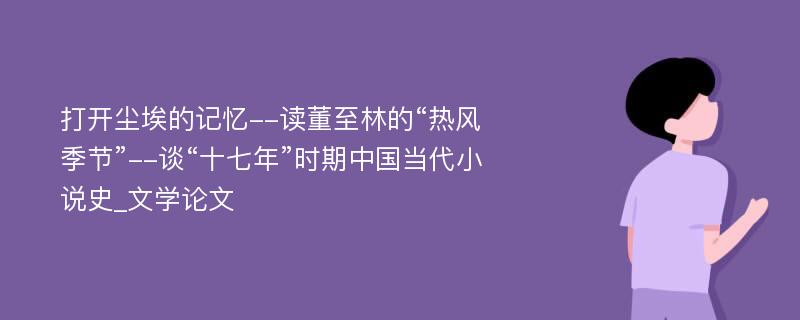
打开尘封的记忆——读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热风论文,时节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之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09)03-0141-04
“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命题提出之后,50年代小说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1](P7)董之林早先的这一洞见暴露了文学研究的“装置”。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学研究的反思无法回避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事件。我们今天的任何作业都离不开“重写文学史”所提供的场域。“重写文学史”曾经是针对既成的文学史秩序的一场反叛和暴动,然而,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名词,成为了一种不可动摇的秩序,成为了一种不容异见霸权。“重写文学史”建立起来的新的文学史秩序,“十七年文学”被编入另册。洪子诚老师在《问题与方法》中论及“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时说:“这个时期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性’,在文革结束后被普遍怀疑。在未能提出新的视角来证实这些对象的价值的情况下,它的被忽视是必然的。”[2](P7)董之林指出,建立在启蒙话语基础上的元叙述,具有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批判都难以企及的摧毁力量,甚至把这一时期的文学逐出文学史讲堂。这是现代性在“全人类”名义下,不同于以往“阶级”革命的另一种粗暴。“新时期”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把过去的评价简单地颠倒过来,把以前认为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把以前否定的加以“平反”,以“文学性”的名义重复了“十七年”和“文革”“大批判”的思路。[3](P119~121)她感叹文革结束后把学术问题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依然存在,某些人把“十七年文学”当成禁区。在他们看来,仅仅接触和研究“十七年文学”本身就有为“错误的年代”和“极左政治”翻案之嫌。[3[(P242~243)他们对“十七年文学”研究者侧目而视。在他们那里,大批判的对象变了,但大批判的思维方式本身却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在今天,研究“十七年文学”本身就需要一种巨大的学术勇气。
洪子诚老师认为,文学史是一种叙述,同时,所有的叙述都有其目的。因此,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同时,另一部分“事实”被不断掩埋的情形。[2](P31~34)董之林的小说史论具有明显的“对话”性质。她在“对《热风时节》的一些补充说明”中自谦是“与时弊同时灭亡的文字”。她说:“我选择‘史论’而不是小说史,是因为其中有太多需要论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或者不改变一些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这一时期小说的历史就难免不是支离破碎或毫无根据、不能成立的。”[4]她用自己的阅读悄悄地撬动了一些凝固了的结构和定论。
一体化/多元化、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回到自身等二元对立结构已经成为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固定的思维。很多人用“一体化”来概括“十七年文学”。然而,事实上,当代文学内部充满了空隙、悖论和张力。董之林指出,尽管“十七年文学”受到政治的制约,但是,它仍然与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保持着联系。“即便到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文学也没有全部被纳入所谓‘一体化’格局,小说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还在进行,因此对作品的批判也就从未间断。”[3](P19)“这些批判和干预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创作规范在具体实践中难以彻底实施。”[3](P86)因此,“一体化”可以说是追求的目标,却恰恰不是现实。
“十七年文学”创作受到政治粗暴的干涉,作家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有的甚至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由于这一段创巨痛深的历史教训,新时期一开始便有人提出文学要脱离与政治的关系,希望“纯文学”为“创作自由”提供一个庇护所。“十七年文学”作家的命运确实值得我们同情,“十七年文学”政治对于文学的粗暴干涉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但是,历史的灾难应该让人走向成熟而不是让人溺于天真的幻想,不然,我们就难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展开,我们对“理想的创作环境”等诸如此类的幻想有了初步的觉醒。洪子诚老师曾经指出:“作家的生活、创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有作品发表、出版的自由,以一种公正的尺度来获得评价:也就是文学生产处于一种没有暴力的、强制性的外力干预,特别是政治性质的干预的状态下——这种环境是我们长期以来所盼望出现的。但是,没有任何干预、制约、规范的文学环境是否可能?即使没有这种强制性的政治的干预,文学也会受到各种其他因素的干预,这些干预也不见得就是‘健康’,或者说‘自然’的调节。”[2](P142)董之林认为,“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与政治、经济、文化有一种张力关系。尽管紧张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不能成为文学史判断某一时期文学唯一的根据。事实上,作家从来没有等到文学的太平盛世,才去写不朽的作品。压抑与禁忌无所不在,但文学实践活动从来没有屈从于这个限制的过程。”[3](P12)既然“理想的文学环境”从来就不存在,因此,她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是去幻想“理想的文学环境”,而是努力真实地呈现“十七年”创作本身具体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她发现了周立波的唯美倾向,“它在不尽如人意、逼人就范的现实面前,高傲地展开自由的翅膀,为社会主义时代留下作家想象人性、感觉生活的文学经典。”[3](P175)赵树理没有被固有的现代知识和建基于此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所束缚,而是以自己顽强的个性开辟了自由的环境,使创作得到了自由的开展。[3](P129)不论是五四新小说、左翼文学、大众化运动,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赵树理的小说没有屈从于其中任何一个的限制。她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去理解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点。赵树理的小说采用的是一种“评东家长,说西家短”,近似“传闲话”的讲故事的方式。《登记》包含的是一个婚姻悲剧,但是,作家独特的叙述方式冲淡了这份沉重。赵树理把启蒙时代严肃的哲理转化为娓娓道来的世俗谈资的人生故事。她将长篇小说《三里湾》称作“是一部描写农村家长里短的小说”,传达了乡土中国的文化。赵树理把自己的政治观点隐藏在人物的生活故事里,把对人物的褒贬放在扯闲话、拉家常中,使作家对拥戴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意图表现得十分含蓄。赵树理在评书这一文学传统中形成的描写方式和价值取向,使他真正关注的是人物的道德审美价值,传统的道德审美追求无形中使故事逃脱了时代的政治说教给小说艺术带来的厄运。她认为,《三里湾》所反映的合作化运动可以不断地重新评价,但不同的时代都会倾向于赵树理的玉生、灵芝这些凝聚着比较恒定的传统道德审美酵素的正面人物,而不会认同“铁算盘”、“惹不起”这些卑俗的人格。[3](P80~85)如果说赵树理的小说顽强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的话,对赵树理的批评恰恰表现了它的僵硬、狭隘。“重写文学史”运动中对于赵树理的重新评价,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意。从历史上看,1980年代对赵树理的否定实际上是重复1940年代对赵树理的文化偏见。赵树理的小说尽管在出版以后风行一时,但是,当时却争取不到出版的机会,而压迫赵树理的是“现代小说观念”之类神话。[3](P127)
建国后最早反映农村阶级分化和合作化思考的作品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开后来五六十年代合作化小说政治激进化之先河。然而,董之林却指出,小说作者并没有生硬灌输,而是把现实演绎成一个有趣的故事,把合作化农村生活的矛盾和斗争,散漫在家长里短,吵吵闹闹,善良人之间不存芥蒂的原宥、关怀与抚慰中。小说家的政治见解在作品欣赏中反而退居其次,体现了作者对生活和人与人情感的和谐状态的追求。[3](P129)小说意在防止农村两极分化,但这层忧虑在宋老定的转变中被冲淡。让宋老定这个一辈子把心思扑在土地上的农民认识到乘人之危买地的错误,并自己拿出钱来资助一个因不善经营而濒临破产的农民。“作者选取的方式是将表现政治内容的作品日常生活化”。[3](P130)宋老定的转变不是通过生硬的“思想教育”,而是由于人性的感悟。这也应该是这些作品在当时被接受的重要原因。
董之林在评论1950年代出现的革命英雄传奇这样一种文学现象的时候曾说:“以当时社会的整体氛围来看,这些作品恰恰映现了新中国初期回荡在文化精神领域的浪漫情愫。”[3](P179)她将王蒙以及“干预生活”这一文学现象放置在另一种脉络上,从而具有颠覆性的阅读效果。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显然把“新”赋予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生活。[3](P218)“王蒙五十年代刻划了在时代背景下,一批热情、单纯、富有理想的青年跌跌撞撞地扑向生活的身形。”[3](P116)这些观点真正呈现了一个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富于青春、理想和浪漫的王蒙。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干预生活”的作家,实际上都是一些带有理想主义和激进化倾向的年轻人,把他们打成“右派”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误会和颠倒,是一个历史的玩笑。董之林敏锐地发现了“干预生活”的作品的“追求冲突,使日常生活尖锐化的创作倾向”。[3](P117)邓友梅的《在悬崖上》这样一篇描写爱情的作品,描写工地技术员“我”爱情、婚姻的波折,已经结婚的“我”爱上了从艺术学院毕业的雕刻师加丽亚。作品前半部分描写加丽亚如何有魅力、风度,让“我”一见倾心,觉得以往“平静似水”的婚姻生活原来是人生一场误会。但作品后半部分,加丽亚逐渐露出“在感情上剥削别人”的嘴脸,“我”也越来越“弄得像个资产阶级大少爷”。这样一来,原本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日常生活故事,人物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由于作者将作品的矛盾紧张、尖锐化、平庸的生活不平庸,平凡的人物也不平凡,与其说作品反映了一种生活的紧张,不如说是‘干预生活’的小说观念加剧了作品中的冲突的戏剧色彩,并逐渐形成一种将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紧张化、冲突戏剧化的小说发展趋势。”[3](P120)“干预生活”的作品的这种尖锐化现象反映了1950年代日常生活革命的特点。从1950年代“干预生活”到19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从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林震”到刘震云的《单位》中的“小林”,我们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中人物“成长”这样一个有意味的现象。《组织来了个年轻人》是青春和革命的故事。不论是1950年代的革命权威,还是1980年代的启蒙权威,都把“干预生活”的作品看作是“另类”,然而,实际上,“干预生活”这一文学现象正是激进政治的产物。
董之林将文学现象不是孤立起来,而是放在历史脉络之中去加以分析。“干预生活”这一文学现象,它既受到苏联特写作家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和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等同时代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同时,它也延续了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奠基的现代文学传统。像《红旗谱》和《林海雪原》等1950年代流行的革命英雄传奇满足了市民阶层的阅读趣味和要求,这些小说和中国古代小说、现代通俗小说血脉相联。1940年代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和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以传统评书和章回小说结构来反映现代战争生活,构成了这些小说直接的源头。
董之林注意到1940年代到1950年代文学环境的转换。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全国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文学的读者对象和阅读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解放区作家在解放后创作所遭遇的困惑和变化因此可以获得了解释。从解放区过来的作家萧也牧的变化,也只有放到这样的文学环境的变化中才能认识清楚。萧也牧在创作中对“趣味”的追求正是当时解放区作家适应文学市场、适应市民读者、适应这种文学环境变化的结果。而《关连长》注重对日常生活情怀的描写也同样和这种创作和阅读环境的变化有关。
在对骆宾基的短篇小说《父女俩》的分析中,董之林发现“农村合作化运动对妇女解放的意义”。合作化的生产活动,给香姐儿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带来了生活转机。香姐儿过去虽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如意,但是狭窄的生活范围束缚了她。合作化运动扩大了人与人的交往,打破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比较狭隘的封闭的格局,香姐儿终于有机会冲破传统的限制,找到了理想的爱人。作品通过一个女人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幸福的故事,表现了新时代和生活改变了人际关系。[3](P138)由于合作化运动生产关系的变革,造成了乡村日常生活的革命,产生了乡村新的生活样态。农村合作化运动形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高潮。在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中,大量渗入了乡村青年爱情的描写。农村日常生活的突变和乡村生活经验的更新,是为我们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
董之林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批评术语“史诗”的含义进行了有益的辨析。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与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中国古代倾向于把文言小说视为“史余”。董之林认为,“史诗”继承了中国史传的传统,而非西方古典传统中充满了幻想和征服色彩的“史诗”。[3](P68)这一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当代批评中将“史诗”作为一种充满价值倾向的评价,无疑包含了西方“史诗”区别于个人叙事的有关民族叙事的宏大叙事的特点。而作者在后面的论述中所展开的正是这样的特点:“现代长篇小说深受18、19世纪欧洲小说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以鲜明的历史观念来统帅作品的布局,也就是黑格尔关于史诗的哲学阐释,把现代长篇小说当作‘是一件与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的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为具体形象’。这种历史画卷表明‘这一民族已从混沌状态中觉醒过来’,‘已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感到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种世界里’。在这种写作观念统领下,作家对史诗小说的设计,自然有别于那种‘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一段一段没有总体结构的小说体”。[3](P70~71)胡适抱怨中国传统小说没有结构和布局,而像茅盾的《子夜》等现代长篇小说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时间的渗入和民族国家叙事的特点,现代长篇小说后面蕴涵了新的历史哲学,所谓史诗品质无疑与此相关。
董之林孜孜不倦、长期专注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追逐时尚的今天,董之林对“十七年文学”的专注和执着,说明了她不世故、不势利的性格。在我们看来,不世故、不势利正是学术的一种必要的品质。
[收稿日期]2009-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