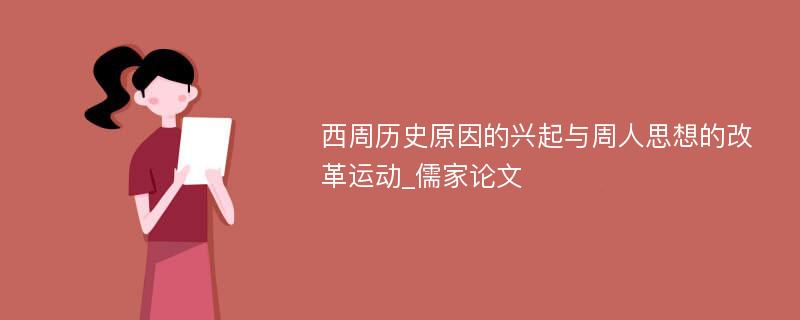
西周历史理性的崛起与周人思想维新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新运动论文,西周论文,理性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是先秦时期最重要最关键的思想家,借用雅斯贝斯的话来说,他是中国文化轴心期的中心人物(注:Karl Jaspers,'The Origin and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65.)。但是, 孔子“述而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他崇拜周公,笃信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毕一生之精力用来总结继承西周时期的礼制、思想伦理和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文化的初步建构是从西周时期开始的。这种思想文化的初建是从历史理性的崛起以及往古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批判开始,并在思想维新运动中逐步形成的。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分析总结的。
一
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认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史前时代,二是古代文明时代,三是枢轴期时代,四是今天的科技时代。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在公元前800—200年的第三个枢轴期时代,许多哲学家首次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地区出现,这反映了人类意识的觉醒。这时人对历史有了认识,开始以自己的内心世界抗拒外部世界,借此超越自己和世界。这一时期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起点,在此过程我们看到了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这就是“枢轴时代”。雅斯贝斯的枢轴时代是他的历史理论的核心。他认为在历史枢轴时代之前,由于精神运动没有进入意识,因此人们对历史得不到领悟。这时历史出现停滞状态。而当历史变革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时,旧秩序崩溃了,人们的压力增强了,人们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思绪翻腾。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首次感到了精神压力,而这种压力后来一直对人类起着作用,探索人类的全部活动,并用来赋予它新的意义。而且这种历史的反思使人们意识到,今世是以无限的过去的历史作为先导的。这时历史意识会获得解放,历史就发生了“突破”(注:Karl Jaspers,'The Origin and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65.),这样就进入了历史轴心时代。
中国历史的轴心时代也是首先以认识历史和历史意识的解放作为前提的。笔者以为中国轴心期的发展历程有两个重要阶段:一个阶段是在周初,另一个阶段是在春秋中晚期。第一个阶段是殷商灭亡之后,周人面对着大邑商的顷刻瓦解,不断总结夏人和殷人的经验教训,从殷人神权崇拜与天命观的禁锢中苏醒过来,历史意识获得了解放。
周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回顾,大概始于文王时代。《诗·大雅·荡》篇引文王所说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则为文王叹惜殷纣王不借鉴也不重视夏后氏被商汤灭亡的教训,朱熹《诗集传》说:“殷鉴在夏,盖为文王叹纣之辞。然周鉴之在殷,亦可知矣。”文王一方面为殷纣王而叹惜,而另一方面则以此作为可供周人借鉴的历史教训。殷商灭亡之后,周武王、周公以及其他一些有为的周王和辅政大臣更是常常总结夏殷两代人的经验教训。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对夏殷两代成功的统治经验的总结以供学习、效法;另一种是对罪过、错误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以供戒备和警惕。
姬周统治集团武王、周公等人在总结经验时首先对先公先王特别是周文王成功的业绩、美好的品德给予充分的肯定。《书·康诰》中周公说:“惟乃丕显考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周公认为周人之所以能够受天命是因为文王有美好的品德,“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而且能够“敬贤讨罪”:“庸庸,祗祗,威威”义即“用其所当用,敬其所当敬,威其所当威”(朱熹《诗集传·康诰》)。因而感动皇天上帝,并降天命于文王。《逸周书·祭公》(注:李学勤先生比较了西周金文与《逸周书·祭公》中的文字,认为《祭公》篇是西周时期的作品,是可信的。见《祭公谋父及其德论》,《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中总结了周文王、武王等先王克殷及其守业的成功经验,其篇中祭公说:“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维天贞文王之董用威,亦尚宽壮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绥厥心,敬恭承之。维武王申大命,戡厥敌。”在《书·无逸》中,周公对太王、王季、文王的美德作了总结和赞美:“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特别是周公把文王和殷先王中宗、高宗及祖甲放在一起,给我们描绘出一副宽宏大量的哲王形象:“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也就是这四位哲王不仅对埋怨自己、詈骂自己的小人不生气发怒,而且警戒自己的品德,也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正是他们有这样的宽宏大量,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才有极高的地位。与那种一听到说“小人怨汝詈汝”——即使这小人的造谣,却信之不疑——且不宽大为怀并“乱罚无罪,杀无辜”的昏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人们怨恨也就自然而然地集中到这些昏王身上了。周公语重心长地告诫后来继位的周王要以此为鉴:“呜呼,嗣王其监于兹!”另外《酒诰》中叙述周文王时期禁止人们酗酒:“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也正是由于文王的教令,周人才取得了殷人的天下,“我西土……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这些都是周人之所以成功的宝贵经验。
周人不仅总结了周先王成功的历史经验,而且总结了殷先王成功的历史经验,并对这些经验予以高度的赞扬。周公在《康诰》中反复要求康叔“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在《酒诰》中,从成汤到帝乙时的“殷先哲王”和帝辛纣王时“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等现象完全相反:“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在《无逸》中,周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君王之子不能只图安逸,而应“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的观点。与祖甲之后因立储君而“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的情况相反,“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可见帝辛纣王之前的殷王,既有美德又很贤明,对人恭敬,不敢酗酒,亦不敢追求闲暇安逸的生活,这是殷先王之所以能长久统治天下的原因。这些是从正面对勤劳和关心小民的历史经验作了肯定,对君王追求安逸舒适、酗酒淫泆的生活方式作了否定。
姬周统治集团的领袖们还对辅政大臣的重要作用及其用人的成功经验作了历史总结。《书·君奭》中周公说:“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也正是殷先王有这么一些辅政大臣对殷王忠心耿耿的辅佐,“保乂有殷”,所以殷代才有“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的局面。在那个时期,连众官小臣,也都是有德明理,尽职尽责:“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这也是殷人能长期统治天下的原因。不仅殷人如此,周人也是如此。《君奭》还谓文王有天命之时,有四位贤臣辅佐: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正是这四人“纯佑秉德,迪知天威”,后来周文王才“受有殷命”。到武王时也用了这四个人,武王才“诞将天威,咸刘厥敌”。《君奭》篇中周公对殷代不少辅政贤臣保殷而殷王享国多年的历史事实,以及文、武王时期四位贤臣辅政而克殷受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回顾,这是为了在武王死后年轻的成王即位之初,共渡周初“天下未宁”之时的难关。
《书·立政》中首先对夏桀和成汤用人的情况作了回顾比较:“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亦越成汤陟,丕厘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接着又对纣王和文武王用人的情况作了回顾比较:“鸣呼!其在受德,愍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亦越我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夏桀不用旧臣而亡,殷纣用暴德淫泆之人而灭,成汤文武用有德有能之人而兴,周公认为这些历史经验值得周一代又一代的后嗣王接班人借鉴。
周代的统治者甚至回顾远古时代的历史,以此作为治国的经验与教训。《书·吕刑》篇记载了周穆王正刑书,回顾传说中黄帝惩罚苗民建立刑典的史实,以作为制刑典的历史依据。也就是这些历史经验的回顾为周穆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说:“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这就是说断狱要合情合理,不能像苗民那样乱罚无辜,否则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在《逸周书·尝麦》(注:李学勤先生认为《逸周书·尝麦》篇与《吕刑》记载同一件事,时代亦应相近。见《〈尝麦〉篇研究》,《西周史论文集》上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篇中亦记述了周王以“古遗训”来正刑书的事迹。周王回忆说:“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这正是“天之明典”的正面教材,为当时的周王室正刑书、明刑典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资料。
二
周代的统治者对刚刚覆灭的殷王的过失和教训尤其重视。《诗·大雅·文王》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大邑商”现在不得不“侯服于周”,这真是“天命靡常”。但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周初周王室的统治者武、成、周、召等王公常常思考殷代以及夏代灭亡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末代君王都残暴无德。《逸周书·商誓》中周文王说商纣“多罪”,武王指责商纣“昏忧天下,弗显上帝,昏虐百姓”,而且竟然“弃成汤之典”;《逸周书·明堂》中说“大维商纣暴虐,脯鬼侯以享诸侯,天下患之”;《诗·大雅·荡》中总结商纣的罪行有“天降泆德,女兴是力”,“寇攘式内”,“敛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而且不用旧臣,不用典刑,以至于国内“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远近不服,人神共怒,导致“大命以倾”。
周人总结夏桀、商纣的灭亡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用人不当。《书·立政》说“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其在受(纣)德,愍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代)商受命”。商纣用人不当的过失还见于其他不少的载籍,如《书·牧誓》说“今商王纣,惟妇言是用;……昏弃厥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大雅·荡》篇也说“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等等。可知商纣一是不用宗亲,二是不用旧臣,也不用《大雅·荡》中所说的“老成人”;而用的尽是残暴、有罪和无德之人。夏桀也是如此,用人不当则加速了夏桀、商纣的灭亡步伐。
夏、商败亡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周初统治者也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总结。首先是由于不敬其德。在《书·召诰》中,周公反复告诫成王要敬德,“王其疾(亟)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殷人、夏人败亡的反面教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尽管夏殷两代享国均有许多年了,但他们“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这一教训应该认真地总结并引以为鉴。因此《召诰》中两次说“王其疾敬德”,《康诰》中提出“明德慎罚”,《酒诰》中说“经德秉哲”,也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反复强调、反复宣传的。
其次,是由于逸乐游田、酗酒等恶习陋风。周公在《康诰》中告诫康叔“无康好逸豫”,在《无逸》中一开始便提出“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原因也就是从祖甲之后的殷王全都是逸乐享受的短寿之徒:“自时(指祖甲)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是厥后,亦罔或克寿。”正是因耽乐淫泆而导致殷人灭亡,《书·多士》谓商纣“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而夏人的灭亡也与淫泆有关,《多士》说夏人“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因此,《无逸》中告诫以后要接班的周王,“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严禁逸乐游田。周初统治者对殷人群饮酗酒的风气更是深恶痛绝。《书·酒诰》中回顾周文王时告诫“有正有事,无彝酒”,因此国人只有祭祀时才饮酒,且未到醉的地步——“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而殷人从成汤到帝乙时期的殷王也都是“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那时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内服百官百僚、庶尹、亚、服、宗工以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这就是说成汤到帝乙时期的内外服众臣百官都不敢沉湎于酒,不仅不敢,那时他们都忙于自己的职守根本没有闲暇时间去饮酒取乐。而到帝乙之后的继承人商纣时期就不行了,他自己饮酒作乐,因而百官百姓都沉湎于酒,淫泆作乐,无法无天,以至于惊动了上天。此类记载也见于其他的文献及金文之中,《无逸》篇说“无若殷王受(纣)之迷乱酗于酒德哉”;金文大盂鼎铭文中周康王告诫其臣盂说“酒无敢酣”,并把殷商灭亡的原因直接地归于嗜酒成风:“我闻殷述(坠)令(命),唯殷边侯田(甸),越殷正百辟,率肆于酒,古(故)丧师祀”(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9~170页。)。因此周初统治者下决心禁止群饮嗜酒的恶习, 《酒诰》中专门责令有关大臣“刚制于酒”;并下令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这些措施命令都是出于总结殷人亡国教训的基础上而采取的,也都很典型地反映了周初统治者的历史意识,也充分发挥了历史的认识功能和借鉴作用。
另外,周人克殷后也曾为自己的夺权斗争寻找历史依据。《书·多士》中成王告诉殷遗民多士说:“尔殷遗多士,弗吊(淑),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我闻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适逸,则惟帝降格,……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与此大致相同的说法也见之于《书·召诰》当中。这就是说,从历史典册中可知,你们殷人革了夏人之命是听从了帝命,是正义的;那么,我们周人革你们殷人之命也是听从了帝命,也是正义的。这种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告诫后人的做法在西周时期是周人的一贯做法。
历史意识的升华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批判总结,使周人逐步摆脱了殷人那种完全用神权来维护政权的思想观念。周初以武王、周公为首的姬周统治集团及其有识之士能够以历史理性来认识政治、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否定天命并提出“敬德保民”等思想主张,推动了一场思想维新运动。
三
殷末周初,周人常称自己为“小邦周”、“我小国”(《书·多士》);而另一方面不仅殷人在卜辞中把自己所居住的商都称作“大邑商”(合集36482,36507,36511,36530)、 “天邑商(合集36541 ,36542,36543,36544,英国2529); 而周人也把商都称之为“天邑商”(《书·多士》)、“大邦殷”(《书·召诰》)。但是文明程度不甚高的“小邦周”一下子打败了文明程序相当高的“大邑商”,取而代之而为天下共主,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周初姬周统治集团的领袖们(周武王、周公等人)的思考,“天命靡常”,可见天命是不可靠的:“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书·召诰》),说明自己也不是上帝一味偏袒的“元子”、“帝(嫡)子”。而早在文王时代,以周文王为首的姬周统治集团就对“天命”观产生了怀疑,并把这种怀疑用变易观点反映在《周易》之中了。同时,周初武王、周公伐商取得天下,但不得不总结借鉴过去夏、商两代的反面经验教训,“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书·酒诰》),意思是我们别只在水面前观面容、整衣冠,还应当借鉴夏殷两代的反面教训来检查我们的缺点和过失。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
姬周统治集团的领袖们对殷人的天命鬼神观反思的同时,认识到了“天命靡常”之理,树立了敬德保民的思想。殷人认为天命素定,故尊神事鬼。《墨子·非命中》引《太誓》所说“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我民有命,毋僇其务”;《礼记·表记》谓孔子比较三代之礼,谓夏周均是“事鬼敬神而远之”,唯独“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正好与卜辞中所见的情况是一致的。而周人认识到了天命是无常的(《诗·大雅·大明》),把殷人眼睛中上帝祖先神偏袒子孙的观念矫正过来了,《左传》僖公五年载宫之奇之语说:
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翳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凭)依,将在德矣!
《周书》佚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民不易物,惟德翳物”,正是周初统治者反思尊神敬鬼的殷人骤然亡国的教训而产生的思想成果,并由此产生了人道观念、俭朴精神和敬德保民的思想。《书·无逸》中周公要求周之子孙应“先知稼穑之艰难”,居于统治阶级上层应“知小人之依(隐情)”;不可“盘于游田”,不可“酗于酒德”,不可“乱罚无罪,杀无辜”;应该宽大为怀,“宽绰厥心”。《召诰》曰:“肆惟王疾(亟)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在这些诰命之中,周公反复强调要以“敬德”来祈天保命。“敬德”就能保住天命,不敬德就不可能保住天命。尽管你现在享有“天命”,但最终还是会失去天命。而这种“明德”可以追溯到周文王时代,《书·康诰》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梓材》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君奭》:“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曷)申劝宁(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周文王由于“克明德慎罚”,由于“惟德用”,受到了上帝勉励、奖励:“在昔上帝割(曷)申劝宁(文)王之德”,“割”是“曷”的通假字,“申”是申令,“劝”是勉励、鼓励,意即上帝为什么申令、勉励文王的美德呢?春秋时代的人们对周文王的“明德慎罚”思想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周人兴起的关键所在。《左传》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对楚庄王说:“《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
而从西周金文中也可看出周人对“德”字的重视。如:
惠(惟)王恭德裕天,顺(训)我不敏。(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页。)
丕显皇祖考穆穆克誓(哲)厥德,严在上……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丕显元德。 (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9页。)
臣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保(?)纯,乃用聪弘正乃辟安德,惠(惟)余小子肇淑先王德,……丕自作小子夙夕敷迪先祖烈德。(注: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2页。)
周初统治者认为要维护国家的统治,要保住天命,就必须加强德治。天命是难以固定的,是时常变化的;皇天也是没有亲人的,仅仅辅佐有德之人,随时随地可以“改厥元子”。因此受天命者必须经常地注意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大雅·文王》)。显然这种观念是有进步因素的。
雅斯贝斯认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转折点在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时代,他曾经说道,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最伟大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此时中国有孔子和老子,还有墨子、庄子和诸子百家,产生了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而孔子无疑则是先秦诸子中最早最关键的思想家,是轴心时代的中心人物(注:Karl Jaspers,'The Origin and Histo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1965.)。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所提出的思想观点以及许多命题,都是诸子所争论辨难、或赞成或反对的热点话题,他的主要工作是认真总结继承前代的礼制、道德观念以及文化遗产。孔子所憧憬向往的时代主要是西周,他所崇拜的偶像是周公,甚至做梦梦不见周公则认为是他衰老的标志、人生的遗憾。孔子崇拜周公大概与周公建立了有周一代的礼乐制度有关。孔子醉心于礼乐制度,《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古籍传说中谓周公是礼乐制度的创建者。《史记·周本纪》谓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礼记·明堂位》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周公制礼的最早记载是《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大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能事民。”依此,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不尽可知,但其传说应是可信的。也正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因而周代的礼乐文明在鲁国保存得最为完善。《左传》昭公二年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杨向奎先生说:“鲁遵守西周传统,‘周礼在鲁’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而齐偏离此一轨道,遂有‘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适当概括”,“‘周礼尽在鲁矣’等于说‘周之文化中心在鲁’”(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这是对的,但周公制礼有哪一些内容呢? 传说中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的说法,也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曲礼》)的说法,但对于这些,过去我们是不知哪些周人古已有之,哪些又是承殷人而来,又有哪些是经周公的创造而成。杨向奎先生曾经分析说:
来源颇古的礼,西周初经过加工改造,以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比如《大武》来源于原始战争中的呐喊助威;原始社会礼仪之交易的性质变作西周之交易而带有礼仪色彩,也就是在“礼尚往来”中减轻了交易性质。这种改造工作出自西周初的统治者,当时和后来人都把这种工作推到周公身上,所以有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因此遂谓《周礼》、《仪礼》也出自周公。(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1页。)
杨先生的说法代表了大部分学者的看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近现代学者也已认识到西周至秦朝时期在历史上的重要价值与作用。王国维曾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用“能动时代”与“受动时代”来概括我国古代思想学术发展的几个历程。他认为从周朝衰落到汉以前,“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郭沫若在30年代所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曾有三次社会革命运动。他说:“中国在事实上只经过三次的社会革命。所以我们在文化史上也可以看出三个激越的时期——真真正正是划时代的时期:第一,《易》、《诗》、《书》所代表的一个文化的集团;第二,周、秦诸子(孔子一门包含在里面)的一个文化的集团;第三,近百年来科学与中学的混战。”还有一些学者则从儒家与周礼的文化渊源关系来讨论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主体文化的来源。梁淑溟在1949年所作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把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特征称之为“周孔教化”,周即周公,孔即孔子。梁氏说道:“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杨向奎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鲁遵守西周传统,‘周礼在鲁’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道’也就是宗周的礼乐文明,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时代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宗周→春秋;周公→孔子,构成三千年来儒家思想之完整体系。”(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
今天,我们在讨论孔子之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作用之时,不能不首先肯定周公等人的历史功绩,不能不给周公等人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因为周初周公等人是2000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思想的奠基人,而孔子只是继承和宣传者。在上述引文中,王国维所指出的关于殷周之际是中国制度文化大变动时期以及春秋末到战国时代是我国唯一的“能动时代”的观点;郭沫若所说的我国文化史上真真正正的划时代的三次“革命运动”,而最初一次就出现在西周时期;梁淑溟和杨向奎等学者所指出的儒家在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儒家文化的来源在于西周之初。这些学者虽然分析角度不同,但结论却大同小异,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总的说来,春秋战国时代的确是中国思想文化能动的创造时代,是轴心时期,而西周时代是这一思想文化的奠基和发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