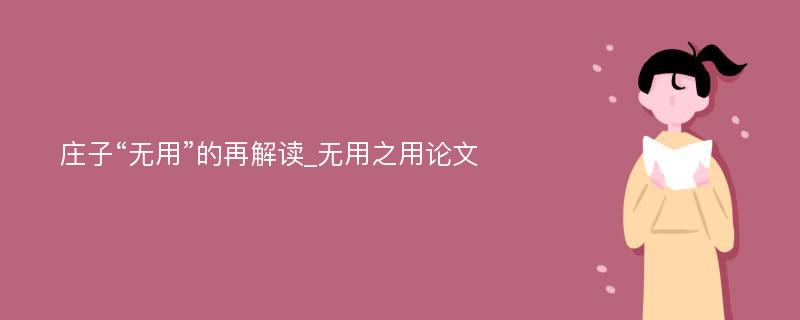
庄子无用之用的另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之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庄子关于无用之用的意向一直没有受到特别关注。一般认为,它是以隐喻的方式对自然无为之道的拟说。任何物只要运用得法,都能带来大用;一切用都资大道的无用而成其用。即是说,它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道和物的用是什么?本文认为应该继续追问下面一个问题:用对物意味着什么?尤其是,无用之用对物的意义意味着什么?这个追问才在某种意义上触及了庄子写作的核心,它显示了庄子与其时代的遭遇方式。本文准备抛砖以引起对庄子无用之用的相应关注。
一 孔孟的天命承当和老子的无与用
一个时代的巨变往往导致思想的空前繁荣。处于轴心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儒道墨法等诸家之说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局面。
孔子所在的春秋之末已是“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而且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和大夫出,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等“无道”的现象。孔子以继承文王、周公为职志,力图恢复周礼,并认为这是一种上天赋予的使命,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这种约束个人心志、承天负命的伦理实践就是克己复礼的内涵,也就是仁。“为仁由己”开始了儒家觌体承当的传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论语·卫灵公》)孔子以一以贯之的实践理性精神,挽历史于既倒。
孔子的仁在孟子那里回落到心上,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孟子·告子上》)就是说,人同此心,心有仁义礼智四善端,它是普遍之性,每一个人生而俱备,即善性。而性是天在心上的反映,所以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歼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可知,从孔子的承天负命,到孟子的修身立命,更多了一层义理的追求,承天负命变成了自觉的心体承当的精神守护。
牟宗三认为,“尧、舜、三代之开物成务皆是有德有生命、自身挺立、合聚群力以创造者……及孔子对于道之本统之再建与孟子之承孔子再建而展开之理想之弘大。此是重造之源,开物成务之本。”[1—p251] 而这也就是“天之命於穆不已,以成天命之流行,天道之生化,……亦即性命之不已,以成道德的创造,以成道德行为之无间,纯亦不已。”[1—p421] 即是说,牟先生认为孔孟证成的是一种仁体的“生化之大用”[1—p258]、一种生成不已,没有间断的仁德之实功。
牟先生正确地指出了原始儒家弥合时代质变和断裂的一种无间不已的道德创造之功用。儒家要树立一个承天负命以救世的理想,通过某种圣德仁智证悟、彰显天道性命为一,打通道德界与自然界,成就内圣外王之道。这是浑然一体的生化大用之境,也就是无,不过“与道家之只以有为与无为对遮而显之‘无’,复直以‘无’为道之本,固有间矣。”[1—p215] 牟先生以此批判道家:“老庄只知就此化境而言‘无’以为道,而实体之道(仁,天)则蕴而不出,隐而不彰,其生命总不肯向此鞭辟入里而觌体承当,此其所以一间未达而流于偏支之故也。”[1—p215] 这也是继荀子对庄子的“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无用性批评的展开。
其实,老庄是作为儒家的对立话语出现的,老子批判统治者以仁义之词掩盖下的巧取豪夺、用民无度,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四十八章)即是说,大道已经荒废,现在的统治者所做的一切,和替匠人斫木头一样,徒劳无功。所以,他开启了无—用、道—用之用。毋宁说这是一种反思而不是救蔽之用。
在第十一章,老子说:“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用之为用,如车之用,器皿之用,居室之用,只是因为它们自身含有虚空之处,而成就了各自的有用性。虚空在这里就是老子的无,此无被认为属于车、器皿、居室本身,是它们的构成,不是和别处的虚空相同的虚空。在常识看来,只有摸得着、看得见的材料才构成用,老子却突出了无对用的构成。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老子》第四十五章)就是说,最丰满的东西好像有欠缺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衰竭的;最充盈的东西好像是空虚的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没有穷尽的。
这样,老子就把无和用联系在一起。无作为最丰满最充盈的东西是天地的本始,《老子》第一章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从无中观照道的奥妙,从有中观照道的端倪,无和有共同来自无限深远的道。所谓观照就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第十六章)“观”王弼解为:“以虚静观其反复。”[2—p36] 即认为老子领会到:万物以静为根,静而无穷无极,万物反复其中,得性命之常。观万物复归其根,就是经验道的以无为用,环转往复之态。也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老子》第四十章)无成为道的本质规定,而道是万物归根复命之所,所以万物以无为本。由于无的充盈性和丰满性,万物之用就获得了无限性。又因为无没有极尽而且不引人注目,所以物之用还具有平凡性。
可见,老子区分了有之用和无之用,更强调无与用、道与用的关系,认为无才是用的根源和构成,用只是作为无和道的结果。这样老子的用就不是无用之用,而是具体的用,是无和道自身产生的具体之用。就是说,老子是揭示无、道之用,而不是关于用之为用本身。
所以在最终的目的上,与孔孟理想期望于直接的拯救之用不同,老子把用置于无、道之下,其实是主张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策略。因此,老子推崇自然无为,给具体之用以无本体,追求无、道之用,是对春秋时代“有之用”的反冲,是对另一种不同于当下用之为用的尺度的追求。这另一种尺度老子在他的“理想国”中有所透露:“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这个国家里,器械、车船、铠甲武器无所可用,而人们却生活得安宁快乐,预示了庄子的无用之用。
老子的“无之用”是与时代关于“有之用”的主流态度的脱离,它必然是在与时代的冲突中产生的。冲突意味着相遇。老子的理想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子这样做本身以无—用、道—用的间距性方式与时代相遇了,暗示了时代的某种转折。
庄子不再追问无和道本身之用,而是颠倒过来,从无用之用本身出发,追问道和无,追问物的意义。
二 庄子的无用之用
庄子在《天下》篇中对他所处时代的学术境况进行了如下描述: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
在学术上,庄子作了方术和道术的区分。全者谓之道术,分者谓之方术。[3—p757] 治方术者,得一偏以为全,以所治之术为无以复加。治方术的百家“往而不返”,即不再返回显现天地之纯美、完备的古之道术;道术是对作为存在者整体的宇宙人生本源的探讨。百家以一曲之小道为用衡量整个世界,道术之裂成为必然。庄子要跳出这种纷争就不能再投入其中去辩论,而是以无用之用来比照小道的不足。
庄子是如何引出对用的讨论呢?我们选择从《逍遥游》进入,这看似与用不沾边的篇目,其实正是需要我们极力注意的。《逍遥游》开篇,北冥中的鲲化为鹏而高飞,之后出现了斥鴳对大鹏的疑惑:“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一发问,大鹏无从知道,它距地面太高无法作为提问的对方,所以,斥鴳是在向自己提出疑问,支道林认为:“鴳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之心也。”[4—p1] 矜伐之心也许有,但主要是疑问被大鹏的高飞摄来。大鹏作为“飞”之大者,在无言中象征了对“飞”自身的超越,不管斥鴳自己如何回答,这个疑问本身显现了某种不安;同时,把我们这些汲汲以求有用性的阅读者也卷入其中,惊异于庄子这一不同寻常的小大之喻。
对于斥鴳与大鹏的关系,郭象注云:“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4—p9] 郭象是在字面上理解斥鴳的话,而斥鴳为何能提出此问的机缘被他漏掉了。如果是自足其性斥鴳就不会产生疑问,疑问源于不足,关键的是斥鴳大鹏互相参照所呈现的“飞”的差异和距离被突出出来,而不是各自的自足其性。如此一个势态没有被郭象把握住。大鹏致远绝不仅是树立一个无限自由的理想典范,然后我们再跟着它作玄而又玄的空想。这里面隐藏着庄子的玄妙。
庄子在《逍遥游》中以大鹏致远开篇,以惠子和庄子辩用结束,难道有什么特殊的关联吗?惠子借困于瓠大而无所可用之题向庄子抛出辩题:我种的瓠的果实有五石那么大,用它盛水,它的坚固程度连自身的重量都难以承负,把它剖开用作瓢,它又太大了而没有地方放,大物如瓠因其大而无所可用所以应该打碎它。成玄英疏云:“惠子所以起大瓠之譬,以讥庄子之书,虽复词旨恢弘,而不切机务,故致此词而更相激发者。”[4—p36] 这一疏解是郭象所没有的,并且是点睛之笔,惠子的内在用意全出。相对于惠子的观点,庄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蓬心,是拙于日常之用的常识之心,大瓠之实大而不适日常之用,超出了日常需要的范围。瓠可以作为大樽,浮于江湖才是瓠之用。但此用与日常之用只是用途不是一样吗?如果所用相同,为什么庄子说惠子拙于用很大呢?
惠子又问难樗树之大而无用,也直指庄子:“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说:“子独不见狸狂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事实已经清楚:惠子认为庄子的言论大而无用如同“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人不顾”的樗树。庄子认为,无所可用没有什么可困苦的,随即他给惠子描述了那个著名的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植大树其间,逍遥乎寝卧其下,虽无所可用却免遭斤斧之害。
其实,庄子所在的时代物只作为有用之物才成为物,一切都要经过用的衡量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就是说,用现在成为了物的主宰,物只存在一种可能性、一种意义,那就是作为实用之物而存在,物失去了生命和精神性。精神要么被斥之为无用,要么就得被有用化、实物化。然而,只要世界上当且仅当只存在一个尺度,那么这个世界就必然可以被判定为是分离和断裂的。一个尺度是一厢情愿的掩盖,而掩盖本身就揭示断裂。
所以庄子的用不同于惠子的用就在于,庄子区分了用和无用之用,前者是日常的具体的、直接之用和无用,后者是使用成为用的用。在《外物》中,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只有区分了用与无用之用才能理解本真的用。物诚然是有用的,但用并不是物的本性,物自身涵有更多的东西:天与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自身存在的至理却不显露;物方生方死灵妙精纯,六合之大不足以超越它,秋毫虽小却不能被遗弃,万物沉浮变化,各有顺序,受到蓄养而不知。物的日常的有用性要以无用之用为归宿,仿佛只是沧海中的一瓢而已,所以庄子认为圣人观于天地,不作无为,即是说要参入到万物的无限之中。
无用之无,是在用上开的一个开口,用被无化,无用之用意味有什么东西在另一层次上,它就像能容大物的冥海,深不可测,那里聚集了物的本质和意义。那个无何有之乡穿过具体之用的界限,提供了另一种尺度和感受方式,用成为无用之用的无所用、无何有,同时无何有之乡敞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是一个精神世界,是物能保持自身的意义的王国。一个逗留于断裂之中而成就自身的精神王国,同时也就是对丰满、完备的世界,对物的自身意义的保持和尊重。
开篇的北冥与南冥,终篇的无何有之乡,都是大物、大用的栖身之所。大物者是对物的出离、超出,大用者是对用的出离、超出,出离用的大用是对物的本质的保持,即无用之用才是物的意义。鹏和瓠樗是大物的象征,它们给沉浸日用之间的人以一种惊醒和无措,打乱日常的思路安排的可靠性,就是说,让我们在与日常之物保持的间距中和它相遇,因为“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5—p20] 与熟知的东西相遇,就是与它亲近,但此时不再是在无间性的具体直接之用上的亲近。没有出离就没有相遇,出离就是保持与物的切近。春秋战国时代的质变和断裂表现为对无用的抹除,物只是有用之物;同时,思想也被有用化,被削除了精神性。任何出离有用性表面的东西都要被削除。被有用性打包在一起的无间性的东西恰恰失去了切近性,“切近之缺失已经使无间距的东西占据了统治地位。”[6—p1182] 所以在第一篇《逍遥游》中,庄子就透露了他的写作意图,那就是对间距性本身的保持。
然而,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保持无用之用的间距性是庄子的努力之处,那么,又如何理解以《齐物论》为代表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无间性”呢?
三 齐物论与无用之用
关于《齐物论》的题解历史上各家争论不休,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认为,不外“齐物”论、齐“物论”两派。现在也有人认为再加上齐“物我”综合三派而贯通才是庄子的本意[7—p19]。
无论哪一种立场,理解“齐物论”,首先要知道齐的含义和来历。注家对齐有几种解释:一是,齐被作为一,合众论而为一之义;二是,平等、平均之义;三,齐被释为适宜之义。如果我们再往下追究这些解释的本源,那么就要回到中国夏商周开始形成的礼乐祭祀文化,儒道诸家都源其而来。《礼记》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礼记·乐记》)礼乐模仿天地五行之流动不息,礼用来区别事物,确定事物自身的界限,乐用来调和阴阳动静,以承天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沟通生者与死者,通乎鬼神,祭祀先祖:“圣人……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以由生也。”“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礼记·祭义》)祭祀是对天地、鬼神、祖先的敬畏和感恩。为了表示敬,祭祀前必须斋戒,斋戒属于礼,斋与齐有什么关连吗?《礼记·祭统》中有一段话:
及时将祭,君子乃齐。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非有恭敬也,则不齐。不齐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齐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
齐,就是斋的意思。徐灏《段注笺》:“齐斋古今字,相承增示也。”[8—p10] 斋是齐的后起增偏旁体。《说文》:斋,戒,洁也。齐省声。斋戒就是祭祀之前整洁身心以示虔敬的行为。斋戒就是心志齐一,精诚纯洁。齐,《说文》: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古不用斋字,凡斋祭之字即作齐,所以齐具有心性内容。齐不齐,防备、限制人的嗜欲,使心志齐一,就是保持纯洁、恭敬之心,这样才能达到精诚之境而与神明交通。钱穆认为:“惟其齐之心境,其最初所指,乃为先祭当祭时之一种心境,故古人常以诚敬训齐,《礼记·祭义》:‘齐齐乎其敬也。’《国语·楚语》:‘齐敬之勤。’《诗·洞酌》:‘齐絮之诚。’《诗·采絩》:‘有齐季女。’传‘齐,敬也。’凡此,皆古人以刘训诚敬之心情之证也。”[9]
在《人间世》里,孔子告诉颜回心斋致虚之事,其中的斋就是齐一的意思,就是虔敬而专一,孔子曰:“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只有心志专一,用心体会,才能空明照物而通达大道。
所以齐在原有的含义上还具有虔敬专一之义。万物齐一就是保持斋戒的虔敬之心,以无用之用与物相沉浮,保持作为存在者整体的物的丰满性和无限性,天地万物寓于道枢的环转中。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其实最关键之处是:人们对世界失去了虔敬之心,礼乐成为外在的形式、工具,被用来包藏私心,为各自的一点实利,师心自用,只争朝三,守一隅而尽失其余,道物互失,世道互丧。礼乐不再应天配地,它们失了精神性的意蕴。
庄子以“齐物论”名篇,实是以“吾丧我”除去小我之私,外物与生死,保持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因是因非的道枢之无穷环转,齐物论是精神的一次对私心之用的脱离和超越,也是对自身的返回;以齐敬之心观天地万物,才能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虔敬之“我”不再仅仅以有限性、有用性度量天、地、万物,不以承天命自居,而是与天、地、万物保持无间不离的关系,只有保持虔敬才能保持物性、最终也才能保持人性。这是齐物论的意义。具有齐敬之心才能成就大道、大言、大仁、而与实用的道、仁、言保持存在论上的间距,这是对界限的一种真正的确定和守护。就是说,齐之为齐,消除了言物道的封限,体现的是存在论上的天地一体的无间的道境;同时,此无间性就是对存在者层面的物的超出,此时,在对物的虔敬中,恢复物自身的意义,让物自己存在,因此,无间的道境作为一种对“有用之物”的超出,就是对物的无用性的保持,物作为无用之物存在。
我们可以借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来理解无用者,他说:“人对无用者无需担忧。凭其无用性,它具有了不可触犯性和坚固性。因此以有用性的标准来衡量无用者是错误的。此无用者正是通过无物从自身制作而出,而拥有它本己的伟大和规定的力量。以此方式,无用性乃是物的意义。”[10] 现代技术对物的态度是工具性和有用性的,海德格尔从现代技术对物的遮蔽的意义上追问物本身的意义,把物作为无用者是对物的一种新态度,是一种诗意的态度,是追问存在本身。而在庄子看来,物在这种无用之用的无限中体现着道的不息,而道的无处不在、宁静肃穆的力量赋予物自身以尊严和意义。虽然海德格尔与庄子对物的无用性的阐释有重要区别,但他们仍具有独特的比较意义,那就是,无论何时对物的态度就是人对自己的态度,对无用之用的保持就是人对自身意义的保持,“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我”与万物在相敬之中的共存。任何物包括人都有它的不可触犯性、坚固性和深广度,即,都有它们的非透明性,都有它们无限的存在意义,在存在论层次上人与万物一体无间。
众所周知,人和动物都依赖它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但只有人对物作出了有用和无用的划界,而这个划界最终把人与动物和其他物区别开来,但在这个区分中,人一直与实用或不实用之物打交道,渐渐地把存在者层次上的不同混淆为存在论上的不同,使自己孤立出来,且自诩为天地万物的主宰,无法回转身去思考这种关系。庄子作出了无用之用与用(日常之用)的区分,在存在论层次上超出人与物的实用关系,思考这种关系的局限,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存在,那是一种无用之用的关系,此时,人与天地万物无间共存,无用之用是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齐敬和守护的态度,无用之用保持了物的意义也生成了人自身的本质和自由,因为自由不仅是在克服物中获得,更是从让物存在、心怀虔敬、与物共存中获得。在此区分中庄子也为人自身赢获了自由之域,在这个意义上,物回到自然,成为物本身,人成为自由的人。庄子认为自三代以来,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伯夷为清名死于首阳山下,盗跖为利死于东陵山下,这些都是对肉身的残害,在此意义上他要做一个无用之人,而游戏于天地之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篇》)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篇》)
“材与不材之间”的“之间”与庄子要进入的世界相似,但又不是,因为庄子那个世界不在用与无用、材与不材中间的某处,那个世界是对它们进行否定之后开启出来的,是一个全新的空间,如果囿于日常之用的二维空间里,生命就会要么像那不材的大木,要么像那有“材”的雁,总之最终因有用而死。那么像“名利”和“天下”这样的字眼并不能让庄子放弃肉体生命,那些在巫祝看来连给神做牺牲的资格都没有的无用的痔病患者他也认为是大祥,所以他自己宁可做在泥里拖着尾巴爬来爬去的龟也不去做一个有用的官而束缚自己。无用之用对他来说是真正的自由。
道家的老庄转向思“无”,就是说它面对言物错离,道术分裂,诗书礼易乐春秋的经典被工具化、实物化的事实本身,思“无”成为它对这一局面的本体论批判。老子思“无”而致用,庄子思“无”是思想对自身的回归,在齐敬中保存物的意义,从而以此来言说道、处于道之中。它形成了居间性、间距性,这是道家所理解的界限,是一种真正的哲学态度。庄子开启和显现了这个界限、这个居间性。
把以上的理论现象回归到现实,可以看出,庄子自觉地处于时代巨变之中,这一“处于……”方式本身必然是对时代的超越,同时也就是与时代的真正相遇。在这种意义上,庄子与其时代的分界线相遇了。这一相遇却在不引人注目的因随顺势之中,可是,正是这平凡而愚迂却相显出了时代纷乱浮杂的刺眼。在理论上,平凡之举倒成为出类拔萃之物,它显现了庄子哲学的精意和深度。
原始儒家在承继天命中要达到天道性命相贯通,欲仁尽心知性知天而无有所间隔。其实,正因为这种不可为而为之之路,使它无法与历史的分界线在更深的层次上相遇,当然这不是说它有意回避了历史的分界线,而是说它以一种试图弥合分界线的态度与之相遇了,最终由于它的努力而错失了对此一相遇本身的思考,就是说,历史的分界线以一种被主观敉平的方式在它的视界中消失了,历史的分界线被看作时命:“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而道家尤其是庄子却居留于其中,此居留正是一种真正的超越和相遇。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只说这是虚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他向不再闻问那样,相反,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5—p21] 道家居留其中的否定是历史自身的生成物,标示了历史的分界线。
四 结语
庄子的无用之用突出了日常之用的有限性;无用之用就是通,是对道的通达,以它的伟大力量守护物的意义,由区分无用之用与用而获得的界域是我与万物相敬共存得以可能的空间。任何物都有它的不可触犯性、坚固性和深广度,即,都有它们的非透明性,都有它们无限的存在意义,在此意义上物具有认知维度上的不可能终极的未完成性。物在这种无用之用的无限中体现着道的不息,而道的无处不在、宁静肃穆的力量赋予物自身以尊严和价值;同时,无用之用所开启的界域也是人之为人的自由空间,是为一种新感觉方式的产生所进行的奠基。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庄子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其时代相遇了,他的著作充满了“无……”、“不……”等类似的句型,显示了与时代的距离,同时这也是他与其时代的真正的相遇。相遇是度量与被度量之张力的形成,是人与世界的重新调整;一般地说,如何与过去相遇即是我们如何与现在相遇,也将决定我们如何与自己的将来相遇。基于我们现在的遭遇,(注:彭富春在中国现象学网站上(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哲学与当代问题》,他认为,我们身处三大基本遭遇,一是虚无主义,二是技术主义,三是欲望主义。)重新解读无用之用就是期待理解现在和开辟我们将来的新路。因此,对庄子无用之用的“另一种”解读不是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