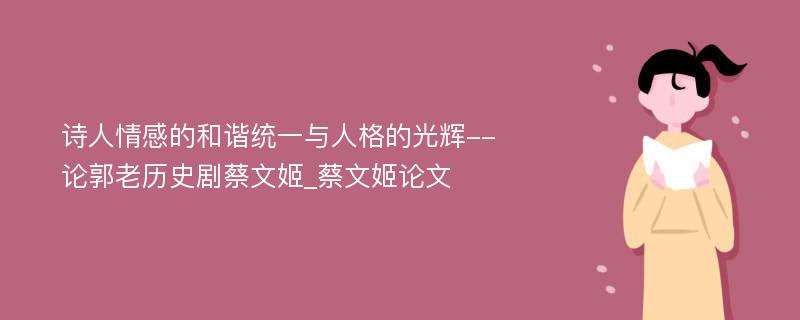
诗人情怀与人格光辉的和谐统一——郭老史剧《蔡文姬》纵横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辉论文,诗人论文,人格论文,情怀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老分别在民主革命时期、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写了七个新编历史剧,引起强烈反响。评论界对其中的五个剧评价基本一致,而对《蔡文姬》和《武则天》毁誉不一。特别是对《蔡文姬》争论颇大。本来争鸣是好事,无可厚非。但有人却借评戏之机,“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这是不能容忍的。现重读《蔡文姬》及其许多评论文章,感到有必要进一步作科学探讨,活跃正常的学术空气。
一
黑格尔老人曾精辟地指出:“艺术的最重要一个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美学》第一卷)这也许就是郭老选择写《蔡文姬》的动因,而不可能是其他原因。蔡文姬是诗人,郭老是诗人,曹操也是诗人。诗人是多情而敏锐的。他们的心灵的旨趣和情操是高尚的。试想一个美丽而有才气的女人因战争失去家园,被匈奴人擒去,作了左贤王的妻子并生儿育女,面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异国他乡,有多少眷恋祖国之情要诉说,有多少缠绵悱恻之情要抒发,一起溶入她写的《胡笳十八拍》里。成为自屈原《离骚》之后又一首闪跃着灿烂光辉的艺苑惊葩。郭老曾激动地宣称:“蔡文姬就是我!”可见诗人们心有灵犀。为什么要写蔡文姬,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情理之中的事吗?
据郭老考证,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遭遇,比蔡文姬本人的遭遇更为悲惨。如此伟大不朽诗篇居然被某些史家遗忘?!《后汉书》里的《董记妻传》没有提到它,《晋书》、《宋书》里的《乐志》也没收入。唐代刘商曾写《胡笳曲序》云:“蔡文姬善琴……,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在最关键的“后嫁董生”,把嫁字写掉差点造成大错。近代两位大学者郑振铎和刘大杰分别在所著《插图本文学史》和《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胡笳十八拍》不是蔡文姬写的,是伪作。郭老相信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写出如此哀婉动人的诗。“务必请大家读它一两遍,那是多么深切动人的作品啊!那象滚滚不尽的海涛,那象喷发着融岩的活火山,那里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我是坚信那一定是蔡文姬作的……”(引自郭老《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老是历史学家,并不会用感情代替科学分析。唐开元年间的诗人李欣有《听董大弹胡笳声》里有这样的句子:“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这便是有力的证据。
有人以为只写《胡笳十八拍》的悲剧就行了,为什么要掺合进曹操为蔡文姬归汉并翻案这样的喜剧结局。如果说郭老自称是“蔡文姬”,那么曹操是谁?我们姑且当成一个学术问题来探索!别忘了这样的事实:曹操是大政治家又是大诗人。他写了许多诗篇如:《蒿里行》、《短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和《神龟虽寿》等,对人民在战乱中的灾难寄予无限同情;对招纳贤才、帮助建功立业的渴望;对士兵行军打仗之艰苦深表不安;他的诗气势雄浑,意境深远。特别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作为政治家曹操的积极奋发的世界观的自我写照,成为不朽的传世佳作。具有诗人情怀:当然理解同情女诗人蔡文姬。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里,举了一系列名人,说明贵古贱今、祟己抑人是通行的诟病、于是感叹道:“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一乎!”曹操是蔡文姬的知音,郭老又是他们的知音,实现在舞台上表现,是合乎情理的。歌德曾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文里提出:“莎士比亚首先是一个抒情诗人,然后才是剧作家,勃郁的诗情和舞台直观不无抵牾。”有人打起辩证唯物主义的幌子,贩卖的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表面上反对庸俗社会学,要实现戏剧艺术长期没实现的品格,但走到它的反面去了,以随意性的清测和片面性的推理方式,怀疑郭老写作的动机。其文章荒唐可笑,早被文化界有识之士唾弃,不值得浪费笔墨再作反驳。恰好在选材这个问题上,显示了郭老诗人的情怀和人格的光辉的统一,达到审美最佳境界的高度,出手不凡,宝刀未老。
二
涉及剧中的关键人物那就是曹操。史学家们都公开承认历史人物曹操不同于传统戏台上的曹操。历史人物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清官和诗人,舞台上的曹操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奸雄。他们都同意这个案该翻。可是当《蔡文姬》上演,曹操的形象变了,一改过去传统的“粉脸,”恢复其本来面目时,有的人则茫然了,犹豫了。反而问之曰:“他是谁呀?难道他就是曹操?!”对,他就是真实的曹操!作者借董祀之口,对曹操作了言简意赅的描述:“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又通过周近,向右贤王讲:“曹丞相会做诗,会写字,会下棋,会骑马射箭,会用石,会用人。他的手下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啊!”右贤王似乎也知道,“所说曹丞相的部下有荀或、荀攸、郭嘉、钟繇,都是神机妙算的军师;还有张辽、许褚、夏侯渊、夏侯惇,都是一将当千的勇士。”对于曹操要赎回文姬,匈奴首领单于表示理解:“曹丞相这次送来的厚礼要迎接蔡文姬回去,实在也是对于我们南匈奴至诚和好的一种表现。”“曹丞相既然看重蔡文姬的文采,要他回去参与文治声教的事业,我们理当从命。”董祀向蔡文姬介绍:“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在曹丞相的治理之下,‘千里无鸡鸣’的荒凉世界,又逐渐熙熙攘攘起来了。”曹操在舞台上的形象的变更是符合史实的,决不是胡编乱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里记载了不少曹操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功绩,建安九年,他颁布抑制豪强兼并的命令,“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为治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又兴屯田制、解决了军粮问题,更解决了农民有田可耕的民生问题。“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他所作的《对酒》篇中,曾描绘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那就是”……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爵公侯伯子男,感爱其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虫。”曹操是军事家,据史载:“三郡乌桓,承天下乱,破幽州、掠有汉民合十万余户……数入塞为害。”曹操指挥柳城之战,打败乌桓,使边疆得以安宁。曹操善做诗文,气势磅礴,不再赘述,《文心雕龙》卷九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令。”《魏书》也称曹操:“登高必赋,及造就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建安文学开一代诗文,曹氏父子是有卓越贡献的。从以上史实与《蔡文姬》中赞扬曹操的话相对照,何其相似,并无美化拔高之嫌。
但奇怪的是:有人因为此剧作于一九五八年,便以为曹操翻案与歌颂大跃进不无关系,甚至进一步把历史上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后,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民族文化”,深谋远虑,广罗人材和由于他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气象万千,与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粮食亩产几万斤,天天捷报飞舞相比较,认为郭老在粉饰现实,歌颂三面红旗。还问颂曹为谁?这不是歌功颂德吗?把郭老赞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艺观,诬蔑为“文学侍臣”。很显然这是向一代文学泰斗头上泼污水,妄图毁坏郭老的形象。但我们要说这是徒劳!“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写过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杂文,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自然,中国历来文坛上,常见的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见《南腔北调集》)。
三
李渔认为:“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闲情偶记》卷一)郭老写过颇多的传世佳作,《蔡文姬》无疑是其中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的诗人情怀与人格的光辉会越来越被人理解。但值得研究的是:剧中人物的塑造,是否在艺术上站得住脚。
郭老写《蔡》剧遇上难题,同曹禺先生写《王昭君》遇上的难题一样,是写一个传统的悲悲切切的王昭君,还是写为民族大义欢欢喜喜的王昭君?这就是说写蔡文姬是写《胡笳十八拍》的悲剧还是写为曹操翻案的喜剧?有人深刻地作过如下的概括:“我们平视对象时,看到的是生活的正剧,当我们仰视生活时,则从生活中感受一种悲剧精神,而喜剧精神则是我们以高于对象的视点俯视生活所获得的审美意识。”《蔡文姬》应该说是悲喜剧。这是从题材角度出发所决定了的。蔡文姬的悲喜剧交织是当时的政治情势所决定了的。汉朝在曹操的治理下相当的强大,匈奴望而生畏。当汉的使臣来到,一谈便成。后来蔡文姬的一双儿女被单于送回,这也是基于此原因。可以说蔡文姬的命运是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曹操这样贤明的丞相谁会想到她。父亲已死,没有机会再回中原,确是事实。如果没有曹丞相的撮合,蔡文姬的结局不会是喜剧的。蔡文姬嫁董祀还有段插曲,据《汉书》本传载,“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曹操终于怜悯她把董祀放了。人物随故事情节自然展开,主人公曹操与蔡文姬的生动形象得以完成。既是塑造蔡文姬,又是塑造曹操,在事件进程中相辅与相成,水乳交融。蔡文姬与曹操两个新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成为戏剧画廊的新形象,这一点是不过份的。
但是《蔡文姬》在艺术上引起的争鸣是有益的,其影响不可低估。当然不能用“成功”或“失败”作结论。剧作家安·冈察洛夫说过:“今天的戏剧是一个结构的复杂机体。”而戏剧家马丁·艾林在《戏剧剖析》中,探讨戏剧本质时指出:“更为深奥、更为微妙得多的是戏剧如何能同时在几个方面发生作用……戏剧表达形式让观众自由地去判断隐藏在公开的台词后的潜台词。”据著名导渲焦菊隐先生介绍:“郭老写《蔡文姬》是从某个角度替曹操翻案的,主要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争论而写的。”目的也就更清楚了,郭老是自己为自己出难题。文姬归汉的故事只不过是个载体,借这故事的动人魅力来表达为曹操翻案的目的。所以戏里有两个中心人物。蔡文姬这题材在中国古画中最早出现是宋代,画蔡文姬离别匈奴丈夫,涕泪交流。元代赵孟頫画的是衣锦归来,愉悦富贵、悲和喜谁优谁劣只有比较才能分辨得出。郭老想表现得更深沉一点,使一位历史人物闪耀光辉,那就是贤明的政治家曹操。这是否带来蔡文姬的“今别子兮归故乡,旧怨平兮新怨长”的悲剧冲突和为曹操翻案的喜剧结局不协调的后果呢?剧评家们有种中肯的意见,以为戏在力度感知上可能产生缺憾,究竟重点支撑在《胡笳十八拍》悲剧气氛上,还是支撑在翻案喜剧气氛上。如果兼跨二者,势必缺少力度。
不妨再听听两位著名导演的论述:一位是导过郭老许多戏的北京人艺大导演焦菊隐先生,一位是中国京剧院著名导演阿甲先生。焦先生太了解郭老,他说导演郭老的戏有股巨大的激情。他把郭老最有争议两出戏分为感情的化身(《蔡文姬》)和理智的化身(《武则天》)是很高明的。蔡文姬离别丈夫和儿女回国可以想象是何等的矛盾。不回?丞相又如此器重,等她续《汉书》呀!别忘记她是多才多艺的诗人,感情应该特别丰富,所作《胡笳十八拍》便是证明。曹操也是诗人,同情蔡文姬的遭遇,受感情的驱使才花重金赎回她。相信她是会归汉的。曹操多么爱才啊!但也许忘了女人的痛苦!若归汉又陷进感情旋涡中。焦菊隐先生恰如其分地总结出:《蔡文姬》表现的是生活矛盾和自我矛盾。蔡文姬有两重矛盾,后一种是曹操制造的也是他解决的,如此看来似乎是郭老有意而为之,并不存在两个支点缺少力度的遗憾。焦菊隐曾担心过,他说初时分析剧本感到剧情不合逻辑,但随着诗人所塑造人物的发展,就进入诗一样的境界,随着人物的悲而悲、喜而喜,激动起来,使一切趋于合理。
倘若说焦菊隐先生沉浸在他所导的戏剧激情里,对郭老的创作有种偏爱的话,另一位资历颇深的阿甲先生,则是站在冷静的观众席位上去审视全剧得失的。他在《真实,还要够味儿》一文里,从排导技巧这个视角切入来谈《蔡文姬》的观感。他强调光有技巧是成不了伟大作品的。阿甲很欣赏《蔡文姬》里一段台词,他说:“正如《蔡文姬》中曹丕称颂屈原、司马迁、蔡文姬时说,‘他们的文字是用生命在写,而我们的文字只是用笔墨在写。’可见没有宏大的感情,也难有生花妙笔!”这同焦菊隐的见解相同。阿甲承认:用艺术方法为曹操翻案比用历史材料方法翻案要困难得多,但在舞台上不要说“翻案”,就是“翻脸”也很不容易的了。
《蔡文姬》远非无瑕疵的作品。比起郭老的《屈原》、《虎符》来也略逊一筹。但写这戏要有勇气,从提笔到写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诗人情怀与人格光辉的艺术统一。对一部著作的优劣尽管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批评,可以商榷。但不能人生攻击。著《闲情偶寄》的剧作家李渔曾告诫过:王实甫写成《西厢记》已有数百年,直到获得了金圣叹的批评,作者才安心暝目。“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可见有见地的有份量的批评并不是随意褒贬中得来的。著名美学家、评论家余秋雨教授说过一段推心置腹的话:“要使全剧上下均能以千仞转石般的情势,对观众造成完整而强烈的心理包摄,可谓难矣!但对观众来说,要在总体印象上得出一个信服或同意与否的结论,再方便不过了。戏剧家最大的困惑也在这里,辛辛苦苦的调配和组合可能经不起文化水准和审美能力或许远远低于自己观众的轻轻一尝。厨师百巧,归乎一舌。为对付千万普通食客的‘总体感受’,再高明的烹饪师也不能不竭尽全力、艰苦摸索。”(摘自《戏剧审美心理学》)这种全力的摸索毫无疑问已取得预期的效果。不但将毁坏了的美好给观众看,而且仰视这段历史,从生活中感受到一种特别精神的同时,以高于历史局限的视点俯视生活所获得的审美意识,使观众清楚地领略到,这不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再现,却是浸透了剧作家主体意识对历史的折射与投影,其必然撞击起巨大的感情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