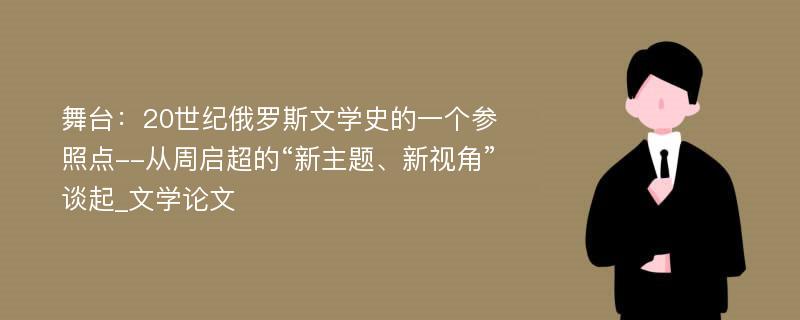
阶段性: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一个参照点——从周启超《新的课题,新的视角》①一文说开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文学史论文,阶段性论文,一文论文,开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由于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也不仅是由于1991年苏联的解体。如果说,80年代中期苏联文坛上出现的“回归”与“开禁”现象,在我国读书界眼前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使人们开始感到俄罗斯民族在20世纪为世界文学所提供的,远不只是传统的“苏联文学史”所介绍的那一部分作家作品;那么,我国学术界对同一问题的关注与思索则要更早一些。当然,只有在社会与学术氛围进一步宽松,文学史资料充分展露和思想成果日趋丰硕的今日,郑重地提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概念并考虑重新描述这一文学史进程完整图象的尝试,才成为可能。
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它既囊括周启超先生在他的论文中所屡述的“显流文学”、“潜流文学”和“侨民文学”三大部分(其中后两部分都曾长期被排除在“苏联文学”之外),也包含自上世纪90年代到十月革命前的“白银时代”的文学遗产,还应包括目前仍在演进中的本世纪90年代文学。启超的描述无疑显示了一种追求切近历史本相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开阔视野,但是,却不可将他的“三大部分”(“三块基石”)视为新文学史的体例框架。这是因为,不仅“白银时代”文学与1991年以来的文学无法以“三分法”区划,即便是1917--1991年间的文学现象也同样存在着难以划分的情况。例如,“潜流文学”中的扎米亚京,在1931年便被“批准”出国,成为侨民作家;别雷、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茨维塔耶娃等人,也都各自有过一段侨民生活史。而“侨民文学”中的索尔仁尼琴、维克多·涅克拉索夫、阿克肖诺夫和西尼亚夫斯基等人,则都是“潜流文学”中有影响的人物。又如,“显流文学”中的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等人,也同样曾侨居国外,其中高尔基于1921年出国,1933年才正式回国定居。“显流”与“潜流”之间,有时也难以截然划清界限。如高尔基向来被认为是“显流”文学的代表,但是他的《两种灵魂》、《致读者的信》、《不合时宜的思想》、《论俄国农民》、《〈列斯科夫文集〉序》等大量随笔、文论和政论,事实上一直是被当作“潜流文学”的一部分对待的,这些作品连《高尔基三十卷集》也未收录。另外,像库普林、勃洛克等作家,也很难归属到哪一类文学中去。总起来看,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确实存在着“显流文学”、“潜流文学”和“侨民文学”,但是,要建立本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框架,则要作进一步思考。
当然,试图将一些研究者看待20世纪欧美文学的“三家鼎立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移过来区分衡量20世纪俄罗斯文学,并以此为基本标尺来建立文学史的编写框架,更是值得商榷的。上述三大“主义”并不能包括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请注意:现代主义并不包含象征主义)等文学思潮和流派。因此,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格林、帕乌斯托夫斯基、奥列沙、卡扎科夫等浪漫主义作家,列米佐夫等自然主义作家,从索洛古勃到勃留索夫的一系列象征主义作家,究竟划入哪一块,便成为棘手的问题。另外,像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皮里尼亚克、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普里什文这样一些在艺术上表现手法上极为灵活的作家,也很难包容在某一种“主义”之中。“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际界限,也同样是难以划分的。首先是高尔基的一系列作品,如“奥库罗夫三部曲”,《罗斯记游》,《日记片断》,《俄罗斯童话》,《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自传体三部曲”以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便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范,虽然所有这些作品全是在“奠基作”《母亲》问世之后完成的。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特别是它的第一部,大概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第一部代表作;但是,为作家带来世界性声誉的长篇《静静的顿河》,却因其强烈的批判倾向而一直未能被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一致认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是的,假若用70年代曾名噪一时的“开放体系”来包容,或许是可将上述所有作家作品统统包罗进去的。因为据说这一体系除了神话之外是无所不包的。然而这样一来,除了说明这一体系本身缺乏任何美学特征,在把一切都包容到自身的同时也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之外,便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
回顾一下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客观进程,我们便会发现,这一百年来的文学并不是由若干贯穿始终的文学运动构成的。这一文学史进程特别明显地显示出它的阶段性。本世纪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后者直接受影响于前者)中某些最重大的事件,无可争辩地成为划分这些阶段的历史界碑。信奉庸俗社会学的研究者们每每以政治斗争史的分期标准来切割文学史进程乃至作家的创作道路,把艺术理解为政治的附庸,其观念与方法都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谬的,我们当然不可步其后尘。彻底摆脱庸俗社会学的阴影,是建构新文学史的思想条件之一。应当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恩格斯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方法。
根据这一原则和方法,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历程可划分为白银时代(1890-1917)、变迁时代(1917-1929)、滑坡时代(1930-1953)、“解冻”与“停滞”时代(1953-1985)、改革时代(1985-1991)以及解体以后(1992-)这几个阶段。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客观进程所显示的清晰的阶段性,应成为我们构想新文学史框架体例的基本参照。这部文学史应当客观地描绘各个阶段文学生活的实际面貌,并力求勾勒出各个阶段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它当然不排斥属于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运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各种体裁样式,具有各种风格特征的作家作品。那种以作家的政治态度为唯一标准来决定该作家能否“进入”文学史的做法,显然应当坚决摒弃。唯其如此,才可能提供切近历史真实的文学史的完整图象。在“现象描述的客观性”的基础上,这部文学史将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目光重新审视一切文学现象,以及似乎早有“定论”的作家作品。但它决不采用“非白即黑”、肯定否定的简单判定式方法,只是准备把“充分颂扬”和“一笔抹煞”的对象来一个根本颠倒,并以此来冒充、代替文学史研究中的真正革新。新文学史的任务也决不是通常所谓“重点作家”的人马大换班。在这部文学史中,每一作家的意义与地位,都不是以他存在的时间(革命前或30年代)和地域(国内或国外),他和他的作品的命运,他的政治生涯的特点,他所运用的“创作方法”为标尺来确定的。基本的标尺只能是:他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本世纪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情绪和体验,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精神,他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俄罗斯语言艺术的发展。这样,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进程的完整面貌、它的特点及它所显示的规律性,或许就能够明晰地显示出来。我们相信,这样一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将是我国读者所欢迎与需要的。
1994年4月于南京
注释:
①载于《国外文学》,199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