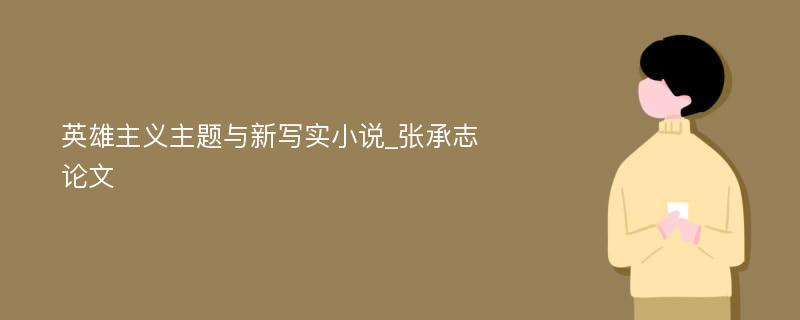
英雄主义主题与“新写实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雄主义论文,主题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英雄主义是当代文学精神史上最炫目的主题之一。但这一主题到目前为止的流变过程及其轨迹也许能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
单就“英雄主义”这一主题而言,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也许已经将它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至。从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雷锋之歌》等诗歌作品对“英雄主义”的纵情歌唱,到《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欧阳海之歌》等小说对英雄人物日益炽烈的景仰赞颂之情,让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崇尚英雄主义的时代。
十年“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似乎开始了一个“再叙事”的过程,在文学精神上,经历了一个将“人”重新找回来的过程,因此,在“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等新时期初期的小说思潮中基本上是以批判的方式对人性、人道、人权的肯定,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似乎还是奢侈的精神装饰。正面展示英雄主义的作品出现在局部的、特殊的传统的题材领域:军事题材与改革题材。前者如《西线轶事》、《天山深处的大兵》、《高山下的花环》,后者如《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男人的风格》、《花园街五号》、《祸起萧墙》等。这些传统题材的小说表现的英雄主义也是传统的、古典的、是在集体与个人,人民与自我的冲突与矛盾中,通过弘扬、肯定集体与人民的利益,否定自我和牺牲个人而成就的一种悲壮而神圣的英雄主义,与五六十年代文学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同质同构的。
一种新质的英雄主义似乎是伴随知青题材小说的蜕变过程而出现的。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张承志的《老桥》、《大坂》、《黑骏马》、《北方的河》,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作品中的主人公试图摆脱“旧梦”走向“新岸”,在这样一个反思和脱胎的过程中逐渐从初期“伤痕小说”中的“感伤的”、“愤怒的”的情绪中走出来,重新点燃、升腾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之火。但和传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有所不同的是,灌注和渗透了澄明的理性思考和个性主义的特征。在易杰(《南方的岸》)、陈信(《本次列车终点》)、肖疙瘩(《树王》)、解净(《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人对“新岸”的憧憬与“旧梦”的作别中,在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包含着深思熟虑的理性反思和对自我实现的热切关注和充分肯定。尤其是出现在张承志小说中的那个主人公“我”,他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包涵在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思想之中的,具有极强的个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色彩。
1985年前后出现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黑森林》,刘毅然的《摇滚青年》等被指认为中国的“现代派小说”。我认为这样被指认的主要原因是主人公所表现出的那种激烈的个性主义的反传统性,他们是以传统文化精神的叛逆者而不是继承者的面目而出现的。他们的文化个性不仅与林道静、梁生宝、江涛(《红旗谱》)这样一些集体主义和“人民文化”语境中的年轻英雄不同,而且也与易杰、解净和张承志小说中的硬汉“我”等个性主义文化语境中的英雄也划出了深深的沟痕。他们的英雄主义或许正表现在传统的对峙和对自我、对个性的纯粹性的坚守。把他们与西方文学中“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直接比拟或许是不恰当、不准确的,但我们确实明确地看到他们的“英雄主义”已失去了理想主义(与社会和民族利益相结合的理想主义)的陪伴和护侍。失去了社会理想主义强有力的护持,单纯的“英雄主义”变得日益空洞、乏力、失去了充盈的社会与道德内涵,它几乎变成为“不合作”和“标新立异”的代名词。
这或许标志着一种文化上的开端,即一种非社会化、非建设性的消解文化开始具有了流行的背景。我们看到,王朔笔下的“顽主”们在叛逆的道路上更向“前”跨出了一步,他们的“不俗”,他们的“英雄气”不但失去了社会理想主义的护侍,而且也失去了“正义”的支撑,他们在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俗利主义的牵引下干着反秩序、反道德的勾当,英雄主义发生了畸变,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
当代文学中英雄主义的底蕴由社会理想主义到个性主义再到赤裸的个人主义的变化轨迹,显示出令人悲哀的“精神滑波”。这种“精神滑波”现象不仅表现在王朔小说中个人主义和俗利主义的精神畸变,还表现在“新写实小说”中的“非英雄主义”和庸人气息的流溢。
对于“新写实小说”,人们最明显的观察到的是它对生活形态的日常性、世俗性的内容的侧重。与传统的写实小说将经验性的内容抽取为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不同,“新写实小说”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等推举到了本体性的地位上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强调要创造典型人物就必须创造典型环境,这种典型环境是对政治经济关系的本质性概括;“新写实小说”也创造了自己的典型环境,但这种典型环境恰恰淡化了政治经济关系等经验内容,而特别推重人的工作起居、邻里悖忤、家庭纠纷等日常性经验。如果用一个已经熟烂的概念表达的话,“新写实小说”推重的不是人的生存关系中作为本质内容的“生产关系”,而是作为表象存在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新写实小说”的这种“典型环境”被意象化为“烦恼人生”这一压抑而沉重的生活命题。在《烦恼人生》中写工人印家厚从早起床到日落归家一天的生活流水帐,这一天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烦恼”和“不如意”:住房拥挤、厕所拥挤、汽车拥挤、奖金分配不公、爱情失意。生活成了一场沉重的劳役。在《风景》中,“河南棚子”里猪狗一般的生活与亲子手足之间的仇视和互相折磨,更是一片独异的生活与人性的风景。在《单位》、《一地鸡毛》中,人与人之
化氛围比喻成“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出的出口”的铁屋子,表示出自己心情的焦虑与沉重。“一地鸡毛”的意象似乎是一个更加纷乱,消磨热情、意志与理想的“万物之阵”,作者的心情是无奈帐惘而沉重的。)纷乱、沉重的“风景”。
在日常性和世俗化的“烦恼人生”面前,“新写实小说”中的人物普遍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厌弃,对激情和浪漫生活的拒绝,而无可奈何地认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现存秩序;传统文学中对理想主义的炽热向望,对改造社会而达成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冲动,对人生的价值及意义进行形而上思考的真诚与执着都被日常性的生存经验、被“好好过日子”的世俗性号召所取代。王朔小说在消解传统文学精神至上,意义至上的崇高和理想化的价值形态时建立了一种新的世俗化的乌托邦幻想,即过一种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在汰除以社会为己任,以彼岸性、终极性为人生追求的“古典英雄”的同时,还创造了自己的“痞子化”的“当代英雄”。与之相比,“新写实小说”似乎透露出更加透心彻骨的悲观主义,世俗主义和投降主义。它摒除了任何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结,其基本信念就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二
传统文学中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两种精神价值其向度虽有所不同,但两者的存在几乎是不可分的,是两种互为表里的积极的价值形态)有两种价值向度,其一,是将人生理想与改造社会相结合,社会理想的实现及其为之奋斗甚至牺牲,是人生理想的替代方式。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包含着巨大的充盈的道德与伦理内涵;这种包含着丰富的“善”的内核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主题构成了文学价值的主要形态。无论是周大勇(《保卫延安》),沈振新(《红日》)、江姐、许云峰(《红岩》)、杨子荣(《林海雪源》)等这些战争中的英雄,还是象梁生宝(《创业史》),刘雨生(《山乡巨变》),阎兴(《在和平的日子里》)等这些在“和平的日子里”的行进人物,都是将自己融入改造社会,建立幸福未来的伟大事业中,他们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因为具有“善”的内核而变得崇高而悲壮。或许具体到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确存在着拨高、“虚美”缺陷,把它视作唯一合理的价值尺度并成为排斥其他精神主题的理由也给当代文化生活带来消极影响,但作为一个形象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形态本身,这种以“善”为核心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绝不应该被否定。
在新时期小说中,虽然其主要的精神特征是批判的向度,表现出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呼唤,主要价值形态是人道主义,但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并没有寂灭。乔光朴(《乔厂长上任纪》)陈抱贴(《男人的风格》),李向南(《新星》),郑子云(《沉重的翅膀》),隋抱朴(《古船》)等改革者形象和梁三喜、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刘毛妹(《西线轶事》),郑志桐(《天山深处的大兵》)等军人形象身上仍体现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强大精神感召力。即使同样以生活日常性与世俗性内容为描写对象,《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人到中年》、《普通女工》、《流逝》等仍表现出力图穿透这种世俗性生活达到一种非世俗的价值认同的努力。李顺大、陈奂生、陆文婷、何婵、欧阳端丽所生活其中的无非是吃饭、穿衣、造屋、上班等日常性的世俗生活,但是这些日常生活内容表现为它的不平常、不如意,表现在它对精神与人性的否定与伤害。或者说,这些作家恰恰是在物质/精神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框架内坚定站在了“精神”一边,批判了“物质”、日常生活的庸俗性,其背后仍然是改造社会与精神至上、人文至上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陆文婷、何婵身上表现出的那种柔韧、坚定、执着的精神与信念是理想
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取消了精神至上这一传统的价值立场,物质生活、日常的生活经验成为唯一的存在,被本体化甚至是浪漫化、理想化。没有了崇高的精神价值立场映衬与导引,物质与日常性生活经验成为唯一的、最终的经验,“过日子”成为目的,无论日常生活是“诗性的”还是“烦恼的”,你都得接受,都得认同。“生活就是这样”、“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社会改造的主题,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主题统统消解于这种日常经验当中。
在《烦恼人生》的文本结构中,存在着物质/精神,世俗性的生活经验/浪漫化的精神理想这种二元视角,日常性经验:孩子掉床,上厕所,吃饭,挤车,上班迟到,奖金分配,托儿所的经历,被工会抓差,下班回家听到住房折迁等贯穿在主人公印家厚一天的行动线上,这是一个外在的明显的叙事线索,这一线索的叙述意识突出了生活的琐碎与“烦恼”。作品还有另一条线索即隐附于行动线上的印家厚的心理活动,是印家厚对琐碎、“烦恼”的日常生活所作的精神反应,以回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两条线索表现的是两种经验,前者是当下的现实经验,后者则是记忆(提及的主要经验性事件是初恋、下乡生活),实际代表的是青春、爱情与理想。这两种经验两种视角恰恰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叙述张力,但与传统文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叙事的归依不是理想与精神对世俗性生活的超越、改造与征服,张扬理想主义与人的主体精神;恰恰相反,而是表现为生活逻辑对人的改造,现实原则来修正理想、使之纳入世俗生活的轨道。“少年的梦总是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一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哪有功夫想入非非呢?”“雅丽怎么能够懂得他和他老婆是分不开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
“大文本”这一角度解读小林这一形象的话,他的思想性格特征与林道静、梁生宝、陆文婷、解净、何婵等形象类型崇高或优美的美感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了“互文”,映衬出小林和小林生活其中的这一时代在文化上的苍白与平庸,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小林的出现未必不是对生活的批判与反讽。但这种大文本式的阅读与批评同样需要批评者的眼光与勇气,特别是需要批评者站定人文主义和精神至上的价值立场,否则小林的批判与反讽意义是很难发现,发掘,是无法被接受,只能助长精神失败主义的文化颓风。
其二,文学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还有一种价值向度,即表现在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追问,表现在对平庸生活与平庸人生的永无止境的超越以及对生命极限的挑战,这种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主要不是以其道德伦理内涵表现为“善”的特征,而是表现为求“真”、求永恒的执着与坚定,是对精神与哲学命题的形而上思索,其极至状态的美感特征是悲凉与悲怆。这一价值向度表现出更加纯粹的精神至上的乌托帮情结,物质性、世俗性的生活常常表现为难以容忍的庸俗性,是生命价值的否定力量。以“真”为内核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主题在“十七年”文学中较少见,而在“新时期”小说中,特别是在一些年轻小说家诸如张承志、史铁生、阿城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在张承志小说的经验世界中存在两种经验两种价值的尖锐对立。我们在他作品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张力就来自于两种经验语码及其相关的情感与价值内容的冲突。物质化、世俗性的经验语码通常是:拥挤嘈杂的都市、琐碎扰人的日常生活,诸如八平方米的小屋,蜂窝煤等等。总之,日常性的经验世界在张承志笔下总是表现为窘迫、逼仄、烦恼的非人性非理想的特征。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对抗与超越,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作为理想人生与精神家园的象征而出现的另一套语码:大草原,北方大河,冰川中的大阪,黄泥小屋,金牧场等等。这些作为精神家园和理想人生的寄足地而出现的“新大陆”与世俗性的现实生活构成了张承志作品的两极;而超越世俗,追求理想、实现诗性的、有意义的壮阔人生永远都是张承志小说所倚重,所关怀的。因此,精神、信仰、彼岸性是构成张承志小说世界的话语中心词。
在史铁生笔下,主人公大都是为各种各样肉体的残疾所困扰,如《我遥远的清平湾》中的下乡知青“我”,《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和小瞎子,《阿勒克足球》中坐轮椅的主人公等等。对于这些人来说现实世界是竖立在他们面前的一道又一道的屏障,是人生道路上横亘着的沟沟坎坎,是他们现实生活经验中难以克服难以逾越的困窘、难堪而又屈辱的记忆。但是,尽管身体的残疾阻碍了他们享受世俗生活的幸福,但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的天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体验着生命的忧伤与欢乐。史铁生笔下的人物常常呈现为生命的极至状态:生命的沉重、艰难造成的缺憾与在精神上对这缺憾顽强的超越使“灵”“肉”达到了一种既尖锐对立、严重分离又高度统一的状态,这是一种生命敞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让人触摸、感受到生命如琴弦般(《命若琴弦》)震颤、张驰,它是那样脆弱、易折,瞬间就会喑哑、寂灭;但即使断裂了,那也是在震颤之后的断裂;即使喑哑了,但冥冥之中,在空旷而寂静的生命状态中仍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袅袅余音。正像很多人所感受到的,史铁生的小说中充满一种宗教般的情绪体验;但这种宗教感不是来自于神性崇拜的中世纪宗教:一种自我渺小、甚至是无我的迷狂颤栗与噤语的状态;而是来自自然与生命崇拜的现代
面对世俗性的经验和人生困境,阿城找到了一条不同于张承志和史铁生的生命超越的道路,即从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中引入了老庄式的“逍遥”之途。在《棋王》中,人生经验被抽象为“吃饭”和“下棋”即“生道”和“棋道”两类。在二者的关系中,强调“为棋不为生”,“为棋是养性,生会坏性,所以生不可太胜”;在“棋”中,人通过“坐忘”的方式进入纯粹精神化,艺术化的人生经验当中。
尽管张承志,史铁生、阿城等人在选择人生超越的方式上各有不同,其精神资源、文化价值背景也相互有别,但他们表现出的共同点则是对精神价值的倚重,对物质世界与世俗性生活超越的意向,在人生意义的探究、求“真”的价值范畴内表现出精神至上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精神倾向。但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受到怀疑和拒绝,而世俗主义的价值观却被普遍认同。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在业余诗人四和小市民猫子所代表的价值观的交锋中,代表“启蒙”和人文立场的四成为一个不合时宜倍受嘲笑和冷落的人,而猫子所代表的小市民生活却充满了乐陶陶的诱人光泽。《一地鸡毛》中,诗人“小李白”由一个诗的信徒变成了一个卖烤鸭的小小暴发户,反而是“小李白”的这一转变真正给小林以“启蒙”:
“你还写诗吗?”“小李白”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在写诗,不得饿死!你结婚了吗?”
小林说:
“孩子都三岁了!”
“小李白”拍了一下巴掌:
“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
小林深有同感,于是点点头。
……
这也许是当代文学中又一经典性的场景,它表明两种生存观、价值观、两种文化价值心理的新倾斜。“写诗”与“卖烤鸭”作为精神生存、诗性生存和物质生存、世俗性生存的象征与隐喻,“卖烤鸭”的胜利标志着形而下的务实性、世俗性的生存观与价值观的胜利。
三
无论是以悲壮为特征的古典的崇高,还是以悲凉为特征的现代的崇高(这种崇高体已经不是很纯粹的了,它吸纳了荒诞、滑稽、幽默等异质的美感因素,但其主导的美感形态仍然是崇高感,如加缪笔下的西绪弗斯比之普罗米修斯这一“高尚的圣者与殉道者”显然不具有悲壮、神圣这种古典主义的崇高感,但他参透了世界及生存的荒诞本质之后仍然“选择”了拼搏、抗争这种生命形式说明,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富有崇高感的英雄。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有些形象如史铁生笔下寻求生命超越的“残疾者”,阿城笔下的王一生,肖疙瘩等也同样具有了这种现代的崇高美感特征,其构成的基本的精神因素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美学上的表现形态就是坚定、柔韧的意志品质和宁折不弯的抗争与超越意识。而“新写实小说”中的美学形象印家厚、小林、迟钦亭、七哥、猫子、庄建非等反理想主义和非英雄化的平庸者从根本上与崇高、悲壮等美感形态相悖离,也与陆文婷、解净、何婵等柔韧、优美的美感形象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与悲剧英雄和“极平常的悲剧者”均不同的是,他们在异己的力量和环境面前,不是采取对立、抗争、拒绝等积极、主动的主体化的姿态,而是采取认同、“混”、随俗俯仰甚至是以恶抗恶(比如《风景》中的七哥)的非主体化、非对象化
“新写实小说”是一种“还原性”的经验写作,这一方面是指对生活的反映变成了一种机械性的“模仿”,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呈现为同样的“生活流”的随意、松散、似乎是未经组织加工的状态(实际上这也只是表象,“新写实小说”实则在有意躲避生活中重大,本质和有组织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指作家写作态度上从主体性位置上抽离,未对生活经验进行“精神性的装饰”,或者说是一种知识分子化的哲学性、意识形态性的表述被有意拆除了,文学文本完全变成了近距离的生活经验的描述,而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段进行的种种表意性的努力,在文本中建立精神高峰的企图都被取消了,所以“新写实小说”在阅读经验上来说,因为没有任何精神的“障碍”而变得非常朴素和平易近人,而从审美心理上来说,因为人物的生活化、世俗化、非英雄化,已经不存在精神上的挑战和哲学化的形而上思考,也难以出现悲剧式的怜悯或恐惧等高峰式的审美体验。从文本到精神,“新写实小说”可以说变成了一部消解精神生存的通俗性的大文本,与“十七年文学”和1987年以前的“新时期文学”在文化精神上已经呈现明显而尖锐的裂痕,缘于此,有人将1987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指称为“后新时期”也是不无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