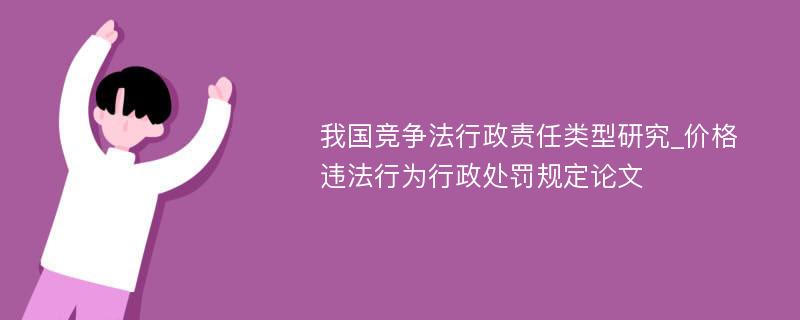
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的类型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竞争法论文,类型论文,行政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在中国竞争法的实施过程中地位显著,竞争法行政执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对于中国竞争政策的逐步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为切实推进竞争法的实施,除正确认定违法行为外,更需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以保障竞争法行政执法的实效性。但同时,干预措施应具有正当性,否则,其造成的损害将远远大于反竞争行为造成的损害。干预措施的正当性,主要源于具体干预手段、相应构成要件以及竞争法法益目标三者间的密切联系之中。①那种未紧密结合相应构成要件与竞争法法益目标而对干预措施的列举,仅展示了行政执法机构可资运用之干预手段的大拼盘,很难满足执法实践中论证干预手段正当性的规范性需求,也很难澄清竞争法行政执法制度的特点或政策性倾向。鉴于此,本文将“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针对反竞争行为主体所应当施加的强制性不利负担或干预措施”,表述为“竞争法行政责任”,以承载说明实施干预措施之应为性的使命。②同时,将具体干预手段、相应构成要件及其法益目标或功能的统一体归结为竞争法行政责任的不同类型,借助不同类型间的联系与对比来阐释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的特点,并在不同类型的细节之处探求不断完善竞争法行政责任的路径和措施。
一、提醒告诫:威慑涉嫌违法的行为
目前,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包括提醒告诫、金钱制裁、禁令、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其中,提醒告诫是严厉程度相对最轻的责任承担方式。为防止反竞争行为的发生,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当特定情形出现时,即使尚未构成违法行为,或者违法行为轻微而可以不予处罚,行政执法机构也可予以提醒告诫。提醒告诫在中国竞争法行政执法的主要领域均有所使用,③但仅在价格反竞争行为领域有较明确的规定。
根据《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规定,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可能显著上涨、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价格举报问题集中或者呈上升趋势、价格收费政策出台或变动、季节性周期性价格或者收费行为发生、节假日或者重大活动期间等价格行政执法机构认为有必要提醒告诫的情形发生时,若尚未构成违法行为,或者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执法机构可采取公告、会议、书面、约谈等方式予以提醒告诫。提醒告诫的内容包括提醒告诫对象有关国家价格收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提醒告诫对象应履行的价格收费义务及不规范的价格收费行为的表现形式,提醒告诫对象规范价格收费行为的具体意见及期限等,提醒告诫对象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应承担的责任。提醒告诫具有强制性,对于经提醒告诫仍未规范价格收费行为,并违反价格收费法律规定的,价格行政执法机构可以依法从严查处。
提醒告诫对涉嫌违法的反竞争行为具有威慑、放缓功能。当受到提醒告诫,意识到反竞争行为已受到执法机构的关注后,经营者可能停止涉嫌违法行为的实施,或从竞争法的角度再次审视该行为,放缓实施进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FTC)也会向涉嫌违法的经营者提出建议以实现该效果。但由于FTC能直接实施的救济有限,④三倍损害赔偿、罚金等救济只能通过提起诉讼来实施;对涉嫌违法行为的威慑,事实上大多也是通过提起诉讼来实现的。比如,2002年FTC曾建议搜索引擎服务商对竞价排名作出“清晰且显著的披露”,但竞价排名的披露情况并未因此得以改善。⑤与此相对,美国政府对IBM提起的垄断化诉讼及其诱发的四十多起民事诉讼,虽多以IBM胜诉而终结,但客观上放缓了IBM实施涉案行为的进程,为潜在竞争者的进入提供了时间,有助于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和软件市场中竞争格局的形成。⑥在中国,以《价格法》第41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反垄断法》第50条为核心的竞争法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并未确立类似于美国法的三倍损害赔偿规则,威慑力不高,涉嫌违法的行为很难因竞争民事诉讼的提起而被放缓。相比之下,行政执法机构的提醒告诫对涉嫌违法行为的威慑功能便得以突显。
除提醒告诫外,中国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还使用行政指导来威慑涉嫌违法的行为。行政指导与提醒告诫都不以行为违法为要件,但行政指导不具有强制性。⑦比如,《工商总局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全面推进行政指导工作的意见》规定,行政相对人拒绝接受行政指导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得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行政强制行为以及其他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理手段强迫其接受行政指导。欧盟也采用不具有强制性的非正式指导来实现类似功能。但欧盟主要通过正式执法与判例法来威慑预防涉嫌违法行为的发生,欧盟委员会仅在例外情形下,于收到请求并经评判后才以书面形式发布指导书。⑧与之相比,由于竞争法判例经验尚不丰富,为提升经营者理解竞争法的能力,弱化竞争法实施的阻力,中国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普遍采用提醒告诫与行政指导来更加主动、灵活、及时、有效地维护竞争。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指导在日本禁止垄断法的实施中占据显著地位。⑨与日本相比,中国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尚不具备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那样的主导地位,权威性不高,容易受到其他行政力量的干预与牵制;⑩因此,为实施及时有效的干预,中国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在行政指导外还采用了具有强制性的提醒告诫。
因此,提醒告诫不以行为违法为归责要件,形式灵活,可容纳的内容广泛。具有强制性。目的主要在于威慑涉嫌违法的行为。它的正当性基础是,中国竞争法民事责任的威慑力较低,竞争行政执法机构试图采取更灵活及时的措施以推进竞争法的有效实施,但因权威性不高、柔性执法手段的效果有限,故而采取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形式灵活、内容多元的责任承担方式。
二、金钱制裁:威慑违法行为,补偿受害人损失
金钱制裁有助于消除反竞争行为主体实施违法行为的动机,威慑违法行为,也可在某种程度上对受害人予以补偿。鉴于《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未就间接受害人诉讼主体资格、集体诉讼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11)竞争法民事责任的实际作用范围被限缩,行政责任在金钱制裁方面的作用也因此被强化。
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中的金钱制裁包括退还多收价款、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三类。它们都以行为违法为归责要件,且均不要求行为主体的主观过错。与欧盟《理事会第1/2003号条例》第23条、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34条和第81条前两款、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典》第2条中的过错原则相比,主观因素主要被用于考察违法情节,不影响行政责任中金钱制裁的成立,仅影响罚款(而非没收违法所得或退还多收价款)数额的确定,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1条到第28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0条、《反垄断法》第49条以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定。
在适用范围方面,罚款适用于全部反竞争行为。没收违法所得适用于除《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公用企业限定交易、虚假宣传、侵害商业秘密、有奖销售和串通招投标外的,存在违法所得的反竞争行为。退还多收价款的适用范围最窄,主要适用于存在违法所得的价格反竞争行为,以补偿受害人损失。根据《价格法》第41条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6条,若违法所得属于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责令经营者限期退还;难以查找多付价款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责令公告查找;经营者拒不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以及期限届满没有退还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予以没收,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退还时,由经营者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9条第4款和第10条,退还多收价款后,视为没有违法所得;期限届满后逾期不退或者难以退还的价款,以违法所得论处。因此,在交叉适用领域,这三者间的关系是:有违法所得的,先退还多付价款。退还多付价款后视为没有违法所得;有违法所得但未退还价款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罚款。
与日本和欧盟仅以罚款为主的金钱制裁相比,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并处,为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提供了依据,但也可能造成制裁过度。与德国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和收缴额外收入三种金钱制裁相比,中国又尚未对罚款与没收违法所得予以协调,既未像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34条那样规定。额外收入已因为损害赔偿、罚款或没收违法所得冲抵的,不再收缴额外收入;也未像德国《行政违法法案》第29a条那样规定,罚款数额未明确的,可先没收违法利益。为了对没收违法所得与其他金钱制裁措施予以协调,以保障金钱制裁的谨慎适用,2003年美国FTC曾宣称,将仅在例外情形下才适用没收违法所得。(12)但在实践中,尤其是在垄断化案件中,该政策无法提供足够的金钱救济。(13)更重要的是,该政策被误读为,没收违法所得不应适用于初次发生的案件,并且FTC必须证明“其他救济措施不足以实现反托拉斯法的目的”。为此,2012年FTC撤销该政策,强调将不再仅于例外情形下才主张没收违法所得,而将根据既有法综合考量金钱制裁的适用。(14)为实现合理的金钱制裁,美国执法实践仍面临着如何协调三倍损害赔偿、刑事罚金、没收违法所得、退还多付价款等难题。对此,学界大致存在两种认定标准。一是William M.Landes于1983年提出的净损失(net harm)标准。(15)William Landes主张金钱制裁的数额不应过高,也不应过低,应为违法行为的净损失,包括过高要价(overcharge)和无谓损失(deadweight welfare loss)。若违法行为的总收益大于净损失,经营者将不会放弃该违法行为,即使接受惩罚,依然对社会整体有益;若违法行为的总收益小于净损失,经营者将放弃该行为,同样对社会整体有益。某类型违法行为的具体制裁数额,还应结合被发现的几率再调整。二是Wouter Wils于2006年提出的非法收益(illegal gain method)标准。(16)Wouter Wils主张为了达到威慑违法行为的目的,应以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收益为标准,保障罚款数额大于违法行为的预期收益。Wouter Wils认为,William Landes以违法行为造成的整体损失为标准,仅制裁无效率的违法行为,目的在于追求社会整体福利;但竞争法应以禁止违法行为主体从受害人处获得利益为目的,应制裁所有违法行为。对于以上两个标准,虽然OECD认为William Landes提出的那种理想的理论标准在现实世界中不具有可操作性,在确定金钱制裁时不应考虑违法行为的正面效果;(17)但美国学者多赞同净损失标准,主张在理念上,救济措施至少不应降低社会整体福利。(18)目前,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中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的广泛共同适用,更倾向于非法收益标准,重视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尚未明确强调金钱制裁与社会整体福利或国家政策目标间的紧密联系。
在具体内容方面,多收价款和违法所得相对明确。多收价款集中于受害人损失,违法所得集中于违法行为主体因违法行为而获得的利益;它们主要关注过高要价而非无谓损失,不包括违法行为因限制产出而导致的消费者剩余,以及其他竞争者成本提升而导致的社会损失。根据《价格违法多收价款计算办法》,多收价款是指经营者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违反国家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根据《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认定违法所得的基本原则是,以当事人违法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适当的合理支出,为违法所得。违法生产商品的违法所得按违法生产商品的全部销售收入扣除生产商品的原材料购进价款计算;违法销售商品的违法所得按违法销售商品的销售收入扣除所售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违法提供服务的违法所得按违法提供服务的全部收入扣除该项服务中所使用商品的购进价款计算。
但罚款的具体内容则相当复杂,大致存在直接规定具体数额、以违法所得的倍数为标准计算、以销售额为标准计算三种方式。一般而言,有违法所得的,按违法所得的倍数计算罚款的上限;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根据行为类型、违法情节等,直接规定罚款数额的上下限。例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分别对价格串通、低价倾销、价格歧视、变相提价等价格反竞争行为的罚款数额作出了相当细致的规定。但若某反竞争行为也同时构成垄断协议和滥用支配地位,则一般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的百分比为标准确定罚款的上下限。其中,“销售额”的界定标准尚未明确,域外也无较成熟的共识。(19)英国公平贸易局将其解释为“相关市场内受违法行为影响的销售额”;并沿用欧盟《关于销售额的计算的通告》的规定,将“销售额”解释为“净销售额”,扣除销售折扣、增值税及与销售额直接有关的其他税收。(20)美国执法机构虽然也将其解释为“受影响的销售额”,但内涵仍存在争论。1995年Hayter Oil案(21)主张,相关销售额是违法期间所有销售的总和,无论是否采取违法定价,在确定罚金基准时都应被计算在内。但1999年SKW案(22)以后,法院便逐步主张仅考察采取违法定价的销售额,排除未采取违法定价的销售额。为使罚金更精确,更接近于William Landes提出的净损失标准,Robert Kneuper提出应将民事损害赔偿额认定中因果关系的因素纳入销售额的计算,要求执法机构证明销售额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3)但鉴于该经济分析方法给执法机构带来的举证负担,更精确的计算方式是否应替代原有较为笼统但更具操作性的方法,目前尚无共识。这样,在罚款的具体内容方面,不仅存在着“具体罚款数额”、“违法所得的倍数”和“销售额的百分比”这三标准间竞合的问题,还存在着如何确定具体罚款数额、如何界定销售额的难题。这都需要结合不同违法行为类型及其后果,在执法实践中不断探索。
因此,在金钱制裁中,相对于社会整体福利,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更强调对违法行为的威慑。但由于没收违法所得与罚款间的适用关系尚有自由裁量的空间,销售额的百分比、违法所得的倍数、具体罚款数额等各罚款数额计算标准间也亟需协调,中国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可在现有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政策目标不断推进金钱制裁制度的完善。
三、禁令:制止违法行为,引导违法行为的纠正,贯彻国家政策目标
禁令是指直接强制要求竞争主体作为或不作为,它与金钱制裁共同构成竞争法法律责任中最主要的责任承担方式。与金钱制裁相比,禁令并不以威慑为主要目的,更注重制止违法行为,消除违法行为的影响,防止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恢复被损害的竞争秩序。(24)在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中,禁令主要包括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强制性禁令和结构禁令,它们的归责要件和功能并不完全一致。
(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制止违法行为,引导违法行为的纠正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不以主观过错为归责要件,也不考虑除行为违法外的其他因素;只要行为具有违法性,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便应“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在价格反竞争行为领域中,这种责任承担方式被表述为“责令改正”。
与美国法的禁令相比,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不以“其他救济不足以维护竞争”为归责要件,中美两国禁令制度的立法目的也不相同。美国法的禁令可分为两类,分别是法院颁布的禁令和FTC颁布的停止令,它们均以“其他救济不足”为要件。根据衡平原则,法院颁布的禁令必须同时满足原告已经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法律上的救济方式无法适当地补偿此损害、此项衡平法的救济方式是有正当理由的、禁令的颁发不会对公众利益造成危害等要件。(25)虽然《联邦贸易委会法》第5条规定,只要FTC认为禁止某行为具有重要的公众利益,便可颁布停止令。但Herbert Hovenkamp在论证其合理性时提出,当缺乏足够证据来支持三倍损害赔偿等救济时,FTC颁布的停止令便可及时制止反竞争行为。(26)William Page将禁令的正当性总结为,只有当其他救济不足以维护竞争时,才需要禁令;若威慑是有效的,禁令仅在重复法院予以禁止的态度,并没有实际意义,也便无需浪费执法资源去纠正和监控竞争行为。(27)可以说,美国法中的禁令是社会整体效益理念下,制止反竞争行为的补充性制度。
从William Page的角度看,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中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不要求行为违法之外的其他要件,并且适用于全部反竞争行为,很可能沦为浪费立法和执法资源的毫无意义的举措。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从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内容来看,除责令停止行为外,还可能包括侵权物品的处理。比如,对于侵害商业秘密的,责令并监督侵权人将载有商业秘密的图纸、软件及其他有关资料返还权利人;监督侵权人销毁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生产的、流入市场将会造成商业秘密公开的产品。对于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等的,收缴并销毁或者责令并监督侵权人销毁尚未使用的侵权的包装和装潢;责令并监督侵权人消除现存商品上侵权的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收缴直接专门用于印制侵权的商品包装和装潢的模具、印板和其他作案工具等等。其次,从与相关法律间的协调来看,《行政处罚法》(1996年)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皮纯协教授认为,该规定的理由是,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必须把发现违法行为,处罚违法当事人与责令其改正放在工作的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不能仅仅简单施以处罚便了事。(28)该规定体现了《行政处罚法》中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在该原则下,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在竞争法中全范围适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及时制止违法行为;还在于在竞争法经验尚不丰富、竞争文化尚需培育的当下中国,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应承担起“积极引导、支持、培育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文化”(29)的职责,为违法行为的纠正提供帮助。亦即,反复强调对违法行为予以禁止的态度,在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对于竞争法的实施具有更重要的价值。
(二)强制性禁令与结构禁令:贯彻国家政策目标
强制性禁令包括强制许可、开放网络或平台等基础设施、许可关键技术、终止排他性协议等等;结构禁令包括禁止合并和拆分。
目前,除专利强制许可外,其他强制性禁令均由经营者集中制度予以规范与保障。至于如何在经营者集中程序之外适用这些强制性禁令,中国竞争法尚无明确规定。仅就专利强制许可而言,根据《专利法》第48条第2款,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被依法认定为垄断行为,为消除或者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仅对此作出了程序性规定,并未明确“消除或者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的审查标准。这样,强制许可的归责便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只要竞争执法机构认定拒绝许可构成违法,鉴于在认定违法性时已考察了“正当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便直接以此为由实施强制许可。另一解释是即使在认定行为违法时,已考量了“正当理由”,但国家知识产权局仍将采独立的标准对“消除或者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予以审查。这些问题都需执法实践的进一步澄清。
在经营者集中制度中考察是否应适用强制性禁令与结构禁令时,首先考察是否符合《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中的要求,若符合便应承担申报义务,否则依《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予以处理。在进入申报程序后,再根据“消除或减少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决定是否应附加限制性条件以批准经营者集中。这些限制性条件包括剥离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部分资产或业务等结构性条件,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开放其网络或平台等基础设施、许可关键技术(包括专利、专有技术或其他知识产权)、终止排他性协议等行为性条件,或者结构性条件和行为性条件相结合的综合性条件。根据《关于评估经营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考察对竞争的影响时,应综合行为人的动机、附加限制性条件对竞争的影响、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各种因素。此外,根据《关于实施经营者集中资产或业务剥离的暂行规定》,行为性条件、结构性条件的实施还应考虑实施的可行性、行政执法机构对实施过程的监督等问题。
因此,强制性禁令与结构禁令均采用原则性规定和一般性法律概念,相应归责要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到底是采纳William Page的观点,只有当其他干预措施不足以维护竞争时才适用,还是像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那样予以普遍适用,这需要执法实践的逐步澄清。但同时,这种不确定性也为在行政执法实践过程中不断贯彻国家政策目标提供了制度基础和衡量空间。
四、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制止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
撤销登记、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业整顿、暂停相关营业等这些竞争法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都属于能力罚,是一种限制或剥夺相对人特定行为能力或资格的,比较严厉的处罚方式,目的在于为制止、威慑违法行为提供足够的保障。它们适用范围相对狭窄,且均以行为违法和情节严重为归责要件。
其中,撤销登记仅适用于情节严重的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也包括行业协会或者其他单位组织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吊销营业执照仅适用于情节严重的价格反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等的擅自使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第50条规定的行为。吊销营业执照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责令停业整顿仅适用于情节严重的价格反竞争行为,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等的擅自使用。根据《责令价格违法经营者停业整顿的规定》,价格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是指社会影响较大,或者屡查屡犯,或者伪造、涂改或者转移、销毁证据,或者转移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资金或者商品等情形。责令停业整顿期限最长不超过7天。暂停相关营业仅适用于同时具有如下情形的价格反竞争行为,即违法行为情节复杂或者情节严重,经查明后可能给予较重处罚;不暂停相关营业,违法行为将继续;不暂停相关营业,可能影响违法事实的认定,采取其他措施又不足以保证查明。
五、结语
“竞争法起源于竞争的正常运行需要有法律保障,但成就于国家经济职能(即国家政策目标)的落实与实现。”(30)竞争法既要制止反竞争行为以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又要规范竞争以确保市场竞争按照国家既定目标有序进行。目前,以提醒告诫、金钱制裁、禁令、吊销营业执照等为主要承担方式的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方式多样灵活,功能多元。它相对重视反竞争行为的制止,但尚未达到在制止反竞争行为过程中实现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程度。但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也足够灵活,在实施过程中可容纳类似于美国《标准制定组织促进法》等(31)为实现国家政策目标而调整反托拉斯责任的规定。在竞争法行政执法实践中,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应以完善竞争法行政责任制度为契机,不断提升运用竞争法以实现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能力。
注释:
①当然,干预措施的正当性还源于正当程序。目前,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的程序规范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行政立法程序中的公众参与问题,行政责任程序中行政相对人“要求听证”的权利在行政立法程序中尚很难实现。中国竞争法行政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大多经由行政立法程序确定后,由行政执法程序负责落实。若行政立法程序无法保障公众的充分参与,行政执法程序的“准司法化”努力便被架空。二是非正式程序,尤其是行政约谈的规范化问题。行政约谈已被我国竞争法行政执法机构广泛应用,但尚无关于行政约谈程序的规定或指引,应按照“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的要求对行政约谈予以约束和保障。三是行业监管机构与竞争执法机构在竞争法行政执法方面的协调问题。虽然行业监管机构也享有竞争法执法权,但有些国家(如英国)规定,只有竞争执法机构有权发布关于法律责任的指南。我国尚无如此协调两者的规定。以上这些问题均较复杂,笔者拟另辟专文论述,本文仅限于竞争法行政责任实体规范的讨论。
②与“实施体制”、“行政制裁”或“公共执行”等表述相比,“法律责任”承载着说明责任施加的“应为性”的使命。参见朱景文主编:《法理学关键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页。
③例如,国家工商总局曾于2006年对某跨国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捆绑销售产品的行为进行了调查,并对该公司提出了行政告诫。参见《破除市场垄断倡导公平竞争——全国工商机关反垄断执法综述》,http://www.saic.gov.cn/ywdt/gsyw/sjgz/200903/t20090321_29239.html,2013年7月30日访问。
④除“停止令(cease and desist order)”外,FTC的执法权限还包括类似于罚款或赔偿损失的救济措施,如没收违法所得。See Hovenkamp,Herbert J.,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Sherman Act(June 16,2010).Florida Law Review,Vol.62,2010.n.36.
⑤参见董笃笃:《搜索引擎竞价排名中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对策》,载《消费经济》2013年第3期,第83~86页。
⑥See OECD,Remedies and Sanctions in Abuse of Dominance Cases,DAF/COMP(2006) 19.p.30.
⑦参见杨建顺:《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页。
⑧See Antitrust Manual of Procedures,Internal DG Competition Working Documents on Procedur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101 and 102 TFEU,March 2012.
⑨参见[日]栗田诚:《日本反垄断法的执行程序》,张军建译,载王艳林主编:《竞争法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日]村上政博:《日本禁止垄断法》,姜珊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7页。
⑩参见李俊峰:《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的资源、意愿与威慑力》,载王晓晔主编:《反垄断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8~356页。
(11)参见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竞争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编著:《中国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报告(2012年)》,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108页。
(12)See FTC,Policy Statement on Monetary Equitable Remedies in Competition Cases(Aug.4,2003).
(13)See Einer Elhauge,Disgorgement as an Antitrust Remedy,76 ANTITRUST L.J.79(2009).
(14)See FTC,Withdrawal of the Commission's Policy Statement on Monetary Equitable Remedies in Competition Cases(July 31,2012).
(15)See William M.Landes,Optimal Sanctions for Antitrust Violations,50 U.Chi.L.Rev.652(1983).
(16)See Wils,Wouter P.J.,Optimal Antitrust Fines:Theory and Practice.World Competition,Vol.29,No.2,June 2006.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com/abstract=883102.
(17)同注⑥,第24页。
(18)See William H.Page,Optimal Antitrust Remedies:A Synthesis(May 17,2012).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com/abstract=2061791.
(19)See James H.Mutchnik et al.,The Volume of Commerce Enigma,THE ANTITRUST SOURCE,June 2008.p.2.
(20)See OFT's Guidance as to the Appropriate Amount of a Penalty,OFT423,September 2012.p.9.
(21)51 F.3d 1265(6th Cir.1995).
(22)195 F.3d 83(2d Cir.1999).
(23)See Robert Kneuper and James Langenfeld,The Potential Role of Civil Antitrust Damage Analysis in Determining Financial Penalties in Criminal Antitrust Cases,18 GEO.MASON L.REV 953(2011).
(24)同注⑥,P.20。
(25)2006年Ebay案以后,该四要件标准在判例法中的演进,See The Evolving IP Marketplace:Aligning Patent Notice and Remedies With Competition:A Repor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March 2011).pp.253-279。
(26)See Hovenkamp,Herbert J.,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Sherman Act(June 16,2010).Florida Law Review,Vol.62,2010.n.56.
(27)同注(18)。
(28)皮纯协主编:《行政处罚法释义》,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29)吴宏伟:《法益目标: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之灵魂》,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第12页。
(30)吴宏伟:《我国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目标》,载《法学杂志》2005年2期,第16页。
(31)参见赵歆:《科技政策视角下的竞争与创新——美国科技政策立法对合作创新的反托拉斯规制》,载《科技管理研究》2012年5期,第10~13页。
标签: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论文; 竞争法论文; 法律论文; 商品标准论文; 经营者集中论文; 没收违法所得论文; 法制论文; 行政执法论文; 反垄断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