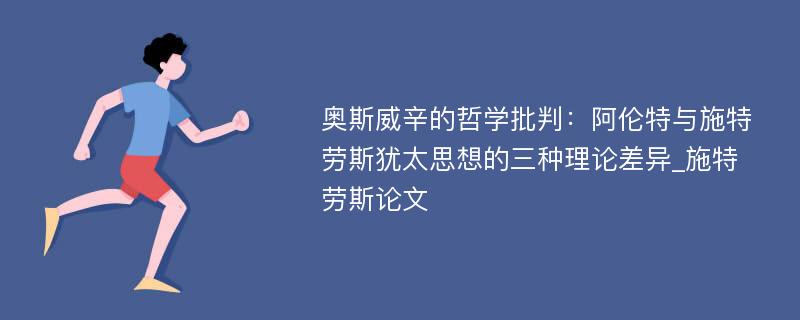
“奥斯维辛”的哲学批判——阿伦特和施特劳斯犹太思想的三个理论歧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施特劳斯论文,阿伦论文,犹太论文,歧见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013-06
在20世纪犹太流亡哲人当中,阿伦特和施特劳斯是两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哲学家。二者之间有着重要的背景相似性:他们都是有着犹太身份认同的政治思想家;作为犹太人的生存境遇、社会边缘人的经验体悟和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构成了两者学术思考的理论起点;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到马堡大学求学,海德格尔对古典思想的有力阐释和深度掘进对二者学术理路的最终成型影响很大;二者对纳粹极权主义有着重要的反省意识,并将理解和反思极权主义现象的根源视为自己重要的学术使命;二者都曾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①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践产物——以色列国都保有哲人克制的沉思距离;他们都走向实践的政治哲学而非纯思的理论哲学,都致力于政治问题和时代危机的审理,都对建构一套政治理论体系或政治设计方案持怀疑态度……然而,共同的身份认同和时代背景因素并没有拉近阿伦特和施特劳斯的思想距离。二者从相同的起点走向了不同的探究之途:前者将目光锚定于启蒙以降的现代社会,试图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和事件中洞穿本质,找到症结;后者试图从现代精神的诸思想前提中抽身而出,通过重启古今之争,意图站在古人的立场为现代政治哲学的“误入歧途”开方。为什么起点相同而终点迥异呢?我们如何评价两者理论诉求的视点高下?本文试图从犹太思想的角度入手,通过廓清二者理论观点的三个歧见,管窥两位政治哲人思想旨趣和理论观点差别的实质及其原因。
一、犹太人问题:政治问题抑或现代性问题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用一卷(共三卷)的篇幅来处理犹太人问题。在阿伦特看来,犹太人问题的实质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即“一种世俗的19世纪意识形态”。②换言之,阿伦特将“犹太人问题—反犹主义”定性为西方现代社会独有的一种政治现象,从而将“仇视犹太人”(Jew-hatred)和反犹主义区分③开来。翻开一部犹太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古罗马帝国末期到中世纪、近现代,犹太人连续不断地遭到歧视、驱逐和屠杀。阿伦特又是依据什么标准将19世纪之前的仇视犹太人和19世纪之后的反犹主义加以斩断的呢?这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阿伦特看来,“反犹主义只有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通过种族范畴,而非通过宗教信仰范畴进行区分时才开始出现”。④阿伦特将反犹主义置于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在阿伦特看来,以往仇视犹太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信仰的敌对而煽动起来的,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尤其是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转变为宗派选择,仇视犹太人的“理论根据和感情缘由”发生了质性变化,即不再是由于教义信仰的不同,而是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世俗因素的原因导致社会的反犹行为。因此,从犹太人迫害原因的变化上看,反犹主义实质上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晚近之事,是区别于前现代宗教反犹的现代政治事件。
二是阿伦特将仇视犹太人与反犹主义加以区分是为了反对纳粹屠犹事件的两个流行偏见。在阿伦特看来,与反犹主义事件本身相比,这两种流行解释“都是仓促的胡编乱造,只是为了掩盖问题,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衡态感受与明智愿望”。⑤第一个流行见解是“替罪羔羊”(scapegoat)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犹太人作为受害者是完全无辜的:“他不仅未曾作恶,而且根本未曾做过与面临的问题有关联的任何事情。”⑥在阿伦特看来,替罪羔羊论无法解释世界如此众多的民族为何唯独犹太民族遭到灭顶之灾,它也无法解释为何在“本世纪悬而未决的全部重大政治问题中,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犹太人问题”,而不是其他民族的迫害问题,“启动整部地狱机器”。⑦说到底,替罪羔羊论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或说明,其“内在破绽足以说明它是一种逃避主义的说法是应该被抛弃的”。⑧第二种流传甚广的见解是替罪羔羊论的反面说辞:“永恒的反犹主义”(eternal antisemitism)。这种理论认为,现代反犹主义不过是犹太人两千多年迫害史的自然延续。令阿伦特吃惊的是,这种说辞不仅受到反犹主义者的推崇,而且许多并无偏见的历史学家,甚至相当多的犹太人也接受了此说。对阿伦特而言,这种解释无视犹太人迫害原因的现代转变,“否定犹太人的一切责任,并且拒绝从特定的历史出发来讨论问题”。也就是说,要想获得反犹主义根源的合理解释,只能“在民族国家发展的比较普遍的框架中来观察现代反犹主义,同时应该从犹太历史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上几个世纪里犹太人所起的作用方面去寻找它的根源”。⑨
正是藉由这种政治的、历史的视角,阿伦特开始了反犹主义诸影响因素的考察。阿伦特将反犹主义定性为一种政治问题,通过分辨“社会歧视变成政治争端的时刻”来理解反犹主义的本质。⑩在阿伦特看来,反犹主义是极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触发原因。极权主义及其官僚统治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压缩了现代人自由行动的公共空间,因此,作为极权主义组成部分的反犹主义在本性上就是政治的。阿伦特强调:“犹太人命中注定走向历史事件的风暴中心,决定性的力量无疑是政治力量。”(11)然而不幸的是“只有它的敌人——而且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才理解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12)原因似乎很简单,因为犹太人长期处于一种无领土和民族政权的散居状态,因此缺乏必要的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这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事件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并且影响重大,原因在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错误问题,而是牵涉到“一场有组织地针对着他们(犹太人,笔者注)的政治斗争”。(13)当然,德雷福斯事件也并非全无结果,它导致了犹太人对反犹主义做出了唯一一次政治回答,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犹太复国主义可看作是犹太人认真地从敌对角度采取的唯一意识形态。(14)
在将犹太人问题视为现代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的观点上,施特劳斯与阿伦特观点一致,但二者的理由不同。阿伦特的着眼点是针对反犹主义的主流偏见进行批判,从而将前现代的信仰差异原因引发的犹太人迫害和现代社会的世俗原因导致的反犹主义区分开来。施特劳斯则将目光瞄向古今之变的开端处,试图在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背景下理解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因此施特劳斯对阿伦特那种对现代社会反犹主义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的琐碎分析不感兴趣,而是试图跳出现代思想的前提,通过疏解古典作品为现代性危机和犹太人问题把脉。基于这样的立场,施特劳斯认为犹太人问题完全是一种现代式的提法。因为在前现代政教合一的体制下,犹太人基于犹太教信仰的选民意识和弥赛亚观念认为犹太人迫害问题是犹太民族独有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一个需要人为方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只是当启蒙理性主义对正统神学及其治下的生活方式实现了彻底翻转,并试图依靠万能的理性来解决尘世人的所有问题时,犹太人的迫害问题才转变为一种亟需解决也能够得到解决的社会压迫、民族歧视问题。
然而,理性主义提出的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如自由主义同化方案,民族建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方案并没有达到最初的理想。在施特劳斯看来,犹太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事件已证明现代理性主义解决方案的彻底失败。“由于现代文化是特别理性主义的,相信理性的权力;这样的文化一旦不再相信理性有能力赋予自己的最高目的以效力,那么,这个文化无疑处于危机之中。”(15)换言之,施特劳斯通过犹太人问题存在的历史事实看到了理性主义的覆灭或现代性的危机。
依照阿伦特对“永恒的反犹主义”观点的批判,施特劳斯应该属于那类愚蠢的“并无偏见的历史学家”,因为后者没有对反犹主义的现实因素和历史演进花费精力,因而无法看清反犹主义存在的真正原因。而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阿伦特是一位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家。正是历史主义以及其催生的虚无主义才导致了极权主义和纳粹屠犹事件的发生。在施特劳斯看来,历史主义否定永恒的哲学观念,将真理还原为特定时间、地域,以及受这一时空背景下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的相对真理,这无疑取消了那种试图把握永恒真理观念的哲学问询。因此,是历史主义助长了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而一个没有好坏观念和敬畏意识的虚无主义立场与技术理性辉煌成就的联姻促成了史无前例的犹太人大屠杀。因此,在施特劳斯看来,那种囿于自由主义前提的历史主义理解和实证主义分析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自欺欺人。既然犹太人问题的存在已经表明现代理性主义解决方案的彻底失败,那么,我们或者回头,从前现代的理性传统中寻求药方,或者前进,彻底摒弃现代理性主义和现代文明,重开一种迥异于现代设计的方案。正是坚信回头优于前进的路向选择,施特劳斯埋头皓首穷经,向前现代的中古阿拉伯—犹太律法学说中寻求资源,以图找到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万能密钥。
二、极权主义的起源:群氓心理抑或虚无主义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生仰赖于群氓(the mass)(16)的形成与发展。所谓群氓,是指那些“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17)阿伦特指出,群氓现象的出现是欧洲国家内“阶级制度崩溃”的结果,阶级制度的崩溃导致了政党制度的自动瓦解,因为利益政党已不再能代表阶级的利益。“阶级保护墙的倒塌将一切政党背后迟钝的大多数人转变为一种无组织、无结构、由愤怒的个人组成的群众”,(18)转变为没有共同利益,没有共同纽带的原子式个人的混合体。当人数规模巨大的没有共同利益的个人混合起来,就产生了一种群氓心理,即“面对死亡或其他个人灾难时显出玩世不恭或因厌倦而冷漠,激情倾向于最抽象的概念(例如对生命的引导),普遍地嘲弄甚至最明显的常识规律”。(19)极权主义运动正是利用了这种冷漠和嘲弄一切既有秩序的群氓心理颠覆了民主原则的自尊和宪政制度的基础,实施了一系列“蔑视现实”、捣毁一切的征服运动乃至种族屠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将极权主义运动定性为“分子化、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的运动。(20)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群氓及其心理的描述,尤其是群氓个体的孤独、原子化、自我放逐于群体的生存结构的分析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此在生存结构的本质直观,对此在的沉沦、焦虑情绪和常人状态的现象学描述依赖于他对所处时代精神状况的敏锐洞察。而阿伦特的群氓及其心理的社会历史分析可以视为海德格尔此在的生存论描述在政治实践领域的一种精彩运用。然而,这种思想上的承继关系也表明阿伦特仍处于海德格尔精神影响之下,她缺少对海德格尔的哲学限度,尤其对海德格尔作为哲人的政治失足事件做出独立性的批判反思。(21)
同样是海德格尔的弟子,(22)施特劳斯则认真对待了海德格尔纳粹丑闻的哲学意义。(23)作为严肃的政治思想家,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的反思并非出于褊狭的犹太人的天然情感,而是基于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激进历史主义的一种哲学思考。在施特劳斯看来,纳粹极权主义不过是德国虚无主义的一个变种。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将民族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欧洲现象不同,(24)施特劳斯将虚无主义看作特别是德国的,将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视为“德国虚无主义最有名的形态”。而且,施特劳斯强调,“民社主义的失败未必意味着德国虚无主义的终结。因为,那种虚无主义的根基比希特勒的煽动蛊惑、比德国在世界大战的战败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要深得多”。(25)
那么,什么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它又是如何导致纳粹极权主义起源的呢?
施特劳斯认为,虚无主义是“对文明本身的拒斥”。这一本质性表述包含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这个定义的前提是要求虚无主义者必须知晓文明的原则。或者说,一个不了解现代文明的未开化者、野蛮人绝不是虚无主义者。因此,是否知晓文明是区别希特勒代表的现代极权主义与过往专制政府、僭主暴政和独裁的一个基本原则。二是在程度上,虚无主义并非绝对的虚无主义,即德国虚无主义并不意欲万物全都毁灭,它只意欲现代文明的毁灭。更准确地说,虚无主义只是意欲现代文明中道德价值方面的毁灭,而不反对现代文明的技术原则,如依靠现代技术成果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依据技术理性设计的官僚科层统治,等等。也就是说,虚无主义实质上指的是价值虚无主义。三是在源流关系上,要知晓虚无主义的起源还需廓清虚无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关系。因为“德国军国主义是德国虚无主义的父亲”,或者反过来说,“德国虚无主义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激进形态”。(26)因此,要透彻理解虚无主义就需要先理解军国主义。在施特劳斯看来,要找到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就要撇开“德国文明的史前史,直接观察德国文明本身”。我们知道,现代文明的源头是英国和法国。现代文明的倾向,尤其是法国革命的知识倾向是降低道德标准和要求,将道德善好等同于个人权利和自身利益的目标。由于德国较之英、法步入现代文明较晚,其传统自身残留的贵族意识和神法观念具有一种对道德和哲学精神堕落的本能抵触。在这一本能抵抗过程中,英勇、武德作为“毫不含糊的非功利德性”突显出来。因此,“德国虚无主义为了战争与征服的缘故,为了武德的缘故拒斥文明本身的原则。由此德国虚无主义接近德国军国主义。”(27)在施特劳斯看来,将德国军国主义最终导向虚无主义主要是由于德国思想家的工作,如尼采、斯宾格勒、布鲁克、施米特、恽格尔、海德格尔,等等。他们为这种消解性而非肯定性的反对现代文明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并“有意无意地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28)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批判尼采、海德格尔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导致了否定文明本身的原则,最终走向了虚无主义。“尼采与德国的纳粹革命的关系一如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最该对德国虚无主义的产生负责的,乃是尼采”。(29)作为尼采思想的强有力阐释者,海德格尔自然难辞其咎,罔论他那众所不齿的政治丑闻。可见,对海德格尔的辩护或批判,构成了阿伦特和施特劳斯对纳粹极权主义反思的重要区别:阿伦特群氓心理的政治历史分析及其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倚重在施特劳斯看来无非是混淆本质的做法,而施特劳斯对虚无主义的海德格尔式问责也是阿伦特在美国竭力为海德格尔辩护的一个原因。然而,二者之间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二者的思想旨趣的差异。对阿伦特而言,对20世纪主要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弊端分析是其著述的要点,而施特劳斯则将目标瞄向遥远的中世纪和古希腊传统。
三、理论旨趣的差异:躬身现代抑或返身古典
施特劳斯的《德意志虚无主义》系1941年在美国的一个演讲,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正酣,德国纳粹主义的铁蹄所向披靡。施特劳斯在文献很少且前景极不明朗的情况下向远离欧陆本土的美国听众解释极权主义的成因及其危害。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手稿写于1945-1949年,初版于1951年。阿伦特试图用“历史学家的回顾眼光和政治学家的分析热情”来理解和把握极权主义这一20世纪的主要政治现象的原因及其后果。与施特劳斯的著作不同,阿伦特的作品涉及大量现代文献、史料和事例,并试图深入现代社会的机理当中寻找反犹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当代景观。阿伦特的理论旨趣相当明显,她是立足于现代社会,通过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为现代极权主义的发生把脉。
比较而言,施特劳斯从犹太人问题看到了现代理性主义及其政治设计方案的致命缺陷。(1)现代理性主义试图取代上帝的位置,解决人的所有问题,但事实证明它无法取代信仰在人的灵魂中的位置。因此,现代理性主义支配下的现代社会不过是满足了人的物质需求和无限膨胀的欲望,却导致了现代人精神上的无家可归甚至价值的颠覆。(2)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试图通过政教分离的方式将宗教信仰转变为私人领域可供自由抉择的宗教派别,由此消除因信仰不同导致的犹太人政治迫害。但自由民主制是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为前提的。“私人领域不仅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还必须被理解为不受法律的干预”。(30)因此自由民主制能够免除公共领域犹太人的政治迫害却无法消除私人领域的反犹情绪。(31)既然自由主义同化方案无法解决犹太人问题,施特劳斯放弃了深入现代社会内部分析反犹主义现象及其原因的努力,而是试图回到现代社会的发端处,试图重启古今之争的方式来理解现代性的产生及其演进。
然而,要想重启古今之争,就必须像启蒙哲人一样了解他的批判对象——正统神学教义及其古典思想的涵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估价启蒙哲人在哪些方面战胜了古人,在哪些方面只是悬置了问题。由于施特劳斯关注犹太哲人斯宾诺莎思想的革命意义,对斯宾诺莎的研究引导施特劳斯回到中古伊斯兰—犹太律法宗教,尤其是迈蒙尼德的先知律法学说,进而回归律法的古希腊来源,即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思想。因此,施特劳斯的思想旨趣是在预设现代社会整体退步而非进步的前提下,通过疏解古代经典作品恢复对政治哲学原初问题的检审,从而得出自己对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判断及其对策。(32)
施特劳斯意图在超逾现代思想前提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33)这阻碍了他像阿伦特那样借助现代学者的思想文献资源,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心理、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分析当中。站在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施特劳斯反对众人平等的启蒙观念,反对历史主义将永恒真理消解为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相对真理。而阿伦特的工作正是在承认启蒙精神的某些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开展着施特劳斯一直反对的研究工作。
结论
综上可见,施特劳斯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他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人自以为是的傲慢倾向,以谦卑的求教心态去接近古人,去阅读和理解古代经典作品,并反思现代文化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固执于施特劳斯的立场而抹煞阿伦特哲学探索的意义。正如伽达默尔在评论施特劳斯时所谈到的:“人们可以承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优越于我们,但这不意味着人们便必须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可恢复的。”(34)换言之,现代人已经成功地创建了古人所不知道的现代政治制度及其原则,尽管现代民主制度弊端重重,但它仍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之一,而且目前尚无更好的政治方案来替换它。如果我们深处现代社会而无法回返到前现代,阿伦特的方式,即历史地深入理解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现象及其本质的做法就是有益的,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时代重大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弊端。
另一方面,依照阿伦特的观点,施特劳斯将犹太人问题视为绝对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观点是一种极端悲观的论调,是放弃理解尝试的逃避主义。阿伦特在“‘犹太人身份’和‘犹太教’之间作出区分”,她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否认作为犹太传统遗产的犹太教律法学说。这在施特劳斯看来是回避耶雅永恒冲突的表现,虽然阿伦特在黑暗的政治现实中仍然坚持犹太人问题有解决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淹没在诸种不定因素和邪恶政党政治的不确定性当中。因此,在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和政治本性的不完善性的理解方面,施特劳斯对神学政治问题的关注以及封闭政治社会的残酷性的表述比阿伦特的美好心愿在本质上更接近于真相本身。
注释:
①施特劳斯在17岁时加入犹太复国主义,成为复国主义运动在德国最辉煌的一段时期的活跃分子。随着学术思考的深入,施特劳斯最终在十年后(1928年)脱离了该组织。阿伦特一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曾直接或间接地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工作,但她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学者批判意识,并且一直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②[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一部《反犹主义》序言,第4页。
③克里斯蒂瓦认为阿伦特是第一个对旧极权反犹主义和现代极权反犹主义加以区分的政治哲人。参见[法]克里斯蒂瓦:《汉娜·阿伦特》,刘成富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④[美]约翰逊:《阿伦特》,王永生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26页。
⑤⑥⑦⑨[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7、40、37、43、45页。
⑧[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0页。所谓逃避主义,是指这种反犹主义解释回避了反犹主义的严重性,以及降低了犹太人被驱赶到事件的风暴中心这一事实的意义。关于逃避主义参见,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1页。
⑩参见[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63页。同时参见[美]约翰逊:《阿伦特》,王永生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26页。
(11)(12)(13)(14)[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38、100、176、179页。
(15)[美]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译,《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刘小枫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16)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卷第十章,中译者将“the mass”翻译为群众,笔者认为群众一词过于中性,无法体现这一概念的贬义成分,因此采用“群氓”的译法。
(17)(18)(19)(20)[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07、411、412、421页。
(21)阿伦特在美国多年来一直努力捍卫海德格尔的思想,抵制学界对海德格尔向纳粹主义妥协的攻击,这在1969年阿伦特发表的《马丁·海德格尔80寿诞》一文中表现尤为明显。参见克里斯蒂瓦:《汉娜·阿伦特》,刘成富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页。沃林教授认为海德格尔的弟子,诸如阿伦特、马尔库塞、约纳斯等人都没有对海德格尔政治丑恶的一面作出深刻的反省。参见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张国清、王大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代译者序,第4页。
(22)施特劳斯的海德格尔弟子身份不如阿伦特正宗,但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讲座对青年施特劳斯思想触动很大,这在晚年施特劳斯与克莱恩公众对谈——《剖白》中可见一斑。毫不夸张地讲,施特劳斯著作中或隐或显的海德格尔痕迹可以看出施特劳斯的哲学努力始终是以理解和对抗海德格尔思想为主要对象的。参见《剖白——施特劳斯与克莱恩的谈话》,载于《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华夏出版社,2008,第271-272页;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甘阳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一章;施特劳斯:《〈斯宾诺莎宗教批判〉英译本导言》,汪庆华译,载于《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226-272页。
(23)在生命末期的一封致索勒姆的信中,施特劳斯坦言:“在度过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我现在才明白,他(指海德格尔,笔者注)究竟错在哪里:具有非凡的才智,这才智却依附于一个俗不可耐的灵魂。”参见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迈尔编,朱雁冰、何鸿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481页。
(24)[美]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张国清、王大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25)[美]施特劳斯:《德意志虚无主义》,丁耘译,载于《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26)(27)(28)(29)[美]施特劳斯:《德意志虚无主义》,丁耘译,载于《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26、125、124、112、124-130、126、128页。
(30)[美]施特劳斯:《我们时代的危机》,李永晶译,载于《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8页。
(31)参见Leo Strauss,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Essays and Lectur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nneth Hart Gree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p.315.
(32)参见[美]施特劳斯:《评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余慧元译、李致远校,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33)参见[美]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刘宗坤译,载于《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迈尔著,刘小枫主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34)[德]伽达默尔:《访谈:伽达默尔论施特劳斯》,田立年译,载于《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迈尔编,朱雁冰、何鸿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487-488页。
标签:施特劳斯论文; 极权主义的起源论文; 阿伦特论文; 反犹太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奥斯维辛论文; 哲学家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犹太民族论文; 现代性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