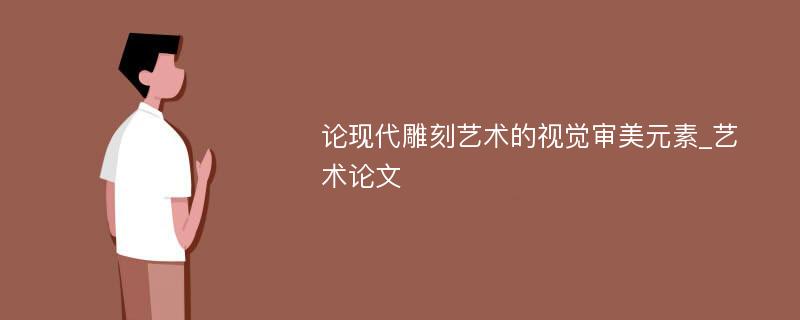
论现代刻字艺术的视觉审美元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素论文,视觉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刻字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艺术。从历史上看,源远流长,最早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乃至更早的刻划符号,伴随着汉字的产生而出现。而本文所指的现代刻字艺术是指近三十年来方兴未艾的新兴刻字类型,是指有别于传统实用刻字而成为独立艺术门类的现代刻字艺术。现代刻字艺术产生的时间比较短,它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八十年代后期传入中国,除中国和日本外,开展现代刻字艺术活动的国家还有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现代刻字艺术的创作理念、模式和技艺完全不同于传统刻字。传统刻字是依附于书法而进行再度摹刻(往往是应实用所需要),以纤毫毕现摹刻书家书法、再现和保存文字书法形象为目的,刻字本身没有创作的审美追求和审美创意。而现代刻字以创造性的构思和手工制作为基点,无论内涵和技艺都要比传统刻字丰富得多,就其技法而言,融合了书法、绘画、篆刻、雕塑、版画、装饰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综合性。它不仅使“刻”本身成为独立的审美语言,而且深入挖掘构成、色彩、肌理、装帧等内涵,使审美的语境达到理想化。同时刻字艺术的手工操作,是人的心手和自然材质的最原始化触摸,是现代商业化、信息化时代人与自然的深度和谐体验。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刻字艺术是一门有着自身独立审美语言,能传达独特审美意境的新兴艺术形式。迄今举办了七届的全国刻字艺术展,基本上代表了现代刻字艺术的基本状况和创作成就。
纵观古今书法经典,精神追求重“质”,于笔精墨妙中显现书法的特点和精神,纸笔交融间体验心灵的虚静和安宁,展示汉文字语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由于文化环境的变迁和差异性,当代书法在适应书法展览化的过程中,由于人文性书写和文化内涵的缺失,使当代书法处在一种尴尬的矛盾之中,既不能完全回归传统书法追求文化精神的道路,又无法避免展览式书法的内涵缺失。反观现代刻字艺术,以书法为基,在视觉上从平面到立体,在理念、色彩、材质等方面多方拓展,在根植书法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艺术的表现力,对古老的汉字书法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创造性诠释,开拓了一个新的人文精神视域。作为极富视觉装饰艺术效果的现代刻字艺术,重“形”的审美理念和创作模式,巧妙地化解了当代书法在适应展览过程中由“质”转“形”的矛盾,其对传统书法的消解和转型,使传统文化转型在当代文化视域中找到了一个新的模式和平台。所以,相比于传统的书法形式,现代刻字艺术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其兼容性和边缘性:它与木刻画等雕刻艺术都讲究刀法与多维空间的表现,但它刻的是汉字;它与书法都讲线条结构、章法,但它是彩色的、立体的、木质的、刀刻的。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抒情性,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而不像传统刻字那样仅仅是手工劳作。相对于传统书法的文化内涵诉求,现代刻字艺术的审美理念和模式更多地体现出一种重“形”的创作理念和模式,在传统刻字的基础上,吸纳版画、雕塑、装饰等艺术的技术优点和共通点,把汉字书法与刻凿技艺巧妙结合起来,强调“视觉元素”在刻字过程中的应用,追求一种“视觉惊艳”的审美效果,使现代刻字艺术完全区别于传统的实用刻字。
现代刻字艺术的重“形”特征和其本身独具的视觉审美元素特征,使其能第一时间“跳”入人的视野。这种让人“惊艳”的直觉反应是一种普遍的视觉感知经验,它缘于观赏者的反视觉经验。有关研究表明:“接受者面向美术作品时,最初感受到的是作品中的可视形态、形象和形式,如作品的大小、色彩、光影、线条、描绘的对象等。”[1]也就是说,眼睛首先感受到的是“可视形态、形象和形式”。其原因在于一切物体都是借助光而被眼睛觉察,“从太阳或别的光源发出的光线照射到上述对象上面,一部分被这些对象吸收了,另一部分则被这些对象反射回去。在这部分反射的光线中,又有一部分透过观察者的眼睛投射眼睛最敏感区域——视网膜上。”[2]所以当我们看作品时,那些通过一定媒介等物化出来的“可视形态、形象和形式”,在光的反射作用下首先投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所以,在一个空间结构下,首先被感知的物体是视觉相对注意的物体,这种视觉注意与视觉积极主动的选择有关。经验和实验都证明,人们在观看事物时,总是善于捕捉眼前事物的某几个最突出的特征。用心理学家的话说就是“能引起优势兴奋中心的各种刺激物”。[3]如刻字作品的文字书法构成图像、色彩搭配和材质肌理的效果是最吸引观赏者注意力的视觉审美元素。
刻字艺术的文字书法构成图像必须根据主题内容的文字进行深度的构思和设计,反复提炼和完善,达成美的形式法则。所谓形式美法则是指构成造型艺术的诸要素按照美的规律的有机组合。[4]不论是在平面构成还是在立体构成中都存在着许多矛盾,如形的方圆、大小、曲直,体的轻重、厚薄、虚实等,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使它们秩序化、条理化、理想化,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贯穿于构成始终的“变化与统一”这条基本原理,即形式美的基本法则。形式美的要求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是秩序的美,一是打破常规的美。这两种形式都能产生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以达成完美的视觉效果。在刻字构成设计中,要重视对比与调和的应用和体现,对比具有强烈醒目的特征,容易成为视觉中心。调和就是在对比中找出统一的因素,使设计组成的各个部分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相互配合,使作品整体协调。在设计构成中,对比不是无限度的,如果变化过多,就会破坏整体的秩序美感。可采取渐变、重复和近似的元素,使对比的矛盾相互接近,达到协调。其次,重视构成设计的对称与均衡,一般情况下,对称与均衡是一对相对的矛盾,对称是从均衡中分离出来的,是一种严肃、庄重、静穆、条理、大方、静止的美,是最完美的平衡形式。但过于完美,就有可能产生单调、呆板和沉闷的感觉,均衡则是打破这种静止的局面,追求一种活泼、轻快、丰富和富于动感的美。而节奏与韵律则是借用音乐的“节奏”和诗歌的“韵律”在构成设计中的应用,节奏可以是视觉对比的造型因素有规律地重复呈现,引起观赏者视觉心理的有序律动,韵律则是使节奏具有强弱起伏变化,使人审美心理变化产生良好的反应。通过对比与调和、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的作用,从而达成多样统一,构成完美、统一、协调的整体。在第六届全国刻字展中,吴东民、吕如雄、崔志安、汪德龙等人的作品,在主题立意上,初一看去,就让人产生一种大朴不雕、自然简约的审美感受。如吕如雄的《矛盾》,主题字法的构成设计极富巧思,黑、白、红色的对比调和、线条的方圆曲直相得益彰,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其在刻字艺术上达到的高度,令人叹服。崔志安《寒窗》中象形“窗”字的排列,卷轴、线装书的巧妙结合运用,较好地表现了主体的审美要求,创造出与主体思想相和谐的意境。
色彩构成,就是将两种以上的色彩加以配置,进行比较,并根据不同的目的,按照一定的比例,有秩序、有节奏地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使其产生新的视觉效果,从而构成和谐的色彩整体。[5]色彩组合所产生的美感,离不开色彩的对比与调和。对比色拥有一种令人兴奋的视觉感,但是它缺乏单色调与和谐色的那种安全感,所以对比色彩的成功运用依赖于良好的色调平衡。刻字艺术家一方面要经常加强主观综合感觉的个性投入,另一方面要理解色彩的属性和体系,系统把握色彩的情感代表特征,将两种以上相同相近或者是色相、色谱完全不同的色彩,根据创作的目的性,按照既定的创作原则,利用自己的学识、修养和审美趣味将其重新组合、搭配、安排,构成新的色彩关系。它的构成必须是有机的、科学的,才能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现代刻字艺术的迅猛发展,越发凸显出色彩元素的重要作用,色彩成为现代刻字的重要语言之一,几乎每件刻字作品都不得不涉及到色彩因素。作为一种符号语言,色彩在视觉感受方面的传播能力和感染力甚至超过了文字内容,因为色彩对于深入刻画形象,抒发情感,烘托氛围,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作品内容,具有和构图构思同等的作用,在特定的表现题材上,它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其他因素。一幅优秀刻字作品必然是有独特色调倾向的,那种杂乱无章、各自为政、缺乏色调协调性的刻字作品是不会给人们带来美感的,色彩运用得好,就能为主题思想增添光彩,提高艺术感染力。在第六届全国刻字展中,《雪花飞舞》、《寒窗》、《矛盾》等作品都较好地利用了色调构成,用归纳和强调的手法,突出了作品的视觉效果和整体感,字形构成也因此充溢着情感张力,并使线条的展示与整体空间相映相掩,取得了简约中寓丰富的效果,让人体验到当代刻字创作对色彩的大胆实验和大胆挑战的意味。吴东民《雪花飞舞》绿底上的白点搭配,“飞舞”二字的纯白色调和灵动如飞舞般的书法笔势相谐,取得了与主体思想相和谐的意境。《寒窗》清幽的浅棕褐底衬托着淡蓝色调,从色彩上看,非常完美地表现出了寒窗书斋淡雅的氛围。
刻字艺术是借助有关材质来进行雕刻的,材质本身的质地,即材料的本质属性所显示的表面效果,是通过视觉和触觉直接感受的。雕刻的材料,质地本身是静的、深邃的、朴素而雅致的。而经过刀刻斧凿的材质表面效果,质地没有变,肌理改变了,使观赏者在视觉和触觉中加入了某些想象的心理感受。所以,经过造型行为的肌理效果呈现出来的美是动的、实用而智慧的。现代刻字的视觉元素特征除其整体形式构成、色彩以外,保留凿刀痕迹这一形式肌理感是刻字作品的另一重要方面。所谓肌理感,即由物体的表面组织构造所引起的视觉触感和触觉质感。[6]现代刻字作品的视觉艺术效果,很大程度上是由刀痕肌理表现出来的,而传统刻字中较少保留凿刻的刀痕斧迹。
现代刻字的材质主要是木材,将一块木材转化为艺术品,主要工具是刀,能不能成为令人愉悦的艺术品,刀痕肌理表现也极为重要。现代刻字的刀痕凿迹是一种全新的独特的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看不见刀痕凿迹的作品,谈不上什么刀法,体现不出刻字的本体意义。而刀痕凿迹不显、不美、不力,或不能完美展示这独特的视觉元素,则不能成为完美的刻字艺术作品。现代刻字在刀刻锤凿的过程中,通过刀的平面高低角度、锤击力大小、刀痕重叠交叉的多寡等变化,使材质的刀痕肌理表现出来的意境丰富多彩。尤其是大面积凿铲的块面,往往充分体现出凿痕特有的粗犷美和锤凿的力度美,能在不同层次的观众读者心中引发不同的意象,产生形有尽而意无穷的自然意境。在第六届全国刻字展中,如果说陈拥军的《推陈出新》是以构成设计为主来展示主题意境,那么丘超平的《推陈出新》则重在刻凿刀痕肌理的表现,都取得了很好的刻字艺术表达效果。相比于汪德龙《大梦敦煌》刀痕肌理的苍凉粗犷,崔志安《寒窗》刀刻的平整不着痕迹,则表达了一种淡雅安宁的主题思想意境。
从审美知觉的“图—底”关系来看,“一个视觉样式,是不能在不考虑它所处的空间环境的结构而孤立地被观看的。”[7]所以在现代刻字艺术中,各种元素的作用也不是孤立地存在,而应该是一个互补、和谐的有机整体。在进行主题构思的设计时就应该考虑色彩、刀法的选择与协调,色彩的构成也必须充分考虑主题构思和形式构成的需要,刀法的造型则应当与作品形式内容相和谐,要使那种看似乱凿的刀痕表现出一种美的形式肌理。当然,刻字作品的构成、色彩和材质被视知觉捕捉,也会因观赏者的审美经验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关注点,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从而产生不同的审美价值评价,则是难以避免的。
本文为全国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