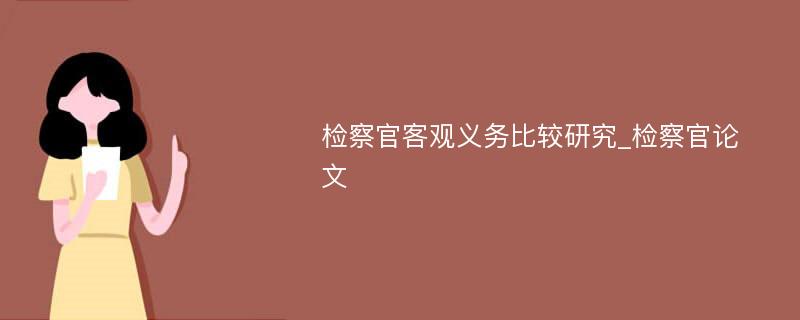
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检察官论文,客观论文,义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进行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对抗制的合理因素,庭审对抗程度有所增强,为了适应这种诉讼模式的转型,检察官的角色和定位理应相应地作出调整。全面地解决检察机关的定位问题,不仅要考察纵向的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要考察横向的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西方诉讼法学界提出的检察官客观义务问题恰恰就是以检察官与被追诉者之间的关系为重心的一个学术概念,基于抑制检察官过度追诉而出现的角色混乱问题,国内学者近期开始对检察官的客观义务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应当说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而言,是一个纯粹的舶来品,而且更是一个新兴的概念,鉴于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对待这一理论,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做好比较研究工作,包括界定概念、梳理内涵、对比主要国家的表现形式、分析各种争论。
一、关于客观义务的内涵界定:从客观义务的历史产生根据与本质出发
从法制发展史来看,关于检察官承担“客观义务”的规定,创设奠立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德国,随后传播到了欧陆以及亚洲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注:林钰雄:《检察官论》[M],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2页。) 在欧洲大陆国家如比利时、丹麦、希腊、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刑事司法构造中都能或多或少找到德国法上客观义务的痕迹,显示出来德国法在这一方面的深远影响。此外在亚洲,包括日本、我国的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刑事诉讼中也都规定了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但恰恰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概念迄今我们还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界定,至于这种“客观义务”到底包括哪些内涵也不是十分清楚。(注:产生于德国法上的这一概念,加上日本学者的转述令我们很难找到其合适的英文对应词,一般情形下,英文作者们往往使用" objectively" ," in objectivity" 这些副词来表述“客观行事”的涵义,但基本上没有" objective obligation" 或者" objective duty" 的用法。) 目前国内学者运用较多的概念主要来自于日本学者松本一郎先生的论述,他认为“客观义务是指检察官为了发现真实情况,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活动”。(注:[日]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J],郭布、罗润麒译,《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 这种界定方式的核心就是客观立场,但到底什么是客观立场?这种客观的立场与法官的立场是否应当相同还是应当介于法官的“客观”与当事人“主观”之间?客观义务到底是一个明确的概念,还是一种开放式的多种特征的集合体,客观义务包括哪些内涵,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一系列问题作为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必须予以明确。囿于笔者资料与语言的限制,尚未能找到德国学者关于“客观义务”的明确界定,因此不得不尝试从“客观义务”在德国的产生历史以及有关表现出发,同时运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的两种界定方式,尝试着对这一概念进一步予以明晰。
(一)客观义务历史产生过程中的内涵
日本学者认为“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这一概念是以实体的真实主义和职权审理主义为基本原理的德国法学的产物”,(注:[日]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J],郭布、罗润麒译,《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尽管本文翻译的年代较早,而且其主要论述内容也只是集中在日本检察官的客观义务问题上,但该文仍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研究客观义务问题的一篇重要参考译文资料。) 从检察官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这一判断无疑是十分准确的。客观义务产生于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引入法国的检察官制度、创设1877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过程中,当时对于检察官的角色与定位存在着“主观的一造诉讼当事人”和“客观的法律守护人”两种对立的观点,前者将检察官定位于如民事诉讼原告相同的诉讼中的一造,职责在于攻击对造(被告),与刑事诉讼中的自诉人相类似;第二种观点认为检察官应当“担当法律守护人的光荣使命,追诉犯罪者,保护受压迫者,并援助一切受国家照料之人民”;“在对被告的刑事程序中,作为法律的守护人,负有彻头彻尾实现法律要求的职责。”(注:林钰雄:《检察官论》[M],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2页。,第32-34页。) 经过激烈的争论,法律守护人的定位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客观义务也就成为了对这种“法律守护人”定位的一种诠释。所谓“法律守护人”的角色也就是要求检察官为着实现法律所体现的公正,应当同时注意到有利于与不利于被告人两方面的事实,同时承担起追诉犯罪与开释无辜的责任。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职责统一于刑事诉讼的目的即实现实体真实与正义。(注:林钰雄:《检察官论》[M],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2页。,第32-34页。) 由德国先儒们对客观性义务以及检察官定位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客观义务”产生的两个理由:刑事诉讼发现实体真实目的与平衡控辩实力差距。要求检察官承担“客观义务”目的就在于发现实体真实,因为有利于与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对于全面发现案件事实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检察官代表国家天然强大,应当使其承担帮助被追诉方这一弱者的义务,平衡控辩差距,防止诉讼演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游戏。
此外,从检察官产生历史来看,客观义务的第三个理由在于检察官的诞生标志着控审分离原则的实现,旧制度下法官承担的查找证据、起诉犯罪者的任务逐步地开始转给检察官承担,检察官从纠问式法官那里承继了客观公正地评价事实的义务。(注:[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简而言之,从客观义务的产生历史来看,检察官负有的客观义务有三个方面的涵义:检察官应当尽力追求实质真实;在追诉犯罪的同时要兼顾维护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通过客观公正的评价案件事实追求法律公正地实施。客观义务的归宿在于强调“法律守护人”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客观义务的本质就是要求检察官只对法律的公正负责。
(二)客观义务表现特征的列举式外延
在界定客观义务时,经常使用的另一方式就是引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三项客观义务条款,即检察官在收集证据时,对于有利于与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均须予以收集;审判过程中,检察官如果认为证据不足以定罪,可以要求法院宣布被告人无罪;检察官可以为被告人利益提起上诉或者请求再审。(注:分别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60条第2款、第156条和第296条、第365条。尽管德国法中没有检察官“要求无罪判决”的明文规定,但在第156条规定了公诉不能撤回,根据该款,即使审判中证据显示的情况与检察官在审前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不同,检察官唯一的选择就是要求无罪判决,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这种列举式的界定方式很难说具有独立性,应当将其看作是对德国法上客观义务内涵的一种印证方式,如同时收集有罪与无罪证据体现了对实质真实这一诉讼目标的追求,要求宣告无罪与为被告人利益上诉体现了检察官对被告方利益的关照与公正实施法律的努力。本文认为在界定检察官客观义务时始终还是应当以概括式的界定方式作为内涵,而德国法律上这三种表现只能是作为客观义务的一种印证,是概念的外延。如上所述,客观义务的内涵有三:追求实质真实、平衡控辩实力悬殊与追求法律的公正实施。这三个方面的内涵相互联系,但同时也是相互独立的。三种内涵之间的独立性使得三项要素可以部分地被移植、传播到其他国家,在客观义务的传播过程中这一趋势十分明显。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对德国诉讼程序中产生的客观义务理论,进行了全盘移植,包括德国法上有关客观义务的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在台湾刑事诉讼法中都有相应的可资对照的条款,而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在移植客观义务的规定时并没有全盘移植完整的客观义务的内涵的各个方面,而是根据各自的诉讼构造、诉讼制度选择了其中的部分因素,形成了多样化的、程度各异的客观义务的规定与理解。
二、欧陆主要国家对客观义务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欧陆主要国家对客观义务的规定或者说阐释从用语上、内涵上多少有些差异,体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具体内容参见表一。
表一(注:表格中关于各个国家检察官客观义务的论述,分别参见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Christine VAN DEN WYNGAERT eds,Butterworths1993,p14,p58,p168,p190,p290,p318,p386.有关苏格兰检察官定位的论述参见Julia Fionda,PUBLIC PROSECUTOR AND DICRETION:A COMPARATIVE STUDY,Clarendon Press.Oxford 1995,p203.)
国家
对客观义务的阐释方式采纳的客观义务
内涵的要素
检察官有义务追求实质真实即检察官有义务收集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如果检察
比利时
官认为被告人是无罪的,必须向法官请求无罪判决;检察官因此在理论上并没有当
全部三项要素
事人的作用,而应当以法律公正实施为唯一追求客观地履行职责。
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并非真正地“反对”被追诉方,他的任务是为了法律与正义的利追求实质真实与
丹麦 益客观地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发现客观真实。因此检察官可以为了被告人的利益提 法律的公正实施
起上诉。
希腊 检察官不是反对被追诉方的一方,他是司法机关,有义务追求客观真实。 追求实质真实与
法律的公正实施
检察官的责任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地给被告人定罪,而是向法庭出示所有他知悉的证 公正实施法律与
据,确保法庭正确地适用法律,即使这样做是对被告人有利也是如此。检察官应当 平衡控辩实力差
爱尔兰
主动或者在被追诉方提出请求时,告知被追诉方所有对其有利的信息,他不应当仅仅异
追求对被告人除以某种具体的刑罚,而是应当将所有与量刑有关的事项展示给法庭。
荷兰 检察官代表公共利益,为了正确、公正适用法律而行事,检察官无需不惜一切代价地法律的公正实施
追求给被告人定罪,他只需公正地处理案件。
葡萄牙
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是与法官协作共同发现真实、实现公正,检察官在诉讼 追求实质真实与
程序中应当遵循严格的客观性标准。 公正实施法律
西班牙
检察官必须捍卫法治、保护公民权利与法律保障的公共利益以实现公正。 公正实施法律
检察官更多地被认为是中立的官员,在日常的司法程序中,检察官提出有利于被告 追求实质真实与
苏格兰
人的证据的做法十分常见,检察官客观立场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检察官的 公正实施法律
客观义务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说教。
通过表一中列举的几个欧陆国家检察官客观义务的规定与阐释,我们可以发现德国式客观义务的规定是所有国家中最为严格的,尤其是作为客观义务外延的三种表现形式(全面收集证据、要求无罪判决、为被告人利益上诉或请求再审)更是如此,即使与之最为接近的比利时也仅仅具备了三种表现形式中的两种,而对为被告人利益上诉与提起再审没有规定。以上的粗略对比初步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客观义务在不同的国家确认形式有别,外延的表现形式也存在种种差异;二是对这种表现形式多样化的客观义务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必须注意到客观义务内涵的多层次性与可分性,并抓住客观义务的本质即检察官只对法律的公正负责。否则在多种缤纷复杂的客观义务表现形式面前,我们很难开展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
三、对抗制下的检察官客观义务
(一)美国法中检察官的客观义务:理想与现实的反差
美国是个判例法国家,寻找美国法上关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规定自然应当以各级法院的判例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美国的检察官同时具有律师身份,也就应当受美国律师协会发布的一系列执业行为准则与职业道德的约束。如果说判例法的规定对于检察官的定位囿于具体案件情况的考虑而显得过于零散与宽泛的话,有关职业道德规范与执业行为准则中对检察官客观义务的规定作为近似制定法的法律文件则显得更为清晰与具体,本部分对以上两种法律渊源中关于检察官定位与客观义务问题的看法分别予以介绍。
从判例法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美国一些州法院就开始在判例中认为,检察官的角色应当为准司法官员,并主张从这种角色定位出发,探寻检察官的各项职责与义务。(注:Bruce A.Green,Why Should Prosecutors" Seek Justice" ,26 Fordham Urban Law.Journal(1999);有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几个州法院作出的在检察官定位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参见,People v.Cahoon,50 N.W.384(Mich,1891); Meister v.People,31 Mich.99(1875); People v.Lee Chunk,20 P.719(Cal.1889).)在这些判例中,密歇根州法院的一份判决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判决中法官认为:“检察官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对无辜的人错误定罪绝非公共利益所允许。检察官的职责应当与法官一样,只是实现公正,检察官不能为了任何职业荣耀而牺牲法律的公正。无论他个人对被追诉人有罪的怀疑有多么强烈,检察官也必须记住,或许不公正的手段在个别案件中会让罪犯受到惩罚从而在个案中实现了公正,但这种做法对整个社会来讲却是不公正的,甚至是危险的”。(注:Hurd v.People,25 Mich.404,415-16(1872).) 联邦法院系统有关检察官角色的经典判例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35年伯格诉合众国一案作出的裁决。(注:Berger v.United States,295 U.S.78(1935).) 在这一判决中法院明确地表明:“美国检察官代表的不是普通的一方当事人,而是国家政权,他应当公平地行使自己的职责;因此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不能仅仅以追求胜诉作为自己的目标,检察官应当确保实现公正(do justice or seek justice),也就是说,从这个特别的、有限的意义上讲,检察官是法律奴仆,具有双重目标,既要惩罚罪犯,又要确保无辜者不被错误定罪。检察官可以而且也应当全力以赴地追诉犯罪,但在他重拳出击时,却不能任意地犯规出拳。不允许使用可能产生错误结果的不适当手段追诉犯罪,与用尽全部合法手段寻求公正的结果,二者同样属于检察官的职责。”这一判例明确了联邦检察官应有的角色定位,“检察官不应仅仅追求有罪判决,而是要实现公正”的诫命成为了美国司法实践中经常为辩方律师引用作为质疑检察官行为不当的抗辩理由,检察官应当追求公正的司法判决意见也成为了随后美国律师协会制定有关检察官行为准则时重要的参考依据。美国学者、司法实务界对于检察官角色定位以及客观义务问题的争论无不以此判例作为论述的对象与分析的起点。
从成文规定的角度来看,美国检察官的职业道德与执业行为准则中关于检察官角色与义务的内容规定在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责任示范法典》和《律师执业行为示范规则》两部法律文件中。《律师职业责任示范法典》规定检察官的职责不同于普通律师,他的职责是实现法律公正,而不仅仅是寻求被告人的有罪,而《律师执业行为示范规则》规定检察官不仅仅要承担普通律师的职责,更要承担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国家官员所应当具有的职责。(注:参见Model Cod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EC 7-13;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Rule 3.8.) 实际上在以上两个文件中美国律师协会对检察官角色定位的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早在185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美国律师协会的论文中就表明了下列观点:检察机关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机构,在其中一位像法官那样公正的官员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行使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观点也成为了后来美国律协制定律师职业道德法典的重要参考论点。(注:Bruce A.Green,Why Should Prosecutors" Seek Justice" ,26 Fordham Urban Law.Journal(1999).) 从这两份文件的影响范围来看,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采用了两份文件中对律师定位的基本方法,接受了政府律师应当“追求公正”这一标准。(注:Fred C.Zacharias,Structuring the Ethics of Prosecutorial Trial Practice:Can Prosecutors Do Justice? ,Vanderbilt Law Review,January 1991.)
美国学者与司法实务界人士认为之所以应当令检察官负有“实现公正”的义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平衡控辩双方实力的巨大悬殊,被追诉者作为渺小的个人与代表着巨大国家权力的检察官相比,实力悬殊显而易见,检察官相较于被追诉者的巨大权力,要求检察官在履行职责的同时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特别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义务;二是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检察官代表着公共利益,作为国家在刑事司法中的代表,检察官应当实现国家委派其参加刑事诉讼的目的,而国家在刑事司法中的目的正是实现公正,实现公正就要求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开释无辜,要确保给予被追诉者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公平的诉讼程序这种角色定位也常常被界定为准司法性质。(注:参见Bruce A.Green,Why Should Prosecutors" Seek Justice" ,26 Fordham Urban Law.Journal(1999).美国各级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都确认过检察官的这种准司法定位角色,参见Imbler v.Pachtman,424 U.S.409,423 n.20(1976); State v.Chambers,524 P.2d 999,1002(N.M.Ct.App.1974); State v.Moss 376 S.E.2d 569,574(W.Va.1988).)
尽管美国判例法与职业道德中对检察官公正执法的义务树立了很高的理想,但现实情况却与理想状况有很大差异。由于执业行为准则与职业道德中对“追求公正”这一标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界定,实践中也很难找到普遍接受的界定方式,解释起来也十分困难。这一标准的模糊性给检察官自行理解这种公正执法的义务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一些检察官认为公正就是竭尽全力追求有罪判决,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检察官大多怀有有罪推定的心理倾向(注:Felkenes,The Prosecutor:A Look at Reality,7 SW.U.L REV.98(1975); Fred C.Zacharias,Structuring the Ethics of Prosecutorial Trial Practice:Can Prosecutors Do Justice? ,Vanderbilt Law Review,January 1991.);这种标准的模糊性也削弱了对检察官不当行为进行职业纪律制裁的力度。(注:参见Fred C.Zacharias,Structuring the Ethics of Prosecutorial Trial Practice:Can Prosecutors Do Justice? ,Vanderbilt Law Review,January 1991.) 长期以来检察官过度地追求有罪判决而实施偏见性不当行为的判例比比皆是。(注:可参见Brown v.Borg,No.91-555148,1991 U.S.App.Lexis 28490(9[th] Cir,1991); United States v.Robert,618 F.2D 530,535 (2d Cir 1980); United States v.Vargas,583 F.2d 380,388(7[th] Cir.1978); United States v.Corona,551 F.2d 1386,1391(5[th] Cir 1977),转引自Gordon Van Kessel,Adversary Excesses in the American Criminal Trial,Notre Dame Law Review(1992).) 检察官经常对是否有罪存在强烈怀疑的被追诉者提起控诉;在研究完卷宗之后,在说服了原本不愿作证的证人出庭作证后,在设计好庭审策略之后,检察官往往认为自己已经对这一案件付出了很多,从而必须要将该案起诉到法院并竭力争取有罪判决;检察官的案件胜负率是衡量检察官工作业绩的重要标志,对于选举产生的检察官来说,胜诉率更是作为选举的重要因素受到关注。(注:参见Gordon Van Kessel,Adversary Excesses in the American Criminal Trial,Notre Dame Law Review(1992).)
促使美国对抗制诉讼结构部分接受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诉讼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对“司法竞技”理论的逐步改造。“司法竞技”理论将诉讼视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场争斗或者一场竞赛,陪审团作为竞技的观众对双方在对抗中的表现进行评断,从而作出是否有罪的裁决。由于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对庭审激烈对抗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对抗制诉讼模式的绝对崇拜,“司法竞技”理论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对抗式的真实发现方式恰恰是美国诉讼制度的灵魂所在。但随着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也开始逐步显露出来,过分强调对抗已经使得美国的诉讼模式越来越偏离了诉讼程序发现真实、正确定罪的既有目的。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一理论提出质疑,主张通过向美国诉讼程序中加入更多的真实发现的因素抑制司法体制中由于过分强调对抗而带来的各种弊端。(注:有关这一理论的争论参见Roscoe Pound,The Cause of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40 AM.L.REV.(1906); JEROME FRANK,COURTS ON TRIALS:MYTH AND REALITY IN AMERICAN JUSTICE 80-102(1949); ALBERT GUERARD,TESTAMENT OF A LEBERAL 114-15(1956).)“真实发现”理论对美国司法实践的影响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要求控方不仅应当向辩方开示有罪证据,对那些明显对被告人有利、可能影响到案件结果的无罪证据,检察官也应当开示,这反映出检察官负有一定的公正执法的义务或者说客观义务。但由于对“司法竞技”理论的固守,美国的制定法与判例法均不主张检察官全面开示证据,而是将证据开示机制建立在控辩双方互惠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既然辩方由于受宪法上不得自证其罪特权的保护而不被要求开示全部证据,那么检察官也不应当单方承担过重的证据开示义务,毕竟美国的刑事程序在本质上被看作是控辩双方律师之间进行的一种“竞技”。(注:参见Gordon Van Kessel,Adversary Excesses in the American Criminal Trial,Notre Dame Law Review(1992).) 可见“发现真实”理论不是取代而是与“司法竞技”理论进一步融合,相应地美国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也并没有突破对抗制的基本结构。
二是在美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的趋势面前,美国对抗制中既有的若干正当程序原则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协,特别是辩诉交易的广泛使用和转化程序的不断增加使得检察官决定被追诉者处罚的权力越来越大。(注:Julia Fionda,PUBLIC PROSECUTOR AND DICRETION:A COMPARATIVE STUDY,Clarendon Press.Oxford 1995,p204,p206.) 检察官权力的扩大特别是部分准司法权的行使要求检察官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公正义务,为了保障被追诉者要求公平审判权利以及正当程序权利不被过度减损,就非常有必要加强检察官公正行事的职业道德与执业行为准则方面的要求。实际上伴随着检察官筛选案件权力的增加,只有那些最为严重的案件才进入到审判程序中,对于大量的轻微或者中等程度的案件,在令检察官负有公正执法的义务的同时从传统的对抗制程序分流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与对抗制的诉讼结构在美国的诉讼程序中得以同时并存。
在此有必要对美国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进行一下小结。一方面,美国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体现为“追求公正”的义务,同时体现出来了平衡控辩实力差距的考虑,与德国检察官负有的客观义务的内涵相比,对实质真实的追求这一要素的强调并不十分突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抗制的价值目标与既有传统更倾向于依靠诉讼双方的对抗实现真实的发现,而真实发现也并非属于美国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程序的正当性经常被置于真实发现之上。在这里,对抗制与讯问制两种诉讼模式对待“法律公正”的理解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大陆法传统中通过发现实质真实、正确处理案件而追求的“法律公正”与英美法中更加重视程序公正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法上检察官追求公正的义务比起大陆法系上的检察官客观义务来看,贯彻得并不彻底。这一点在检察官对待无罪证据的做法上体现得较为明显。根据美国学者的判断,一般而言对抗制并不要求一方帮助另一方进行审判准备工作,检察官不负有为辩方收集无罪证据的宪法义务。(注:Fred C.Zacharias,Structuring the Ethics of Prosecutorial Trial Practice:Can Prosecutors Do Justice? ,Vanderbilt Law Review,January 1991.) 但由于检察官负有宪法义务开示对辩方有利的证据,如果检察官知悉了对辩方有利的证据,根据宪法判例负有义务开示给辩方,同时检察官不得采取积极行为妨碍辩方收集证据,在许多情形下,检察官还应当为辩方收集证据提供便利。(注:如配合辩方检验、鉴定控方掌握的物证材料,根据辩方的要求组织辨认,检查控方证人的精神状态,帮助辩方寻找可能提供有利于辩方证言的证人,这方面美国联邦法院、州法院作出的有关判例参见Bennett L.Gershman,The Prosecutor' s Duty to Truth,Georgetown Journal of Legal Ethics,2001 Winter.) 这种客观义务的表现形式与德国法上要求检察官同时收集有利于与不利于辩方的证据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美国法对检察官客观义务的要求,主要是消极性义务居多,即检察官不得从事妨碍真实发现的活动,在特殊情形下,检察官也负有配合义务帮助辩方发现真实,但美国法上的客观义务并不要求检察官负有积极义务收集无罪证据。
考虑到检察官权力的不断扩大,为了防止因诉讼对抗过度而威胁到诉讼程序的整体目标,同时也为了平衡控辩双方的实力悬殊从而为真正平等的对抗创造条件,美国也开始要求检察官应当承担“实现公正”的义务,并通过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权利告知制度部分地将客观义务落实到具体的诉讼程序中。同时通过判例,确认了检察官违反公正义务可以作为提起宪法救济的理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客观义务具有了可救济性。但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检察官的客观义务界定模糊又缺乏细化的解释,加之对抗制诉讼结构对这种客观义务的“磨损”,实践中客观义务的贯彻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原因在于美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一直以来都十分强调通过赋予被追诉方大量的诉讼权利来与控方对抗,实现自己的权益,而不是将保护被追诉方的任务委任给同时负有追诉任务的国家机关,这种制度设计的方式与德国强调公权力机关在发现真实、实现诉讼目标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也折射出德国与美国对待国家权力的不同观点以及对法治社会的不同理解,“英美刑事诉讼最值得借鉴的,应该不是什么‘主义’或者体系,而是在刑事诉讼中对人性有比较深刻的透视,只要是人,就可能滥权,就可能怠惰,就可能麻痹,就可能犯错……不相信任何一个有权的人,是英美刑事诉讼制度的上位概念”。(注:王兆鹏:《当事人进行主义之刑事诉讼》[M],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序言部分。)
(二)英国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
在1985年英国检察机关皇家检控署成立之前,英国没有专门的起诉机关,由警察负责起诉,但出庭指控事务由出庭律师代理进行,英国律师职业道德准则一直以来并未将控方律师视为普通律师,而是将其视为司法公正的管理者。早在1865年英国的一位著名法官就对控方律师的职责与定位作出过经典的论断:“控方律师不应当将自己视为普通律师而单纯地追求有罪判决,正确的定位应当是协助实现司法公正的臣仆(ministers of justice)”。(注:Puddick(1865)4 F & F 497,per Crompton J,参见CASES AND MATERIALS O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Michael Zander,2003,p255.) 皇家检控署自创立之始就十分注重强调检察官的中立地位,《皇家检控官准则》第2.3条、第2.4条分别规定,检察官应当始终为着司法公正的利益行事,而不应单纯地追求有罪判决;检察官应当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确保将所有相关证据提交给法庭,并确保证据开示义务得到遵守。(注:《皇家检控官准则》英文文本THE CODE FOR CROWN PROSECUTORS下载自www.cps.gov.uk,最后访问时间2004年8月5日。) 另一方面从英国的整个诉讼结构来看,侦查程序与起诉程序的分离使得皇家检控署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能够客观地评价警察收集到的各种证据,全面地衡量各种法律意见与政策需求,衡量有利于与不利于控诉的各种理由。这样检察官的法律地位就不应当是不惜代价地寻求有罪,而应作为法律的臣仆确保案件根据现有的证据而得到公正地处理;这种定位使其与具有“过度追诉倾向”的警察区别开来,警察的定位就是通过自己的调查发现犯罪,而无需考虑证据是否充分、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恰当地保护。(注:Julia Fionda,PUBLIC PROSECUTOR AND DICRETION:A COMPARATIVE STUDY,Clarendon Press.Oxford 1995,p58.) 皇家检控署有责任确保向法庭提交所有的证明有罪或者无罪的相关证据,这种规定使得英国检察官的角色定位与欧洲大陆检察官的角色定位更加接近了。(注:Julia Fionda,PUBLIC PROSECUTOR AND DICRETION:A COMPARATIVE STUDY,Clarendon Press.Oxford 1995,p58.推动着英国检察机关的角色进一步向大陆法传统靠拢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欧洲一体化对英国司法改革进程的影响,上文提到的欧盟部长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的建议》,也将适用于英国,因此英国检察机构的定位必须要作出一些调整来回应上述法律文件的要求。) 皇家检察署自己也声称:“认为相互对立的两方当事人只需关注自身利益的观念是把目前的司法体制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必将造成一种错误的认识,因为这种观念忽视了检察官负有的开示证据的义务与在发现案件事实中的作用。”(注:Julia Fionda,PUBLIC PROSECUTOR AND DICRETION:A COMPARATIVE STUDY,Clarendon Press.Oxford 1995,p58.) 英国检控方在庭审中的角色与美国的同行相比更加客观,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英国庭审中负责出庭控诉的是与皇家检控署相对独立的出庭律师(barrister),出庭律师并不直接参与案件的起诉以及侦查或者案件的准备,这直接减少了庭审胜诉与否对出庭律师的压力;出庭律师也经常在控诉与辩护两种角色之间进行转化,因此胜诉与否的意义,对英国的出庭律师来讲就比美国的同行更加弱化了。(注:Gordon Van Kessel,Adversary Excesses in the American Criminal Trial,Notre Dame Law Review(1992).)
四、意大利与日本混合式诉讼模式中客观义务的表现与争论
(一)作为公共方当事人的意大利检察官所负有的客观义务
1988年意大利刑事司法改革进行了由讯问制向对抗制的剧烈转型,此次改革被许多国际比较法学者看作是二十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次司法改革运动。(注:Ennio Amodio & Eugenio Selvaggi,An Accusatorial System in a Civil Law Country:The 1988 Italian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62 Temp.L.Rev.1211(1989).) 在此次改革中,诉讼程序中的检察官转变成为了一方当事人,检察官在旧法审前程序中享有的一系列司法权力被转交给了审前法官行使,这种改革的旨意主要是为引入对抗制打造一个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平台。但即使是作为诉讼当事人,意大利的检察官也不被认为是普通的一方当事人,因为他的职责不是单方面反对被追诉者,而是应当客观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保障检察官这一公共当事人能够为着法律与正义的目标开展独立的、公正的调查,意大利的法律规定检察官适用自行回避的规定。(注:参见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Christine VAN DEN WYNGAERT eds,Butterworths1993,p230.) 意大利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也有与德国法大致相似的规定,该法典第358条规定:“公诉人为实现第326条列举的目的而开展一切必要的活动,并且也核实对被调查人有利的事实和情节”,而且检察官也可以在庭审中请求无罪判决和为被告人利益提出上诉。(注:Elisabetta Grande,Italian Criminal Justice:Borrowing and Resistance,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2000.) 意大利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的另一原因是根据意大利宪法的规定,检察官与法官同样属于司法官员,检察院属于司法机关,因此检察官必须负有职责作为公正的机构实施法律,意大利宪法法院曾经裁决检察官的这种公正地位与作为公共方当事人的新角色并不矛盾。(注:Corte cost.,decision no.88 of 15 February 1991[1991]II CP,no.71,p.207,转引自EUROPEAN CRIMINAL PROCEDURES,Mireille Delmas-Marty and J.R.Spencer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361.)
(二)日本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及其争论
日本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受德国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引入了检察官客观义务的规定,(注:日本学者松本一郎认为,尽管1922年日本颁布旧刑事诉讼法时没有明文规定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学说上也没有使用“客观义务”一词,但实际上把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保护被告人的正当利益视为当然的事情,参见[日]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J],郭布、罗润麒译,载《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 传统上的观点仍然认为检察官的职责不单是与被告人进行对立、斗争的一方当事人,同时也是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检察官必须在充分考虑被告人利益的基础上,从客观立场公正地执行职务。作为实在法上的根据,日本学者经常援引《检察厅法》第4条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39条来印证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前者规定:“检察官请求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后者规定了检察官为被告人利益请求再审。(注:[日]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J],郭布、罗润麒译,《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 伴随着二战后,日本在占领国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改采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检察官的客观义务问题也开始遭到了部分日本学者的质疑,认为客观义务的规定与当事人主义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理念相抵牾,令检察官负有客观义务,其结果是助长检察官的权威、冲淡当事人主义的性质、趋向“侦查审讯化”和进一步提高“精密司法”的程度;即使是为了约束检察官行使不公正的检察权,倒不一定必须使用“客观义务”这样一种媒介。(注:[日]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J],郭布、罗润麒译,《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松本一郎先生质疑客观义务的主要观点是客观义务是与实体的真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的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的产物,而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不相兼容,即使考虑到检察官权力的控制这一问题,也可以选用其他更好的方法进行,因为客观义务的规定必然会带来种种副作用。) 为了合理解释对抗制结构下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并应对上述质疑,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法中逐渐发展出来了“新客观义务论”的观点,分别从检察官的司法属性与行政属性出发论证了客观义务的表现形式,各种观点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检察官在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同时,必须肩负其维护正当程序的职责或者说协助实现公正审判的义务。(注:[日]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J],郭布、罗润麒译,《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
五、客观义务的国际化
近年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的认同,在一系列国际公约与文件中,都规定了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增强了客观义务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影响。这种客观义务国际化的趋势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对客观义务的采纳。该准则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表明,准则的作用就在于协助各国确保和促进检察官在刑事程序中发挥有效、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的作用,在该规则第12条、第13条与第14条进一步明确了检察官的公正品性与客观义务,这些条款要求检察官“应始终一贯迅速而公平地依法行事;应不偏不倚地履行其职能;保护公众利益,按照客观标准行事,适当考虑到嫌疑犯与受害者的立场,并注意到一切有关的情况,无论是对嫌疑犯有利或者不利;如若一项不偏不倚的调查表明起诉缺乏依据,检察官不应提出或继续指控,或应竭力阻止诉讼程序”(注:该《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的相关内容参见程味秋等编:《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汇编》[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第264页。);二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检察官承担客观义务的规定,在该规约第54条与第81条的规定明确地体现了客观义务的两项德国式外延,其中第54条规定“检察官进行调查时,应同等地调查证明有罪与无罪的情节”,第81条规定检察官可以代表被定罪人的利益提起上诉(注:参见《批准与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手册》[Z],赵秉志、王秀梅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450页。);三是2000年10月6日欧盟部长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的建议》,该建议在2004年再次得到了欧洲议会的肯定与推广。(注:英文文本Recommendation Rec(2000)19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to member srat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ion in the criminal jusitce system下载自http://cm.coe.int/ta/rec/2000/2000r19.htm,最后访问时间2004年9月10日。) 在这一规范欧盟国家检察官角色定位的区域化文件中,对检察官的客观义务进行了详尽地列举:检察官在庭审程序中必须保持客观与公正,特别是要确保提供给法庭所有相关的事实与观点以实现司法公正;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检察官应当公正地、无偏倚地、客观地行事,按照《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尊重与保障人权,并尽力确保司法程序尽可能迅速地进行;检察官应当尽力确保法律的平等适用,应当注意到所有对被追诉人产生影响的事实,无论这些事实对被告人有利还是不利;当公正的侦查表明指控缺乏根据时,检察官不应提起指控或者终止起诉;检察官不得使用有合理根据认为是违法取得的证据指控被追诉人,在对有关证据有疑问时,应当请求法院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裁决;检察官应当尽力实现武器平等原则,特别是应当向对方公开(在法律规定了证据开示制度的国家,应当开示)自己持有的可能影响程序公正的所有信息。(注:分别参见该建议第20条、第24条、第26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
三项国际性法律文件对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强调都十分明显,但也各有侧重,其中对于公正适用法律与平衡控辩实力悬殊两项客观义务的内涵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对于发现实质真实这一客观义务的要求在《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与《关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的建议》中都多少有些弱化,比如两个国际文件中均使用了“注意”一词,而不像《罗马规约》中直接使用了德国式的“调查有罪与无罪证据”的提法。但无论如何,这些国际性法律文件,特别是《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与《关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的建议》两份文件对于型塑世界主要国家与欧盟成员国检察官的角色,强化客观义务在检察官定位中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六、比较研究的启示兼答两种针对客观义务的质疑
(一)客观义务与对抗制的兼容问题
客观义务与对抗制能否兼容这一问题实际上是英美国家在检察官是否负有客观义务这一问题上产生争议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诸如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借鉴对抗制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难题。从纯粹理论分析上来看,客观义务与对抗制之间的确具有一些不太契合之处,对抗制强调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而客观义务要求控方帮助辩方,但随着英美国家对抗制理念的逐渐更新,特别是纯粹的“司法竞技”理论逐渐吸收“追求真实”的理念,鉴于控辩双方实力上的显著悬殊,在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同时更多地给作为公益利益代表的检察官增加一定程度上的客观义务,是实现控辩双方在实质上平等对抗的重要条件。此外对抗制毕竟是一种旷日持久的资源消耗程序,上世纪后半期以来,面对诉讼爆炸、案件复杂程度的日益增加,英美国家不得不赋予检察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通过辩诉交易或者转化程序从正式的对抗制程序中分流案件,在大部分被分流的案件中,为了确保检察官正当行使权力,英美国家的处理方法之一就是赋予检察官更多的客观义务、公正执法的义务以约束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英美国家对客观义务的规定主要是集中在平衡控辩实力差异与确保公正执法两个方面,由于客观义务在内涵上的多样性,使得客观义务的规定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可塑性,英美国家能够在对抗制的语境下发展出与对抗制得以兼容的客观义务。
日本学者与意大利学者在对待检察官客观义务时,一个共同的担心或许就是唯恐检察官权力过度膨胀会威胁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诉讼结构。在中国目前关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争论过程中,同样的担心也出现了。检察官承担客观义务是否会破坏控辩平衡是目前质疑检察官客观义务的理由之一。笔者认为客观义务的存在不会破坏诉讼结构的平衡,而是恰恰相反,客观义务是平衡控辩实力差距的重要工具,须知客观义务令检察官负担了更多的义务,而不是扩充了检察官的权力。上述美国关于检察官是否应当追求公正的争论中,赞成者的主要论点就是强调该义务乃平衡控辩双方实力差异之举,正是为了平衡控辩双方之间天然的不平衡,才出现了调节控辩悬殊的客观义务。(注:笔者还注意到上述担心恐怕更多是担心客观义务会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从而造成控辩失衡,囿于本文的主旨,对法律监督问题在此不作展开论述,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法律监督主要涉及检察官、法院、公安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客观义务主要涉及控辩双方之间的关系,二者规范的领域显然存在明显区别,不应混为一谈。)
客观义务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另一冲突在于在保障被追诉者个人权利方面是委诸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检察官还是依靠被告人个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方式来实现。反对客观义务的观点认为,“在诉讼程序中主张或者强调检察官保护被告之客观义务,其结果被告反须付出比受检察官保护所得利益更高的代价,因为检察官为早日发现真实,必须对被告有利、不利证据一并彻底侦查,俾使无辜被告早日从刑事程序中解放,如此便会造成侦查长期化、侵犯被告隐私权等不合理情事,为保障被告人人权,及维护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实不宜采行赋予检察官保护被告之客观义务方式,应该采赋予刑事被告诉讼防御权的方式。”(注:朱朝亮:《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之定位》[J],《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15期。) 这种观点推理的前提无非是选择客观义务就要放弃其他保护被告人权利的方式,客观义务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相矛盾。笔者认为二者完全可以结合,而且也应当结合,就以美国这个经常被认为被告人权益保护状况最佳的国度为例来讲,被告人自行维护权利、自行调查与辩护的前提条件是个人的经济实力,但现实情况是能够聘请私人侦探、鉴定专家与检控方平等对抗的当事人少之又少,80%以上的案件中被告人无力聘请私人律师,而不得不接受政府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这就使得司法实践中造成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包括检察官强迫被告人接受协商条件的情形。(注:吴巡龙:《美国对刑事诉讼两造对抗制度之修正——证据开示程序》[J],《法学丛刊》第185期。) 理论中所设想的被告人自行维护权利的情形,其前提是辩方当事人具有与控方对抗的平等实力,但即便是在经济实力最为发达的美国,这种前提也是难以实现的。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历来注重使用国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大陆法国家如德国、法国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结果也已经使得“人权保障程度的优劣”这一标准失去了比较法上的意义,自二战之后,大多数实行讯问制诉讼模式的国家就已经开始将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来对待了,在当代大多数实行讯问制模式的国家里,被告人享有一系列主要的诉讼权利包括无罪推定、反对强迫自证其罪、获得律师帮助等权利。(注:Gordon Van Kessel,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he Accused as a Source of Testimonial Evidence,100 W.VA.L.REV.799(1998); Maximo Langer,From Legal Transplants to Legal Translations:the Globalization of Plea Bargaining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Thesis in Criminal Procedure,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Winter,2004.) 对权利保护方式与客观义务的冲突,我们一方面可以从相互融合的保护方式上予以解释,另一方面也应当注意到不同诉讼传统、法治传统的国度对保护方式的选择都具有各自的根据。
(二)客观义务的现实可能性
检察官作为犯罪的追诉者能够做到以客观立场行事吗?这涉及到客观义务的现实可能性问题,也是质疑客观义务最为常见的一个理由。这个角度对客观义务的质疑大致有两种主要论据:一是从心理学上的内在矛盾与诉讼职能区分的角度;二是从检察官自身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看,胜诉的欲望与利益令检察官经常无视毫无任何违反后果的“客观义务”。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让同一人同时承担两种相互冲突的职能确实存在着矛盾。同时令检察官承担追诉职能与辩护职能,甚至有时还要承担维护公正的司法职能,与心理学规律、诉讼职能区分规律相悖。如有学者认为:“要求检察官有效打击犯罪,以维护社会秩序之同时,复要求其应当保障人权,首先就人性而言,宛如对以打猎为生之猎人,要求其于打猎之余,不得滥杀野生动物一般,不是不可能,而是实期检察官会有良好成效,通常会流于伪善的钓鱼式查证,当然检察官也无法如无辜被告所期待的,成为一位热切忠实的人权辩护者”(注:朱朝亮:《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之定位》[J],《东海大学法学研究》第15期。);“全世界最公正客观的公署”云云,在辞藻的堆砌上是有可能的,然犹如晋惠帝不解:“何不食肉糜”,是完全脱离刑事诉讼的现实世界的。(注:王兆鹏:《当事人进行主义之刑事诉讼》[M],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序言部分。)
客观义务在各国实践中也的确存在着现实情况与既有理想之间的反差,在上文中,对于美国情况已有所论述,这里不再赘言。即使是在客观义务的发源地德国这种反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实践中,检察官的作用非常类似于更明确的当事人制度下的指控官员,比如检察官为了被告人的利益而提起上诉的情况就很少发生。与其他制度一样,德国的检察官尽量避免提起日后被证明不成立的指控。但是这与法律要求的公正性无关,而是检察官的效率和职业作风的要求。一旦作出起诉决定,德国的检察官将抛开他们的中立姿态,尽力去赢得诉讼,甚至不亚于美国的检察官。”(注:[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对于这种由于诉讼职能集于一身而带来的心理冲突,首先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冲突在心理学上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德国学者在对客观义务探讨多年也不得不承认“赋予检察官客观义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与其控诉职能是冲突的”。(注:陈卫东、刘计划、程雷:《德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现在与未来》[J],《人民检察》2004年第11期。) 这种冲突是必然存在的,检察官本身就是多种利益的代表者,检察官并非单单代表被害人、代表国家的利益,检察官同时应当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包括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要求。多种利益的维护附加于检察官一身,使得检察官在追诉犯罪的同时,不得不戴上“通过防止冤枉无辜而维护司法公正、追求实质真实”的脚镣。为了能够使得检察官能够最大化地克服上述矛盾心理,检察官的职业修养、职业理念的灌输与培养至关重要,德国的法律教育与检察官职业教育对于客观义务的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良好的职业素养与追求公正的职业准则要求将有助于抑制矛盾心理,指导检察官正确理解控诉职能的全部内涵与司法制度所追求的整体目标。
就第二种质疑论据而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有的制度设计、检察官生存环境的设置使得检察官确实与案件“胜诉”具有了一定的利害关系。尽管我们在理论上一直在强调检察官不是被害人的代理人,检察官与案件结局并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检察官不应涉及是否胜诉的问题,但是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又经常处于案件利害关系之中。比如如果检察官公诉的案件最终的结果不断出现无罪判决,检察官的声誉、职位升迁、福利待遇等方面恐怕难逃不利影响,在我国即使是最终的结果是检察官撤诉作不起诉处理,检察官在业绩考核中也会得到否定的评价。检察官过于关注客观义务,不断地考虑无罪证据、辩护证据势必影响检察官案件处理效率,办案数量也会相应降低,同样也会影响检察官的考核业绩。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抗辩制审判方式下,检察官的胜诉欲望大大增强,这就愈发加剧了检察官履行客观义务的难度。
笔者认为,上述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与生存环境的合理性是值得反思的,检察官属于司法程序公正运行的重要支撑角色,相应地应当享有依专业知识、遵职业准则公正处理案件的独立性保障,业绩考核制度与生存环境不能仅仅强调办案量、胜诉率,而无视案件的结果是否体现了司法的公正。如果说检察官与案件处理真的存在什么利害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利害关系只能是准确的定罪与程序的公正。尽管从目前的业绩考核制度与生存环境来看检察官作出如下举措是可欲的,但恐怕并不是一个健康、良好的司法制度所追求的:检察官发现了无罪证据,却不予收集,留给处于羁押状态中的被追诉者自己收集;庭审情况明显显示案件将会得到无罪判决的结果,检察官仍然主张有罪或者撤回起诉;明显是错误的判决,检察官却不作出抗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