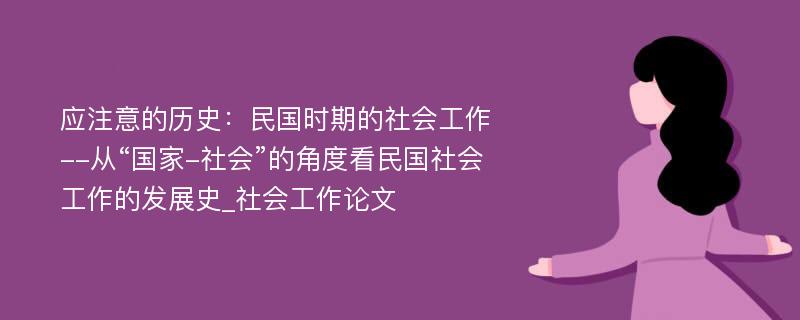
应该留意的历史: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国家-社会”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发展史论文,民国论文,视野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2)10-0004-03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2.10.001
用“国家-社会”的权力关系框架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肇始于西方的汉学界。而在杨念群(2011:22)看来,这种以“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为核心概念的研究工具的普及,大致受两种因素影响:一是1989年波及全球的社会主义危机所导致的理论话语的变迁,一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的影响。自萧邦齐(R.Keith Schoppa)的研究开始,孔飞力(Philip Kuhn)、兰金(Mary B.Rankin)和罗威廉(Wiliam T.Rowe)的研究逐渐系统化。尽管其适用性存在争议,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但对于中国近代的政权更迭和政治社会的变迁,这一框架的解释力目前来看是最突出的。在这一框架的话语体系中,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史实际上是那个阶段“改造传统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力量”(邓正来、景跃进,2011:2)的社会运动中极微小的一个缩影。
一、“国家”与“社会”的此消彼长
在邓正来和景跃进(2011:3)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困境在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运用以及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或者说,要避免因政治危机而引起的社会失序或动乱,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政府权威因其不具有外部社会制约或因社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回归”。其实这就注定了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类似于西方某些政治和社会结构上所主张和宣称的要呈现出一种“对抗关系”,而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化也取决于不同社团、群体和组织共同建立具有对彼此都具有约束力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共识。”(杨念群,2011:34)实际上,笔者认为,自洋务运动开始到民国政府的成立,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和开明乡绅的批判以及诸种社会运动,实际上都在寻求一种和政府的一致性,都在积极致力于推动国家权力的让步和社会的改良。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实际造成的是具有本土和时代双重特色的局面:一是来自外部的“亡国灭种”的殖民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的整合,掩盖和压制了那些可能的对抗因素;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都存在着实现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双方在权力格局的此消彼长中尝试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引入国家治理中。但总体来看,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必然是逐步放松和让渡国家权力,培育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在这二者之间实现一种均衡。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整体上的制度变迁,为社会工作引入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已经拓展到社会调查、社会救助、社会风气改良、社区教育等领域,在实际上开拓了社会工作实务的雏形。与此同时,这些新的社会慈善和救助方式也激发和孵化了当时本土的一些社会组织进行有益的尝试,并且开始影响“官办”的福利机构。
二、“夹缝生存”到合法性获得
民国初期的“国家”权力的衰落是和政权初建以及战乱频频密切相关的,但是在孙中山为首的新兴民族资本主义新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对民主的呼声和政治精英要求参与治理的意愿表达已经成为潮流和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的制度资源成为拿来治疗和改良“国家”和“社会”的“良方”。在这一阶段初期,社会工作的教会背景曾经遭遇了一些阻力,比如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始终存在的排外情绪;但留学归来的知识精英和日益崛起的商业精英以及地方乡绅对变革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已经逐渐加强,改良社会和救济灾民的客观需求同时存在。因此,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两大使命的思考成为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前提。但总体上来讲,当时的战争和政权更迭占据了主流,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尽管可以造成事实的权力衰弱,但同时缺乏对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有力支持,也使得社会工作的发展乏力。这一阶段的社会工作方法基本上还是限制在教会组织及其孵化的社会赈灾和救济组织中;传统的同乡会和慈善堂仍然沿用着救济资助的模式。
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发展体现在知识体系的系统引入方面。以燕京大学为代表,1920年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创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在1925年又将该系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并于1926年成立研究院,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紧随其后,其他教会学校如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等也纷纷开设该专业。至此,国内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体制在高校层面进入正轨。由于是系统引入西方的社会工作教育体制,当时的专业人才培养无论是在理论教学还是实习实践上都已经接近完善,并且在课程设置上还进行了本土化的探讨和安排。这些无论是在当时的教材还是一些专业文章的讨论中都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与此相同步,社会工作的学术研究也在步济时的推动下逐步展开,成为当时社会学界研究的一个分支。
但殊为遗憾的是,这一阶段总体上社会工作无论是实务还是理论,都没有产生与同时代西方发达社会工作角色地位相匹配的影响。诚如王思斌(2012)教授所言:“从1925年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后到40年代末,社会工作的成果并不丰厚。”至少在三个领域,当时的社会工作是处在“夹缝”和“从属地位”的:第一个领域,在教会组织的慈善和福利事业中,具有专业特征的“个案工作”实际上很少被采用,关于风气改良和社会救助的工作,更多采取的是社区发展的模式,而这种综合了救济、赈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的模式更多是和乡村建设结合在一起的,一般不要求工作人员的专业资质和专业技术,因此并没有与专业和职业相联系,只有少数类似于“步济时”这样具备专业背景的知识精英介入。因此,社会工作在这一阶段的教会活动中并非作为主要的理念和专业技术推进的。第二个领域是国内本土的社会组织,多以民主政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为主题,即便是从事社会改良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以社区教育和生计服务为主,从属于广义范围的“社会工作”或者“社区发展”,还是缺乏较为专业的介入。第三个领域是国内的高等教育领域,虽然在燕京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沪江大学等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但言心哲(1944:241)曾指出,“以往对于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人才的训练,则未尝注意,以往国内各大学之社会学系中虽偶有关于社会事业课程的开设,而科目甚少,期望甚短,又因师资与教材缺乏,成效亦未显著。”许仕廉(1929)也曾经在其《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步骤和方法》一文中谈到,“社会事业界缺乏人才,譬如北平社会局成立时,缺乏专门人才,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时时刻刻要我帮他们位置相当人物,担任重要责任。其他公私社会事业机关,莫不有同样的困难。”造成这种现象固然有社会工作教育起步较晚,缺乏系统、规模的人才培养机制的因素,同时也和整体上的职业化专业程度不足,形不成人才培养和就业市场的对接机制有关系。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纳入政府社会行政系统之前,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地位已经在逐渐确立。同样是在其《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步骤和方法》一文中,许仕廉(1929)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工作与社会事业(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包括三部:(一)心理建设;(二)社会建设;(三)实业建设。我们虽不必论那三本书的内容,总之心理与社会建设是中山‘建国方略’的两大部分。社会学的应用方面,就包括心理和社会建设两部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工作,或者他口中的社会事业,正属于社会学的应用分支。许仕廉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精英中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也即“国家”治理重在“心理与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所需要的理念、方法以及技术恰恰是社会工作专业所能提供的。这种提法就在“国家”和“社会”中搭建了一种可以“承上启下”的工作路径,也即“国家”和“社会”实际上可以在作为治国方略的“社会建设”方面经由“社会工作”的知识和技术中介达到统一和协调。
三、“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系统化尝试
许仕廉只是在学理和逻辑上有了将社会工作与社会建设相结合的提法,真正将这种提法串联和嫁接起来的是后继的《社会建设》杂志,以及围绕这一杂志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发刊词中,该刊物已经明确了将统合社会学和社会技术专家,研究社会建设的学理和实践,并且着重强调了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对于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当时活跃在该刊物的知识精英包括孙本文、李安宅、朱亦松、言心哲、李剑华等老一辈的社会工作专家。该刊物1944年发刊,一直围绕着社会事业和社会行政对社会建设的作用机制进行学理和实践探索,刊发了大量的专业研究,实际上成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建设的一个对话平台。更值得关注的是,彭秀良在其研究中曾指出,当时以社会工作为主题的刊物实际上还有一个,那就是同在1944年创刊的《社会工作通讯》。彭秀良认为,该刊“以阐扬本党社会政策,诠释社政法令,研究社工方法,检讨社工绩效,报道社工消息,汇集社工资料,并为社工人员解释疑难辅导进修为主旨”(该刊发刊词),设有专论、工作报告、法令文献、统计资料、社工消息和图书述评等栏目。这是近代中国最早以“社会工作”命名的刊物,意味着社会工作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标志,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彭秀良,2012)。该刊物于1948年5月并入《社会建设》,至此《社会建设》杂志不仅成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统和的综合期刊,同时成为被官方认可的学者与政府对话的一个平台,其专业合法性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同时,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工作讨论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形成了一个中间地带,带有了一定的“公共领域”性质。
同时,从这一刊物刊发的文献以及社会工作通讯报道部分来看,有两个典型的证据表明社会工作已经被纳入“国家治理”的宏观框架中:一是专业资质在“社会部”的社会行政法规及其工作流程中被强调。比如1948年《社会建设》第一卷第四期刊登了《社会部南京伤残重建院组织规程》中的“第三条”的“第五组”明确规定:(在职人员)必须“掌理个案调查、就业指导、职业介绍及预防并心理测验精神病社会工作等事项。”同时更进一步的是,1945年第十七期社会部公报发布“考试院”公告《特种考试社会工作人员考试规则》,将社会工作资格认证分成“甲级社会工作人员”和“乙级社会工作人员”两种。第二是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强化控制,比如直接下设政府办社会福利机构和组织民间社会团体的登记处注册。尽管由于解放战争的影响,没能看到“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后果,但是参照西方国家的模式,社会组织被纳入国家治理,实际上可能产生类似“法团主义”或者“多元主义”两种后果,都可能造成社会工作及其组织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得到系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