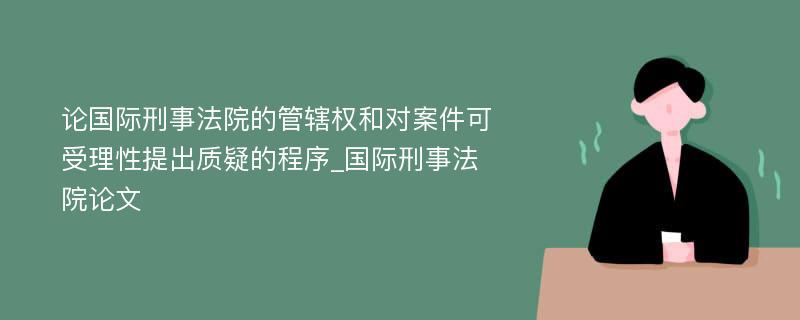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案件可受理性质疑程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辖权论文,案件论文,法院论文,理性论文,程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约》)第19条是关于质疑法院管辖权和案件可受理性程序的主要条款之一。它规定了有权进行质疑的当事方、质疑的内容以及质疑的时间限制,明确了由法庭的什么机构对质疑做出裁决,还规定了质疑对法院行为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经受理了一些国家提交的情势,但是第19条始终没有机会得到适用。2005年3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将苏丹达尔富尔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1593号决议为第19条的适用提供了机会。本文将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和案件可受理性的质疑程序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加以讨论。
一 国际刑事法院的补充性原则
《罗马规约》前言第10段和第1条明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只是对国内管辖权起补充作用。所谓“补充作用”,是指在国际刑事法院与国内法院具有并行管辖权时,承认国内法院有优先管辖权,其实质意义是只有当国家不愿意或确实不能够进行调查或起诉时,国际刑事法院才能受理案件。补充性原则是《罗马规约》的核心,也是质疑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和案件可受理性的基础。
然而,补充性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不得受理案件:(1)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正在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或起诉;(2)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已经对该案件进行调查,且该国已决定不对有关人员进行起诉;(3)相关嫌疑人已经因作为控告理由的行为受到了审判;(4)案件缺乏足够的严重程度,法院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充分理由。①由此可见,国际刑事法院受理案件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于一国“不能够”或“不愿意”进行调查与起诉。
《罗马规约》第17条第3款明确规定了判断一国“不能够”进行调查和起诉的标准。根据该款,“不能够”的情况多指那些较为客观的情况;而对于一国“不愿意”进行调查或起诉的判断标准,《规约》第17条第2款规定如下:(1)该国所进行的诉讼程序或做出的决定是为了包庇犯罪人,使其免于对在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2)诉讼程序发生不当延误,而根据实际情况,这种延误不符合将有关人员绳之以法的目的。但《罗马规约》中对何谓不当延误并未加以界定,需要由法院自己来决定。(3)已经或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没有以独立或公正的方式进行,而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的方式不符合将有关人员绳之以法的目的。可见,在程序法方面,《罗马规约》要求所有相关国家,包括非缔约国,遵守其所规定的人权标准与程序,包括无罪推定,不溯及既往,一事不再理,被告人的公开审判权、选择律师权、免费得到法律救助权、知情权、质讯证人权、沉默权,被告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和反驳责任等。②该款提出的“不愿意”概念更多的是从主观方面来衡量一国适用程序的目的和意图。换言之,国际刑事法院在判定一国是否“不愿意”时,主要是对一国在适用法律程序背后的主观动机做出裁定,亦即国际刑事法院将对一国是否具有管辖和起诉被《罗马规约》禁止的国际罪行的政治意愿做出判断。
补充性原则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监督和督促缔约国切实履行《罗马规约》的规定。补充性原则运用“胡萝卜加大棒”机制来实现其监督功能:只要各国建立并实行的法律体系能够对《罗马规约》所禁止的严重罪行进行有效调查和起诉,缔约国的主权就不会受到影响,国际刑事法院也不会进行任何干涉;与此同时,国际刑事法院可以随时运用手中的“大棒”,接管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够”进行有效调查和起诉的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案件。正如《罗马规约》序言第5段所指出的,补充性原则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犯有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最严重罪行的人不再逍遥法外,防止出现有罪不罚的现象。③
由于通过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情势而启动法院管辖权的这种方式并未对补充性原则和受理性问题产生任何特别影响,因此补充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仍可适用。
二 有权提出质疑的当事方
《罗马规约》第19条第2款规定了有权对法院的管辖权或可受理性提出质疑(即具有出诉权)的当事方。
(一)可以向法庭提出质疑的个人
《罗马规约》没有对“被告人”一词加以明确界定。犯罪嫌疑人是在确认指控以后才成为被告人的,这点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称“前南国际刑庭”)及其他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的做法相同。④但是,在发出逮捕证和确认指控的程序上,国际刑事法院与前南国际刑庭有所不同:后者确认起诉书与发出逮捕证是同时进行,而前者是分开进行的。根据《罗马规约》第58条,在调查开始以后的任何时候,检察官都可以向预审分庭提交申请书,要求预审分庭对犯罪嫌疑人发出逮捕证,而确认指控的程序则是在犯罪嫌疑人到庭以后才进行的。因此,并非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可以质疑法院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而是只有法庭对其发出逮捕证或出庭传票的嫌疑人才具有这种权利。
(二)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国家以正在或已经调查或起诉该案件为由提出质疑
国家可以质疑法院管辖权这一做法是国际刑法的新发展,也是法院补充性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规约》的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国际刑事法院对主权的尊重,是对国家结束有罪不罚现象进行的努力的补充;只有在确认国家的这种努力不切实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才行使管辖权。在这个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同前南国际刑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不同:后两者的管辖权优先于国家管辖权,只有被告人有权质疑法庭管辖权,而国家没有此种权利。
在此《罗马规约》未对一国是否为缔约国做出任何规定,因此可以认为,在质疑法院管辖权和案件可受理性方面,非缔约国同缔约国具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当然也可以说,非缔约国根本就不受《罗马规约》的约束,只是在向法院提出质疑时,在质疑程序方面与缔约国享有同等权利。
但无论是缔约国还是非缔约国,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以及“正在或已经调查或起诉该案件”。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对有关案件具有管辖权,但没有开始调查或起诉程序,那么也不能提出质疑。有些对案件没有管辖权的国家为了阻止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和起诉程序,在法院程序开始之前就启动了本国的调查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该国需要额外证明其管辖权,其中包括要有专家证据来证明其国内法或国内决定有对该案件实施管辖的法律基础。
(三)根据《罗马规约》第12条需要令其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国家
这是《罗马规约》第19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负责《罗马规约》第19条磋商的协调员对该项的解释是:第3项的目的是要为该项所确认的国家提供“明确”的质疑“权利”,尤其是考虑到那些对调查和起诉其国民或在其领土内的犯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⑤对该条款的解释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哪些国家是根据《罗马规约》第12条需要其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国家;第二,这些国家是否要在接受法院管辖权之后才能提出质疑。
关于第一个问题,从《罗马规约》第12条第3款的内容和立法史看,该款涵盖的国家首先是非缔约国,因为只有非缔约国才需要以向书记官长提交声明的方式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但是,这里所指的非缔约国并不是所有非缔约国,而是仅指第12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即犯罪发生地国和犯罪人国籍国,而排除了受害人国籍国、犯罪人拘留地国和具有普遍管辖权的非缔约国等。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第19条第2款第3项和第2项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第二,既然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犯罪发生地国和犯罪人国籍国,而这在第2项中均已包括,那么第3项的规定看起来就有多余和重复之嫌。
实际上,第3项与第2项的区别在于:第2项规定“具有管辖权”且“正在或已经调查或起诉该案件”的国家可以提出质疑,而该第3项没有规定后一个条件。根据第3项,作为犯罪人国籍国或犯罪发生地国的非缔约国,虽然没有“正在或已经调查或起诉该案件”,也可以依据第17条规定中的理由或其他理由向法院提出质疑。⑥例如,在第三国对一犯罪人国籍国的国民进行起诉或调查,而犯罪人国籍国愿意让该第三国而非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情况下,它就可以根据第3项对案件可受理性提出质疑。
此外,在犯罪发生地国对该罪行放弃或让渡了其管辖权,因而不能依据第2项的规定提出质疑时,也可以根据第3项的规定对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提出质疑。例如,派遣国与接受国签署了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向对方领土派遣部队的驻军地位协定,规定派遣国对其国民在接受国境内的犯罪享有排他管辖权;在此情况下,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对派遣国军队成员在接受国领土内的犯罪进行调查或起诉,作为犯罪发生地国和双边协定一方,接受国可以该协定为由对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提出质疑。
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可以这样理解:从字面上看,第19条第2款第3项并未明确要求非缔约国“先接受管辖权再质疑管辖权”,而只是表述为“需要令其接受本法院管辖权的国家”。其次,在安理会依据《罗马规约》第13条第2款向检察官提交情势时,该情势所涉及的国家根本无需接受法院管辖权即可依据第19条对法院管辖权和案件可受理性提出质疑。如果这类国家依据第12条第3款主动接受了法院管辖权,⑦其目是让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该情势或案件,而不是质疑法院的管辖权。如果其接受了法院的管辖权再进行质疑,只会自相矛盾。因此,这些依据第12条需要令其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国家的质疑权利,与其是否已经接受管辖没有直接关系。
三 提出质疑的时间、程序与内容
(一)提出质疑的时间
1.在提交“情势”的情况下
在缔约国提交一项情势或是在检察官自行决定开始对一项情势进行调查时,该情势所涉及的有关国家应依据《罗马规约》第18条第2款,在收到检察官通报的1个月内提出质疑。但是,该提交情势的缔约国不能对检察官的这个决定提出质疑。例如,如果缔约国甲将涉及缔约国乙的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缔约国甲不能提出质疑,而情势所涉及的缔约国乙可以提出质疑。如果一个缔约国将本国情势提交法院,那么它也不能提出质疑。在安理会提交情势后,如果检察官做出开始调查的决定,那么除安理会不能对此决定进行质疑外,对安理会提交情势所涉及的国家依然有权提出质疑。
2.在提交“案件”的情况下
第19条第2款规定的当事各方可以依照第19条规定的程序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质疑。在第19条第2款第1项有关个人质疑的规定中,暗含着对质疑起始时间的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必须是法院对其发出逮捕证以后;而对于被告人而言,则是在其被告人身份被确定以后,亦即预审分庭根据第61条确认了对其的指控以后。
对于国家而言,没有任何关于质疑起始时间的明示或暗示规定,并且第19条第5款规定“第2款第2项和第3项所述国家应尽早提出质疑”。因此,一旦一国得知检察官依据第18条开始调查涉及该国的犯罪时,即可向法院提出关于管辖权和案件可受理性的质疑。不过,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的质疑,都必须在第19条第4款规定的时限之内提出;如果超出了该时限,则必须经法院同意,而且“只可以根据第17条第1款第3项提出”。
(二)质疑程序和内容
根据第19条提出关于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的质疑涉及一系列规定,其中《程序和证据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58条是关于《罗马规约》第19条诉讼程序的专门规定,此外还有《规则》第51条、第59-62条和第122-123条,《法院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38条第1款第3项、第2款第2项以及第112条等。
《规则》第58条第1款规定:“根据第19条提出的请求应书面提出,并附具其根据。”《条例》第38条第1款第3项规定,依据《罗马规约》第19条第2款对可受理性和法院管辖权提出的质疑文件,除非分庭另有命令,否则其页数不得超过100页。
在确认指控以前提出的质疑应提交预审分庭(《罗马规约》第19条第6款),在确认指控期间提出的质疑也是由预审分庭做出裁定(《规则》第122条第2款)。根据《罗马规约》第19条第6款,在确认指控以后提出的质疑,应提交审判分庭;在院长会议依据《规则》第61条第11款组成或指定审判分庭之前,质疑应根据《规则》第60条提交院长会议,在审判分庭组成或指定之后再由院长会议立即将质疑移送审判分庭。对于在审判开始时,或在其后经法院许可,就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提出的质疑,则依据《规则》第133条由该审判分庭加以裁断。
1.通知
首先,根据《规则》第58条第3款,法院应将收到的质疑请求书或申请书转发检察官以及《罗马规约》第19条第2款提到的已被移交法院的人,或者自愿或被传唤到庭的人,以便他们能够在分庭规定的期限内对请求或申请提出书面意见。
其次,根据《条例》第112条,在就可受理性质疑做出任何决定以前,分庭应听取原先移交该人的国家的意见。因此,分庭还应将质疑的情况转告该移交国。
最后,第19条第3款规定,根据第13条提交情势的各方和受害人均可向法院提出意见。为此目的,《规则》第59条第1款规定,书记官长应将根据第19条提出的质疑申请书告知上述提交情势的各方和已就案件同法院进行联系的受害人或其法律代理人;从此时起,受害人正式参与到法院的诉讼程序中来。由于赔偿问题,受害人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同意由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某一案件,而是有可能加以反对。但是,这种反对的立场并不能称为质疑;由于受害人没有出诉权,因此他们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而且只有在质疑被提出以后才能发表意见。换言之,尽管受害人可以参与法院关于管辖权或可受理性的程序,但其是否可以启动质疑程序这一问题还有待法院实践来回答。
2.听证会
《规则》第58条第2款规定,分庭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各方对质疑请求的意见。分庭可以依据《规则》第58条第3款和第59条第3款,要求收到质疑材料的各方在规定期限内对质疑请求或申请提出书面意见。听证会或提交书面意见的程序依照分庭根据《规则》第58条第2款所决定的程序进行;换言之,分庭在决定此种程序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此外,第58条第2款还规定,如果不会造成不当迟延,分庭可以在确认程序或审判程序中一并审理被提出的质疑或问题,但在这种情况下分庭应先行审理并裁定该质疑或问题。为此,《规则》对在确认指控之前或期间提出管辖权或可受理性质疑的问题做出了相应规定。例如,如果质疑在确认指控之前提交,预审分庭依据《规则》第121条第7款有权推迟确认指控的听证会;如果在确认指控听证会期间提交,分庭可依据《规则》第122条第2款在确认程序中一并审理。同样,在审判阶段,如果质疑在审判开始时,或在其后经分庭许可后提出,分庭可依据《规则》第133条在审判程序中一并审理质疑问题。
3.举证责任
关于依据第19条进行质疑的举证责任问题,《罗马规约》、《规则》和《条例》均未加以规定。一般来说,在法院的法律文件中没有提及的问题,应根据第21条第1款第2项,“适用可予适用的条约及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由于质疑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和可受理性并不涉及案件实质问题,即被告是否有罪的问题,因此质疑程序应被视为“审判中的审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中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⑧据此,依据第19条对法院管辖权或可受理性提出质疑的个人或国家必须举证证明该案件或情势不在法院管辖范围之内,或者根据第17条证明其对于法院的不可受理性。如果检察官提出反驳意见,认为案件或情势可受理时,则必须举证证明第17条的规定不适用于该国家或个人。
如果一国向法院提出关于管辖权或可受理性的质疑,那么该国首先应举证证明其愿意和能够管辖所涉案件的理由;如果检察官提出异议,则检察官应举证证明该国为什么“不愿意”和“不能够”进行调查或起诉。
质疑法院的管辖权必定涉及法院在一项情势或案件上的裁判权力,这些权力就是《罗马规约》中涉及法院管辖权的内容,亦即第5条(属物管辖权,即对罪行的管辖权)、第11条(属时管辖权)、第12条(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即基于犯罪发生地国和犯罪人国籍国的管辖权、第26条(属人管辖权,即对不满18岁人不具有管辖权)和第124条(过渡条款)等。因此,相关方可以依据上述条款在质疑书中提出,不存在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第5条);或者所涉罪行发生在《罗马规约》生效(2002年7月1日)之前,或者虽然发生在《罗马规约》生效之后但是发生在《罗马规约》对相关国家生效之前(第11条);或者犯罪发生在非缔约国境内或者由非缔约国国民实施(第12条和124条);或者在实施犯罪时犯罪人尚不满18岁(第26条);或者被指控的对象不是自然人,而是一个团体或整个国家等。
四 法院对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认定
(一)法院对情势或案件管辖权做出认定的义务和权力
1.在提交“情势”的情况下
根据《罗马规约》第18条,法院对所提交情势的管辖权做出裁定有以下两种情况:
(1)在检察官根据《罗马规约》第15条第1款自行决定开始调查并根据第15条第3款请求预审分庭授权调查的情况下,预审分庭应依据该条第4款对检察官提出的有关情势做出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的决定。
(2)在国家和安理会依据第13条第1、2款提交情势的情况下,《罗马规约》中没有规定法院是否应对管辖权问题做出决定,而是将这个责任分派给了检察官。根据《罗马规约》第53条第1款第1-3项,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开始进行调查时应考虑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
在国家和安理会提交情势的情况下,检察官依照《罗马规约》第53条第1款第1项承担了一种准司法机构的责任,因此检察官必须在做出调查决定之前考虑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只有在当事方直接向法院提出管辖权或可受理性问题时,法院才有责任或义务在提交情势之后、提交案件之前,对该问题正式且逐一做出全面的回答和认定。当然,在院长将情势分配给预审分庭时,或者在检察官依据第56条要求预审分庭采取措施时,法院的决定中也会涉及管辖权问题,但通常只是简单地肯定法院根据《罗马规约》享有管辖权而已。
2.在提交“案件”的情况下
根据第19条第1款,法院应对其收到的任何案件做出是否具有管辖权的裁定。法院在收到检察官要求发布逮捕证或出庭传票的申请后,应在其对该申请做出的决定中说明该案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因此,在法院做出对某案件具有管辖权的决定之前或之后,所涉国家(可以在决定做出之前或后)和个人(在决定之后)有权对法院的管辖权或案件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
3.法院拥有裁定其管辖权的权力
法院除了有义务确认其管辖权以外,也有权力确认其自身的管辖权。法院自己对其管辖权做出决定的权力是其职权中所固有的一种权力,也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原则。国际法院在“诺特博姆案(列支敦士登诉危地马拉)”的判决中指出,这是一种“在仲裁事项中被一般国际法所接受”的权力,而且“当这个国际法庭不再是一个仲裁庭……而是一个先前就已经根据国际条约成立且由该国际条约确定了管辖权并规定了职能的机构时,这种权力就拥有了特别的力量。”⑨《罗马规约》虽然没有明确国际刑事法院的这项权力,但其第119条第1款规定:“关于本法院司法职能的任何争端,均由本法院的决定解决。”
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其他国际法庭也都认为它们具有裁定其管辖权的职权。《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6款明确规定:“关于法院有无管辖权之争端,由法院裁决之。”《欧洲人权法院规约》第32条第2款也作了相同的规定。在国际法院判例的基础上,前南国际刑庭也认为它对那些对其管辖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申辩书有做出裁定的权力。在“塔迪奇案”的有关管辖权的上诉决定中,前南国际刑庭认为“对自身能力做出决定的能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或“固有的”管辖权,这种管辖权“是从行使司法职能中自动产生出来的”,“是司法职能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没有必要明确规定在这些司法或仲裁法庭的基本文献中”。⑩
(二)法院对可受理性的认定
第19条第1款第2句规定:“本法院可以依照第17条,自行断定案件的可受理性。”将之同该款第1句(“本法院应确定对收到的任何案件具有管辖权”)进行比较可见,法院对管辖权和对案件可受理性的认定程序是有区别的。法院对情势和案件管辖权的认定是义务性的,无论有关当事方是否对法院管辖权提出质疑,法院都应在适当时候对此做出说明;相反,法院对案件可受理性的认定不是义务性的,亦即《罗马规约》没有规定法院必须对案件的可受理性做出决定,但若当事方向法院直接提出该问题,则法院有义务做出明确说明。
从字面上看,法院对可受理性的确认只与提交的具体“案件”有关,因为第17条的内容仅涉及“案件”;由此排除了法院对一项“情势”做出可受理性决定的可能性。有论者认为,应当对下列情况加以区别:在一国或个人提出可受理性质疑时,法院做出可受理性判定的对象是具体的“案件”;而当检察官为了确定是否有合理根据开始一项调查的情况下,检察官可以决定作为整体的一项情势是否可以受理。因此,当事方只能依据第18条对法院提出对情势可受理性的质疑,而不是第19条。(11)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虽然《罗马规约》第17条和第19条中没有提及法院可对一项“情势”做出不可受理的决定,但《罗马规约》也没有条款明确禁止当事方向法院提出关于某项情势的可受理性的质疑。其次,《罗马规约》中“案件”一词自始至终用语混乱,而在罗马大会时又没有来得及对第15、18、19和第53条中的“案件”一词进行调整。(12)最后,还必须考虑到补充性原则的适用。因此,笔者认为,当事方完全可以不局限于仅对“案件”提出可受理性质疑,而是可以同时对“情势”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
此外,正如法院有权决定自己的管辖权一样,法院也有权对自己是否可受理某个案件做出决定。因此,法院可以在其认为必要或恰当的时候主动对案件的可受理性做出说明或决定。
(三)法院对管辖权和可受理性所做认定的内容
1.法院对其管辖权做出认定的内容
从实体法角度看,“管辖权”可以被界定为“法院判案或发布命令的权力”。(13)“管辖权”一词在拉丁文中的原意是由法院阐明法律。因此,《罗马规约》第19条第1款要求法院应确认“对所收到的任何案件”具有阐明法律的权力。《罗马规约》对法院管辖权的范围和内容做出了规定。根据这些条款,法院必须确认以下几点:
(1)属物管辖权:法院必须确定该情势或事件是否涉及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等《罗马规约》中明确禁止的犯罪,以及罪行是否是“最严重的”国际犯罪。
(2)属时管辖权:《罗马规约》不溯及既往,因此法院必须确定相关情势或案件所涉及罪行是否发生在2002年7月1日《罗马规约》生效之后,并且是否发生在《罗马规约》对所涉国家生效之后;对于在此以前发生的案件,法院没有管辖权,除非相关国家根据《罗马规约》第12条第3款提交了声明(《罗马规约》第11条第2款)。
(3)属地管辖权:法院必须确定所涉犯罪是否发生在缔约国境内或者是由一缔约国国民实施,而不考虑犯罪后果影响地国、受害人国籍国和犯罪人拘留地国的情况。
(4)属人管辖权:法院必须确定被控告的对象是否是自然人,以及犯罪人在实施被控告的犯罪时是否已年满18岁。
(5)“一事不再理”:法院必须确定所涉罪行是否已由其他法院审理过。
(6)过渡条款:法院必须确定其属人管辖权或属地管辖权是否受到第124条过渡条款的影响,因为根据该条款,一国在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时可以声明,在《罗马规约》对该国生效后7年内,如果其国民被指控实施一项犯罪,或者有人被指控在其境内实施一项犯罪,该国不接受法院对战争罪(第8条)的管辖权。
此外,在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情势的情况下,法庭还必须确认在该情势中是否发生了法院所管辖的罪行。
2.法院对案件可受理性做出认定的内容
管辖权是指法院的抽象权力,可受理性认定则是指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过程中所行使的权力。根据《罗马规约》第19条第1款,法院可以依据第17条判断其是否可以对某一特定“案件”行使管辖权。第17条是法院决定可受理性的标准,也是对“补充性原则”最核心内容的概括。本文第一部分已对第17条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五 质疑程序的法律后果
根据第19条第7款,当国家提出质疑时,(14)在分庭依照第17条做出决定之前,检察官应暂停调查。根据该款上下文的意思,暂停调查的范围只限于被国家提出可受理性质疑的那个案件,而在没有被提出质疑的其他案件,检察官继续进行调查不受影响。
在暂停期间,检察官可以依据第19条第8款请求法院授权:(1)采取第18条第6款所规定的必要调查步骤(即如果出现取得很重要证据的独特机会,或者出现证据日后极可能无法获得的情况,检察官可以请预审分庭作为例外,授权采取调查步骤,以保全这种证据);(2)录取证人的陈述或证言,或完成在质疑提出前已经开始的证据收集和审查工作;(3)与有关各国合作,防止已被检察官根据第58条请求对其发出逮捕证的人潜逃。
有关当事方可以对预审分庭或审判分庭做出的关于管辖权或可受理性的决定提出上诉。根据《罗马规约》第82条第3款,上诉本身并无中止效力,除非上诉分庭应要求根据《程序和证据规则》做出这种决定。换言之,预审分庭和审判分庭所做出的关于管辖权或可受理性的决定将对暂停调查产生影响,即决定出台之日就是“暂停调查”的状态结束之时,除非上诉方在提出上诉时要求上诉分庭做出维持暂停调查状态的命令。
如果预审分庭或审判分庭做出的决定是法院不能受理某个案件,那么检察官不得再插手此案,除非检察官根据第19条第10款要求审查并获成功。如果检察官对不受理决定提出上诉,并得到上诉分庭维持暂停调查状态的命令,那么检察官还可继续案件工作。
如果预审分庭或审判分庭的决定是法院可以受理此案,则检察官可以重新开始对此案的调查,除非当事方对此决定提出上诉,并且上诉分庭也应上诉方的请求做出了维持暂停调查状态的命令。在此种状况下,检察官不能重新开始调查,因为此时尚无有效的决定可以结束暂停调查的状态。
六 结论
虽然国际刑事法院的质疑程序尚未有过实践,但了解其内容和程序,对于情势或案件被提交的当事各方,特别是那些非缔约国及其当事人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质疑程序,在法庭上表明各自的观点和主张。质疑程序的设立是为了实现补充性原则的目的,即在保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和起诉、结束国际社会中“有罪不罚”现象的同时,实现公平与公正原则,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及其所属国家的司法主权与利益。
注释:
①参见《罗马规约》第17条第4款。
②参见《罗马规约》第20、21、22、24、33、55、59、66、67及第85条,并参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10及第14条。
③《罗马规约》序言第5段。
④参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程序与证据规则》第47条第7款,IT/32/Rev.41(2008年2月28日公布)。
⑤Holmes,J.T.,"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in Royce Lee ed.,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The Making of the Rome Statute,Issues,Negotiations,Result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p.67 (1999).
⑥Holmes,J.T.,"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in Royce Lee ed.,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The Making of the Rome Statute,Issues,Negotiations,Results,p.67 (1999).
⑦例如,2003年10月1日科特迪瓦就依据第12条第3款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了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参见http://www.icc-cpi.int/NR/rdonlyres/74EEE201-0FED-4481-95D4-C8071087102C/279844/ICDEENG.pdf,最后访问于2009年1月19日。
⑧Kazazi,M.,Burden of Proof and Related Issues:A Study on Evidence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The Hague:Kluwer,p.l17 (1996).
⑨Nottebohm Case (Liechtenstein v.Guatemala),Merits,Judgement,21 March 1953,[1953] ICJ Rep.7,119.
⑩Prosecutor v.Dusko Tadic,Decision on the Defence Motion for Interlocutory Appeal on Jurisdiction,Case No.IT-94-1-AR72,App.Ch.,2 October 1995,paras.14,18-19,20.
(11)参见Olasolo,H.,"The Triggering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Procedural Treat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and the Role of the Office of the Prosecutor",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Review,pp.121,133-135(2005)。在该作者看来,《罗马规约》规定了两个连续但不同的程序:一个是“启动程序”,用于启动法院“休眠状态下的管辖权”,并决定对一项具体“情势”在属物、属地和属时方面的管辖权;另一个是“刑事程序”,从检察官开始一项调查起算,用于决定在该“情势”中的某个具体“案件”的相关个人的刑事责任。在这样的程序规划中,以第18条为根据,提供了在“启动程序”中质疑一项“情势”可受理性的机会,而第19条则只提供了对与一个具体“案件”有关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提出质疑的可能性。换言之,第19条仅在检察官开始对某人进行调查或者申请发布逮捕证或出庭传票后才能适用。
(12)例如,第15条第4款和第53条第1款第2项中均使用了“案件”一词,但从上下文中可以看出,这些地方的“案件”实际上都是指“情势”。
(13)Boot,M.,Nullum Crimen sine Lege and the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Genocide,Crimes against Humanity,War crimes),Antwerp:Intersentia,p.68,para.62 (2002).
(14)在个人提出质疑的情况下,程序的进行不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