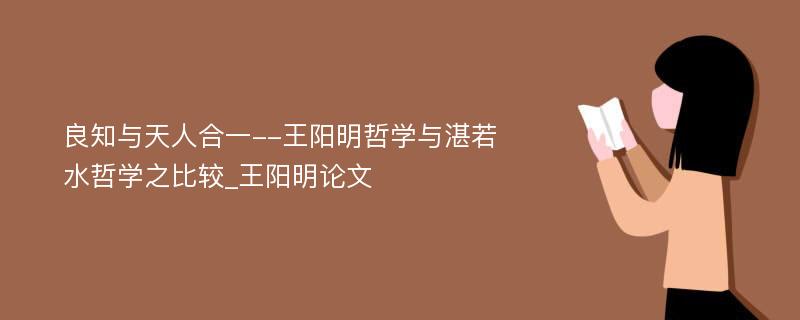
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王阳明与湛若水哲学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认论文,天理论文,良知论文,哲学论文,湛若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的心学运动,有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与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领导的江门学派并行於世。王阳明与湛若水学问之旨趣大体相同,都标榜一种自得自成之学,认为心即是理,涵养体认的工夫唯在心上做,从而都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心学”。但是,这只是基本立场的一致,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仍存在许多不容不辩的区别。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湛若水传》中,简略而又精要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不同:“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对“天理”与“良知”之理解问题,可以说是湛、王论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两人学说的其他方面之区别,几乎均可由此而展开来。
一
自从程明道“体贴”出“天理”二字以来,对“天理”的讨论就成为宋明诸儒所绕不过去基本问题之一,而宋明儒学复兴之见称於“理学”者,盖由此而得名焉。“天理”一词,在宋明诸师看来,似应有不须辩析之公义,无论是在程朱还是在陆王那里,天理都具有本体的意味,既是天地造化流行的本体,又是人伦日用的道德根据。然而,在实际上,诸儒对“天理”之理解又略有异趣,甚至大相径庭,从而导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聚讼不已。因此,如果我们要对宋明理学进行深入探讨,则不可不辩析“天理”一词在不同人物、不同的学派那里所具有的不同旨趣。
湛若水自成学以来,即好谈天理,青年时代即有“随处体认天理”之说而备受他的老师陈白沙之称赞。阳明在大阐良知教以前,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其为学之方,故对湛、王二人来说,“天理”一词都是他们学问中极为重要概念之一。从总体上而言,甘泉与阳明在对“天理”之理解是颇为一致的,即他们一致同意“天理”非程朱末流所持的那种外在於人心之定理,反之,天理维系於人之一心。更进一步地说,两人都共同地把天理看成人心之本体。甘泉说:“所寂所感不同,皆不离於吾心中正之本体。本体即实全也,天理也”(《明儒学案·甘泉学案》)。阳明亦言,“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启问道通书》,《传习录》中)。天理既是人心之本体,自然它不可求之於外,故甘泉认为“天理者,吾心本体之中正也”(《甘泉文集》卷三《雍语》),阳明则以为“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传习录》上)。从实质上说,这两种表述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王阳明所谓的“无私欲之蔽”,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理解成甘泉所说之“中正”(《传习录》下:“天理亦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因此,就本体上而言,湛、王二人对天理之理解非但没有根本性上之差别,而且显得异常之一致,这实际上也正是构成了二人共同的心学立场。较之而言,在二程那里,虽也是将“天理”看成本体,但他们所强调的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而在朱熹那里,甚至有一个在人伦日用之外的“洁净空阔”的“理世界”,其共同的特色则在於离心而说理,从而难以解决作为道德本体之天理与道德实践之主体的关系。就这个意义上说,湛甘泉、王阳明对天理的理解,即心即理,则不存在在主体之外去寻求天理,从而难以解决主体与本体之关系的问题,这也正是心学进於理学之处。
尽管如此,两人对天理之理解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对阳明来说,心外无理,天理完全是就心上说。而在甘泉那里,“天理”这一表述所含蕴的范围显然要更大一些。一方面,甘泉同阳明一致,承认天理是心之本体,不离心说天理,但是他似乎又认为仅仅是从心之本体上说天理,则不足以明天理之体用一源。因此,他继承了二程、龟山、延平一系的“理一分殊”之说,认为除了一本之理外,还存在着分殊之理,即是他所说的“理一之中自有分殊,不能不别也”(《甘泉文集》卷七《答陈惟浚》)。而所谓的分殊之理,在甘泉看来,乃是就“事”而言“理”,即“可见未应事时只一理,及应事时才万殊”(《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故明“理一分殊”乃“学问下手用功处”(《甘泉文集》卷七《与杨士德》)。正是在明“理一分殊”的意义上,甘泉宣说“随处体认天理”。就甘泉之心学立场上说,随处体认天理之意乃在於随已发随未发,随动随静地去认吾心中正之本体(《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因此,在这里,“一本之理”与“万殊之理”乃“二者同体”,从而甘泉强调,“心与事应,然后天理见焉。天理非在外也,特因事之来,随感而应耳。故事物之来,体之者心也,心得中正,则天理矣”(同上)。然而,仅就此说,我们似有理由取消掉甘泉所说意义上的“分殊之理”。因为就此意义上说,分殊的之理依然是就心之本体上说,只是以应事时的心体之状态来界定分殊之理,天理依然只是一个天理,故实质上这仍然在说“理一”。尽管从宋儒那里,就有“理一”与“分殊”乃不即不离,不一不异之关系的说法,但是,从心学的立场来看,天理既是本心之中正,那么无论心之已发抑是未发,只要常守此心体之中正,何莫非天理流行?又何必在一理之外说分殊之理?在王阳明看来,是完全有理由这样取消掉宋儒之理一分殊说的。就应事来说,阳明以“致良知”取代“理一分殊”:“致吾心之良知天理於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这里阳明不是说事事物物之理,而仅仅是说事事物物得其理,得吾良知之天理,这依然不离心而说理。对於甘泉来说,理一分殊从体用一源的角度看,显然包含了阳明所说的含义在内。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甘泉在某种程度上承袭了宋儒尤其是程朱对“理一分殊”之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则认为“分殊之理”应包含“事事物物”之理在内,我们可以看甘泉之所说的:“吾儒学要有用,自综理家务至於兵农钱谷水利马政之类,无一不是性分内事,皆有至理,处处皆是格物工夫,以此涵养,成就他日用世,凿凿可行”(《甘泉文集》卷六《大科训规》)。显然,无论甘泉如何说“水利马政”是“性分内事”,但其在这里是就事说理却是一目了然的,水利马政等的“理”同本体之“理”是有区别的,勿宁说前者已经是在知识论的含义上说“理”了,这亦可以看出甘泉对理的理解上仍承袭了朱子的知识论取向。
对此,阳明则持有显然不同的看法:“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本体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白,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圣人於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传习录》下)。在这里,阳明区分得很清楚,一方面是“所当知”的,即本体意义上之天理,另一方面是“不必尽知”的,即名物度数之“知”,为学之方向,只是要去知那个本体之天理,至於名物度数,或如甘泉所说之“综理家务至於兵农钱谷水利马政”等等,则不消尽知,待到需要知时去问人,本身也是天理节文之体现。这也就是说,只有在本体的层面上,我们说天理才是有意义的,至於具体的就事而言,则只能划入一般知识的领域,它不涉及到我们的身心性命之修养,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说,它并不属於道学家们所关注的主题。这就象德国哲学家康德为知识划界一样,阳明在这里也为“天理”划定了一个“界限”,以便使作为本体之“天理”不至於于无关道德修养的名物度数之“知”相混杂。较之而言,湛甘泉一方面在天理问题上持心学立场,另一方面又折衷於宋儒尤其是朱子後学的旧说,概念的使用上未免有不清之处,这也就难怪王阳明为什么依然要批评他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为求之於外了。
从上面意义而言,阳明是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在其居江右以後,大阐良知教,以良知说天理,大大地把其自身学问推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引起了湛、王之间新的一场辩论。
二
良知之说,最早溯及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朱熹在注《孟子章句》时,虽然也认为良知人所固有,但是语焉不详,并没有对之引起高度的重视,而阳明则第一次将“良知”提到了人心本体的高度,认为“良知者,心之本体”(《传习录》中答陆元静);又说,“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甚至进而阳明认为良知能够与天地同流,“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传习录》下)。把良知升及本体的高度之後,阳明认为,在工夫论上,“致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的“致良知”法门,是千古圣学之秘,儒家的“正法眼藏”,从而将其早期的“存天理,去人欲”之说自然地消融於“致良知”之中了。
对於阳明的良知与致良知之说,甘泉则颇有异议。在甘泉的语录、书信与杂著等之中,亦多有论及良知,但其中大多是针对王阳明及王门後学所发出的批评。作为儒家学者来说,孟子的良知良能说,是其性善论的理论基础之一,自是不容否认,这对於甘泉来说,也不例外(注:甘泉说:“良知二字,自孟子发之,岂不欲学者言之?”(《甘泉学案》,《明儒学案》卷三七))。同时,甘泉说“良知”曰:“良知者何,天理是也。到见得天理,乃是良知”(《甘泉文集》卷八《新泉问辩录》),进而他又指出,“良知”之关键在於“良”,“无所安排之谓良,不由於人之谓天,故知之良者天理也”。从这里可以看出,甘泉认为,良知必须以天理来规定,同时,知之良者也就是天理,天理与良知互训,这其实也就是从本体上阐说良知与天理的意义,同阳明之说原无二致。真正令甘泉怀疑者,乃是阳明“致良知”的教法。在湛甘泉看来,这种教法在实际操作起来,其後果往往是:“但学者往往徒以为言,又言得别了,皆说心知是非皆良知,知得是便行到底,如此是致。恐师心自用,还须学问思辨行,乃为善教”(《甘泉文集》卷十七《赠掌教钱之姑苏序》)。甘泉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正如王阳明自己所强调的,未发之中非常人俱有(《传习录》上),那么常人如何才能在应事之时发而皆中节?甘泉常喜用孔子“大杖逃,小杖受”的教导来说明应事之时与天理相应之难(注:甘泉《答阳明论格物》说:“昔曾参芸瓜,误断其根,父建大杖击之,死而复苏。曾子以为无所逃於父为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间,天人判焉。”(《甘泉学案》,《明儒学案》卷三七))。就常人而言,难免会以自己的一己之知觉误为良知而师心自用,则往往认贼为父,而离天理益远矣。尤其是对於一些王门後学,甘泉特别指出:“今谓常知常觉,灵灵明明为良知,大坏阳明公之教”(《甘泉文集》卷七《答邹东廓司成》)。历史的事实也印证了甘泉的这一担心,王学末流最後流於空疏,甚至发展为一些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注:黄宗羲说:“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泰州学案》序,《明儒学案》卷三二)),这一结果,恐怕王阳明在大阐良知教之时也是始料未及的。
对於甘泉的批评,阳明自己其实也有同样的担心:“某於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做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传习录拾遗》)。“玩弄光景”与“师心自用”并没有什么区别,但这在王阳明看来,不应是“致良知”应有的内涵。阳明之“致良知”,非如其後学所谓的“良知现成”,而由此现成之良知,解缆放船,顺风张棹,自然发而皆中节,此乃龙溪、泰州之论。龙溪、泰州之学,立说固然高明,然用功太捷,并非可以为一般根器的人立教,且有堕入释氏禅悟之嫌。当然,王阳明也有在本体上宣说良知,认为良知即天理而与天地同流,对於圣人而言,自是无所不知,知此良知天理之全体大用,从而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距。这是阳明在存在的意义上为上根之人说法,一旦悟得本体明白,自可超入圣域,从而以为良知是“天植灵根”(《传习录》下),能够“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同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所揭示的良知“积极”的功能,这种“积极”的功能亦是陆象山、陈白沙等人所强调的,也许正是从这一角度看,王阳明继承了陆象山的学问。而龙溪、泰州则更是发挥了阳明良知学说中的这一层面的含义将之推致到极端化。但问题是,良知这种积极的功能,“非是容易见得到”,阳明自己则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岂能如龙溪、泰州辈所以为的那样现现成成?在王阳明看来,要实现良知的这种积极的功能,则要么是具有所谓的圣人之根器,要么就须笃实用功,从工夫中去发明自己的良知本体,否则,这种貌似高明的说法,即有玩弄光景之嫌疑。是以王阳明虽有不少从积极的功能为说良知的话头,但却不以之立教。在他看来,就一般人而言,他的良知总有晦蔽之时,但同时良知也会时有发现,因此,要保此“时有发现”的良知不失,就必须有“致”的工夫。所以阳明说他的教法乃“就学者本心日用间为事,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这意味着,“致良知”的教法,乃是要学者有一渐进用功的过程。在王阳明的晚期作品《大学问》中,其对於“致良知”有着详尽的阐述,我们当可视之为阳明对其这一教法之定论。在他看来,良知自是知善知恶,此善恶乃是就意念上说。良知既知意念之善恶为善恶,倘不能诚有以好恶之,则是自昧其良知,故此好恶之情乃对致良知之关键所在。然有此好恶之情,“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有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意犹为未诚也”(《王阳明全集》卷二六)。因此,所谓的“致良知”,在王阳明那里,并不要待於本体已经明白之後再将之推致开来,其所强调的不是去“致”良知的积极功能,而只是在於自诚其意,由好善恶恶而为善去恶,通过格其非心而致力於将之落实在日用人伦的道德践履之中。这也就是说,在教法上而言,“致良知”只不过是要求学者以自己的良知为是非之准则来审查自己的每一意念,看它是否符合於天理本体,这里实际上体现了良知在阳明工夫理论中的一种审查、批判的“消极”功能,与其说它要求积极地去成就善,勿宁就它更强调消极地去抑制恶。这样一种“消极”的功能,其批判的对象虽然只是意念与动机,而正是这一念之微,善恶判然,涵养的工夫全系於此。
对於湛若水来说,其对於王阳明良知说的批评,如前所述,则集中於两方面,一则以为其有“师心自用”之嫌,二则认为徒致良知,恐难收“位育”之功。但是其所提出的第一个批评,显然是忽视了良知在道德生活中的去恶成善的功能,而过於强调其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的功能,对於圣贤来说是有效的,而对於一般大众而言,的确有持之过高之蔽。由前述可知,阳明的良知学说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则在“积极”的意义上诠良知之“真”;二则在“消极”的意义上立良知之“教”。其说“致良知”时所说的“良知”不同於作为本体上的“良知”,“致良知”根本上说只是一种教法,是一种工夫的法门,其完全是在消极去恶的意义上说的,这样多少可以避免“师心自用”。就甘泉的第二个批评来说,则似乎更切中要害一些,仅仅致良知,能否尽天下万物之理?仅仅考虑“致中”而不考虑能否收到“致和”的效果,则自然是背离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尽管甘泉提出的这一批评有其对“天理”理解的含混之处,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道德两难境地,如何才能无过无不及地予以解决,比如甘泉屡屡提及的“大杖小杖”例子?就这些问题而言,甘泉认为徒致良知是不够的,而必须“随处体认天理”,着实有学问思辨行的工夫。对於甘泉的这些诘难,阳明认为,“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工夫不重效验,仁者以万物为一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全体得仁,则天下皆归於吾”,就此阳明举例说,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只要自己不怨天不尤人,则家邦亦无怨於我,“但所重不在此”(《传习录》下)。从而,在阳明看来,诸如甘泉所提出的“大杖小杖”之类的例子,只要体得廓然大公的良知本体,心中不留一毫私欲,那么,在那样的场合下该逃还是该受,良知自然就会有一评判的标准。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於致良知足不足以尽天下之理,而是学者们是否能“实加体认之功而真有以见夫良知者”(《王阳明全集》卷六《与马子莘》)。这即意味着必须去下笃实的工夫,由工夫之大方可见得本心之明。因此,问题并不在於能否“致和”“位育”,而在於能否养得未发之中,在王阳明看来,即便是“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传习录》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这里并不是在严格意义上回答甘泉的问题,甘泉的问题与阳明的答案是在两个层面上说。甘泉所提出的,依然是建立在其对一本之理与分殊之理的基础之上,多少含有认为致良知不足以能掌握治国平天下的技能之意,故要随处体认天理,需要学问思辨行。甘泉这种看法,本身亦没有什么问题,诸如“水利马政”之类的问题,当然需要学习,而且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亦离不开此类技能的学习。对此,阳明也不否认,然而,这不是“所当知”的,而只是“不必尽知”的,事实上,在知了“所当知”的前提之下,阳明并不废学问思辨行以扩充我们知识技能,所以他说,不知能问,亦是天理的节文所在(《传习录》下)。就此而言,阳明是以完全在化的角度消解了甘泉关於“致和”、“位育”的疑惑。
三
由上分析可知,阳明与甘泉的所异所同,唯在于本体与功夫两个方面。从本体上看,王阳明与湛甘泉所追求的境界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天理即是人心中正之本体,不管他们是主良知之说,亦或是主天理之说,但都不疑问天理即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二者是我们人伦日用间善的根据,并没有什么根据的区别。如果穷本溯源,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可以在北宋周濂溪、程明道那里找以他们精神相契的一面。就工夫上说,王阳明说“致良知”,湛甘泉说“随处体认天理”,都是极端地强调工夫的重要性,无不认为要明天理之本体,都离不开此等笃实渐进的工夫,这也是他们共同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湛两人都迥异於其前辈陆象山与陈白沙,无论是陆象山的“发明本心”还是陈白沙“静养端倪”,实质上都更注重见得本心之明以成就工夫之大,而王、湛二人勿宁说是由工夫之大以成就本心之明,就这点而言,王阳明与湛甘泉都有与朱子相接近的一面。
阳明与甘泉所争者,乃具体工夫下手之处。湛甘泉宣说“随处体认天理”,然而作为本体的天理实难以体认,故其以为只能从理一分殊处入手。虽其认为一本之理与分殊之理可以在“心”中得以统一,但湛甘泉似乎过於强调了行事当然合宜,则在说天理时不知不觉地引进了物理的内涵。因此,“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实际上也有两层含义:一是随处学习人伦日用处“物”之理,一是在学习物理的同时体认天理。但是这两者如何予以统一?在程朱学派那里,实际上已经面临了这一难题。体认天理是一个有关身心性命的道德涵养问题,而学习物理只是一个扩充处界的知识问题,二者之间并无可以沟通的桥梁。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视意、身、心、家、国、天下为体认的对象,并由是而怀疑阳明致良知之工夫偏之於内,虽有格致诚正的努力,却无修齐治平之功。然意、身、心与家、国、天下终非平列之事,下手用功之际,则难免有阳明所讥向外求索之病。而王阳明就工夫下手处,则以致良知立教。而其所谓致良知,唯在正人之一念之微,然而正是这一念之微,就个人的身心性命之涵养来说,天下万事万物无不包罗,故我们亦可称之为“随意体认天理”,它自然地含摄了“随处体认天理”在内。因此,从心学的立场上看,王阳明的学说较之甘泉无疑要彻底得多,也要精微得多,是以王阳明评说两家之异同曰:“凡鄙人所谓致良知之说,与今之所谓体认天理之说,本亦无大相远,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种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达之枝叶者也;体认天理者,是茂其枝叶之生意而求以复之根本者。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达之枝叶矣;欲茂其枝叶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别有生意之可以茂之枝叶之间者乎?”(《王阳明全集》卷六《与毛古庵》)阳明此说,应该是比较公允的。
尽管如此,他们的立场仍然是一致的,虽然两人在学术上相互辩难,但其为学之根本旨趣与精神却是一致的,对本体理解的一致,决定了他们并不以其区别为根本的分歧,而更为强调相互调和的可能性,王阳明曾致书甘泉曰:“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却似有毫厘未协,然亦当殊途同归也。”(《王阳明全集》卷五《答甘泉》)而湛甘泉亦评析“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说,“皆圣贤宗旨也。而人或舍其精义,各滞执於语言,盖失之矣。故甘泉子尝为之语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则同也。”(《甘泉文集》卷三十一《阳明先生王公墓志铭》)这种相互调和的倾向,在湛门后学那里,表现得尤其显著。由於甘泉哲学内在固有的问题,使得其四大弟子吕怀、何迁、唐枢、洪垣皆出入於王、湛两家之间,甚至逐渐消融在王门之中,从而在甘泉没后,江门湛氏一脉遂告式微。
标签:王阳明论文; 王阳明全集论文; 湛若水论文; 传习录论文; 读书论文; 心学论文; 明儒学案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致良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