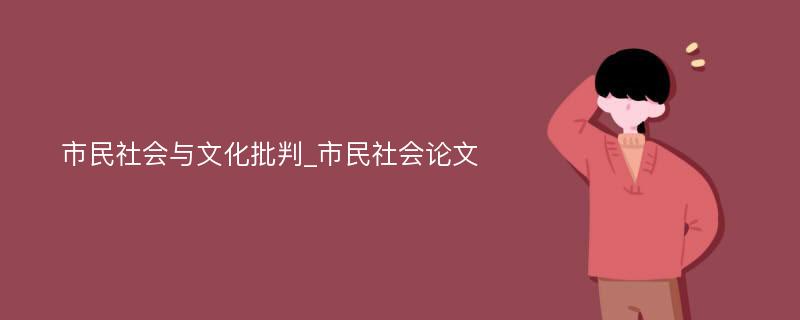
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民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市民社会”是近年来一些人热衷的话题。但是,“市民社会”这个能指的所指本身并不确定。一般而言,它既指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形态;又指指称这种历史形态的概念。但后一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究竟由哪些特征与条件构成,人们也还未完全达到一致。尽管如此,“市民社会”仍不失为一个有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以及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广度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它的兴趣不仅始终不减,而且日渐浓厚的缘故。
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说法,“市民社会”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约在14世纪时为西方人采用,但西塞罗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用它来不仅指单个国家, 也指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态。(1)从古希腊人开始, 城市就是与野蛮相对的标志。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这一传统。因此,西塞罗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首先是要将“城市的文明共同体”与野蛮人的社会和野蛮状态相区别。“市民社会”的文明标志在于:1.它有自己的文化、商业生活;2.它有自己的法律制度;3.它有自己的道德体系。后来西方“市民社会”的概念尽管千差万别,但多少都不能完全脱离上述三个特点来谈问题。
在近代的契约论政治哲学家(如洛克、卢梭和康德)那里,“市民社会”指的是与自然状态或自然社会相对立的政治社会,也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由货币经济、在象自由市场一样的地方随时发生的交换活动、给开化而聪颖的人带来舒适和体面的技术发展,以及尊重法律的政治秩序等要素构成的一臻于完善和日益进步的人类事务的状况。”(2 )契约论政治哲学家的“市民社会”概念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以民权来抗衡专制君权的政治理念,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概念。然而,他们的“市民社会”的合法性仍然是古代的文明—野蛮的区别。市民社会或政治社会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
黑格尔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贡献尤其体现在他将市民社会规定为与国家相分离的独立领域。市民社会是黑格尔国家理论的一个环节。他试图让市民社会成为各种利益和社会力量冲突的场所,而让国家从各种社会与历史力量中抽绎出来,成为普遍利益的体现和代表。因此,区别于家庭和国家,市民社会是经济和经济关系的领域,是“需要的系统”,是法律和司法行政与内务行政管理的领域,是实施立法和强制立法的公共权威的领域。实际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就是现代国家主要的经济、司法和社会制度,这是一整套产生自由的理性设置。因此,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世界的成就”。(3 )与以前的市民社会理论家不同,对黑格尔来说,市民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的现象,它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人所生活的那个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化,因而带有那个时代(现代)主要的理想色彩。象洛克笔下的市民社会一致,它通过司法行政来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象霍布斯的市民社会一样,它使个人免于公权的横暴。它与法国大革命的目标相一致,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领域,但无需恐怖来实现。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4 )这个联合的种种设置都是为了保证自由的充分发展和个人利益与需要的满足。个人权利与自由在社会范围内获致自由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因为它通过一整套理性的设置实现了个人要求得到满足的权利:市民社会使个人可以个别地选择在市民社会中能期望获得的东西;市民社会的设置提供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使个人可以获得可能的东西。与希腊的城邦国家(polis)相比,市民社会使家庭与政治的冲突缩小到最低限度。由于没有市民社会,希腊的城邦国家不承认、接受和鼓励个人的特殊性、主体性和权利;而市民社会刚好相反。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只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法哲学要讨论的归根结底是伦理生活,因此,市民社会只是伦理生活的一个必要的辩证因素。然而,不管它的这种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意义,它仍充分反映了现代性(modernity) 的社会政治理想。
马克思是第一个揭露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神话的人。黑格尔讲的那种“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的市民社会在他看来不过是唯心主义的虚构。任何关于个人的有意义的说法必须同时联系他的环境,个人在概念上也不能与他的社会语境分开。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只看到个人的肉体特征。“他的胡子和血液”,却忽视了个人的社会涵义。市民社会归根到底是物质交往形式。这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5)
与黑格尔从伦理精神的角度来考察市民社会不同,马克思是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市民社会的。虽然他对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唯物主义”的领域与国家的“唯心主义”或“精神主义”相对十分不满,认为人的异化就是生活分裂为这两个领域,但他对现实历史研究得出的是同样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结论。马克思认为,古代城邦国家,无论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的特征都是没有区分社会与政治。因此,市民社会完全从属于国家;没有政治结构把自己与现实的、物质的社会,与人类生活的现实内容相分离和相区别。当政治国家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形式时,res publica (公共事务)意思只是公共生活是个人生活的真实内容。因此,任何私生活缺乏政治地位的人就是奴隶,政治不自由意思就是社会奴役。政治渗透到一切私人领域,社会与国家,私人和公共自我,个人和团体间没有区别。中世纪把这种关系倒了过来:在这里,私人领域,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地位。财产、商业、社会关系和阶层,甚至私人,都成了政治的。马克思说在封建时代财产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只是因为私人财产的分配是一种安排。只有在中世纪政治才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自动反映。在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完全区分开来了。市民社会完全摆脱了政治限制;私生活,包括经济活动,完全不管与国家有关的考虑;一切对财产和经济活动的政治限制都取消了。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表达了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这种两分。人类社会现在完全意识到它的异化和人的生活分为私人和公共两个领域。经济活动本身变为目标既是这种人异化于他存在的普遍内容的证明,又是它的一个条件。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后来的市民社会理论有重大的影响。尽管如此,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有一值得注意的发展,就是人们不再将市民社会看作是政治或经济的领域;而是恰恰相反,主张将市民社会与经济领域区分开来,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由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组成,其功能在于整合社会和抵御危机。葛兰西在著名的《狱中札记》中就指出,在最发达的国家,市民社会已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结构,它能抵御当下经济因素(危机,萧条)的灾难性“入侵”。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象现代阵地战的战壕系统。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攻击似乎摧毁了敌方整个防御系统,但实际上只是外部的环形防线,等到进攻时才会发现敌人的防线仍然有效。市民社会就是在经济危机时起这种作用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6)也就是说,在他看来, 资产阶级国家还只是外壕,市民社会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工事。它通过文化和教育使大众心甘情愿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使现行制度得以建立在大众“同意”的基础上。现代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言之,是由强制的武力保护的文化霸权。(7)显然,在葛兰西看来, 批判的武器一定比武器的批判更为重要。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与葛兰西的政治立场南辕北辙,但在将市民社会视为通过将社会价值制度化来整合社会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帕森斯把现代社会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子系统,把市民社会主要理解为社会子系统(或社会共同体)。社会子系统主要是通过各种社团或协会来完成社会整合的任务。在社团或协会中,通过社会化机制和社团控制机制(如人际制裁和仪式活动等),个人将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行的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接受下来。(8)
美国学者柯亨和阿拉托在他们所著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中也主张市民社会、经济和国家鼎足而三,市民社会自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它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的领域(特别是自愿性社团)、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9 )他们的这一分法显然是从哈贝马斯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一书中将社会进一步区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系统三个子系统来的;他们的“市民社会”概念又相当于哈贝马斯最近十几年讲的“生活世界”的概念。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和人的存在三部分组成,是一个交往行为的公共领域。对于他们来说,“市民社会”已不是一个现实状况的写照,而是一个有待实现或重建的目标,是达到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团结、公正等理想的途径。
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代的演变的确意味深长。这种演变一方面表明当代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产生的种种问题有了足够的认识,使得他们对于现代社会及与其相关的问题越来越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市民社会理论上就是他们不再简单地将市民社会等同于文明和进步。另一方面,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涵义表明人们对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文化既是维系和整合社会,使其价值制度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对抗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无情逻辑,重新找到自我更新的价值和意义的手段。所以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市民社会又被一些人视为有待重建和实现的理想。
二
如果说当代人们逐渐将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社会文化领域,反映了人们对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那么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在当代的迅速崛起,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实践这一事实,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市民社会和文化批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文化”、“批判”和“市民社会”是三个与现代性有着密切关系的概念。虽然“文化”这个词在我们古代文献中也出现过,但那时指与武功相对的文治与教化。现代汉语中“文化”一词的含义显然是从西方的culture一词来的, 而与古代的“文化”一词的含义反而只有间接的关系了。
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cultura,它的词根是colera,意思是“照料,开垦,居住”。因此,culture 一词最早的用法都是同农业活动有关的。通过西塞罗对它借喻的使用它才有了人文的内涵。西塞罗说:“一块农田即使是肥沃的,如不照料的话,也不会结出硕果,精神如没教育的话也是一样……照料精神的是科学;它将恶习连根拔出,使它准备好去接受种子并将其播下——如此说来——一旦它已开始,那就会硕果累累。”(10)在西塞罗那里,“文化”有了通过智慧教养人的意思。但智慧的教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使人的生活高尚和获得人的尊严的途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莫斯和托马斯·莫尔继承了西塞罗的这份遗产,将文化又理解为本性的培养。人必须自己关心他的尊严,通过爱智慧自己从灵魂中将恶习象杂草一样除去。也就是这时,16世纪早期,“文化”一词才逐渐广泛用于人文世界而不是自然界。德国早期启蒙学者普芬道夫干脆将“文化”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将文化与自然状态相对。
维柯对文化理论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与启蒙时代许多思想家不同,维柯认为变化是人类经验的本质特征,变易不仅是人性的特点,而且也标志了人在与世界的关系中不断理解自身的努力,为寻求理解人们不断改变自己和世界。但不断变化的历史世界不是无迹可寻;相反,由于它有一共同的形态,或者说,领会和评价事物的方式,我们也能科学地认识它。这就是文化。任何民族的自我理解最清楚、最典型地表现在它的文化感觉的现实实践,艺术、宗教、道德、法律、语言这些东西中。但这些都需要以适合它们自己时代和地点的观点来进行解释。这样,通过理解文化我们就可以理解变化的历史和变化的人本身。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地不同的存在模式或生活方式。因此,要理解或改变我们和世界,必须先理解和改变文化。文化成了一个历史的生存性概念,具有明显的存在论意义。由于它的这个特点,任何对文化的研究都会带有人类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意欲。
在启蒙时代,人们对文化也象古代人们对市民社会一样,把它看作是野蛮的对立面。在法国的“哲学家”(philosophes)们看来, 与野蛮、原始和蒙昧状态相反,文化不仅构成了已经达到的状态,而且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成员完善自己的标准,这种标准不是被看作是一个进化到这种状态的过程,就是被看作由它代表的种种标准。赫尔德在这种文化概念中看到了近代的傲慢和历史偏见。为此,他用“文明”一词来指维柯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以代替启蒙运动的“文化”概念。赫尔德用“文明”主要指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标准或一个过程。他和维柯一样,将文明看作是多元而不是铁板一块的。他的目的是要瓦解启蒙运动的文化观:文化只代表一个长期的精神成就的最高阶段,而这个阶段正是在18世纪达到的。赫尔德以“文明”来与启蒙运动的“文化”概念相抗衡,与维柯的“文化”概念一样,已经隐含了对现代性的某种批判意味。无独有偶,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也指出,在英国,从柏克开始,“文化”概念就是对工业主义,尤其是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一个回应。(11)
到了浪漫主义者那里,“文化”作为对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的一个批判概念,就显得更为明显与自觉了。赫尔德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浪漫主义者。他们将他的思想用于各个方面:维护民族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攻击现代工业社会的机械与异化;将精神与物质,人与非人相区别等等。“文化”这个术语成了浪漫主义者针对现代社会政治变化产生的种种问题的批判武器。与启蒙价值的代言人常常将“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相反,为了突出文化和上述批判意义,浪漫主义特意要区分文化和文明。在《论教会与国家的构成》中柯勒律治这样写道:“国家的长久存在……国家的进步性和个人自由……依赖于一个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如果不以教养为基础,不与人类特有的品质和能力同步发展,那么文明本身如果不是一种腐败的力量,也是一种混杂的善,是疾病的发热,而不是健康的红润,而一个以这种文明著称的国家,与其说是一个完美的民族,不如称之为虚饰的民族。我们必须是人以便成为公民。”(12)柯勒律治这里讲的“教养”(Cultivation )其实指的就是文化。(13)文化才是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一切社会安排都要服从的上诉法庭。将文化和文明相区别,实际上是要提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惟因这种价值是一种必须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即人的完美发展,它也必然成为批判社会的指南和出发点。
对此,阿诺德有更为明确和自觉的认识:“提倡文化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摆脱目前出现的困境;文化就是追求我们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为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并通过这种知识将源源不断的新鲜自由思想输入我们固定的概念与陈旧习惯……。”(14)“文化即是对完美的研究,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作是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的所有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15)这里,文化不仅是一种理智的活动,一种“研究”,而且也是人们存在的追求。既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行为模式。文化不仅关系到个人,更关系到社会,实际上它是社会的目标。正因为如此,它必然也是批判:“文化成为制度的最终批评者,成为取代和改善的过程,然而在根本上又超乎制度之外。”(16)
随着人类学的发展,出现了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这就是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所做的,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的能力与习惯都以“文化”称之。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从表面上看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概念。然而,它产生的现代性语境决定了它不能不蕴涵着批判的因素。它在本世纪成了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张文化多元论、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等等一系列特殊的文化批评的依据之一。正如威廉斯明白指出的那样:“文化概念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对所谓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念的一种批评。对文化观念的含义作出贡献的人,从差异极大的立场出发,达到了各种差异极大的对文化观念的依附和忠诚。但是他们有个相似之处:他们都不认为社会只是一个中立区,或者只是一部抽象的、具有调节作用的机械。他们强调的是社会的积极功能,强调个人的价值植根于社会,并且强调必须以这些共同的条件来思考与感受。”(17)文化概念自身的历史其实也已暗示了它对于近代社会的根本意义。
“批判”这个概念与“文化”概念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近代的概念。critique一词是从希腊文krinein派生而来。krinein的意思是“区别”和“辨别”的意思,英文中crisis (危机)一词也是从krinein派生而来的。“批判”一词的古典用法主要指三个层面的活动:它可用于司法行政指在法律争论中重建秩序;用于医学指一种病的转折点;还指对文学文本的研究。当“批判”一词在17世纪成为近代欧洲语言一部分时,它还带有上述司法、医学和语文学的背景含义。(18)“批判”一词在17世纪被西方人广泛采用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术语特别适于启蒙。在文艺复兴时,它基本上还只有古典的语法和语文学活动的意义,但在17世纪后期,它在当时全欧洲如火如荼地展开的神学大争论中被广泛采用,使它有了较广的现代意义,因为上述神学大争论正是欧洲“现代化”的一个最极端的症象。
在“批判”的概念史上,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培尔的《历史批判词典》在1697年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从那时起,“理性”和“批判”这两个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批判首先就要区分理性和天启,它被看作是区分这两个方面的理性的活动。批判和理性逐渐被认为是不可分的,是因为理性概念在时间过程中也经历了根本的变化。传统和古典的理性概念的目标是发现和描述第一原理和支配现象的普遍真理,并用“先定理由”来证明它们。这样,合理的东西就是“适宜的”和“正当的”。亚里士多德因此可以将规律等同于“秩序”或“理性”,断言理性是人的最高能力,因为它使他们可以理解宇宙的秩序和继续他们的生活。
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种新的理性出现了。理性不再是联结思维和知性的能力,而是以其无限和透彻的分析揭露了古典传统的理性概念的局限。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概念相比,它与其说是肯定的力量,不如说是否定的力量。培尔就直截了当地写道:“人类理性……是一种破坏的原则,而不是开导的原则。”(19)但这决不是说,寻求真理不再是理性的任务。恰好相反,理性的任务仍然是去寻求真理,但不是先定的真理,而是有待确立的真理。这种意义的寻求才是真正的寻求。理性概念转变的重大关键即在于此。也因此,理性必须将自身视为批判,既然它不再是说明已经存在的既定真理,而是要理解一切可能的事实。康德对于理性在近代的这种演变有最为深刻的认识,他将批判视为时代的特征:“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须受到批判。”(20)更为深刻的是,他不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一切外在的制度,而且也指向进行这种批判本身内在的条件——理性本身。理性既是批判者又是被批判者。任何规范本身必须先接受批判。“在原则尚付阙如之时,冷淡,怀疑,最终严格的批判是缜密思想的证明。”(21)他认为只有能经受自由和公开考察者,理性才能予以诚实的尊敬。这位“批判哲学”的大师关于“批判”的理解揭示了批判的本质:批判不是根据某种现存权威的规范来判断或评价事物,也不只是要得到所谓正确的思想和逻辑确定性,而是要把批判引到批判的条件和前提,弄清在批判过程中发生的事。按照“批判”的原义,它不只是纯粹的反思和判断,而是本身既有理论的因素又有伦理的因素。批判的这种复杂性使它截然不同于单纯的批评。
“批评站在它批评的对象之外,维护规范反对事实,维护理性的命令,反对世界的不合理,批判拒绝站在它的对象之外,而是将其对象内在正常的自我理解与其实际的现实并置。批评给一个阿基米德点以特权,不管它是自由还是理性,进而去表明用这个理想范式去衡量时世界的不自由和不合理。通过给这个阿基米德点以特权,批评成为教条:它不解释自己的立足点,或在进行批评任务前就假定了它的立场有效。”(22)
美国学者塞拉·班哈比卜的这段话清楚地指明了康德以来“批判”概念最重要的特点。正是这种特点使它成为现代思想与文化发展的真正内在动力。
三
以上对“文化”和“批判”概念的系谱学分析已清楚表明,这两个概念在近代的产生和流行决非偶然,实际上它们都是人们对现代性作出的反应。现代性在极大地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他们感受世界的模式。最初人们认为一切新的都是合理的,而所有新的东西虽然对传统的东西以历史必然性的身份出现,但它们自身却似乎具有永久性。然而,一方面,传统不可能完全被颠覆;另一方面,现代性的辩证逻辑却使那些似乎是永久合理的东西的基础很快发生了动摇。当传统和现代都不再能给人以确定的信念和经验的规范时,文化批判就应运而生了。人们希望通过它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这个似乎越来越疏离的世界。人们认识到今天的一切固然是现代的问题,但又肯定与我们自以为了解,其实始终必须去了解的人性有关。于是,文化批判又成为一种知识,一种有别于近代客观知识模式的生存的知识。作为知识活动,它可以称为文化研究,但这种研究必然是一种深刻的批判,所以文化研究归根结底还是文化批判。由于现代性问题的广泛性,这种批判涉及人类一切基本的创制。它包括哲学批判,语言批判、心理批判和社会批判等等。
除了人类心智方面的条件外,还必须注意文化批判兴起的历史语境。市民社会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生存领域的分野和相对独立性日益明显和多样。政治和经济领域在现代的强势作用固然对文化社会形成了极大的压抑和限制,但也促进了它独立的进程。现代一方面使权力和金钱的逻辑越来越广泛地渗入一切文化活动;但另一方面文化第一次有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现代为此准备一切必要的物质条件: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独立的文化机构——大学、研究所、出版社等等,现代的传播流通手段。这一切使得文化对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现代更为文化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种种负面的条件,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如果说人们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社会——文化领域,是想要以此来抗衡权力和金钱的逻辑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并以此来保持人类的理想,那么文化批判正是这个领域活力和作用的体现。
文化批判通过对我们经验和感知的前提条件的反思和批判也许不能改变权力和金钱的逻辑,但却可动摇这种逻辑的基础。我们看到,一方面,权力和金钱对西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和深入;但另一方面,造成西方现代政治和经济逻辑的西方文化正在产生深刻的根本变化。尽管这是一个漫长而又缓慢的过程,但其内在的革命性、激烈性已不容怀疑了。这种变化离开从浪漫主义到尼采、海德格尔,从批判理论到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批评等持续了一个世纪以上的西方文化批判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说市民社会是人的生活在政治、经济方面获得越来越大自由的产物,那么文化批判就是这种自由在精神上的体现。没有文化批判,市民社会最终将失去其独立性,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又一跑马场;反之,也许在权力和金钱之外还可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世界”,一个新的可能性的世界,一个能给予我们希望的世界。
文化批判产生的历史语境也决定了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无法改变它本身内在的道德—批判的特征,哪怕是那些表面看上去最形式主义的、公开声称非存在论的文化批判,概莫能外。例如,后结构主义似乎通过将一切归结为语言和文本,以符号和形式置换以前使文化批判合法的种种假定挖去了文化批判的一切可能性。一切文化形式在后结构主义看来都是多少任意的构造,与它们所指涉的事物很少或没有内在关系。德里达和其他一些人甚至认为文字的文本只是由白纸上的一些黑色标记组成的东西,区别这些标记的不是它们可能有的内在意义,或它们可能传达的意向,而只是它们彼此的差异。德里达称之为differance。这个differance纯粹由标记的大小,它们间的空间,它们黑色的程度和它们的形状组成。这种differance可让我们将随便多少意义附于那些标记,但这些意义无论与它们附于其上的标记还是与它们意指的对象都无内在的关系。标记和符号下面并无作为它们本质的意义或含义,因此,任何特殊文本下面、前面或周围都无积淀下来的其它东西。批评纯粹是一个语义学和符号学的活动,它的运动方向最终是瓦解文本的意义。然而,后结构主义的这种极端的批评策略不仅未使它成为一种文字游戏,反而使它不仅是一种激烈的语言批判,而且也是当代最激烈的文化政治批判之一。福科和拉岗就不用说了,德里达也从不掩饰这一点。相反,针对西方学术界某些人将解构看作又一种新鲜的学(技)术操作或方法,他明确指出:解构
“在其分析工作中,至少也是一种对支配和使我们的实践,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行为可能的政治与制度结构采取某种立场的方式。恰恰是因为它从不只关心所指的内容,解构不应同这个政治——制度问题分开,而应寻求重新研究责任,这种研究对从伦理学和政治那儿接受的符码提出疑问。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太政治了,这将吓瘫那些只凭最熟悉的路标来认识政治的人。解构既不是使这个体制安居其位的方法论的改进,也不是花里胡哨的不负责任和使人不负责任的破坏,这种破坏最确定的结果就是使一切一如其旧,巩固大学里最顽固的势力。”(23)
这样一种激进的文化批判立场居然被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挪用”为对一切文化形式无批判的认同的招牌与工具,恰恰证明了文化批判的匮乏和紧迫。
文化批判的历史语境还告诉我们,与启蒙不同,文化批判既然不是绝对的破坏与否定,也不是独断与盲目的弘扬与肯定。从“文化”和“批判”的系谱学研究中可以看出,它们的产生反映了现代社会自身的调适和纠正机制。文化批判实质上是反思和探寻:反思我们经验的前提与条件,探寻新的可能性。文化批判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我批判。任何不包含自我批判的文化批判必然会成为新的教条。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批判:以一套既定的价值来对事物作出判断和批评。无论批判是多么激烈,这套既定价值本身是被绝对先予肯定的。也就是说,批判者自己的立足点是不受怀疑和批判的。批判者似乎可以站在历史之外,超越他所批判的文化,向人们指出历史发展的正道。中国现代反传统的文化批判,就是一种这样的文化批判。批判者自以为他们可以超越传统来对传统作出终审判决,却不知正是在这样做时他们陷入了传统的吊诡,传统的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仍有效地控制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批判同样如此,同样没有对自己经验和思维的前提与历史语境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批判成了意见的表达与否定,而不是对真理的探求。几乎所有的批判者都认为自己已真理在握,却不知一套先定的价值无论如何其真理性是可疑的。这样,现代中国文化批判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一再重复的意见,却很少开拓的思维与理解的向度。80年代的文化批判低水平地重复五四文化批判的意见,深层原因即在于此。
文化批判的悖论和困境在于:它不能超越自身的文化——历史语境,又必须批判产生它的历史文化条件。这就要求它不仅要批判对象,而且也要时时审视自己的立足点,承认它的局限性,允许它的可变性。还要求它不是给事实以合法性的说明和认同,而是不断地探索新的可能性。没有可能性的世界是一个停滞的、没有希望的世界。可能性既是对事实的批判,又是新的经验的起点。对于前一点杜威有过很好的表述:“对没有实现和可能实现的可能性的感觉,当将它们与现实条件相对照时是可能产生的对后者最透彻的‘批判’。”(24)可能性归根结底是新经验的可能性,批判同时揭示了这种新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文化批判也是一个建设性的事业。它在不断反思和批判现有的文化形式和结构及其前提的同时,也在扩大我们经验与理解的领域;在重新解释我们熟悉的一切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它也在不断重塑自己。只有这样彻底的文化批判才能使我们不至在一个千年一遇的沧桑巨变中失去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才能使人性在巨大的非人力量面前仍然保持它的地位与尊严。
很显然,既然文化批判是要重估一切价值,那么它必然是一种道德批判。提起道德批判,时下有些人总象小偷被人提起偷窃那么不自在,以至“道德拷问”成了一个这些人常用的时髦字眼。其实文化批判着眼于社会性问题,把对个人私德的评判留给每个人的天良。文化批判的任务不是道德审判,而是价值重估。它不是要褒贬某种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而是要检验我们对自由和人性的承诺及其强度。它对人类命运和未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关心,促使它不断为人类寻求新的可能性。当它指出新的可能性时,它是在指出一个“应该”,尽管这种“应该”不一定象康德的“绝对命令”那么强烈,但却同样体现了人类不为自然的因果性和物质的逻辑所囿的自由意愿,这正是道德的本质。正因为如此,美国批评家凯钦把文化批判定义为“historie morale”(道德史), “它总结我们生活的时代精神,然后让我们超越它,使我们能从宏观的角度,即以马克思论希腊哲学,基尔凯郭尔论莫扎特,尼采论悲剧的诞生,肖伯纳论易卜生,劳伦斯论美国文学的方式来看事物,让我们——不仅根据人类的历史,而且根据他的全部努力——去创造一个与我们的创造力相符的未来”。(25)
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能没有这样的文化批判,不管我们将它称为市民社会还是别的什么。
注释:
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中国人民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第125页
2.同上。
3.G.W.F.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P.182
4.ibid.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页
6.Antonic Gramsci,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p.235
7.ibid.P.263
8.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第76—77页
9.Jean L.Cohen & Andrew Arato,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2)P.IX
10.Wilhelm Perpeet,"Zur Wortbedeutung von Kultur",Natur plan und Verfallkritik-Zu Geschichte der Kultur,Herausgegebenvon Helmut Brackert und Fritzwefelmeyer(Frankfurt/M:Suhrkamp,1984),S.21
11.参看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7—98页
12.Samuel Teylor Coleridge,On the Constitution of Church and State,3rd ed.(london:William Pickering,1839),P.46
13.参看《文化与社会》,第97页
14.Ma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Selected Prose,ed.P.J.Keating,(New York:Penguin Books,1970),P.142
15.ibid.P.145
16.《文化与社会》,第176页
17.同上,第406页
18.cf.Paul Connerton,The Traged of Enlightenment:A Essay on the Frankfurt Scho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Ch.1
19.cited in Paul Connerton,The Tragedy of Enlightenment,P .19
20.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in Vernunft,A Xll
21.ibid.
22.Seyla Benhabib,Critique,Norm,and Utopia:A Study of theFoundation of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86),P.32—33
23.Quoted in Jonathan Culler,On Deconstuction(London &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P.156
24.John Dewey,Art as EXperience(New York:Putnam's.1934,1958),P.346
25.Alfred Kazin,Contemporaries(New York:Little,Brown,1962),P.497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政治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代性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