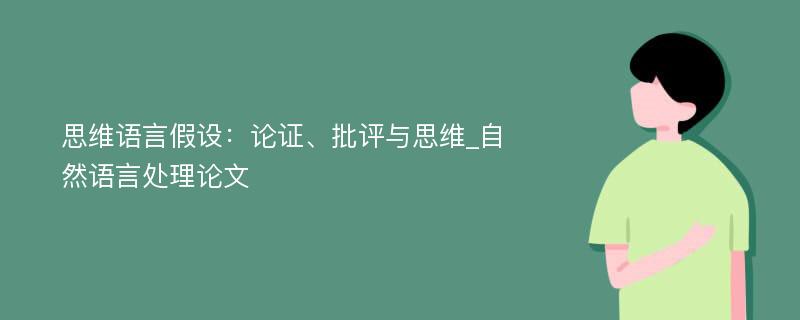
思维语言假说:论证、批评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批评论文,思维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人类心灵认识史上,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历来有这样一种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观点,即人的思维离不开各自所掌握的自然语言,并以之为加工的直接对象和媒介。近20年来,随着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的迅猛发展与长足进步,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心灵尤其是思维的认识向精确化和具体化方向的迈进,上述观点受到了一些西方哲学家的尖锐挑战:具有音或形特征的自然语言怎么可能进入人脑并为之储存、提取和加工呢?有些人还根据计算机的计算以机器语言为媒介作类比推论,大胆地提出了“思维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或者说“心灵语言”(mentalese)、“大脑语言”的假说。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认知心理学家J.福多(Fodor)在1975年出版的《思维语言》一书中最先明确提出上述概念,并在其后许多论著如《表征》(1981年)和《心理语义学》(1987年)等中加以进一步的阐发,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肯定并论证过这一假说的人非常多,其中主要有:H·普特南、W·塞拉斯、W·利康(Lycan)和D·代菲特(Devitt)等。
所谓思维语言就是指人在思维过程中所专用的一种不同于自然语言而近似于计算机的机器语言的、内在的、特殊的符号系统,是储存、载荷信息并可为思维提取出来、直接呈现在思维面前为其加工的语言媒介。从现象上看,或借助于我们的内省和体验,人的思维所用的好象是自然语言的字、词、句。其实不然,自然语言不能直接进入人脑,因而不可能为其理解和加工,它们只有转化或翻译成思维语言才能如此。就像计算机只有将原语言程序翻译成机器语言程序才能对之进行计算一样。依此类推,人在思维中所用的只能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化语言,在思维后说出与写出的自然语言词句则是人脑将思维语言予以转译的结果。福多论证说:表征(representation)以及对表征的推论操作离不开表征的媒介即思维语言,在人类主体和计算机中都是如此;例如计算机所能“理解”并加工的只能是机器语言,基于人类思维与计算机的计算的类似性,可以合理地假定:人的思维由以进行的是一种或更多种的“机器语言”([1],P.277)。普特南说得更简明:思维语言“是一种表示假设的、大脑中的形式化语言的类似物的名称。”([2],P.528)
对于这种语言的组成单元、结构、本质特征和作用,福多等人作了大量而繁琐的论证。这里不妨从两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从思维语言自身的组成单元与结构等方面看,它有如下一些规定性和特征:(1)作为一种语言,它有近似于自然语言的地方,如有特定形式的词汇、记号或标记(tokens)、惯用语或公式(formulas),它们也可按一定的语法规则组成为句子;所不同的是,在它们中,一符号码一个意义,而没有自然语言词语的那种一词多义性和歧义性,就像计算机的机器语言只有一种意义一样。(2)思维语言的词语也有指称力和丰富的表现力,能表示世界上纷繁复杂的现象,其原子部分指称世界上的个别事物与属性。(3)它的语词和句子也有意义。其意义作为整体是由原子部分的语义属性以及产生它们的整个句法结构的语法规则决定的。(4)思维语言的句子有真值条件,相应地,真值条件又是由世界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5)这些句子具有相互依赖和包含的逻辑关系,因而按照表征理论,人类有作为特殊词汇或语汇的物理状态的系统,人类(不知什么原因)在物理上有把那一系列要素结合成系统的规则,而这些系统具有复杂的表征内容。(6)思维语言是天赋的、普遍的,对于操不同自然语言的民族来说是共通的。这正是不同民族语言能相互转译的前提和基础。(7)思维语言可能不止一种,也就是说,每个正常人可能使用一种以上的思维语言,就像计算机有多种机器语言一样。⑧作为思维语言的个别单元的标记乃至整个符号系统都是物理的,或者说是“神经系统的客体”,福多说:思维语言的“符号有意向内容,而符号在各种已知情况下是物理的”,“是有因果作用的那类事物。”([3],pp.282-283)
第二,从思维语言与心理表征、自然语言、内部言语以及思维的关系看,思维语言是一种与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殊的符号系统。
就心理表征是信息、思维内容的储存、提取和加工过程中的呈现方式而言,思维语言就是心理表征。福多经常在此意义上将两者等同使用,他说:“我严肃地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内部表征体系构成了一种(计算)语言。”([4].P.335)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思维语言的组成单元、结构、句子及句法、语义属性等的探讨揭示心理表征的构成与本质。普特南的看法略有不同,认为:思维和心理表征都是以思维语言为媒介的。他说:“心理表征是具有指称定义的形式化语言”,“一当给予一种形式化语言以指称定义,在那种语言中的一组语句就可视之为‘表征系统’或‘世界的模型’。”([2],pp.527-528)这就是说,心理表征由形式化语言和信息内容两部分组成,前者是后者的载体或媒介。因此思维语言是没有指称定义的形式化语言,有别于心理表征。
从思维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关系看,尽管两者都是语言,有类似性,但两者在词汇、句法、起源等方面有明显不同。前者比后者简单明了,没有歧义性,具有更大的准确性,其表征式的意义由某种抽象的程序来表征,在适当的环境下能决定命题的真值和行为的成败;其次,同一思维语言句子可由不同的自然语言句子表达;从起源上说,前者是天赋的,而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从两者与意向性的关系上看,意向性是自然语言句子的语义性的源泉,而对于思维语言来说,情形恰恰相反,即思维语言的语义性是心理状态的意向性的根源(详后)。
从思维语言与内部言语或语言(inner speech)的关系看,在特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思维语言就是一种内部语言。不过由于对内部语言的本质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两者的关系的看法也就有很大的分歧。有的认为:“内部语言”如果指的是一种不同于自然语言的内在形式化语言,那么思维语言就是这种内部语言。如果它指的是一种减去了声音或形象的自然语言或类似于外部言语行为的内隐言语活动,如“喉头肌肉运动”、“内心独白或自言自语”之类,那么思维语言就不能等同于它。福多等人就持此看法。而W·塞拉斯则恰恰相反,他坚持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思维本身就是内部言语活动或默默的自言自语,这种言语活动与外在言语行为、自然语言有“实在的类似性”,或者说是减去了声音与形象的外部言语,而思维语言正是这种内部的语言活动([5],pp.372-379)。
关于思维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福多在《心理语义学》等论著中作了经典的表述。他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直接的、名副其实的媒介。因为思维作为内容是以思维语言为媒介而储存和表征的,思维作为操作、加工活动是对思维语言的提取和处理。他说:“有一种内在的表征系统,一种内在的思维语言,我们正是以之进行我们的思维活动的。”他还具体解释了“我们用这种语言思维”的两层含意:a.与思维有关的心理状态就是有机体与作为标记的心理表征的关系,或者说思维就是有机体处在与一定思维语言句子的一种特定的关系中;b.心理过程(如推理、信念的形成等)是对这种内部语言的符号的一系列计算操作([6],pp.312-313)。
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把思维语言设想得尽善尽美,但是如果客观上没有思维语言或没有可靠的根据说明它的存在,那么关于思维语言的一切论述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思维语言的倡导者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用了许多材料证明思维语言的客观存在性与作用。首先从否定的方面来说,他们认为:通常把自然语言当作思维的媒介是不对的,因为这建立在内省的基础之上,而大量事实已表明,内省本身是不可靠的。同时作为思维器官的大脑是不可能让带有音或形特质的自然语言进入的,也就是说,自然语言的文字或话语、形或音不可能直接地、赤裸裸地、原封不动地进入思维,必须转换成与思维相适应的、特定的符号形式才能为其把握和操作。就像计算机只能“理解”机器语言一样,自然语言要为其加工,必须转换成机器语言。
从肯定的方面,福多等人论证说:由自然语言表达的信念可以分别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由不同的语句表达出来,如“相信‘狗咬了那人’”可换成“相信‘那人被狗咬了’”。为什么同一信念用不同的句子表达仍保持同一的意思呢?这是因为它们根源于并可翻译成同一的思维语言句子。他们还通过对语言学习和亚人思维(sub-personal thought)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认为:语言学习像其他学习一样,一定包含着假说的形成和检验,而假说的形成和检验以假说得以在其中形成和检验的符号系统为前提,即离不开一定的、在前的语言或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正是思维语言。对此有人也许会提出质疑说:这是一个学习“怎样”而不是学习假说的形成的问题。福多回答说:技巧的获得、学习“怎样”与亚人(即假设的存在于人脑之内的似人的部分)的表征系统或在先的语言、符号系统有关。没有这种符号系统即思维语言,就不可能学习“怎样”,不可能有自然语言技巧的获得。其次,动物和婴儿都有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而没有自然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他(它)们的命题或思想的句子构成物就不是自然语言句子,而一定是由思维语言组成的句子。如果不能否认这一点,那么也有同样的理由主张:成人的命题或思想也是直接以思维语言句子表征的。最后,福多论证说:不会讲英语的外国人也可能相信“(Grass is green)”(草是绿的),他们有这样的思想不可能是由于与“(Grass is green)”这一英语句子发生了关系,而一定是与他们自己语言中的某一意思是“草是绿的”句子有关。只有当不同的句子用来表达同一思想时,它们的思想才会是同一的。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说:相信“草是绿的”就在于与自然语言发生了关系,而应认为:操不同自然语言的人之所以能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的信念,就在于信念与思维语言句子有某种关系,即都有共同的思维语言。这也正是不同民族语言可以相互转译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否认思维语言的存在,将不可能合理地解释差别那么大的民族语言为什么能够相互转译。
在思维语言的倡导者们看来,思维语言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是我们全面而科学地解释心理现象的一个条件。这些作用本身也可作为思维语言存在的根据。如前所述,它是思维的直接的、名副其实的媒介,其语义性是心理状态意向性的根源;其次,它还是我们习得、掌握母语的基础,因为思维语言是先天的,因而它便成了习得母语的中介或桥梁。在H·西蒙看来,思维语言实质上就是乔姆斯基所说的深层句法结构,而深层句法结构正是人们习得母语的基础。最后,它为我们说明心理状态的因果作用、解释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大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常用信念、意图之类解释人的行为的发生,而在福多看来,信念之类的心理状态对行为的因果作用取决于心理表征或思维语言的性质,这些性质不用提及头脑之外的事情就可得到描述。因为信念所“关于”(aboutness)的东西编码在内在表征之内,换言之,表征的唯我论性质决定了它们的语义描述。他像S·希夫尔(Schiffer)一样设想:人脑中有一种“意向盒”,其中每一意向就是使某命题P为真的意向。当你打算使之为真时,你所做的就是把意含P的思维语言句子放进“意向盒”中,“意向盒”接着要做的就是“搅拌”、计算、引起,结果就是你如此那般地行动,也就是使P为真。例如我想把左手举起来,就是我打算让“举左手”的命题为真,我所做的就是把意含“举左手”的思维语言句子放进意向盒中,经过适当的计算,我的举左手的行为便发生了。这无疑是对行为发生的原因与过程的一种隐喻式的、形象的说明,但又较好地说明了思维语言在人做决定的意志活动中的作用。
(二)
一般都承认:人的心理状态具有语义属性。尽管一些持排除主义立场的人否认心灵的存在,但仍同意说大脑状态具有语义属性。倡导思维语言的人把这一新的结论阐发得更加具体,即认为思维语言具有语义性。这一来,研究思维语言或心理或大脑状态的语义性的心理语义学(psychosem antics)便应运而生。在许多论者看来,研究思维语言的语义性不仅是思维语言研究不可缺少的环节,亦即是关于思维假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广义的心理表征理论的完整性也是至关重要的;还有,如果不研究和解决心理语义学问题,那么对于思维等认知现象的“进一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新的收获和突破([6],P.315)。
心理语义学的首要主张就是:心理符号或思维语言的词句有语义属性,而有语义属性就是有指称、意义和真值条件,即每一心理符号或语句总是指向它之外的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及属性,有其特定的内容,内容有真值、有真假,而真假取决于它所断定的对象与条件。假如有一与“Snow is white”(雪是白的)相对应的思维语言句子,它的单词有指称,即指的是人之外的雪与白;单词以及由之而组成的思维语言句子有意义,即表达的是雪的属性与主体的某种关系;同时该语句有真值条件,如“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2],PP.528-529)。
心理语义学的第二个基本主张是:思维语言的语义性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可以说明心理状态为什么具有意向性。长期以来,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即认为:意向性是心理现象区别于其他现象的根本属性,从作用上来说,意向性是自然语言句子的语义性的源泉,亦即是说我们说出和写出的语句之所以有指称及意义,根源在于说写时的心理状态具有意向性。福多等人同意后一观点,但不赞成前一看法。因为还有比意向性更为根本的属性,这就是思维语言的语义性。它决定了心理状态的意向性,是意向性的根源或基础。因为思想、信念等心理状态是有机体与思维语言句子的一种关系,如某人想到或相信“天要下雨”,这是一种有意向的心理状态。有此状态实即某人心中有“天要下雨”这样的思维语言句子,处在这种状态中就是处在与特定心理符号的特定关系中。他的思想或信念之所以指向如此这般的意向对象,就在于呈现在他心灵面前的心理符号具有如此这般的语义属性。因此福多说:他的理论的“目的是要用心理符号概念解释、重构心理状态的意向性理论”,在他看来,“心理状态依据心理表征的语义属性而成为有意向性的。”([6],P.315)。
但是思维语言的语义属性的根源或基础又是什么呢?心理语义学的第三方面的内容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思维语言的倡导者们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当提供了严肃的、能说明什么东西把语义属性授予思维语言的理论,那么借助于思维语言的语义性说明意向性才可能算是一种理智的进步,才能有力地回击持否定立场的人的责难与批判。因为在反对把意向性作为心理现象的不可还原的根本特性的那些人看来,把语义属性作为心理符号的不可还原的特性同样是令人费解的,有些人正是由此而走上怀疑论的,即怀疑能为心理符号为什么具有语义性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那么能否效法自然语言语义性的解释方法即求助于心理状态的意向性来说明思维语言的语义性呢?显然不能,W·奎因(Quine)曾严厉地警告过这一点。因为心理语义学要用心理符号的语义性解释心理状态的意向性,因而自然不能再用后者解释前者,如果这样做,就陷入了循环解释。
尽管问题十分棘手,但心理语义学的探索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还是提出了许多尝试性的理论。这里只考察其中较有影响的二种。
(1)福多的目的论功能主义语义学。在《心理语义学》中,福多开宗明义地说:“在本文中,我想做的就是概述对心理表征的语义性的(大略的目的论的)解释。”([6],P.316)这一解释主要包括对下述两个问题的回答:第一,思维语言有什么样的语义属性?第二,这种符号由于什么而有那些语义属性,或者说是什么把心理符号与满足它们的真值条件的事态联系起来的?福多说;”第一个问题是通过提供规范性语义学而予以回答的。我假定:就心理表征而言,它们的语义属性就在于它们具有真值条件。因此一种关于心理表征的规范语义学就采取了真理理论的形式。“([6],P.317)也就是说,心理表征的语义性由真值条件所引起,并映现了作为真值条件的事态,决定心理表征的语义性的唯一的“符号—世界”关系就是它们所具有的、与决定它们真值的事态的关系。到此就进到了第二个问题即是什么把两者关联起来从而使思维语言的语句具有语义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借用了上述“意向盒”假定。假设有思维或有信念的有机体头脑中有一盒子,上面标有“是”(yes)。它能接纳心理表征或思维语言句子。它的内容由下述原则所决定,即对于每一思维语言句子M来说,O(即有机体)具有与M的关系(因而相信M所表达的东西),当且仅当M的一标记出现在意向盒中,也就是说,当某人的某一思维语言句子如“天要下雨”进入该盒中,某人就处在与该句子的关系中,就使该句子与作为其真值条件的事态相关联而具有语义属性,某人就知道了它的语义内容,从而进入了相应的意向状态,如出门拿雨具等。简言之,由于思维语言句子进入了意向盒中,因而也就现实地具有语义属性,进而相关的心理状态也就有了意向性。当然意向盒的活动不是决定哪一标记进入其中的唯一机制,除此之外,大概还有知觉的、记忆的、推理的机制等起作用。他把所有影响意向盒内容的心理机制组成的结构统称为事实性认知系统。然而,这样的认知系统为什么能影响意向盒的内容、从而决定思维语言的语义性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他的目的论功能主义假定。他说:为了对付解释上的难题,“我打算提出一条目的论假定”,这就是:存在着一些心理机制,它们是认知系统的子集,“它们的功能就是把记号放进‘yes—盒”中。”([6],P.322)具体地说,由于事实性认知系统的这样的目的论功能即“……的功能是使……产生或发生”,思维语言或心理表征的记号,才进入了“yes—盒”中,并与作为真值条件的事态相关联,从而具有特定的语义属性和因果作用。总之,心理表征之所以具有语义属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认知系统的目的论功能作用。他说:“我打算做的下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从关于认知系统的目的论的某东西中派生出心理表征的语义性。”([6],P.323)出于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人们必然会问:这里所说的目的论事实是不是最根本的、不可再还原的事实呢?福多认为:还不是,因为目的论事实是根源于达尔文主义所说的“自然选择的事实”。即是说,人类思维语言之所以能与作为真值条件的事态相关而具有语义属性,是因为认知系统的目的论功能作用,而此功能作用又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通过生存竞争、自然选择而获得的。
(2)H·普特南关于思维语言的证实主义语义学(the verificationist semantics)。他像福多一样认为:思维语言的意义、指称等语义属性不是由心理状态决定的,因为“意义不存在于头脑之中,”([2],P.530)事实也说明,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词的意义可能有相同的理解,但不一定处在相同的心理状态之中。其次,“关于表征的媒介即思维语言的大脑语义学”“不是真值条件的”,即不像戴维森(D.Davidson)所说的那样,通过陈述一语句的成真条件,就能给出该句的意义。他强调:思维语言的语义学应是证实主义的。根据他的观点,思维语言的符号或句子有意义和指称,其根源在于“大脑有一种可计算的、能表现可接受性或被证明的可肯定性或可信性的谓词,”质言之,符号或句子的意义在于大脑中的谓词的可证实性,取决于这些谓词从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的方式。只有在从逻辑上说可能有一些观察语句为其提供证明或反证的情况下,它们才在经验上具有意义。他还根据他和克里普克(S·Kripke)所倡导的“因果的历史的”指称理论说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一心或脑单元M即一思维语言的符号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指称一事物X,因为“意义存在于那个词的指称之中”而它能指称X,则正好是由于X“恰当地”出现在M的原因论(etiology)中,即由于M被人用来指称X,然后“经过共同体的实践”,逐渐在M与X之间历史地社会地形成了因果链条,基于这种因果链或原因论,M被固定地用来指称X([2],PP.528-534)。
(三)
思维语言假说无疑提出了一些新颖深刻、发人深省的问题与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思维的研究,同时也为心灵哲学中的一些著名难题如意向性问题提出了不无独创的解决方案。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但是毋庸讳言,由于它主要是基于一些类比和想象的方法而提出的一种假说,或如普特南所说:是科学上有用的、宝贵的隐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因而除了有许多人继续加以论证、充实和完善之外,也有相当多的人提出了各种质疑和批评。
我们先考察齐硕母(R·Chisholm)等人对思维语言假说的内在矛盾的揭露和批判。他们认为:自然语言句子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因而依赖于说话者的信念和意向,而信念和意向是命题态度,因此如果不循环或回归,那么命题态度的内容怎么可能根据思维语言的语义属性而加以阐释呢?其次,当公共语言以几种方式中的一种而约定俗成时,明显不存在关于大脑的工作的约定的或社会的因素,所谓的思维语言的词汇单元的指称必定是自然的。英语中的“狗”一词就是作为音、形单位而不是意义单位在全社会中为说英语的共同体归之于狗的,但思维语言中表示狗的词又是基于什么原因而必定自然地、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与狗有关呢?这被认为是思维语言的倡导者们难以圆满地解释的问题。
杜拉特(D·Dennett)等人更进一步对思维语言作出了否定性的论证。他基于几方面的根据论证说:“头脑中的句子”表现为用大脑粉笔写在大脑黑板上的铭文,这种观点不说是怪诞的,起码是想象出来的。另外,主张有思维语言的观点还必然碰到这样的问题:关于思维语言,除了已有的那些类比说明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总之,在他看来,“关于心理表征的思维语言模型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已成了指数爆炸的牺牲品。”([10],PP.350)。
思维语言假说并不因为这些强而有力的批判和打击而消声匿迹,相反倒是引起了对它的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其倡导者在反击中进一步将其修改、充实、发展和完善;批评与反批评针锋相对、唇枪舌战;原先对此反应冷淡的心灵哲学家、认知心理学家现也纷纷加入到探讨、争论的行列,从而使思维语言真正成为当今心灵哲学、认知心理学中争论的一个焦点。
依笔者看来,思维语言假说的确有不成熟、不完善乃至错误的地方,且缺乏充分、可靠的科学和实验根据,有些观点值得谨慎地对待和冷静地商榷,如它认为思维语言是先天的、普遍的,是习得母语的基础,作为心理状态意向性根源的思维语言的语义性本身是根源于目的论事实、在人的心灵内部有一像“yes-盒”一样起作用的结构等。但又应看到,它对思维以自然语言为媒介这一传统的、常识性观点的否定则是发人深省的,也有其合理性。很显然,自然语言作为一种特定的符号系统,音或形是其固有的特征,而以音或形表现出来的符号如字、词、句表面上能进入人脑为思维接受、理解和加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书面语言的字词句只有经过复杂的能量转化,变成没有形体特性的信号或形式,才能为思维所把握。如首先书写符号以光性刺激的形式屈折地射入网膜感光层,使那里的感受细胞发生化学反应,经过复杂的感光──换能系统的作用,光能变成了神经电信号,中途又经过复杂的能量转换,变成能为中枢视觉皮层接受和整合的能量形式,最后形成一定的神经元连接或构型,储存在记忆中或呈现在思维面前,以声音形式表现出来的字词句也要经过复杂的能量转化、形式变换,才能为思维理解和加工。总之,自然语言不能直接地、原封不动地进入人脑而成为思维的直接对象和媒介。其次,神经科学的有关理论也告诉我们:大脑内并没有形象的表象、图画以及以声音和特定形状表现出来的自然语言的字词句,只有神经元及其各连接方式或构型。从现象上说,我们借助内省和想象的作用想到字词句甚至或画面时,好象有自然语言的字词句,它们好象按比例缩小而出现在思维面前。其实不然,我们内省和想象中所出现的有形象或有声音特性的东西,从客观的观察和实在的存在上来说都是神经元的某种连接或构型,即是思维语言假说所说的物理符号。另外,从逻辑上说,如果坚持思维以自然语言为媒介,必然碰到无穷后退,即如果我们的大脑里有以音形特性表现出来的自然语言的字词句,那就得假定大脑内还有一个“小人”在那里听或看那些字词句,就象肉身的“大人”看纸上的或听别人说的字词句一样,如果有“小人”,那么还得推测“小人”的脑子里有“小人”,如此递进,以致无穷。由上看来,思维中被储存、提取和加工的媒介不是自然语言,而是某种或某些别的呈现方式,不妨把它们称之为思维语言。它们也有字词句,有规则有句法,但在存在形式或表现形态上、在结构和载荷信息的方式上以及在储存、传输、转换的方式上都不同于自然语言,而类似于计算机的“机器语言”。
思维语言假说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观点,如认为思维语言具有物理性,是一种物理符号或者说是大脑中神经元的某种连接方式,这显然坚持了唯物一元论。其次用思维语言的语义性解释哲学和心理学中聚讼纷纭的意向性问题,即使也碰到了一些理论上的困难,但颇有启发性,至少丰富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扩展了我们的视野。最后,思维语言假说的诞生和最近一、二十年来的初步发展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对心灵尤其是思维的认识朝着由肤浅向纵深、由抽象向具体、由模糊笼统向精确化方向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促进和推动了思维研究的方法论变革,不仅是认识发展的必然,而且也为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我们知道,心灵研究由于对象的特殊性,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一直是建立在类比、隐喻的基础之上,如把心灵比作蜡块、白板或白纸、镜子、“电报系统”([11],P.151)等,因而使对心灵包括思维的认识带有较大的肤浅性、抽象性、笼统性和隐喻性。尽管思维语言假说从根本上说是以机器语言为类比基础的,因而仍主要是一种类比推论的产物,但由于计算机是一种模拟人的思维、且在功能上更接近于人脑的实验工具,而且对它的内部结构、工作过程、原理和机制、对机器语言的各有关具体细节、对计算机的计算或“思维”与作为其媒介的机器语言的关系可作出具体、精确的描述和说明,因此以此为类比基础较之以前的认识自然是一种进步。它能帮助我们比较具体、精确地描述和说明人的思维的结构、过程以及由以进行的媒介,较好地说明这种媒介的构成因素、结构和实质以及与思维的关系。如果我们肯定思维有其直接的作用对象,其进行离不开一定的媒介,而自然语言的字词句又不能是这种对象和媒介,那么以计算机为根据,从对思维运作的解释的角度,提出思维语言的假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必然的。当然,也应看到,仅仅着眼于计算机类比,只看到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在认识思维中的作用,而忽视对人的思维过程的客观观察和实验,轻视神经科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作用,尽管可以合理地提出思维语言及其与思维的关系的假说,但不可能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不可能使思维语言模型成为人的思维的现实的、真正的工作模型。有些心灵哲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如P·M·丘奇兰德和P·S·丘奇兰德等已注意到了这点,不过有的在强调神经科学和对大脑的实验、观察的时候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即彻底否认思维语言的存在。笔者认为:对思维语言的进一步研究的较合适的方案就是:把计算机模拟与神经科学的实验观察、把主观内省与客观观察结合起来,在人用“思维语言”思维时,借助脑电图、微电极技术、分子生物学、脑化学的技术与手段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更先进的技术,辅之以认知心理学的实验和观察材料,研究神经元是如何连接的,例如当我们想到某个词时,借助有关的技术揭示神经元是如何连接的。在此基础上,心灵哲学再综合人类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进化论等有关学科的成果,加以高层次的概括、整合和抽象,发展和建构关于思维语言及其与思维的关系、思维语言与自然语言的相互关系的哲学理论。
标签:自然语言处理论文; 自然语言论文; 语义学论文; 系统思维论文; 语义分析论文; 大脑思维论文; 语言学论文; 目的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