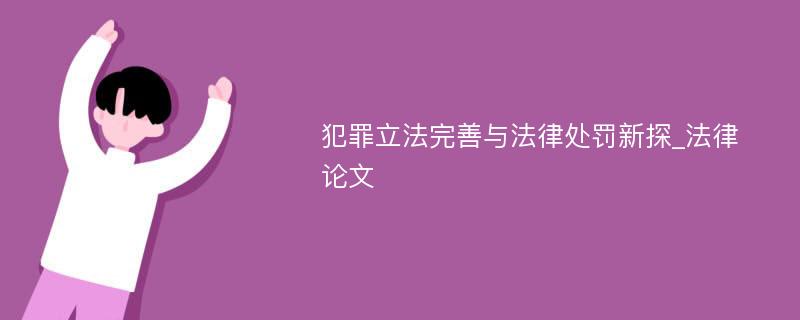
罪状与法定刑的立法完善新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罪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罪状与法定刑是刑法典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定罪量刑的直接依据,因此,其立法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定罪量刑的准确性。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一方面证明我国刑法关于罪状及法定刑立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存在着不足之处。本文试就如何完善我国刑法典罪状与法定刑的立法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罪状及法定刑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罪状立法的不足
所谓罪状,就是对具体犯罪的名称及其构成特征的表述。这种表述是否科学、准确、全面,直接影响定罪的质量、量刑的准确性。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对罪状立法的总体框架和基本表述是较为科学的,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1.有的罪状对犯罪构成特征的表述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基本特征,不利于正确定罪量刑。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的罪状以行为人对他人行为所具有犯罪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作为对其定罪的必要要件,违背刑法的基本理论,给正确适用刑法带来不便。如刑法第172 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构成窝赃罪或销赃罪。这就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所窝藏或代为销售的物品是“犯罪所得”,即要求窝赃、销赃犯对他人取得赃物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性质必须有明确认识。这显然违反我国刑事立法原则和刑法理论,即故意犯罪的构成,不要求犯罪人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只要求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认识。实践中犯罪分子常常以不知道赃物是犯罪所得来逃避法律惩罚,使得司法机关对依法打击窝赃、销赃犯罪感到为难。
第二,有的罪状,把“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以营利为目的”作为构成某种犯罪的必要要件,如盗窃罪、偷税罪、破坏集体生产罪等。但是,未规定此要件的犯罪,不一定就不要求这一要件,也不是说该要件可有可无,如贪污罪、故意伤害罪、受贿罪、非法管制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等。
2.有的罪状违背罪质与罪责的统一,把性质不同、社会危害性相异的犯罪规定在一个条文中,适用同一个法定刑,不能体现刑与罪相适应的原则,并给量刑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不符合现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潮流。如刑法第144条把非法管制罪、非法搜查罪、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规定在一起;第145条把侮辱罪、诽谤罪规定在一起;第151条把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规定在一起等。
3.罪状表述过于简单、笼统,不能全面准确反映犯罪的特征和表现形式,不利于审判机关正确适用刑法。如故意杀人罪、贪污罪,虽为广大公众所了解、熟悉,然而这种了解和认识只停留在朴素的感性认识和一般了解上,并没有上升到理性和法律的高度。因而往往造成认识和适用法律的不统一,导致定性不一和量刑失衡。类似的立法还有刑法第133条过失杀人罪、第144条非法管制罪、非法搜查罪、第154条敲诈勒索罪、第182条虐待罪。又如,关于赃物犯罪,刑法第172条仅规定了窝藏和代为销售两种。但从司法实践来看,还包括转移、收买、收受赃物的行为。但由于法无明文规定,打击此类犯罪于法无据。
4.原则性、概括性太强,不利于审判机关操作。主要表现为对有的犯罪的罪状采取“口袋式”规定方法,对一种犯罪,不分轻重,不加区别地把该罪的可能表现形式规定在一起,然后规定一个从最低到最高的可以自由选择的、比较宽泛的法定刑。如刑法对流氓罪的规定就是如此——刑罚有轻有重,但从罪状中看不出罪行的大小。类似的立法还有玩忽职守罪、投机倒把罪、贪污罪、受贿罪、杀人罪等。
5.过多地使用模糊性、抽象性术语,给实际操作带来一定困难。在刑法分则中,许多罪状都把诸如“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较重”、“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等作为构成某种犯罪或者适用某种刑罚的要件,这可以为审判机关适用法律提供灵活掌握的余地,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个方面,由于刑法本身缺乏使用这些术语的具体条件和限制,再加上这些词语本身没有固定或者特定的内容,在具体适用时又有一定困难。这一术语越多,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造成定性失误和量刑偏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据笔者统计,带有上述模糊性术语的刑法分则条文有64个,占分则有罚则条文的32%,其中是构成犯罪要件的有34个,占模糊性条文的56.2%。
6.有的条文对罪状的立法不利于罪名的确定和刑罚的适用,也不利于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例如刑法第162 条规定窝藏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犯罪分子的构成窝藏罪或者包庇罪,刑法界一致认为该条规定的是两个罪名,两种犯罪。因此它不同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有关选择性罪名的法律适用(如第112、167条等)。那么,既窝藏又作假证明包庇犯罪分子的,如何定罪,是否适用数罪并罚,在审判实践中理解和作法不一致。又如刑法第172条规定窝藏或者代为销售赃物的, 构成窝赃罪或者销赃罪,但既窝藏又代为销售赃物的,如何定罪,是否数罪并罚,认识不统一,类似的立法还有第170、112条等。
(二)法定刑立法的不足
所谓法定刑,就是在刑法分则条文各条罪状之后,根据各具体犯罪的性质、情节规定的刑种和刑度。我国刑法实行的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制度既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又可防止任意裁量。但实践证明这种立法也存在不尽合理之处:
1.刑种失调
刑种的不同,标志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不同。如果对同一种犯罪规定多个刑种或者对多种犯罪规定一个刑种,势必造成社会危害性大小不明、罪行轻重不分、量刑不公的现象,从而导致一罪多刑或者多罪一刑,引起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据笔者统计,我国刑法分则只对56个条文的60种犯罪规定了一个刑种(如第181条破坏军婚罪); 对42个条文的46种犯罪规定了两个刑种(如第184条拐骗儿童罪);对36 个条文的38种犯罪规定了三个刑种(如第183条遗弃罪);对8个条文的8种犯罪规定了4个刑种(如第157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如果说一 种犯罪对应二个、三个刑种是为了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那么对应四个刑种显然是不正常的,且为任意裁量开了绿灯。例如:刑法第166 条对“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这一简单罪状规定了4个刑种(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对相同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行为处以不同刑种刑罚,或者对情节不同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行为处以相同刑种的情况。类似的立法还有第98、99、102、157、158、167条等。
2.刑度失衡
所谓刑度,即量刑幅度。我国刑法在刑度的规定上,除管制、拘役、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在分则中不规定具体的刑度而按总则规定执行外,对有期徒刑,在分则立法中,有的只规定上限,有的只规定下限,有的规定有上、下限。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刑度较大或者太大,从而使审判机关、审判人员在裁判具体案件时,对被告人究竟科以什么刑罚才适当,不易掌握,从而导致量刑上的轻重失衡。例如刑法第141条规定,拐卖人口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即对情节严重的拐卖人口犯罪分子可以在5年至15年内选择刑罚。 量刑偏差可想而知。
据笔者统计,我国刑法量刑跨度为五年、七年、八年、十年的条文有93条之多,占分则中规定了有期徒刑条文总数(共149条)的62%。 量刑跨度较大的法定刑的普遍存在,是影响平衡量刑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人们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对主刑还有个上下限的限制的话,对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除外)则只规定有刑种而没有刑度,这在各国的刑事立法中是少见的,也违背相对法定刑的原则和要求:即刑罚必须有量的规定性。首先,关于罚金,刑法第48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这一规定有三点不妥:一是由于罚金必须由犯罪人交纳,因此判处罚金不仅应根据“犯罪情节”,还应考虑犯罪所得和犯罪人之交付能力等:二是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与刑法第57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不相吻合;三是罚金刑既无起点又无最高限。其次,关于没收财产,刑法第55条规定:“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但对适用没收财产“一部或全部”的条件未作任何具体的说明。再次,关于剥夺政治权利,虽然有期限限制,但由于政治权利的内容多种多样,那么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一部分还是剥夺全部则不明确,也缺乏针对性。
法定刑由刑种和刑度组成,对一种犯罪,刑种越多、刑度越宽,法官选择正确刑种和适当刑度的难度也越大,量刑也就越费斟酌、越困难,因为在众多的刑种和跨度很大的量刑幅度内选用适当的刑种、刑度确非易事,审判人员把握不准或者素质较低时,往往难以避免任意性,甚至给个别审判人员的任意裁量、枉法裁判以可乘之机。同时,造成量刑偏差的机会与可能性也就越大,量刑偏差的程度也越大,相应地,纠正这种偏差的难度也就越大。因此,在这种制度下,量刑风险也最小,责任也最小,极易使审判人员产生不负责任的不良心理和工作态度,从而造成多判一年、少判一年没有多大关系的心理和后果。
二、罪状与法定刑的立法完善
根据上述分析,参酌近年来我国有关单行刑事法规立法的有益尝试,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例,笔者认为,改革目前的立法形式,使罪状明确、具体、全面,做到法定刑多档次、小幅度,应成为完善罪状与法定刑立法的主要内容。
(一)罪状的立法完善
1.规范法律用语,对犯罪构成特征的表述应科学、准确,且符合刑法的一般理论。
例如对刑法第172条规定的窝赃罪或销赃罪的罪状立法, 应将“明知是犯罪所得”修改成明知是违法所得,或明知是非法所得,或明知是不法所得。
另外,在罪状中尽量避免使用那些不易于审判机关掌握、不能准确反映该罪的构成特征或不是该罪构成必要要件的术语,如“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以营利为目的”等,或者使这些“情节”具体化。
2.采取一罪一刑、一罪一条的立法模式,摒弃多罪一刑的立法形式,从而使罪质与罪责统一起来,使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与其应受到的刑罚处罚对应起来。
同时,对那些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或者经常同时发生的犯罪以及现行刑法典采取“选择性罪名”规定的犯罪,如第162 条规定的窝藏、包庇犯罪,第170条规定的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犯罪,第172条规定的窝赃、销赃犯罪等,也应予以分解,根据各自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性大小分不同款项加以规定。
3.对特别法律用语(如罪名)下定义,使罪名法定化,使罪名定义条文化,尽量避免使用简单罪状的立法形式,以避免人们在认识上的分歧从而引起在执法上的不平衡。
目前,对罪名下定义,或对简单罪状表述的犯罪所作的描述、解释,一般以法理解释的形式体现在有关的法学论著、教材中。但由于法理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理论和实践中的认识也不一致,争论颇多。有的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表现,如1992年“两高”《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笔者认为,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法理解释和司法解释上,条件一旦成熟、经验一经丰富,就应使其上升到立法的高度,成为刑法典中罪状的组成部分。这种立法方式,不仅符合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更重要的是对于正确理解、适用法律,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极有益处,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立法技术的成熟度和科学进程。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单行刑事法规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第1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其他法规还对贪污、受贿、偷税、抗税等犯罪的罪名作了立法规定。笔者认为,这应当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的普遍方法。
4.罪状应当明确具体,要有层次性,要显示出轻重差别、罪行大小。对犯罪特征的描述尽可能具体些,能列举其主要表现形式的最好列举,尤其是对那些常见、多发性犯罪更应如此,如杀人罪、流氓罪、玩忽职守罪等。
国外的刑事立法,大都对常见、多发性犯罪作了详细、具体的列举式分款项规定,如对故意杀人罪,几乎都规定了一般杀人、谋杀、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杀害婴儿、教唆或者帮助他人使之自杀、受他人嘱托而杀人、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等多种情节,并根据各自的危害程度和罪行大小,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刑。前苏俄刑法典对故意杀人罪分4 条对13种不同的杀人行为作了规定。这种立法模式符合犯罪的一般规律,也便于审判机关操作,值得我们借鉴。
5.模糊术语内容具体化,减少模糊术语在罪状中的使用。
立法语言必须是能够准确无误表现立法者意志的语言,必须是易于为人们理解和遵行的语言。立法者应当“尽可能坚持使用可以找得到的确切言词,并给这些言词以它们原来的和通常的含义”(<英>丹宁:《法律的训诫》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当然, 制定法和法律文件的语言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使用模糊语言也是不可缺少的立法技术,正确使用可以成为确切语言的必要补充。而过多、过滥地使用模糊语言则是不当的。因此,在法治的社会,在实行“罪刑法定”的国家,立法者应尽量避免使用弹性很强、模糊性很大、无明确具体内容的语言,至少不应使其过多地出现在法律条文中。
我国刑法分则中,类似“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术语很多,且无明确、具体、固定的内容,给具体适用刑罚增加了困难。笔者认为,这在刑法典刚颁行或者法律还不健全的时期作这种原则性、粗线条式的规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法制的健全、理论的完善、条件的成熟,应逐步在刑法典中明确这些术语的主要内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行之有效的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上的规定。同时,在立法时,就应当充分研究和考虑每种犯罪的各种表现形式和轻重情节,而不应当把比较明显的轻重情节的内容留给司法解释去解决,从而避免刑法一颁布,紧接着与之相应的司法解释就随之出台的立法习惯。近年来颁布的单行刑事法规在这方面也作了有益尝试,模糊用语在多数情况下具体化了。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对拐卖妇 女儿童的严重情节规定了六种情形,《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2 条对强迫他人卖淫罪的严重情节也列举了四种情形。
(二)法定刑的立法完善
1.刑种要少。即对每一种犯罪或者对具有一定情节的犯罪,规定的可供审判机关选择的刑种(主刑)要少,我们认为一般规定1—2种为宜,最多不要超过三种。这样一方面可以使量刑更准确、适当,另一方面可以限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避免任意裁量。
2.立法上实行以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为主,以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为辅的法定刑制度。
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即在罪状之后规定没有量刑幅度,没有选择余地的刑罚,如对某种犯罪只规定“处死刑”、“处十五年有期徒刑”等。由于其对极其严重和不可饶恕的罪行没有赋予法官和审判机关以自由裁量权,因此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将其作为实行相对确定法定刑制度的必要补充而确认下来。如瑞士刑法第112条规定:“行为人之杀人, 显由于特别卑鄙之意识、或危险之情况、或经深思熟虑者,处终身重惩役”。这种立法例也被我国近年来的刑事立法所采取。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条规定:绑架妇女儿童,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关于禁毒的决定》第2 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这种立法模式对现行刑法典是一种改革和突破,同时也为刑法典的修改完善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范例。
当然,应严格限制适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的犯罪,只有对极个别的、法定刑中挂有死刑的、不具有法定的或酌定的从轻处罚的情节、而具有法定的从重或加重处罚情节的犯罪行为,才能作这种立法。
3.对附加刑的立法应采用以下办法完善,对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应明确规定其上、下限。剥夺政治权利刑也应明确其具体内容(如剥夺哪一部分政治权利)。
4.有期徒刑的法定刑,要多档次、小幅度,要根据犯罪行为轻重不同的形态和其他情节,划分多种量刑幅度,每个量刑幅度要小。在美、英等国家,甚至制定出了指导法院量刑工作的判决指南和确立了某些犯罪的标准判决幅度。这在我国虽然条件还不成熟,但缩小有期待刑的法定刑幅度,设立多档次的法定刑标准,以限制较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划分为若干量刑幅度档次。笔者认为每个档次的跨度应限制在三年内较妥,个别犯罪可以规定为五年。比如我们可以将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划分成半年—3年、3—6年、6—9年、9—12年、12—15年这样五个量刑幅度档次。一种犯罪或者具有一定情节的犯罪,只能与一个档次(或两个档次)相对应,而不能与多个档次相对应。档次越多、幅度越小,量刑也就越精密,偏差程度也就越小。
5.使法定刑与罪状挂勾,避免采取在笼统的罪状之后设定一个笼统的法定刑的立法模式,使一定的法定刑与一定的罪状相对应,一定的犯罪、犯罪情节与不同的法定刑相对应。条、款、项分明,罪状、法定刑层次分明,为实现罪刑相适应的法制要求提供一个良好的立法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