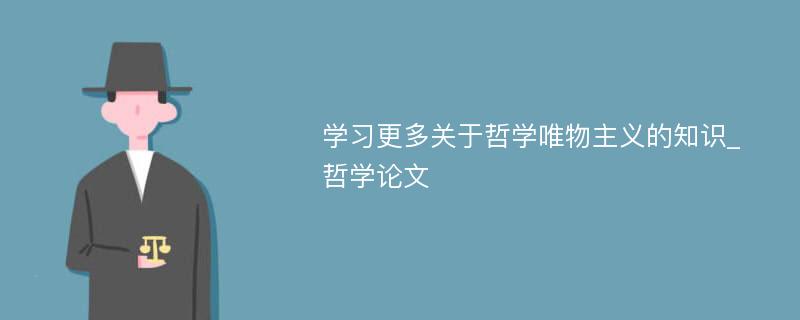
多学一点哲学唯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如下提法:科学是战胜迷信的有力武器,但这一提法不够全面。
迷信现象的思想本质(暂时不谈社会本质),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即是一个哲学问题。缺乏科学知识,很容易对某类或某种自然的与社会的现象,产生愚昧迷信的看法。
现在生活好了,大家都在奔小康了,封建迷信倒反而多起来了,为什么?我以为,这是对轻视哲学的一种惩罚。
迷信思想总是与相信某种超自然的能力或超自然的存在的观念相联系的。从产生迷信、产生神灵观念那一天开始,也就有人反对这些观念。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大多认为是无知。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曾经有人把这些反对意见作过一番总结和发挥。如果把他们的总结与发挥作一个漫画式的陈述的话,那可以这样说:神是骗子加傻子的产物。即狡滑的骗子对无知的傻子说,凌驾于我们之上的全能的神,命令我来统治你,无知的傻子相信了。因此,神完全是统治者为驾驭被统治者而设下的一个骗局,由于被统治者无知而相信了。但是无知是通过发展文化科学而得到克服的,迷信和神灵的观念却并没有相应地消失。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化主义观点的肤浅性。
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特别是费尔巴哈,对迷信和神灵观念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认为,为什么人会去崇拜神,把子虚乌有的东西当最高的存在来崇拜,原因在于人的存在方式。费尔巴哈认为,人作为一种感性存在物与其他的感性存在物有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与对象的关系不同。例如,食草动物只能以草为对象,没有草它便活不了。食肉动物只能以肉为对象,没有肉它便活不了。这些动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赖和取决于特定的对象。人则不同,人这种感性存在物并不是由外在于自己的异己的存在物来限定自己,而是自己限定自己;自己限定自己,即自由。或者说,人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的感性存在物。但是,费尔巴哈也不能不承认,在一个个体身上,有限和无限、自由和不自由这两方面是有矛盾的。这就是说,人之为人的本质,存在在自身以外,正是这种在自身以外的观念,把人的本质外化、对象化成了一个全知全能全在的实体,即神。所以费尔巴哈把精神称为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固然不可能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它体现在发展中的全人类中。为此提出要用爱人的宗教替代爱神的宗教。这是他1843—1844年以前的观点。
由于费尔巴哈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是错误的,因此,他由此得的结论必然也是错误的。但是,他指出要从人的存在方式中去寻找神灵观念产生的原因,这是有启发性的。这表明了迷信的神灵观念的产生,不能仅仅归结为无知,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即使暂时撇开社会的原因不说,还有世界观上的原因。虽然这个原因还是在思想认识的范围内,但比归之为欺骗加无知要深刻得多了。而且我们也得承认,正是人的存在方式中的内在矛盾,才使迷信和神灵观念不可能随着科学的昌明而全部消失。
(二)
人的存在方式中,的确如费尔巴哈所说的,存在着有限与无限、自由与不自由的矛盾。没有这个矛盾,便无所谓人,但在任何一个个体身上都难以实现其统一。概而言之,人的一切喜怒哀乐,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似乎并没有自觉地去思考这个矛盾,或思考这个矛盾对自己存在的意义,可是实际上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在这个矛盾的支配下生活。总而言之,只要是人,生活便会有二重性:非常重视给定的现实,又极力想超越现实;而且把超越看得比现实更重要,认为只有它才是理想的存在。
理想之所以为理想,就在于它还不是现实;理想一旦实现了,便不理想了。反之,现实之所以为现实,就在于它永远是不理想的;现实与理想等同了,便是世界末日了。显然,在这里有没有辩证的思维方式,理解不理解辩证的思维方式,比具备不具备某种科学知识更重要。没有辩证的思维方式,就有可能把理想的世界独立起来。这就会形成与此岸世界对立的彼岸世界,一切神怪也就有了栖身之地。只有哲学与科学的联盟才是战胜一切迷信的有效法宝。
当然,彼岸世界是不是真正统治了人们头脑,成了人们行为的准则。这还要有一系列社会条件,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但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彼岸世界是对此岸世界绝望的产物。这有一定道理。只要人相信自己、相信此岸的生活时,便难有彼岸世界的地位。
人的存在有超越性的一面,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即如果有正确的世界观来引导,它便是好,便能脱离低级趣味,升华为一个高尚的人。但是,只让迷信牵着鼻子走,就可能比自然界的猛兽更疯狂。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哲学世界观的重要性。
(三)
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联盟,似乎是一个十分陈旧的老话题了。从形式上说是如此,这决不是新主意。但是,以往的数十年间,我们始终没有处理好这一关系。在我看来,主要问题出在哲学方面,从这一关系的角度看,哲学主要有两项错误:
第一是长期混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把哲学简单等同于政治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了绝对真理的总和。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发现了生产劳动在人的存在和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发现了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永远结束了哲学家们要用某种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来剪裁历史的幻想;指出了永远要从实际出发,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的道路。
第二是形而上学地来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所谓直接的或形而上学的,即以为哲学可以直接确证或否证某一个科学命题与科学结论(在把哲学了解为绝对真理的情况下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反之亦然,似乎科学可以直接证明证伪某一个哲学命题与哲学结论(这一观点,恰恰是上半世纪在西方十分混乱的实证主义观点,确切点说,即取消哲学的观点)。
我们既反对用哲学去代替科学,也反对用科学来代替哲学。抽象地说,哲学和科学都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但是,它们是不同层次上(指认识的层次,不是价值的层次)的认识。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性的实证的认识,哲学则对直接性认识的一种反思性认识。科学是哲学思维的理论源泉,哲学则是科学认识的理论思维的基础。所以,两者是不能直接等同的,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
我们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错误了解,首先是来源于对哲学研究对象的错误理论。似乎哲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从经验上给定的事实开始的。如果这样,哲学当然也就是一种实际知识了。因此,它与其他科学的关系是直接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黑格尔早就说过,科学的认识活动,可以从一个研究对象(起点)开始,而哲学却不可以。因为哲学要科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不致于把科学遗留在假设的风化石上。
其次,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错误了解,还直接来源于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经验主义的理解:即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简单等同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就是把两极对立当作一个给定的事实作为认识的出发点。
康德所以要提出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恰恰就是为克服上述困境。虽然他并没有成功,却是有成效的。黑格尔从他的物自体与纯形式的关系中总结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即作为思维的思维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对普遍存在于科学中并以之作为存在的科学认识出发点的给定关系的反思的结果。作为思维的思维与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关系,根本不同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之处,就在它不是一个给定的对立。如果作抽象的概念分析,那么,作为思维的思维和作为存在的存在是一件事。如果作具体的事实的研究,那我们会发现,它指的正是个人的存在方式的二重性,是指人是具有自私意识(作为思维的思维,即“我”)的感性存在(作为存在的存在,即个体)。不过,不要对人的感性存在作直观的了解。如果对人的感性存在作静止的直观的了解,最具体的东西就会变成最抽象的东西,如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分析“这个”所表现出来的。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把人的感性存在了解为感性活动,没有感性的生产实践活动,就不会有人的感性存在,或者说,这种感性存在便不是人,而仅仅是一种自然动物。
在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中,原来内在于人的存在方式中的矛盾,便外在化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所以,在直观中,科学知识似乎是从一个先验的前提(即给定的对立)开始的,但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却并不是如此。这个似乎是认识的先验的前提,恰恰是认识活动的结果。因此,以为人的认识永远只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或前提)上是没有根据的。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辩证的,不是直接的等同关系。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拥有了科学知识了,世界观就一定是唯物的了,不一定。哲学唯物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学到手。
提倡多学点哲学唯物论,不仅对当前批判封建迷信有好处,对正确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使今后的道路走得更顺利一些,更是大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