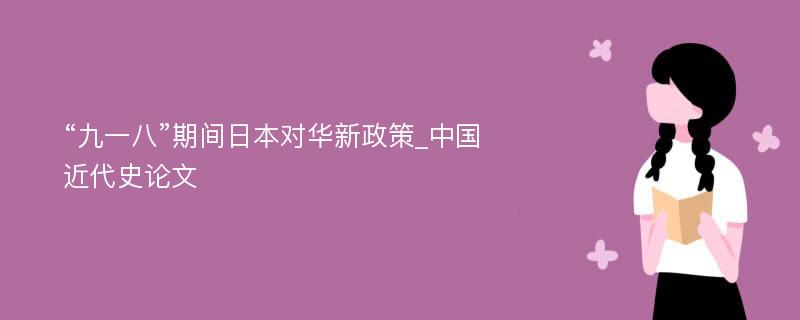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事变论文,新政策论文,九一八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为配合实施“满蒙政策”这个侵华的中心任务,也开始酝酿对于中国本土特别是与东西地区毗邻的华北地区的侵略政策,(注:中方当时所称“华北”,系指除东北三省以外的包括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六省在内的地区。日方所称“满蒙”,其中的“满洲”,系指东北三省;“蒙”系指内、外蒙古地区,而“内蒙古”又分东、西两部,东部内蒙古包括热河省,西部内蒙古则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境内。故“内蒙古”应属中国的“华北”范围。)并干预在华南兴起的反蒋运动。
华北是日本仅次于“满蒙”的在华“权益之地”。北洋政府时期,日本曾在此大肆活动。南京政府北伐统一之后,它又利用与华北地方实力派和北洋余孽的特殊关系,进行以反对蒋介石为名的谋略活动。
早在中原大战前夕,当阎锡山、冯玉祥策划联合反蒋之时,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升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即来到北平大肆活动,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为幌子,策动成立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派大同盟”,以便日本混水摸鱼。(注:许念晖《土肥原策动成立“北洋派大同盟”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149页;鄂森《土肥原与日本侵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3页。)
1930年4-10月的中原大战期间,日本对于此次战争以及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政权,就颇为关注。(注:[日]外务省编纂、发行《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四卷(东京,1994年版),就收录了来自驻华官员关于中原大战的电报近50份(第729-779页)。)在大战近于尾声、国民党扩大会议于9月初改变北方政府之时,9月16日,日本在一份经外务省大臣、次官及亚洲局长等官员圈阅的《我方对于北方政府的建立之态度》的文件中,分析了北方政府之不同于1927年的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明确表示:“我方因在平津地区有相当重大的关系,此时对于已成为该地区实权派的北方方面,采取不必要的冷淡态度,实非上策。……不必要因该政府改变外观,而直接改变我方对北方方面的一贯态度”。(注:《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S49(胶卷号,下引同),S1615-7(文件号,下引同),第53-56页。应当指出:该卷第1-79页所收外务省文书相当零散且残缺不全,笔者判断绝大部分可能已被毁坏了;而且,该文件并未收录于上述《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第一部第四卷“中原大战关系”之中。)这表明,日本对于阎锡山、冯玉祥等华北地方实力派,将仍然持一贯的支持态度,由此也就奠定了它与该派的特殊关系。
中原大战之后,因东北易帜和入关助战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但因“皇姑屯事件”与日本结有宿怨的张学良,入主华北且遥制东北。日本此后乃利用华北各反蒋派对于张学良的“反感”,继续策划谋略活动,以牵制张学良的实力及南京政府的注意力,配合在东北发动事变。
1931年3月,土肥原受日本参谋本部的派遣,再次来到华北,在天津设立了特务机关。土肥原此次选中的是反复无常但倾向反蒋的石友三,“企图利用石友三之乱,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与华北同时一举解决满洲问题”。(注:土肥原谈话录,[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9页。)为此,土肥原机关进行了“石友三工作”。日本外务省文书中,也留下了“帝国丿摇石说”的文件。(注:[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编《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总目录战前期》第2卷(昭和战前期),A.6.1.5.1-16-4,原书房,东京1993年版,第6页。)
为配合“石友三工作”,日本还开展了对于蛰居大连的阎锡山的工作。6月15日,阎锡山乘坐日本飞机,秘密由大连返回山西,加紧与石友三等进行联络,共同进行反对张学良的活动。他还派军人专程赴天津,经由土肥原机关,办理日方供应武器事宜。(注:《土肥原秘录》第109、111-112页。又参见:《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
石友三的反蒋行动,还受到了广东方面的支持,被任命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通电讨张。但战事发动后,应者寥寥,又受到蒋、张两军的南北夹击,不出半月即告溃败。(注:《张学良讨伐石友三文电一组》,《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6期。)土肥原本人也于8月18日被调任奉天特务机关长。
经过此次“石友三工作”,“土肥原机关长虽说未能达到目的,但可以说取得拖住张学良部队的效果”。(注:《土肥原秘录》第112页。)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为镇压对手,在中原大战之后再次调兵入关,其在关内的兵力已达11.5万多人,约占东北边防军总兵力(26.8万)的40%强。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实际上就考虑到了张学良方面驻满兵力减半这一事实后而进行策划的。(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第二卷《满洲事变》,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85页。)“石友三工作”,有力地配合了日本对九一八事变的发动。
在华北进行“石友三工作”的同时,日本也插手了“宁粤之争”后的华南政局,以利于其解决“满洲问题”。
1931年5月,拥护胡汉民的南方各反蒋派,在广州组织了国民党“非常会议”,并于28日成立了“国民政府”。由此形成了30年代中国国民党内部最大的反蒋地方实力派——广东派(1932年起改称“西南派”)。6月下旬,汪精卫、孙科及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人,通过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蒋运动及赴日的请求。(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P69,PVM57,第16-23页。)币原喜重郎外相于7月2日回电称:现在与广东政府商讨将来问题,不合时宜;虽然广东政府未经日方承认,但对其强烈要求派代表赴日,也无异议。(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P69,PVM57,第24-30页。)
经过一番磋商之后,7月26日,陈友仁等人化名成日本人,秘密前往日本。至8月13日离日之前,陈友仁在东京,访问过陆军省、参谋本部及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并与币原外相进行过多次会谈。其间,双方并未涉及到承认广东政府、聘请军事顾问等具体问题,对于武器援助问题,也只是淡淡涉及。(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P69,PVM57,第238-241页。)
陈友仁此次秘密渡日的主要结果,是与币原外相进行的五次会谈。但现存外务省文书中,只有7月28日、31日、8月3日的三次会谈记录,主要是前两次。在此会谈中,币原代表日方提出的要领主要有:在广东政府成为中国被认可的政府之后,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或条约,并以此结成同盟;该条约除一般性条款之外,还必须规定不侵略条款以及日中两国正纠缠或尚未解决的所有问题与事项,其中须特别规定解决满洲问题,包括赋予日本在满洲的诸多权益,确立日本国民(不论内地人或朝鲜人)在满洲的安定居住及和平从事商、工、农等职业的状态;上述条约须经中国国民的承认。陈友仁表示,可以通过国民党等机关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全国大会批准此种条约。(注:[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文书》第172-180页(以下简称《主要文书》)。)
可见,日本对于广东派的要求,并非如南京方面所宣扬的那样,它主要是企图以条约的形式,使这个有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广东政府,承认并确立其在满洲的权益。此时正当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与南京政府紧张交涉万宝山、中村两事件之际,它允许广东派派代表赴日,并向其直接提出关于满洲问题的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日本对广东派反蒋活动的支持和更大的期待,也是它对解决“满洲问题”的一种外交上的配合。
二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军部在集中解决“满洲”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酝酿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在《1931年秋末的形势判断及对策》中,陆军中央部分析、判断了事变之后的形势,并提出了《关于中国的对策细则》。其中规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迅速树立满蒙政权”,与此同时,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根本方策是:“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还特别规定了日本对于华北的方策是:“依靠操纵华北军阀的谋略,摧毁张学良政权”。(注:[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东京みすず书房1965年版,第165-171页。)这是日本在事变后侵占了奉天、吉林两省大部、但尚未占领北满的情况下,由军部制定的第一个日本对华政策文件。尽管其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国东北的,但其中对于中国本土的对策,再次反映了事变前夕,军部在同类文件的“对华谋略”中提出的“打倒中国中央政府、拥立亲日政权”的方针。(注:1931年4月参谋本部制定的“形势判断”及“1931年度参谋本部对华谋略”两文件,迄今未被发现。学界所用,系关东军对此的意见,载[日]《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第107-109页。)
按照军部的上述方针,关东军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的要求下,再次起用了土肥原。
10月25日,土肥原再次潜赴天津,设立特务机关。他此次的秘密使命是,除了利用山东的韩复榘,通过各种谋略活动,扰乱平津地区、破坏张学良政权之外,还要利用间隙,设法策动隐居于天津日租界的溥仪出走满洲。(注:《土肥原秘录》第114页。)为此,11-12月间,土肥原策划了两次天津事变。但除了劫持溥仪逃往满洲之外,土肥原并未实现其华北谋略,第二次天津事变后又被军部召回而受责。(注:《土肥原秘录》第116页。)
但天津事变后不久,关东军又派遣土肥原到达广州,与在此酝酿进行反蒋运动的胡汉民会见。土肥原在攻击南京政府的同时,表示愿意由日本帮助他“出面组织健全政府”,而胡汉民则以本国内政不要他国干涉为由拒绝了。(注:蒋永敬编:《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1页。)
1931年底,日中两国的政局都发生了动荡。12月11日,若槻内阁总辞职,第二次币原外交宣告结束。13日,犬养毅组阁,并暂兼外相。15日,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成立了以广东派为主的孙科内阁,陈友仁出任外交部长。
犬养毅曾与孙中山关系密切、颇受其“大亚细亚主义”的影响。他企图借孙科内阁成立之际,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满洲问题。为此,他与胡汉民互通意见后,决定派遣“民间人士”萱野长知秘密赴华。12月23日,萱野以个人资格来到南京,与孙科内阁的要人们讨论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但萱野的工作受到了军部和驻华外交官的强烈反对,犬养毅被迫于1932年1月5日训令其立即回国。(注:详见拙著,第58-61页;又参见李吉奎《犬养的“和平”试探与“五一五”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萱野工作,含有日本对西南派及中国政府的双重意义,反映了犬养内阁对华新政策的某些特点。它的迅速失败,“是因为外务、陆军、海军的官僚们认定,萱野工作乃是日本满蒙分离工作的障碍”。(注:[日]崎村义郎著、久保田文次编:《萱野长知研究》,高知市民图书馆1996年版,第225页。)
而日本军部则在炮制伪满傀儡政权的同时,继续规划新的对华政策。1931年12月23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提供的方案,共同商定了《处理时局纲要方案》,在主要规定对满蒙政策的同时,再次提出了日本对于中国中央政府及中国本土的政策,主要有“支援反张、反蒋势力,特别是北方实力派(例如段祺瑞),以期消灭作为排日祸根的国民党”。(注:《现代史资料7》,第320-321页。)
陆军中央部1931年底的上述两份文件,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最早产生的对华政策方案,它对于中国本土政策的规定,既指导了关东军和天津军(指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新的侵华行动的发动,又奠定了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基础。
根据军部的上述方案,犬养毅内阁在否定“萱野工作”的同时,由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商定了《处理中国问题方针纲要》,并于1932年1月6日,在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到东京会谈时,向其出示了这份文件。该文件除了对满蒙问题的政策之外,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政策主要有:其根本方针是“彻底清除排日、抵制日货的祸根”,处理纲要是“消灭中国本土的赤化运动、反日军阀及反日政党”。(注:《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第171-172页。)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制定的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其中关于对中国本土的方针与处理纲要,规划了日本在事变后的对华政策走向。据此,参谋本部第二课于1月21日拟订了一份《对华一般方策》的方案,规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决满蒙问题之既定方针迈进”,同时,“一面努力封闭第三国对此容喙之机会,确立东方门罗主义;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需要,相信有必要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分别建立与满蒙一样的亲日、独立国家”。(注:《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第175-176页。)
犬养内阁的主要使命是解决满蒙问题。3月12日,犬养内阁召开“阁议”,通过了《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注:《主要文书》(下)第204-205页。此文件在有些书中与前述1月6日文件相混淆,被误记为《处理中国问题方针纲要》,如:[日]《现代史资料7》第494页;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5页。)以及两个附件:《伴随满蒙新国家成立的对外关系处理纲要》、《伴随满蒙新国家成立的诸问题中特别需要紧急处理的事项》。(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27,IMT149,第25-39页。)但除了扶植伪满洲国之外,踌躇于承认问题,且在一二八事变后的扩大侵华中无所作为、与中方签定了上海停战协定的犬养首相,随即于5月15日丧身于法西斯势力发动的政变之中。
“五一五事件”之后上台的斋藤实内阁(26日),成立初期在对华政策乃至对外政策上的关键问题是承认伪满洲国。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较之于“独立”问题,承认伪满是一个更能引起列强关注的敏感点。(注:United State of america,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Diplomatic Papers,1932,Vol.Ⅲ,The Far East,p420.)7月6日,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被任命为外相后,提出了“焦土外交”的口号,以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注:[日]内田康哉传记编纂委员会、鹿岛和平研究所编《内田康哉》,东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版,第357-359页。)他上台不久,即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之间,围绕日本新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多次磋商,并达成一致。
在此基础上,8月27日,斋藤内阁“阁议”通过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处理时局方针)。该文件规定,在对华政策上,日本要将“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区别开来、分别对待。关于“对满蒙政策”,虽被视为日本外交的“核心”,但却只规定了继续奉行前内阁3月12日决定的方针。它以大量篇幅规定的是日本在新的国际关系之下的对中国本部、国际联盟及各国的政策,特别是被列为首位的对华政策。关于“对中国本部政策”,文件在正文中规定“以发挥其贸易及工业品市场的作用为主”,但在“附件甲号”中规定的具体内容,则与此迥异:“我方要密切注视因近来中国本部的地方政权愈加明显的分立状态而带来的政局演变。对于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政权,应尽可能尊重其立场及体面,或者进而采取善意态度,使其有利于我方”;“在情况允许之时,努力谋求与各地方政权之间实际解决各种案件,并避免发生事端”。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上海方面、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以及“山东地方及华北”的不同对策;对于“山东地方及华北”,规定:“万一该地区治安发生显著混乱、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重要权益绝对需要保护时,就应当出兵”。(注:《主要文书》(下)第206-210页。)上述文件,以较为隐晦的内容和“正文”与“附件”矛盾的方式,表明了日本在即将结九一八事变之后,仿效伪满洲国,对中国本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斋藤内阁的上述“阁议’决定,在将“满蒙政策”与“中国本土政策”分开处理、以及不惜出兵“山东地方及华北”这两个根本点上,与以前的田中内阁“东方会议”所决定的对华政策及其出兵山东之举,并无二致。(注: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文件,参见《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但它不同于以“满蒙政策”为重点的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是,它的对华政策的重点,已转向了“对中国本部政策”。因此,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达成的斋藤内阁的“阁议”决定,就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满蒙政策向中国本土政策的过渡,从而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既是此前酝酿一年多的对华新政策的总结,又此后日本继续探索与实施对华新政策的根据。
此后不久的9月13日,日本枢密院在天皇亲临、内阁阁僚全体与会的情况下,讨论通过了《日满议定书》及其附件。(注:[日]国立公文书馆藏《枢密院会议议事录》第71卷(昭和七、八年),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第115-131页。)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定了上述条约,正式加以承认。
三
经过九一八事变、基本解决了满洲问题之后,按照上述“阁议”决定的方针,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重点,转向了其原本就有工作基础的华北地区。1932年间,日本以热河与山东地区为重点,实施其华北政策。与此同时,日本军部的特务机关也在河北与热河境内,策动以段祺瑞为首的旧安福系政客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旧直系军阀,进行反对张学良的谋略活动。(注:参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致内田外相电(9月14日)、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致内田外相电(9月30日),[日]外务省编印:《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一部第一卷,东京1996年版,第594、597-598页。)
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由淞沪抗战转向了反蒋抗日之后,在华北联络冯玉祥等人,企图“南北并起”以倒蒋。(注:参见: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与蒋胡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西南派在对日态度上虽有变化,但并未放弃与日本的交涉。9月间,胡汉民派陈中孚秘密赴东京,探求日本军部的意向。陈中孚回到上海后,又与日本公使馆要人交换了意见,随后到广州向胡汉民汇报。西南派乃向日方建议:让张学良下野,使之担负“满洲问题”的全部责任;借讨张,使广东在反蒋方面成为与华北相匹敌的策源地,并在武器与财政方面请求日本的支持。(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一部第一卷,第596-597页;[日]外务省编印《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一部第一卷,东京1981年版,第816-818页。)这些主张,当然也反映了日本的意向。
1933年元旦,日军在山海关挑起事端,由此开始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又一新的侵华步骤——热河与长城作战。2月9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声明,宣称进攻热河乃是满洲事变的“画龙点睛之笔”。(注:[日]仲摩照久编《热河讨伐及热河事情》,东京新光社1933年版,第32页。)10日,关东军公布热河作战计划,则指出其“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的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日]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二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71页。)23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上村伸一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不亚于“宣战书”的声明,内称:日军在热河的行动,“原则上仅限于满洲国领土以内,惟张学良军队等若采取积极行动,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注:外交部长路罗文干致蒋介石电(2月2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00页。)据此,日军在3月4日攻占承德之后,迅速进攻长城各口,并实施配合长城作战的华北谋略。
此次华北谋略的实施者,日本军部选择了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少将。板垣在东京获得了参谋本部的同意,陆军省也以只搞军事谋略为条件,拨给其活动经费。(注:《土肥原秘录》第18-19页。)2月13日,板垣以参谋本部未公开人员的身份,来到天津,担任特务机关长。板垣机关在以往华北谋略的工作基础上,对华北当时的政情进行了观察与分析,他们把现在华北的军政人物分为四派:“蒋介石派”、“反蒋派”、“维持现状派”、“首鼠两端派”。其工作计划是:以“关东军武力、天津机关、张景惠等其他满洲国要人”,联络“反蒋派”与“首鼠两端派”,并通过这两派,联络“维持现状派”;然后再以“维持现状派”与“首鼠两端派”,继续与“蒋介石派”联络;同时通过“反蒋派”(包括安福派、直隶派、张作相派等),对“蒋介石派”实行军事攻击。(注:详见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所制《华北政情的观察》附表,《现代史资料7》第545页。)这就是板垣机关华北谋略的主要内容,其工作对象的重点是“反蒋派”,工作目标的重点是“蒋介石派”。3月底,关东军发动了“滦东作战”,以配合板垣机关的工作;军部也为其增加了活动经费,企图一举实现“策动内变”为主的目的。
但直到5月初,板垣机关的华北谋略也没有取得太大进展。而在此时,南京政府已决定对日缓和、进行直接谈判,并派黄郛北上,在北平设立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收拾华北时局。为此,日本决定放弃“策动内变”为主的方针,改取“以战迫和”的政策。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赴东京,与参谋本部协议后,回到大连与武藤信义司令官进行了密商,于5月3日发出第503号命令,对华北方面的中国军队“再次予以致命的打击,挫败其挑战的意志”。(注:《现代史资料7》第541页。)6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及上海武官、北平及天津特务机关下达了《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提出了以关东军武力打击为主、华北谋略为辅的处理华北时局的方针,以“造成华北军政的实质性屈服或分解”;并且要“更加助长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分离倾向”,在华北施策时,要“利用华中现政权的动荡而巧为操纵,使这一动荡反映于华北、华南两地区,从而造成用于我方的环境”。(注:《现代史资料7》第543-544页。)这份文件表露了日本以华北政策为主、华南政策为辅,操纵南京政府,再以南京政府的动荡,导致华北、华南两地区的动荡,最终造成全中国分裂的企图。这也是对于去年8月27日“阁议”决定的日本“对中国本部政策”的最好而全面的体现。
按照上述方针,关东军于5月7日开始了向长城各口及冀东地区的攻势作战,以武力造成华北当局的“迫和”之势。板垣机关继续以北平、天津为中心,配合进行华北谋略的工作,企图以旧北洋系人物为主,树立华北新政权乃至“华北五省政权”。(注:内田外相致上海有吉明公使电(5月19日),[日]外务省编印《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三卷,东京1981年版,第857页。)
在关东军达到“造势”目的而华北谋略仍无多大进展之后,22日,参谋次长通过关东军,训令天津特务机关结束工作;参谋总长则训令北平公使馆武官永津佐比重,受关东军指挥,开始停战谈判。(注:《现代史资料7》第517-518、555-556页。)日本军部在华北政策上的变化,是由于他们已经认识以黄郛为首的华北当局,基本上符合其需要,从而企图“使南京政府以黄郛去实施改造华北的国民党、禁止排日等政策;万一出现黄郛已经努力,而结果仍然是党部横行、排日运动依旧的情况之时,再另外打算也不迟”。(注:《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三卷,第863-864页。)28日,关东军给天津特务机关的电报中,又对此再次加以说明:“此时应迅速抛弃过去以北洋系军人为中心的计划,而应劝说黄郛,并以他为中心,迅速树立亲日满政权”。(注:《现代史资料7》第559页。)这表明,日本的华北政策已由板垣机关的工作,转向“树立以黄郛为首的亲日满政权”了。
5月25—31日,日本在逼使北平军分会与之签定关于停战的军事协定即《塘沽协定》的同时,又在酝酿与华北当局签订与该协定相关的“第二次协定”即政治协定的问题,企图以此实现其新的华北政策。
还在确定上述华北新政策之时,参谋本部就考虑,要在第一次停战协定成立后,进行第二次谈判,以签订一项包括善后问题在内的“另外协定”。关东军也同意这个意见,并指出该协定的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一)彻底取缔排日;(二)严禁策动扰乱满洲;(三)在缓冲地带(中国军队不进入的地带)的治安维持与交通规定”。(注:《现代史资料7》第555页。)当黄郛在北平与日方密谈之时,24日,内田外相致电北平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要他在停战协定成立后,不失时机地与黄郛达成一项“政治协定”,其内容有:“(一)北平政整会镇压辖区内的一切排日运动;(二)由该委员会镇压发生于辖区内的给予反满义勇军的一切援助;(三)该委员会对其辖区与满洲国领土间的适当而和平的交通,扫除一切障碍(该项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便于从华北方面向热河省供给物资)。以上三项,重要的是要达成某种形式的协定;(四)要商定停战区内的治安维持方法,并将此协定与军部协商”。(注:《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三卷,第870-871页。)
29日,关东军再次向参谋本部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在停战协定后,签订“第二次协定”,并希望在该协定中增加“华北政权禁止一切排日运动”、“开始满洲国与华北之间的合法交通与贸易”等项内容。(注:《现代史资料7》第559-560页。)同时,内田外相也以“大至急、极密”的电报,致电中山详一,再次提出了外务省关于华北停战的政治协定的内容;还特别指出,该协定已与陆海军协商过;并提出了签订该协定的时机与方法。(注:《主要文书》(下)第273-274页。)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达成的、急于要与中方签订的这份“第二次协定”即关于华北停战的政治协定,暴露了日本将要付诸实施的华北新政策的内容。
从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结果来看,上述内容并未形诸条约文字。故在《塘沽协定》签字后的第三次会谈中,关于第四项,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又提出“取缔排日不在协定范围之内,但此问题实为中日争执之源,希望华北当局速结第二次协定,厉行取缔以示诚意”,中方代表熊斌当时则回答“本职军人不能直接处置,当代传达”。(注: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三),台北1965年版,第184页;《现代史资料7》第527页。)这样,就埋下了继续进行塘沽协定善后谈判的伏笔。而日本政府与军部之间酝酿的关于《塘沽协定》的“第二次协定”或政治协定,就构成此后日本逼签《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的依据,其内容也成为该两协定的滥觞。
《塘沽协定》,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实施对华新政策特别是华北政策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它又开启了新的阶段。负责谈判的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认为“它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期间,我国长期对外战争中的最重要的转折点”。(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3页。)日本外务省在七七事变后的一份文件中也认为:“谈到现在的华北政权成立之经过,则至少要从塘沽协定的签订讲起才合适”。(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59,IMT456,第55-56页。)因此,《塘沽协定》之逼签,又可视为“华北事变”的前奏。
在板垣机关策动华北谋略时,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也在闽、粤一带策划过一次“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和知此前得知两广的实力派人物“企图再开日中直接交涉,以日、满、华提携结成亚细亚联盟”之后,亲自出马,以港币买通了广东归侨中的一些人,组织了“广东大亚细亚协会”,并由该会组织了“归国华侨旅行宣传队”,计划于4月23日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土墓前举行仪式(4月23日系旧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曾在此发生黄花岗之役,72名反清志士牺牲)时,公开散发“大亚细亚主义、王道政治”的标语,由此开始发动华南的“大亚细亚联盟运动”。但在仪式时,他们却出乎意外地散发了内容完全相反、宣传抗日排日的传单。和知非常狼狈,却谎报了参谋本部,日本报纸亦宣传“广东大亚细亚联盟运动抬头”的消息。(注:《日本外务省档案》,S13,S1200-14,第75-87页;S510,S1110-40,第238页。关于此时日本在华南策动的“大亚细亚协会”组织,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版,第837-840页。)这次流产的运动,表明了日本在华南的政治企图。
从1931年初的“石友三工作”、到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的近两年半时间,是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对华新政策即除“满蒙”之外的对于中国本土政策的酝酿与探索阶段。这期间,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的既定目标,以针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满蒙”政策,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和工作重点:继侵占东北后,扶植并承认了伪满傀儡政权;又侵占热河及长城地区,扩大与巩固了对伪满的统治。与此同时,为配合九一八事变的发动与扩大,日本又酝酿并探索实施了“对中国本部政策”:以毗邻东北的华北地区为中心,以反对张学良以至蒋介石为幌子的谋略活动为主要内容,并以对广东—西南派的华南工作相配合,阴谋北南夹击、搞乱国民党中央政府,达到仿效伪满洲国、分裂全中国的企图。这些对华新政策。从内容、方式与目标等方面,奠定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
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满蒙问题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关东军论文; 九·一八事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