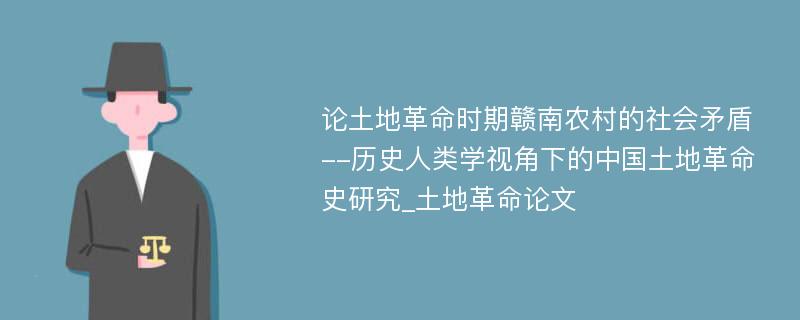
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地革命论文,人类学论文,中国论文,社会矛盾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赣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赣南土地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与该地区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具有紧密的历史关联。(注:本文所谓“土地革命”,泛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在赣南等江西南部农村地区领导发动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包括早期的农民暴动和随后的苏区革命乃至长征之后的游击战争。)从往常的革命史研究视野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赣南等地的中国现代土地革命运动,其最重要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特征就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即在革命前夕,赣南农村的土地问题和社会分化十分严重,且集中表现为土地的分配极端悬殊,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尖锐;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即以这一深刻的社会危机为重要时机,用一种新型的革命理论即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而策动了这场土地革命运动。长期以来,人们对土地革命运动的了解和认识也大体如上所述。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或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地区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即会发现,在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共产党人所面对的其实远远不只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的问题,土地革命运动的历史内容也不仅限于单纯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因为,当时赣南农村社会的分化,不仅包括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分化,还包括各种不同社会人群(或族群)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如在早来的土著居民与晚来的客户之间,大姓与小姓之间,大族与小户之间,以及不同的地方政治派系之间,都存在着很深的界限和矛盾;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农村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土地革命的发展进程,并对党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策略提出了挑战。由此,笔者以为,要对土地革命运动的历史内容以及党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策略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就必须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高度和区域社会史的总体视野,去了解和探讨赣南农村地区整个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问题及其与土地革命运动的历史关联,而不应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讨论和分析。(注:换言之,就是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占有地方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包括革命亲历者的调查报告和回忆录)的基础上,把土地革命运动置于发生发展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对其进行整体的、内在的和相互联系的考察和分析,以超越单纯的片面的阶级分析模式,深化对中国土地革命运动史的研究。)本文依据有关地方历史文献及文史资料(包括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当时的调查报告及后来的回忆录),着重从土客矛盾、地方宗族主义和地方派系斗争等方面,对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地区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及其对党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影响和制约,以及党的革命策略作综合考察和初步分析,以期深化对赣南土地革命运动的认识,并就开拓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的新视野进行讨论。(注:有必要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也有研究注意到了土地革命时期赣南等边界地区的土客籍矛盾问题、乡村宗族问题并加以考察,但笔者以为,这些考察或注重于阶级斗争的分析,或是一般性的叙述,缺乏深度的历史分析或区域社会历史环境的整体把握,仍然属于单纯的革命史或党史角度的研究,因此,对土地革命发生发展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进行整体的、内在的和相互联系的考察和分析,仍然是有必要的,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有关研究请参见万芳珍:《清前期江西棚民的入籍及土客的融合和矛盾》,《江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裘之倬:《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客籍矛盾问题》,收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林济:《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与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二、户籍差别与土客矛盾
土客籍的界限和矛盾问题,是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社会分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所谓“土客籍”,指的是拥有本地户籍(即“本籍”或“土籍”)的本地人和来自外地的“客籍人”两大社会群体;他们分布在赣南(以及赣西南和赣西北)等广大的江西边界地区,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十分尖锐、严重。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即指出:“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1](P74)由此看来,赣南等边界地区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双方不仅界限分明,而且积怨很深,构成了这一地区严重的社会分化和族群矛盾。
从历史渊源来看,那些与“土籍”对立的“客籍”,其实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早期历史上的北方移民,而是明清时期从东南地区来的福建人、广东人。明末清初以后,江西沿边的丘陵高地地带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开垦高潮,其中大量的闽粤民人翻山越岭来此进行垦山种地,他们后来逐步定居下来,成为近现代江西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P17-33)[3](P26-31)不过,在当地定居入籍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清代里甲(或称图甲)户籍制度以及土著居民的制约,这些闽粤移民并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即与土著户籍同等并列的正式民图户籍,他们多数情形下只能把户口和田产寄放在新移居地的、由当地土著控制和支配的图甲户籍中,这就是所谓的“寄籍”或“客籍”。[4](P49-56)[5](P84-93)具体说来,清代闽粤移民“寄籍”赣南的情形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在新移居州县土著民之图甲户籍(即一般民籍,是为“土籍”或“本籍”)的末尾另立户名而附籍当地,名曰“民尾户”。如据乾隆《南康县志》记载,雍正九年(1731)有“东粤新民五十一户入籍”南康县[6](卷19《杂志》),即“附于土著各图甲之尾,编立户名,收银完赋”[6](卷3《赋役志·户口》);又如乾隆《赣县志》卷3《疆域志·坊都》指出,赣县“坊都皆有图,计一百零九图,每图凡十甲。……赣近数十年来,闽广流寓者,置立田产,并不遵例入籍充役,创立民尾户名色,附於百九图之外,钱粮自行完纳,编审书算概不与闻”。这种专门为福建或广东等外来移民而设置的“民尾户”户籍,是一种既附于土著图甲户籍末尾、又与土著图甲户籍相区分的户籍类别,这就从制度上使外来的处于“客籍”地位的闽粤移民与本地的处于“土籍”地位的土著居民区分开来。这种户籍区分或差别的实质在于:“民尾户”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临时性的户籍,它未配有科举名额,属于“民尾户”户籍的闽粤移民在新移居地并不享有土著民所拥有的在民籍定额中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其结果造成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地位,特别是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并由此形成深刻的社会裂痕。闽粤移民“寄籍”赣南的另一种情形,就是把田产及税粮都附寄在当地土著的图甲户籍内,即他们依附“土籍”之下,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故而就不可能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等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1989年石城县花园岭罗氏新修的《罗氏闽赣联修族志》中收录了撰于清中叶的《户籍志》,其中即指出:“自古有田则有赋,有赋则有户,流寓、土著莫不皆然。惟石(城)邑之规独异,编户九里,里分十甲,立一长。自里长之名创,凡寄居者,置(产)必附其末,名为甲首。甲首之户,世数虽多,粮赋虽广,子孙不得莅籍与试。”在这里,外来的“寄居者”把田产钱粮附寄在普通里甲中的“里长户”(一般为土著大户)末尾而获得的“甲首户”户籍,虽然在形式上构成州县正式里(图)甲户籍系统中的一户,但在实质上,它完全受到“里长户”的控制和约束,属于“寄籍”的性质;纵使子孙繁衍数世,田产粮赋众多,寄籍的“甲首户”亦难以取得独立的户籍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例如,明末清初从闽西先后迁居赣南石城县珠坑乡等地的罗氏和孔氏均属此类“寄籍”户,长期遭受其主户的控制和勒索,土客籍矛盾极为尖锐。[7](P108-111)这种“寄籍”性质的“甲首户”受制于土著大户(即“里长户”)的情形,其实并不是石城县所独有的现象,在赣南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如康熙年间,瑞金县绅士杨兆嶦在《与张邑侯书》中曾指出:“有不能起户者,寄其丁粮于大户,谓之甲首。本户(即‘大户’或‘里长户’)之于甲首,如驱使奴隶,大当之年恣其需索,莫敢谁何。弊习相沿,牢不可破。”[8](卷11《艺文志》)
综合以上情形可见,明末清初以后开始移居赣南各地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即所谓的“客籍”、“客户”,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之间之所以形成“牢不可破”的界限和矛盾关系,主要的社会根源在于双方在户籍制度和户籍地位上的差别(进而是整个社会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而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阶级差别。那么,由这种户籍差别所造成的土客籍两大社会群体的社会分化,既是土地革命时期赣南乡村地区土客籍界限和矛盾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也是其实质所在。
正因为土客籍分化与对立的原则(即户籍差别)与阶级分化的原则(即阶级差别)不一致,清代以后所形成的土客籍界限和矛盾问题,对党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纲领的土地革命斗争造成干扰或障碍也就不可避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1](P75)同属农民阶级的土籍农民与客籍农民之间,也时常发生激烈的对抗,这就模糊了阶级界限和影响了阶级斗争,不利于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建立;土客籍斗争甚至存在于党内,成为引起党内政治斗争或路线斗争的社会因素;所有这些都对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害。[1](P75)曾经于1934-1937年领导赣南山区游击战争的陈丕显,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提到当时赣南革命斗争中所存在的“来自外地的客户”与本地土著之间的界限和矛盾问题。[9](P60-64)此外,陈正人、康克清等共产党人的回忆也都提到土客籍矛盾问题对于革命斗争的消极影响。[10](P310-342)[11](P35)总之,清代以后形成的土客籍界限和矛盾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分化问题,无可避免地卷入到土地革命运动中来,从而使赣南等广大的江西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充满了复杂性。
三、姓氏界限与宗族矛盾
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社会分化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地方主义(特别是地方宗族主义)的盛行,它通常又具体表现为严重的姓氏界限和宗族矛盾。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谈到江西边界地区的地方主义问题时,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在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边界各县,“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而且“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1](P69,74)也就是说,农村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往往不是主要表现为阶级分化,而是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各自为阵,形成明显的姓氏界限和严重的宗族割据的态势。在赣南,这种姓氏或宗族的界限,不仅体现在居住空间的区隔上,也非常具体地体现在对山林土地等日常生产生活资源的控制与争夺上,如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寻乌县的姓氏界限观念十分严重,当地的山林都被各姓控制,不容外姓侵渔,“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这种受姓氏界限限制的山林制度即是一种典型的地方宗族主义。[12](P201)
在赣南农村地区,姓氏界限与宗族矛盾这一社会分化的问题,可以说要比土客籍矛盾更严重和更普遍,因为它存在于千千万万的姓氏宗族及宗族村落之间。追根溯源,这是明清以后赣南乡村宗族发展及宗族矛盾演化的历史结果。从地方文献的记载来看,至迟到清代前期,赣南乡村宗族已获得了普遍发展。在乡村地区,到处是“聚族而居”的聚居宗族,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赣州府志》载:“(赣州)诸县大姓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聚族而居。族有祠,祠有祭,祭或以二分,或以清明,或以冬至,族之人皆集,尊卑长幼亲疏秩然而不敢乱。”[13](卷2《地理志·风土》)同时,当地乡民的宗族观念也普遍深刻,对待宗族的态度极为严肃,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杨龙泉志草》载:“巨家寒族莫不有宗祠,以祀其先;旷不举者,则人以匪类摈之。报本追远之厚,庶几为吾江右之冠焉。”[14](卷11《风俗志·宁都州》)可见,在清代,“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及宗族生活已经成为赣南乡村社会生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宗族广泛发展的同时,不同宗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非常普遍,集中表现为宗族间的武装械斗(当地通常称之为“姓氏械斗”)。具体地说,比邻而居的不同姓氏宗族之间,往往因日常细故发生纠纷而导致械斗,如同治《会昌县志》卷11《风俗志》即载:“(会昌)乡民皆聚族而居,室庐鳞次,多至数千家。睚眦小怨,动辄格斗,各庇其族,不逞之徒往往夹刃以游,捐躯不悔,故命件较别邑为多。”因为争夺各种生产生活资源而引发械斗的情况更多,如光绪末年于都县北乡天井湖胡姓与当地大族谢姓之间,即因为争夺风水龙脉而发生械斗,据《胡氏族谱》载:“光绪癸卯春,因争后龙,故迨至乙巳年七月间,(胡姓)与谢姓械斗。谢姓素称于(都)北(乡)悍族,蓄意鲸吞,几欲蹂躏其地,灭此朝食而后快。”[15](P114)会昌县周田乡上营村的王姓与邻村的张姓,因为争占水利陂圳,双方从1911年元月开始,展开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武装械斗,据说周边几个与双方有亲缘关系的村庄都卷入此次械斗,结果酿成死伤数十人的惨案。[16](P105)大庾县新城东乾的刘姓与他的西邻李姓之间也因争山霸水而发生流血冲突,据说这次姓氏械斗持续18年之久。[17](P75)宁都县湛田乡湛田墟的曾、宋两姓则因为争夺对墟市的控制权而在民国17年发生械斗,结果导致湛田墟焚毁。[18](P168)种种现象表明,从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在赣南的乡村地区,为争夺风水龙脉、水利陂圳、山林土地以及农村市场等各种社区资源的宗族械斗不仅非常普遍,而且盛行不衰。[7](P138)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形成了宗族械斗的“恶俗”,如会昌县“西冈(即西江)恶俗好作姓族械斗,岁必数起;当之者倾家荡产,尽其所有;每斗,杀人多至数十,或数百不等,惨无人道”。[15](P172)而且这种姓氏界限的观念及械斗的“恶俗”往往根深蒂固,不易破除。民国26年《寻乌乡土志》即载:“吾邑人民向称淳朴,勤俭是其本能,耐劳实出天性。虽间有秉赋强悍,□习武功,流弊所至,易生械斗。然民性随环境转移,苟能施以教化,破除姓界,化私斗为公战,亦易无事,则此勇敢之性,乌足为吾民病哉!”总之,清代以来乡村宗族的普遍发展以及宗族械斗的盛行不衰,直接造成了赣南农村社会严重的姓氏界限和宗族矛盾。
上述历史演变的一个直接的社会后果是,到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地区的聚落格局是一团一团的宗族村落,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形成了各自为阵的宗族割据态势。当共产党领导的以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为纲领的革命洪流到来时,这些宗族割据势力就像暗礁一样,阻挡着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兴国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陈奇涵将军在回忆1927年兴国的早期革命斗争时就曾经指出:当时“兴国党组织看到革命运动中有两大暗礁”,其中之一就是,“人们聚族而居,死地主(祠堂、庙宇、会社)占有很大部分土地,族绅、头人可以利用这部分土地为所欲为,在‘有事不离祖’的宗法幌子下笼络群众,树立门户,党同伐异,寻找借口,挑起氏族或地方的械斗。这种械斗有的连年累月,甚至结成世代冤仇。”[19](P9)由此看来,姓氏界限和宗族矛盾实际上成为乡村政治斗争的工具,常常被宗族中的绅士或族长之类的家族头人用来争权夺利。曾经参加1928年兴国县崇贤乡农民暴动的共产党人李挺的回忆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兴国县东北部的)崇贤,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族长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常常挑唆和发起氏族之间的仇视、械斗。”[20](P134)显然,这种状况模糊了群众的阶级意识,影响了阶级的分化,因而不利于共产党人动员和发展革命力量。此外,“聚族而居”的宗族居住形态和深刻的宗族观念,也不利于党组织在农村中的发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即指出:“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1](P74)由此可见,土地革命运动(包括革命斗争的开展和党组织的建立)也深受姓氏界限和宗族矛盾这一地方主义问题的困扰。
四、地方政治派系及其斗争
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地区的社会分化与社会矛盾,也体现为地方政治的分化与对抗,具体则表现为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集团组成不同的地方政治派系,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如在土地革命前夕的于都县,全县大致分成两个地方政治派系,即昌村派和于水派,这两个地方派系操纵于都县的地方政治,在地方利益竞争中既对立冲突又妥协合作。曾经领导1928年于都县农民暴动的于都籍早期共产党人丘倜(1903-1980),在回忆中介绍了这两个政治派系的社会基础及斗争状况:“全(于都)县的土豪劣绅,当时分成了昌村与于水两派对峙,两派之间既有勾结又有倾轧。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左右于都全县的反动政权。昌村派代表了农村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势力,他们以北乡的银坑、马鞍石、赖村、葛坳、水头,东乡的固院、梓山,南乡的禾丰、小溪等村乡为基础,这些乡村都是聚族而居的,宗族观念高于一切,他们受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统治,本族的土豪劣绅就像土皇帝,操着生杀予夺之权。于水派的势力范围在县城和西南两乡,这两个乡中小地主居多,除禾丰、新陂、小溪等处有些较大氏族聚族而居外,其他大部分村庄是杂姓散居,人少姓小,其中有些中小地主兼营工商业。两派竟相勾结伪县政府,把持地方政治,分赃地方利益,包揽词讼,武断乡曲,鱼肉乡民,无恶不作。凡是想在地方上混饭吃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于昌村派就得拜倒于水派下,否则就无进身之阶。”[21](P64)从这个回忆大致可看出,昌村派和于水派分别是由不同的姓氏宗族联合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政治派系的社会基础分别是不同乡村的宗族势力。这意味着当时于都县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已经超越了村落和姓氏宗族的范围,而在更大的范围及更广泛的社会人群之间展开。当然,这两个政治派系的斗争又集中反映在双方精英人物之间的斗争上,即昌村中学师生与于水中学师生之间的斗争。[21](P64)
可以说,土地革命前夕赣南各地的派系斗争十分普遍和复杂。如在大余县,晚清之际即已出现了分别以城区士绅和乡区士绅为首组织的“忠良祠”与“众志局”两个派系。为了左右地方政治,他们互相倾轧,斗争激烈。到民国16年,该县又出现了“三师”与“四中”、“四大金刚”与“十八罗汉”等地方派系,他们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22](P71)又如在瑞金县,以地主豪绅为首的“三虎”、“六豹”、“十二狼”,是当地最大的几个地方势力集团,他们把持着瑞金县的宾兴会、桥局会和考和会等三个最大的公堂;有的地主豪绅则以“土围子”等军事堡垒为基础,组织民团、团防、靖卫团等独立武装,盘踞一隅,不断扩充势力,瓜分地方权利。[23](P9)在兴国县崇贤乡,地方派系斗争则发展到同一所学校的两派学生当中,如兴国籍的早期共产党人李挺回忆说:“(崇贤高初两级小学)学生多系本乡地富子弟,学生中形成两派斗争,即‘山地派’与‘平地派’的斗争。这些斗争常常是以山区、平地出身贫寒、学品兼优的学生联合起来,使大地主纨绔子弟陷于孤立而告终。”[20](P134)
这些形形色色的地方派系斗争,固然直接表现为地方政治精英之间的争斗,但由于各个派系各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如村落的、姓氏宗族的、师生关系的等等),因此,派系上层分子的斗争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派系分化和派别界限。那么对于在当地发动革命运动的共产党人来说,正如丘倜回忆所指出,如果不打倒派系上层分子(如土豪劣绅),肃清各社会群体“狭隘的”派系观念,也就无法团结更广大的社会力量以发展革命运动。[21](P64)这就说明,地方政治派系斗争对于土地革命运动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五、结语:革命者的办法与研究者的方法
综合以上考察可以看到,在土地革命前夕的赣南农村地区,人群的分类和社会的分化十分复杂,除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外,还有土客籍的分立对抗、宗族割据和家族主义的盛行,以及地方政治派系林立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问题。这些错综复杂的农村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既构成了土地革命时期赣南乡村地区复杂的社会形势,也使土地革命斗争受其纠缠而充满了复杂性,可以说,在革命地区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土地革命斗争并不完全表现为单纯的阶级斗争,还有可能表现为不同社会人群或族群之间的斗争。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边界地区这种复杂的社会形势,当时毛泽东、陈丕显等共产党人不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而且还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采取了灵活、有效的办法来处理这些社会矛盾关系,尽可能地利用其有利的因素,避免其不利的因素,以推动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例如,当年领导赣南山区游击战争的陈丕显曾这样回忆当时党的工作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像钉钉子一样,一步一步地钉牢在这一带,深深地扎下根子,把赤白交界区变为赤区,把工作推向平原。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红军的群众纪律,努力消除赤区的人民与白区的人民之间隔阂。……‘天下穷人是一家’,大家都有责任向贫苦农民宣传,介绍好的对象加入组织(贫农团)。……对于那些来自外地的‘客户’,不能歧视,要团结帮助。并且告诉大家,运用多种多样活动的方式,交朋友,结同庚,或者通过宗族关系、社会关系广泛地团结群众,一起战斗。”[9](P60-64)在这里,共产党人以阶级斗争路线为思想指导,强调“天下穷人是一家”,其目的就是要淡化和消除土客之间的族群界限,乃至地方宗族之间的姓氏界限,强化人们的阶级意识,以便调动尽可能多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同时也利用乡村社会既有的文化资源,如宗族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等,“广泛地团结群众,一起战斗”。而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有力地挫败政治对手,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非常明确而坚决地坚持运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革命办法来处理土客矛盾和地方主义问题。他认为,“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并且明确指出:“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地主阶级搞起来的,天下穷人是一家。……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著,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总之,要强调土客籍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都平等。”[10](P310-342)实际上,当时的敌对势力也在利用这类社会矛盾对付革命力量。如据陈奇涵回忆,在兴国县的早期革命斗争时期,“兴国的反动商业资本家就不惜资本,利用封建的氏族矛盾,乘机收买了闽赣边境惯匪段起凤十兄弟,以及竹坝的部分落后农民,在四月间举行了反革命进攻,捣毁了党的领导机关和县总工会。接着,其他的工会、农民协会和学生会也都遭到严重破坏,兴国革命暂时转入了低潮。”[19](P7)由此可见,在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中,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对垒,并不全然是介于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不平等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各种社会的、文化的因素经由敌对双方的策略性途径而卷入其中。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如上所述,作为当时的共产党人或革命者,他们采取“阶级斗争”这一新型革命理论和策略来发动和领导土地革命斗争,本身是对当时边界地区复杂形势的一种因应,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土地革命斗争的复杂性。但是,作为研究者,除了要注意到这场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策略背景外,还必须意识到这个被强调的“阶级斗争”背后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复杂的历史内涵,这就要求:在对土地革命运动进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研究的同时,应当引入其他社会矛盾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分析。也许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深入而具体地揭示土地革命复杂的社会历史内涵,因而对它才能有完整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也只有从革命进程中具体的社会历史事实(而不是抽象的阶级概念或意识形态)出发,才有可能丰富“阶级”或“阶级斗争”概念的社会内涵,发展其理论解释力。总之,笔者以为,要达到此目的,就应该转变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即从传统的革命史(或党史)的研究视野转向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从赣南(或其他革命地区)本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传统出发,把土地革命史的研究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传统的乡村社会环境与现代的土地革命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注:事实上,随着“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强调革命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可以说是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正如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在1993年的一次报告中指出:以前对革命史的研究和对社会的研究是互相脱节的,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不注意吸取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以致难以对中国革命作出完整、深刻的解释,因此他强调应该从社会史的角度加强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参见范力沛:《西方对中国革命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第2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62页。另外,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早在20世纪70年代讨论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时,就曾萌芽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即认为只有把党内领导层的斗争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才能“明白什么是中国革命——那是在江西时期开始形成的一场巨大的社会运动”。这既是一个值得注意和强调的学术思考,也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实证的研究课题。参见Philip.C.C.Huang.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Society,1927-193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具体历史问题。
标签:土地革命论文; 赣南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矛盾论文; 农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