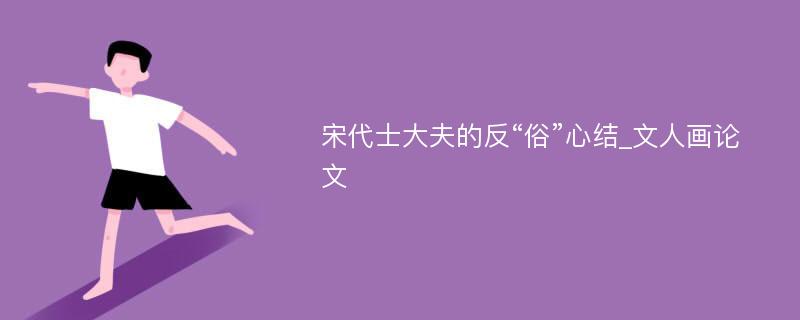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反“俗”心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大夫论文,心结论文,宋代论文,文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士大夫文人的自信不但体现在对时政的关注与积极参与,对高尚人格理想的追求,同时也表现在对文化艺术活动与日常生活中的高雅品味与情趣的重视。通过对宋代士大夫文人关于“文人画”的理论表述及其对“小词”的复杂态度的分析,本文企图说明宋人对“匠技”与“俗”的反对,一如对“雅”的崇尚,生动反映了宋代士大夫文人这一享有特殊地位的新社会群体对自身价值的敏感的体认,也表现了其作为文化精英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一、“离画工之度数”:宋代文人画之要义
宋代文人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所关注的远不只是艺术形式问题(文人画在形式体制方面的具体规定要到元明才完成),要界定文人画,就不能将目光局限于画本身,只计较其风格法度,而必须将其视为一种复杂的文化活动,详细考察决定其性质的三要素,即文人画的作者、过程,及其目的功能。
先看作者,苏轼的“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①,说的虽然是古往今来的“画师”,实际上指的就是其理想中的文人画画家。在其称赞燕肃山水画的一条题跋中,苏轼又说:“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② 两段话说的是一个意思:真正的文人画画家必定脱俗,而脱俗的标志是远离画工而向诗人靠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轼看来,作画的技巧,即所谓“画工之度数”,对提高画品不但毫无帮助,反而是画家必须克服的障碍。一个理想的画家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便只能用诗的境界才能言说比拟了。
如此看来,文人画画家首先必须是诗人,而不是画画的人。这便点到了文人画的本质。“画者,文之极也。”“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③ 士人能诗能文,自然晓画。苏轼的高人不学画之说,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高人岂学画,用笔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④
诗中后两句用《庄子·达生》篇典故,善游之人视水若无物,自然能操舟若神。同理,既然士人能诗能文,更能书——“用笔”是他们一生浸润其中的勾当,“乃其天”——挥毫作画自亦当若神。结合上文所引的几段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人画画家本是文士诗人兼书家,稍一放手,便又成了画家,或者换句话说,作画不过是其才识性情的扩展与延伸。倘要论画,本来职业画家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在技法上有几乎不可超越的优势。现在文人画画家要用他们的看家本领书法来置换画技,画工与院体画家们的优势竟顿时丧失殆尽。轻松一句话,文人画画家这个“高人”就将作画的“话语权”从职业画家手中抢了过来。
可见,苏轼这几句诗的要害并不在于鼓吹士人无须学画,而在于把绘画在技术层面上的种种因素皆统摄于“用笔”之下。经过历代文人千锤百炼的书法本来就具有精神性与抒情性,极具抽象表现力。无怪乎韩愈评论张旭草书的那段文字,读起来恍惚是画评。如今宋代文人画的倡导者提出以书入画,强调笔的书法审美价值,这就意味着书法的气韵及其抽象表现力在绘画中将起决定性作用,也必然导致文人画重意轻形、就约舍繁的倾向。文人画与职业画家的画,“高下”立判: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宋子房]真士人画也。⑤
这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出现“士(文)人画”一词的有关论述之一,治画史者耳熟能详。当年九方皋相马,为了抓住事物的本质,竟至牝牡不分,骊黄不辨,换来伯乐一声太息。苏轼以此寓言来说明文人画画家不主形而专主神的道理,自然十分传神。不过,其言语间似乎还有一层意思至今没得到充分揭示。辨别公母骊黄之于九方皋,是能为而不为之。文人画画家面对物象时只“取其意气所到”而不计皮毛,“俊发”则俊发矣,但那种使绘画者得以逼近“形似”效果的雕虫小技(即今人所谓“绘画基本功”)之于“士人”,究竟是能为而不为之,抑或是不能为却大大方方地宣称不屑为之呢?耐人寻味。笔者拈出这一点来,并非吹毛求疵:士人“不能为而不屑为之”的轩昂高妙,很能说明其凌驾于画工画匠之上的那种理所当然且不容分说的心理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于宋人画论中可以说无处不在。凡欲褒扬,便称“拔俗”,“远俗”,“一洗工气”;凡欲贬抑,则有“鄙浅可恶”,“未脱工气”之说。高者“非俗画所能到”,下者“未免画家者流”。显然,宋人衡量一个文人画画家的首要标准是“不俗”。而“俗”或“不俗”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有无“工气”。“工气”为何物很难状写,但大致指的是有工巧之技而无神理意趣。所谓“曲尽其态,然工巧有余,而殊乏高韵”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只画工画匠,就连受过良好专业训练、供职于宫廷画院的院体画家,亦只是一个“俗”字。
其实,宋人对“俗”的批评,矛头所向,主要是院体画家,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当中某些沾染“俗气”之分子(文人的画并不一定就是“文人画”)。画工与士人的巨大区别一目了然,无搅乱阶级阵线之虞。而服务于朝廷或供职于宫廷画院的职业画家,大多经过专业训练,不少人具有一定文化素养⑦。胸襟趣味虽与士大夫文人尚有距离,但却有进出士人圈子的机会,以捍卫文人画纯洁性为己任的士人对这些人特别警惕。至于文人士大夫队伍之中的个别“鄙俗”人对整个群体的潜在破坏作用,更是让士人不敢掉以轻心。要认识这一点,只须看看李公麟的事例。
李公麟系北宋颇负盛名的画家,“家世业儒”,本人也登第入仕,与苏轼、黄庭坚等人过从,有文名。但就是这样一位正牌的士大夫文人,是否有资格被视为文人画画家,居然还相当有问题,原因是其有“不能远俗”的嫌疑:
伯时(公麟)痛自裁损,只于澄心纸上运奇布巧,未见其大手笔。非不能也,盖实矫之,恐其或近众工之事。⑧
其罪过是只会“运奇布巧”。李这种精致奇巧是“俗工或可学焉”⑨ 的鄙俗事,当然不能见容于正统文人画画家,难怪李的好友米芾也要因之对李侧目。据说米芾曾提到过“伯时病臂三年,予始画”⑩。听起来好像自谦为后学,实际上是暗示与李相比,自己乃后来而远居其上。个中原因无他,按米芾自己的说法,“李笔神采不高”,“以李尝师吴生(吴道子,在士人眼中还只能算“画师”一个),终不能去其气,余乃取顾(恺之)高古,不使一点入吴生”(11)。《画继》作者邓椿称“其木强之气,亦不容立伯时下矣”(12),实乃春秋笔法,直是在遮掩米芾对李的蔑视。
有了对文人画作者的一番了解,就不难认识决定文人画性质的第二个要素,即创作过程。文人画画家既要“俊发”而“浑然天成”,其作画时就不会正襟危坐以“运奇布巧”,而更可能是随意命笔。据说米芾就曾亲见苏轼如何“以酒为神”,即兴挥毫(13)。黄庭坚也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14) 又有甘氏风子,虽身世不详,其作画过程倒是典型的文人画画家派头:
酒酣耳热,大叫索纸,以细笔作人物头面,动以十数,然后放笔如草书法,以就全体,顷刻而成,妙合自然。(15)
画家文同的外孙张嗣昌也因“每作竹,必乘醉大呼,然后落笔”而留名画史(16)。以上诸例均缺不了酒,酒能让作画人忘乎所以,从而更无拘束地表达出不经掩饰的自我。这与作画过程的即兴性,以及材料选择的随意性(或纸或壁,或纤毫细管或垩帚)倒也一致。作画人如此解衣般礴,虽不好说是刻意为之,但人人如此,每事如此,而当下的旁观者及后来的议论者亦跟着如痴如醉,就不禁引人思索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文人画画家作画时显露出来的飘逸高蹈已经成为一种程式化的姿态,一种旁若无人,傲然不与俗子为伍的姿态。这种伴随着整个创作过程的似有意似无意的姿态肯定左右了作画人的情绪,并最终在作品里留下痕迹。文人画之所谓不俗与职业画家之所谓俗,与其完全不同的创作过程大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画之过程亦是内容,应被视为其整体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至此,宋代文人画的第三个要素,即其目的功能,已差不多不言自明了。首先,无论抽象具体,画不是事物的摹本。对有些画家来说,甚至连神似形似问题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画家只要能通过画的过程显出个性,宣泄情感,就连“神似”什么也无所谓了。其次,既然是士大夫文人诗文才识的外溢延伸,文人画便自是“自公之暇固有琴樽书画之乐”(17) 之一乐。苏轼曾说:“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18) 即如前面提到的严格起来还不能算是地道文人画画家的李公麟,也要强调“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奈何世人不察,徒供玩好耶”(19)(后半段话最妙,一副为自己开脱,极力要与“俗人”拉开距离的委屈模样)。与“宋画院众工,凡作一画,必先呈稿本”(20) 的窘迫相比,文人画画家的自在就更见“拔俗”了:“时时寓兴则写,兴阑辄弃去。”(21)又每每说不是作画,而是“墨戏”(22),是“聊游戏笔墨以玩世者”(23)。
综上所述,文人画是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不能以“文人画的画”一言蔽之。那么,为什么文人作画古已有之,而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却要到宋代才兴起?
宋代士大夫文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以政治文化精英的面目在历史上出现,即便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个值得大书特书、值得每一个社会学家深究的现象。其原因及意义已有定论,兹不赘。这里要强调的是,宋代士人的高度学养,借助于其所享有的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使其有可能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同时也在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中大显身手,在诸方面多有反思、探索与开拓。绘画既是宋人乐此不疲的公余雅事之一,又是与传统诗文这种经国之大业有密切关系的艺术门类,士大夫文人当然也要在其中见出功夫。与此前文人画家不同的是,他们不满足于通过对“绘事”的揣摩学习与熟练掌握以求最终成为绘画能手,相反,他们以不谙技巧“度数”、不是专家为荣。说他们是业余画家大致不错,但宋代之前的文人画家亦多是业余,宋人的业余大有不同。这是广义上的业余,却又是最彻底的业余(24)。不只是不以画为业,更是在技巧体制上不斤斤计较;不“认真”,极随意;不为画事而惶惶不可终日,甚而至于视画若无物,画与不画亦无甚关系。就说竹吧,在纸是竹,在胸亦是竹,从破壁凹凸痕中“自现”出来的又何尝不是竹?“已发”、“未发”耳,只要吾人浑身是竹便足矣。宋人于此倒是深得庄子三昧。这也可佐证笔者在前面指出的,文人画的过程,即作画人之本身,生活本身,也是文人画的内容。
笔者以为,宋人的这种“业余”还有一层意思。业余人必须与“正业”之外的“旁业”中人(此处即“画业”中人)洗清关系一“一洗工气”,“离画工之度数”是也。不可否认,士人业余画家要与“业中人”撇清,有其艺术上的考虑。写意的士人,当然要避免沾染某些画匠的斤斤于琐碎的习气。画工以画为生,需为稻粱谋,院体画家还得仰人色笑,他们画出些俗物来不可避免,文人画画家因此与之划清界限也可以理解。士大夫文人的这种态度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即文人对技艺手工的不屑与轻视。笔者一直怀疑,法国文化史学家谢和耐提出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起自宋而迄于今的“纯知识者”对体力之事的“根深蒂固”的蔑视(25),是否就“滥觞”于此?
因此,事情看来并没有那么简单。文人画画家对“俗”的极端不耐烦,恐怕并不全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其中还掺杂了别的东西,没那么单纯。我们今天看得到的画论,均站在文人的立场。对“俗”的批判,言之凿凿,大义凛然,可是被批判的一方画工及“画家者流”却集体失声。他们根本就没有解释抗辩的机会。是不是凡工匠凡“画家者流”必俗?“俗”与社会地位低下有无必然联系?对“工俗”的判断有没有什么较客观并具操作性的标准?有些在画论中说得很轻巧的东西,在实践中如何具体实行?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宋代文人对画事的大力参与和前代文人不尽相同。宋人特别不能接受职业画家基于画技的价值取向,又不屑于与这些人“竞技”。他们对“俗”的种种看法,便既有合理因素,又常带有情绪性的内容。所以画论里的一些说法,不能看得太绝对。洪惠镇就指出,所谓院画也不是那么整齐划一,并非都是一味求形。到了南宋更有梁楷(梁疯子)开创的笔墨简练的写意一派(26)。虽其笔墨与文人画仍有不同,但终为写意。其“俗”耶“不俗”?文人画画家也不总是那么排斥形之细微末节。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27),可是据岳珂《桯史》记载,他自己看画时,却连画中人发音的口形都不轻易放过。又周煇《清波杂志》提到米芾曾欲以自己的临摹本偷换向人借来的一幅牛图,却因其摹本忽略了原作中“牛目有童子影”的细节而被人识破。言论者对此津津乐道,不能掩饰其对“牛目有童子影”的深深敬意,米芾本人虽未看出“童子影”,但显然并不觉得原作在整体上表现出来的对形的极琐细的追求是“工俗”,要不怎会爱到企图将其掠为己有的程度?
其实,画作之俗与不俗有时很难说得清楚,不是检查其用笔如何,“神似”(“神似”此物又要如何把握?)与否就可以了然。倒是画家身在哪一个阶层这一确切无疑的事实更会经常影响人们对画作之价值的判断。最早对文人画作系统研究的美国学者苏姗·布什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认为苏轼对文人画的论述所使用的并不是艺术批评的概念,所以总体来说不是艺术流派意义上的界定,进而提出苏轼是“以社会(学)概念来定义绘画的第一人”(28)。布氏的看法似乎过于肯定。中国古代文论画论用的是文学语言,不喜意义相对固定的概念“范畴”语,语体上又多为印象心得式,布氏大概不是十分习惯。其实苏轼的有些论述,如上文讨论到的其对用笔的看法,尽管尚嫌简略粗疏,但已涉及艺术形式问题。不过布氏的洞见还是不可抹杀,她毕竟嗅出了文人画理论中某种牵涉到社会阶层意识而与艺术无关的内容。她的说法是否有道理,我们不妨看看下面的例子:
尝有显人孙氏,知[李]成善画得名,故贻书招之。成得书,且愤且叹曰:“自古四民,不相杂处,吾本儒生,虽游心艺事,然适意而已,奈何使人羁致,入戚里宾馆,研吮丹粉,而与画史冗人同列乎,此戴逵之所以碎琴也。”(29)
李成何人?这是个“善属文,气调不凡,而磊落有大志”之人,只因才命不偶,才一生不得仕,成了专业画家。他的愤懑在于“吾本儒生”,却被当作“画史冗人”。令人惊异的是,自己因社会地位低下而大志不为人知,居然又要将“自古四民,不相杂处”之偏见视为铁律,深信不疑!他是不是该与“画史”“杂处”,是俗是雅,何人问去?
英国艺术史学家克雷格·柯鲁纳斯更直截了当地对“文人画”的概念本身及其相关理论表示怀疑,认为文人画画家与职业画家之间的界限不好成立。“米友仁这样的人物究竟是‘文人’画画家还是‘宫廷’画家?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简单答案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有错。”(30) 文人画的概念很复杂,是不可胶柱鼓瑟,但若因此就否认其存在,恐亦失之偏颇。不过,柯氏随之而来的假设却令人深思:“或许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人人都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可以夸耀,才使得那种将‘文人’画与‘画匠’画横加区别的理论在十一世纪变得绝对化起来。”(31) 说得很晦涩,但隐隐约约地,似乎在暗示,有关文人画的纠葛其实与阶级意识有扯不断的干系。
二、“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宋文人词之雅俗
宋词也是雅俗争锋的一个阵地。这个题目,有关著作汗牛充栋,甚至在欧美汉学界也是一门“显学”,这里无须再泛泛地复述。但看过了文人画,再看宋词,捡出几条大要来考察,虽挂一漏万,有些问题或许能因此看得更清楚。这也是本文选取二者作为可以相互对照的案例的原因。
文人画的情况与词的情况有可比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二者都牵连到士大夫文人圈子之外的画匠、院体画家和民间词人、歌妓、乐工。词起自民间。最早的作者歌者与听者都来自下层,处于传统文化、伦理势力范围的边缘,原本就很少感受到来自以厚人伦美教化为宗旨的诗教的压力,词作所歌唱鼓吹的虽然不全是“言闺情及花柳者”,但在总体上艳情化的倾向很明显(32)。这种无高雅趣味的胡夷里巷之曲通过娱乐场所向四方传播,并经由私家筵宴等渠道渗透到上层。其长于言情的丰富表现力与感染力诱使文人也加入了创作者的队伍。从唐五代起,无数文人写了无数的艳词。他们寄情声色之作的浓艳比民间词更甚。当然,文人与民间作者毕竟不同,在实践中亦能从表现形式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对词体加以改造。措词语气较雅致,表达较含蓄,在个别词人的作品中可见题材的扩大,甚至风格上也开始有多样化的迹象。但此时的文人词主要还是以女色为中心,以满足感官刺激的行乐为价值追求,在趣味上依然不能脱艳俗。可以说,是文人词作者跟着都市娱乐文化的大流走,而不是相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代才有了变化。
变化的原因是,宋代文人词的作者与前代文人已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群饱读诗书,素养极高,在科举制度完善之后通过国家人才选拔过程的严格筛选才进入社会政治核心阶层的文化精英。这些人具有此前任何时代的文人都不能比拟的政治抱负与道德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不只涉及现实政治生活,更包含了弘扬传统文化的内容。美国史学家包弼德在给他那本讨论唐宋文化转型时期的士人的专著命名时,使用了“斯文”一词的英文“硬译”:“我们的这个文化”(33),硬是把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刻画了出来,可谓入木三分。此前的文人虽也多忧国忧民,但只有到了宋代,作为一个享有政治特权的社会群体出现的士大夫文人才真正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斯文”。当然士大夫文人也是性情中人,加之受世风影响,也会写娱乐遣兴的“小词”,但这种属艳科的文学形式之“艳俗”与传统文学的雅正在价值观念上的格格不入,他们了然于心。对宋词的改造或“雅化”也必然在他们手中完成。
“雅化”可以是“诗化”,词向诗靠拢。北宋改造词体最力的苏轼诗化了的词,夸张地说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凡诗的任务,词都能担当。“雅化”也可以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34),意境深厚,清丽典雅。虽还坚持“诗庄词媚”的原则,但骨子里也是向“诗言志”传统的一种回归。及至南宋,辛弃疾既能“以文为词”,大声镗鞈,又能浑厚沉郁,曲折尽情,词成了可论道可表情的理想的“陶写之具”(35)。至于姜夔的清空,吴文英的质实,则是词之精致的潜在表达力在骚雅化一路走到了极至。与早期的市井民间词相比,词竟然已面目全非了。极而言之,通过词的雅化,士大夫文人不只将词的话语权,甚至最终连创作权也夺了过来。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文人画画论中的画之“诗化”说。尽管文人画的诗化是从方法上入手,其内容所强调的是画不应为技艺,而应是“言志”式的表达抒发。但从其强调拔俗,强调“离画工之度数”的角度看,词人非俗士与“画家非俗士”,异曲同工。
要进一步领会词之雅化的实质及意义,可再检视柳永的事例。
李清照是这样评价柳永的:“……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36) 语中俨然有柳为数百年一遇的天才之意。何故?其词“协音律”!鉴于李关于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之最重要的依据是其严格的音律,晏殊、欧阳修、苏轼这些“学际天人”的词因为不协音律,在李“听”来只是“不葺之诗”,不能算词。而对柳永,李则明白无误地肯定其“变旧声作新声”开创词作新局面的重大贡献。与晏欧苏诸人比,柳不知高出凡几,是本色的大家。可惜他有一个毛病,“词语尘下”(37)。上半句刚褒其为大家,下半句马上贬其“尘下”。细看来,与“协音律”的评价不同,“词语尘下”非关艺术形式,而是指趣味。借用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苏珊·布什观察苏轼画论时的说法,李清照说的“尘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概念,丽属于社会文化价值判断。
李的批评很有代表性。宋代其他评家论及柳永,用的几乎都是这个模式:词中高手,但词语尘下。比李更甚,他们还进一步点明其“尘下”的要害是“俗”。徐度说“流俗人尤喜道”柳词。王灼说其词“浅近卑俗……不知书者尤好之”。沈义父说其“有鄙俗气”。世传晏殊与柳永发生正面冲突的那个尽人皆知的故事,关键也全在于俗不俗: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问:“贤俊作曲子么?”三
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38)
这个众多论者再三引用的例子的深意,似乎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柳三变说,咱们彼此彼此,晏相公正色曰:否,你我根本不同道。汪据是柳写过“针线慵拈伴伊坐”。“针线”一句出自柳的《定风波》(“自春来”)(39)。全词读起来其实像闺怨。晏殊不提上片“暖酥消,腻云亸”的香艳,却偏挑下片“针线”的毛病。然思妇渴望跟夫婿在一起的亲热,好像并不怎么“尘下”。分析起来,只能有一个解释。晏殊并不把这首词当闺怨词看,他认定,既然柳以尘下的艳词闻名,只要一动到男女,就指向与“鸳鸯绣被翻红浪”(40) 有涉的猥亵。晏殊因此将“针线闲拈伴伊坐”视为柳永这个“伊”与他笔下大量娱乐圈中女性之关系的概括,看作柳对市民阶层下里巴人的价值观之态度的象征。“针线闲拈伴伊坐”是半贫不富的小家女子短浅的目光所能见及的幸福,又极自然地透露出词人与这一极平庸的市井女性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之间那种毫无间隙体贴入微的关系。这个极亲昵的相互融为一体的象征性姿态,晏殊显然没有放过。
假如柳永只是个活跃于《东京梦华录》中所见勾栏瓦舍里的词人,无论其如何“尘下”,晏殊也不会在意。刘克庄讥笑柳“有教坊丁大使意”(41)。“丁大使”必定俗,然而无人追究,倒是只有其“意”的柳三变惊动了士人卿相。原因很简单,柳出身世宦之家,本人也是士大夫队伍中的一员,理应拔俗,却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同一条板凳上“伴伊坐”,这就立场尽失了。
宋代文人也写词,然“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42)。他们很清楚自己与市井歌妓乐工所代表的“俗”之间须有一界限。尽管他们的词作也免不了有士人与歌妓人等杂坐娱乐的描写,但认真一看,被娱者与娱人者的区别绝不混淆。再者,士人总将自己的“小词”归为“空中语”(43),忍不住写了,也要“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44)。柳永不同,不自扫其迹也罢,还要炫耀:“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45) 斥其“卑俗”的王灼说:“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46) 口气中是深深的憾与痛。“脱村野”在此无任何褒义,村野尚有朴素,不失根本,而一个士人若沦为市井之无耻,便集利与欲于一身,俗已入其膏肓(47)。
前面讨论文人画时提到的李公麟还只是在技艺的追求上同情接近“工俗”的立场,就几被逐出文人画画家的阵营。柳永则在趣味与情感上都完全地“伴伊坐”到“俗”的一边去了。晏殊、王灼诸人的嗅觉灵敏而准确:在高雅与鄙俗的冲突中,柳永的行为使所有的士人蒙羞,他背叛了他所在的阶级。
三、忌俗尚雅:文化精英捍卫自身特殊属性之努力
宋人审美理想的主流是“平淡”,渗透于宋代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平淡”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在南朝出现时还带有非正面的意义。中唐皎然的诗论才将其提升为一种诗学理想(48)。其在宋代“成了压倒众声的主调”,“升格为文坛的核心范畴”(49),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不少学者认为是宋世“处于封建社会走下坡路”之际,“内忧外患”所致。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局限,很多相关的问题据此得不到解释。本文愿从“平淡”的对立面入手,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考察。
对某种理念价值的强调,总是意味着对其对立面的否定与批判。笔者认为宋人所崇尚的“平淡”的对立面就是“俗”。“平淡”并非只有一种风格,一个面目,如此才能成为个性不同的创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宋人所热衷的“简”、“清”、“老”、“野”、“拙”等等都是“平淡”之不同侧面的具体内容,其内涵有细致的不同,但有意思的是,追究起来,它们大致都可以用“不俗”来解说。
“简”是大音希声,“清”是出淤泥而不染,其“不俗”的意思较清楚。“老”、“野”、“拙”呢?宋人关于“老”的言论不少。苏轼云“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可见平淡“其实不是平淡”(50)。从内涵上说,“老”是“天凉好个秋”的从容与不矫揉造作;从方法上看,是梅尧臣“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51) 之“难”的境界。其反面就是不识愁滋味之少年的“浅”,与“好风花”之“后生”的“俗”(52)。其避浅拔俗的味道就在于此。至于“野”,子曰“质胜文则野”,“野”虽失之过“朴”,但同时亦就免了绮腴鄙俗之病。吕本中说:“初学作诗,宁失之野,不可失之靡丽;失之野不害质,失之靡丽不可复整顿。”(53) 戒俗之意切切。风雅之士喜自称“野人”,也是取其不俗的意思。“野”又与“拙”相关。包恢说:“野近于拙”,认为“野”有“拙趣”,可纠文病(54)。“拙”回头又可转注“老”,老杜的“老大意转拙”(55),虽非言诗,亦有此旨趣。
可见,“平淡”与宋代忌俗尚雅观念互为表里。正如王水照指出的:“到了宋代,‘雅俗’作为评价人格及文学艺术方面的标准,更为突出和强调,从而成为成熟恒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56) 宋代尊平淡而反俗的风气,不只及于传统诗文,也见于书法、绘画、文物收集鉴赏、园林、茶艺、琴、棋等文化艺术活动与日常生活雅事中。作为左右时代风气的文化精英,士大夫文人心中大多有一把衡量雅俗的尺子,自觉规定自己的言行。苏轼“士俗不可医”(57) 与前引黄庭坚“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的谆谆告诫,均是明证。
这里就不能不谈到所谓宋代文学因处于新的社会形势而出现的“雅俗贯通”现象的问题。“贯通”若指雅与俗可以共存,有接触有相互作用,则可。若指融汇甚至合流,似有问题。有宋一代,确有“雅”与“俗”共存的现象。如前文所述的文人词、“柳永词”、乐工词之共存,或文人画、画工画、院体画家画之并立。若无世传仁宗落柳永于功名榜之事,无晏殊对柳的奚落,无士人作了艳词又“自扫其迹”,无米芾之讥李公麟,无李成之受辱于孙氏,两者似可“贯通”。然而实际情况是二者之间摩擦冲突不断。有意思的是,这种冲突并不激烈,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暗中较劲。用“雅化”一词之“化”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从宋词的雅化到文人画的兴起壮大过程看,较劲的结果好像还是“雅”占了上风。
谈到“雅化”,还得说说有论者以宋人开始大量以俗事入诗,以俗字俚语人诗,即所谓“俗中求雅”的现象,来证明“雅俗贯通”确实存在的问题。此说是否言之成理,还得先弄清“雅俗之争”、“忌俗尚雅”的“俗”与“俗中求雅”的“俗”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个美学概念,含价值判断;后者用来指事,区分事物之类别。“俗”字有不同的含义,正如“俗人”既可指一般人,也可指见识趣味低的人。文人写进诗中的肉鱼羹汤、牛溲马渤等“俗世”中之“俗事”及所用“俗字”、“俗语”,其“俗”的含义是“世俗”、“通俗”之“俗”,而非趣味不高,浅鄙,或“庸俗”之“俗”。二者虽多少有点关联,却是全然不同的概念。“俗事”不必尽“俗”,端看你如何掌握。朱熹语录中使用大量俗语及俚俗表达法来说明“通俗”之理,粗通文字的福建人今天读起来还会受感动,然朱子岂“俗”欤?其实,宋代士人以“俗事”、“俗语”入诗,恰恰证明了宋人忌俗尚雅的精神无处不在。“俗中求雅”或“以俗入雅”是其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却不失其志的表现。文化精英之责任感常在其心,即使是在日常“世俗”生活的“俗事”中也要努力见出雅之大义,其“雅”心可鉴。
宋人孜孜于忌俗尚雅,事关能否保持其赖以生存的作为社会精英的自身特殊属性。科举制度在宋代的最终确立完善,使中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成为常态,但这并未导致阶级阶层之间界限的消失。寒庶俊造一旦晋身,对自身的新地位新特权的意识立即形成。维持其既有,便成了要务。譬如,在科举向读书人广泛开放的同时,却曾有严禁“‘大逆人’近亲、‘不孝’、‘不悌’、‘工商杂类’、僧道还俗、废疾、吏胥,犯私罪等人应试”之事发生(58)。这虽只是一时的有针对性的行为,未形成长期政策,但“工商杂类”、“僧道还俗”确曾被打入另册的现象,引人注目。约翰·查菲认为,这种做法的关键不在于限制哪类家庭出身的人的升迁,而在于绝不容许对士大夫价值观念有敌意之分子通过科举进入精英阶层(59)。前述士人之叛逆柳永不见容于士大夫,专业画家李成之“阶级归属”不明等,皆是佐证。
为了维护自身的纯洁性以保证本阶级的生存,除了排斥潜在异己之外,对已在本阶级中人不断鞭策鼓励也是一种做法。一个常为人忽视的事实是年谱的突然兴盛始于宋。为了表彰先进弘扬传统。宋人除了沿用碑铭墓志行状祭文之外,还致力于年谱的编写。宋人留下来的年谱不下165部,其中106部写的是文人士大夫(60)。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大人物各占9部。与此相关的是家谱修撰在宋代的复兴。从东汉到唐末,由于家谱在政府选拔人才豪门家族联姻及政治生活其他方面的作用,谱牒修撰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门阀制度在唐末五代被消灭,政府编修谱牒亦随之取消。及至宋朝建立,科举制全面实行之后,出身不再是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家谱遂也失去先前的重要作用(61)。有意思的是,就是在这种家谱式微的情况下,本无显赫家世而以寒庶晋身的士大夫文人一层却重新拾起了家谱。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间欧阳修和苏洵“不约而同”地编写了各自的家谱(62)。更重要的是,两人还对家谱修撰的传统方法作出了重大修正。欧苏所修的家谱使用的都是“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本家族始祖,五世一提(断),只记本支,各支别自为世,各详其亲(63),而不是历来那种追根溯源直至炎黄的“大宗之法”。这种做法体现了宋人求实的一面。如欧阳氏所称,“大宗之法”的弊病在于“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而如用“小宗之法”,世系“断自可见之世”,“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64),说得很有道理。但如论者指出,“小宗之法”其实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宋代士人不少出身卑微,一要追溯上始,大多不见光彩(65)。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既无显祖,为什么又要像前代门阀那般重视家谱?答案可能是,本家的荣光虽从近世今世才开始,但一定要得到传承。家谱修撰的重心很微妙地由追远转为慎终。一个处于上升状态中的生气勃勃的知识新贵的复杂心理,显露无遗。
温斯顿·罗在其对宋代科举及官制的研究中指出,除了在政府官僚系统中的作用之外,宋代士大夫还得扮演一个不可忽视的“形而上”的角色,即作为“国家民族智慧之积累的储备力量”与“保证这个朝代的合法性、权威、及稳定的伟大传统的传承者”。这个朝代需要“一个在性格气质上能比之于前代门阀的文官人群”(66)。士大夫因此被“授予”一种名望,一种“舍之其谁”的功能性特权。据此,士人对有损其气质或可能破坏其道德文化权威的来自各方面的“俗”的高度警惕与自觉抵制,就很可以理解了。兹事体大,关系到其作为精英阶层的存亡。科举制度与保证科名之外的吏胥不能僭越的严格的拔擢制度在“公”的层面从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的特权不受圈外人侵犯(67);在“私”的层面,如何维护士人赖以获得重大利益的“权”与“威”,就得靠士人自己的努力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士大夫文人这一新贵的自我阶级意识绝不逊于门阀中人。门阀生而贵,对与生俱来的种种特权只觉得理所当然,没有特别敏感的知觉,也不会有刻意追求高尚情趣的欲望。宋代士人的一切均来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身的努力。自下而上的提高如何不易,点滴在心。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对自身的价值与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和自信,但也有唯恐退步的焦虑。因此,他们在坚持对高尚人格的不懈追求,对学识的不断积累之外,还不忘日三省其身,问问自己是不是依然有高雅的趣味,依然超凡拔俗。
注释:
① 苏轼:《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② 苏轼:《跋蒲传正燕公山水》,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91页。
③ 邓椿:《画继》卷九,《学津讨原》本,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69页。
④ 苏轼:《次韵水官诗》,《苏轼全集》上册,第19页。
⑤ 苏轼:《跋宋汉杰画》,《苏轼全集》下册,第2194页。
⑥ 佚名:《宣和画谱》卷十五,《学津讨原》本,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第163-164页。
⑦ 关于文人画画家与文人士大夫画家及职业画家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的重要性,见洪惠镇:《中西绘画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245-246页。
⑧ 邓椿:《画继》卷九,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第71页。
⑨ 《宣和画谱》卷七,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第74页。
⑩ 邓椿:《画继》卷九,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第71页。
(11) 邓椿:《画继》卷三,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第14页。
(12) 邓椿:《画继》卷九,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第71页。
(13) 邓椿:《画继》卷三,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第12页。
(14) 邓椿:《画继》卷三,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第12页。
(15) 邓椿:《画继》卷五,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第33页。
(16) 释莲儒:《竹派》,《百川学海》本,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五册,第2页。
(17) 郭若虚:《图画见闻录》卷六,《四部丛刊》本,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第92页。
(18) 苏轼:《书朱象先画后》,《苏轼全集》下册,第2191页。
(19) 《宣和画谱》卷七,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第75页。
(20) 文震亨:《长物志》卷五《院画》,见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从书》第一册,台北:广文书局,1963年,第171页。
(21) 《宣和画谱》卷二十(写生墨竹二),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第253页。
(22) “米友仁每自题其画曰‘墨戏’”,邓椿:《画继》卷三,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一册,第19页。
(23) 《宣和画谱》卷十一,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第124页。
(24) 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在其对明清时代士大夫文人精神风貌的描述中,使用了“业余理想”(amateur ideal)一词,其要义是重“君子不器”,提倡完整人格之人文精神,并举文人画为例。列氏所谓的“业余理想”,其实在宋代文人画中已见端倪。见Joseph Levenson,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A Trilogy(《儒家的中国及其在近代之命运》),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5-22页。
(25) 见Jacques Gernet,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社会文明史》),J.R.Foster与Charles Hartman英译,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31页。与《孟子·滕文公上》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泛泛之论不同,宋人对体力之事的蔑视有具体的时代内容及深刻的社会原因。史学家刘子健对唐代盛行的马球运动如何因时代文化的变迁而失势于北宋进而衰落于南宋的精到分析,可以参考。见James T.C.Liu,“Polo and Cultural Changes:from Tang to Sung China”(《马球与文化变迁:由唐至宋的情况》),《哈佛亚洲学刊》(HJAS)总第45期(1985年)上卷,第203-224页。
(26) 洪惠镇:《中西绘画比较》,第59-60页。又见其《现代院体画》,《美术研究》2003年第1期。
(27)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苏轼全集》上册,第351页。
(28) Susan Bush,The Chinese Literation on Painting:Su Shih(1037-1101)to Tung Chi-chang(1555-1636)(《文人论画:从苏轼到董其昌》),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9页。
(29) 《宣和画谱》卷十一,见于安澜编:《画史丛书》第二册,第114页。
(30) Craig Clunas,Art in China(《中国的艺术》),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
(31) Craig Clunas,Art in China(《中国的艺术》),第141页。
(32) 参见刘扬忠:《北宋时期的文化冲突与词人的审美选择》,《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33) Peter K.Bol,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
(34)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52页。
(35) 范开:《稼轩词序》,见刘辰翁编,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61页。
(36) 李清照:《论词》,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0页。
(37) 李清照:《论词》,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0页。
(38) 张舜民:《画墁录》,见《稗海》卷一三二下,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年,第2页下。
(39)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0页。
(40) 柳永:《凤栖梧》(“蜀锦地衣丝步障”),《全宋词》第一册,第25页。
(41) 刘克庄:《后村诗话》,转引自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香港:中华书局,1957年,第27页。
(42) 黄庭坚:《书缯卷后》,《山谷集》(内集)卷二十九,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年,第8-9页。
(43) 黄庭坚语,见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7页。
(44) 胡寅:《向芗林〈酒边词〉后序》,《斐然集》卷十九,《四库全书》本;又见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288页。
(45) 《鹤冲天》(“黄金榜上”),《全宋词》第一册,第51页。
(46) 《碧鸡漫志》卷三,《词话从编》第一册,第34页。
(47) 宋人对“都下富儿”的不齿,在陆游的《放翁家训》中可找到注脚:“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之读书……但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戒之!”转引自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店,1974年,第94页。
(48) 韩经太:《中国诗学的平淡理想》,《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49) 汪涌豪:《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50) 苏轼:《与侄论文书》,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18页。
(51) 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傅璇琮等主编:《宋诗选》第五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71页。
(52) 范温《潜溪诗眼》有“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句,转引自韩经太:《中国诗学的平淡理想》,第189页。
(53) 吕本中:《童蒙诗训》,转引自汪涌豪:《范畴论》,第137页。
(54) 包恢:《书侯体仁存拙稿后》,载包恢:《敝帚稿略》,转引自汪涌豪:《范畴论》,第136页。
(55)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第二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89页。
(56)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50页。
(57) 苏轼:《於潜僧绿筠轩》,《苏轼全集》上册,第101页。
(58)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一),“科举制”。具体事实可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十四、卷三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五。
(59) John W.Chaffee,The Thorny Cate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60) 来新夏、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页。
(61) 来新夏、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第104一108页;连心豪:《宋儒与谱牒之学》,见周仪扬、陈育伦主编:《谱牒研究与闽台源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64-66页。
(62) 来新夏、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第109页。
(63) 连心豪:《宋儒与谱牒之学》,见周仪扬、陈育伦主编:《谱谍研究与闽台源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67-71页。
(64) 《欧阳修全集》下卷,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本,第517页。
(65) 来新夏、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第109页。
(66) Winston W.Lo,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of Sung China:with Emphasis on Its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宋代中国文官制度介绍:人事》),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2页。
(67) 如温斯顿·罗指出,在宋代,由吏晋升为官变得极为困难。而在此之前,吏胥与官之间的界线没有这般严格,吏升为官的情况并不罕见。见Winston W.Lo,An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of Sung China,第22-25页。
标签:文人画论文; 苏轼论文; 苏轼书法论文; 宋代绘画论文; 艺术论文; 士大夫精神论文; 文化论文; 柳永论文; 宋朝论文; 画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