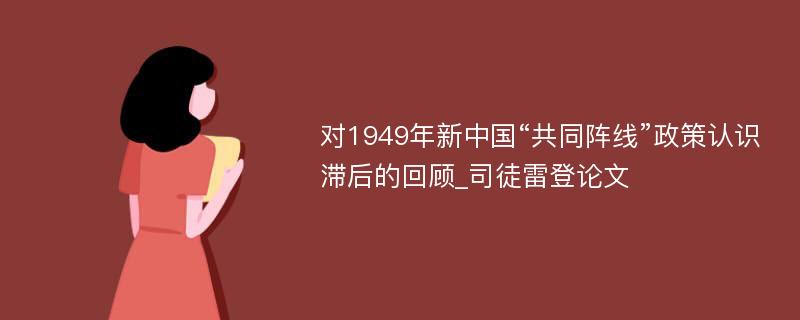
1949年美国延宕承认新中国“共同阵线”政策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阵线论文,美国论文,新中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围绕“承认”新中国问题,即是否承认,以及在何时、何种条件下承认或不承认新中国,美国政府推出了鼓噪一时的“共同阵线”政策。美这一政策不仅涉及新中国与美初期关系,也涉及当时数十个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因而对当时中美关系及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均产生过影响。国内史学界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对美“共同阵线”政策虽多有涉及,但尚缺系统考察。本文拟以当时中美关系历史和冷战格局为总背景,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美“共同阵线”政策为何推出?何时推出?又如何贯彻?其实质内容与其所追求的政策目标是什么?以及结果如何?
一
1949年春夏之交,中国内战结局日见明朗。中共军队继解放长江以北广大地域后,又于4月下旬强渡长江,夺取南京之后分兵东取沪杭、南取两广、西取川甘。中共替代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已势在必然。中美关系的主体朝中共与美关系的总方向急剧过渡。如何适应中国内战结局和中美关系主体的质变,是否承认即将问世的中共新政权,以及何时承认,予以何种形式的承认,便提上美对华政策日程。这导致美推出有关承认新中国问题的“共同阵线”政策。
率先主张推行“共同阵线”政策的是当时美驻蒋政权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949年4月29日,他从南京致电华盛顿,就美承认新中国问题发表意见,电文大意为:依据固有传统和公认的国际法标准,在承认问题上,是中共“处在被告席上”,美应推动“尽可能多的国家”,主要是北约、英联邦、拉美及东地中海各国,采取联合行动。5月初,司徒雷登又两电华盛顿,更明确建议:“基于策略原因”,美主动承认新中国“不明智”,应“等新政权迈出第一步”。为达此目的,最少要争取北约各国,尤其是争取美英法意四国一致支持。后两封电文还正式使用了“统一阵线(united front)这一提法。[1]综合这三封电文,在司徒雷登建议中的“共同阵线”政策,就有了大致轮廓。即在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美不应主动行动,应留待中共走“第一步”;同时美应推动西方各国与美联合行动,建立“统一阵线”(即“共同阵线”的原始提法)。
司徒雷登的建议立即得到华盛顿认可。5月6日,美国务卿艾奇逊依据司徒雷登之意,同时致电美驻中、英、法、意、比、葡、荷、加、澳等9国大使馆,表示国务院赞成司徒雷登建议,授权上述各处使馆官员就“共同阵线”问题与各驻在国政府会商。电文把司徒雷登建议中的“统一阵线”(United front)一词,改为“共同阵线”(common front)。此后,“共同阵线”便成为对这一政策的标准表述。关于“共同阵线”内容,艾奇逊概述为两点:(1)西方国家主动承认新中国或作出欢迎中共谋求承认的表示,都对西方国家没有好处;(2)西方国家应结成“共同阵线”。艾奇逊5月6日电表明美决策层正式接受了“共同阵线”政策并立即予以贯彻。
司徒雷登为何主张奉行“共同阵线”政策?华盛顿又为何作出积极反应?从相关各力量相互作用的观点考察,有两个因素值得强调:其一是美政策与中共政策的相互作用。其时美面对中国内战结局。正考虑如何从蒋政权这条沉船“脱身”,进而不得不认真考虑对新中国政策。当年2月问世的NSC34/2和41号文件提出,美对新中国的政策目标是“防止苏联为战略目的控制中国”,并规定相应的政治手段是与中国各方面维持“积极可行的官方接触”。艾奇逊据此指令司徒和驻华官员们“设法接近中共”,尽可能维持美在华外交存在。[2]美驻沈阳、北平等地的官员根据这一指示,先后与中共地方当局进行过不同层次的接触。南京易手后,司徒雷登未依惯例随接受国政策迁往临时新都,而是留驻南京并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这些做法分别被认为是美走向承认新政权的“第一步”,[3]或干脆被解释为是对新政权的“默示承认”。[4]综而观之,不论其动机如何,当时美决策人还不认为拒不承认新中国符合美国整体利益,还没有排除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不过,美决策集团自上而下,都认定美承认新中国不是双方对等往来,而是美对新中国的“恩赐”及美在政治上与新中国讨价还价的“杠杆”。在获得满意条件前,美不打算轻易承认新中国。[5]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长期受列强凌辱的痛苦历史,中共推出了民族独立至上的外交原则,具体执行时,便有“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间再请客”之说。[6]毛泽东明确提出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一切卖国条约的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7]根据这些原则,中共不承认美驻蒋政权领事人员的官方地位,将其一概视为侨民。又基于对美反苏反共世界政策及其支蒋反共历史的认识,在承认问题上,中共的立场是不急于谋求美承认。毛泽东又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8]中共决不会为取得美承认而放弃原则,迎合美方要求。于是,司徒雷登在南京以承认为“杠杆”,对中共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试探,一一碰壁。
促使司徒雷登提议实行“共同阵线”政策的第二个因素,涉及美与其西方盟国的关系。在承认问题上,美与其盟国有明显分歧。早在3月19日,英国就向美表示,基于英在华拥有巨大商业利益及香港问题,英打算尽早承认新中国。[9]英联邦成员印度和澳大利亚也作过同样表示。司徒雷登担心英等率先承认新中国,会促成中共“以夷制夷”,破坏美“杠杆”战略,因而要求华盛顿采取措施,约束它们的行动,阻止它们“见利忘义”,因短期商业利益破坏美对华政策大计。[10]他留南京的基本意图之一,便是为协调西方各国对新中国的政策。[11]
值得提及的是,恰当司徒雷登建议问世前数日,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英舰“紫石英号”在长江下游与中共军队炮战,英军死伤近百人。[12]中英一时交恶,给英尽早承认新中国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司徒雷登认为,该事件证实了中共对西方的“不妥协立场”,同时也增加了美英之间在承认问题上协调立场的紧迫性和可能性。华盛顿决策人物的看法,也大体如此。[13]
概而言之,司徒雷登提出,美国政府并接受“共同阵线”政策,一是为推行“杠杆”战略,施加压力,迫使中共在政治上向美让步;二是为约束英等西方盟国,使其在承认问题上,服从美国对华战略策略。二者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美认为只有西方国家联合行动,才能真正造成压力,迫使中共“就范”。
二
美“共同阵线”政策启动后,共分三阶段贯彻执行,各阶段的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也有差别。艾奇逊5月6日电,也同时标志贯彻“共同阵线”政策第一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美政策的基本特征是试探深浅,看各方面如何反应。
美各有关驻外使馆官员,接到艾奇逊指示电后,皆分头行动,与各驻在国政府有关方面奉行会谈,试探各国立场,并陆续发回会谈报告。司徒雷登更未雨绸缪,早在5月6日前,即已在南京多方活动。5月13日,国务院根据这些报告,对主要西方国家的立场作分析后,将之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意葡荷诸国,完全追随美国;第二类包括法加等国,有保留地赞成“共同阵线”政策;第三类是英澳诸国,不赞成“共同阵线”政策。[14]这一分析结果表明,美组织“共同阵线”政策的前景并不乐观。
尽管如此,国务院仍于5月13日再指示各有关驻外使节,要继续努力,争取与西方各国达成协议。[15]以后,美以会商形式,开始全面贯彻“共同阵线”政策。主要会商安排分三路进行:一在华盛顿,由国务院官员分头向各有关国家驻美使节做工作;二在南京,通过司徒向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做工作;三是由美驻各有关国家大使馆,直接与各驻在国外交部商谈。会商对象也由试探期的8国扩大到数十国,其中有北约英、法、意、加、荷、葡6国;英联邦印、缅、澳、新、巴5国;东亚和东南亚韩、越、菲、泰和印尼5国。以后又有土、希、瑞士、瑞典、埃及、巴西、伊朗和阿富汗等国相继成为美争取对象。不过,主要的会商只在美与英、法、荷及英联邦印、缅、澳等国间反复举行。其中美英会谈又居最突出地位。司徒雷登评论说:在承认问题上,英美一致最重要。[16]
针对不同国家,美所施策略各不相同。对东南亚缅、泰、菲等中国邻国,美喧染中共一旦得到承认并与东南亚各国建交,势必要利用其使领馆在当地培植“第五纵队”,宣传共产主义,从而威胁东南亚各国生存,同时又以美援为饵,诱其加入“共同阵线”;对法国以是否支持其在印支地位为杠杆;[17]对英国以是否助其继续占据香港作要挟;对英联邦各国则反复陈述过早承认中共如何于其不利。尽管如此,美国的努力仍不成功。除英、澳等国继续不肯合作外,一些原来表示赞成“共同阵线”的国家也发生政策变化。如法表示其在华无重大利益,仅关心印支地位,一俟中共表示“尊重双方边界”,法便承认新中国。[18]荷表示其立场须与印尼协调,而印尼承认新中国呼声很高。真正表示完全追随美国的只有菲、韩、泰、意等少数国家,但它们当时依附于美国生存,国际影响不大。总之,在第一阶段,美外交部门虽然紧锣密鼓,多方努力,其“共同阵线”政策仍无着落。
美推行“共同阵线”政策第二阶段始于7月20日。该日,艾奇逊急电美驻英大使道格拉斯,指示他面见英外相贝文,就承认问题“坦率地”告诉他,美对传言英接触中共官员,并向其表示“合作”意向不满。还要他明确以美在是否支持英国在香港地位问题上,拥有自由选择权这张牌,诱英支持美“共同阵线”的政策,以换取美支持与其在港地位。[19]
艾奇逊7月20日电表明美开始全力贯彻“共同阵线”政策,这其中原因大体有四:一是其时美正准备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国务院官员普遍认为,这一行动将震动美朝野及其盟国,其政策反响殊难逆料,美在承认问题上,更难有所作为,因而更不能允许其他国家承认中共;二是美对中共的政治战彻底失败。自5月以来,美国务院在推行“共同阵线”政策的同时,又指令司徒与中共代表黄华会谈,但双方立场相距太远,不能达成共识。[20]6月底,因司徒雷登访问北平计划受阻,双方政治联络渠道中断。此后中共加强了对美援蒋政策的抨击;公布了“沈阳间谍案”;以违反交通规则罪拘留了美驻上海副领事威廉·奥利夫;下令关闭美驻上海北平新闻处及其领事馆所属宣传机构。[21]中共与美关系一时急剧恶化;三是中共按国际统一战线原则,区别对待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收到实效。鼓噪一时的“紫石英号事件”已接近平息,[22]英、印、荷、法、澳诸国愈益倾向于尽早承认新中国;[23]四是毛泽东于当年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宣布中共奉行“一边倒”对外政策[24]美认为以政治承认为武器,离间中苏关系,影响中共内政外交的杠杆战略,一时无望成功。
美“共同阵线”政策第二阶段的基本特别是以英国为突破口,软硬兼施,全力诱迫英放弃其相对独立和较为现实的对华政策,参加“共同阵线”。由于英既是美冷战伙伴,又是北约主要成员和欧洲“头羊”,其背后还有一个英联邦,英在华经济重要性又居西方各国之冠,英如何动作,便举足轻重。一些国家期待英领头打开承认新中国的通路。也有些国家以英加入作为自己参加“共同阵线”的条件。因而争取英支持“共同阵线”政策,便成为美这一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
接到艾奇逊7月20日电次日,道格拉斯往访贝文,陈述美“共同阵线”政策,贝文却王顾左右而言它。稍后,贝文通知美说,英在承认问题上愿与美会商,但对是否保持一致,却不承担义务。[25]此后,美英就“共同阵线”问题举行过一系列会谈,包括7月末乔治·凯南秘访伦敦,与英国务部长海克特·麦克尼尔会谈;8月中英外交部次官助理邓宁与美驻英使馆官员会谈;9月初邓宁与美国务院官员巴特沃思会谈。9月中,贝文率团访美,与艾奇逊直接交锋,把系列会谈推向高潮。英坚持认为:(1)在承认问题上,最少应遵循西方与东欧诸国关系模式,[26]西方不承认新中国在政治上不利,法律上“讲不通”,会“严重损害”在华利益;[27](2)西方坚持不走“第一步”,会破坏推动中共“自由化”的努力;(3)为维持英在华利益和香港地位,英将承认新中国。对于美方诸多要求,英仅承诺在进一步行动前,先与美国相商。[28]但这一承认对急于组织“共同阵线”的美国并无实际意义。
在诱迫英国的同时,美并未放弃对其他国家施压。但除泰、意、韩等少数国家外,法、荷、印、奥等主要西方国家与英一样,继续倾向于承认新中国,不愿加入美“共同阵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外长周恩来照例函告各国,宣布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于是,承认新中国问题便由西方国家拟议中的外交难题转化为外交实践问题。西方各国分歧开始落实到外交实践中。10月5日,英复照新中国,建议在英领事官员与“中央人民政府辖区内的相应当局之间”,“先建立非正式关系”。[29]显然,这在国际法意义上,构成了对新中国“事实上的承认”,英对此亦自认不讳。不仅如此,英复照内容还暗示将很快予新中国以“法律承认”。除英外,荷、比、印、缅、加等国也对周恩来信函作了积极答复,表示将承认新中国。[30]而巴基斯坦、埃及等国,追随美国政策的色彩,则明显淡化。
凡此种种,使美“共同阵线”政策遇到新挑战。美政府内部这时出现不同意见,但占优势的观点依然坚持“不急于承认”新中国以及使西方各国保持一致的重要性。[31]即是说,新中国成立后,美继续坚持“共同阵线”政策,其具体内容也明确规定为西方各国一致行动,“不急于承认”新中国。“共同阵线”政策相应进入第三阶段。
为维持“共同阵线”政策,美继续向英荷印缅澳诸国施压。10月初,正值印度总理尼赫鲁访美,杜鲁门(Harry·S·Truman)与尼赫鲁会谈,称美希望“非共产党国家”在承认问题上“充分协商,一致行动。”[32]10月17日,国务院中国事务司司长斯普诺思约见荷驻美公使罗克林,指责荷偏离约定的政策。[33]对英10月5日复照,美更利用各种渠道轮番批评。10月11日,美国务院官员弗里曼、麦钱特专为复照事约见英驻美使馆参赞格拉沃批评英复照使用“中央人民政府”的称呼又不打引号,构成了对新中国“事实上的承认”,因而违背了9月英美华盛顿会谈精神。[34]10月14日,艾奇逊致函贝文,批评英复照有违“共同阵线”政策,事先又不与美商量。要求英如采取导向承认的新行动,务必知会美方。杜鲁门针对英复照,恼怒地评论说:英国人“很不够意思。”[35]
美高压政策照样一无所获。英、加、澳、荷、印各国皆为其立场辩解。澳认为不承认新中国会损害西方地位,不如使用承认“杠杆”,通过谈判促使中国尊重邻近地区安全;印强调印中毗邻,历史命运相近,因而印需尽早承认新中国;荷推说其政策模仿英,而英坚持承认新中国合情合理,表示要“尽快”承认,并宣称在承认问题上,各国有权作出最后判断。[36]12月1日,英照会美宣布将于12月中旬承认新中国。在此前后,加、印、荷等国相继作出类似表示。
面对诸多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的潮流,艾奇逊只得在12月8日会见英驻美大使弗兰克斯时表示:西方各国在承认问题上应相互协商,却不必承担一致行动的义务。各国利益不同,可根据其利益,自行作最后判断。[37]即是说,艾奇逊代表美政府承认“共同阵线”政策失败,并予以放弃。
1949年12月底,缅甸率先宣布承认新中国。稍后不到一个月,印、巴、英、锡兰、挪威等10余个国家相继宣布承认新中国,美苦心经营8个月之久的“共同阵线”政策终于彻底破产。
三
美“共同阵线”政策失败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其一在于西方盟国不与美合作,所谓“共同阵线”其实是美国在唱独角戏。
1949年美是从全球战略高度看承认新中国问题的。战后美奉行冷战政策,反对一切社会革命。与此相适应,美深深介入了中国内战。在支蒋打内战的同时,又从蒋政权处攫取巨大利益。国民党失败,既是美对华政策的失败,也是美反苏冷战政策的重大失败。美由此可能丧失其在华权益,其战略态势也受到极大削弱。面对即将掌权的中共,美决策人矛盾重重。他们对中共怀有深刻的敌意,同时又认定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缺乏资金和管理人才,要实现工业化,须求助于美。中共对美政策,终因经济因素将软化。只要美政策得当,必能影响中共内政外交。[38]美还相信承认新中国是美对中国的一种奖赏。美可迫西方各国与美一致行动,以承认为武器,迫中共承认美在华权益,进而迫其放弃革命理想,屈从美对苏战略需要。
美国的西方盟国,情况却大不相同。这些国家大体为四类。第一类,以英法荷葡为代表,战前多为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或多或少以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待美在华政策失败,甚而把美在华失败看成自己卷土重来的机会。[39]它们主要从经济和其他现实利益出发,选择对华政策,不愿为抽象的反苏冷战及主要属于美国的“西方在华权益”由美支配,开罪新中国;第二类以印缅等国为代表,从前多为殖民地附属国,与新中国命运相似,也没有在华特别权益需要维持。他们在政治上还同情中国革命,不会追随美与新中国为敌;第三类以丹麦、瑞典、瑞士等为代表,皆为传统中立国,虽划入西方阵营,却乐于与各种类型国家共处。它们一般依据其中立传统,相对独立地处理对华政策,不会无条件追随美;最后一类以意、菲、韩等为代表,当时在政治上依附美,因而在外交上屈从美,支持“共同阵线”政策。但它们缺乏国际影响。概而言之,除少数影响力小的国家外,大多数西方国家并不认为美“共同阵线”政策符合本国利益,因而,美“共同阵线”政策明显缺乏政治基础,这是这一政策失败的基本原因。
美“共同阵线”失败的第二个原因,与新中国的初期外交有关。新中国的初期外交,促成美与其盟国的政策朝背离“共同阵线”的方向运动。
新中国成立,是一场深刻社会革命的结果。它不仅涉及政权更迭,更涉及社会性质、政治制度及对外政策原则等系列变化。外部世界承认新中国,不仅是国际法行为,更是政治经济行为。由于中国是大国,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与美、英、苏三大国,皆有历史渊源,固而争取国际社会承认的斗争,就更加复杂。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对此就有清醒认识。三大战役完成后,中共解放军飞渡长江,迅速解放全国大陆,并在解放区清匪反霸,分配土地,争取人民拥护。当美摆弄国际法条文,抛出承认“三原则”,诱迫其盟国参加“共同阵线”时,中共已对全国本土实现了国际法意义上的“有效统治”。而美承认“三原则”中的“国际义务”条款,其内容主要指美在华权益,这对美以外的西方国家缺乏吸引力。到10月,当新中国照会各国,提出建交问题时,即使按西方国际法理论,也有充分依据。[40]
关于新中国对外政策选择,毛泽东坚持“一边倒”向苏联的原则。新中国据此奉行对苏联与社会主义各国友好的政策并收到实效。新中国成立不到一个月,便相继得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承认,并基本越过从承认到建交的时间差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就为新中国取得国际法主体资格奠定了最初的国际法基础,冲淡了美与西方国家是否承认新中国国际法意义上的重要性,加强了新中国与美及西方国家交涉时的国际法地位。
对西方国家,中共政策并不僵化。新中国对西方国家实行区别对待政策。首先是区别对待帝国主义国家与一般西方国家;其次区别对待美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区别对待美英,把英视为争取对象。在宣传方面,报章杂志屡次点名抨击美侵华政策,却尽力避免点名批评英;经济上对英在华企业人员也比较优待;“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中共未作渲染性宣传,而是力争冷处理。[41]在香港问题上,中共政策也十分灵活,中共军队未乘胜夺占香港,这就消除了当时英对新中国的最大疑虑。中共对英政策,是促成英在“共同阵线”问题上不与美合作的重要原因;而英不合作则是导致美“共同阵线”政策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
最后,中共虽宣布“一边倒”,但也未关死与美打开关系的大门。当年初夏黄华与司徒雷登的会谈及中共非正式邀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就是证明。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一改从前点名抨击美的提法,以“外国帝国主义”这一泛词替代“美帝国主义”也是一个信号。[42]中共对美政策的灵活性,在客观上能加强美官员中主张承认新中国一派的地位,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共同阵线”政策的贯彻。
美“共同阵线”政策失败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美政策的内在矛盾。首先在政治上,美虽积极推行“共同阵线”政策,但究其本质,是要凭西方国家联合行动造成的压力,迫中共满足美要求。美政策中的“延宕”承认或“不急于承认”,既不同于无条件承认,也不同于绝对不承认,它表明美尚未下决心不承认新中国,因而未排除按美国条件,打开美与新中国关系的可能性。美在推行“共同阵线”政策时,又与中共秘密会谈,这就构成了一种相互排斥的双轨政策。由于要组织“共同阵线”,美与中共会谈的诚意就打上了问号,国务院阻止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正是贯彻“共同阵线”政策的需要和逻辑结论。[43]反过来,与中共接触,又使“共同阵线”政策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全力贯彻。美对新中国的“默示承认”;与中共会谈,加重了其西方盟国对“共同阵线”政策的怀疑。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担心美诱迫它们参加“共同阵线”,自己却与中共达成秘密妥协。
美“共同阵线”政策第二重内在矛盾在于其逻辑。1949年美制订对华政策的依据是美认为中苏有矛盾,中共内部有派系纷争。美据此制订NSC34/2和41号文件,以离间中苏关系和促成中共“铁托化”为目标,但美诱迫其西方盟国参加“共同阵线”时却使用了另一种逻辑。艾奇逊9月5日与贝文会谈,声称他不相信可凭借承认新中国离间中苏关系,影响中共政策。[44]这正好与34/2和41号文件所应用的逻辑相反。贝文据理逐条批驳艾奇逊。滑稽的是,贝文用以批驳艾奇逊的逻辑,正是34/2和41号文件反复使用的逻辑。
美“共同阵线”政策第三重内在矛盾在于其法律依据。美向来标榜以法治国,严守国际法。美关于承认新中国的“三原则”是套用奥本海姆国际法理论;美还列举苏俄革命和西班牙内战时期政府承认问题等国际法案例,为其“共同阵线”政策寻找国际法依据。事实却证明,美只是套用国际法术语,掩盖其自私的政策行为。1949年底,中共解放了全国大陆,多数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共已对中国建立起“事实上的控制”,美依然抓住“三原则”不放手,这就暴露了其国际法原则的虚伪性。不仅如此,美还开创了以“安定性”和“自主性”为借口,拒绝承认不同意识形态新国家的先例。[45]套用国际法术语,执行时又任意将其政治化,反使美作茧自缚,更形虚弱。美“共同阵线”政策所导向的必然政治后果是不承认新中国,这不符合大多数西方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原则。当英模仿美决策人口气,宣称其承认新中国符合国际法原则时,美便难置一言。
前述三个原因,不但在各自作用范围内影响美“共同阵线”政策的贯彻,三者还互相交织,相互作用。中共政策在美与其西方盟国之间打进了强有力的楔子,使美盟国纷纷重估新中国,怀疑并抵制美“共同阵线”政策。中共对美外交也使美政策中的内在矛盾逐步展开,影响美“共同阵线”政策的贯彻。结果,喧嚣一时的“共同阵线”政策,只能以失败告终。
从根本上说,美“共同阵线”政策失败,还源于美错估了世界大潮,低估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的信心和能力;也源于美高估了其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及驾驭其西方盟国的能力。美“共同阵线”政策失败说明西方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它还反证新中国初期对外政策所具有的坚定性和灵活性。
注释:
[1]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9,The Far East:China),美国政府出版局1974年版,第13页。
[2] 多洛斯·博格和海因里希编著:《未定之秋:1947—1950年中美关系》(Dorothy and Heinrich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3]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8卷,《远东:中国》,第767页。
[4] 寺泽一等主编:《国际法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15页。
[5]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24—25页。
[6] 薛龙根主编:《国际政治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3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24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5页。
[9]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2页。
[10]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3页。
[11] 向兰辛:《1949年英美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的争论》(Lanxin Xiang:The Reconition Controversy,Anglo-American Relations,China,1949),载英国《当代历史杂志》,伦敦赛格出版公司1992年第4期,第332页。
[12] 康矛台:《英舰紫石英号事件》,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5页。
[13] 《当代历史杂志》,伦敦赛格出版公司,1992年第4期,第333页。
[14]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7—23页。
[15]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23页。
[16]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25页。
[17]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34—40、47—48页。
[18]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47页。
[19]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50—51页。
[20]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载《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9页。
[21] 爱德华.W.马丁著,姜中才等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第58页。
[22] 外交部外交史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7—45页。
[23]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47—48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2页。
[25]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57—61页。
[26] 《当代历史杂志》,英国伦敦赛格出版公司,1992年第4期,第35—336页。
[27] 爱德华.W.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第76—77页。
[28]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76—78、81—85、88—91页;
[29]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03页。
[30]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55页。
[31]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23页。
[32]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54—155页。
[33]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20—121页。
[34]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20—121页。
[35]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29—132页。
[36]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149—154页。
[37]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219—220页。
[38]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492—295页。
[39] 《当代历史杂志》,英国伦敦赛格出版公司,1992年,第4期,第322页。
[40]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22页。
[41] 外交部外交史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4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3页。
[43]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767页。
[44]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远东:中国》,第81—84页。
[45] 寺泽一等主编:《国际法基础》,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