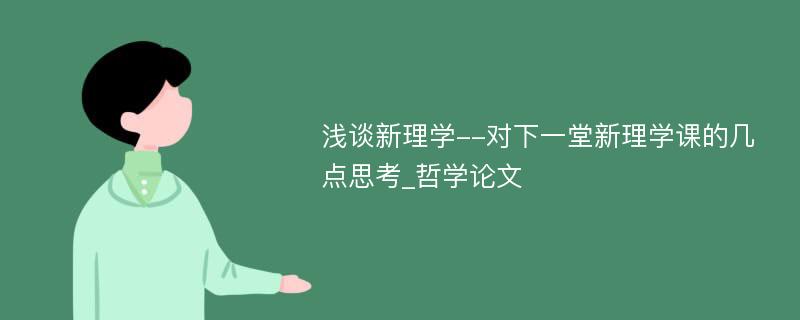
略论新理学——关于接着新理学讲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接着讲与创造的诠释
新理学一开始就标明是“接着”程朱理学讲而不是“照着”讲,那么,从方法的意义上,此接着讲究竟有什么含义呢?冯友兰对于其接着讲的思路,有一个逻辑的说明。冯认为,哲学是形式的释义,只是“以心观大全”,只讲事物各有其理,而不研究各个理的具体内容(属于科学),因而古今哲学不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新哲学不可能超出前人的“大致轮廓”,只能更“完备精密”而已,此所谓“完备精密”,即在于思之能力即逻辑的进步。所以,冯友兰说:“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中国哲学近代史》,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7页)
使传统哲学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就是在确定传统哲学“应有的”逻辑的基础之上,把传统哲学想要说却没有说或没有说清楚的,说出来。冯依此来区别哲学史家与哲学家,他说:“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字句,这些人自己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指什么。……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这样的工作,就再不是一个历史家的陈述性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2—383页)
对照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倒可以充分理解此接着讲的方法意蕴。傅伟勋对哲学研究过程有一个从原典解释到原有思想“深层结构”的发掘,直至突破原有思想结构而有新系统之自我创立的诠释学的描述。傅将此过程分为五个层次:1、实谓层次,关涉“原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包括考证、训诂、版本等文字方面的工作。2、意谓层次,关涉“原思想家真正意谓什么”,包括生平研究、语言解析、义理彰显等。但是,由于语言含混、多种结构并存、逻辑矛盾等原因,几乎不可能说出原思想家的真正意蕴。3、蕴谓层次,关涉“原思想家可能说什么”,这是超越“客观的释义”而一跃成为“可能的释义”,于此承认原思想家种种丰富的哲理蕴涵,并借助深广的“史的传统”来把握其蕴涵。4、当谓层次,关涉“原思想家本应说什么”,此是突破“史的传统”,来断定原思想家“在现代应该说什么”。5、必谓层次,关涉到“我应该说什么”,此是跳出原思想家立场来决定我要说什么。(参见《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126页)
所以,冯友兰所谓“推到逻辑的结论”,可以获得这样的解释:原哲学虽有“自己的逻辑”,但由于语言的含混、内在理路的矛盾、逻辑方法的缺失等原因,“此逻辑”在原哲学中是“暗晦不明”的,它表现为两种情形:或者是“此逻辑”在原哲学中没有被清晰完整地表达出来(在更完备精密的现代逻辑学的对比下,冯主要是此意);或者是“此逻辑”在原哲学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亦即被其它逻辑线索所掩盖(纯哲学家于现代的立场看,傅主要是此意)。如果说哲学史家所关心的是原哲学的“实际意蕴”,那么,哲学家或是一个创造性的诠释家所关心的则是原哲学的“真正意蕴”。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创造的诠释还是接着讲,都启示了一种“传统本位”或“民族本位”的哲学发展观。既是接着讲,就必然与传统哲学有着某种共同的问题、线索、方向,就仍是一种延续、一种传承,仍然涵括于传统的范畴;同时,它又是对传统的发展和创新。
如果严格按照这种“接着讲”的方法接着新理学讲,首先要做的,就是整理出新理学应有的逻辑,由此来决定所“接”的线索。
一、逻辑分析与方法自觉
新理学最为显著的现代品格无疑是逻辑分析法。它对新理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形式上、程序上的,与义理本身无关,只关涉义理在表达上的明晰性和在论证上的逻辑性。二是哲学观上的,以为哲学是从经验出发的逻辑的知识系统,由此决定了新理学哲学定位的逻辑经验主义倾向。
冯友兰对逻辑分析的方法意义有充分的自觉和系统的说明。从分析与认知而言,认知始于分析。在分析之前,对象“这”是一个“漆黑一团”,要把“这”弄得可知,就必须进行分析,由分析来获得事物的共相,即“知类”。而哲学是一言说系统或理论系统,它离不开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中国哲学史》上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页)。清晰不是哲学的目的,却是哲学所必须的。至于直觉,它只能提供一种经验而不能“成立一个道理”。
如果说哲学的理论性和明晰性要求有逻辑分析的话,那么,在新理学形上学,其内容本身也要求逻辑化、形式化,不仅形上学的命题、推论是形式的,其形上观念也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具体地说,新理学形上学从“事物存在”这一最基本的经验出发,所有的形上观念都是“存在”的蕴涵。新理学形上学依此“不着实际”的形式性来区别于科学的“积极的释义”。(参见《中国哲学简史》,第371页)即便新理学“负的方法”(与逻辑分析法相对)也充满着逻辑分析的意味,其气、道体和大全之所以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是因为“全”或“大全”超越了能(知)所(知)两分的认知关系。此“神秘主义”因而是一种“清晰”的神秘主义,一是神秘之所以神秘是清晰的,二是神秘产生于分析运用的极限处,是在充分清晰之后的神秘。
新理学对逻辑分析的重视和运用,体现了新理学充分的方法意识与方法理性,新理学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个方法自觉、方法反省与方法运用有机结合的过程。《新理学》一开始,就系统讨论何谓哲学,涉及哲学的定义、起点与对象,哲学的功用与目的,哲学的运思方法和哲学的发展诸问题。《新原人》有意突破逻辑分析法,而有整合正负方法的努力。《新知言》则是一本专门讨论形上学方法的方法论专著。从逻辑上说,此对一般问题(如一般哲学)的起点、对象、方法、程序、功能、目标等要素的讨论,不是具体问题(如某具体哲学)之具体解决本身,而是它的方法前提。新理学的方法意识和方法探索,对于方法理性最终落实于中国哲学有着明显的开拓意义。
概括地说,新理学的方法意识集中体现为哲学之“学”的意识及哲学方法的逻辑分析意识。新理学紧扣这样的线索:哲学是学,是一客观的知识系统,它的方法只能是科学的理智的。现代中国哲学要建立起“学科”意义上的新哲学,就必须克服中国传统哲学在论证、说明、系统性方面的严重不足。
于此,新理学启示我们,对于哲学与知性的关系须作两方面的分疏;一是知性与哲学的方法层面或形式层面的关系,就方法而言,哲学之为学,必是一种“知性探求”。另一是知性与哲学的内容层面的关系,它指一具体的哲学如何看待知性与认知、知性与本体、知性与人生等的关系。就此方面说,又有两种趋向:一是重意志、重直觉、重实践;一是重理性、重认知、重学问。所以,形式上、方法上的知性与内容上的主知或反知倾向并无必然的关联,或者说,知性方法与内容上的“反智主义”并不构成矛盾;相反,反智主义或超智主义的思想倒必须运用知性方法来加以系统的论证与说明。众所周知,牟宗三哲学在逻辑分析、义理论证、义理架构等形式理性或方法理性上并不逊于新理学,而其所主张者,却是超理性的“智的直觉”。所以,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直觉主义者,是“新”理学还是“新”心学,都不能回避哲学认知在方法层面或形式层面上的知性问题,都不能没有相当程度的方法意识和逻辑训练。只有从此“普遍知性方法”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冯友兰关于逻辑分析的“手指头”说和“永久贡献”说。
新理学的方法探索,同时也启示了中国哲学在方法论、知识论上的重要课题。从逻辑上说,对某一具体学科的方法探讨,必须以一般的方法论和知识论为逻辑基础。一哲学家建立一哲学,其哲学系统中不必有系统的知识论,而在方法资源上,却不能不依靠高层次的方法论和知识论。逻辑分析法如要在中国哲学中扎根,必须有方法论、认识论的深厚支持。现代中国哲学如何理解、融汇、回应西方哲学在认知理性和方法理性上的长处,应是当前中国哲学之发展的一个紧迫课题。
二、道德形上学与客观存有论
基于接着讲的立场,冯友兰认为,程朱宇宙论的合理意蕴就是形上与形下、理与事二分的存有论线索。新理学形上学作为“客观存有论”系统,是自觉根据西方在论传统来改造和发展程朱宇宙论。
随之而来的疑问是,程朱宇宙论虽也有“客观存有论”的部分,也讲理是“平铺放着”、“元来依旧”的本然实有,也讲理与事、形上与形下、所以然与实然的两分,也从生物之具(气)与生物之性(理)来讲存在的发生和要素(形式与质料)等等,但其根本的宗旨是讲此理“浑然为善”,是确立一道德本体,以道德的原理为宇宙的原理;再进一步,是说此“道德化”的天理即是吾人性体。
冯并非无见此,只是,新理学依据自己对哲学“应”是什么的理解来建立“新哲学”。新理学明确指出:“在程朱及一般宋明道学家之哲学中,所谓善即是道德底善;而整个宇宙亦是道德底。我们的说法不是如此,我们以为道德之理是本然底,亦可说是宇宙底,但宇宙中虽有道德之理,而宇宙却不是道德底。”(《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页。下引此书,只标卷次、页码)新理学视传统理学“一理万理”、“物物一太极”为神秘之说,而不主张“存有论”或“宇宙论”意义上的道德善恶。
冯采取此种形上学路向,主要是受西方哲学知性传统,特别是维也纳学派强调哲学分析化的影响。冯主张哲学(形上学)要从“科学的”或“综合的”立场中超拔出来,不再建立诸如“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之类的假定和玄设,而是从最基本的自明的经验“存在”出发,对“存在”作纯粹形式的逻辑分析。由此,新理学形上学不是通过本体来证立道德为人性本然,而是从“事物存在”出发,演绎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形上范畴,形成一解释存在与存有(实际与真际)、实际世界与理世界(事与理、殊相与共相、实际与纯真际)、存在之形式与质料(理与气)、存在之动(道体)与存有之全(大全)的存有论系统,其具有本体意味的“理”是一众理皆具的“理世界”,只肯定事物各有其理而已。
至此,新理学并没有根本上的逻辑矛盾,冯可以以哲学家而非哲学史家的方法来处理程朱宇宙论,新理学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存在,即如形式的形上观念可以提高人生境界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新理学系统最终仍要讲传统儒家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此境界是天人合德的生命境界,既非新理学境界说那种即概念即境界的知性境界,亦非新理学形式化的无德性内涵的形上观念所能蕴涵。显然,新理学实证化、逻辑化的形上架构,并不能为其仍皈依道德的人生境界说提供宇宙论或存有论的逻辑基础;相反,依此超道德的自然的形上观念,所引致的倒可能是齐物逍遥、与道(大全)为一的道家境界。新理学的形上学对于其人生境界说,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种觉解类型以为天地境界的觉解前提而已。
新理学形上学此种分析化、逻辑化的倾向遭致各种批评,其中以洪谦和牟宗三的观点尤具代表性。洪谦认为:“传统形而上学虽不能成其为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的体系,但有其在人生哲学方面的深厚意义。但是冯先生的形而上学似乎是两者俱无所厝。”(《维也纳学派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1页)从传统形上学命题如“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中,我们可以得到理想上的安慰、丰富的感觉和优美的境界,而对新理学形上学命题如“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非山,水不是非水”,只能是无动于衷。(同上)牟宗三则基于道德形上学的立场,针对“自然本体论”或“知性存有论”倾向(并非专指新理学)提出系统的批评。牟宗三认为,此种自然论、客观论是纯粹的知性外求,是把自然宇宙看成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实体,寻求其要素,是探求外在存在及其属性的“实有论”,至多只是对自然世界的一种解释。此种“自然本体论”只提供了一套空洞的静态的逻辑结构,而不能把真与善、存有与价值、自然与人生统一起来,不能引导人们获得一种物我一如,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不能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整体主义、有机主义的生命意识。牟认为,真正的形上学应研究应然的、价值的、超越的世界,应探求真与善、存在与价值的统一,而不是“纯客观的”本质。(参见郑家栋:《本体与方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226页)
上述批评虽具有力度,但都不是对新理学的内在批评。新理学形上学不只是“山是山,水是水”之类的形式命题,而是要讲理、气、道体和大全几个形上观念,按新理学的逻辑,有某种观念或概念就有相应的精神境界,尽管此境界难免知性化、概念化。牟的批评则是揭示了一种不同于新理学之类的“自然本体论”的形上学路向,即传统儒家的“道德形上学”路向。此路向是为人性归依寻找本体依据的“人学形上学”或“价值形上学”。从逻辑上说,牟的批评涉及到各自对形上学“何谓”的“承诺”问题,而不同的形上学可以有不同的问题、方法和目标。
冯友兰的新理学与以熊十力、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新心学”一系在形上学路向上的相互批评,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前者是解释存在或存有的“自然属性”;后者是关于人性本原的形上探求;前者是从经验出发的逻辑架构,后者则是先验的超越的思辨;前是主张“价值中立”的客观存有,后有主张存有与价值的统一;前者严格区分真理与信念,后者则是信念真实的实用倾向。新理学“客观存有论”的形上学路向在逻辑上是自足的,是对“存”或“有”的形式的普遍的分析,但是,人的价值问题、生命问题没有涉及,是知于自然而蔽于人,因而显得抽象空洞。“价值形上学”则试图统一价值与存有,但终究无法弥合主观信念与客观真理的差异,而以道德实体为绝对必然之宇宙实体的“道德形上学”,终难免有些道德神学的独断意味。
那么,究竟何谓“真正的形上学”?也许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形上学”,如牟宗三所说,“自然本体论”至多只是对自然的一种解释而已,“道德形上学”也是一种对存在与人的解释。哲学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建立形上学,因为形上学并没有一个绝对确定的模式。我们只能是根据其“内在的”逻辑来理解某种形上学,或是根据某种自我设定的标准和线索来评估某种形上学。
按照新理学的线索,“存有论”只是形式地肯定那客观的超越的“理世界”,至于价值问题不属于普遍的存有问题,而只能归于人生论。
三、理性与德性
新理学是一种典型的实在论与实用论的并用方式。其存有论是实在论的(客观本然的理),而其认知论和人生论则是经验论实用论的。从认知说,理虽客观超越,而我们的认知只能从经验开始;在人生论,虽承认价值有其超越的根源(价值之理、人之理),也只能存而不论(形式地肯定其有而已),至于人生价值的“实际建立”,不应是从某种绝对的假设出发,而是从人生最基本的自明的经验出发。所以,新理学人生论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人生各种经验事实的描述和分析。如对善恶问题的形式分析、对人性善的逻辑论证、对正性与辅性的分疏等。而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即有一种不确立伦理规范而只对伦理概念与伦理命题进行逻辑分析的“元伦理学”倾向。
当然,新理学人生论不是纯粹形式的,新理学不仅有价值的描述和分析,也有价值的建立。新理学明确提出两个价值方向:觉解与道德,一方面是觉解对于人生的本质地位;一方面是道德作为人生理想的归宿。
《新原人》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觉解。《新原人》说:“有觉解是人生的最特出显著底性质。因人生有觉解,使人在宇宙间,得有特殊底地位。”(第4卷,第523—524页)《新原人》力图把意义建立,表示为一种意义觉解或价值认知的过程,“一件事底意义,是对于对它有了解底人而后有底”(同上书,第515页),“我们对某类事物有了解,某类事物对于我们即有意义。我们对之了解愈深愈多者,其意义亦愈丰富”(同上书,第520页)。有无觉解,不仅是对人生的意义有无觉解,而且直接就是人生意义之有无的问题。觉解是构成道德意义的必要条件,无觉解的行为,虽合于道德,却不能是道德的行为,在新理学看来,人之性具有多种内涵:理性、社会性、德性等,而理性具有最优先的地位。新理学此种柏拉图式的理性(理智)主义人生观与程朱理学已有很大的不同,程朱理学虽有主知倾向,却始终坚持德性为吾人性体,而不是独立地把心之知觉灵明作为人性本质。
另一方面,新理学仍是把人生的最高境界归于德性的完满实现,其人生境界说的中心线索仍是“德性自我”的觉醒与扩充。新理学的天地境界是顺着义利之辨讲的,其“超道德”的意义,不是超越是非善恶,而是指道德行为不仅有社会的意义且有宇宙的意义,是德性自我扩充至极,是“无我”而“大我”。由此体现出新理学鲜明的儒家立场。只是,它与传统儒家德性本体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已经大相径庭。
新理学于此方面的合理意蕴集中体现为意义与觉解、价值与认知、德性与理性的统一倾向。新理学是用理性来了解德性,用理性来限定德性,理性已成为德性之所以为德性的一个必要环节。《新原人》四种人生境界,从无我到自我,从个人之我到社会之我,从社会之我到宇宙之我,既是一个意义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理性觉解过程。如果说新理学的方法自觉肯定了“逻辑分析”对于“知性探求”的方法意义,那么,在此,新理学是确定了“知性探求”于“价值建立”的方法意义,前者是方法与知性,后者是知性与人生。
当然,《新原人》对此方面的讨论,还十分简单笼统。《新原人》中的意义不同于我们所谓价值,其意义更近似于内涵、涵义之类,其所谓“了解愈深愈多者,其意义亦愈丰富”有把意义浑同于一般知识之嫌。《新原人》只注意到觉解与“觉解的觉解”的区别,而无意区分“客观的了解”与“意义(价值)的了解”。《新原人》把整个价值过程简化为价值觉解,而未注意到价值实现还须有一个价值实践的过程。总之,在《新原人》的价值生命或德性生命中,情感、意志、实践等的应有之义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意义觉解化、德性知性化的片面倾向。
不过,新理学面对强调主观、生命、亲证、践履的深厚传统,异军突起,弘扬以方法理性和理性人生为主要内容的理性精神,对纠正传统哲学把知识问题和人生问题直观化、神秘化、自然化的偏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新理学在相当程度上启示了德性与理性、价值与知识、信念与真实等方面的关系课题,特别是如何用知识来确立价值、用理性来规范意志。新理学在此方面的努力及其理论上的矛盾,迫使后来的哲学必须在更高的层面上去处理理性与德性知识与价值的关系。
四、未来世界哲学:歧出与整合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仅凭接着讲的思路,很难在整体上把握新理学的过程和方法。新理学不是单纯地挖掘和发展传统哲学的“深层意蕴”,而是在一个新的方法下进行新哲学的建立,在新的结构中融汇传统。牟宗三对哲学之新的有两种说法:一是引申之新,一是歧出之新。(参见《心体与性体》第1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6页)前者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思想原有向度的引申扩充,后者则依心学正统立场对理学歧出有贬损之义,我们可理解为不满足传统思想的原有向度,而引入新的向度。如果超出“唯正统”的立场,后者的意义是明显的:引入新的向度,是从整体上开拓、丰富了传统哲学。从义理上说,超出原有向度之所以可能,正因为原有向度不足以表达更丰富、更复杂的义理。再进一步,就是超越单纯的歧出立场,基于更高的整体和更完全的理性,在更大的系统中实现原有向度与歧出之新的整合。所以,哲学创新不止于引申之新和歧出之新,还应有一种“歧出整合之新”,先有歧出再有整合。
新理学之建立正可谓歧出整合之新。新理学方法上的逻辑经验倾向以及心性道德论的理知倾向,是传统哲学所缺,而从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中引入的。新理学不仅试图贯通理学与心学、儒与道,从整体上说,更是力图综合中西哲学。此综合依据于客观本然的理,依据于对此理的“完全的了解”。对于本然完全的理来说,各种哲学均是只见其中的部分。因此,哲学的发展,必须表现为不断创新、不断歧出又不断整合的辩证过程。
所以,冯友兰认为,民族哲学之所以是民族的,“其显然底理由是因为某民族底哲学是接着民族的哲学史讲的,是用民族底语言讲底。”(《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页)其意义不在于义理,就义理说,哲学只有一个,因为客观本然的理只是那一个。据此,冯对于狭隘的民族哲学意识提出明确的批评,他说:“如果事实上哲学家受所谓民族性的拘郁,哲学的目的,正是要打破这些拘郁,而求普遍底公共底义理。如果有所谓民族性,哲学家于讲哲学的时候,正要超过之。”(同上书,第432页)
基于普遍本然完全之理,冯提出其“未来世界哲学”的构想。冯认为,一方面,西方哲学没有充分发展出真正的神秘主义,一方面,中国哲学没有充分发展的理性主义,所以“只有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哲学相称的哲学。”(《中国哲学与未来哲学》,载于《哲学研究》1987年第6期)新理学依此路向,建立出一种整合正方法与负方法的形上学;一种结合理性觉解与精神境界的人生论,一种既有存有论又有人生论的哲学系统。
当然,新理学并没有最终完成这些融合,其形上学仍有分析与存在、经验与超验等的矛盾;其人生论仍有概念与境界、认知与生命的矛盾;其整个系统,仍有存有与价值、价值中立与价值建立的矛盾。总的说来,新理学更注重方法理性和理智理性,而未注意到多种理性形式的区分与关联;在人生论上,更注重价值确立的认知环节,而对整个价值过程中的意志、直觉、实践等层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许,新理学正是犯了冯自己曾批评过的那种错误,没有“使逻辑分析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以内”,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冯还没有真正观照到生命之整体和理性之整全。
总之,新理学启示了两种重要的哲学路向,同时按照这两个路向走下去,就是接着新理学讲的内涵:一是中国哲学中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建立,一是世界哲学意识。所谓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中国的建立,主要是指从西方哲学中引入以方法理性和认知理性为主要内容的理性主义哲学,以弥补中国哲学传统在此理性向度上的缺失。简单地说,它包括两方面相关的内容,一是知识及其方法,一是知识与价值;前者是元理性、纯粹理性,是“理性的方法学”,是方法论知识论,后者是理性在社会人生中的应用,是“理性应用学”,是知识社会学或知识价值学。如何在一种新的结构中真正确立方法、容纳知识,应是当前中国哲学之发展的主要任务。所谓世界哲学意识,也就是“整体本位”或“理本位”意识,它不只是从民族传统出发,不只停留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对峙与批评;或者说,不是从单一的向度出发,而是从真实或真理的“整体”和“普遍”出发。比如,从对整体的把握出发,是“一”与“多”相互批评或不断分析、不断整合的辩证过程;从整体生命说,是理性与意志“背向而同体”;从整体理性说,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机械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多元与统一等。(参见成中英:《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现代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235页)应该注意的是,此种“整合意识”并不否认“整体意识下单元倾向”(如只是由中国文化来批评西方文化)的合理地位,只是须自觉其是多元整体或多元理性中的一元。
标签:哲学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理学论文; 人生价值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史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宇宙论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牟宗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