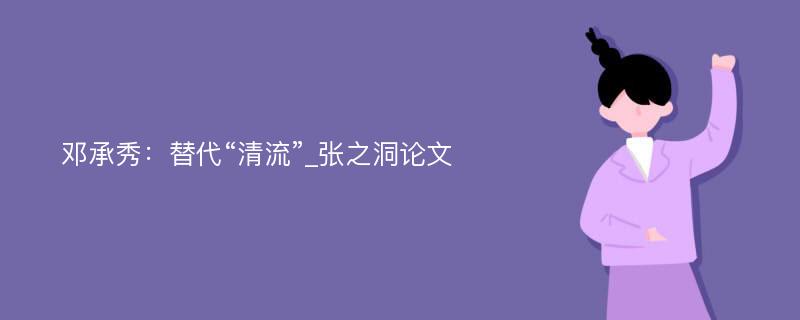
邓承修:另类“清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流论文,另类论文,邓承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5—0056—12
说起同光年间的“清流”人物,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头脑里浮现出的人名,首先是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宝廷、何金寿和黄体芳等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类似的科甲经历及其名人效应:中进士,授编修,兼差考官和学政,升转于翰詹的不同职位,最后擢为内阁学士,进而入部为侍郎,跻身部堂卿贰。这样的进阶之路,用宝廷的话来说,是“名士兼名臣,千古垂不朽。”①在仕途拥挤的同光时期,绝大多数人走通这条道路所需的时间是以前的双倍,即二十年左右,②而名士“清流”只花了十余年的光景,成为官场的例外。
成名须趁早,不然快乐会减半。这句话特别适合同光时期士子们的心态。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宝廷、何金寿和黄体芳等人是那个时代的幸运者,大多场屋通顺,少年成名。③“清流”的一大特征,就是由科甲而登官场,由名士而致名臣。40岁左右,就成为影响兼及政坛和学界的士大夫。
但并非人人都如此幸运。如果正途走不通,是否还有成为名士兼名臣的可能性呢?比如邓承修,他没有正途的出身,似乎也没有走正途的勇气。他20岁中举,作为偏僻的广东归善(今惠州)人,这已算是不错的开端。但两年后,即同治二年(1863),当张之洞、黄体芳联翩进士及第的时候,年方22岁的邓承修却匆忙捐赀为郎中,签分刑部,做起了庞大官僚体系里的一无名小部吏。邓承修传记中未有交待,也许是他对科甲没有信心,也许是家有余资,捐官正五品的郎中,那比通常正六品的部吏主事要花去更多的银两。④
如果没有光绪初年风起云涌的“清流”建言活动,邓承修的官履轨迹,是绝无可能与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宝廷、何金寿和黄体芳等人有相交相汇的,晚清历史上也许就不会留下邓承修的名字;而正因为有了“清流”建言活动,邓承修才得以跻身“清流”的行列,同时也晋升到名臣的行列。
两种仕途,一种结果,殊途而同归。前者由名士而成名臣,后者由俗吏而致名臣。“清流”建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够将部院寻常书吏,造就为一代名臣?为何一被人目为“清流”人物,仕途前景就大有不同呢?
一 另一个交往圈子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内乱和外患之后,世道承平的同治朝,被官方得意地自诩为“中兴”,而中兴时期官场面临着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是——仕途拥挤、出头无望。这其中的原因,一是靠镇压太平军崛起的湘淮军人,以军功占据高位;另一是以捐纳挤入官场的杂佐,以银子铺路、以夤缘晋阶,攫取了大量府县级的官职。谁都知道,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⑤而大家都愿意挤这条独木桥,因为这是传统的正经仕途。但现在情况突然变了,“咸同以降,翰林拥挤。”⑥而“拥挤”的原因,不是翰林过剩,而是鸠占鹊巢,非正途出身的官员抢了正途出身官员的饭碗。
这怪谁呢?当然怪太平起义军,同时也怪西方列强。不是明摆着吗?军功和洋务,为非正途的开辟了广阔的为官道路;而这批“粗才俗吏”的窜升,又极大地改变了京师官员的交往圈子和交往方式,在正途和非正途官员之间,似乎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由军功而擢升为疆吏的刘坤一光绪七年(1881)的感受非同寻常:
弟上年出都,照章分送别敬,乃香涛询知未送黄漱兰与宝竹坡诸处,遂亦不受,此何意耶?弟自知粗才俗吏,不能罗致清流,而亦不欲轻为罗致,…⑦
哪怕官至封疆,面对乳臭未干的名士“清流”,心中升起的,仍然是自卑。主动以白花花的银子“罗致”,换来的却是白眼相对。承平时期,军人地位下降之日,就是文人地位上升之时,作为名人文士的“清流”,必然成为社交场合的宠儿,由此也引起了京师交往方式和生活氛围的改变。亲历了同光两朝的满人震钧,观察到了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咸丰中,肃顺尚骄侈,士大夫化之,以奢华倨傲相尚。至同治初,恭邸性谦恭,文、倭二相性俭朴,士大夫遂易而谨饬,且多以布衣相尚,至光绪初犹尔,后遂不然。未几诸言臣蔚兴,人皆以名臣相期。及癸未张幼樵编修佩纶以庶子署副都御史知贡举,而清议益重。后生初学,争以清流自励。不数年,此风顿改。及潘文勤主持风雅,常熟尚书和之,皆尚小学,坊间《说文》盛行。⑧
震钧生于咸丰七年(1857),卒于民国九年(1920)。虽经历了咸同光宣四朝,但咸丰朝的事情,他多为耳食,所记多有不确。此处把咸丰朝“尚骄侈”的责任归之于肃顺,便是未脱“成者为王败者寇”的窠臼。咸丰帝本人荒淫无度的效应,难道还超不过一个权臣肃顺?同治朝的官场风气,也断非恭亲王、文祥和倭仁几个人的个人品质所能左右,同治年间屡谏不止的重修圆明园风波,凸现出刚刚攫取朝纲的慈禧太后的奢靡之心,⑨更不用说后来愈演愈烈的、乃至动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的闹剧。“布衣相尚”,岂非梦呓?光绪朝“清流”崛起、“清议益重”的效应,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小学”和《说文》的“盛行”。绘画、碑帖、金石、书籍,哪个不都是可以鉴赏和收藏的宝货?俗话说,“乱世的黄金,盛世的古董”。古董的行情见涨,固然是世道太平的一个标志。但在以“中兴”为招牌的盛世里,外在的“风雅”只是其表,内里又是什么呢?京城士大夫风气之蜕变,不是几个朝廷重臣的个人行为可以决定的,它与整个政局的变迁密切相关。同治初肃顺被整肃、慈禧垂帘听政的政治新格局,成为直接影响士大夫行为举止和交往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南方底平,肃党伏诛,朝士乃不敢妄谈时政,竞尚文辞,诗文各树一帜,以潘伯寅、翁瓶叟为主盟前辈。会稽李蒓客,亦出一头地,与南皮张香涛,互争坛坫。⑩
这也就是说,京师士大夫的趋向,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政治。就象乾嘉考据的走红与康雍乾的文字狱有关一样,同光朝“文辞”、“诗文”的时髦,也与朝廷政局的变迁紧密相连。但不管原因是什么——鄙视非正途的官员也罢,“避席畏闻文字狱”也罢,其客观的效应,则是京城官员交往圈子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翰林出身的六部九卿,多不愿与军功和捐纳出身的官员来往;碰巧又遇到京卿中出现了潘祖荫和翁同龢这样的世家子弟:潘祖荫23岁中得探花,翁同龢则26岁摘下状元。他们既有才,又有钱——二者都是当名士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当然,他们还具备一般人没有的由名士而为名臣的充分条件——即其父辈在京师结成的广泛人际网络。潘、翁两人的仕途发展,正如前述崇彝的引文,确实是十年左右的时间,便在同治年间由翰詹词臣而升转为侍郎,再历经十年左右在各部副职上的磨砺,在光绪最初的十年间(即中法战争之前)掌部印,任军机。宦海壅滞,不对他们产生丝毫的影响;在他们面前,军功、捐纳出身的官员的最深体会,便是自惭形秽。与此相反,潘、翁对比他们小十几岁的翰林后辈却青眼相加,竭力揄扬提携,由此赢得了千古“好士名”。(11)而潘、翁与后辈的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宝廷、何金寿、王仁堪等翰林官的交往,就形成了一个声震京城、夺人眼球的名士“俱乐部”。(12)
在这个俱乐部里,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俗吏。仅举一个例子,张佩纶光绪四、五、六年的日记中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他密切交往的友朋,这个名单就是由一群翰林名士组成的:陈宝琛、张之洞、洪钧、吴可读、吴大瀓、缪荃孙、黄体芳、何金寿、汪鸣銮、王仁堪兄弟,等等。(13)这些人,有太多的理由和借口聚集在一起:翰林院的同僚是其最基本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翰林同年关系,如张之洞与黄体芳,如宝廷、洪钧和吴大瀓。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同乡关系,张之洞和张佩纶是大同乡,洪钧、缪荃孙和吴大瀓是大同乡,陈宝琛和王仁堪兄弟是小同乡。其实,名士这个头衔,就是社交场上最鲜亮的名词,其中任何一条关系都能成为联结和扩张人际网络的有效途径。有这么多交结的理由,“清流”名士的交往便是无日无之。而交往的形式和内容,大多为燕饮和郊游,附着上清谈学问的“风雅”,落实到打探消息、热议朝政的目的。有理由要聚,没有理由也要聚。张佩纶光绪四年的一条记载:“孝达邀饭,以余疏太辣,亦颇称其胆。”(14)则是先喝酒吃饭,再商量奏折,难逃标榜吹捧之讥。这就难怪时人指责“清流”名士有党援之嫌了。
这个名士“俱乐部”并非只吸纳翰林正途官员。既然是名士“俱乐部”,当然是只问名士,不问出身。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自古皆然。京城没有翰林头衔的名士,哪怕是杂途,也能被此“俱乐部”所吸纳。条件只有一个——有名,名声越大,越容易被吸纳。而博取名士的途径,就在于当时的时髦学问——金石书画。
同治十年(1871),各省士子汇集京师,参加会试,这自然也是潘、翁显示礼贤下士的良机。由张之洞倡议和策划的以潘祖荫名义举行的雅集,非常典型地显示了这种交往,绝不仅仅是吃饭应酬而已。否则,为了一顿饭,张之洞致潘祖荫的请示信函就达七启之多,细密得有些女人态。函件不厌其烦地就聚会的地点、饭庄、邀请的人数、请柬的书写格式,尤其是拟邀请的客人名单,与潘祖荫反复函商。(15)千细万密,张之洞最后竟忘记了准备酒水饭菜——这才细密地显露了名士的风度!台湾著名文史作家高阳从这里窥出张之洞的“疏密互用”的宦术——“是则岂有本人请客,竟忘设馔之理?此当是故作疏忽,示其名士派头。”(16)
所有被邀请者,尽管尚未金榜题名,却都是各有学术专长的年轻名士,将来的政治前途自然不可限量。李慈铭、陈乔森、潘存、赵之谦、秦炳文、桂文灿和杨守敬等,都赫然出现在被邀名单上。其实这种做秀的把戏,当时的被邀请者又何尝不是心知肚明?只不过大家相互利用、共同扬名而已。被邀者也许还得感激潘、张的提携之情。但也有人并不领情,杨守敬就对这样的风流宴集有些反感,没有出席:
是时南皮张文襄(之洞)为翰林。提倡风雅,大会天下名流于城南陶然亭,守敬与陈一山与焉。守敬以为迹近标榜,不赴,厥后南海桂君文灿有记刻其集中。(17)
杨守敬这种反感的产生,应当与邓承修有关。两人的结识,则是源于另外一个交往圈子的存在。与名士“俱乐部”相比,这个交往圈子非常暗淡和寒碜,因为参与其中的都是非正途出身的小京官。本来,杨守敬只是一个风风尘仆仆进京赶考的外省人,在京逗留期间,得到有金石同好的京官陈乔森的介绍,才得以认识邓承修,并借住其寓中。一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杨守敬每次入京,都是宿在邓寓。他发现,邓承修是一位金石学的爱好者:
是时,铁香亦好金石,每日游市上觅所得,其精者归铁香,其次者守敬收之,缘守敬无力买精者。然饮食之费、租屋之费皆铁香任之。计铁香亦非殷实富人,每年不过得其叔津贴数百金,而以之养吾闲人,其志非寻常好客之比。(18)
此事发生在同治四年(1865),杨守敬第二次赴京应会试。因为结识了潘存和邓承修,才得以领悟京师的政治和学术风气,才立志钻研金石学。小部吏热衷费钱费力的金石收藏,那可是勒紧裤带追赶时髦学问,确实耐人寻味。同治十年(1870),杨守敬又一次公车入都,仍寓邓宅。其科场时文水平未见长进,金石和版本的学问则见涨,成为京城大名士延揽的目标;而邓承修呢?金石学问如同其郎中官职一样,六年里没有发生任何变动。长安居,已属大不易。成名无望,岂止是快乐减半,还有宦途投资成本的增长。捐纳已是不小的一次性投资,而邓承修的追加性投资,不得不借助于“其叔津贴”,“其志”当然不是“寻常好客”,而这里的“志”,自然也不是单纯的学问志向了。然而,潘祖荫和张之洞的眼里只有如雷贯耳的名士,邓承修的金石学玩不到顶尖的水平,自然就没有资格做名士,也就没有资格成为他们的座上宾;但在杨守敬的眼里,邓承修是自己的恩人,无论从官履还是道德学问上衡量,他都是前辈,潘祖荫、张之洞邀请一个后辈而不邀请邓承修这样的前辈京官,便是“标榜”做秀的明显证据。外省士子杨守敬是参不透京城学问时尚和仕途升迁之间的关系的,否则,他能抵挡住其中的诱惑吗?
杨守敬没有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邓承修没有研究金石学的天赋,也不具备收藏金石的财力,他为什么还要执着地“好金石”呢?
当然是为了追赶京城的学术和交往时尚,之所以要追赶这种时尚,是为了能够藉此晋身名士,进而取得进入名士“俱乐部”的门票。就在“清流”群起建言的光绪五年,金石热仍没有降温的迹象:“伯潜过谈,缪小山编修见过,名荃孙,江苏人,香涛名下,能鉴别金石,校勘经史,时髦也。”(19)伯潜是陈宝琛,香涛是张之洞。从同治初年怂恿而起的金石热,到了光绪初年,已经传染和延续到了张之洞的学生缪荃孙身上,初擢编修即追逐时髦。张佩纶是大名士,不必借助于时髦学问抬高自己,故可以对金石学表示不屑。“清流”名士,也并非都要靠金石学出名。对金石学的态度,正折射出“清流”名士的道德品格和政治品行:张佩纶、陈宝琛和宝廷不屑一顾,其建言亦多直抒胸臆;张之洞“始乱终弃”,金石学只是他的一块敲门砖而已,其建言则密布技巧,多政策建议,少人物击弹;(20)吴大瀓一生痴迷,终成金石大家,其建言则多书生气,政治实践则比张佩纶更加“杀贼书生纸上兵”;何金寿才气稍逊,终成二流的书画家,其建言则口无遮拦,招人怨恨,最终被一下提升到外官知府的任上。
就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来看,邓承修在京城的朋友不多,仅有的几个都是非正途出身的部吏:潘存为广东文昌人,长邓承修23岁,与“鸿胪寺卿邓承修交谊尤挚”,“服官三十年,竟无所遇。”(21)这是含蓄的表述,直白地说,半辈子都耗在户部主事的位置上了。他不可能在仕途上给予邓承修有力的帮助;陈乔森长邓承修九岁,广东遂溪人,亦捐为户部主事,而买官的银子,还是潘存和邓承修联合给凑的;李慈铭是潘、陈两人在户部的同僚,很可能是通过潘、陈的引介,邓承修得以与李慈铭结识;杨守敬则是需要邓承修照拂的外省士子。都是天涯沦落人!他们所赖以维系的人脉资源,除了同僚,就是同乡,这实在不可与翰林名士同日而语。所以,小部吏追赶京城金石学的时尚,最急迫的现实目的是多拉名士和名臣关系,爆得大名已属很奢侈的目标了。可笑的是,潘存、陈乔森、李慈铭和杨守敬通过时髦学问都成了大名士,却无缘升官发财;邓承修钻研金石未成大家,却成了光绪初年的名臣,位列京卿。其中的因缘际会,当然是由于光绪初年的“清流”建言活动:由金石而为名士,由建言而为名臣,故名士“清流”声动京师;仅止于金石名士,那就只能止步在名士。邓承修未能成金石名士,仍然成为“清流”名臣,成为另一类的“清流”。
在名士京卿与无名部吏之间,横膈着一条身份的大沟。如果部吏混不出名声来,就永远不可能跨越这条鸿沟。都是非正途出身的名士,陈乔森、潘存、李慈铭和杨守敬的官职尚不及邓承修,(22)但他们的声望却远非邓承修所可及。正因为这种声望,他们可以跨越鸿沟,游走于两个交往圈子,并且为两个交往圈子所尊敬、所倚重,通常就比其他的非正途出身官员拥有更多升擢的机会。潘存和陈乔森,或因病告老,或厌倦了等待,在“清流”建言之前,都已返回广东,否则,他们的官运很可能有戏剧性的转变。局限在小部吏交往圈子的邓承修,金石学的声望远未达到其仅有的几个友人的水平,他很可能会老死在郎中的位置上,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二 另一类“清流”
幸好“清流”建言活动在光绪初年狂飙突起,这为邓承修提供了出名的机会。然而与交往圈子一样,上折建言同样也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圈子。或者说,同治年间有名气的翰詹词臣圈子,也就是光绪初年声震京师的名士“清流”圈子。这个圈子里的重要人物是有迹可寻的,因为当时重要“清流”人物在诗歌中留下了可供爬梳的纪录。比如,光绪七年(1881),宝廷填写五言诗一组,祝贺四十五岁的张之洞擢升为山西巡抚,分别咏颂了他最亲密的三位朋友:张之洞、何金寿和黄体芳;在他光绪十年(1884)所赋的另外一组七言诗中,思念的是陈宝琛、张之洞和黄体芳。(23)张之洞在赠黄体芳花甲寿辰的七言诗中,也提到了“四谏荣名冠翰林”,只是没有开具具体的姓名。(24)陈宝琛在1912年到1917年之间写的一首诗里,开列了一个“四谏”的名单:张佩纶、宝廷、何金寿和黄体芳。(25)不同的当事人,开具出不同的“清流”人物名单,但名单总不出翰林名士的范畴,这恰好证明了“清流”有一个特定的圈子,但圈子不等于就是一个结党营私的组织帮派。在中国历史上,“广开言路”的事情并不少见,著名的“清议”活动和人物也时常呈现,同光时期的“广开言路”不被称作“清议”而被称为“清流”,奥妙就在于建言的人物大多数都是翰林院的词臣,而这些词臣在建言之前,已经是通过金石热而成为密友的名士。
这就构成了“清流”建言的特点:同僚是基础,密友是条件;先互通声气,往复讨论,然后再摆出“铁肩担道义”的架势,妙手著弹章。一弹无果,友朋跟进,此起彼伏,前赴后继。王朝时期的言路呈现这样的态势,确实有些诡异失常,这就难怪“清流”的另一位同僚王先谦在言路初起的光绪五年(1879)要参奏这种行为“恐启党援之渐”。(26)王先谦不玩金石字画,不在名士“俱乐部”的圈子里,也就无法理解这批翰詹名士“此唱彼和”、联章而奏的缘由。这有点像后来人办同人杂志,既然气味相投,那就文酒往还,只关乎文字,不关乎党援。但圈子的意识太强,不免令人反感,居于“清流”而江湖气太重,其道德上的优势也会逐渐受到质疑。
“清流”建言活动所包含的时代背景和时尚,寻常部吏如邓承修,是无论如何无法看得透的。“不闻言官言,但见讲官讲”,(27)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以翰詹名流为主体的“清流”,是此次建言活动的主角。但对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才“以部员补御史”(28)的邓承修来说,“广开言路”,也是自己久盼而至的机遇。自己是御史,是言官,知而不言便是言官的失职。于是,作为难得一见的言官之一,邓承修立即就加入到著名“讲官”的建言活动中了。这就构成“清流”建言的奇特一景:讲官群起而上呈奏折,御史单打独斗写白简。
背景不同、圈子不同、心态不同,这就决定了邓承修所写弹章的内容、角度和方法,与“清流”名士不同。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一年(1885)的七年时间里,即所谓的“前清流”时期,邓承修所上的奏折和加片累计达到76封之多,除去其中的一封谢恩折和一封请假折外,其余的都是锋芒毕露的弹劾奏章。(29)仅光绪五年一年,邓承修首论震惊朝野的东乡巨案,所论涉及到礼部尚书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童华和四川总督丁宝桢。其次弹广东学政吴宝恕,再劾使俄特使崇厚,邓承修奏章矛头所指,就是中央的巨卿硕辅和地方的封疆大吏。此后锋芒所及,云贵总督张凯嵩、浙江巡抚谭钟麟、户部右侍郎长叙、山西布政使葆亨、湖广总督李瀚章、大学士、军机大臣宝鋆、户部侍郎王文韶、大学士左宗棠,因引人注目的云南报销案而劾工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和礼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左都御史崇勋、山西布政使方大湜(并涉及到李鸿章)、总理大臣行走周家楣,都难逃邓承修的白简。当然,在中法战争前后,邓承修还弹劾了唐炯和徐延旭,驳斥过李鸿章的媾和设想。
此处之所以罗列出如此冗长的官员名单,是为了说明,邓承修仍然延续的是传统的言官建言思路,即做好朝廷耳目,抓住贪官污吏。在王朝时代的建言史上,邓承修式的搏击枢臣和大吏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因为官官相护是官场通例,官场绝对容不得异己。可以说,邓承修的成功是一个奇迹;也可以说,邓承修的成功是一个特定政治环境下必然要出现的奇迹。
为什么这样说?
首先,邓承修的言论夹杂在“清流”建言的大合唱中,“清流”的得势,无意中为邓承修的搏击提供了保护伞;尤其是在“清流”建言的重头戏中,邓承修无意中也参与其中,比如弹劾崇厚、王文韶以及中法战争期间的李鸿章,由此赢得了“清流”名士的好感,也赢得了对“清流”名士抱有好感的枢臣的关注和护佑。翁同龢本来是从不理睬俗吏的人,在光绪六年看到邓承修为俄事请调左宗棠掌兵权的奏折后,记住了他的大名。到了光绪九年(1883),即使邓承修奏折有不周之处,触犯王公,翁同龢则多方周旋,为其保驾:“其摺有应回避字,今日尚在花衣期内,邸意颇怒,费唇舌矣。”(30)如果翁同龢不愿意“费唇舌”,多少“铁汉”也架不住一个“颇怒”的“邸意”。
其次,尽管邓承修的弹章锋利不留情,但他所劾多指向贪渎事实,不涉及官场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邓承修很少弹劾洋务大员,所涉及到李鸿章的部分,也只是从吏治的角度。历史事实证明,凡是在中法战争前后“击弹”李鸿章、涉及到政府对外政策的词臣和言官都没有好下场:
计自乙酉以来,御史吴峋以劾朝邑相国,目为汉奸;编修梁鼎芬以劾合肥宰相,指为可杀,均革职;侍郎黄体芳以请开李合肥会办海军差,并饬曾纪泽遄归练师,降调御史;朱一新以陈请遇灾修省,豫防宦寺流弊,降调御史;……(31)
本书作者继昌,亦为光绪朝历史的亲历者,但他将以上言官词臣建言遭谴的原因,归结为“措语失当”,“上虑开攻击之风”,(32)则是皮毛之见。试想,每次中外危机,到了媾和的阶段,慈禧哪一次少得了李鸿章?如果李鸿章成了汉奸,那授意李鸿章媾和的慈禧,岂不成了汉奸的幕后主谋?而宦寺是慈禧的闺阁隐私,更容不得由此话题引起的风言风语。所以,凡是涉及到这两个话题的言官词臣,几乎不得以善终。
但反过来说,得到善终,并不足以证明邓承修是个如同张之洞那样的巧宦,借助建言捞取个人的政治好处。这只能说,在风云变幻的官场博弈中,没有什么背景的邓承修无意中配合上了朝廷的政策新走向。于是,本来在御史位置上徘徊不前达九年之久的邓承修,终于在光绪八年(1882)荣迁给事中,而邓承修的名声,也至少与张佩纶、宝廷等“清流”并驾齐驱了:
及补给事中,于是参权贵无虚日,有邓铁面御史之目,以鸿胪号“铁香”也。当时都中市小儿,有‘勿声张,声张邓铁知之不敢当’之谣。(33)
邓承修,字铁汉,故“有铁面御史之目”。而另一位正途出身的著名“清流”何金寿,字铁生,因此二人又被合称为“铁汉”。这都证明了邓承修建言的成功。以无名部吏而与名士“清流”并列,原因也确实在于他的“铁面”。但并非所有的“铁面”都能建言成功,梁鼎芬和黄体芳的胆子,难道不比邓承修大吗?然而,他们的“铁面”过于尖锐地触及到了李鸿章,这会妨碍慈禧的外交利益。徒具搏击大僚之胆,那只是匹夫之勇。邓承修的见识则超过了一味“攘夷”的传统清议观。他已经意识到洋务是不可回避的时代新话题,只能面对,不可回避,更不可仇视。就在邓承修迁为给事中的同一个月,其好友李慈铭发现,邓承修对日本很感兴趣:“诣铁香观日本刀,及日本钱币谱。又阅日本外史,皆何学士如璋使还所赠者。”(34)
但这不等于说邓承修此时已成为“清流”名士的同道,因为不属于一个交往圈子,因为学养和见识的不同,尽管都成为了著名“清流”人物,邓承修不仅与翰林“清流”没有私人来往,而且政治见识也不甚相同:在中法危机逐渐加深的光绪十年,“清流”名士一纸白简扳倒了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邓承修则上章吁请复用奕訢;言路一片主战,邓承修则主“缓和”(35)。这使得邓承修的声音,既区别于梁鼎芬的极端攘夷论,也区别于“清流”名士的坚定主战声。这种区别显示出邓承修的道德品行和政治见识,他厌恶“清流”名士的建言姿态,同时他对洋务不抱好感:
铁香来谈,铁香深恶洋务,又以其乡人刘云生言外夷屡欲推奉合肥,合肥挟以自重,故百计媚夷,遂甚不满之。及云生以劾合肥罢官,尤致愤憾,屡疏攻击。……余屡语知好,谓此两人必不可恃。亦尝为铁香言之,此亦不幸而中者也。铁香以此数事颇与龃龉,然能深知二张之奸,列数诸人之佞。虽为小张所荐,厚与缔交。而亦谓此辈诪张,未可尽信。朋党轻薄,事正可忧。是则雅合吾心,无慙君子矣。(36)
从前后文的语气和逻辑看,此处的“深恶洋务”,其实是深恶洋务领袖李鸿章,这是“清流”的共性之一。真正“深恶洋务”的恰恰是李慈铭本人,所以他很愿意将邓承修引为反洋务的知音。邓承修的政治见识不仅与翰林“清流”不同,而且与好友李慈铭也有分歧;他不仅与翰林“清流”不来往,而且极其鄙视其道德品行。这些,不是再一次证明了“清流”非党援、多层面的特性吗?和而不同亦君子,同而不和则是小人。邓承修显示的是“清流”和而不同的一面,独立思考,直抒己见。这无疑给予慈禧朝廷有忠直之臣的安慰。“清流”人物的职位提升,不是没有可以理解的理由。具体到邓承修而言,正四品的给事中职位,是邓承修参与“清流”建言以来的第一个收获,也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台阶。就如同翰詹词臣由内阁学士而跻身侍郎,邓承修由给事中而即将晋阶卿贰。如果说翰詹词臣为清华之位,科道给事则是清要之职。凭借此席,邓承修不会再在“清流”面前感到自卑,因为他从另一条道路上也走入到名臣的行列,在他的面前,同样是一条通向六部堂官的通畅大道。
三 另一种结局
借助于中法危机中的表现,邓承修果然官运亨通。如同张佩纶、陈宝琛、吴大瀓一样,在光绪十年(1884),邓承修连续官升三级:先是闰五月授内阁侍读学士(从四品),与翰林仕途上升中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和侍读学士同级别,难怪其好友梁鼎芬赋诗祝贺,发出“直从百僚底,上动九重尊”(37)的赞语,这意味着,那批翰詹出身的“清流”们从名士而致名臣的仕途,邓承修从谏臣而致名臣,所谓殊途同归,而且时间上几乎也不分先后;接着是七月授鸿胪寺卿(正四品),至此终于身处卿贰的行列。虽说比不上张佩纶的左副都御史(正三品)和会办大臣的身份,而且鸿胪寺属于传统的闲曹冷署,但重要的是,在八月份,邓承修又兼任总理大臣。假如没有总理大臣的兼职而徒为鸿胪寺卿,那这个九卿之一的高位只能算是一个荣誉职位。道理很简单,总理衙门是巨卿大僚汇聚之地,此时的邓承修,已经可以在总理大臣的头衔下与他们平起平坐。《翁同龢日记》中留下的“始识邓铁香”(38)的记录,就是邓承修以同僚的身份与这位帝师兼尚书的首次零距离接触。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邓承修晋阶的速度,比之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和吴大瀓辈稍慢一拍,这里当然与交往圈子及其人脉网络关系极大。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说,火箭般的窜升将翰林“清流”推上了中法冲突的最前沿,那么,稍慢上升的邓承修则成为慈禧用人夹袋中的“第二梯队”,这使得邓承修能够在中法战争后的清算“清流”行动中保得全身,同时也使得他成为中法战争后深受朝廷倚重的“清流”名臣。陈宝琛于1913年所赋诗中也有对“清流”建言历程的“事后诸葛亮”式的叙述,明显将邓承修看成是“清流”的同路人和后继者:“往日回思真可惜,众芳委绝更谁任?”(39)官场的早升迟降,是福还是祸?还真是很难预料、一言难尽的事情。
既然翰林“清流”尽毁于中法战争,那么,战后所要涉及的洋务交涉,谁是最佳的人选呢?那当然是非正途、非名士出身的“清流”。此时扫视朝廷,忠直而又懂洋务的人物还有几人?红透京城的翰林“四谏”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唯一仅存的硕果张之洞,其实早在身膺山西巡抚之职时,已脱胎换骨,由“清流”变成了注重实效的能臣。中法战争之后的勘界事宜落到邓承修的头上,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至于刘体智所言,“政府用人近于恶作剧”,实在缺乏依据,是民国笔记因厌恶慈禧而将其不断妖魔化的产物:
邓铁香侍御以强项名,派至译署以折之。侍御非文端、文正二公比,不敢不往。虽疏请改武官,军营效力,以为尝试,不获所请,而仍就任。继又以谈边务,而使往勘越南边界,大窘而返。(40)
邓承修不是倭仁,同文馆之争的同治六年(1867)更不是洋务盛行的光绪十一年(1885)。此时慈禧惟恐找不到可以纵横驰骋的洋务高手,而大臣亦深以懂洋务而顾盼自雄。如果慈禧对下属不满,实在没有“派至译署以折之”的必要;再说,中法战争前后的慈禧尚充满励精图治的精神,委“清流”以洋务大任,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实际表现,意在冲破军功和捐纳官员剧增之后的吏治因循和腐败。民国时期笔记中所津津乐道的慈禧先利用“清流”先开言路、又利用中法战争清除“清流”的说法,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想象在内。且不说慈禧不会拿国运去对付几个白面书生,更何况,慈禧用人,自有她的深思熟虑。光绪父亲醇亲王奕譞是这样解释朝廷启用“清流”人物的动机的:
朝廷令张佩纶往福建,原为外间督抚奏报全是粉饰,欲得破除情面之人,使之有所顾忌,非要他去打仗也。伊办事固不妥,闽人所探亦多出于私憾也。(41)
这段话,是钦命广西勘界大臣邓承修离京上任前夕,与醇邸话别时听来的肺腑之言。此时领导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撤职未久,继任的礼亲王世铎能力有限,故慈禧特命有事需与奕譞共商,由此奕譞成为军机处的幕后掌舵人。他的这段话,很有可能得之于慈禧之口。也就是说,这段话实际上反映的是慈禧的真实想法。面对外交交涉,慈禧的难处是,要用洋务能臣,又嫌其过于软弱,一味退让;要用“清流”人物去去力争利益,又嫌其只知争执,坏了邦交。或者说,慈禧启用“清流”,是有鉴于“各省督抚绝少实力任事之人,皆由任用私人,不肯破除情面”(42)的内政现实,而擢升后的“清流”首先要面对洋务交涉的现实,那是时势使然。赏其能“破除情面”,又恨其不能任事,这是战后慈禧处理“清流”时的复杂心情。在勘界大事上继续任用“清流”邓承修,是否也蕴含着慈禧对名士“清流”的眷恋之情呢?慈禧希望邓承修不会重蹈名士“清流”的覆辙,因为她对邓承修的评价是——“向来办事尚认真,才具亦好”,(43)这是对邓承修政治觉悟和洋务技术能力的双重肯定。
但是,慈禧在处理洋务危机时心态和情绪不稳定,一旦对外交涉出现预料不到的波澜,很容易迁怒于人。这就形成被任命的交涉大臣先荣后辱的悲剧命运。郭嵩焘是一个例子,任用时好话说尽,近于谄媚:“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44)后来呢?则屡斥其“不顾大体”。(45)崇厚的例子也是如此。这使得慈禧留下了一个很恶劣的形象:先给人戴高帽,最后下狠手。大概历代帝王都有这种心理和境界,在慈禧身上,这种心理和境界表现得更为典型。邓承修是直接参与弹劾崇厚的“清流”主将之一,他对慈禧的心理不会很陌生。再说,翰林“清流”或充军或撤职的命运,在邓承修的心里,恐怕少不了兔死狐悲的滋味。邓承修勘界日记中记下了在召见时与慈禧的对白:
天津条约已定,北圻统归法人保护,无可活动,只可不令他人到占我尺寸而已。臣昨与德润商量云:此事必须通盘筹划,不可遽云活动。缘北圻与广西联界,土瘠民贫。云南多出产,彼所注意。我若多占粤境,彼必藉口侵占滇境,洋人做事精密,我必吃亏,不可不防。皇太后说:汝这话,说得不错。(46)
邓承修不愧是部吏出身,头脑清晰,说话很有分寸。强调此次勘界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这是实话,因为勘界是中法战后所订条约中规定的事情,既然是例行公事,使臣则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空间,弦外之音,当然也是保全自己的策略;强调“通盘筹划”,那是为了集思广益,以免偏执误事;强调“不可遽云活动”,那也是吸取了前辈的经验,仓促行事,忙中出错,最后倒霉的还是具体办事的钦差;强调“洋人做事精密”,那是暗示京师臣僚不肯“实心任事”,恐怕也是提醒配合使臣的其他官员也应该做事精密些吧?
但事情的发展是邓承修所无法控制和想象的:“通盘筹划”、众人献计的结果,是相关的疆吏、枢臣及幕僚各呈与一己利益或有关或无关的高见宏论:
云贵总督岑毓英则请令法退还北圻数省,于河内、海阳通商;两广总督张之洞则谓三不要地为历朝旧界,宜划归中华;时议又谓法兵病饷艰,议院欲弃北圻,宜划谅山河北驱驴为我界,谅山河以南,东抵船头、西抵郎甲河以北为瓯脱;更有谓越乱方炽,法力已疲,待其计穷,方易就范。持论不已。(47)
这一时期不仅人言言殊,而且同一个人,过几天就会推翻自己的前说,提出新的主张。比如张之洞,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初七日、十二日就推出了三种方案,而其建议始终围绕着慈禧的最高指示——“多争一分,即多得一分之益”(48)而展开,这再次证明了张之洞用心之巧,确为巧宦。这样的“清流”前辈,也为邓承修所鄙视和愤怒:“议论阔大而无当,蹈空而不求实,欲复电辩驳。”(49)战后的两个著名“清流”人物,大有相互看不起之势,如果“清流”有党援,哪有仅剩的两个“党员”公开吵架之理?
然而,主意改得快的不止张之洞一人,慈禧本人何尝不是朝令夕改呢?十一月十三日,慈禧突然一改此前寸土必争的架势,要求邓承修等“速了”:
法办北圻费手,又避弃地之辱,取舍正在两难。我若逾约而争,彼或藉口罢议退去,则釁端终归未了。该大臣等守定“改正”二字,辩论甚是。惟须相机进退,但属越界之地,其多寡远近,不必过于争执,总以按约速了,勿令藉端生釁为主。(50)
其实,“速了”并不是慈禧的初衷。不过,在对外媾和问题上,慈禧往往又成了李鸿章的提线傀儡。只要李鸿章说,法人勘界目的不达,必再起战争,慈禧一定唯李鸿章之马首是瞻。下面一封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函电,明显是以法国勘界使臣的意见来压服他人:
勘界一事,近日叠奉谕旨照约速办,勿滋衅端。原以保乐、海宁叠议,争地过多,恐资藉口。大局攸关,刻廑慈虑,乃连日未得电复,而浦已停议。戈欲进京,显以违约为词,哓哓诘问。若再固持前说,势将决裂开衅。(51)
引文中的“浦”指邓承修的谈判对手、法国勘界使臣浦理燮,“戈”则为李鸿章的对手、法国驻华公使戈可当。谈判老手李鸿章连抛两张王牌——一是要求“速办”的谕旨,一是“势将决裂开衅”的可怕后果——来逼迫邓承修按照自己的谈判路线和策略走。此时是光绪十二年(1886)的正月,也就是说,谈判甫及一个月,朝廷高调强硬的既定方针突然转向低调稀软,这多少有些像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表现,而且慈禧对待邓承修的态度,也恰如道光帝对待耆英的态度,请看此年二月的一道电旨:
饰词规避,始终执拗,殊属大负委任。邓承修、李秉衡着交部严加议处,仍遵前旨迅即履勘。傥再玩延,致误大局,耆英治罪成案具在,试问该大臣等能当此重咎乎?(52)
钦差使臣尚在前方卖命,慈禧竟然以治其死罪相威胁,这是女主心胸狭窄、出尔反尔的典型一例。边事尚无结果,先把替罪羊送上绞刑架,这岂不让邓承修齿冷心寒?在京的老友李慈铭道出了朝廷官员对待勘界的不同态度和复杂的人事玄机:
铁香移檄罢议,朝旨责其专擅,而随同勘界之道员李兴锐驰电上书合肥,言邓星使始则不肯遵旨办理,继则拘泥失机,以致偾事;且云动则负气,辱骂百端,万不能与之共事,故先还龙州。合肥以之内告,而言兴锐老成朴实,其言可信。有旨令粤督察实。张之洞素不喜铁香,又恐触夷怒粤,且受祸己,与粤东抚臣倪文蔚皆称病求去,遂复疏言邓承修违诏挑釁。是实(时)铁香适以病,乞入关就医。亦疏陈关外情形,有惟圣主哀怜,少加明察语,遂被严旨,责其负气规卸,不许入关,如再抗延,有咸丰间耆英成例在,并交部严加议处,有实属大负委任之谕。(53)
引文中的李兴锐为老资格的洋务能臣,长邓承修十三岁,曾为江忠源、骆秉璋和曾国藩的部下,目前又是李鸿章的爱将。勘界前为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勘界时的头衔为直隶候补道,也算是正四品,但资格远非邓承修可及。按照李慈铭的说法,此时的邓承修,不仅仅是腹背受“敌”,而是“中”了四面埋伏:朝廷、疆吏不支持,外交“团队”中的属员也跟自己捣蛋,而且这个属员是大有来头的。这种局面,简直就是郭嵩焘出使英伦人事安排的翻版——辅助正职的,恰恰是与其背景和政见完全相左的人,这大概也是玩弄相互牵制的用人之术吧。而最终的结果,恰恰也是属员扳倒了上级,有李鸿章撑腰,李兴锐就敢背着邓承修,单独给予法方许诺:
及李道回关,即向修说:我今日专擅,已许东界沿边十里。修即云:炮台之炮,可击至十里许,彼若沿边筑台,我界俱站不住,此事何能轻许?李道云:与西人说话,必要爽快方好。(54)
这是邓承修的一面之辞,时在光绪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客观与否,可与其对头李兴锐的记载相印证,时间是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早间,邓忽私语赫政函致文渊,谓文渊以东沿边要十五里,是使我与爵堂失信与法人也,是令法人嗤华人无厌,虽特许昨日十里、三十里之议,恐尚非止境,徒启欲心,不如两说皆不答应,宁可事败而垂成也。(55)
由此可见,李兴锐确实越权行事,背着钦差邓承修做小动作。当邓承修意欲加以修正时,李兴锐丝毫不把钦差放在眼里,并以撂挑子相威胁:
邓以我识破机括,因羞为怒,糊言辱我,我亦不相让,大相争闹,拂袖归斋。少顷,爵堂、虞裳、枢先来相解慰。夜间,护院已如之。余谓:我亦衔命来此,邓某如此无状,尚可一朝居耶?即制电言求合肥代奏,并具禀告病,命仆从安顿夫役,收检行李。(56)
装病的李兴锐可以藉口疾病要挟,朝廷不加严饬;而真病的邓承修以病乞医,竟然遭到“负气规卸”的训斥。两相对照,令人不得不畏雌威之恐怖。事情至此,邓承修除了放弃自己的政见和人格,别无出路。但作为“清流”中的“铁汉”,邓承修仍然难以尽舍“清流”的“固性”和“刚性”,(57)在光绪十三年(1887)正月勘查江平、白龙尾段时,再次提出自己的见解,结果又遭到慈禧“勿再鹜此虚言”(58)的警告。
伴随着这种刺耳难忍的训斥声,邓承修在这年的二月份完成了勘界任务。签下自己大名的一霎那,他的心情到底如何?“饮法人香槟酒,微醉。”(59)颇有借他人之酒,浇心中块垒的无奈与伤感。虽然朝廷将其处分“加恩宽免”,但邓承修去意已定,屡经肯请,终于在光绪十四年(1888)获准开缺。此次返乡,乃生死别离,京师这块名利场,邓承修不会再回来了,这样地离别,李慈铭并非初次遭遇,但仍然感慨万端:
铁香来辞行,为之黯然。铁香自越边划界既不得其志,回京复命,东朝颇慰勉之,遂乞归。朝士得如铁香之归者,有几人哉?知难知止,洁身而退,年甫强仕,归奉老亲,朝廷眷留,天下想望风采。如余者,汨没冗部,头童齿豁,孓然一身,鸡栖不归,真非人类矣。(60)
三年之后,邓承修卒于家乡的丰湖书院,享年五十岁。成名于“清流”建言,遭挫于洋务交涉。中法勘界留给他的身病和心痛,不会与他的过早离世没有关系吧?
注释:
①宝廷《言志》诗,收在宝廷著、聂世美校点《偶斋诗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②“道、咸间,士人多以点翰林为仕官捷径,由编修、检讨十年可至侍郎,虽未必尽然,亦差不多。”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③论起金榜题名的年纪,张佩纶23岁,陈宝琛20岁(17中举),宝廷28岁,张之洞26岁,为探花(15中举),黄体芳31岁(19中举),何金寿生年不详,为同治元年榜眼。
④参见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册,卷63,第5036页;佚名辑《清代粤人传》(中),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版,第769页。
⑤何刚德:《春明梦录》(上)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37页。
⑥同上,第38页。作者何刚德为光绪三年(1887)进士,所见所闻极为真切。
⑦中科院历史所第三所编《刘坤一遗集》(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3页。
⑧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
⑨参见《清朝野史大观》之一《清宫遗闻》,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78-80页。
⑩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11)王伯恭:《蜷庐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王氏为潘、翁的门生,所记当属信史。
(12)《翁同龢日记》中多处记录了与这批翰林官的交往,交往的方式,当然免不了诗酒酬还。参见其日记第1至第4册。
(13)张佩纶:《涧于日记》(1),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从第11页到179页,隔两三页就有友朋聚集的记载。
(14)同前,第1册,第24页。
(15)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12),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00-10102页。
(16)高阳:《同光大老》,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7页。
(17)杨守敬晚年撰写的年谱中,很可能将此次的时间误记为同治四年(1865),此年的与会者,都是同治十年龙树寺燕集的名士。再说,杨守敬于同治二年在京开始学金石,回去又得准备会试,两年之后,不太可能就成为金石学的名家。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收在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1),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18)同前,第1册,第12页。
(19)《涧于日记》(1),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33页。
(20)这一点,宝廷就已在光绪七年(1881)明确区分了:“君言富经济,我言空击弹。”《偶斋诗草》(上),第54页。
(21)《潘存列传》,收在《清代粤人传》(下)第1454页。
(22)邓承修所捐郎中为正五品,与六科给事中、詹事府左右春坊庶子以及各府同知的级别相同,高于翰林院的侍读和侍讲(从五品);而陈乔森和潘存乃户部老主事,为正六品,级别与詹事府的左右中允相埒,高于翰林院的修撰(从六品);李慈铭同治九年(1870)四十岁时才中举人。
(23)张之洞于光绪七年连升三级:翰林院侍讲学士(正四品)、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正二品)衔及山西巡抚(从二品),从文学侍从一跃而为封疆大吏。故知《送张孝达前辈巡抚山西》写于此年;而《岁暮怀人四首》中自注黄体芳“提学江南五年”、张之洞“巡抚山右”、陈宝琛“提学江右”。按黄体芳于光绪六年(1880)提学江苏,张之洞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七日奉旨赴京接受召见,四月二十八日即署理两广总督,陈宝琛于光绪八年(1882)提学江西,光绪十年四月已“会办南洋事务”,那么,宝廷此处的“岁暮”应当是光绪九年,即此诗写作的时间,而这时黄体芳为江苏学政只有四年,宝廷记忆有误。参见《偶斋诗草》,上,第54页、第75页;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5-28页、第38-41页;黄体芳撰、俞天舒编《黄体芳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97页;《德宗景皇帝实录》(3),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50,第117页上及卷181,第532页下。
(24)《张之洞全集》(12),第10539页。
(25)陈宝琛原诗为“同时四谏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浊泾。”自注云:“时称张、宝、何、黄,文襄尚未在讲职也。”按陈宝琛此处所指“四谏接踵”而起的时间当为光绪五年(1879),根据有二:一是此诗为怀念吴可读,而吴“尸谏”发生在光绪五年;二是陈宝琛、张佩纶、宝廷、何金寿、黄体芳于光绪五年皆在“讲职”,即有直接上折权,而张之洞要到光绪六年才获“讲职”。在陈宝琛看来,“清流”兴起的年份是光绪五年,而“清流”的资格,则在于有“讲职”。参见陈宝琛著、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26)《德宗景皇帝实录》(2)卷97,第441页上。
(27)何刚德:《客座偶谈》,上海书店1983年版,卷1,第11页。
(28)《邓鸿胪奏稿跋》,收在《杨守敬集》(8),第1142页。但杨守敬说邓承修升迁御史的时间为“光绪中叶”,这是晚年记忆上的失误。实际上,邓承修于同治十二年由郎中授浙江道御史,光绪元年平调为江南道御史,光绪五年再平调为云南御史,光绪七年(1881)截取外任知府,旋又改为御史。这反映出仕途的壅塞和升迁机会的渺茫。
(29)参见邓承修:《语冰阁奏议》,参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1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30)“文口、邓承修各封事。”此为翁同龢日记中首次提到邓承修的名字。参见《翁同龢日记》,第3册,第1500页;第4册,第1757页。
(31)(32)继昌:《行素斋杂记》,上海书店1984年版,卷上,第30页。
(33)《邓鸿胪奏稿跋》,收在《杨守敬集》(8),第1142页。
(34)金梁:《近世人物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页。邓承修对日本的兴趣,当与杨守敬有关。
(35)《请兵建亲贤疏》,《请急筹战守议》,收在《语冰阁奏议》,第267~269页,第281-285页。
(36)《越缦堂国事日记》(6),第3275页。
(37)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沈云龙编《近代中国资料丛刊》(74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38)《翁同龢日记》(4),第1897页。
(39)《沧趣楼诗文集》(上),第164页。
(40)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6页。
(41)(42)(43)《邓承修勘界日记》,收在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116页。
(44)《郭嵩焘日记》(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45)《德宗景皇帝实录》(2),卷73,第129页上。
(46)《邓承修勘界日记》,收在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第117页。
(47)《清代粤人传》(中),第806-807页。岑毓英的建议得到谕旨首肯。此处“时议”事实上也是张之洞的建议,时在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致龙州邓钦差、李护抚台》电牍中。所谓“法力已疲,待其计穷,方易就范。”是驻法使臣许景澄从巴黎发回的情报,根据是法文报纸。参见《张之洞全集》(7),第5078页、第5082页、第5080页。“李护抚台”指的是广西巡抚李秉衡,亦奉旨参与勘界。
(48)《德宗景皇帝实录》(3)卷217,第1051页下。《张之洞全集》录为“即多一分之利益”,似衍出一字。参见《张之洞全集》(7),第5078页。
(49)《邓承修勘界日记》,收在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第142页。
(50)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页。
(51)《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5页。
(52)《德宗景皇帝实录》(4)卷224,第20页下。
(53)《越缦堂国事日记》(6),第3607-3608页。
(54)《邓承修勘界日记》,收在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第156页。
(55)(56)廖一中、罗真容整理《李兴锐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5、125-126页。
(57)参见杨国强先生对“清流”政治性格的分析。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史林》,2006年第4期,第1-28页。
(58)参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2),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2217~2218页。
(59)《邓承修勘界日记》,收在萧德浩、吴国强编:《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第163页。
(60)金梁:《近世人物志》,第195页。
标签:张之洞论文; 杨守敬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同治中兴论文; 邓承修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光绪论文; 李鸿章论文; 张佩纶论文; 金石学论文; 陈宝琛论文; 黄体芳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