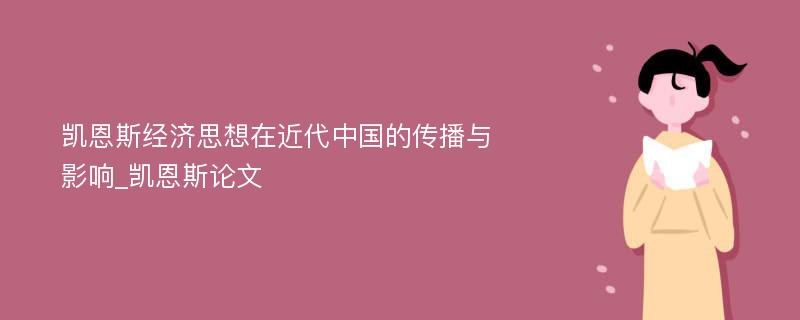
凯恩斯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凯恩斯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经济学界极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大萧条、实现国家经济政策转型时期的枢纽人物。凯恩斯虽然与中国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对于涉及中国的许多问题他都有关注。早在1912年,凯恩斯就曾在《经济学杂志》上撰文评论留美中国学者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英文版,1911),指出中国学者(如明初叶子奇)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货币数量说”。1918年,在反对德国赔款问题上,凯恩斯还援引强加于中国的“庚子赔款”为先例。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他提出英国和美国应中断与日本的全部贸易关系。1941年,凯恩斯提议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①或许缘于此,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凯恩斯传》的中文版序中总结道:凯恩斯“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朋友”。②1946年4月21日凯恩斯逝世,中国《金融周报》予以及时报道③;中国学者发表多篇悼念凯恩斯的文章。④ 那么,近代中国学者是如何看待凯恩斯经济思想?又是如何对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做出回应呢?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国内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此相关的文献较少。本文以在当时中国均产生一定影响的三部凯恩斯著作⑤为线索,以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出版为分界,系统梳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发展转变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并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探察凯恩斯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凯恩斯《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两部著作的出版引发了欧美货币金融讨论的高潮,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货币金融理论思想。《货币改革论》针对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货币失衡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和建议,认为“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并辅以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温和调节,就可以稳定物价,克服萧条,恢复英国经济的均衡和繁荣”⑥;《货币论》则将“《货币改革论》中的货币数量论加以修订,增加一些被认为忽略了的因素,扩展成为‘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了物价水平的稳定和经济的均衡”⑦,从而建立了一套货币经济学的新体系。1925年,《晨报》副刊国际版第6、7期连续刊登了凯恩斯的文章《英国币价与生活》(上、下)。1931年1月,《中行月刊》书评栏目中介绍了凯恩斯的《货币论》一书,这是目前掌握文献中近代中国学者最早关于凯恩斯著作的评介。书评作者卢逢清将凯恩斯译为“经尼斯”,对《货币论》评价较高。卢逢清认为:“经氏(凯恩斯——引者)著此书之取材结构,博适周密殆无复加,在货币论著界中,可称发前人所未发最成功的尝试。”⑧《交行通信》现代经济情报国际经济版两次报道了凯恩斯要求发行国际通货的提案,虽然未加评论,但足见当时凯恩斯在国人货币研究领域中已产生一定影响。⑨此时的中国学界也正展开对于货币金融思想的探讨论证,以寻求中国货币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应对世界经济大萧条及西方各国经济复兴政策的冲击。因此,凯恩斯的货币思想特别是通货管理思想受到中国学界高度重视。 (一)对于凯恩斯货币思想的理论解读 1930年以后,货币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学者们理解和接受新的货币理论存在一定困难。胡寄窗指出:“有的货币学家曾承认自己还看不懂凯恩斯的《货币论》,是无足为怪的。”⑩原因大致有二:其一,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货币学闻名的中国学者大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从国外学习的货币学内容,主要还是分析货币的职能与本位制问题;其二,由于职务变动等因,凯恩斯的《货币论》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数年来论文集结而成,前后并不连贯,其中思想也多有发展改变,本来是支持货币数量说,最后却创立了储蓄与投资均衡说。所以,当时中国学者对凯恩斯货币思想进行理论性解读比较困难,仍处在混沌中摸索的状态。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杨端六、王烈望、袁贤能等。 真正开始学习推崇凯恩斯货币思想的是国立武汉大学金融学专家杨端六。他给予凯恩斯及其著作《货币论》极高的评价。杨氏指出:“凯衍斯新出的这部货币论是货币著述中之别开生面的巨作。凯衍斯为英国新进经济学界之泰斗。”(11)杨氏总结道:“他全书的纲要是在用货币政策促进工商业的繁荣。”(12)同时,杨氏也在反思中国的货币制度。他将货币制度划分为五个等级,中国的货币制度属于第一级,即采用两种以上的金属作为货币,在国家行政、法律不统一的条件下,货币之间相互兑价无法维持。第二级货币制度是指国内行政、法律统一,国内货币兑价稳定,但国际汇兑失衡,例如欧洲各国。第三级是指国内币值稳定,国际汇兑平衡,但货币购买力会发生变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第四级是指货币购买力也达到稳定的状况。杨氏认为当时西方和中国讨论的货币学就是在第四级内解决货币如何稳定购买力的问题,而凯恩斯的《货币论》也最为关注这一级货币制度。第五级货币制度要求能够满足人类的主观欲望,具理想化色彩。杨氏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凯恩斯的货币思想,基本上把握了凯恩斯管理通货思想主张,且联系中国实际情况,注重中西货币制度的差异以及探索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大致前进方向。 上海和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上海商学院教授王烈望也认真研读了凯恩斯的《货币论》,说道:“硁斯之经济思想,变动极快,往往前后判若两人。”(13)他深入剖析凯恩斯由主张到放弃金本位制的主要原因。一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极大变化,世界金融霸权左右国际政治关系,黄金逐渐集中于美、法二国,战争赔款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货币制度在于稳定对外汇价和安定国内物价,而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安定国内物价则成为首选。在金本位制下,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动,国内物价受国际影响较大,“硁斯思想敏捷,观此情形,深觉金本位已无恢复之必要,遂毅然倡言废止金本位,实施通货管理制”。(14)什么是通货管理制呢?王氏认为:“管理货币乃系一种受政府管理之纸币,此种纸币含有一客观之价值标准,国家以管理方法,使此种纸币或合于其客观之价值标准,或离开其客观之价值标准。”(15)且指出,凯恩斯认为管理货币制度是与当时政治经济状况最为切合的货币制度,因而《货币论》中所讨论的货币即是管理货币。 曾有“南马(寅初)北袁”之称的、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的袁贤能博士则主要阐释了凯恩斯的储蓄与投资均衡说,认为凯恩斯的《货币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修正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袁总结凯恩斯所论:“储蓄若与投资相等,那是(如正统派所说)好的。不好的结果(经济恐慌),并不是因为储蓄和投资太多,乃是因为储蓄与投资不平衡。换言之,就是储蓄大于或小于投资的缘故。”(16)袁亦指出,凯恩斯的储蓄和投资都具有特别抽象的意义,与普通含义不同,这也反映出《货币论》本身定义的模糊性。但也进一步指出凯恩斯的贡献还在于提出储蓄和投资的失调决定了物价波动和商业周期的产生。为了使储蓄和投资二者平衡,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国银行“不能专为自身计而定利率的高下”,“也并不是要一个固定不变的利率”,“不过是要一个适中的利率,能使一国的储蓄,完全都用于投资方面去”。(17) 《货币论》是在分析各种经济现象的基础上,用代数方程式表示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著作中的公式,如银行利率公式、投资储蓄公式、货币数量变动公式、物价公式等。虽然中国学者对于凯恩斯著作的学习和理解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由于凯恩斯所提出的新概念本身比较模糊,加上当时中国学者对于金融理论的认识有限,所以对于凯恩斯货币论理解上难免有较大偏差,所做探讨亦缺乏统一的思路,基本上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二)凯恩斯管理通货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实践 币制混乱、流通不畅的问题长期困扰着近代中国。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后,西方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1934年6月,年产银量占世界总产量66%的美国突然宣布实施《购银法案》,授权其财政部高价购买白银,此举造成世界银价飞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如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成为当务之急,关于中国币制改革的讨论和筹划再现高潮。 尽管对于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两部著作中的货币理论理解尚为有限,但是国人对其中的管理通货思想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顾翊群首先主张中国采用管理通货制度,并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践。姚庆三、唐庆永、赵兰坪、杨荫溥、张素民、谷春帆等也先后撰文表示支持。 较早评述凯恩斯管理通货思想的学者是唐庆永,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三江大学教授。1932年7月,唐撰文指出,凯恩斯管理通货思想“虽可谓之纸币本位政策,而对于纸币背后物价——金,却始终未尝抛弃,仍留作为准备之用”。(18)同时指出,在中国信用制度不健全、中央银行发展落后的局面下,凯恩斯的这一主张完全是一种理想化的纸币政策。所以,他主张中国发行纸币的原则一定是要有银块作为准备金,本质上是主张银本位制。 1933年4月,顾翊群发表《再论美国购银之危险性》一文,举述西方国家放弃金本位、实行管理通货制,挽救了生产和贸易,以此说明我国也应该实行管理通货制。他指出:“昔英国银行实业两界,对于J.M.Keynes氏所主张之通货管理制,避之若俛,今则歌颂不已。我国因美国购银,采用斯制,愚信利多于害。”(19)9月,顾再次撰文,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世界和中国为什么都要采取通货管理制度,并系统地阐释其关于实行管理通货制度的思想,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维持物价平衡。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顾翊群主张的“管理通货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行不兑现纸币,其最终目的还是实现金本位。顾翊群认为:“主张管理货币之学者,并不反对金本位,且认为将来世界必须实行管理制之金本位。不过在今日情况之下,金之价值,受国际影响太大,难以管理……故不得不改用便于管理之纸币,为自了之图。”(20) 对于顾翊群的论说,经济学界予以积极回应。马寅初认为这是稳定银价的四个重要方策之一。(21)何廉在提出美国抬银运动的对策时,几乎原话复述了顾翊群提出的管理通货思想。(22)赵兰坪也认为,顾翊群是最早提倡“管理通货制”者。(23)凯恩斯提出的管理通货论在中国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管理通货”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名词,且为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对《货币论》的观点做出了重大修正。《通论》侧重于对全社会总供给、总需求、投资和消费等总量的分析,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等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 《通论》刚刚问世,英文版便在中国上海、汉口等地出售,陈岱孙、巫宝三、姚庆三等人先睹为快。(24)1936年9月,留法归国的财政金融专家姚庆三即在中国经济学社上海年会上引用了《通论》中的观点。(25)1941年,王兼士在《金融导报》上连续发文10篇译述凯恩斯的《通论》。各大期刊杂志上也刊登了多篇凯恩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的译述。(26) 随着凯恩斯《通论》在中国的影响日盛,中国学界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研究逐渐深入,由只关注凯恩斯货币思想,特别是管理通货思想,逐渐转变为关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其中包括凯恩斯的货币思想、财政思想、就业思想等,并将其与西方传统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比较。 (一)中国近代新货币理论体系初步建立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学者翻译或自撰的许多货币学著作虽命名为“新货币学”,但其内容相对于凯恩斯的一些著作,仍属于旧的货币学体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货币学家开始更多关注凯恩斯货币理论,有的还以凯恩斯思想为基础建构自己的货币理论体系。 在中国近代货币理论发展史上,留法归国的财政金融专家姚庆三是较多且较早介绍西方货币理论的知名学者之一。他对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甚是推崇,认为其必将成为今后新经济学的柱石,“现代货币学者之在我国最负盛名者当首推凯恩斯”。(27)1937年6月,姚庆三撰文《凯恩斯货币理论之演变及其最新理论之分析》,分11个专题详细阐述了凯恩斯的货币思想:货币改革论中之凯恩斯、货币论中之凯恩斯、世界经济恐慌与凯恩斯、凯恩斯就业理论之出发点、消费天性、公共建设政策、低廉资金政策、储蓄与投资、关于低利政策之其他问题、高利政策是否可防止恐慌、物价问题。1938年9月,此文被收入《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一书。虽然姚庆三对于凯恩斯的新货币理论大多述而不作,但他对凯恩斯货币理论的介绍和认识无论从及时性还是在系统性上,都达到了当时其他学者所没有达到的高度。(28) 较早对凯恩斯货币思想进行深入论介的中国学者是陈国庆,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和袁贤能,而后在天津达仁学院攻读研究生。读研期间,他撰写了《凯因斯氏的货币理论及其演变》一书。可以说,这是我国最早深入研究凯恩斯理论的专著。(29)陈指出:“凯因斯先生的一般理论推翻了传统的价值分配论与货币理论的分野,他把价值与价格打成一片,造成一部一般理论或是全体出产与雇佣的理论。这至少在方法方面,他自己也这样承认,已经跳出传统的经济学的范围,而步入另一个崭新的境地。”(30)因此,陈国庆是在理解《通论》理论思想的基础上阐述凯恩斯的货币思想,更为客观且更为深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同时代西方学者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陈国庆认识到《通论》中的经济思想主要围绕总产出进行论述,而货币理论的目的也在于为总产出服务。他探讨了《通论》的三个立足点—消费者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论,讨论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心理法则以及消费函数,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货币理论中的流动性偏好、货币的供给与需求、银行如何控制货币量等问题。他非常清晰地指出货币扩张会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提高收入,并在其中正确运用了乘数理论。但是他没有涉及劳动力市场和总需求如何影响产出和就业问题,陈国庆更加关注的应该还是凯恩斯货币思想。 此时,中国已经有学者以凯恩斯专著“三部曲”的出版时间作为标准,将凯恩斯货币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现金余额说”,完全信奉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A.马歇尔和A.C.庇古提出的货币数量论;第二个阶段为“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是对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修正,将利率、现金余额以及各种物价的决定联系起来;第三个阶段则为“物价的一般理论”,对货币数量论持反对意见。(31) 在诸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凯恩斯货币思想为基础建构货币理论体系的货币学著作陆续问世。新的货币理论体系有别于以往主要分析货币的职能与本位制的货币学体系,两部代表著作分别为马寅初的《通货新论》和刘涤源的《货币相对数量说》。1944年,马寅初新著《通货新论》,着重分析稳定币制的问题,借此评述费雪、马歇尔、庇古、凯恩斯货币数量说的不同。他所强调的货币的需求强度、预防意外支出、交易利益、生产和消费以及心理因素等,与凯恩斯就业理论中的一些必要因素如货币的需求弹性、货币的边际效用、货币偏好等,有着惊人的相似。(32)1945年,刘涤源出版《货币相对数量说》一书,用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建构其货币相对数量说,引入均衡的概念,并考虑到生产弹性、时间因素及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数量与物价关系的影响。(33) 此外,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聆听过凯恩斯课程的藤茂桐1945年出版的《货币新论》一书亦评价了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认为“凯氏的理论,在于探讨短期均衡,并非分析动态经济程序”。(34)对于凯恩斯的投资与储蓄恒等、利息理论、倍数理论等都进行了介绍和评析。同样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樊弘于1947年出版《现代货币学》一书,他将货币理论的发展分为货币价值研究时期和货币经济研究时期,认为后一时期的研究范围更为宽广。(35)樊弘指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属于货币经济理论,并重点介绍了投资储蓄理论和利润利息理论。 当然,民国时期亦有学者对凯恩斯货币理论持批驳的观点,代表人物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蒋硕杰。1943年,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经济学刊》(Economica)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进行批评,并对凯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的说法提出挑战。他采用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和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支持自己的论点。(36)蒋硕杰的有力批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并非完全盲从。 (二)中国近代财政思想的新发现 凯恩斯虽然没有财政学专著问世,但是《通论》的出版却标志着西方财政理论的“革命”。凯恩斯主张扩大政府职能,塑造“大政府”的主体特色,政府不再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应积极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他一反传统财政理论中的“就财政论财政”,转而“就经济论财政”。 当时,关注国际经济学的中国学者很快对西方财政理论的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做出了反应。姚庆三的《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一书专门分两节“公共建设政策之理论”和“公共建设政策之例证”介绍了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在财政理论方面,姚庆三主要介绍了凯恩斯财政理论对传统平衡预算理论的冲击。他认为,传统的平衡预算理论以每一年度预算平衡为目的,而当时的财政新思潮则以长期预算平衡为目的。姚赞成后者,试图用经济周期理论进行分析解释。在经济衰落时期,政府税收减少,同时又应积极推进公共建设,以增加就业人数,导致支出反而增加,所以赤字在所难免,但此种亏空可以用繁荣时期的预算盈余来弥补;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税收既可增加,同时因失业人数减少,公共建设亦可从缓进行,使得支出反而减少,因此预算不但可以平衡,且或反有盈余,此种盈余即可用于抵偿衰落时期的财政赤字。所以,从短期看,预算不平衡,财政不健全,而从长期看,预算可以达到平衡,财政是健全的。(37)在财政政策方面,姚庆三主要介绍了受凯恩斯财政思想影响的美、德、意等国实施的公共建设政策,认为这些国家通过公共建设促进了经济发展,解决了就业问题,中国应该仿行。他指出:“罗斯福总统挟美国丰富之资金,以实现其复兴计划,固无足奇,而贫困如德、意,竟亦能完成其伟大之公共建设,何哉?盖德、意两国在独裁政治之下,其政府当局能以坚决之毅力,抛弃自由放任之传统政策,而采用有计划之统制政策固耳。我国失业问题之严重,甚于德国,而荒地太大,粮食不能自给,尤酷似意国;公共建设既可解决失业问题,又可发展国民经济,德、意两国之经验,不亦足资吾人之取法乎?”(38)姚庆三还主张运用公债来推动公共建设。他建议学习德、意两国,设立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以统筹公共建设特别预算,以公债政策作为筹款的主要方式,外加利用外资。姚庆三熟识凯恩斯的投资乘数财政理论,认为“社会所得之增加额亦必远较此项公共建设之原投资额为大,其倍数可称为投资倍数”。(39)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增加政府投资的合理性,基本上把握了乘数理论的实质。总的看来,姚主张的财政政策是基于凯恩斯财政理论和美、德、意等国的实践,关键点在于利用公共建设,增加财政赤字来推动经济建设,“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类似政策建议”。(40)1940年3月《财政评论》刊出的徐宗士《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一文,对凯恩斯在财政学上的贡献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文章开篇指出:“假使我们要指出近代经济学界一颗最灿烂的明星,我们不能不推崇凯恩斯。”该文认为,“凯恩斯的学说,不但影响了英国经济政策,而且与各国现行经济设施,亦不无联系。美国罗斯福总统所行新政与亏空财政政策,以及德国国社党所行经济财政政策,不难于凯恩斯学说中找寻理论的依据”。(41) 1936年《通论》出版后,虽然凯恩斯财政理论很快就传入中国,但是对于宏观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等具体实践方面影响甚微。主要原因在于战时中国财政窘迫,通货膨胀严重,缺乏运用凯恩斯财政理论、政策等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中国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战时财政,无论战时税收论还是战时通货膨胀论均以筹集战费为主要目标,从而忽视了公共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三)就业理论的争鸣和阐释 严格意义上说,凯恩斯的《通论》思想并不仅仅起源于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可以更早地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的长期慢性萧条。(42)在长期慢性的萧条过程中,失业成为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受到了凯恩斯的极端重视,《通论》的全称即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世界经济大萧条后,失业问题越发凸显,也引发了中国学者的积极思考。 1946年,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达到充分就业”问题,学术界再次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43)引起这场争论的是徐建平,他的观点是:“就目前的中国就业情形讲,因为本国货的价格仍在上涨,固仍可从‘货币的有效需求增加而就业量不增’来推论‘业已充分就业’。”(44)吴大业也支持中国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的观点,表示:“我们认定现在通货膨胀之下,有效需要已经太多,达到‘过分就业’。”(45)并进一步指出:“当有效需要(即社会总支出)增加时,就业反应已无弹性,即到了克因斯的充分就业。”(46)他们都认为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致使中国已经达到充分就业,因此明确反对政府再发行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 对此,徐毓枬、甘士杰、丁忱两、桑恒康等人表示反对,认为中国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徐毓枬曾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亲自聆听过凯恩斯讲课,并在中国高校系统讲授凯恩斯的通论课。他还是凯恩斯《通论》的最早翻译者,实际上早在1948年他的译稿就已经完成,由于时局动荡不安,直到1957年才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列入汉译名著丛书之一,直至今天还在不断翻印。针对“中国已经达到充分就业”论,徐毓枬于1947年在《经济评论》上连发两篇文章加以反驳。(47)徐毓枬指出,当时确有一种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可以致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但需要一定的理论前提,如:“(a)货币工资在未达充分就业以前,不随物价之涨而涨,但一达充分就业,则与物价作同比例的增加;(b)劳工间有自由竞争,雇主可以在最低廉时雇用工人,故在未达充分就业以前,已就业者怕未就业者竞争,不敢抬高货币工资;(c)通货膨胀对于消费倾向本身并无多大影响。”(48)而这三个前提在当时的中国都不成立。 财政金融专家甘士杰更加着力于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指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是建立在英美高度工业化的经济社会和自由放任的经济组织基础上,与中国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且人为统制因素过盛的局面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80%以上,并没有完全就业;新兴工业所提供就业机会比重较少,且“人浮于事”、“毕业即失业”现象非常多。他指责通货膨胀和战争对于中国经济的破坏,并进一步表示政府强迫劳工增加工作、从国外输入新式生产设备、提高工人生活水准来增进效能等都可以使就业量大大增加,产量也因此可以增加。所以,中国并没有达到充分就业。(49) 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反驳似乎更具说服力,“中国没有达到充分就业”论占据了上风。“充分就业”之争表面上是经济名词之争,实质上是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理解不同而产生的争论,归根到底是在关注讨论中国是否可以增加就业、如何增加就业的问题。因此,这场争论虽然看似荒唐,但确实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过讨论,徐毓枬越发认识到凯恩斯就业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现实,遂专门撰文介绍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探讨在以私人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义体系下为什么会存在短期失业现象。他阐述了摩擦失业、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的概念和特点,并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的决定理论入手,得出短期失业缘于投资小于储蓄的结论。还将就业的变动理论引申运用到如何解释经济周期。最后,他肯定了凯恩斯的主张,即在维持以私人企业及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下,国家应该运用租税制度、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来干预投资与储蓄。(50)为了进一步明晰就业理论发展的脉络,徐毓枬还详细对比庇古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试图厘清二者之间继承与创新的关系。(51) 曾留学西欧多国的褚葆一也撰文介绍了“供给创造其本身之需求”的“叟依(萨伊)法则”与凯恩斯“以市场之有效需求为其推论之核心”的就业理论的差异。他认为,凯恩斯在就业理论方面的最大特色是宏观分析,是“以整个经济制度之活动为其分析之对象”,而“以前各家之理论,每多着眼于局部经济机构之观察,对于细微末节不惜反覆检讨,而于全局变动,及整个趋势反加忽视,致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讥”,而凯恩斯“则跳出显微镜分析之限制,而用望远镜加以观察,向整体经济学迈步”。(52)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万典武1948年发表《凯恩斯派与古典派关于充分就业的论争》一文,分析了凯恩斯与古典学派在充分就业方面的歧见。该文指出,古典派首先假定充分就业已经存在,他们对失业问题不加讨论,认为只要市场完全而劳动力又有完全的流动性,则充分就业的情形必然与静态均衡同时达到。而凯恩斯则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衰退为背景,创造出因缺乏一般的“有效需求”而发生“非自愿失业”的学说,并提议以增加投资来刺激繁荣,从而消灭“非自愿失业”,达到充分就业。(53) 1949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浦山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技术进步与就业》一文中秉持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皈依于新崛起的凯恩斯主义。他依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建立了一个包含技术进步的模型,运用静态与动态比较方法分析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他认为:“自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以来,在劳动力就业的经济理论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特别是作为凯恩斯理论重要贡献的消费函数的决定因素和作为近来所有动态商业周期理论基石的引致投资支出的决定因素这两大问题,无论是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统计估计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54)在论文中,浦山多处征引凯恩斯《通论》一书的观点分析就业问题。 总而言之,关于就业理论,学者们更多的是从理论层面讨论这一问题。大批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成为这场讨论的主力军,讨论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多是国际上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就业理论的相关概念、逻辑关系、最终结论以及政策建议等均列为讨论的对象。 (四)与其他学派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凯恩斯与其他学派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海外中国留学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群体。其中,曾于1922-1927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袁贤能、1937-193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的樊弘、1947-1948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雍文远等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内攻读学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如胡代光等,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雍文远是较早进行比较研究的中国学者之一。1945年,他准确把握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脉搏,对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雍文远深入分析二者理论上的差异,认为同样是解释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哈耶克用的是“投资过剩说”,而凯恩斯用的是“投资消费不足说”,因而结论不同。并进一步表明,认为如果达到充分就业,哈耶克的理论是正确的;而如果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则凯恩斯的理论更加实用。雍还分析了哈耶克的货币中立思想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他支持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对投资市场进行掌控的主张,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国家可以自行投资以补救自由投资市场的不足,“此种公共投资政策如果运用得当,不仅可以提高一般就业水准,而且可以避免经济恐慌的发生”。在谈到中国的现实问题时,雍认为中国当时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下有效需求过剩,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遏制通货膨胀。他说:“其实,要将西洋任何人的全部学说无条件地来解释中国战时问题,都是很危险的。”(55) 樊弘不仅比较了凯恩斯和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异同,而且对凯恩斯和传统剑桥学派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樊弘推崇马克思经济思想,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凯衍斯的研究始终亦尚未跳出马克思的巨掌之外”。(56)认为,马克思所暗含的利润率大于、小于、等于利息率的思想涵盖了凯恩斯的思想。樊弘同时也肯定了凯恩斯独特的学术贡献,认为其在马克思理论基础上,探讨了生产技术不变条件下的失业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性。而马克思较凯恩斯伟大之处,在于马克思认为不消灭资本主义,失业问题将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无产阶级必须要夺取政权。樊弘认识到经济学的新旧理论是有传承关系的,而且会随着经济状况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因此,他继而对凯恩斯和传统剑桥学派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比较。他通过分析剑桥大学教授罗博生(D.H.Robertson)与凯恩斯长约10年的争论,试图将两种思想融合在一起。他认为凯恩斯和传统剑桥学派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而是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所以,“更伟大的经济的理论,应当建筑在兼有二者之长而无其短的更高一级的基础之上”。(57) 袁贤能则主要比较了凯恩斯和穆勒的经济思想,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凯恩斯的理论“亦始终未跳出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巨掌之外”。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不是新发现,“只不过是正统学派的学说的推论罢了”,但他也肯定了凯恩斯的“小小贡献或修正”,即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派的缺点,承认了失业问题的存在。(58) 胡代光则将凯恩斯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相提并论,指出凯恩斯和马克思“已经做了正统派理论的叛逆”,“他们都根据另一种假定,建立另一种理论结构,以解析现社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虽然他们的理论本身未必完全正确,“可是他们却建立了不少正确的观念,提供了很多实际的建议,颇有耐人深思的地方”。(59)胡氏的观点可以说比较客观、辩证、不激不随。 1936年《通论》出版后,中国学术界围绕凯恩斯经济思想展开热烈讨论的同时,中国大学经济系也开始设置系统讲授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课程。凯恩斯经济理论被纳入大学教育体系,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重要标志之一。1938年上半年,迈克尔·林德赛(Michael Lindsay)来到燕京大学,他写了一本《Keynes for Beginners》(《凯恩斯入门》)作为教材,正式开始宣讲凯恩斯理论。(60)随后,凯恩斯的教学与研讨在西南联大也得到推广,徐毓枬成为主要的推动者。同期,国立武汉大学、安徽大学、重庆大学等教育科研机构均有知名教授系统讲授、研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成为凯恩斯理论的重要研究基地之一。 受此影响,当时不少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学位论文,是以凯恩斯经济思想研究作为选题,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凯恩斯经济思想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的深远影响。如燕京大学的本科生学位论文有《管理通货与稳定物价之研究》(吴奎龄,1940)、《就业理论之研究》(董伟林,1945)、《凯因斯国际收支机构学说》(邓有宗,1946)、《现代利息理论之争辩》(黄金环,1946)、《从凯因斯就业理论看中国工业建设》(吴其进,1947)等(61);武汉大学经济系1945、1946年本科生学位论文有《凯恩斯银行利率理论的分析与批判》(杨叔湘,1945)、《凯恩斯金融学说述评》(刘兆丰,1945)、《凯恩斯利息学说的综合研究》(万典武,1945)、《论凯恩斯价格决定之理论》(王善同,1946)、《凯恩斯货币理论述评》(何爱友,1946)等。(62)此外,于1939年获武汉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一生致力于研究凯恩斯学说的刘涤源,其硕士学位论文《货币相对数量说》即是以凯恩斯经济思想为指引构建其货币理论,该论文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学术奖”。南开大学1943年入学、1945年毕业的第七届研究生雍文远的学位论文选题为《皮古与凯因斯就业理论之比较研究》。(63) 凯恩斯理论在西方世界不仅引发了经济学的革命,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航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援引凯恩斯经济理论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国际潮流的带动下,中国学界从开始探索认识凯恩斯的货币思想,应货币改革的现实要求探讨其管理通货思想,到辩争与中国现实有一定差距的财政理论、就业理论(总生产理论),再到将凯恩斯理论与传统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比较研究,中国学者对于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认识逐步深化。一部分学者坚决支持凯恩斯经济思想,但范围主要局限在其管理通货理论,如顾翊群等;也有学者对凯恩斯经济思想持反对的观点,如蒋硕杰等;还有一部分学者在研读过程中有破有立,如雍文远、胡代光等。 相对而言,基于特殊的学科背景与学术脉络,海外留学生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化。他们中的大部分学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解读与分析讨论,但是他们在治学道路上或多或少地采纳了凯恩斯的分析方法。以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为例,方善桂、谢强、王念祖、桑恒康等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均大量运用了凯恩斯的逻辑思路和分析方法,这表明他们对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已经非常熟识。(64)另外一个较为突出的例证是关于国民经济统计问题,正是基于凯恩斯创立的以总量指标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国家为本位的数量分析和政策取向被强化,国民经济统计遂成为政策选择的依据。在这一领域中,留学哈佛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巫宝三(65)贡献较大,在联合国出版的《国民收入统计1938-1947年》中收录了其所提供的中国1933、1936和1937年的国民收入有关数据。另外,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统计学家金国宝于1948年出版了《凯恩斯之经济学说》一书,因暂时无法获得相关资料留待日后进一步发掘。 除了解读凯恩斯经济理论、使用凯恩斯分析方法以外,许多中国经济学者也试图运用凯恩斯理论来解决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主张,如姚庆三主张设立国民经济建设委员会,运用公债来推动公共建设,这些主张从理论上而言,有助于推动当时经济发展;但事实上,这些主张并没有真正转换为现实政策。其中原因并不在于对凯恩斯经济理论认识上的欠缺,而是因为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关注更多的是战费的筹措,而非经济的真正恢复及发展。从理论层面来看,凯恩斯理论本是应对经济危机的产物,但在中国却遭遇了恶性通货膨胀和战时经济的双重羁绊,因而改变了其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这也是其在政策操作上所起作用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66)由于凯恩斯理论在政策操作上所起作用有限,一些中国学者对其是否适用于中国提出质疑,他们的思辨最终落脚于凯恩斯理论的中国化问题。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王念祖在学位论文《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写作过程中,就对此问题提出疑问。他认为西方国家的萧条是伴随着长期不景气的趋势和战后有效需求急剧下降而产生的,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是经济萧条而是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必将以扩张货币的手段刺激工业化。当时王念祖的导师是被称为“美国的凯恩斯”——汉森(Alvin Hansen,1887-1975)教授,王念祖在学术观点上却“和他唱反调”,表现出极大的魄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67)学者万一华也指出,中国学者在讨论政府贷款政策时,纷纷援用凯恩斯的理论,结果观点大相径庭,出现了中国是否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的争论。他认为,解决这一争论的核心应该在于深入讨论凯恩斯理论能否中国化这一问题。他明确提出“凯氏理论不能硬套在目前的中国”。(68)吴大琨也指出:“有些凯恩斯的信徒们把凯恩斯的那一套‘理论’已完全无条件地搬到中国来应用——这显然是不适用的”;“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把充分就业的理论硬套进中国的社会里来,不如先集中精力来把一些凯恩斯的基本著作……翻译介绍进中国。”(69)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国化问题讨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马寅初。1948年8月,马寅初出版《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一书,在“自序”中,他专门讨论了“凯恩斯的‘一般理论’与凯恩斯学派的主张于中国是否适用”这一问题。马寅初承认凯恩斯理论的巨大价值,但是他同时强调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因此,“不能以西洋最高最新的学说来用于中国”。(70) 马寅初从九个方面论证自己的观点。第一,中国的小农经济中,经营主与劳动力结为一体,无所谓自愿失业与不自愿失业;第二,在中国农村中,储蓄者就是投资者,二者目标一致,所以投资等于储蓄不会成为一个难题;第三,中国经济没有达到饱和点,资本仍有较高的边际效率,而消费额只有增加,一时决无减少的趋势;第四,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农民生存的支柱,即使没有利润也会继续经营,因而利率政策失效;第五,劳动力在中国缺乏流动性;第六,中国的分配不均是在地主与佃户之间,不在劳动力与资本家之间;第七,在中国农业经济的现阶段,物资不会过剩,因此类似西方的经济恐慌决不致发生;第八,中国的现状是百废待兴,大规模的工程无法随举随停,政府亦无法利用公共工程投资的增减来调整经济;第九,中国政府贪污腐败,财政赤字必将产生危机。 马寅初从中国的具体现实出发,也即从理论的最初假定入手,来探讨凯恩斯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凯恩斯的大著以及凯恩斯学派的学识移植于我国,实有格格不入之弊。”且进一步指出:“若再就与本国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毫无关系之外国学说加以详尽的讨论与争辩,实是一种精力与时间的浪费。”(71)可见,在中国遭遇了具体化与适用性问题的不仅仅是凯恩斯理论。 总而言之,凯恩斯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学界及其理论发展的确起到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遗憾的是,它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像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能转化成适应各国现实的经济政策。这应该是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使然。中国经济学者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下理论与现实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赞成政府的一些政策选择的同时,也追求、信仰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割裂,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内在张力。 ①以上史实参见[英]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The Collected Writing of John Maynard Keynes(London:Macmillan Press,1983),XI pp.521—527,XVI pp.321—322,XXVIIIp.82,XXVII p.44。 ②[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相蓝欣、储英译:《凯恩斯传》,“中文版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6页。 ③“凯恩斯爵士于4月21日以心脏病不治,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二岁。”贾文林:《凯恩斯爵士逝世》,《金融周报》第14卷第18期,1946年5月1日,第11页。 ④如穆惜珍《悼凯恩斯先生》,《经济周报》第2卷第17期,1946年5月2日;性初《悼凯恩斯》,《财政评论》第14卷第4期,1946年4月;向冰《凯恩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励行月刊》第2卷第2期,1946年4月。 ⑤三部著作分别为:《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1923)、《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1930)和《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1936)。前两部著作集中阐述凯恩斯的货币思想,第三部著作则主要关注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及政策建议。1920年,陶孟和与其夫人沈性仁合译《欧洲和议后的经济》(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1919),并被纳入“新青年丛书”出版。这是目前掌握的资料中,中国学者对于凯恩斯著作的最早反应。不过,该译本在当时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影响甚微。 ⑥刘涤源:《货币论·序》,[英]凯恩斯著,何瑞英译:《货币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 ⑦刘涤源:《货币论·序》,凯恩斯:《货币论》上卷,第12页。 ⑧卢逢清:《书籍介绍〈货币论〉》,《中行月刊》第2卷第7期,1931年1月,第75页。 ⑨参见《现代经济情报(四):国际新通货(国际经济):世界经济会议之提案,英国硁斯氏之主张》(《交行通信》第3卷第1期,1933年2月,第54页)和《现代经济(九):硁斯氏之幽默语(国际经济)》(《交行通信》第3卷第3期,1933年6月,第29页)。其中“硁斯”为凯恩斯的译名之一,其他译名如凯衍斯、凯因斯等。 ⑩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 (11)杨端六:《读凯衍斯货币论》,《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2号,1931年6月,第375页。 (12)杨端六:《读凯衍斯货币论》,《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2号,1931年6月,第384页。 (13)王烈望:《硁斯之通货管理论》,《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2期,1935年8月,第86页。 (14)王烈望:《硁斯之通货管理论》,《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2期,1935年8月,第86页。 (15)王烈望:《硁斯之通货管理论》,《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2期,1935年8月,第91页。 (16)袁贤能:《硁斯著货币论》,《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2期,1935年8月,第172页。 (17)袁贤能:《硁斯著货币论》,《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2期,1935年8月,第174页。 (18)唐庆永:《废两改元与纸币政策》,《银行周报》第16卷第30号,1932年8月9日,第24页。 (19)顾翊群:《再论美国购银之危险性》,《银行周报》第17卷第12号,1933年4月4日,第8页。 (20)顾翊群:《中国货币应如何安定》,《银行周报》第17卷第36号,1933年9月19日,第11页。 (21)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1935年1月),《马寅初全集》第8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9页。 (22)何廉:《银价问题与中国》,《银行周报》第18卷第10号,1934年3月20日,第15页。 (23)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时事月报》第14卷第2期,1936年2月,第95页。 (24)Paul B.Trescott,“How Keynesian Economics Came to China,”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4,No.2(2012),pp.343—344. (25)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7页。 (26)参见钟淦恩《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经济汇报》第7卷第10—12期,1943年;曹茂良译《凯因斯货币论(第二编货币之价值)》,《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第1卷第1、2、5、6期,1943年和1944年;邝鸿译《货币改革论》,《储汇服务》第80—86期,1948年。 (27)姚庆三:《凯恩斯货币理论之演变及其最新理论之分析》,《国民经济》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第57页。 (28)张家骧、万安培、邹进文编:《中国货币思想史》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7页。 (29)遗憾的是,暂无法找到《凯因斯氏的货币理论及其演变》这一专著,因此本文主要关注陈国庆同期在《经济学报》发表的论文《新经济理论与新货币理论》。其侄女婿的回忆录中曾提及陈国庆与凯恩斯的私人交往,原文为“凯因斯曾为此亲笔致函作者,称赞他在东方从事这项研究工作难能可贵的精神及取得的成就”。http://edu.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03/21/5274675_0.shtml。 (30)陈国庆:《新经济理论与新货币理论》,《经济学报》第1期,1940年5月,第211页。 (31)参见钟淦恩《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上)》,《经济汇报》第7卷第10期,1943年5月15日。 (32)马寅初:《通货新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33)刘涤源:《货币相对数量说》,中华书局1945年版。 (34)张家骧、万安培、邹进文编:《中国货币思想史》下,第1084页。 (35)樊弘:《现代货币学》,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36)蒋硕杰:“A Note on Speculation and Income Stability,” Economica,Vol.10(1943),pp.286—296。 (37)参见姚庆三《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国民经济研究所1938年版,第245—246页。 (38)姚庆三:《现代货币思潮及世界币制趋势》,第249页。 (39)姚庆三:《凯恩斯货币理论之演变及其最新理论之分析》,《国民经济》第1卷第2期,1937年6月,第74页。 (40)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第279页。 (41)徐宗士:《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财政评论》第3卷第3期,1940年3月,第160页。 (42)方福前:《从〈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43)早在1942年10月,杨叔进即撰文《“充分就业”理论与我国战时经济政策》,载于《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2期,第92—108页。文中指出中国学者已经在按照凯恩斯的理论讨论中国是否达到充分就业问题。 (44)徐建平:《目前中国已达充分就业》,《经济评论》第2卷第2期,1947年10月11日,第8页。 (45)吴大业:《有效需要过多还是不足?答徐毓枬先生》,《经济评论》第2卷第12期,1947年12月20日,第14页。关于过度就业问题,可参见吴大业《再论超充分就业与生产:答邵循恺先生》,《经济评论》第2卷第20期,1948年2月31日。 (46)吴大业:《就业与生产——并答李立中先生》,《经济评论》第2卷第8期,1947年11月22日,第6页。 (47)参见徐毓枬《目前中国是否已达到充分就业》,《经济评论》第1卷第22期,1947年8月30日;《再论目前中国是否达到充分就业:兼论增加生产之道》,《经济评论》第2卷第12期,1947年12月20日。 (48)徐毓枬:《目前中国是否已达到充分就业》,《经济评论》第1卷第22期,1947年8月30日,第6页。 (49)参见甘士杰《凯恩斯(J.M.Keynes)论充分就业:兼论中国目前是否已达充分就业》,《新中华》第6卷第10期,1948年5月16日,第44—49页。 (50)参见徐毓枬《凯恩斯就业通论简述》,《社会科学(北平)》第4卷第1期,1947年10月,第91—108页。 (51)参见徐毓枬《就业通论以前的皮古教授之就业理论》,《社会科学(北平)》第4卷第2期,1948年6月,第29—54页。 (52)褚葆一:《凯恩斯氏的就业理论》,《实业金融》第1卷第2期,1948年7月,第11页。 (53)万典武:《凯恩斯派与古典派关于充分就业的论争》,《财政评论》第18卷第1期,1948年1月,第49—59页。 (54)浦山:《浦山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55)雍文远:《从海克与凯恩斯的一般理论谈到中国的经济问题》,《金融知识》第4卷第1、2合期,1945年7月,第52、54页。 (56)樊弘:《凯衍斯和马克思》,《经济评论》第1卷第8期,1947年2月10日,第3页。 (57)樊弘:《罗博生和凯衍斯》,《学原》第1卷第6期,1947年10月,第77页。 (58)袁贤能:《凯衍斯与弥尔》,《经济评论》第1卷第14期,1947年7月5日,第14、16页。 (59)胡代光:《凯恩斯与马克思》,《财政评论》第18卷第3期,1948年3月,第61页。 (60)Paul B.Trescott,“How Keynesian Economics Came to China”,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4,No.2(2012),pp.344—345.迈克尔·林德赛(Michael Lindsay)于1937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聆听凯恩斯的讲座,熟识凯恩斯的学术思想。他接受庚子赔款的“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项目,任教于燕京大学。 (61)参见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库,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b&DocGroupID=11,2014年5月27日。 (62)参见王经伟《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经济思想研究——以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学位论文为研究视角》,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3年。 (63)参见李翠莲《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64)方善桂于194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题为《经济周期和国际收支平衡》;谢强于194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题为《1929年的转折:主要周期理论检验尝试》;王念祖于194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工业化、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研究》;桑恒康于1947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题为《资本形成机制》。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98—99页。 (65)1936年《通论》出版后,正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巫宝三在上海购得一本,随后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学位。留学期间,巫宝三认真研读《通论》并大为折服,遂开始向国内积极推广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法,建设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依据。1939年,他重回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跟随凯恩斯门下高徒汉森学习宏观经济学,同时跟随库兹涅茨学习宏观统计方法,研究北欧的国民收入。 (66)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统制经济到战时经济,中国政府的确实施了干预经济的政策,但是,这与凯恩斯所提倡的政府干预经济是不同的。中国实行统制经济和战时经济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德国历史学派,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和中国统制经济的兴起关系不大。 (67)参见王念祖《我的九条命——王念祖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68)万一华:《凯恩斯理论能中国化吗?》,《经济周报》第6卷第9期,1948年2月26日,第174页。 (69)吴大琨:《介绍一本关于凯恩斯研究的专书》,《经济周报》第6卷第17期,1948年4月22日,第325页。 (70)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11页。 (71)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第21页。标签:凯恩斯论文;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充分就业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货币制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