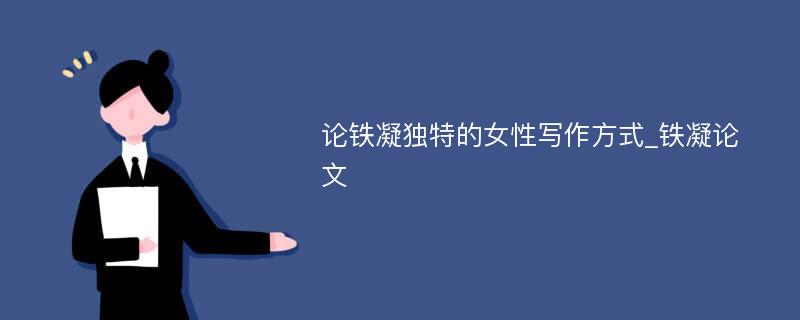
论铁凝书写女性的独特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特论文,方式论文,女性论文,铁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铁凝以其对同类的无比关爱、同情、怜悯和理解,自觉老道地把女人的故事叙说得有声有色。铁凝小说独特的魅力来自于她能够在时而舒缓、时而急促的叙述语流中,将个人性的经验上升为对整个女性命运的关怀和体察,通过对女性躯体的纯净赞美,对女性欲望的坦然承认以及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清醒的理解这一完整的创作理念,全面深入地呈现女性,直逼女性隐秘而又十分敏感、善思、多变的特质。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铁凝的关于女人的长篇小说把那故事操纵得有声有色,为女性心理学和女性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研究可能。(注:参见《对面·跋》,37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铁凝小说显露出的女性世界,可谓女性生存的百态图,多重意义隐含其中。本文仅从铁凝书写女性的方式这一特殊角度,来观照和分析作者对女性意识和生存情形的把握、发掘及显现。
一
阅读铁凝小说会发现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现象,即铁凝在讲述自己的话语时,非常大胆地通过对女性健美躯体的赞美来切入女性生存意识和女性生存状态的话题。在《玫瑰门》、《对面》、《他嫂》等作品中,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对女性健美躯体毫不隐晦的赞美之情。
首先在对女性躯体的描绘上,作者完全摒弃了传统文学对女性躯体柔弱感的追求,也不同于张贤亮所追崇的南国女儿的纤巧亮丽,而是采用了极为独特的比喻手法,描绘出一个让人赞叹的女性躯体。在《玫瑰门》中,作者借助于清纯女孩苏眉的视角,展示出了舅妈——竹西出浴时健美的躯体:
乳房,当宝妹把它当奶吃时,它像是一个仅有奶水的婴儿离不开的器皿。可现在它远远不是,它是球,是两个自己跳跃着又引逗你去跳跃的球。舅妈举起胳膊擦背时那球便不断地跳跃。
臀部,当舅妈坐着马扎抱宝妹时它们不过是人身上为了坐而生就的两块厚垫子。现在它们不再是为了坐而生,那本是引逗你内心发颤的两团按捺不住的生命。舅妈每扭动一次身子那生命就发生一次按捺不住的呼号。
脖子和肩你以为就是一根直棍接着一根横棍吗?那些衔接本身就流泻着使人难以理解的线。那是声音是优美的声音,你想看不如说是想听。
……
人的腹肌是八块,但当你把它画作八块时你才会彻底发觉你的拙劣。那是八块,是八块的妙不可言是八个音符和谐的编织。
在此,铁凝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借用音乐和美术知识,描绘出了一个带有动感和音乐美的十分少见的健美的女性躯体。这里没有过分细致的肉体描摹,也没有迎合低级趣味的庸俗色调,倒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桑提·拉斐尔画笔下的丰丽、端庄、成熟的女性躯体。竹西健美的躯体不仅让苏眉获得了一个绝美的欣赏对象,而且唤起了一个过早地离开母亲的小女孩对自己肉体的觉醒,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的涌动,因而12岁的那个春天对苏眉来说是一个玫瑰的春天,她悄悄地庄严地迎侯着从一个女孩向一个女人的变化。“她的胸脯开始膨胀,在黑暗里她感觉着它们的萌发,她知道有了它们她才能变成母亲,而现在她就是它们的母亲。”这神圣和激荡人心的情感,既是苏眉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期盼,也是作者对女性生命的热情礼赞。这一切发生在60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意义更为重大,生命不可禁锢,这是对于那个非人时代的最大的讽刺。
铁凝在展示女性躯体的外在美时,对男性视角的引入又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女性躯体单一的功能性认识。在《对面》中,当对面的女人因为凉台(兼做厨房)上的米粥锅噗了不顾一切地只披着一件浴衣冲上阳台时,正在一墙之外设计院看仓库的男主人公看到了这一幕:
我目瞪口呆。
我所以目瞪口呆,是因为这个女人只披了件浴衣。所谓“只”,是因为她实在是光着身子的。她冲出厨房时,裸体就被我一览无余。我觉得眼前很亮,像被一个东西猛那么一照。常有消息说,一种天外来的飞碟就是赫然放着光明一划而过。她放着光明一划而过,但还是给我留下了观察的机会。我猜她不再是情窦未开的姑娘,有三十吧,三十出头吧。但她体态很棒。棒,不光是美。有人很美但不棒。她的脖子、乳房、肚子、大腿……我看到的一切都很棒。这是使你觉得最打动人的女人不是美,实在是棒,男人的目瞪口呆只能是面对一个棒女人。
在“我”对“对面”的反应里,不再有对“女向导”、对肖禾的占有欲,“对面”在“我”心目中激起的是一种消除了任何杂念的神圣的美感。长久以来,国人对女性美的塑造并非是对女性本身的尊敬和崇拜。从秦女罗敷到大观园的林黛玉,这些精致的美女偶像只不过都是在男权社会中,男人为了强化对女子的所有权,根据自身利益、审美要求设计出来的。受制于男性观念,女人也相信男人才是女性美的主动欣赏对象。而在铁凝看来,健康的人体美,代表的是人类合乎自然的和谐发展,表现出的是人性的某些本质的东西。特别是女性躯体,它是人类能够真切地感受世界灵性的基本硬件的创造者。它的健康,是种族繁衍进程中更大程度上适合于自然界生存的保证;她的美质,使人类智慧地改造和创造环境,使之更为理想成为可能。对健康女性躯体的赞美、尊重在西方国家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米隆的《米洛的维纳斯》,就是通过对女性健康丰满的肌体的精细描摹,凸现了人类社会创造世界的坚不可摧的生命劲力,而在维纳斯沉静、坦荡而又充满自尊的神情里,再一次让人感到女性对生命自由的热烈向往。当然不能否认,在《对面》男主人公纯洁的感受中有铁凝的理想。但是,也应当看到铁凝让男主人公和读者在“对面”的身体上获得的“一切都很棒”的妙不可言的感觉中,享受到一种朴素、自然、清丽、健康、恬静的和谐之美,同时也让读者从中看到了作者对传统的男性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对抗态度。
铁凝在表述她极力推崇的女性躯体健康美的观念时,没有忽略女性本身对自己躯体的尊重感。女性健康的躯体不仅对他人是一种愉悦,对自己同样重要。铁凝曾经说过:“自赏意识其实是不分男女的。我常常感到,懂得欣赏自己,并敢于公开欣赏的人,原本是可爱的。”(注:引自《与文学一起成熟》,《人物》1999(2 )。)在《玫瑰门》中,铁凝对竹西出浴时的坦然自若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竹西出浴时“就那么随便地把自己的身体转向眉眉”,“那么随意地对着眉眉为自己做着一切善后工作”。绝不能小看竹西浴后的这一系列“沉稳”“从容”的运作,这种既是展示又是自赏的过程,都是要建立在主人公对自己生命自信、尊重的基础上。人只有爱自己,充分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本质,才能尊重与生俱来的各种需求,为摆脱外加于人的奴性、依附性抗争,才会不为被动人格所约束,从而获取一种精神上的浩瀚,人格上的独立。竹西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能在司猗纹所代表的男性意识形态文化的巨大阴影中我行我素,大胆地去爱,大胆地做自己想做的事。铁凝对女性自赏行为的观照,标示着女性对自身躯体尊重的觉醒,对推动人性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根据马斯洛在《自我实现的人》中的划分,人的欲望大致可分为如下五种: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注:[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译者前言》,2 页,三联书店出版,1987。)由于个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生存空间千差万别,人的欲望或者说是生存目标必然会形形色色。但是,无论人的欲望、需求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所有需求都要建立在生理需求的基础之上。只有在本能需求得到满足后,其它层次的需求才会产生、实现。同样,不同的女性,也许需求目标的定位会有诸多的差异,然而实现基本的生存条件,渴望去爱,渴望被爱是共通的。
铁凝在审视女性命运时,就是抓住了这一共通性,从女性最基本、最内在的自然存活方式切入,开掘出了一条通往女性心灵底层的曲折路径。沿着这一途径,铁凝探索性的笔触渐渐靠近和理解了女人近乎于隐秘的内心世界和多难命运。铁凝的作品在审视男权中心社会下女人的屈辱挣扎的同时,也揭露了她们灵魂的病灶。作者发表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颇有影响的“三垛”(《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对女性生存状态及命运的整体性思考。在《麦秸垛》中,作者第一次表述出了女性渴望了解男性、渴望了解自己的欲望。在这里,“麦秸垛”被赋予了生命的意义。女性第一次坦然承认了自己的欲望,承认了对生生不息生命的热情。如果说“麦秸垛”隐喻了生命的勃发、生命的跃动,那么,“棉花垛”则是以性生活为视角体味人生。小说通过米子和她的女儿小臭子的故事,揭示了女人对男性世界的依附心理和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青草垛》同样是通过讲述模糊婶等人的故事,展示了女人世代的悲苦和辛酸。铁凝的“三垛”,仿佛是对人类生命生生不息的谜底的一一揭示,又像是对千百年来女性受压迫受扭曲的命运的诉说。
“三垛”之中,《麦秸垛》更为深刻。小说在讲述大芝娘痛楚的人生故事时,侧重从妇女的天性在她们的人生苦痛中所遭到的扭曲,揭露了传统思想对女性精神上的重压和束缚,以及她们自身的局限及异化现象。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谈到,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597页,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关于“女儿性”,也许可以看做是柔顺、无邪、纯情、期盼得到爱的雨露滋润;“母性”,则是要寻找爱的对象,带有兑现自身孕藏着爱的能量的一种感情意向,“女儿性”和“母性”是女性内心世界中最基本的欲望。然而在无情的现实状态中,对以大芝娘为代表的在中国妇女中占绝大部分的普通劳动妇女而言,往往连这一最基本的欲望都难以实现。《麦秸垛》的中心话题,就是端村的女人们想做个女人的共同欲望和这个欲望难以实现的悲楚。大芝娘,四川女子花儿,知青沈小凤都没能逃离这个怪圈。在此,铁凝用极其精到的构思:两个三天——仅仅六天的时间,就击毁了一个女人用多年心血构筑起来的梦想。无情的命运,首先击溃的是大芝娘在闺房中日思夜想的被爱的梦想。大芝娘(女主人公在作品里唯一的称谓)结婚了!结婚对于一个乡村的平凡妇女实在是意义重大。建立在异性关系之上的定位,不仅让大芝娘获得了合理合法的带有性意向的情感生活,同时家庭带来的生活稳定和心理上的踏实感,更让以家庭生活为全部生存经历的大芝娘们看重这一形式。男人是拴住她们生命之船的最坚固缆绳,而家庭则是飘泊人生的最可信赖的港湾。终于有了一个安乐巢的大芝娘,本以为一生都有所安排,有所依托。不曾想,生活对她总是很残酷的,结婚才三天,丈夫就骑着骡子参军走了。渴望被爱自然也就成了大芝娘的白日梦。可想而知,视婚姻为生命的大芝娘,在失去了唯一可依存的避风港后,是在一种怎样的心境和环境下度过遥遥期待的每一天。第一个三天,大芝娘失去了女儿身。好容易结束了几年的企盼,等回来的果真是提了干,说着一口端村人似懂非懂的话的丈夫:“就目前来讲,干部回家离婚的居多。包办婚姻缺少感情,咱俩也是包办的,也离了吧。”大芝娘不懂丈夫说的感情究竟包含着什么。但她知道外面兴过来的事一定比村里的进步,丈夫说的一定有道理。第二天就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丈夫没有给大芝娘留下一个儿女,就再也不回头地走了。第二个三天,粉碎了大芝娘的母亲梦。大芝娘的可悲之处在于,她不图人间的荣华富贵,她没有多余的人生奢望。她想得到爱,得不到也罢了。毕竟温情呵护和关怀备至对一个终日劳作的粗俗女人而言太奢华,但用健壮的身躯和火热的心肠送去爱总不该被拒绝吧。可命运连这样一个机会都没有给予她。正如大芝娘自己经常琢磨的:“原本应该生养更多的孩子,任他们吸吮她,抛给她不断的悲和喜,苦和乐。命运没有给她那种机会。”大芝娘的遭遇本身,道出了命运对女性的不公和残酷。
作品在控诉外在因素对女性残酷伤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揭露女性自身的弱点。在大芝娘充满矛盾的反抗中,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被逼真地呈现出来。我们在作品中看到,只知顺从、接纳、容忍的女人——大芝娘在精神的一再受压之下终于反抗了。在丈夫离开村庄回省城的第二天,大芝娘也“先坐汽车,后坐火车来到了省城”,出现在被“惊呆”了的丈夫面前。正当我们要为大芝娘的勇敢喝彩时,她的呐喊使反抗黯然失色。“我不能白作了一回媳妇,我得生个孩子。”因反抗的行动在大芝娘身上激起的火花,顷刻又因她的“宣言”而暗淡了。其根由在于,大芝娘的省城之行,只是源于一个受挤压的妇女对自身利益的本能的争取。而这种发自于原始、本能的反抗,爆发瞬间也可能有一定的威慑力,然而由于它缺乏理性的调整和智性的组织,常常因其混沌而被传统权威的力量所异化。从表层意义上考察,大芝娘的反抗,是对自己始终被男人、被命运摆弄的一种抗议,是对男权中心观念的一种颠覆,一种摧毁。究其实质,她的“宣言”,依旧是对千百年来传统道德观念规定于女人的义务和生存方式的一种认同,一种张扬。这种对女性生存状态缺少清醒认识的消极抗争,自然软弱无力,不会持久。果然不出所料,从省城回来的大芝娘在“像落下一棵瓷实的大白菜似的”生下大芝,母爱有了释放的对象后,便踏实和满足了。而由于大芝的意外早逝,大芝娘重新陷入不被人爱,又无人可爱的精神困境中。夜夜低沉的纺线声和那只被她抱得发亮的“又长又满”的枕头,成为了她排遣苦痛安慰自己的最终选择。
《麦秸垛》深刻的意义在于,作者用大芝娘坎坷痛苦的人生故事,尖锐地批判了传统的生命方式和生存方式对普通劳动妇女心灵世界的非人化的折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世界上有两种人,主人和奴隶。前者“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后者“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注:[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自我意识》,127页,商务印书馆, 1981。)如果对黑格尔的话做些细致地研究,就会清楚地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只求“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的奴隶,恐怕只有一类人,那就是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第二性》中也指出:“女人已经成了相对于本质的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只是‘他人’。女人即便不说是男人的奴隶,至少也仍是他的臣仆。”(注:参见张容选编《第二性》,1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的确,对男性而言,即使在社会地位中是最低下的奴隶身份,回到家,在家庭环境里也还有主人的一面,还可以发号施令。因为还有比他更卑贱的妻任他摆布。而传统生活氛围中的女人就不然了,长期被奴役的地位,使她们彻底丧失了对权力的欲望,丧失了自我表现的追求,丧失了言说话语的机能。她们活着的目的意义,说穿了就是滋养自己,以备成为家庭的奴隶,男性的附庸,“事宗庙,继后世”的工具。为男人而活,为家庭而活,为养育子女而活,成为了她们生存的唯一目的。其中惟独没有为自己而活。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个最低下的生活目标,也令胸脯“肥大”,“仿佛永远会有充盈的乳汁”“迸射出来”的大芝娘难以捕捉。铁凝在用她那支精细的笔叙述大芝娘的不幸时,也用她那颗焦灼忧虑的心呼唤着人们对妇女解放现状的清醒认识。尤为深刻的是在作品中,作者借助于城市女知青沈小凤在和陆野明发生了无爱的肉恋后,也发出如同当年大芝娘一样的恳求——“跟你生个孩子”,“孩子也不用你管”这一事实,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作者对女性传统生活方式顽固性的否定态度,进一步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生存方式近乎轮回意义的深度思考。
三
铁凝在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时,不仅注意到从人的本能欲望、生命的自然冲动中探求女性的心理世界和精神走向,而且注重挖掘、表现在时代洪流汹涌前进中,女性精神家园每一细微的律动。铁凝的《哦,香雪》、《他嫂》和《孕妇和牛》三篇作品尽管创作时间不同,主人公的身份也相差甚远(一个是未成年中学生,一个是已为人妻的女人,一个是有孕在身的母亲),但其文本指向却有着不容质疑的相同性,即表现了主人公在社会变革的诱惑和催动下,由女性普遍追求的求生意志转向求胜意志——渴望改变自我,改变个人命运,渴望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完善自我和拯救社会的追求中,渴望实现自我对他人、对我之精神方面的价值兑现。香雪家乡的台儿沟新火车站虽然小,但它的意义却超乎寻常。它使香雪和台儿沟的乡亲们认识了一个大山皱褶之外的更大更有诱惑力的天地。香雪用一篮子鸡蛋换回的不仅仅是一个能自动开启的漂亮的铅笔盒,更是换回一种可能——改变台儿沟祖祖辈辈的生存方式,实现一种更开阔的生活的可能性;换回了一种尊严——与同桌平等的尊严;唤起的是一种渴望——超越封闭的生存层面,追求和享受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渴望。《孕妇和牛》写的是一位目不识丁的村妇面对一个有字石碑的心境,作者用一种抒情的笔调,歌颂了一个从大山里走出的无文化的俊秀女子文化人格的觉醒。以往,俊女子凭着自己“俊”,在家得到父母的宠爱,出嫁后又得到公婆、丈夫的喜爱。一向很满足的她,从远处背书包的孩子们想到自己腹中的孩子,一种对自己生命的遗憾从心底油然而生。自己的孩子将来会问她许多方面的问题,诸如石碑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她该如何回答?对孩子,母亲的“俊”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不让孩子失望,她艰难地描下了那十七个海碗样的字,准备回村请教识字先生。孕妇对文化的认同心理,虽然缘于潜伏在她心灵深处的母爱意识,但也应看到注重文化的时代气息对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她看到了自己人格不完满的缺憾所在。也许,这一觉醒不会给她本人的命运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对文化的认同,相信她不再会让自己的孩子重复她的命运轨迹。这篇小说,与其它写母爱题材小说不同的是,作者在母亲博大、充满爱意和奉献精神的胸怀中,窥探到母亲心底生出的另一种热望,女人的天地不仅仅是在家庭,女人的天职也不再囿于为家庭消磨自己的一生。女人是整个社会的另一半,而不是一个旁观者,她们理应和社会的脉搏一起振动。小说通过一个母亲由生理变化引发出的心理变化,发掘出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深层思考。因此,老作家汪曾祺称:“这是一篇快乐的小说,温暖的小说,为这个世界祝福的小说。”(注:转引《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77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他嫂》则是通过一个来自于被古今村人十分看不起的小山村的年轻女人不折不挠、卓有成效的奋斗过程,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当女性能够自觉地从自然生命力中有意识地挖掘潜藏着的社会生命力,不服输,不认命,不甘寂寞时,同样能够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生命价值。在此,尽管铁凝从香雪、他嫂和孕妇这些普普通通的乡村女性身上发现的求胜意志还只是个端倪,但其中透露出的希望让人欢欣鼓舞。
进一步深刻地思考会发现,《哦,香雪》、《孕妇和牛》和《他嫂》传达出的只不过是一种对原有生活渴望改变的欲求,而渴望从产生到真正的实现还需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坎坷和冲突存在,挫折和失败也是难免的。《玫瑰门》中司猗纹扭曲的性格和沉甸甸的人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司猗纹有过美妙的少女时代,有过浪漫的梦想,也品尝过爱情的甘露。但是不幸的命运最终把她丢进了颓败的庄家。在令人窒息的庄家她的全部青春和激情被囚禁,但她不愿以苟安性的态度对待生活、索然无味地终结一生。在苦水里泡过的司猗纹,生命之火并没有熄灭,她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被社会承认,被环境接受。解放后,她糊纸盒,砸鞋帮,当老妈子,做教师,她对一切都做得尽心尽力,然而一个做过大奶奶的人是很难被当时的社会接纳的。于是她又回到家,从前是什么现在还是什么——家庭妇女,单个儿。“文化大革命”终于又一次给了她摆脱被动人生的机会,她跃跃欲试。遗憾的是大字报点名没她的份,抄家庄家也不在范围。被遗忘的孤寂令司猗纹难忍难耐,但也让她找到了再次出击的机会。她主动给红卫兵小将写信,恳切要求他们在方便的时间来响勺胡同没收她的几间房子和她的祖上不劳而获的财物,她希冀通过自我革命进而达到别人的肯定。司猗纹不安于过家庭妇女的稳日子,渴望被别人承认,渴望发展自我,面对坎坷的人生之路不停息地寻找出击机会,试图在落寂中找到自己人生光辉的一面,从人性角度而言,是人性觉醒的征兆。可悲的是从一开始司猗纹就是在一种畸形的自我发展中徘徊。她的种种与社会脱节的想法做法,让我们看来可笑、愕然,然而她却自认为与社会发展和秩序达到了高度和谐;她得意于自己终于成功地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不曾想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被动生活的涡流。司猗纹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又极不现实的畸形人的典型代表。司猗纹的悲剧意义在于,她徒有一种发展自己的愿望,而缺少对保证这种发展的意志力做出正确明晰的规范。她不甘寂寞、无孔不入地以自己的坚韧、精明企图打碎宿命论的枷锁,希望变被动的消极无为的生存方式为主动积极的生存方式,而最终却以无可挽回的失败告终,蜕变为一个向生活施虐的恶女人。《玫瑰门》这篇小说包容了作者“对东方女性,或者说是中国市民阶层女性的一套比较完整和明确的感想和认识”。(注:引自《与文学一起成熟》,《人物》1999(2)。)
“五四”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呕心沥血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改造国民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主体精神的解放,让人性从必然走向自由。铁凝致力于恢复女性的正常身份,正视女性的自身权利、需要,解放女性的思想、情感、灵性,提倡坚韧、自由、主体性等等,也正是延续了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我们今天竭尽全力追求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完善过程,更是一个人的现代化过程。英格尔斯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所谓现代化,不应该被理解成为是一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理状态”。(注: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22~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诚然,人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思想的现代化过程较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完善是很难的,而促使女性在现代社会急剧发展的现实中,彻底打破传统的自我满足、自我封闭意识,从对自然命运的依附和对男权的崇拜中解放出来,牢固树立起自尊、自爱、自重、自省的文化意识更为艰难。然而,唯有现代意识真正成为整个民族的自觉要求,理想化社会的实现才有可能。由此看来,铁凝的小说,从表象看,是对女性本体精神走向的关注,而它的深层意蕴则往往超出了文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