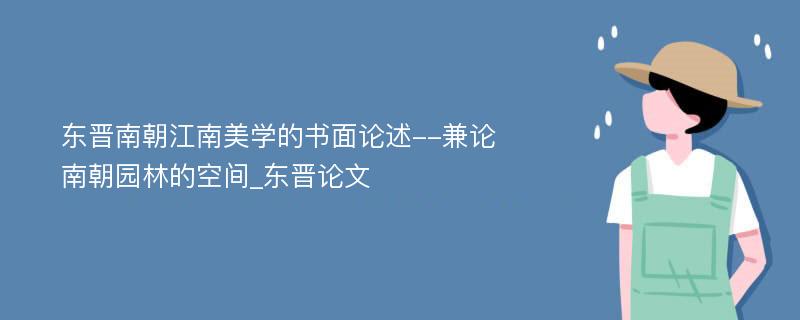
东晋南朝江南美学笔谈——1.被强化的栖居——论南朝园林的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朝论文,笔谈论文,东晋论文,江南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整体上看,南朝的园林设计水平在历史上还远未达到基本成熟的水准,值得称道的只是那强烈的江南地域精神、觉醒了的栖居意识与对江南风物的喜好乃至癖好,并以栖居意识为核心。自栖居意识而言,亦如海德格尔所说:“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匮乏。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战争和毁灭事件更古老。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职,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①南朝园林所反映出的空间感正是这种鲜活的“我在这里”而不是“神在这里”、“皇上在这里”的个体栖居感。这种个体栖居感是通过强烈的江南地域精神具体展现出来的,在南朝那里,则是通过对陈设于园林空间的某些自然物的爱好甚至癖好展现出来的,比如对于“竹”的爱好。
从强烈的江南地域精神来看,到了魏晋时期,尤其是到了南朝之后,南北方在地理风物之上的差异才在中国文化史上表现得尤为显著。这种差异,随之也体现在园林领域。正如吴良镛先生说:“归根到底,建筑是地区的建筑。”②在我国的地理差异之中,既有南北差异,也有东西差异,至少从南北之间的差异来看,秦岭淮河以南,尤其是江南地区,多是湿热的亚热带气候,一月平均气温在0℃以上,没有限制生物生长的死冬,即使是在冬季,大地也是一片郁郁葱葱;其年降水量也在800mm以上,即使在没有灌溉的条件下,水稻依然可以得以生存。反观北方,秦岭淮河以北是比较干燥的温带气候,一月平均温度低于0℃,植物停止生长,有“死冬”,冬季大地缺乏绿色点缀;年降水量少于800mm,没有水利等灌溉条件不能保证水稻等作物栽培。如此进行比较,还只是站在现代的视角,进行宏观的甚至是笼统的比较;真正的比较应该是从中国历史地理演进的角度,来深化、具体化这一比较。正如著名学者吴世昌在《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一文中就提到南北之差异在历史上的体现:“至于宫殿则大都是高大雄壮,很少曲折布置。最多的是台观。那是有许多原因的:第一,古代的都城都在陕洛一带,那里平原多于山水。华山是很险峻的,那时还没有人去凿石开路,不能登临:平常远远地望着,往往把它看得非常神秘,认为是登仙得道的去处。渭水和黄河是又脏又浊的。到处臃堆着泥沙,很不容易使人发生美感。因此这时代的人尤其是帝王对于山水还没有发现它的可爱,当然也就想不到在园子里收罗山水之美。”③还说:“至于私家的园林,却是魏晋以后才兴起来的。私家园林的兴起,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却是对于山水之美的认识和欣赏。在魏晋以前,知识分子都聚在陕洛;江南秀丽的山水,在当地土人看来是熟视无睹的。一直到魏晋,这一带的自然风景才被人发现。”④这段话恰恰能够印证吴良镛先生所说的建筑即是地区的建筑之说。
与此相应,秦汉多的是宫殿苑囿,而少有私家的园林。这在根本上是审美资源在权力分配上的不公体现,即使是帝王的园林也是极为少见,比如梁孝王的“菟园”就是如此,《西京杂记》记此园的内部建筑说:“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作菟园,园中有白室山,山上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峭。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亮渚。宫馆相连,延亘数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靡不毕备,王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⑤从所记此园的体制来看,极为宏达辽阔,不仅“延亘数里”,而且连奇果异树、奇禽怪兽也一并具有。这种在形制上的巨大,完全超出了居住在此的主人在感官上的把握范围,个体栖居于此的体验是很微弱的。《三辅黄图》是一部记载汉时宫殿、苑囿、街衡、桥梁等一切建筑的书,所记载“上林苑”也很有代表性:“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茂陵富民袁广汉藏假巨万,家值八九百人,于北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凫、奇兽珍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敛,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昝,不能遍也。”⑥以上两例尤其是后者既能够显示出审美资源在权利上的分配不公,同时也能反映出北方苑囿的特性,即受制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大多受制于一种实用的生存关系,还不是一种生于斯且乐于斯的栖居关系。
当晋王朝从北方迁至南京之后,北方汉人也大量迁移到江南地区,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无疑对人的心理感受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便是在江南地理环境已经产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一本通俗的地理读物之中感受到地理环境差异所导致的空间感的差异:“江南的山青,山中的溪水也清,山青水必秀。江南山地丘陵,气候更加温暖湿润,年降水量在1500—1800mm上下,是我国的多雨中心之一,比长江中下游平原多200—500mm左右。这里的山,有许多是由花岗岩、流纹岩构成,浙江东部还有玄武岩,这一类石头多裂缝,有的垂直,有的水平,一下雨,地面上的水就流到岩石的裂缝里潜入地下,成为地下水。地下水又通过裂缝流出来,成为泉水。真是山中泉水叮咚响,溪沟流水清又清。由于山上植物繁茂,水土流失比较轻微,长年不断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上的鹅卵石和水中来来往往的游鱼也能看得很清楚。”⑦即如王羲之一家而言,他们对于山水的热爱真的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晋书》上说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其原因就在于:“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⑧王献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此等文人对江南山水之记载,在南朝以来实在是不可胜数,本文不再多做引述,尤其是上述如王献之所云“秋冬之际”的江南诸山,仍然是郁郁葱葱、苍翠欲滴,可谓地理之迁徙所造成的与北方环境大大不同的空间感。
如前所述,秦汉时代的所谓园林充其量大多只能算是吃喝玩乐住行的一个大场地,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地区,只能算是一个显示皇权至上的权利象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园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南朝时期,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许多豪门地主都大肆扩展自己的庄园。刘孝标在《东阳金华山栖志》中描述了这种庄园生活:“宅东起招提寺……寺东南有道观……寺观之前,皆植修竹,檀栾萧瑟,被陵缘埠。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郑白决漳,莫之能拟。……养给之资,生生所用,无不阜实藩篱,充初崖蝎……蚕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当肉,无事为贵”(严可均《全梁文》卷五七)。从其园林的体量而言,突出的特性就是与秦汉的皇家苑囿相比变得小了,皇家苑囿讲究豪华与规模宏大,在营造之时往往是以举国之力,来象征权力或者国势;而“小”就是规模与尺度变小,而且在根本上是对个体感受的尊重,这一感受就是在空间中的栖居感。
空间感的形成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特定关系,从主体而言,其感官在某一空间中的体验是有限的,不管是视觉、听觉,还是嗅觉、味觉、肤觉,都有其在生理上的限度,正如美籍华裔著名人文地理主义大师段义孚所描绘的家乡感一样:“‘恋地情结’是一个新词,可被宽广地定义为包含了所有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这种反应也许是触觉上的,感觉到空气,流水,土地时的乐趣。更持久却不容易表达的感情是一个人对某地的感情,因为这里是家乡,是记忆中的场所,是谋生方式的所在。”⑨自客体而言,特定的客体会引发截然不同的空间体验,因而,在南朝诗文之中所保存的正是以上两个层面所交融成的空间感,一方面,自主体而言,他们乐于忠实地描述在此时此地的空间感,表达江南山水风物的美好;另一方面,自空间环境中纷然杂陈的诸物而言,往往会引发文人墨客们特别的爱好甚至嗜好。因而,南朝园林的“小”恰恰是空间感尤其是栖居感的黄金尺度。陶渊明在《祭从弟敬远文》中描述了自己与堂弟在一起游历的体验:“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寘彼众意。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登高,温风始逝。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在今天看来,就是十足的地道驴友了。再如梁代名士徐勉在《为书诫子篇》中写道:“中年聊于东田间营小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吾经始历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荫,滕陌交通,梁畦相属。华楼迥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蔛蒋,湖里珠富艾莲。虽云人外,城阙密迩。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间隙,负枚蹑跷,逍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不宜复劳家问细务。”文中所提及的小园正像南朝的诸多文章之中所描述的园林一样,虽小却精致,而且其精致就体现在主体的感官是很坚实地奠基在此园林所陈设的诸物之上的;而且在这种描述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在园林中游历的时间性绵延,从桃李到桐竹,走过蜿蜒曲折的小径,登上层楼,远眺美景,除了描述视觉与听觉的愉悦之外,还描述了于此小园中饮酒的味觉之美,可以说是一个很完善的、现象学式的审美生活的还原。此文给人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家”的感觉,这样一个园林宜居、宜读、宜坐、宜留、宜茶、宜酒的所在,这才是真正的个体的栖居,或者说,它是实现在个体感官的感受之中的。如果与上述上林苑相比,那么上林苑就像是今天的北京或者上海,足够奢华广大,但是它们大得超乎市民感官所能把握的阈限,长期生活于斯,只能会有颠沛流离的疏远感、异己感。
因而,从南朝私家园林营造的兴起乃至成为一种很兴盛的时髦活动,其原因当然很多,比如个性的解放、宗教的兴起、庄园经济的发达等等,但是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文化南迁之后,人们对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感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来自北方的文人对此变化尤为敏感,上述所列举的一些原因只不过是这个根本原因的具体化而已。陈从周先生曾经对江南园林空间中所陈设的诸物进行过细致的描述:“在江南的气候条件之下,粉墙黛瓦,竹影兰香,小阁临流,曲廊分院,咫尺之地,容我周旋。……落叶树的栽植,又使人们有四季的感觉。草木华滋,是它得天独厚处。”⑩以下便是南朝那些得到强化的栖居感的事例:
“王子敬(献之)自会稽经吴,闻顾辟检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点好恶,旁若无人。”(《世说新语》)
“(郭文)少爱山水,尚嘉遁。……王导闻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车,荷担徒行。既至,导置之西园。园中果木成林,又有鸟兽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观之,又颓然骐鞠,旁若无人。”(《晋书·郭文传》)
“(谢安)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晋书·谢安传》)
“张讥字直言,……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儒林列传·张讥传》)
“庾銑字彦宝。……而性托夷简、特爱林泉,十亩之宅,山池居半。”(《梁书·庾銑传》)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世说新语》)
不难看出,南朝士人对于园林营造的酷爱甚至癖好。王献之甚至把别人的园林当做了自己的家,沉醉于游历的过程之中;而郭文对于美妙园林的热爱丝毫不亚于王献之,可以想象,设若像石崇一般为了炫富,为了口腹之欲,甚至要把猪圈修筑在园林之内,哪里还能让郭文保持如此绵延而纯粹的注意力呢?谢安在竹林之中设宴欢会,出手阔绰,而他并不为意,只为那片刻的园林之中的欢愉;而张讥则崇尚在园林之中与清流清谈,庾铣则更加讲究园林营造的精致,他的园林思想可谓超越了狭隘的建筑功能主义;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王徽之对竹子超乎寻常的癖好,宗白华先生曾从时间性的角度对此做出了精彩的发挥:“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11)也就是说,只有此刻“竹子”在他的眼前,才会引发那独一无二的美妙的生活体验,从以上所引述六个事例可以看出,尽管南朝园林艺术在建造与思想上都并不成熟,但是南朝士人对于园林的热爱却是前代少有的,而且他们是把园林与日常生活或者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园林空间在栖居的意义上得以形成。
综上所述,由中国文化南迁导致的南朝园林美学,在日常生活的个体栖居的维度显得尤为珍贵,这也正是其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独特的价值。
①海德格尔.依于本源而居:海德格尔现象学文选[M].孙周兴编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72.
②吴良镛.广义建筑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34.
③④吴世昌.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G].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魏晋南北朝卷,张燕瑾,赵敏俐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29-130,130.
⑤葛洪.西京杂记[M].周天游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114.
⑥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5:240.
⑦雍万里.中国自然地理入门[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69.
⑧耿相新,康华标点.标点二十五史[M].晋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407.
⑨约·瑟帕玛.环境之美[M].武小西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196.
⑩陈从周.园韵[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202.
(11)宗白华.意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