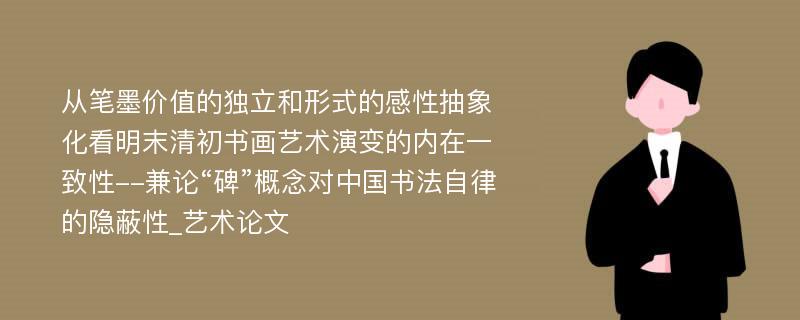
从笔墨价值的独立和形式的感性抽象看晚明及清代书画艺术演进的内在一致性——兼议“碑学”概念对中国书画艺术形式自律的遮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论文,笔墨论文,在一论文,清代论文,抽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后期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景象,政治上分权体制态势的产生,相对削弱了封建皇帝的“专制”地位。经济上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客观上也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和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逐渐扩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素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发生。这种社会现实情况下,出现了一股以王阳明“心学”思想和其后的李贽“童心”说思想为核心的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在其影响之下。汤显祖与公安派的美学思想紧跟其后,形成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强调追求“情”、“趣”和“性灵”的美学思潮。他们的思想不仅是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表达了当时市民阶层的要求,同时也是政治黑暗所带来的人们渴望自由与解脱的要求,对晚明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明的中国,心学对理学的反动和社会开放风气的蔓延,终于突破了道学的束缚。明代后期书画艺术正是在这种人文氛围和社会背景的变化局面中开辟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其中书法和水墨花鸟画领域的变局最大,成就亦最为可观。
中国画坛从明后期至清初期由于保守思想的笼囿,以临摹照抄为主流,陈陈相因,缺乏生气。明代的宫廷绘画和清前期以“四王吴恽”为代表的正统画派,虽然在当时的画坛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其强调用古法作画,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和唯技术的向度单一的审美指向,极大的减弱了艺术性,严重束缚了画家的艺术才华。终于在明代后期由“青藤”、“白阳”发出了变革的声音。徐渭和陈淳的充满独特个性和创造精神的写意花鸟作品不仅打破了正统院体花鸟画独占花坛的局面和历史,而且颠覆了传统绘画“道-艺”二元统一的理念和审美理想,对花鸟画乃至整个绘画领域的发展和审美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徐渭以他所创作的密集、狂乱,满纸云烟,摄人心魄的立轴作品,为世人打开了一扇全新的视窗。不仅他的大件作品将传统的以横向拓展的手卷尺牍,改为以纵向拉长的立轴。在徐渭的巨幅立轴书画作品里,笔法、结体、章法、构图、线条、墨色乃至形质、神采均大大的超出了以往的书画美学范畴。他的作品,不再一一展示传统意义上的物象或线条、结字及章法构图等方面,而是创造了一种具有强烈视觉感受的笔墨形象。这种作品形式的更新大大拓展了艺术的表现力,而且也一定程度的改变了书写和绘画的技术,对晚明以后的艺术风格具有启示意义。如果我们对徐渭及其身后的艺术稍作审视,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他们在文化上的尖锐的对抗性质和颠覆力量。就是他看似信手涂抹的绘画作品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的笔墨形式,从而开创了一代新风貌,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徐渭(1521-1593)、八大山人(1626-约1705年)、石涛(1642-约1707年)等作为不同时期代表的革新画派,强调独创,反对当时以“拟古”、“仿古”为能的僵化画风,在一直以来因体制原因占主导地位的正统画风之外开辟了另一条日渐清晰的绘画发展线索。他们以笔墨为形式语言主宰的注重表现个性,表现情感的作品大量出现,有力的改变了历史上笔墨作为形式语言长期被物象压制的情况,不仅释放了笔墨的价值,并且给予其超越画题物象的礼遇。确立了其作为形式语言超越“对象”在“内容”层面的独立的价值,揭示了晚明以后中国书画艺术变革的总体态势,在中国艺术史上开启了新的一轮自律进程。并以其开创风气的艺术实践,对“扬州八怪”的形成起到了画坛先驱和奠定理论基础的积极作用。
从晚明到清代晚期以来的书法历史来看,期间经历了晚明重视觉效果,表现个性和表现情感的以拙、重、厚、大、古、媚等新的审美风尚推动书法向视觉化转化的书法艺术表现潮流,和以提升使转和点画的地位,突显笔墨的独立价值形成的具有高度形式质感的笔墨意蕴的清代主流书法风格,共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的书法风尚,开辟了一条由晚明滥觞至清代形成高潮的书法变革的道路。在这一大的时期内出现了包括来自于帖学和金石学等均不同于传统的各种书法现象:如来自于帖学的晚明视觉化书风;以王铎和傅山为代表的胎息于二王法帖的大字行草书风;以刘镛、王文治和铁保等人在帖学体系内致力于笔墨形式语言探索的新帖学书风;以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碑学书风等。
本文之所以把明末的书法变革与清代的碑学运动作为具有内在关联的现象或者干脆当成一个现象的两个不同阶段来进行阐发。是因为如果纯粹从书法艺术形式语言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系列变革的话,这两个时代的书法情况,不仅具有同样强度的艺术内在驱动力量,而且在复活书法作为艺术的独特形态和价值上具有同样的诉求和作为,甚至可以说是一次书法艺术在形式语言抽象进程上的演进之旅,而且均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演进平行的文化现象之一。明末的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的书法作品中体现的使书法摆脱与文字实用功能相纠缠的意识已经非常强烈,所以在他们那里才会出现大量与传统书法面貌极为不同的作品。这类作品不仅风格与以往不同,而且无论是在整体布局上,还是在笔墨的形式上都令人耳目一新。他们和徐渭以及后来的王铎、傅山、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等大批的艺术家都对书法的变革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有力的提升了书法的艺术价值,廓清了书法的艺术轮廓,使书法艺术的价值直接指向了审美,极大的改变了书法发展的方向。如果说明代中期以前的书法史的变化是在风格上求变的话,那么此期的变化则更多的指向了在形态上求新。这种形态的求新既包括整体布局改变,也包括对笔墨的质感的多元探问和笔墨所具有的审美能量的解放。这种关于书法艺术形式语言的探问和尝试,对后面的清代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后来的清代书家们渐渐的把目光越来越集中的转向了对作为书法形式语言的核心的笔墨所蕴藏的审美能量的开发和追求,以至于在他们眼里,那种更为感性的笔墨的形式意蕴才是最为重要的和最可玩味的,也是最值得追求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催生出大量不同于以往概念的作品。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完全可以忽略文字内容的写意性临写作品,王铎、傅山、八大和金农、郑簠、伊秉绶、邓石如、何绍基、杨沂孙、吴昌硕等人的大量临摹古人或古碑的作品不再仅是他们勤恳向学的所谓日课,而是他们眼中对书法的独特的崭新的理解。在他们那里正是由于发现和认可了笔墨和视觉构成在形式层面上的审美价值,才不再轻视临摹作品,给它们以和创造完全相同的礼遇。而他们临摹古人的作品也不再是像前人那样亦步亦趋的简单重复,而是按照自己和时代的要求和认识对待临摹对象,用具有时代特征和个性的笔触,把感觉到的古代作品中的运动和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去除掉古代作品中的文学性和实用性的东西,转化为视觉的单纯形式,借临摹对象来释放书法的形式能量,在完全形式化的高度上重新阐释临摹对象,使那些在人的深切感动中体会到的,感受着的事物被富有魔力的表现出来。在他们那里,所谓的临作和创作并没有本质区别,而观赏者也不会因为是临作而对其不解。这其实是一种让传统为我所用,进而改造传统书法认识的艺术演进过程。所以说,这是一个观念和认识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有共同风尚和精神追求的时代,更是一个有着艺术上内在联系的承前启后的发展的大时代。
晚明以后,中国书画艺术主体意识逐渐增强。作品从以表现客体为主转变为以表现主体为主。最重要的内在形式演进的趋势和特征是“笔墨”的进一步独立,使笔墨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由紧贴对象形体,逐渐趋向于与对象之间的疏离,而且强化和突显了笔墨对生命意蕴的传达,所以说总体上是走向一种感性的抽象。而明末的那次书法高潮,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明代艺术史的内在问题暴露乃至激化的结果,由于政治的黑暗和社会变化,晚明知识分子的政治欲求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满足,使政道合一的传统思维模式下的文人士子在远离政体的同时,淡化了对道体的亲近,导致道义承担与艺林优游的冲突愈发尖锐,最后终于被彻底打破,它所造成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精神的苦闷、焦虑和无家可归的状况,使一直以来习惯于“天人合一”文人艺术观念受到质询和挑战。这一改变所积郁和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在明末社会文化的现实情境中转化为了艺术内部的自我实现的力量,形成了因主体的意义和价值处于晦暗不明状况而产生的“抽象冲动”,进而启动了在形态上让人感到铺张扬厉、抒情写意而内里实际是书法艺术的形式自律的艺术进程。
与晚明及清初书画艺术的笔墨的形式化变革一样,清代篆、隶书及魏碑的兴起和形成的那种尚古之风亦并非是单纯意义上的“复古”行为,而是人心思变的时代诉求使然。因政治和社会原因形成的金石学兴起的契机,使清代学习碑刻,追摹三代、秦汉魏晋,不是对传统的一种简单重复,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书法风格的依据提取出来,通过长锋羊毫和生宣纸等材料的改变,在风格、技巧诸方面予以分解和重构。因此,篆、隶书和碑体书法在清代是一个充满新意的诠释时代。清代书家在从这些书体中所看到和所提取的,是属于他们时代的书法的既古老又崭新的笔墨和体式。蕴藏在篆、隶书和魏碑体势笔法中的朴素茂然的古意对应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求,由金石碑碣传递出的斑驳绚丽的感性的古意成为了有清一代书家学者竞相追求的新的审美目标,使得篆、隶书笔画的独立的审美特质,在清代书家手中进一步的在笔墨韵味和形式语言的层面被深化为体现人文情怀的载体。这一具有更强形式价值的新笔墨为思变的书坛注入了强劲的金石气息和生命质感,使清代书法在晚明和前清书法的形式自律的道路上继续披荆斩棘,有所拓展,逐渐达到了这一大时代的艺术变革的高峰。
从晚明和清初的艺术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情形与西方后来的现代艺术开始前的情况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观念与文人士子作为艺术主体的心理的冲突和矛盾上,并且对当时艺术的转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德国美学家沃林格总结艺术的历史时说:“一切艺术创造不外是对人与外在世界的巨大冲突过程的不断记录,因为,人与外在世界的冲突从自万物形成之始就已出现,而且永不会止息,因而,艺术只是某种心理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这种心理能量同时也制约着宗教现象,而且它受到变动不止的世界观的影响。”①如果我们同意说晚明以前的艺术追求的“天人合一”的艺术感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世界相交融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相同的统一的观念之上的,那么这种统一意识的产生其实是一种先验于书画主体性的存在,是人化的创造与自然世界相同一,书画艺术的道义承担与艺林优游相统一的整体。艺术作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和集中体现的代表,在与外部世界的同一中见出了自身感受的对应存在,因此,客观的外在世界就不再被视为外加到人的内在世界中去的外来的东西,而是人们在客观的外在世界中见出了自身及感受的同构性和对应性,实现了它们的人格化。而这个人格化的过程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一种移情的过程,是自身有机活力向现象世界所有客体上的转移,是一种移情冲动实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追求的“天人合一”艺术观念在晚明社会观念发生变化以前在人们心中具有巨大的普遍性,书画家和艺术俱是在相同认识和观念背景下的追求,这个过程在精神上也具有很大的从众性和安全感,所以拥有共同的精神之乡。而与此相对,作为艺术审美实现的相反的两极之一,与移情冲动相对的则是“抽象冲动”,如果说“移情冲动是以人与外在世界的那种完满的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密切关联为条件的”话,“那么抽象冲动则是人由外在世界引起的巨大不安的产物。”②沃林格总结说的这种不安,在处在晚明和清代中前期的文人士子们的精神深处同样存在。正是从晚明开始随着社会生活中市民意识的觉醒和文人士子们对道体的疏离,中国书画艺术的主体性亦有所增强,但与此同时,书画家们在强调个性,否定传统,疏离共同精神背景的同时,精神世界也会形成某种不安,在他们那里,同样也产生了强烈的寻求精神安定的需要。这也可以看作是晚明和清代中国书画艺术的自律开始在形式上有所变革的深层原因,是那种从原来的致力于“天人合一”的移情冲动转而形成的期待有所突破的抽象冲动,导致了书画艺术中感性的抽象因素的普遍出现。从晚明至清代乃至近现代中国书画艺术的变革演进的现象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几对具有阐发意义的表里关系:一、相对于绘画历史的从徐渭、八大到“扬州八怪”再到海派乃至近现代的齐白石的大写意绘画的变革演进的进程来说,从晚明到王铎、傅山到八大、金农及晚清书法艺术的形式化追求更为元生和内里;二、相对于作为绘画的形式语言的笔墨来说,书法的用笔、用墨本身具有的形式化元素更为内在和根本;三、相对于从晚明滥觞到清初的自觉再到晚清“碑学”中兴的书法笔墨演进的进程来说,作为书法艺术自律的笔墨的价值标准的演进和形式本体的演进更为根本和核心;四、相对于中国书画艺术的自律性沿革变化来说,作为书画家的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与主体意志的冲动更具有内因作用。这里首先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把中国书画艺术这个复杂的艺术门类看成一个体系。具有在一定的内因外因影响作用下,发生、发展、成熟、衰老、重生的本体演进的潜在能力,与价值标准演进的同时,形式本体的演进与之平行发生。
之所以这样说还在于,不仅是在书法领域,同时在与书法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绘画领域,也有同样的变革现象。在与作为书法最为核心的形式要素的笔墨技法和审美改变的同时,在绘画领域,青藤、白阳亦对传统以来的作为造型对象的附庸的笔墨价值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极大地开发了笔墨表现空间,使笔墨逐渐摆脱以往为描绘对象服务的被动、附庸的地位,而突显出自身的审美价值。这一点在其后由明入清的八大山人的艺术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扬和典型体现:如果我们把八大山人艺术面目成熟以后的书画作品与其早期学习董其昌的风格比较会发现,最大的变化是他早期的用笔有明显的起收笔动作,线条呈两端宽中间窄的传统书法线条的习常所见形态,画里的笔触也多是强调传统提按笔法的楔形特征。而在他后来的书法中却多为较为匀宽的笔道和在画作中出现了明显具有抽象性特征的笔墨,这种改变与他早期学习阶段显得有些寻常的作品中大有不同:笔墨意蕴增强了,变得更加富有感染力。在八大山人的书画作品里之所以有那么多被今人说成是抽象性的元素,是因为八大山人认识到了笔墨作为形式语言在书画艺术中独立的地位,因而有力的改变了一直以来,笔墨被客观对象的造型要求所奴役和忽视的境况,给予了笔墨高度的礼遇,第一次与描绘对象平起平坐,成为了欣赏的内容之一。甚至有些时候超越了描绘对象,越升为表现和欣赏的终极对象和全部内容。对于八大山人的笔墨境界,论者多持“笔墨简练,以少胜多”的说法,而当我们在中国绘画的形式独立和抽象的进程的角度来审视的时候,却会发现情况刚好相反,八大山人在看似简单的做法上实际是将笔墨提高到作为书画艺术的形式语言的层面上来对待。因为笔墨从作为文字的附属和表现绘画对象的附属地位提升为审美的直接对象,吸引观赏者的目光和延长对其关注的时间,就必然要表现更多的内容,必然要比以往更为复杂和更加深刻。这种来自于形式的思维和追求,隐含着一种趋于抽象的审美意志,需要实现书画艺术的化整为零,将人生的现实存在、人生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精神等方面与技法的提练、语言的表达形式、个性的形成等问题分解开来,再将作为形式语言的笔墨放在与上述其他方面平行的层面来思考,才能实现问题间的对应转换和恰当表达。这里的这个“抽象”是指抛弃传统绘画对所要描绘的自然物象的依赖、模仿和固着,通过对抽象形式和结构因素的安排和组合来实现对主体的表达,不再受自然物象的时空限制,进行自由的构造,依据主体内在的审美需要的逻辑来对脱离了物质实体的抽象形式进行建构,使其成为一个完整自足的审美有机体。而这一切在中国书画艺术中,都要通过对作为形式语言的笔墨的形式内容和价值的不遗余力的寻求才能获得,以达到笔简而形神俱具的绘画境界。
八大山人对笔墨的抽象形式的追求并非完全不同于传统绘画语汇,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八大山人的绘画与西方现代艺术早期的情况确有很多相类似之处,具有后来西方现代艺术早期的某些具象抽象的特征,可以说是一种感性的抽象。所以,在八大山人的书画艺术中,我们其实看到的并不仅是有所谓的以伤感、孤独为特征的浪漫主义的情感主体,同时还有致力于形式创造的主体意志,因为在八大山人的艺术中,我们既感受到了因摆脱了物质现实的羁绊而获得的傲慢、憧憬和对因失去和谐而弥漫的怀旧形成的体验,也看到了从情感抒发转换成的形式的构造和创造。他高度夸张的造型和引人遐想的笔墨表达了一类新书画艺术想要表达的新内容,不仅在相当程度上也具有后来的西方现代艺术的某些特征。也为后来的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突出的可资借鉴的新的艺术财富和思想平台,然而,八大山人的艺术要比后来的西方现代艺术的出现早几百年,不能说是与对西方艺术的借鉴有关系。所以他卓而不群、风格独特的艺术,不仅是我们民族乃至世界艺术的杰出创举,在中国艺术史的角度上更有其独一无二的,非常典型的意义。德国美术史家瓦尔特·赫斯曾经说过:“绘画寻找着‘新的形式’,但还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那却是一种不自觉地寻找新的内容。对每个时代来说,有它自己的艺术,自由的尺度和它相应和。对于这个自由的界限,最有天才的力量也不能跳过;但每次须做到竭尽这个尺度,而每次也是被竭尽了,不管障碍多么大。”③作为中国书画艺术从晚明到清代乃至近现代演进的既具有承前启后作用,又体现时代高度的人物,不仅具有中国艺术形式自律分析的个案价值,同时更具有贯穿这一大时代的艺术普遍性。他所昭示与人的是一个大的艺术时代的来临,并为人们指出了发展的方向。他的存在也帮助了后人们的研究,使他们能够跳出这一大时代中的不同阶段的艺术现象形成的谜雾,在艺术史的高度,找到其中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推动这一时代的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晚明至清代乃至近现代中国书画艺术的变革演进的一个主导趋势,就是走向笔墨的价值独立和感性的抽象。它构成了这一大的时代进程中书画艺术和审美的根本特性,笔墨的独立和形式的感性抽象是其艺术语言的根本语法。这样说来,由康有为在晚清才明确提出的“碑学”概念,虽然成为了那个时代书法艺术的代名词,但却并非是这个大的时代的艺术自身发生变革的真正原因和元动力。也并非是贯穿和统辖这个大时代的整个变革的全部逻辑,而只是这个大变革全程的一个阶段性的文化附着现象。所以,“碑学”概念和主张,应该说也只能是说成是一种作为文化层面的概念和社会层面的运动,它的出现和存在,形成了人们对这一大的历史时期艺术演进中的阶段性现象的误读,遮蔽了作为艺术的书法的本身的艺术意志和自律进程。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可以看作是“碑学”运动受到普遍响应的深层的内在原因。
这样说还因为,不仅是当时的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对此有所期待。同时,走向感性抽象也是晚明以及清代中国书画艺术追求内在表现的必然结果。抽象冲动其实就是表现冲动,真正的表现并不是内心的呐喊或抒情冲动,而是对所体验的世界的审慎的坚定的坦白。也许晚明和清代书画艺术的历史进程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和答案,但是唯有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我们才能在书画艺术本身中深切理解清人石涛的著名的“一画”和“笔墨当随时代”等命题的深刻意义。也才能对上个世纪初的“道咸中兴”说和世纪末的那场关于笔墨的争论有一个理性的思考。更才能对中国书画艺术的未来发展和方向有所判断。
注释:
①②沃林格:《抽象与移情》,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第16页、第43页、第17-18页。
③[德]瓦尔特·赫斯:《欧洲现代画派画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标签:艺术论文; 书法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书法欣赏论文; 文化论文; 作品书法论文; 八大山人论文; 书画论文; 徐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