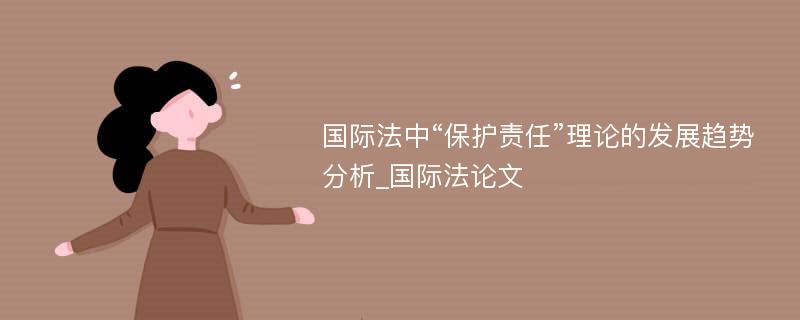
解析国际法上“保护的责任”理论的发展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态势论文,理论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6-0116-05
近年来,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论,即“保护的责任”理论(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这个理论由西方国家首倡,而后逐渐被联合国采纳。西方国家在很多涉及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上都积极奉行该理论。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联合国民主基金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所言:授权西方国家干涉利比亚内战的第1973号协议是安理会第一次以“保护的责任”的名义授权使用武力。很显然,该理论给国际法与国家主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因此,有必要从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中总结规律。
一、“保护的责任”理论的形成轨迹
“保护的责任”理论从2001年被提出至今的形成轨迹,大致可由四个国际文件来归纳:
首先,2001年12月,加拿大“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以下简称“ICISS”)发表了题为《保护的责任》的报告,首次提出该理论。该报告所谓“保护的责任”是指主权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人民免遭可以避免的灾难——大规模屠杀、强奸和饥饿,当该国陷于瘫痪而且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时,为了预防和制止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势,应当由国际社会来承担该责任。[2]引人注目的是,该报告认为:在需要进行军事干预而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又无法及时授权的情况下,可由个别国家或者临时性国家联盟进行军事干预。
其次,2003年11月成立的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以下简称“名人小组”)在2004年12月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Kofi Annan)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的研究报告(A More Secure World: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以下简称《更安全的世界》)。名人小组基本接受了ICISS的观点,但同时也对“保护的责任”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名人小组虽然同样使用了“可以避免的灾难”的措辞,但认为“可以避免的灾难”不仅包括大规模屠杀、强奸和饥饿,还包括种族清洗和故意传播疾病。对于军事干预的程序问题,名人小组强调安理会授权的极端重要性,反对个别国家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①
再次,2005年3月2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上作了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In larger freedom:towards security,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以下简称《大自由》)。该报告明确表示赞同ICISS和名人小组的意见。但是安南同样也对“保护的责任”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例如较为明确地对“保护的责任”进行了范围限制,即针对“种族灭绝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又如在军事干预的程序问题上,安南强调“我们的任务不是寻求取代安全理事会的权力来源,而是要安理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隐指军事干预不应绕开安理会。②
最后,2005年10月24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首脑会议成果》(World Summit Outcome,以下简称《首脑成果》)。这份文件同样对“保护的责任”进行了重大修正。例如,一方面,它将“保护的责任”的范围排他性地局限在使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另一方面,它将军事干预严格限定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范围之内,即在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框架下,强调联合国的主导地位。③
二、“保护的责任”理论的发展进化
从上述的形成轨迹中,笔者认为,“保护的责任”理论存在如下三个发展进化:
第一,基本理念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2001年《保护的责任》是由ICISS制定的,认同范围主要是西方国家。《更安全的世界》是由名人小组制定的,层次比ICISS更高。安南以秘书长身份发表《大自由》后,“保护的责任”理论已从单纯的研究报告升格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更进一步的是,《首脑成果》的发表场合是200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这是联合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首脑会议。因此,《首脑成果》的影响力是先前三个文件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二,基本概念正在逐步向清晰化发展。《保护的责任》和《更安全的世界》都使用了“可以避免的灾难”来界定责任的范围。“可以避免的灾难”很显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大自由》摒弃了这种笼统的提法,将责任范围限定为“种族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首脑成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由此可见,后两个文件不仅使用了国际刑法上定义相对成熟的法律罪名来代替之前笼统模糊的非法律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们所采用的是穷尽式列举方法,这就使“保护的责任”在概念上逐渐地朝着清晰化的方向发展。
第三,对军事干预的限制不断得到明确。军事干预是“保护的责任”理论中最敏感和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保护的责任》允许武力干涉绕开安理会。在《更安全的世界》中,名人小组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军事干预。但它在军事干预的理由上也还只是笼统地归纳为“灭绝种族和其他大规模杀戮”。《大自由》在坚持安理会的唯一授权地位的同时,对包括干预理由在内的等一系列问题寄希望于安理会通过决议来确定,所以,它也没有将干预理由明确化。最终,《首脑成果》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军事干预必须得到安理会授权;第二,军事干预的理由只有四个,即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三、“保护的责任”理论的不确定性
尽管在不断进化,但“保护的责任”毕竟是一个尚不成熟的理论,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首先,我们在承认其认同范围日益广泛的同时,也不得不认识到,目前尚无一部普遍性国际公约采纳该理论,换句话说,“保护的责任”还只是一种“宣示性”的共识,各国还不愿意将其转化为“约束性”的规则。为什么呢?军事干预问题的复杂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保护的责任”理论自身还尚不成熟,存在被西方列强滥用的风险。
其次,“保护的责任”的内涵在变化——《保护的责任》中的责任内涵被《更安全的世界》所取代用了约3年;《更安全的世界》中的责任内涵被《大自由》所取代用了约1年;而《大自由》中的责任内涵被《首脑成果》所取代用了仅7个月。很显然,这是理论不成熟的典型特点。
再次,虽然《首脑成果》对军事干预问题作出了重要规定,但在该问题上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例如怎样衡量威胁的严重性、拟议的军事行动的适当目的、不使用武力的手段是否有可能遏制威胁、军事办法与面临的威胁是否相称、等。因此,这些诸多空白也反映出该理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保护的责任”理论距离成熟尚有一段距离。它的不确定性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西方列强借该理论干涉别国内政的担忧挥之不去。正如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巴基斯坦代表苏雷什·钱德拉·拉贾拉南(Suresh Chandra Rajaratnam)所指出的那样:很多国家由于对殖民规则的历史经验,对该理论被实际应用十分敏感。④因此,该理论还处于发展时期,尤其需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关切。
四、“保护的责任”理论的现有共识
尽管“保护的责任”理论由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处于发展时期,但是目前至少有以下几点共识在大多数国家之间已经基本达成。
第一,国家的“保护的责任”的确存在。这主要得益于主权观念的进化。在20世纪中叶以前,主权几乎是绝对的,国家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即使是种族屠杀。时至今日,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Ghali)所说:“绝对主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⑤前苏丹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登(Francis Deng)在1995年发表的《主权的边界》(Frontiers of Sovereignty)一文中首次提出“作为主权的责任”(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的观点。之后,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于1999年发表的《主权的两个概念》(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一文进一步完善了弗朗西斯·登的观点。“保护的责任”理论正是在这种新的主权观念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一方面,“保护的责任”首先强调国家主权不仅仅是一种权力,而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另一方面,它还强调国家主权必须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第二,国际社会的“保护的责任”也的确存在。这主要得益于安全观念的进化。自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例如难民、海盗、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某个国家,还会威胁全球安全。自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出现“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一词以来,国际社会对“安全”的观念又开始发生变化。新的安全观认为:全球化已使安全的界限远远超越国家,必须从全球安全的高度通盘认识安全问题。各国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国际社会整体的安全,否则就无安全可言。[3]“保护的责任”恰恰是这种新观念的具体表现。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权问题已成为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权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国家层面,可能会危及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第三,国家的“保护的责任”优先于国际社会的“保护的责任”。这体现出“保护的责任”理论对新的主权观与新的安全观进行的整合。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广泛认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既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也在《联合国宪章》所列各项原则中居于首位。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使是ICISS也只是提出在国家陷于瘫痪并且不愿或不能履行责任或义务时才实施干涉。应当指出的是,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判断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责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也是该理论可能被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利用的重要原因。
第四,进行军事干预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事先授权。ICISS在《保护的责任》报告中提出的绕开安理会进行军事干预的极端主张显然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保护的责任》报告之后的《更安全的世界》、《大自由》和《首脑成果》都对ICISS的错误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和及时的修正。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后三个文件对此的批驳和修正,才使得“保护的责任”理论得以被挽救和继续发展,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因此,国际社会在军事干预问题上的这点共识实际上是通过对ICISS观点的批判达成的。
五、中国对“保护的责任”理论的态度解析
当“保护的责任”理论刚刚被提出的时候,中国对该理论持怀疑和抵触态度,因此只承认国家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强调国际社会的关切应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和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这种怀疑与抵触的立场曾经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4-5]但在2005年《首脑成果》获得通过以后,我国的立场与该文件是基本一致的。
2005年6月7日,外交部公布了《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在涉及“保护的责任”问题上,该文件提出:各国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一国内乱往往起因复杂,对判定一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保护其国民应慎重,不应动辄加以干预。在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时,缓和与制止危机是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有关行动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尊重有关当事国及其所在地区组织的意见,在联合国框架下由安理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和处置,尽可能使用和平方式。在涉及强制性行动时,更应慎重行事,逐案处理。[6]2009年7月24日,刘振民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立场,其核心观点有四个方面:第一,各国政府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第二,“保护的责任”概念只适用于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等四种国际罪行;第三,当发生上述四大类危机且需要联合国做出反应时,安理会可发挥一定作用;第四,在联合国以及区域组织范围内,应将正常的人道主义援助与履行“保护的责任”时的国际援助相区别,以保持人道主义援助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并避免“保护的责任”的滥用。此外,刘振民大使强调:“保护的责任”迄今还只是一个概念,尚不构成一项国际法规则。因此,各国应避免将“保护的责任”作为向他国施压的外交手段。“保护的责任”能否得到各国一致接受、能否真正有效履行,还需要在联合国或有关区域组织内进一步探讨。[7]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析中国的态度。一方面,中国基本认可了国际社会对“保护的责任”理论的现有共识,即前文所述四个方面。中国认为“各国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并且“在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时,缓和与制止危机是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这说明我国既承认国家的“保护的责任”,也承认国际社会的“保护的责任”,而且通过“首要”二字强调国家的“保护的责任”优先于国际社会的“保护的责任”。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在2005年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由安理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和处置”,而在2009年将这一立场的措辞弱化为“当发生上述四大类危机且需要联合国做出反应时,安理会可发挥一定作用”。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我国开始放弃原有的立场。从我国在国际事件中的一贯立场来看,我国仍然坚持军事干预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事先授权。另一方面,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对“保护的责任”理论也表示出担忧,反复强调“不应动辄加以干预”、“(武力干涉)应慎重行事,逐案处理”、“只适用于四种国际罪行”、“应与正常的人道主义援助相区别”以及“避免滥用”。我国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担忧,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保护的责任”理论目前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正因为这种不确定,使中国担心“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有可能借此理论而被逾越。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强调该理论“迄今还只是一个概念”,尚不具有国际法效力。应当讲,中国的态度是有根据的,是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利益的,也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保护的责任”理论为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在截至目前发展的过程中,该理论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影响力是来自于国际社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而这些基本共识的达成是由于该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剔除糟粕,发扬菁华。这也是该理论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如果该理论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认可,尤其是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就应当恪守相关共识,消除不确定性,打消发展中国家的合理顾虑,为国际社会的稳定提供积极因素。中国政府应当坚持现有立场,尤其是要坚持国家的首要责任和武力干涉需得到安理会的事先授权,以防止“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成为一纸空文。
收稿日期:2012-03-09
注释:
①UN Doc.A/59/565(A Mote Secure World: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②UN Doc.A/59/2005(In larger freedom:towards security,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
③UN Doc.A/RES/60/1(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
④UN Doc.GM/0850.
⑤UN Doc.A/47/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