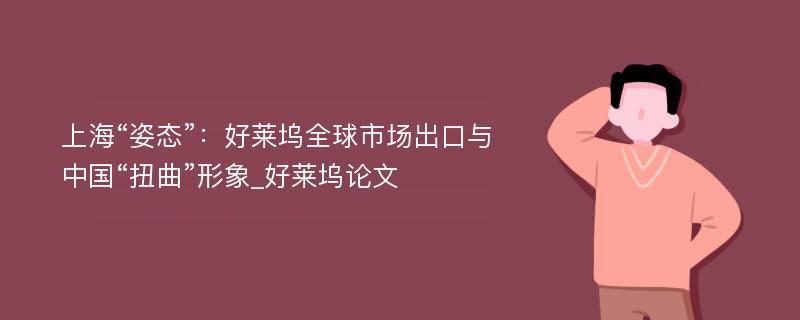
上海“手势”:好莱坞全球市场输出与“扭曲”的中国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好莱坞论文,手势论文,上海论文,中国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处不在的好莱坞商业电影迅速占领了世界市场。尽管大制片公司时代的发行商们认为欧洲是他们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但他们也并未放弃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城市。20世纪20年代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好莱坞电影在上海这座远东城市的众多首轮影院院线占据了支配地位。
美国电影和电影明星受到了上海与其他内陆城市剧院观众的欢迎,也对中国电影人和电影演员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反对美国电影的呼声也很高。一些中国评论家认为,本土电影人在毫无独创地模仿好莱坞电影,而好莱坞电影在本土影院中的特权地位也阻碍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风格的发展。另一些人则对内在于美国电影中的意识形态成分颇为警觉,认为好莱坞影片轻浮堕落,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及信仰格格不入。不过,好莱坞电影最具争议性的一面在于其表现中国人和中国故事时所暴露的简单化和程式化倾向。
好莱坞制片机构很擅长在洛杉矶摄影棚和摄影场惟妙惟肖地再现外国的风土地貌。不过,好莱坞的作家和导演们在用这些异国电影景观表现丰富的人性方面却很难让人满意。他们在叙事上依赖的仅仅是美国公众对外国文化和国民性的狭隘成见。这种懒惰而缺乏文化敏感性的做法令那些出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美国新移民感到既难堪又愤懑。而当好莱坞制片公司天真地试图将这些表现外国生活的电影出口到恰好是电影所表现的那个国家时,其反应常常激烈无比。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讨论好莱坞大制片厂时代导致中美两国之间不信任感的四部影片,并以另一部电影为例讨论美国电影业与中国政府官员之间建立的敏感的合作关系。
好莱坞对中国的偏见式描述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它们是复杂历史文化过程的汇聚,并体现在美国电影最早表现中国人方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身为美国移民,他们在影片中通常都是刁滑、邪恶、没有感情的危险人物。美国一些早期电影如《红灯笼》(Red Lantern,1919)、《曲折的街道》(Crooked Streets,1920)、《飞行玩具》(Wing Toy,1921)、《紫色黎明》(Purple Dawn,1923)和《异教徒的激情》(Pagan Passions,1924)等均属此类。的确,除了格里菲斯的《被摧残的花朵》(1919)等少数例子外,绝大多数美国电影在涉及中国时,都将中国人的事情表现得神秘而奇怪,从他们吃与穿的习惯到家庭礼节和语言。到20世纪20年代末,任何一部表现中国人的美国影片都可能是以下这些类型的混合:
1.极端狡猾和善骗的官员形象:这类人拥有邪恶的玄奥知识和非凡法力。最著名的形象是英国编剧沙克斯·罗姆(Sax Rohmer)笔下凶残的复仇恶魔傅满洲先生。
2.“龙女”形象:具有异国风味、但却同样危险的中国蛊惑女。这类女人精通情爱术,善于利用催眠般的魔力来达到往往令所征服的男人身败名裂的目的。这类角色通常由唯一一位在好莱坞达到明星地位的华裔女演员黄柳霜扮演。
3.聪明狡猾的中国侦探形象:矜持、稳重但却拥有过人的才智。与傅满洲不同,他是破案的而非罪犯。陈查理就是这种形象的原型。由于他是一个英雄,所以该角色过去常常被视为是对中国人负面形象的反拨。不过,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一些评论家转而认为,陈查理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形象,他对那个时代统治美国银幕的白人侦探不构成任何威胁。剧作家、小说家弗兰克·金认为,陈查理是“无性的”,他“过分屈从”,完全是“白人种族主义的象征”。
4.残忍、贪婪的军阀形象:这类形象麻木不仁、毫无怜悯之心,完全沉迷于霸省而治的权力欲中,其蓝本明显出自美国黑帮形象。这些军阀通常被描写成是不关心百姓疾苦的恶魔,与贪婪、自负、权欲为伍。
5.强盗、土匪或黑帮成员:此系军阀形象的另一版本,不过他们往往更加愚蠢、粗俗、暴戾,贪图钱财、偷盗物品,也很好色,尤其是对白人女性。
6.农民工形象:这一人物有时也富有尊严,比如在《土地》(The Good Earth)中。但更多时候,他/她只是仆人、厨子、铁道工或洗衣女。这些人物常常因怪异的行为和一口面目全非的英语或其它原因而被嘲笑。
中国人的形象通常出现在那些以阴暗、险毒的黑道世界为背景的影片中。这一环境充满了鸦片烟馆、赌场、妓院、私刑室以及众多帮派和黑道分子为争夺当地地盘而两败俱伤的混战。
尽管这些充满偏见的人物和场景常常受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中文报纸的谴责,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才开始提出异议。后来,他们曾通过驻华盛顿和洛杉矶的领事官员来游说好莱坞,希望其以更正面、积极的态度来表现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也仿效上海租界和其他城市的先例,建立了电影审查机制,这样至少可以使一些容易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影片不能在国内电影院上映。
在1922年担任美国电影制片与发行人协会(MPPDA)主席后不久,威尔·H·海斯(Will H.Hays)创建了对外部来管理与美国电影出口有关的事宜。陆军上校弗瑞德里克·L·海诺(Frederick L.Herron)被任命来管理这个部门。几年间他处理了很多因美国电影中表现他国人形象而引起的争议。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开始抗议之前的数年间,海诺一直警告各制片厂,他们塑造的外国人形象,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其它国家,都常常是令人反感的。
海诺的工作并不轻松。很多大制片厂的创作人员对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估计严重不足。他们不仅对自己在银幕上表现的外国人的历史、风俗、传统和制度所知甚少,还自大地认为外国人应该为他们的生活在美国电影中得到表现而自豪。无知加自大是一杯效力浓烈的鸡尾酒。外国观众通常很喜欢好莱坞电影对美国人和美国生活的多彩表现。不过,美国电影对其母国生活的歪曲表现却令他们既震惊又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建议也许并不过分,即好莱坞制片厂的老板们本应明智地将故事背景限制在美国境内。
比如,在格斯·李(Gus Lee)关于其父母二战前及二战期间在上海生活的回忆录中,他解释了美国电影,尤其是那些由凯瑟琳·赫本主演的电影是如何使他们着迷并深受启迪和鼓励的。这些电影在格斯·李全家对美国及美国人的好感认识中起了重要作用。或许是因为审查制度,格斯·李的父母并没有看到几部可能会让他们改变这种好感的影片。
这些影片包括《尹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和《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两片均于1932年上映。在美国电影艺术科学学院图书馆查阅有关电影审查制度的卷宗时,笔者颇为震惊地发现,甚至连审查机构的专家们也没有预料到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会对影片产生不悦。在看完《苦茶》后,制片厂公关委员会的詹姆斯·费什(James Fisher)认为,中国视点的处理很得当,应该不会产生任何麻烦。《苦茶》讲述的是一个凶残贪腐的中国军阀(由瑞典出生的尼尔斯·阿瑟扮演)把一个白人女传教士(芭芭拉·斯坦维科扮演)软禁起来,希望她会钟情于自己的故事。影片含有许多费什先生本该意识到的令中国人不悦的因素。
事实亦是如此。费什先生讲那番话的两个月后,一名当时驻华盛顿中国领事馆的官员看了这部影片,旋即与海诺联系。他要求删除军阀枪杀靠墙列队的囚犯的可怕场景,还要求删除影片中令人反感的对白,如“在中国,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黄种猪”和“(中国人)都是诡计多端,不忠不义,道德低下的人”等。
制作这部影片的哥伦比亚公司的一名高管却认为,这些因素被反对方断章取义了。在给海斯的信中,威尔逊(Mr.Wilson)声称:“事实上,每一段看似贬低中国人的话都在影片中得到了反驳。整个故事其实是一篇对中国哲学、公正、美德和雅致的颂歌。”他继续写道,“故事的目的是为了令人信服地驳斥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颇看法。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影片第一部分那些看似贬低中国人的言论是必需的”。
然而,不用威尔逊先生来帮助他们“理解”电影的意图,中国人所看到的是另一个故事,它强化了以往所有的偏见,还在军阀这个人物上增添了注定会令中国人不悦的逆转:尹将军虽是一个非凡、果断、且具世界眼光的领袖人物,但他却会为一个西方女子而魂不守舍,甚至因为这种炽热的爱而抛弃了他的全部。影片结尾时,从军阀变为爱情俘虏的尹将军以自杀了断了一生。
由《上海快车》引发的争议与《苦茶》相似。《上海快车》由玛琳·狄尔特(Marlene Dietrich)主演,她的良师冯·斯登堡(Von Sternberg)导演。作为行业监察人,制片厂公关委员会成员詹森·乔埃(Jason Joy)虽然对剧中的几处不雅对话颇有微词,但他同时认为,“我们很希望中国人会喜欢这部影片,因为在我们看来,你们在全片中都尊重了他们的观点。电影公映时,你们可以去请华盛顿的中国公使们一起来看”。
派拉蒙公司是否发出过类似邀请无从查考,但有记录显示很多中国人与乔埃的看法迥然不同。一篇刊登在中国杂志《图画周刊》上的文章讨论了影片中很多时代错乱的习俗(如“早被抛弃”了的满清长辫和靴子),认为影片展示了“中国政治的最黑暗面”,而其对各式中国人的表现,尤其是黄柳霜扮演的慧飞更令人反感,她是“一个可鄙的中国妓女”。这篇文章总结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制作者们总是迎合了“蔑视所有中国事物”的偏见。
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们显然也是这样看的。在一场流产的上海放映之后,他们禁演了影片,并警告派拉蒙公司,如果不停止该片在世界各地的放映,他们就将禁止派拉蒙在中国发行影片。尽管派拉蒙依然故我地在世界上发行狄尔特和斯登堡版《快车》,美国大使馆还是出面平息了这场争端,派拉蒙的影片也得以继续在中国影院里上映。
派拉蒙作为好莱坞最罔顾文化敏感性的制片公司的声名四年之后又一次浮现。正当派拉蒙盘算开拍一部名为《将军死在黎明时》(The General Died at Dawn)的影片时,在制片厂公关委员会积累了经验,任职制作法典机构的约瑟夫·布林(Joseph Breen)写信给派拉蒙高管约翰·汉姆(John Hammell)称:“我们强烈建议你们在投拍之前,一定要找权威人士来咨询,就中国政府可能会有的反应提供指导。在我们看来,把王某写成中国军队的将军是危险的。我们也认为,中国人会很痛恨这样一种指涉,即外国利益在欺骗、虐待中国劳工。因为这一点和其它细节,我们希望,为了贵公司起见,在开拍前应先听取关于中国方面的意见。”
尽管派拉蒙的确雇佣了一名顾问,当时的中国政府仍然觉得完成后的影片极度辱华,随即禁映该片,并再次威胁要禁止派拉蒙生产的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受此反应的激发,海诺于1937年4月给布林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深感好莱坞电影人“每次拍片时似乎都会在表现中国人形象和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方面出错”。他继续写道:“我觉得,我们的制片厂已经存在了这么多年,本应该有丰富的经验和才智在表现中国情境时不再经常发生对中国人、中国机构和习俗如此愚蠢而固执的描述。”
海诺在《将军死在黎明时》的剧本和一部假想的、将当代美国人生活等同于禁酒时期地下酒吧生活的影片之间做了比较。他认为,《将军》一片虽然聚焦在10到15年前的中国土匪军阀身上,但却给人以“这就是中国目前的面貌的错误印象”。再加上故事中的其它元素,全片“在阐释中国人生活方面毫无说服力”。在提到美国大使馆不得不再次代表派拉蒙与中国政府斡旋时,海诺告诉布林,“我们不可能永远逍遥于此类谋杀行为之外”。
几星期后,派拉蒙的亨利·赫伯润(Henry Herzbrun)写信给布林抱怨称,给他的公司冠以“叛逆”的名号是不公平的,并提醒布林其它公司也曾使中国人不悦,光挑派拉蒙公司的茬,认为派拉蒙“一家公司制造了与中国人的麻烦”是不对的。几个月后,约翰·汉姆也写信给布林,为派拉蒙公司辩护,支持公司的做法,并声称,“我们在上海的代表潘京先生(Mr.Perkins)认为,在涉及中国时,到底拍哪种影片并不重要,因为任何涉及中国的电影,都会引起中国人的不快”。
事实上,从米高梅公司筹拍根据赛珍珠的畅销小说《大地》改编的同名史诗片的例子看,有比派拉蒙更好的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办法。米高梅慷慨地购买了赛珍珠故事的版权,将小说中的中国家庭搬上了银幕。这部小说被认为会确保票房的成功,因为它能深深地打动那些被大萧条折磨的美国观众,尤其是大公无私、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女主人公阿兰这一形象。
米高梅最初打算在中国摄制该片,因此公司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多特别的让步。这些让步包括:删除书中大量中国官员“认为有辱中国和中国人”的材料,米高梅公司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史无前例的“合同”。合同包括六点:
(1)电影要表现中国人真实、愉快的生活画面;
(2)中国政府可以指派代表监督拍摄;
(3)米高梅应尽可能多地接受中国监督员的意见;
(4)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在影片中加开场白,米高梅应据此办理;
(5)所有米高梅员工在中国拍摄的胶片都必须在出关前通过中国方面的审查;
(6)中国政府希望这部影片的演员全是中国人。
米高梅后来还是在好莱坞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只是派剧组去中国摄取了一些背景材料。不过,他们基本遵守了合约的规定,除第六条之外。好莱坞明星制盖过了全部中国演员班底的愿望。保罗·缪尼(Paul Muni)饰演了最重要的角色王郎,路易斯·云妮(Luise Rainer)则出演阿兰,还有其他几个白人演员也演了中国人。
在拍摄过程中,米高梅确实仔细听取了中国政府代表的建议。公司也印发了大量宣传资料,强调要拍一部让中国人愉快的影片。电影完成后,公司先请当时的驻华盛顿中国大使观看,同时在洛杉矶、旧金山安排了类似的放映场次,请当时的中国领事代表观看。这一策略颇为有效。尽管在美国和中国以外国家上映的《大地》版本含有某些中国政府并不喜欢的场景,但影片还是被当时的中国政府接纳,顺利在中国上映。不过,当时的中国审查官还是删除了其中被认为有冒犯中国人嫌疑的片断。
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中日战争的日趋激烈,美中政府间的关系也日益增强。在此情势下,好莱坞各制片公司在处理中国题材时也更加小心和敏感。但有一部影片却威胁到了正在发展和稳固中的美中关系。
《上海手势》原是一部声名昭彰的话剧,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约翰·卡顿(John Colton)搬到了百老汇舞台上。这部剧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MPPDA的成员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把它列入了“禁拍”之列,也就是意味着不能把它改编成电影。不过,在随后的十年中,环球、雷电华、派拉蒙、华纳兄弟、哥伦比亚、米高梅和几个独立制片公司都尝试过将其发展成大纲和剧本,以期尽量满足审查人员的要求,从而达到解除禁令的目的。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原因当然十分清楚。《上海手势》讲述的是女掌门人高德姆(Goddam)在上海经营世界上最著名的妓院的故事,在它的情节元素中充满了大量道德低下的人物、异族婚恋、私生女、白人奴隶和谋杀。1941年,制片人阿诺德·瑞斯伯格(Arnold Pressburge)最终递交了布林觉得尚可接受的剧本。当然,布林在给瑞斯伯格的信中,仍不忘带上如下的忠告语:“我们强烈要求你能找到合格的人,就电影中所出现的中国用语方面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使中国人不至于对完成的影片有所抱怨。”
瑞斯伯格显然没有理睬布林的建议。他请了联美公司来帮他发行影片,并雇用了冯·斯登堡来导演该片。由于《上海快车》事件,斯登堡决非中国政府喜欢的导演之一。顺便提一句,在后来的日子里,斯登堡还写了一部题为《中国洗衣店趣事》(Fun in a Chinese Laundry)的自传。当时的中国官员了解了该片和导演的情况后,立即与瑞斯伯格取得了联系。1941年8月,当时的中国驻洛杉矶大使T.K.张读了剧本的副本后,马上写信给制片人。张觉得剧本中的很多场景都令人不悦,尤其是其中对黑道世界的描绘和中国人正面形象的缺乏。张还列举了剧本中一系列不恰当的成分,认为如果照此拍摄的话,影片注定会激发中国人和了解中国人善良品格的世界友人的抗议之声。
在回信中,瑞斯伯格告诉张,“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电影并非是为了反映现实,而是展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想象的世界与今天现实的各个层面是没有联系的”。他继续写道,“我和冯·斯登堡先生都很热爱中国。我们当然不希望影片伤害到存在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对中国的好感与同情。”
然而,张先生并不这么想。9月,他写信给制作法典办公室的乔夫瑞·夏洛克(Jeoffrey Shurlock),表达了他的失望之情,并寻求对方的帮助。在描述了他与斯瑞伯格、冯·斯登堡两次“并不令人满意”的会面后,张提到在过去几年里,“主要通过贵机构的有效运作,中国人与好莱坞电影业之间建立了非常诚挚的友谊。我们一直都很希望好莱坞电影业能彻底放弃制作那些重点表现中国人丑陋一面的电影”。最后,他要求舍雷克“说服制片人尊重我们在信中表达的要求”。
这以后,双方展开了进一步的协商,但张先生得到的唯一实质性让步是在影片片头加上一条说明,声称故事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这一“既非中国,亦非欧洲、英国或美国”的地方,因此“影片与现世无关”。
如果张先生得知《上海手势》放映后不仅票房惨淡,而且影评人恶评如潮的话,那么他至少会觉得有所安慰。比如,《纽约时报》的鲍斯利·科如斯(Bosley Crowther)认为影片“极端狂妄自大”,“晦涩难懂”,它“唯一拯救自身的一点在于影片最后变得滑稽可笑”。《上海手势》消失得很快,不久就被同时期诸多重要事件淹没得销声匿迹。影片在美国上映时,珍珠港事件已经发生,美中也成了忠实的盟友,而好莱坞对中国的表现,如《龙种》(Dragon Seed)、《王国的钥匙》(Keys to the Kingdom)、《东京上空三十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和《中国的天空》(China Sky)等,都欣然抛弃了旧有的偏见,代之以正面的、通常具有英雄气概的形象。不过,二战一结束,诉诸于旧偏见的倾向再度回潮。
总括而言,责难好莱坞电影业造成了笔者在本文中所描述的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是简单化的误导。对于在银幕上真实表现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中国人自己并不比好莱坞电影人更感兴趣。中国人希望好莱坞电影能以完全赞许的方式表现中国,剔除任何涉及政治乱象、国民动荡不安、腐败、贫穷、肮脏的因素。他们可能会欣喜于一种对其国家和民众更平衡的表现。不过,这并不是好莱坞制片人相信他们的观众会有兴趣掏钱看的影片。
很多年来,好莱坞的种族偏见曾激怒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这一点在当前时代依然如此。因为没有人能估量出这一做法如何影响了外国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在讨论美国声誉和威望日趋下降时,电影人很少被提及。不过,很难说好莱坞电影在外国人对美国及其领导人的印象不佳方面未起一点作用。相当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什么都倒过来了。就像美国人曾将中国人表现得很刁滑,不值得信赖,且具有破坏力一样,现在美国人却开始被世界上大部分人看成是这些品质的化身。想得到尊重的人,必须先学会尊重别人,笔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华盛顿和好莱坞的领导者们能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所在。
标签:好莱坞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上海电影论文; 电影市场论文; 米高梅论文; 苦茶论文; 中国人论文; 上海快车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美国电影论文; 艺术电影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