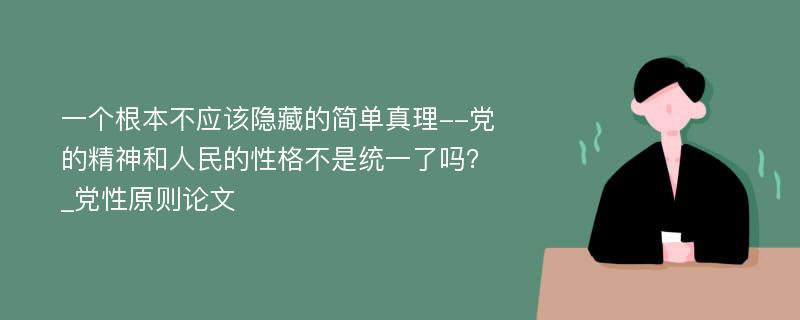
一个完全不应该隐讳的浅显真理——党性和人民性不是统一的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性论文,党性论文,浅显论文,不应论文,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性、人民性的提法是早就有的,但这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两者是相一致的还是有原则性的差异),就这个问题公开争论的事却少有,就我所闻只有一次,那就是1978年在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因此发生争论时。那个时候,因为《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发生了一场“两个凡是”是否正确的争论。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负责人激烈反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可以解释为不同意“两个凡是”的观点,但只是采取了理论说理的温和方式),对《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提出了出人意外的非常严厉的批评,其中就有“人民日报没有党性”这样一句话。《人民日报》负责人当即回答说:“党报固然要有党性,但也应当有人民性,为人民说话。”(大意)这是一场即兴的争辩,批评和反批评双方都是临时的当场顶撞。不意,这场顶撞不仅把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出来了,而且实际上形成一种党内只能提“党性”而不能提“人民性”的倾向,并进而在后来又形成一种回避谈论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的倾向。
共产党的报纸只为党说话,不为人民说话,或者说,共产党只讲党性,不讲人民性,两者不相统一——如果这不是怪论,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什么怪论了。
作者要为此而写文章,自己都觉得有些多余,但既然中国有这种怪论出现,作者在这里说几句话看来也是有必要的。
首先要说明的自然是:什么是党?什么是党性?从来没有什么人、什么党的文件为党性下过定义,对党性做过完整的解释。所以这里我们只好先讲什么是党,党从何产生?我们历来把共产党定义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正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民的先进部分。中共“十六大”的党章更是这样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在这里是更加明白无误、更加无可怀疑了。
而人民又意味着什么呢?这里必须进一步说明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然后才能够说明党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手头恰好有一篇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题为《唯物史观的精髓》(作者施大鹏)。这篇文章记载下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接见外宾的一条新闻报道。这条报道是熊向晖起草的。报导的原稿中本有这样一句话:“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把它修改为:“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毛泽东给作者解释时,通俗地讲了一段哲学道理: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熊向晖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领导人的作用。”毛泽东接着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领导和人民不能等量齐观。“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笔者按:这里所谓“决定因素”和“非决定因素”也只能是在最终意义上说的)。
不要小看了这一通俗的哲学道理(大家知道,对于这条原理本身在我们这里过去曾有人提出过怀疑,但这一原理最终仍然无法否定,尽管其表述方式可以有所不同。这个问题这里就不谈了)。这一哲学道理正是提出了“人民·党·领导者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社会学的重要问题。我们在这里暂且搁起人民与领导者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只谈谈人民和政党之间的关系。
人民要表现其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角色,首先自然要表现在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而这首先要依靠于一定的生产组织(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和凭借一定的文化技术创造出来的劳动技能。而处于一定生产组织中的人们又为财富的分配进行争夺,于是又产生各不同阶级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在现代,就有代表这些不同阶级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的政党产生。
这些现代政党的利益表现是五光十色多种多样的。不少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政党并不代表人民利益而只顾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和特权,只知道掠夺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对内腐败透顶,对外昏愦无能,从头到脚卑鄙龌龊,因而阻碍和摧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政党自然和人民无缘,毫无人民性可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党则不同,这些政党之所以产生,完全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在中国还包括各民族的利益)而进行斗争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全体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也只有全体人民的解放,才有本阶级人们的真正解放。即使在革命获得政治权力以后,这个政治权力也是属于人民的,确切地说,这时政治权力才真正为民所有,而为民所有才能为民所用(这两者是绝对统一的),它所追求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要求和权利,谋求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它绝不将权力据为一党一阶级所私有,或垄断权力以追求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中国共产党宣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就实实在在地表明了共产党的人民性。
那末,党性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好像从来没有人明确论述过,因此它有时甚至被利用来束缚和抑制党员的自觉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依我看来,共产党员作为组织中人,自然应当具有党所要求的一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执行党的决议方针政策的责任(甚至包括入党誓言中的那些条目),这方面的自觉性应当被认为是有党性的表现。然而,这还只是在比较狭义的意义上提出的要求。党性的最高要求是什么呢?毫无疑义,党性的最高要求是真正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有民用”的原则行事,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地充当社会的公仆而绝对不允许窃居社会主人的地位。按照这种要求,很显然,所谓党性正是党的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离开党的人民性的党性,正好像没有不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一样。
党性论决不是驯服工具论。党性更不是“奴性”,毋宁说,党性是同时贯彻着党的民主精神和党员的独立思考精神的。党员个人有执行党的集体决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有提出个人的不同意见和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特别是,如果党的领导人提出的方针是错误的,或者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末,为了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任何一个党员都可以而且应该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论辩之,纠正之。这也是党性所允许和要求的。例如,1978年别的报纸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当时党的领导人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理论上的论辩,《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表示对这一论辩的赞同和支持。这是党报应有的权利,也是党报党性的表现——以后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也证明了这一点,证明这是完全符合党的利益,也是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
那末,究竟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在有些共产党人甚至相当负责的共产党人那里,会产生讳言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乃至否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和现象呢?在我看来,归根到底,是由于我们尚未实现党的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缘故。举其大者如:第一,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制度。一党长期执政,而且以党代政,政治权力实际上集中于党,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权力和人民(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相隔离的弊端(如入党为权、从政为权而不以民生为念,官僚主义、专制主义横行,把一些民意机关当做装饰,权力腐败不受监督,等等)。1986年试图实行党政分开,但最终未成功,某些方面反而更加“党政合一”(如有的地方省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即一例)。政治权力属于人民,而共产党居于政治领导地位——这两者如果要兼得的话,其关系究竟应如何处理,即人民的政治权力应如何掌握和运作才不致从人民手中流失,党的政治领导应如何实施才不致形成以党代政,这个重大问题始终横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在民主化道路上几乎动弹不得。第二,我们还没有真正实行选举制度,干部(当然包括国家公务员)实际上由党委派任命,代表实际上由党最终裁决(尽管有的经过协商的形式)。这样产生的干部或代表,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或是被人民所雇佣为人民打工的,相反,会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是社会的主人或人民的“父母官”,他们的权力欲望只是希望自己一步一步地往上升,哪管人民的困难与死活。因此,说到底,没有真正的选举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民公仆,也不会有民主。毫无疑义,这也是横在民主化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之一。
依我之私见,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不能理解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甚至怕提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即如上述。是耶非耶,愿闻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