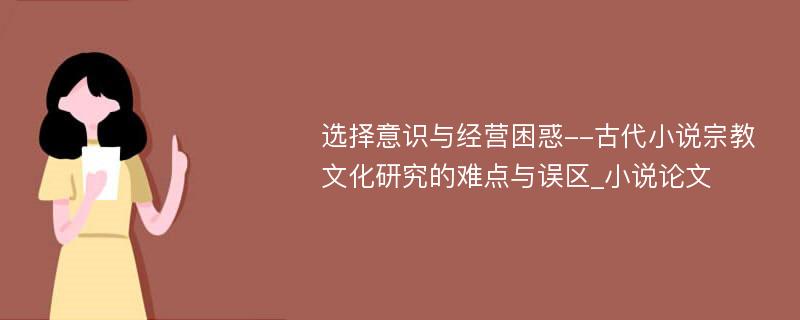
选择的自觉与操作的困惑——古代小说宗教文化研究的几个难点和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难点论文,误区论文,困惑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1—9162(2001)03—0021—06
“人就是人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1](第1卷,P1)作为“人学”的文学,其“重头戏”——小说,与宗教之关系甚密,以至有学者称:“所有的中国通俗小说中均包含着宗教的主题。”[2](P139)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文学与宗教在本质上的趋同之处——人们对人生的终极关切——成为联结二者的纽带。卡西尔在《人论》中说,在艺术活动中同在语言、宗教、科学活动中一样,“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正由于此,当我们把古代小说家及其作品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决不仅仅是某个个别的性格或某种个别的思想所能涵盖包容的,一部部小说中都无一例外地蕴藏着深邃的宗教文化结构和深层的宗教思想内涵。这种现象吸引和启发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选择宗教文化这一独特的视角和切入点,对包罗万象的古代小说世界进行观照和把握,对“人”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透视和剖析。从小说研究的领域为之拓展,活力为之激发的实际看,这无疑是可喜可贺的,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选择的自觉并不等于操作的清醒。综观近年来这方面的著述,尚存在一些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互为矛盾的方面:
一、浑沌与清晰——小说宗教内涵本身的混杂与研究中指向单一的矛盾——将宗教现象从小说中剥离出来的困难
作为历时悠久、分布极广、影响深远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密切关联。人类文明的各部门,人类活动的各方面,包括哲学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伦理、价值取向,乃至个人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小说家面对“人”的世界,如同油画家面对调色板上各色齐备、五彩纷呈的颜料,在其创作运思的实际操作中,各种色彩虽未失去其固有的特质,然而,更多的则是交混杂糅,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分难解的局面,很难用贴标签的方法将已完成的绘画作品里某个色块中的成分说得斩钉截铁,一清二楚。这一现象的成因,笔者已有专文论及,此处不赘。[3](第7章,第2 节“古代小说文化内涵模糊性成因”)可自清代以来,有不少研究者不是综合把握小说中的各种宗教文化成分,而是以主观的预期目标作为出发点,进行硬性的剔除、剥离,以求从中寻找出立论所需的东西。其结果必然如盲人摸象一般,形成对同一作品、同一情节的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些研究者手下,宗教文化似乎成了脂粉一类的化妆品,而小说则成为可以任其打扮的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姑娘。下面,我们还是结合作品的研究情况进行讨论。
关于《西游记》的主旨,清代就有所谓“谈禅”、“讲道”、“劝学”之争;近年来,所谓“扬佛抑道”之说盛行不衰,似成定论;还有人望文生义,随意发挥,断定《西游记》是一部“科学巨著”[4];更有人“求证”出《西游记》的主题是修炼心性,结构是金丹大道,原型是《性命圭旨》和《还原篇》,进而断言《西游记》不是神魔小说,而是融合了儒、释、道、医、易等中国传统文化,剖析心灵,图解性命,反思人生,实现觉悟的文化小说![5]
关于《水浒传》的文化定位,也是各执一端,见仁见智。有人说:“在《水浒传》流传成书的200多年中, 理学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加之金元统治者主要信奉佛教,佛家文化思想实际上是其基础统治思想;佛教众生平等、不受礼法道德束缚的观念根深蒂固,佛教所结构的理想化国度自然而然地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在理学与佛教的浸润中,梁山故事由细民的流传,游民的传播,至元末明初经文人加工成书,其中这些阶层的文化教养、思想意识、情趣理想融合在一起,其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否定与批判就有了依存的思想文化基础”。[6 ]也有学者指出,《水浒传》属绿林文化范畴,而“墨家才是孕育绿林文化的母亲”,因为严格地说,“儒道互补”所能解释的,主要是体现贵族文人思想观念与生活情趣的雅文化。不能否认它对俗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作用,但如果像解释雅文化一样地用“儒道互补”来解释俗文化的话,那就未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能解释绿林文化思想渊源的,恐怕非墨家不可。[7]
同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登坛祭风、祈禳北斗,有人认为是借用了道教的观念和法术;有人却认为其仪式出自佛家密宗。再如,对《三国演义》的“开卷诗”,或认为流露出强烈的“色空”观念,或以为反映出浓厚的道家色彩。
本来,从不同的角度观照一部作品,自然会得出各有差异的局部结论,正如千条江河归大海一样,这些局部结论便集成整体结论。然而,同样从宗教文化的视角出发,却得出上述南辕北辙的结论,这就让人不由不联想起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的一段话:“你之所以为你,是因为你是一个意欲着某种东西的人。除非与其意向的关系,以行为作为意向的表现来看行为,你就根本不可能理解任何表面的行为……每一种意识行为,都迎向某种东西,都意味着人转向某物,而且,都在其自身内——无论多么隐晦——包含着指向某一行动的动力。”如果小说研究者的每一种意识行为都迎向自己预先确定的命题,而不充分顾及作品文化内涵固有的模糊性,那恐怕无异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作品中本处于混一状态的宗教因素,这样得出的结论能靠得住吗?
那么,如何才算是对待小说宗教文化内蕴的正确态度呢?我以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在承认其不确定性、正视其混一状态的前提下,做综合的分析,而不是去做硬性的剥离工作。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为我们提供了典范。谈到《西游记》,鲁迅先生说,文章本出于游戏,亦非语道,“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情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意附会而已。”[8 ](《中国小说史略》)《红楼梦》中“僧道合行”是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对此,已故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在《评〈好了歌〉》中指出:“前面原是双提僧、道的,后来为什么只剩了一个道人,却把那甄士隐给拐跑了呢?这‘单提’之笔,分出宾主,极可注意。这开头第一回书,就是一个综合体、糊涂帐,将许多神话传说混在一起,甚至自相矛盾。原说甄士隐是随道人走的,而空空道人却剃了头,一变为情僧,既像《红楼梦》,又像《西游记》,却把道士变为和尚,岂不奇怪!”对此,钱钟书先生解释道:
《红楼梦》中痢僧跛道合伙同行,第一回僧曰:“到警幻仙子宫中交割”,称“仙”居“宫”,是道教也,而僧甘受使令焉;第二五回僧道同敲木鱼,诵“南无解冤解结菩萨!”道士尝诵“太乙救苦天尊”耳(参观沈起凤《红心词客传奇·才人福》第一二折);第二九回清虚观主张道士呵呵笑道:“无量寿佛!”何不曰“南极老寿星”乎?岂作者之败笔耶?抑实写寻常二氏之徒和光天町畦而口滑不检点也?[9 ](第4册,P1511—1512)
问题提出后,钱先生令人信服地分析了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一为当时道士拾掇僧徒牙慧,以致“清信弟子”“耳熟而不察其张冠李戴”;二为“妄冀福佑,佞佛谄道,等类齐观,不似真人大德辈之辩宗灭惑、恶紫乱朱。”继而,又追源溯流,进一步引《南史》所载夷孙之语,证明“六朝野语涂说已视二氏若通家共事”,且以李白、陆游等人的诗文证明“后世《封神传》、《西洋记》、《西游记》等所写僧、道不相师法而相交关,其事从来远矣。”[9](第4册,P1511—1512)
总括上述鲁迅、钱钟书先生的论述,对我们至少有三点启示:
其一,从创作动机看,小说在本质上是文学创作,而不是某种宗教思想的宣传品或教科书。实际上,以小说作为宗教思想之载体的真正意义上的“辅教之书”,只是在小说发展初期——魏晋南北朝时才有的。随着佛道文化自身的发展演变,它们对小说的影响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态势,亦即从直接宣扬佛道教义,发展为将佛道观念作为创作主旨和艺术表现手段、教化辅助手段。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不至于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其二,从创作方法看,古代小说中的宗教因素,在作者笔下一般被用来作为鬼神外壳,即仅借用宗教鬼神观的超自然、超社会的神学形式和鬼神形象,而其宗教内核则被遗弃了,其被崇拜的资格丧失了,由居高临下的主宰者屈尊为可供作者任意剪裁的布料,加以增减、组合,再造新形式和新形象。假神道以设教,得道成仙以劝善,阴谴冥诛以惩恶。实际上,小说家通过借用鬼神外壳,借得了具有极大魔力的评判是非、解决矛盾的权杖。至于这个权杖本真的宗教蕴涵,小说家并不介意。如果研究者误将外壳当作内核,硬性地追究作品是扬佛抑道,还是扬道抑佛,那岂不是买椟而还珠?这样做,即不符合作品实际,也有悖作者原意。
其三,从研究方法看,宗教固然有排它性,但也有兼容性,然而,就小说本文而言,后者远大于前者。这是因为,在中国社会文化基础层面上,三教合流,功能互补,提供了小说文化内涵模糊性产生的背景;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三教互补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心态与社会思想结构,沟通了小说文化内涵模糊性产生的根源;在小说文化自身层面上,古代小说世界存在的雅与俗、主与辅、显与隐的内在矛盾,造成了小说文化内涵异彩纷呈而又界限不清的状况。
二、共时与历时——宗教文化自身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与小说研究中共时与历时的分裂之间的矛盾——对小说进行宗教文化定性的困难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是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在宗教文化这条长河流经的各个河段,有着不同质地的“泥土沙石”。因而,越到下游,其裹挟的成分越杂、因素越多。一部部古代小说中所表现的宗教文化内容当然较多地反映出其特定时代的特色,但也绝难排除此前历朝历代宗教文化的“遗传因子”。正因如此,在对小说进行宗教文化考察时,既要注重共时性的横向的分析,以不至于埋没其独有的时代风貌;亦应强调历时性的纵向的梳理,以不至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遗憾的是,这些年小说研究领域中见流不见源或重流轻源的倾向并未稍减。一些研究者面对小说中的宗教文化因素,不是把它当作流动不居的长河的一个河段,而是一头扎下去抓起几把泥沙就滔滔不绝,大发议论,这岂不显得过于盲目?
我们知道,宗教观念的核心是鬼神观念。西周以后,神话在上层的历史化和在下层的灵怪化,使得它比神人同形的希腊神话更快地走向世俗人间。从宏观上看,由于这种世俗化的过程始终未能摆脱同一文化心理的支配,故而有着共时性的表现;又由于这种世俗化是沿着从天人感应、神鬼灵异到神人交通、神界人化的历史过程进行的,所以同时亦具有明显的历时性形态。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乔基姆谈到中国通俗小说中包含的宗教主题时说:“首先,通俗小说中由无数神祗、妖魔、鬼怪、精灵组成的王国与构成中国民间宗教背景的一样广阔和神异。其次,这些小说的情节中向来不脱离因果报应的观念。”[2 ]这句话是否失之偏颇姑且不论,但至少道出了古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少研究者在论及小说中的果报观时,几乎无例外地给其贴上佛教文化的标签。其实,从历时性上考察,这绝非佛教文化之“专利”。中国传统的“天命观”中早已孕含了果报因素,只不过不大明显罢了。《尚书·汤诰》有语曰:“天道福善祸淫”。后来,以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为核心的佛教传入中土,此种“福善祸淫,天之常道”的观念很自然地融入佛家,并且使得果报说以它无可取代的震慑力成了儒家教化的得力助手,它集社会教育与法律强制功能于一身,弥补了道德说教的苍白乏力,把道德自完的积极性移植到人的心灵深处。
此外,道教这一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鬼神报应。老子《道德经》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道”是至公至正的,而在冥冥中维护这种公正的则是鬼神。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道教尤其是民间道教的鬼神报应思想加快了佛教因果思想通俗化、中国化的进程,使其突出了现世报应、扬善惩恶的思想。也正是道教的鬼神观交给儒家一把鬼神报应的尚方宝剑。北宋末年先后出现的《太上感应篇》、《阴骘文》,将鬼神信仰与伦理纲常加以糅合,标志着道教在向儒学靠拢的过程中迈出了一大步。其核心即《太上感应篇》的首句:“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身”与《阴骘文》的首句:“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指文昌帝)存心,天心锡汝以福。”《太上感应篇》说:“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而它的“善”、“恶”标准,却并非道教自己的,而是儒家的标准。在这里释道儒已无界限可言,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用鬼神因果来督促人们遵循伦理规范,维护秩序稳定。
再往远追溯,早在本土道教产生、印度佛教传入以前,我国已形成了自然神、祖先神为轴心的多神崇拜观念,即已出现自发的兼容性极强的“准宗教”文化现象。在后来道教的产生发展以及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都自觉兼容了汉以前庞杂散乱的“准宗教”遗产中原有的鬼神观念。也就是说,从纵的历时的角度看,佛道二教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单一发展的,而是在宏观上经历了一个从多元并立向复合混一发展;从混一化的低级形式(复合境界)向混一化的高级形式(整合境界)发展的历程。古代小说所反映出的宗教文化因素恰与这一历程相吻合。以幻想小说为例: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早期幻想小说内容驳杂,原始神话系统、道教神仙系统、民间精怪系统等多元并立,又类属分明,而“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创作目的则成为多元共存的基础;至中唐前后,随着“三教合一”渐成趋势,小说幻想艺术进入了境界混一化的阶段,出现了虽分别以佛教系统、道教系统和民间信仰系统为主,却又吸收容纳其他系统形象的小说;宋元至明清,理学、禅宗和新道教的发展,使得小说幻想艺术进入混一化的高级阶段——整合阶段。这一时期的幻想小说,不仅以其整体的宏大的统一的艺术境界的构思而与复合境界阶段只是单篇故事中不同系统形象的组接有了明显区别,而且此时期三教圆融中已包含着对其信仰与体系自身的内在否定,标志着小说幻想艺术从信仰化到意念化的转变。因而,讨论某一部小说的宗教文化内蕴,必须进行共时性研究,否则就很难把握其时代的地域的特色;同时也必须进行历时性探讨,否则就难免见流不见源,而在表层搁浅。
再往深追究,中国文化对于人伦道德的基本哲学,始终建立在因果报应的观念上。无论儒、道都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只不过是程度深浅的区别而已,后来加进佛家思想,更特别注重三世因果的信念,于是三教思想不谋而合,相互扶掖并行了。但是,在小说宗教文化本身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对道家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不够,重佛而轻道,这还是因为缺乏历时性探讨,而不察“周秦以前儒道并不分家之渊源脉络,与其演变为百家学说之因由”[10](P77—78),以至于忽略了“中国文化之中坚,实为道家之学术思想”[10](P77—78)这一事实。正是有鉴于此,南怀瑾先生深刻分析了道家学术对中国政治社会的深层影响:“盖自秦汉以后,儒道与诸子分家,儒家学术,表现其优越成绩于中国政治社会间者,较为明显。道家学术则每每隐伏于幕后,故人但知儒术有利于治国平天下之大计,而不知道实操持拨乱反正之机枢。更何况后世之言治术与学术思想者,虽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而故作入主出奴之笔,使之迷惑其源流。”[10](P77—78)南先生的话虽仅就儒道之渊源关系及道家学术之地位而言,但其研究方法对我们颇有借鉴意义。当我们观照文学作品中的宗教现象时,应当把某一特定宗教纳入整个民族的文化模式中加以考察。文化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是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而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是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它以内在的、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着每一个体的行为,赋予人的行为以根据和意义。虽然文化的影响力不像政治、经济制度那样外显、直接、自觉和强烈,但更为持久和稳定,它往往能够跨越时代、超越政治经济体制而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行为。因而,文化模式是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这就告诉我们,对小说中宗教文化的把握必须照顾到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一方面,要在共时的维度上揭示小说宗教文化包蕴的特定时代、民族、地域的因素,以在更大尺度上讨论类似东西方小说文化差异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历时的维度上,探讨主导性文化模式的转换,并以此为深层坐标,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视小说宗教文化演进的轨迹。
三、单一与综合——宗教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小说研究中妄下断语之间的矛盾——对小说宗教因素作准确辨析的困难
在宗教的信仰、理论、实体、文化四个层次中,宗教文化的概念最为宽泛,它涵盖宗教推动和影响下形成的多层多向文化,且其边缘又与非宗教文化交叉融渗,具有广泛深刻、模糊不居的特点。佛道二教对小说施加影响的整个过程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态势,并具化为:直接宣扬佛道教义——以佛道观念为表现手段——以佛道观念为教化工具——以佛道哲理为创作主旨等四种方式。近年来,由于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的影响,使得小说宗教文化的研究过于零散,过于浮浅,缺乏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严谨态度。当然,中外文学史都反复昭示着这样一个原理: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因其自身积淀着丰厚的文化价值,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总会有新的观照、新的发现,但是,正如“刻舟求剑”的寓言所揭示的,尽管乘舟之人完全可以在船上刻出宝剑落水的不同方位,可剑的落水处毕竟是唯一的。要加以精确测定,只能将船、岸、河三者互为参照,综合考察。我以为,面对古代小说中蕴含的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只有分出上层与下层、主导与辅助、显赫与隐蔽三个不同层面,进行全方位析理,才能客观准确,避免失误。
(一)上层与下层
在中国社会,佛道二教从来都分为上层宗教和民间宗教两种。一般说来,下层信徒多注重于形式方面,而上层信徒多注重于精神方面。《感应篇图说·流通善书说》所云“遇上等人说性理,遇下等人说因果”正反映了宗教精神与形式的分离。在古代小说中,对上层宗教和下层宗教都有反映。具体说来,由于宗教本身又是一种哲学,所以作品中的哲学观念往往表现为上层面的,而作品中的宗教形式以及芸芸众生对宗教的态度则是下层面的:中国民众一方面崇信神佛,求助于超自然、超现实的神秘力量;另一方面信仰又不那么认真纯粹,仙、佛、菩萨、阴阳风水在他们的头脑里共生并存,各有各的用处,借以求得灵魂的慰藉和希望的寄托,但又不时持一种游戏态度,神佛甚至可以成为嘲弄对象。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小说中的宗教成分是上层宗教充分世俗化后的产物,而从上层宗教到民间世俗宗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从清晰到混沌、从相对纯粹到相对混杂的过程。认识不到这一点,搞不清上层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区别,小说研究不仅会事倍功半,而且会不得门墙而入。
(二)主导与辅助
儒释道三驾马车,以儒为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架。这种构架的功能在于以三教互补,为整合社会服务。纪昀在《滦阳消夏录(四)》中借人物之口说:“儒以修己为体,以治人为用。道以静为体,以柔为用。佛以定为体,以慈为用。其宗旨各别,不能一也。至教人为善,则无异。于物有济,亦无异。其归宿则略同。”“盖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这番议论既精当地指出了三教不同的思维路向与学派特征,也肯定了三教宗旨归一,即儒学操其本而治其根,释道抵其隙而补其缺,成为儒学的拐杖。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的小说家都自觉地将作品的价值定位于“释道辅教”之书,当作“《六经》、《国史》之辅”。与此相适应,在创作方法上往往借神道设教宣传儒家思想。以《聊斋志异》为例,谁都承认它是一部谈狐说怪之书,然而几乎所有为其作序跋的清代评论家又都将其归于儒教之范畴。冯镇峦曰:“聊斋圣贤路上人,观其议论平允,心术纯正,即以程朱语录比对观之,亦未见其有异也。”[11](《读聊斋杂说》)但明伦曰:“惟喜某篇某处典奥若《尚书》,名贵若《周礼》,精峭若《檀弓》,叙次渊古若《左传》、《国语》、《国策》……于人心风化,实有稗益。”[11](《聊斋志异·序》)赵起杲云:“其事则鬼狐仙怪,其文则庄、列、马、班,而其义则窃取春秋微显志晦之旨、笔削予夺之权。可谓有功名教,无忝著述。”[11](《青本刻聊斋志异例言》)《聊斋》所反映与印证的是一种普遍的历史文化现象,即宗教伦理对儒家伦理体系的自觉皈依和深刻影响。当我们探讨小说宗教文化因素时,如果忽视这一现象,得出的结论恐怕只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三)显赫与隐蔽
在儒释道三家中,儒为主而释道次之;在释道二教中则又释显道隐。古代小说中的宗教文化因素也恰呈现为这样一种状况:儒家正大堂皇,理直气壮;释家慈悲为怀,无所不能;只有道家韬光养晦,深藏不露,却又在暗中起着不小的作用。一些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佛教的成分,实质上却是以道教为根基的。这是因为“中国过去的教育,与中国前辈谈书人的知识分子,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大多数都以儒家的思想做规范,以道家与道教的精神做基础”。[12]道教的两本书:《文昌帝君阴骘文》和《太上感应篇》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教育人的范本。它们以天道好还,福善祸淫的因果做依据,制定道家与道教的戒条和上天成仙的标准,注重阴德的修养。民间流传甚广的“救蚁得状元之中,埋蛇享宰相之荣”的思想,便源出于此。可以这样说,借助宗教形式讨论干预天下大事已是行之有效的艺术传统,然而,在古代小说中,宗教的表现形式却往往佛表而道里,佛显而道隐,最终佛道指向的兴奋点又总是落实在儒家教化上面的。
收稿日期:2000—11—20
标签: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宗教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太上感应篇论文; 西游记论文; 读书论文; 道教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