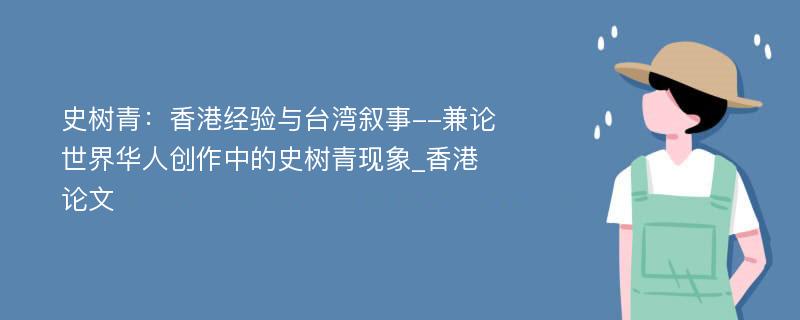
施叔青:香港经验和台湾叙事——兼说世界华文创作中的“施叔青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香港论文,现象论文,经验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4年,施叔青离开她生活了16年的香港,回到台湾。
施叔青的创作本来就从台湾出发。尽管1970年出版第一部成名小说集《约伯的末裔》后就离开台湾,但她的视线一直未曾离开过台湾,只是二十多年在世界各地行走,毕竟使她获得了另一份不同于台湾的体验和视野。在这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境外人生中,香港是施叔青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一段,不仅生活的时间最长,创作的收获也最丰。如果把施叔青的人生与艺术经历,简约为从东方走向西方,再把西方融入于东方,那么这个从人生旅程到文化意义的“东西融合”,其最后的完成是在香港。阅读施叔青的境外小说,可以感到她的每个故事主人公几乎都有着来自台湾的生活背景,实际上施叔青关注的是这些带着自己生命痕迹的故乡同胞来到异邦的生存境况。这些大多体现为“情变”或“家变”的故事,背后牵扯的是生命变迁所蕴涵的历史跌宕和文化冲突。显然,对于大多有着良好家庭出身和知识背景的他们(从台湾来美国帮佣的常满姨是个例外),物质生存的压力并不大,倒是知识者敏感的文化差异是他们主要的精神困扰。这也区别了施叔青70年代以后的境外小说与50年代的於梨华、60年代的白先勇小说主题与人物的不同。初抵香港,施叔青基本上还是沿着相近的创作路线发展,以女性命运为中心地来描写香港名流社会的众生相。九篇“香港的故事”构成了施叔青观察和讲述香港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角。只不过人物的身后,有着更多样和复杂的背景,既来自台湾,也来自大陆,虽着墨于当下,却交错着历史,借助香港这块大英帝国的最后殖民地——同时也是中国政治涡漩的避难之地,“过客”似的以瞬息的诡丽与辉煌,展演在这个“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舞台”。“香港的故事”较之施叔青此前的创作,例如《常满姨的一天》和《完美的丈夫》等,当然有所突破,但其人物类型和讲述风格,基本上还是我们所曾熟悉的。作者“东”—“西”—“东西融合”的这一文化逻辑,大抵隐喻在人物的生命经历和精神建构之中——虽然这样建构充斥着差异、误读和矛盾的杂音。
《维多利亚俱乐部》和“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过去创作的痕迹(特别是《维多利亚俱乐部》),但却是作者创作逻辑发展上的全新展现。作者不甘于被定位为“女作家”的身份,而决心超越性别地以“作家”的全能视角,来观察和讲述世界;因此她也不再满足于主要是通过知识女性的情感波澜来透视生活的某些侧面,而是直面百年香港的屈辱历史和殖民大厦崩塌之前的瞬息繁华,展示自己独特视角的叙事。虽然贯穿“香港三部曲”的黄得云也是一个女性,性别和性在小说发展中是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小说结构和人物命运的是历史,而不是其他。施叔青直面的是一段东方和西方冲突和交会的历史,是一个既互相分离又互相渗透的华洋杂处的社会。这是作者面对的一个书写对象,也是作者处理这一书写对象秉持的一种精神。
如果说,当九篇“香港的故事”蜚声香港文坛时,施叔青还被视为是一个如她故事主人公一样的客居香港的“外来人”;那么《维多利亚俱乐部》和“香港三部曲”问世以后,人们就不能不承认施叔青的香港作家身份。其实香港并没有太多“土著”,所谓香港“本土作家”都有根或长或短地深深牵系于祖国内地。“香港作家”是个宽泛的称谓,往往以其在香港居住的年限和作品描写香港的深广程度来确认其身份。居住了16年且有这样深刻反映香港历史和现实的作品行世的施叔青,当然无愧于“香港作家”这一身份。
这些无疑为施叔青的文学生命积累了一份独特而重要的经验——香港经验。对于一个作家说来,经验无可拒绝,犹如你无法拒绝生命曾有的历程一样,它甚至潜意识地会左右你手中的那支笔。虽然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所有的今天都是昨天的延续”,这又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改变的:历史如是,文学创作也当如是。当施叔青离开居住16年的香港重返台湾,面对一个对她说来既是熟悉又是新鲜的世界,她的香港经验如何在新的台湾书写中发酵,站在“香港”的这级台阶上,有助于或者有碍于她登上另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人们所十分关心的。
二
从出版时间上看,“香港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寂寞云园》,应该是在施叔青于1994年回到台湾之后才完成的。(注:施叔青1994年离开香港,《寂寞云园》出版于1997年7月。其实,在该书的《自序》中作者就说“动笔时,我已离开香江……”。)但她决定回台湾时,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写“台湾三部曲”。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了新的创作目标,《寂寞云园》写得有些匆忙,还是作者自己所说的,前两部耽溺于一段充满殖民色彩的情恨纠葛,叙事过细,迫使最后一部只能匆匆了结,这也是不得已之事。不过,“香港三部曲”整整准备了十年,先有了“香港的故事”和《维多利亚俱乐部》垫底,最后才依循《维多利亚俱乐部》的人物线索追溯整部香港的殖民史。以鹿港为中心展开的“台湾三部曲”,即使写的是故乡旧事,也不可能一回台湾就一蹴而就。尤其是施叔青在“香港三部曲”,以虚构的人物穿梭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之间,从而在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之间搭起一座互文和对读的隐喻的桥梁。这一经验使作者在进入“台湾三部曲”写作之前,无论阅读史料还是熟悉社会,都必须十分较真地付出许多时间。倒是在这段时间,作者对都市生活的敏感,使她对90年代末期台湾盛行的“红酒”风潮别具慧眼,借此以一部《微醺彩妆》的长篇扫描了当下台湾都市社会的众生相,成为一种“世纪末”的隐喻,同时也以此作为“台湾三部曲”开笔之前的一种准备和铺垫。
《微醺彩妆》充分表现出施叔青对都市人生的熟悉和敏感,这与她在被喻为“东方明珠”的香港一年生活的都市体验,恐怕不无关系。香港和台北,是两种文化孕育起来的都市,虽然它们之间渐渐有了一些渗透和交融。台湾在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前就有了深厚的中华文化传承,而香港则几乎是在割让英国之后才发展起来。这在两地的酒文化上划开一道鸿沟。中国的酒文化史可远溯至三千年前的先秦。以粮食作为主要原料的黄酒和白酒,是中国漫长农业社会的产物,所有宴酒的仪礼,也都是为了维护尊卑有序的封建建构。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礼制压抑下,酗酒便成为放纵个性的有悖于封建秩序的放浪行为。酒礼从庙堂走入民间,形成一套以张扬性情为中心的民间酒俗,整个儿就是对封建酒礼的叛逆和颠覆。民间豪饮的酒俗,在近半个多世纪来的台湾发展有加。台湾坎坷的历史命运,卷裹在历史浪潮之中无法自控的悲情人生,一夜暴富或瞬息破产的机会与挫折,如此等等,都使压力过大的内心五味俱全的情感需要宣泄;而酒——尤其是白酒,能让你如癫如狂、欲死欲仙的烈性白酒,从金门高粱到白兰地和威士忌,都是最好的释放剂。夸张一点地说,当代的台北(或者竟至整个台湾)是靠白酒养育起来的。而香港则有些不同,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相应也远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酒礼。香港的开埠,英国殖民者带来的是西方的红酒文化。其源头虽可远溯至古希腊文明,但希腊的城邦制,使酒只是张扬个性的助燃剂,而不是封建秩序的符征物。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红酒生产的精致化,使细品成为西方酒礼的中心,体现着西方不同于东方的士绅风度。中国称酒为“饮”,唯茶才“品”,“豪饮”是一种酒风,唯此才显气概。中国文人的风度是从魏晋甚至更早就建立起来的,其特征就是放浪形骸的豪饮。这和西方的“品”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如果说台北是座白酒的城市,而香港则应是座红酒的城市。当红酒“侵入”台北,并且形成“风潮”,其意味是复杂的。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融入,更是在融入中出现的一种文化。豪饮的台湾人,开始细品起红酒,却又不仅在于“细品”,而是附以诸如“喝出健康”、“喝出友情”、“喝出政治”之类的神话(这和今日的祖国大陆一样),实际上仍是把酒和巫、和医、和政治相联系的古代传统的延续。红酒成为一种时尚,而时尚引导消费。这就在文化与经济之间留出巨大的空隙,让品尝者既在走向精致的消费中展演奢靡,也在竞相消费和提供消费中暗藏心计,映现出一种世纪末的“精致的颓废”与“末世的疯狂”。稔熟红酒文化的施叔青对红酒进入台湾之后迅速发生的异变,当始料所不及,也因此有了敏锐的发现和施展想像的用武之地。
如果说,西方人是从家乡来的葡萄酒“找回失去家乡的味道”,这是小说的引言所说的;那么红酒在台湾,恰恰相反,是要“制造一种疏离本土的感受”:“一杯在手,让人把花都巴黎联想在一起,品饮红色液体,不仅体味它的香味口感,也同时感受到精致的法国文化。”这是比较雅致的宣传,还有更粗俗的广告:“葡萄酒颠覆台湾。把酒当女人,享受她。”为什么一标榜“疏离”、“颠覆”,就有如此巨大的煽动力,使台湾的红酒市场,“原本五、六十个进口商,到了一九九七年的夏天,竟然增到七、八百家”,其背后的社会心态若何,可以想像。这让我们想起小说描写的那位退休的外交官威灵顿·唐(唐仁)。这个台大出身一路顺风顺水进入外交界,偌大的抱负却只在南美洲一个小国当一名领事,又不得已因为台湾的外交困境而提前退了下来。这个品味高雅的前外交官,困居在台北的公寓里,在台湾红酒风潮面前也不能免俗地放下身段,成为南部红灯区出身的土财主洪久昌旗下的一名媒士,从法国专门仿造类似于某种脱销的地产葡萄酒口味,以迎合中南部民众拿葡萄酒配蒜泥白肉和宫保鸡丁的粗俗习惯。这种“以真代假”既不离本土又制造一个虚幻的“疏离”感觉,使台湾红酒风潮充满吊诡。红酒的迅即走红,不在红酒,而在炒作。那个从股票场上败退下来的鸿展证券公司老板邱朝川,在异想天开投资美国的所谓“航天地产”无着后,以生意场的老手一眼看中台湾的红酒市场,和洪久昌一样地坦言只要“进口商把红酒当股票炒作,一哄抢,价格上去了,抛出去,新台币落袋,安心。”而且和媒体合谋,制造出诸如品酒师吕之翔那样的名记者,以高雅掩饰粗俗,借媒体虚张声势,神乎其神大灌迷汤,弄得大半个台湾心旌摇晃、如痴如狂。至此,红酒已离开了它的自身,异化为弄潮儿手中推波助澜的“神器”,不仅制造酒的神话,更重要的是制造财富的神话。即使“素以品味和懂得享受闻名于台北社交圈的二世祖”,宏亚企业的继承人王宏文,在玩遍高雅之后,最终也憋不住要下海做红酒生意。只不过他与洪久昌和邱朝川那些小商人不同,过剩的财富和更深的心计使他在聚饮摆阔、豪饮斗奢中,幻想买下一整座波尔多酒庄,或者垄断酒庄全年的出产;碰壁后又不惜搭机穿梭于世界各地的名酒拍卖会,圈出了其中三公升装的顶级陈年红葡萄酒十五瓶,并以一瓶六公升的大樽装命名为“十五全”至尊,计划在国民党“十五全”会议结束的那一晚进行拍卖。酒与政治的这种“联姻”,在南部红灯区出身的土财主洪久昌和精明不过的股市老手邱朝川心中,也是无法想像的。台湾的红酒风潮,经天行地,无所不至,确是一大奇迹。
《微醺彩妆》中的某些人物,常常会使我们想起施叔青香港小说中的一些人物的影子。例如唐仁和《窑变》中的姚茫,洪久昌和《愫细怨》中的洪俊兴,吕之翔和《维多利亚俱乐部》中的徐槐等等。不过《微醺彩妆》写的是世纪末的“精致的颓废”,是一种在高度的感官享受中的疯狂和失意;而施叔青此前的香港小说,更多的却是一种“末世的感伤”。如果说其女性主人公大多属于情感的斲伤,而男性主人公的命运背后,却大都有着中国政治的跌宕,其感伤更多来自被政治漩涡甩出中心而栖落在香江滩上的孤寂和愤郁。施叔青不是一个精于政治的小说家,但却是一个善于将政治隐喻在人物情感和身世背后的说故事者。她的并非刻意使政治了无痕迹的融入在她的小说中,其中韵味值得我们去深深品察。
“微醺彩妆”其实是一种新流行的化妆术。唐诗说:“一酌发好容,再酌开愁眉”,酒至微醺,酣态可掬,却又不忘所以,是谓饮者的最高境界。然而现代的化妆术,不需酒助,也可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轻扫腮红,装出微醺的样子,多扫几次,脸红红的,不必喝酒就有醉茫茫的酒意。现代社会,什么都可以作假。当洪久昌仿本地口味从法国调制葡萄酒进口以真乱假,而小说主题的“微醺彩妆”又以化妆术来以假乱真,真作假时假亦真,世界的颠倒已经无可辨识。难怪作者意味深长地以品酒师吕之翔的嗅觉失灵作为全书的开篇,又以吕之翔在遍寻药石好容易恢复了一点嗅觉之后,又以味觉的香臭不辨为代价来作全书的结尾。对于吕之翔来说,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好容易从一名小小记者乘着红酒风潮攀上了品酒师的高位,却又乐极生悲地跌了下来。那么对于整部小说,以及小说所说事的社会,它又将隐喻着什么呢?
三
现在来讨论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或者为时尚早。小说的第一部《行过洛津》于2003年底才出版,接下来应当是重头戏的第二部、第三部还在读者的期待与想像之中。这个时候对《行过洛津》过多地说三道四,无论对作家还是对读者,都不适宜。然而“三缄其口”也不是作家和读者所期待的,这里只就“管窥”说点“蠡测”的粗浅印象。
洛津是施叔青家乡鹿港的旧名。“一府二鹿三艋舺”,不仅是民谚,也是历史。这里是台湾先民最早从祖国内地登陆垦殖的地方,也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开放海禁第一个允许放船与泉州蚶江对渡的港口。不过《行过洛津》的故事只从嘉庆中叶说起。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户口编查,几乎成为治台湾史者划分台湾从汉族移民社会向移民定居社会转型的一道分水岭。因为根据这一年户口编查的统计,台湾的汉族人口达23.2万户,190.2万人(注:见道光《福建通志》第四十卷“户口”篇。而《嘉庆一统志》所载人口为24.5万户,178万人,相差12万人。),比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福建巡抚雅德奏报的台湾府实在人口91.29万人,30年间翻了一倍多,平均年增三万多人。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只能是移民。而此后,据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文献资料,台湾人口254万人(注:见《台湾省通志·人民志·人口篇》。),82年间人口只增加63.8万人,平均年增人口0.78万人,接近了自然增长率的水平。从嘉庆十六年以前台湾人口的增长以移民迁入为主,到嘉庆以后移民潮逐渐回落,人口以自然增长为主,这是台湾向定居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行过洛津》略过了台湾早期移民“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最初开发阶段,直接切入台湾进入定居社会之后,以农业垦殖提供的丰富物资(米、糖)为基础推动效商贸易的繁荣阶段,这也是鹿港最为繁华风光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当泉州泉香七子戏班艺名月小桂的小旦许倩,第一次于道光年随戏班应洛津郊商首富石烟城之邀,搭乘石家万合行的戎克船,渡海来为重新彩绘的天后宫妈祖庙举行庆贺演出时,以一个外来人的眼睛看到了洛津泉州街有如“清明上河图”般的热闹繁富,和石家“仿如从水中浮起一座华丽无比的水晶宫殿”的连云甲弟。石家的发达从石烟城的父亲那辈开始,当还在嘉庆年间。到许倩第三次于咸丰初年作为一名落魄的鼓师被邀来洛津教戏时,不过几十年间,“转眼繁华等水泡”,不仅石家败落,洛津也因为港口淤塞,渐渐做完了它的海上繁华梦。
这就呈现出了“香港三部曲”小说结构的意蕴:人物的命运与历史的曲折同步,作者是通过人物命运的编排来透视历史发展的曲折的。施叔青也像写“香港三部曲”那样下功夫在大量的文献史料乡情民俗上做功课,使小说人物命运的每一步曲折和坎坷,都准准而稳稳地踩在历史的脉穴上(注:作者在介绍石烟城的家世时,有一个地理上的小小的差错,书中称石家在永春山区落户,传至第四代“移居晋江边的诏安”,按诏安在福建西南端,与广东的潮州相邻,一向隶属漳州(前龙海地区),不在“晋江边”,这里显然有误。又第280页称“陈盛元祖上是晋江海澄人”,海澄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置县,现与龙溪合并为龙海市,一向隶属漳州,在地理位置上与晋江隔着同安和厦门,不可能属于晋江。这些都无伤大雅,提出仅供参考。),让我们从人物的喜怒和伤痛中,隐约感应着历史的喜怒和伤痛。不过《行过洛津》在结构上,并不是“香港三部曲”的翻版。“香港三部曲”以一个家族的四代人物贯穿全书,特别是让黄氏家业的开创者,那个从东莞乡下被绑卖到香港陷身烟花柳巷的妓女黄得云,穿梭于香港的华洋杂处的社会和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中,银线穿珠般地结构起一部从黄氏家族侧映出来的香港殖民社会的百年兴衰史。《行过洛津》虽然也意图透过人物命运写历史,但历史只在人物记忆和倒叙之中,成为人物朦胧的背景,而不是小说直接叙说的对象。虽然人物的命运应合着历史的命运,但更多的还有掺杂着人性的偶然和必然,不像“香港三部曲”的黄得云那样,具体表现为各种事件的历史的变迁,决定(!)着人物的命运变迁,也推动着人物性格和小说情节的发展。如果说“香港三部曲”是迹近于由“点”(黄得云)划成“线”(黄氏家族)地来结构香港的殖民史、社会史,那么我们从《行过洛津》看到的,则更迹近于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几组不同人物跳跃式地穿插于不同时空的生活,风俗化地展示社会生活的“面”。故事从一个人物移向另一个人物,或者有所交错或者独立存在,犹如展开一幅偌大的风俗画,一角一角地呈现出整体的风貌与蕴藉。
《行过洛津》人物繁多,如一棵树,枝蔓纠缠。作者以艺名月小桂的许倩三次来洛津为线索,串连起一个枝重叶覆的世界。首先是许倩身边的优伶娼妓人生:七子戏班会放“目箭”的大旦玉芙蓉,后车路如意居的艺旦珍珠点和她的“童养媳”艺名花月痕的阿婠等等,这是社会最不齿却又最能使社会骚动起来的一个底层生活群体。由这里切入带出了过海请戏的洛津泉郊首富石烟城,想把月小桂“去势”包养下来的南郊顺益兴掌柜乌秋等等,这是洛津社会暴富的上层,执掌洛津的生死命穴:郊商兴、洛津兴;郊商败,洛津败。而每个郊商兴衰的背后,都有他们带有那个时代痕迹的历史因缘,从而使这些看似平面的叙事因为有了背景而“立体”起来。还有另一个阶层也由这一枝蔓的伸展而卷入其中,自诩扬州名士的洛津海防同知朱士光,以及开埠以来第一位洛津举子陈盛元等,这是高居社会上方的官僚阶层。这样本来八杆子打不到边的传统社会互相区隔和对峙的三种人生,由于一个戏班的到来和一个戏子的命运,盘根错节地纠葛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如今看到的这样一部难以一语道明的繁富繁杂的小说。
五岁就绑卖给戏班的艺名月小桂的许倩,其命运的出发有点像黄得云,都是除了自己身体以外一无所有。不过黄得云靠自己的“身体”攒下偌大一份家业,而男扮女身的月小桂/许倩,却在两小无猜地认识了童年的阿婠之后,唤醒自己的性别意识,从乌秋的股掌中逃了出来,接着就由于变声而被逐出戏班。当他第二次、第三次以“正笼”和“鼓师”的身份再随戏班到洛津时,他已经逸出洛津故事的主轴之外,而以一个“看客”的身份为洛津的兴衰作见证。这和“香港三部曲”有很大不同,作者只是借着许倩的眼睛来看洛津,而不是如黄得云那样,以其自身的参与来演义洛津的历史。
不过,作者的深意或许正在借此来颠覆男性中心的大历史观。向来的历史,都是居于权力中心的男性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讲述的帝王将相的历史。作者有意选择优伶娼妓作为主角,通过他们的眼睛和经历来看兴衰、说事变,而把居于权力中心的那些表面道貌岸然,内里肮脏龌龊的豪商士绅,贬为“龙套”,围绕着他们团团转地来发展故事。让“后车路”落寞的夕照,映衬出洛津港淤船停的衰败。这种颠倒的历史,正是“以小搏大”用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来讲述上层大世界兴衰故事的历史的颠倒。作者充满人性关怀地揭开了优伶娼妓不甚为人所知的那些幽秘人生的悲情一面。他们从童年的裹脚开始就被按照男性中心的审美标准所塑造,把玩于男性股掌之间却又不齿于他们的口中,待到人老珠黄失去了可供男性赏玩的条件,便弃如敝履地走入人生悲凉的晚境。男旦许倩变声后的沦落,红极一时的艺妓珍珠点肺疾后的死无葬身之地,色艺双全的花月痕(阿婠)晚年的失态暴躁,莫不是这一悲剧的重复。作者真切地进入他们的生活,为他们的不幸发声,有着极为感人的力量。
《行过洛津》另一个让我们不能忘怀的是作者深入细腻地刻绘出一个“民俗台湾”。随同大陆移民携带而来的汉民族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实际上沿着两条互相渗透和抵牾的渠道:一是以士人为代表的来自官方上层的精雅文化,体现在《行过洛津》中的朱士光和陈盛元身上;另一个是以俗民为代表的来自下层民间的世俗文化,它构成了整部《行过洛津》的民俗生活基础,敷展在许多民俗节日、民间信仰、戏曲、说唱和传说故事之中。民俗的形成,也是移民社会走向定居的标志之一。在作者“以小搏大”、颠倒传统史观的众多招数之中,其重要一点是让许多民俗人物进入历史现场、我们不仅看到七子戏班的众多优伶,还看到讲古的青瞑朱、爱摆史的疯辉、追寻浊水溪源头金山银山的风水堪舆师,以及关于石家败落的种种神乎其神的传说等等。这些本来都不登大雅之堂的稗说邪议,惶惶然地登上洛津的舞台,和正史融于一炉,让你难辨是真是假,是讲史还是说书,使整部《行过洛津》摆脱了它掉书袋的抄摘史料的陈腐气,而弥漫着一种来自民间和民俗的活泼生命。这也是《行过洛津》的乡土性所在。在这点上是“香港三部曲”所难以企及的;恐怕也是除了施叔青那种对家乡每一寸土地,每一条袖子一样狭窄的幽径小巷、每一堵墙、每一扇窗、每一棵树……都深入细察得那么知根知底,所难以胜任的。
四
施叔青的文学历程从自己的家乡鹿港出发,一直到今天仍深深影响着她的写作。那种来自童年、来自家族、来自乡土的经验和记忆,那种一闭眼仿佛就能闻到的沧桑港城的气味,插满头饰走在幽幽狭巷中的女人的风韵,道地的唱歌一样软软的泉州腔口音……一不经意就悄悄溜进她的文字里,隐身在她笔下人物的灵魂中。但施叔青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尽管乡土人物不断走进她的小说,在满世界浪游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又从“离客”变为“归人”,从头来写故乡沧桑的历史,她仍不是!她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华作家”,虽然从1970年离开台湾就去了美国,在那里读书、恋爱、结婚、生女,写下了一个又一个从台湾或从其他地方来到美国的中国人的故事;入籍使她在政治身份上成为美国人,但依然没有多少人把她当作“美国的”华人作家。她既不是汤婷婷们那样的美国华裔的第二代、第三代,也不像五十年代就移居美国的於梨华们那样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即使在如今时髦的“新移民作家”的名单上,也寻不到她的名字。她居停香港十六年,作品进入香港文学史,是名正言顺的“香港作家”,但在香港文坛上人们习惯都在她的“香港作家”上面加了“台湾来的”四个字修饰词,还是个不同于“根生”的“外来人”。
她好像不属于谁,但又都属于谁。
这种“身份”的尴尬并不是施叔青的尴尬,而是当今世界华文创作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现象——或曰“施叔青现象”。值得我们深究的是这一现象的意义。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日益频密的交往,使天地变窄、地球变小;它也加速了作家的流动。李白浪漫的想像,朝发白帝,夕至江陵,还在一个文化国度之中;而今天的朝发夕至,可能要跨越或亚洲、或美洲、或欧洲、或非洲几种不同文化与国家。作家穿梭其间,或短暂停留,或长期定居,或定居了再迁徙,使他们失去了地区的专属身份。但没有身份正是一种“身份”,不属于修饰词的地区,而回归到“作家”的正身。这种“身份”的消失,同时也是“身份”的多重性的获得,使他们拥有了双重(或多重)的视域、经验和记忆,也拥有了双重(或多重)的文化参照和选择,这些都赋予了他们新的观照视野,犹如生物学的“复眼”有了文化的意义。这种“身份”的消失和复得,恰正是跨出国门以后作家的创作优势,或应当自觉去追寻的优势。
在施叔青的创作中,狭义的“身份”消失另一面,是她对生命原乡的文化身份的坚守。在长及三十多年的创作中,施叔青不失时尚而又未曾媚俗,无论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还是后现代、后殖民,她的小说堪入教科书为这些经典浪潮作注解。但每部作品都活生生是施叔青式的,一种以来自原乡的文化体认去解读原乡人在异域的人生遭际和情感波澜。外来的文化以及那些万花筒一般转换的时尚思潮,都纳入在她坚守的民族文化逻辑之中,给予丰富、补充或另类的展示。这使她的作品越来越走向写实,即使再怎么后现代和后殖民,都蕴寄在写实的背景和基础之上。
离开了原乡的世界华文创作的文化坚守与文化融合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实它包含着文化发展的两种向度,一方面,已经成为所在国公民的华人,正努力融入于所在国社会,以自己的华族文化作为所在国多元文化的一个构成成分,参与所在国多元文化的共建。这种情况在已经有了两代、三代华裔传承的东南亚国家,尤其如新加坡那样确认了华文官方地位的国家,显得特别突出。这里所说的“华族文化”已经不能完全等同于华人原乡的中华文化,而是华人移民之后以中华文化为底蕴,不同程度地融摄了所在国文化而建构起来的华人族群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方式。它虽来自原乡却又有别于原乡,是中华文化在异域呈现的一种特殊形态。另一方面,融入所在国社会不是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是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坚守,来建构自己的族群记忆,形成族群的凝聚力,从而成为参与所在国多元文化建构的一种成分。融入与坚守,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融入以坚守为前提,而坚守是为了更有效的融入。它们各有侧重地存在于不同国情的华人社会和海外华人生存的不同阶段之中。当今世界华文创作,从东南亚到欧美,都不能不程度不同地面对这一问题。
然而对于施叔青来说,正如她淡漠了区域专属的作家“身份”,这一问题主要并不体现为对所在国社会和文化的融入。因此“文化坚守”在她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坚守”。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和当代以西方为代表的文化思潮的强大传播力,使她既要不落时潮之后地受之影响,在创作中表现出她反应敏锐的前卫性,但又不甘受时潮左右而完全沦落和丧失自己。她总是在坚守来自原乡的民族文化的底蕴上,融摄某些异质文化和时尚文化的因素,将前卫性融入于民族性之中。她身在世界各地行走居停,她是个“过客”;她的文化灵魂在原乡,她又是个“归人”。走近了局部地看,她写台湾,是台湾作家;写香港,是香港作家;写美国,是美华作家;但拉远了全面地看,她就是作家,以她所稔熟的华人(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和其他不同种族的人为对象,叙讲他们的生命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她所坚持的文化目的,略为夸张地说,就是人类文化——以中华文化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在海外的各种呈现形态,参与人类文化的建构。这也是所有世界华文作家,共同服膺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