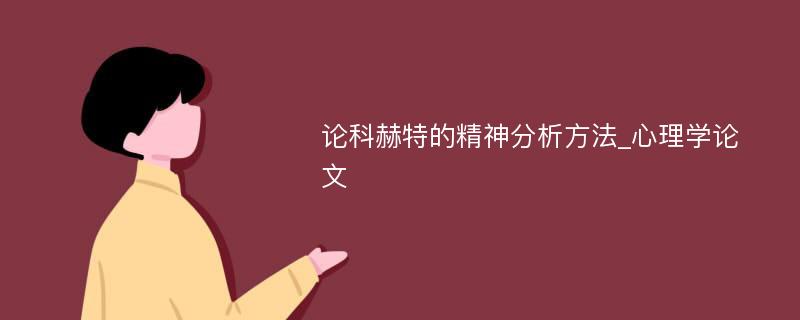
论科赫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精神分析论文,论科赫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6-0074-09
科赫特(Heinz Kohut,1913-1981)是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他从传统精神分析的营垒里杀将出来,先后发展出了狭义自身心理学理论和广义自身心理学理论。广义自身心理学理论是继驱力理论、自我心理学理论和对象关系理论之后的又一个精神分析范式。科赫特的精神分析思想的发展、变化与其所信奉的精神分析方法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详细阐述科赫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论,并深入剖析这一方法论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一、神入和内省确定精神分析的实质
科赫特指出:“自身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是科学的合法分支”。[1](p.275)
那么,作为一门科学,精神分析区别于其他科学门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精神分析的实质是什么呢?
科赫特是这样理解精神分析的实质的:“精神分析是研究复杂心理状态的心理学,它通过观察者持久地专注于人类的内心生活来收集人类内心生活的资料,以解释复杂的心理状态”。[2](p.302)
由此可见,科赫特是从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两个方面来界定精神分析的实质的。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复杂心理状态,它包括复杂的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这两个方面。要了解人类的主观经验,要体察他人的主观情绪状态和思想观念,只有运用神入(empathy)和内省(introspection)这样的主观方法,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因为“神入是一种特别适合于观察(知觉)复杂心理结构的认识模式”。[1](p.300)
科赫特认为,所谓神入就是“替代的内省(vicarious introspection)”,[3](pp.459-465)是“思考和感受另一个人内心生活的能力”,[4](p.82)其中包含认知的成份和情感的成份。
科赫特认为,经验科学所采用的观察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外部观察(extrospection)和替代的外部观察(vicarious extrospection);一是内省和替代的内省。外部观察和替代的外部观察适用于研究外部现实的科学,是物理学和生物学所采用的有效方法。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常常不能亲自去观察某些外部现实,那些亲自观察到这部分现实的人可以将他所观察到的外部现实报告给我们,我们因此得到关于外部现实的资料,这就是所谓替代的外部观察;而内省和神入则是研究内部现实的有效方法,是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所采用的方法。[5](p.565)[6](pp.527-528)神入的观察适用于心理学的领域,而非神入的观察适用于心理学以外的领域,“如果将非神入的观察模式用之于心理学领域,就会导致有关心理现实的机械的、无生命的观念”[7](P.79);反之,如果对复杂心理状态以外的领域进行所谓神入的观察也会产生有害的结果,就会导致错误的、泛灵论的、前理性的概念,总的来说,这是知觉和认知发展幼稚的表现。
由此可见,在科赫特看来,神入是心理学观察的基本成份,对精神分析学家而言,神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精神分析学家应当努力从被分析者的立场上去体察和理解被分析者的主观经验。要研究人类的复杂心理状态,只有运用神入和内省。要对复杂的心理形态进行解释,就必须先领悟复杂的心理形态,由神入和内省得来的有关人类复杂心理状态的资料是精神分析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科赫特在考察精神分析实质的时候,一方面强调研究复杂心理状态必然要以神入和内省作为精神分析收集资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强调神入和内省在确定精神分析实质过程中的作用,强调神入和内省界定了精神分析的研究领域。
科赫特指出,“精神分析的内容是世界的由观察者的神入和内省的态度所确定的那个方面”,[2](P.303)是用内省和神入可以感受到的那部分现实。这就意味着,精神分析的研究领域是由神入来确定的。[1](p.318)在科赫特看来,真正能说明精神分析实质的是神入和内省,神入和内省使得精神分析不同于其他研究人的科学,他指出:“在研究人类本质的科学当中,精神分析是唯一在其基本活动中将……神入同切近经验的和远离经验的理论说明……结合起来的科学。……换言之,精神分析是一门独特的科学,因为它一贯以内省和神入得来的资料为基础”。[2](pp.302-303)
科赫特认为,精神分析的实质在精神分析发轫之初就已存在。[2](p.303)也就是说,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以神入和内省的方法来收集有关人类复杂心理状态的资料的,弗洛伊德所发展的诸如自由联想、抵抗分析等精神分析方法,都是运用精神分析的根本方法——神入和内省的具体手段;各种各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论是心灵的地形学模型,还是心灵的结构模型,都不过是整理由神入和内省得来的资料的工具而已。由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所提供的各种手段,如自由联想和抵抗分析都不是不可替代的,都是可以改进的,都是用来为神入和内省的观察方法服务的“辅助性工具”。[3](p.464)[2](p.303)精神分析的内容一直是世界的由观察者的神入和内省的态度所确定的那个方面——人类的复杂心理状态。
自身心理学家所采用的神入与传统精神分析学家所采用的神入并无质的区别,而只有量的差异。科赫特既没有说过自身心理学家要比传统精神分析学家更为神入(empathic),也没有说过自身心理学家所采用的神入同传统精神分析学家所采用的神入有什么质的区别。科赫特只是强调,自身心理学家将神入作为精神分析的主要工具,同传统精神分析学家相比,自身心理学家能够更为“持久地沉浸于病人的总体心理状态”(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2](p.102)其神入更为系统、更为深思熟虑。在科赫特看来,持久地沉浸于病人的总体心理状态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精神分析方法的核心。自身心理学家的神入是持久的、系统的、全面的,它针对的是病人的总体心理状态,而不是病人心理状态的某些片断。在对病人的总体心理状态进行系统的、持久的神入的基础上,自身心理学家发展出切近经验的(experience-near)理论,而这切近经验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并强化自身心理学家的神入。自身心理学理论极大地拓展了神入的范围,使得精神分析扩展到原先不曾注意到的心理结构之上。[8](p.23)而传统精神分析学家对病人的神入是偶尔的、暂时的、片面的,其神入的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及自身心理学家。
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它运用神入和内省来研究复杂心理状态,那么,它是怎样保证其科学性的呢?
首先,科赫特认为神入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天赋,这就保证了精神分析有可能对复杂心理状态进行科学研究。他指出:“在精神分析中进行有效的科学研究是……可行的,因为(1)同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一样,通过神入理解他人的经验是人类的基本天赋;(2)精神分析能够克服妨碍进行神入的理解的障碍,就像其他(门类的)科学已经学会克服妨碍其掌握所使用的观察工具——感觉器官、包括凭借工具来扩展和改进感觉器官——的用法的障碍一样”。[2](p.144)
其次,作为经验科学家,精神分析师运用神入的方式与非科学的纯粹内省论者有所不同。
科赫特认为,在运用神入的方式上,精神分析师和非科学的纯粹内省论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受过有关神入的训练,不在于神入时是否投入,不在于神入时是否超然,更不在于收集资料时内省和神入的步骤有什么不同,而在于对所收集的经验资料的研究。所有已经超越收集原始资料这一初始阶段的科学,都必须采用与经验观察有一定距离的术语来对所研究的内容进行一般性陈述。精神分析也不例外,它以其特有的理论(心理玄学)对其所研究的内容进行一般性陈述。也就是说,对精神分析学家而言,用神入和内省的方法来收集有关人类内心生活的资料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他必须运用明晰的概念架构,必须运用与所收集的经验资料相关的明确的符号系统来整理这些资料。从而得出科学结论。与此相反,非科学的纯粹内省论者从所收集的资料中得出的思想,要么是描述性的、与所收集的资料太过接近,要么是走向另一极端,直接从观察资料跃升至最高的概括水平。而精神分析学家总是先建构一系列与直接的观察资料比较接近的中间(intermediate)理论,然后,在反思这些中间理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建构更为一般性的原理。总之,在精神分析中,神入的观察是为经验科学服务的工具,而在非科学的纯粹内省论中,神入并不是为经验科学服务的工具。[9](pp.87-88)
为了说明精神分析的概念和理论同人类主观经验的关联程度,科赫特对“切近经验的”概念和理论和“远离经验的(experience-distant)”概念和理论进行了区分。所谓切近经验的概念和理论,是指那些以得自于神入和内省的观察资料为基础的临床概念和理论——它们是关于经验的概念和理论;所谓远离经验的概念和理论,是指那些通过其他观察模式(如关注行为的观察模式)得来的概念和理论,或(也)是指那些有关心灵活动的心理玄学假设,这些心理玄学假设或是潜在于经验,或是传达经验,但并不是、也根本不可能直接以神入所能把握的经验资料为基础。[10](p.40)当然,切近经验和远离经验是相对的、比较而言的。科赫特提倡切近经验的概念和理论,认为即使是远离经验的概念和理论也应当以切近经验的概念和理论为基础。归根到底,所有的概念和理论,不管是切近经验的概念和理论,还是远离经验的概念和理论,都必须以神入和内省所观察到的主观经验为基础,因此,应当绝对尊重病人的主观经验,概念和理论如果与由神入和内省得来的经验资料不相符,就应该进行修正。
二、澄清有关神入的各种误解
在科赫特提出内省和神入是精神分析研究人类复杂心理状态的方法之后,各种批评纷至沓来,但大多数批评都是基于对“神入”这一概念的误解。对此,科赫特在各种不同场合作出了澄清。
第一,神入不等于直觉,神入与直觉没有必然联系[11](pp.302-303)[2](p.304)[1](p.312)[5](p.540)。所谓直觉,实际上就是一种快速反应、快速判断、快速再认或快速知觉。除了快速之外,直觉与非直觉的反应、与非直觉的判断没有任何区别。无论是在心理学的观察过程中,还是在非心理学的观察过程中,都可能出现直觉。神入既可以以直觉的方式进行,也可以以尝试错误的方式进行。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专家有时就能够迅速地把握他人的心理状态,似乎并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就可以发现这种以直觉的方式进行的神入过程其实也是有中间步骤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神入是以尝试错误的方式进行的,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更是如此。也就是说,神入不一定总是准确无误的,它也有可能出错,正如研究外部现实的科学(如生物学和物理学)所运用的外部观察一样。
科赫特特别强调神入和直觉的区别。他认为,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既有理论的影响,凭直觉得来的知识容易使人陷入既有理论的窠臼,歪曲神入的知觉。因此,为了使神入的观察不为既有的理论和思维模式所歪曲,必须保持神入的态度,尽可能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反对直觉。分析师应该学会怀疑脑海中闪现出来的似乎是确定无疑的解释。因此,科赫特说:“神入是科学的分析师最好的朋友,直觉有时也许是他最大的敌人”。[2](p.168)
第二,神入既不等于同情,也不等于爱。[2](p.304)[1](p.311)同物理学所运用的替代的外部观察一样,神入也是价值中立的过程,既可能出于善意,也可能出于恶意。[1](p.311)(p.316)神入既是感受他人善意的前提,也是感受他人恶意的前提;同样,要向他人有效地表示善意、或恶意,也必须以神入为前提。因此,批评科赫特强调神入就是主张以爱和同情来进行治疗,实在是出于对神入这一概念的误解。
第三,神入不等于设想自己若处于他人的境遇会有何感受。即使是对相似的遭遇,分析师和病人的感受也未必相同。如果分析师以为对相似的遭遇病人会和自己产生同样的感受,就会导致有害的结果。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H先生是一个抑郁的人,25岁,有严重的自身障碍,其母不幸横遭车祸时,他正要开始为达成许多目标而努力。在车祸之后的一次治疗中,病人平静地描述了其母遭遇车祸的细节。分析师的父母也是因车祸而丧生的,分析师以为自己的体验会和病人一样。因此,在和病人谈到这起事故时,分析师痛苦地回忆起自己在失去亲人时的痛苦,不禁说道:“这真是个悲剧啊!”。马上,H先生陷入了沉默,接着,突然开始谴责自己怎么没有感受到应该感受到的损失。病人不停地把自己同分析师作消极的比较,使自尊低下的情形更趋恶化。[8](p.20)因此,科赫特强调,分析师应该站在病人的立场去体察病人的主观经验,而不应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病人。
第四,要通过神入来感受和理解他人的主观体验,并不等于必须采取与他人同样的态度、产生同样的情感。就分析师而言,对病人保持神入的态度,并不是要病人喜则喜,病人悲则悲。如果是这样,分析师就会丧失应有的客观性,其帮助病人的能力就会遭到削弱;而通过神入来理解病人的悲伤,则不会使分析师丧失客观性,也不会削弱其帮助病人的能力。在前面所援引的例子中,分析师如果在H先生描述其母葬礼的场景时对病人的情绪发生自居作用,丧失客观性,并对病人表示同情,那就是神入的错误。
第五,神入只能用于收集资料,而不能用于理论建构。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分析师运用神入来理解病人当下的心理状态;在运用神入收集到病人内心生活的资料之后,就要整理这些资料,并向病人作动力学解释和发生学解释。在构思表述的时候,并不需要运用神入。[1](p.312)
因此,科赫特强调,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既要有神入的能力,又要有超越神入的能力,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他们不是神入的,那么他们就不能观察、收集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料;如果不能超越神入,他们就不能建立假设和理论,因而,最终也不能得到解释”。[11](p.303)
需要注意的是,收集心理资料需要神入、而建构理论必须超越神入,并不意味着理论和实践是对立的。科赫特指出:“如果不包括不断提高的、超越神入的理解(即领悟),连临床工作也只会导致暂时的效果。如果不能不断地同只有通过神入才能观察得到的材料保持接触,理论工作就会很快变得空洞而少独创性,就会有沉醉于心理机制和心理结构的细枝末节的倾向,就会失去同精神分析的全部最终都必须以此为基础的人类经验的深度和广度的接触”。[11](pp.303-304)因此,科赫特强调,分析师训练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分析师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或舍弃神入的态度。
科赫特有关神入的论述也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他主要把神入当作价值中立的观察工具,但有时也赋予神入积极的含义。例如,他曾说过,神入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强有力的因素,能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块人性化的空间。[12]另外,科赫特还曾提出过所谓“神入价值观”,以同传统的“认识价值观”相比较。[13]
科赫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但他强调,自己关于神入的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它们是在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层面上说的。[1](pp.312-317)科赫特认为,科学意义上的神入和日常语言中所说的神入含义有所不同,应该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其科学意义而言,神入是价值中立的科学观察的工具,是精神分析研究领域的界定者,是价值中立的“过程”或“操作”。应该严格区分神入和神入所产生的结果,作为一种过程或操作,神入既可能产生正确的结果,也可能产生错误的结果。这与心理学以外的领域所运用的替代的外部观察是一样的。
在日常语言中,在诸如“他(她)是神入的”或“某人善解人意、是神入的”这样的话语中,“神入”或“神入的”等词语通常含有神入必然会导致正确的结果这样的含义.因此,在日常语言中,神入一词容易使人产生诸如“友善”、“情绪热烈”之类的联想。科赫特认为,根据远离经验的逻辑,应该抛弃神入一词的通俗意义;但从切近经验的角度来看,神入一词的通俗意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科学意义上的神入和日常语言中所说的神入之所以容易混淆,有其心理上的原因。在正常情况下,婴儿初到人世,就同照料他的成人、特别是母亲形成神入的关系,母亲通过神入理解孩子的需要,并及时给子满足,这就是弱小的婴儿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因此,神入这个词汇容易使人下意识地联想起早期母子之间的那种温暖的关系。当然,人们也知道父母的神入不可能十全十美,也知道有许多孩子由于父母神入的缺陷而遭受严重的创伤,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倾向于美化早期的母子关系,这种美化多少有些防御的性质。人们最感恐惧的是周围的人不能与自己保持神入的协调,从而使自己在心理上无法生存下去,因此人们就会防御性地强调母子关系的积极方面,否认其消极方面,运用否认这一防御机制来逃避恐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普遍地将一般意义上的神入等同于完美的神入,才会普遍地将既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是歪曲的神入当作是完美无暇的。
虽然将神入混同于同情是错误的,但却有其心理上的原团。神入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过程,既可能出于友好,也可能出于恶意,但就心理感受而言,错误的神入、恶意的神入总要比根本没有神入好一些。有时,面对在神入的基础上表示敌意的敌人,也要比面对没有任何神入的敌人强一些。
因此,说神入——甚至是错误的、歪曲的神入——有益于身心健康、具有广义的治疗作用并不为过。[1](p.316)对某些人来说,仅仅是身处受到他人长时间“神入的注意”的环境也是有益的。大多数心理治疗情境实际上就是为病人提供了这样一种环境。这种情形也适用于有人出于敌意而对他人进行神入的环境[1](p.317)
科赫特认为,在精神分析当中,神入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神入本身就是精神分析治疗氛围的一部分,在神入所营造出来的治疗氛围中,病人和分析师比较容易形成支持性关系,病人也更有可能展现其内在体验,更有可能展现其早年没有得到满足的发展需要,更有可能形成自身对象移情。科赫特认为,除了行为疗法之外,在大多数心理治疗形式当中,神入都起到了营造治疗氛围的作用,这就是神入的非特异性作用;另一方面,神入是价值中立的收集资料的操作或过程,是为分析师的认知服务的。这就是神入的特异性作用。只要分析师能够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就能够不断提高神入水平,不断提高觉察病人内部心理状态的准确性。精神分析学家可以根据神入得来的资料建构远离经验的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与专业上的同行进行交流,为病人进行发生学解释和动力学解释。[1](p.317)
因此,科赫特说神入具有广义的治疗作用是就神入的非特异性作用而言的。所谓神入的广义治疗作用,实际上就是指神入能为精神分析治疗营造一个良好的治疗氛围。但真正能起到治疗作用的是分析师的理解和发生学解释、动力学解释。当然,分析师的理解和发生学解释、动力学解释也是以神入为前提的。因此,认为强调神入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强调用“善意”、“同情”来进行治疗是错误的。
三、科赫特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界定的意义
科赫特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界定不同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只有承认移情和抵抗机制才是精神分析的方法。[14](p.16)对此,科赫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一门科学,特别是像精神分析这样的基础科学,是不能用它所使用的工具来界定的。而工具有两类:一类是方法意义上的工具,就是研究当中所使用的工具;一类是概念性工具,就是具体的概念和理论。因此,精神分析既不能用它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来界定,也不能用它所使用的概念和理论来界定。科赫特特别强调,不能根据什么具体的理论来确定精神分析的实质,不能说运用了某种理论就是精神分析,反之就不是精神分析。科赫特认为,像精神分析这样的基础科学应该以它的总体方法来界定,这种总体方法决定现实的哪些方面是这门科学的研究领域。[2](p.305)
科赫特认为,神入就是这样一种界定精神分析研究领域的总体方法,而不是普通的研究工具。科赫特是这样表述他的观点的:“神入不是在病人采用躺的姿势、运用自由联想、运用结构模型以及运用驱力和防御概念都是工具那种意义上的工具。的确,神入实质上界定了我们的观察领域。神入并不只是一种我们用以进入人类内心生活的有用方法——如果我们没有通过替代的内省——我对神入的定义(参科赫特,1959年,第459-465页)——认识人类内心生活、认识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所思、所感的能力,人类内心生活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复杂心理状态的心理学这一概念本身也因此是不可思议的。”[2](p.306)
我认为,科赫特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界定、以及对神入和内省的方法论的强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科赫特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界定,为精神分析理论不断打破教条、不断得到发展开辟了道路。科赫特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界定,使得精神分析学家能够在理论同由神入和内省得来的临床资料不相符合的时候,敢于怀疑既有的理论,另创新的理论。因为在科赫特看来,理论不过是用来整理资料的概念性工具而已,[2](p.306)当工具不合适的时候,自然可以改进。与此相反,如果以采用某种具体理论作为精神分析的实质,就会阻碍精神分析学家为使理论同神入得来的新资料保持一致而改造理论,就会导致精神分析理论的教条化,就会阻碍精神分析的发展,就会导致精神分折不能适应人类精神状况的发展变化。而科赫特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界定,为精神分析学家根据新的资料改造理论扫清了障碍。[2](pp.306-30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见出,科赫特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界定为其提出迥异于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自身心理学理论开辟了道路。既然理论只不过是用来整理资料的概念性工具,那么,精神分析就不应该受既有理论的束缚,而应该以神入和内省得来的资料为基础,一旦理论同神入和内省得来的有关复杂心理状态的资料不相符合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修正。自身心理学的出现正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
很长一段时期,科赫特是传统精神分析的忠实信徒,有“精神分析先生”的雅誉。但在临床实践中,他发现有些病人自尊特别脆弱,对失败、不满和怠慢特别敏感,但根据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分析这些病人的心理冲突并不能缓解他们的痛苦,也不能如人所愿终止他们的不良行为;但在分析治疗过程中,这些病人出现了传统精神分析未曾发现的移情现象,当病人感到分析师对自己的内心体验有所理解的时候,其症状就得到明显的缓解,[15](p.360)科赫特后来称这种移情现象为“自恋的移情(narcissistic transference)”或“自身对象移情(selfobject transference)”。科赫特就是以此为起点,在修正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精神分析的狭义自身心理学理论的。科赫特后来之所以进一步从狭义自身心理学走向广义自身心理学,也是由于发现狭义自身心理学不足以解释由神入和内省得来的经验资料。由此可见,科赫特所信奉的精神分析方法论是其能够突破传统精神分析教条的束缚、发展出自身心理学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赫特一生都坚持“神入——内省的”观察立场,认为这对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对自身心理学理论是至关重要的。早在1959年发表的《内省、神入和精神分析》一文中,科赫特就提出“神入——内省的”观察立场对精神分析是至关重要的。自此以后,虽然科赫特关于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观点有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神入和内省是价值中立的观察工具、是研究人类复杂心理状态所必需的唯一方法、神入和内省确定精神分析的研究领域这一思想从未有过丝毫动摇。[9](p.85)[11](p.303-304)[2](p.309)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科赫特依然坚持这一思想。《神入和心理健康的半圆》是科赫特在去世前不久所撰写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用了一半的篇幅重申自己在《内省、神入和精神分析》中所提出的观点,并指出《内省、神入和精神分析》为其一生在精神分析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论神入》是科赫特在去世前几天在自身心理学第十五届年会上所发表的演讲。在这一演讲中,科赫特对其在《内省、神入和精神分析》一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进一步作了解释。从这一侧面,也可以看出科赫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论同其所发展的自身心理学理论之间的联系。
由于认为精神分析研究必须以神入和内省得来的有关复杂心理状态的资料为基础,科赫特对自己所创立的自身心理学理论抱有开放的态度,他欢迎后来者在新的由神入和内省得来的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对他的理论提出质疑、并发展自己的理论。这种开放的态度同弗洛伊德不容他人怀疑的近乎偏执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科赫特和弗洛伊德对自己理论的不同态度,一方面是各自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是各自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理解使然,当然也与各自的认识论、方法论立场有关。
基于上述分析,就不难理解科赫特为什么会认为其有关神入的认识论陈述和方法论陈述是其对精神分析的最为重要的、最为核心的贡献。[16](p.663-684)[12](pp.685-724)
第二,科赫特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界定、对神入和内省方法的强调为自身心理学在精神分析内部赢得合法地位奠定了基础,为证明科赫特本人所创立的自身心理学理论仍然属于精神分析传统提供了充分依据。自身心理学的研究主题同传统精神分析有了很大的不同。传统精神分析主要研究驱力、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冲突、阉割焦虑、结构性神经症;而自身心理学主要研究自身的发展状况和自身障碍。自身心理学的心理病原学解释、心理病理学解释都与传统精神分析有了很大的不同,所发展的理论、所采用的术语也与传统精神分析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么,自身心理学是否仍然是一种精神分析理论呢?如果根据弗洛伊德的标准——只有承认移情和抵抗机制的才是精神分析的方法,自身心理学就不属于精神分析传统;如果根据科赫特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界定,自身心理学就属于精神分析传统。 Joseph Reppen对此作了精当的说明:“如果同意科赫特将精神分析界定为一门其领域仅是由神入的认知来界定的深度心理学,那么,自身心理学就处在精神分析的主流之中。相反,如果认为精神分析是一门关于驱力及与此相对的限制力量和驯服力量的冲突心理学,那么,自身心理学就不是精神分析的一个新增(部分)。其观点就构成一个新的心理学学派”。[17](p.206)
第三,科赫特对精神分析实质的界定、对神入和内省方法的强调,可以保证精神分析作为一门纯粹心理学的特性,可以防止和反对精神分析的生物学化倾向和社会学化倾向。精神分析的研究领域就是用内省和神入可以感受到的那部分现实,也就是说,作为一门研究复杂心理状态的科学,精神分析的研究领域是由神入来确定的。这一断言表明,研究人类复杂心理状态和内心生活的科学(也就是精神分析)是心理学,而不是化学,也不是物理学和生物学。[1](p.318)科赫特声称,自己之所以要研究精神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之所以要明确精神分析的实质,初衷之一就是要防止和反对精神分析的生物学化倾向和社会学化倾向。
精神分析的生物学化倾向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中就有所表现。在从事精神病学研究之前,弗洛伊德主要从事神经生理学研究和神经病学研究。在追随布洛伊尔研究神经症之后,弗洛伊德之所以能够逐渐发展出精神分析理论,主要是由于他采用了神入和内省的方法。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恋母情结理论与其自我分析的关系尤为密切。但弗洛伊德没能彻底贯彻神入和内省的方法。他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和动物既具有差别性又具有连续性,认为生物本能对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生物本能——性本能和攻击本能——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与这种本能观相对应,弗洛伊德提出了“驱力”这一概念,因此,弗洛伊德所谓的驱力具有明显的生物学特征。这样,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伊底、自我和超我这一三分人格结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生物学的架构,具有内在矛盾。弗洛伊德认为,伊底当中的本能驱力遵循快乐原则,不断地要求满足,而自我和超我则起到驯服驱力和升华驱力的作用。问题是,心理性的自我和超我如何驯服和升华生物性的驱力呢?如果驱力是一种生物禀赋的话,那么控制这种生物禀赋的应该是脑,而不应该是心灵。
弗洛伊德的这种生物学化倾向虽然受到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批评,但却进一步为一些理论家所发展、所极端化。如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弗兰兹·亚历山大将精神分析运用于生物学,运用“驱力的向量”这一主要概念来解释各种医学症状。
精神分析的社会学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弗兰兹·亚历山大运用精神分析于社会心理学之中。他主要用“口腔驱力所激发的依赖倾向”这一概念来解释人类的大部分行为。科赫特认为,亚历山大的做法模糊了精神分析和社会心理学的界线。[5](pp.547-548n)精神分析的社会学化倾向还表现在哈特曼通过引进“适应”这一概念来扩展精神分析。虽然科赫特承认,哈特曼为他研究健康的心理机能开辟了道路,但他认为,将适应这一概念引进精神分析,导致精神分析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之上,而不再关注人类的复杂心理状态。
科赫特认为,精神分析的生物学化倾向和社会学化倾向对精神分析具有消极影响。将生物学意义上的“驱力”概念和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依赖”和“适应”概念引进精神分析,导致精神分析的实质发生决定性的改变,导致分析师改变内省和神入的基本态度,导致分析师不再全身心地关注病人的主观经验,从而导致分析师在进行研究和分析治疗工作的时候知觉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歪曲。对精神分析而言,这是最为严重的问题。同这一问题对精神分析的威胁相比,诸如为精神病学所吞并这样的外来威胁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这些概念之所以会歪曲分析师在研究、治疗工作中的知觉,主要还是由于这些概念本身就蕴含着某种人性观和生命观,引进这些概念的精神分析理论本身就蕴含着某种价值观。
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把人当作是充斥着原始的本能冲动、有待于驯服的动物,认为个体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克服和控制这些本能冲动、臣服于道德压力的过程。这种观念使得分析师在进行研究和分析治疗的时候孤立地关注病人的驱力,孤立地关注由驱力引起的潜意识冲突,而忽视病人的总体心理状态。这一理论所蕴含的价值观就是所谓“认识价值观”。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症状是由本能冲突引起的,本能冲突导致自我产生焦虑,而焦虑则是一种信号,它动员起自我之中业已发展起来的防御机制来防止本能的泛滥,而防御机制的固化和极端化则形成神经症症状。弗洛伊德认为,只要使病人认识到潜意识中的本能冲突,使本能冲突大白于意识,就能够消除病人的神经症症状。在弗洛伊德看来,潜意识中的本能冲突仿佛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有待于分析师引导病人去认识的东西。这一治疗观就是精神分析理论中所蕴含的认识价值观的表现。[1](p.321)
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某些对象关系理论认为,从幼稚向成熟的发展就是从自恋向对象爱的发展,就是从依赖向独立的发展,从自恋到对象爱是唯一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观体现了西方个人主义的独立价值观。[1](p.323)如马勒认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正常的自闭、正常的共生以及分离与个体化这三个阶段。正常的自闭阶段实际上是一个无对象的发展阶段,个体在这个阶段处于原始的自恋状态;共生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与母亲的表征形成一种幻觉式的全能的融合;分离与个体化就是个体从母亲处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性。[18](pp.108-118)
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所蕴含的“认识价值观”和“独立价值观”,歪曲了分析师的知觉,导致分析师在心理学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知觉、采取有选择的行动。这些价值观使得精神分析不太像一门科学,而更像一个道德体系。与此同时,随着应用的日益广泛,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精神分析变得不太像一种以动力学解释和发生学解释为基础的科学步骤,而更像是一种有预先确立的外在目标的教育步骤。这种目标同样是含而不露的,分析师竭力引导病人达成这些目标,病人也努力达成这些目标。[5](p.549)此外,科赫特认为,这两种价值观妨碍分析师认识到自身的核心地位,妨碍分析师认识到自身在人类心理结构中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涉及现代人以及现代特别流行的心理状态时更是如此。[5](pp.550-551)
第四,对个体早期的心理发展,科赫特只描述其一般状况,而不关注其具体内容。我认为,这也与科赫特把内省和神入作为精神分析研究的根本方法有关。
神入是精神分析观察的主要手段,而神入的可靠性取决于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相似程度。两者越是相似,神入的程度就越高,可靠性也越高;反之,神入的程度就越低;可靠性也越低。因此,如果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那么神入的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人对人的神入程度比较高,而人对动物的神入程度就比较低,对植物、无生命之物就根本没有什么神入可言。[9](p.86)
作为成年人,分析师与婴幼儿有着很大的差异,早期发展阶段的心理内容是分析师所无法把握的,如果试图对早期发展阶段的心理内容进行推测,就容易犯成人化的错误,就容易用发展后期的心理状态来代替发展早期的心理状态。[11](p.37)
因此,和弗洛伊德一样,科赫特主要根据成年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移情表现(在弗洛伊德是俄狄浦斯移情,在科赫特是自身对象移情)来对相应的童年期经验进行神入的重构。[11](p.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