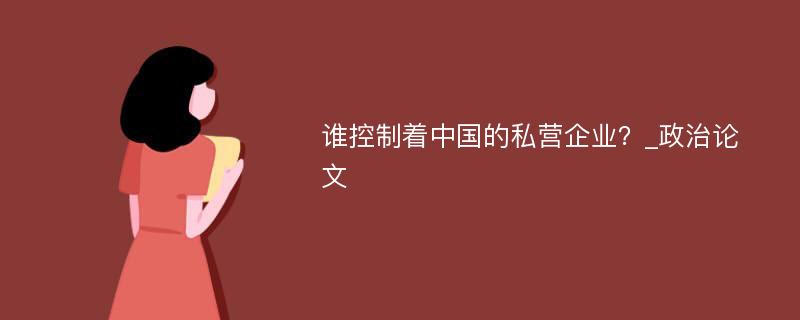
谁在掌控中国民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企论文,谁在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角色的矛盾与重复
记:您曾经谈到从去年底以来的一系列“民营企业家风波”凸显了一种“政治危机”。这种提法可能让人不太容易理解,甚至容易导致误解,我想请您具体谈谈“政治危机”的涵义。
仲:这一提法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领域出现了危机。它主要是指部分民企过去所采取的依赖政治权力及与政界的关系实现超高速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因为中国目前及未来的政治领域将越来越规范和透明,政府行为会越来越公开和公正,我称其为“政治回归”。在这种情况下,部分过去走“捷径”的民企再难有大的生存空间。一句话,就是部分民企因为政府行为的规范而出现的生存及发展危机。
记:按照您的这种看法,政府应该是民企“出事”的首要原因?
仲:可以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我的板子都是打在政府屁股上。因为民企是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而政府对制度环境的好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民企来说,对不合理的制度作出的反应也只能是不合理的。
记:不过,后一种“不合理”是由政府说了算。由此,我们似乎看到了政府的角色和身份出现了矛盾和重复,即一方面,部分民企超高速发展是由于政府及权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对这部分民企合法性的认定又是由政府作出的。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明显出现了自我推翻的情形。
仲:可以这么说。我国过去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但政治领域并未出现相应的改革。这种不同步导致了经济领域同政治领域的某些不适配。政府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介入到经济领域的现象、政府配置资源的现象就不可避免,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突出,这在房地产和国有企业领域最明显,因为这两块是最后的两块“公共肥肉”。而这正好使部分善于察言观色或投机的民企得到了发展“良机”,但同时也为今天的遭遇埋下了伏笔和祸根。
记: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政府行为对经济领域的控制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一种特色,进而衍生出其它更多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及社会现象?因为由权力导致的特别的经济及社会现象相当多,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下半期的“官倒”,只要能打通关节、靠近权力、获得批条就可以进行。再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股票市场,企业的整个股票发行及上市过程要牵涉到十多个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部门,在企业还未上市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内幕交易”,而因此出事的官员也不在少数。
仲:只要是权力较为集中的地方,就容易出现寻租活动。特别是那些掌管着稀缺资源甚至是垄断着资源的政府部门更是如此,其租金水平要高过其它领域。要减少寻租活动及租金水平,政府行为的公开及民主程度必须提高。否则,权力介入经济领域的现象还将以新的形式出现。
民企的政治经济学:外在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
记:我们再回到民企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既然政府不管民企的想法如何而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制定了制度,那么,民企要做的就只能是顺从和适应。这是一种现实的态度,是一种最务实的经济计算,同时也是民营企业的一种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从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私营企业“戴红帽”的现象中就得到了反映,而现在“出事”的民企是另一种反映。
仲:我们可以重新探讨一下“政治危机”的涵义。当一套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时候,会在经济领域产生许多不合理的做法,而一旦政治制度开始规范有序的时候,过去的模式就会出现存在危机。虽然有些做法和模式不合理,但从民企和经济学的角度看,它的成本是最低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不管是“戴红帽”还是拉关系都是如此,都是民企出于使自己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驱动的。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部分民企只是获得了一时的利益,最终却是前功尽弃。
记:民营企业的这种政治经济学现在还在延续,最新的情况是各地出现了“商而优则仕”的现象,同时也再次出现了“官员下海”的现象,即许多地方的官员纷纷兼职民营企业的管理层。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仲:我对这种现象表示担忧,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政企不分。以前是计划经济下的政企不分,主要是由产权不明引起的,而现在则是产权清楚了,但政府权力及私营资本出现了合谋,这是一种更可怕的政企不分。这种情形所带来的后果会相当糟糕。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民企发展壮大后,在政治领域确实需要有自己的代言人,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所采取的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我一直主张民企要远离权力,否则现在的快活可能会导致以后的苦果。而且,即使民营企业家可以进入到政府里面去,你又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
记:不过,民企的行为属于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您说它们所采取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不可取,但在目前政府主导一切的情况下,民企又能有什么其它的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希望政府行为能够规范起来,能有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话题。这一话题炒得如此热,让人觉得整个舆论环境及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都被与富人有关的问题所牵引,相反那些弱者的处境则无人问津。
仲: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如果修改宪法明确保护私人财产的话,受益者会包括所有拥有私有财产的人,而不仅仅是富人。另外,如果真正修宪的话,还可以防止目前仍不断发生的大量的侵犯私人财产的现象出现。现在的问题是,一旦修改宪法成功,过去那些靠侵吞国有资产而发家的私人财产就会成为合法财产而受到保护,这一道理与“洗钱”差不多。
记:不过,关于保护私有财产话题的讨论好像是由富人引发的,而不是由要保护穷人的财产引发的,尽管穷人也有自己的财产。另外,即使修宪成功,受益最大的也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对穷人来说,他那点财产保不保护都无所谓。
仲:不过,财产再少,在受到别人侵犯或掠夺时,有法律保护总比没有法律保护好。有了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一方面可以防止“公权”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部分人通过非法占有甚至剥夺他人的私有财产而发迹,就像周正毅剥夺拆迁户的财产一样。
看懂了民企及房地产就看懂了中国社会
记:您刚才谈到房地产及国有企业是两块最后的“公共肥肉”。其实,也正是这两块与部分民企的高速发展紧密相关。据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前100位富豪中,有40%都拥有房地产业务。
仲:中国民企对房地产的依赖度太大,民企太多地集中于房地产。这又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特色。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属于房地产或涉及房地产业的企业只占总数的8%左右,准确数字是多少,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反正不高。
这种现象的起因与前面所谈到的种种现象是一样的,即政府介入到了经济活动中。我国每年出售地皮所获得的财政收入为6000亿元左右,但每年从房地产业流走的却有几万亿,这部分由权力与资本瓜分了。
记:房地产业每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3%左右,按GDP一年增长10万亿计算,房地产业所占部分就为3万亿。不知民企在其中占多大份额,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分国民收入流进了部分官员及民企的腰包。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前不久央行作出收紧及规范对房地产的信贷业务管理时,部分与房地产业务有关的民企对该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
仲: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吴敬琏组织了几个学者用模型计算与国民收入的流向相关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由权力部门拿走的租金每年占GDP的15%至20%,而民营房地产商拿走的部分估计占GDP的10%左右。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还是由于政府配置资源所致。土地目前是最大的一块国有资产,许多人都在想将其作为“摇钱树”,从中捞一把。过去的土地市场化率只有10%,出售方式改革后,现在的市场化率也就30%左右,还有70%的部分是由政府直接处理的。
记:这表明,在房地产领域,政府依然起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正是这种做法导致了诸多不公平,无论是起点还是过程都是如此,而这两种不公平又直接导致了结果上的不公平。
仲:所以,我认为政府权力应该尽快退出市场,将资源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杜绝黑箱操作。
记:可不可以这样说,能看懂中国的民企,看懂中国的房地产,看懂民企与房地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懂中国这个社会。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许多现象都可以与它们扯上关系,比如,人们一直很关注的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及仇富心态问题。
仲:正是由于部分民企与政府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导致了社会各个成员及阶层在占有资源的机会上出现了差别,资源向富人阶层倾斜。这种趋势的后果就只能是贫富分化。
在这种情况下富起来的人,一般人对他们是不太容易产生认同感的。而且,这部分人对弱势群体及社会的贡献度也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及占有的资源不成比例。那么,社会因此而产生仇富心理也就很正常了。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民企都是这样,也有许多民企是靠自己的勤劳致富的,而且富起来后,对社会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
民企一定要走正道
记:我们从不同角度及层次讨论了民企与政府间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两面,一个是政府,一个是民企。对政府来说,将来要做的是如何退出市场;对民企来说,就是如何选择自己的成长道路的问题。您觉得民企完全可以像西方企业一样成长吗?
仲:从微观层面来看,有些民企在组织、经营及管理方面已经同西方企业相当接近了。不仅如此,我们的民企还有自己的创新,比如,拉关系、走后门。
记:但这两种方式都难以持久。您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是否应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必修课,比如,刚“出事”的孙大午就主张“传统的儒家思想,现代的法制思想及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相结合”。
仲:总的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素质还不够高,他们需要不断地得到教育,就连我们的政府也需要我们这些人不断地呼吁。
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定要走正道,否则,过去的一时所得将来也要吐出来。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中国的古典名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劝人向善,也就是佛家所讲的轮回和报应。
记:但愿我们的民企能好自为之,一路走好。
仲:未来的环境也使得民企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并作出调整。
既是经济观察家也是民营企业家
仲大军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新华通讯社,1986年到新华社-英国汤姆森基金会国际新闻培训中心学习,1989年到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进修,1993年被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聘为特邀研究员,1995年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任编委、高级记者,并兼任数家研究机构特约研究员,2000年创办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现任中心主任,研究员。
他是国内目前知名的经济观察家、社会评论家、批评家、专栏作家、政府和企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