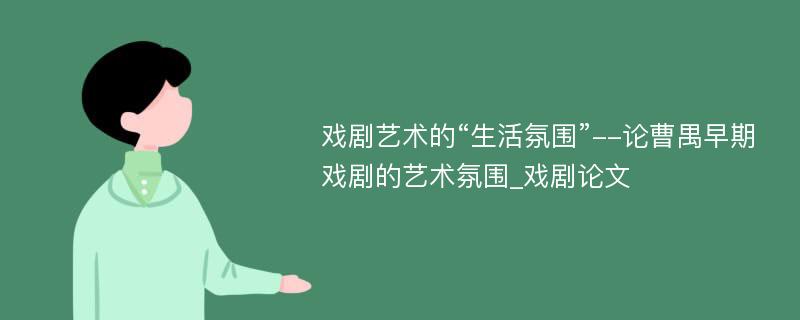
戏剧艺术的“生命气息”——论曹禺早期剧作的艺术氛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剧作论文,戏剧论文,氛围论文,气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戏剧氛围,是戏剧艺术的审美形式范畴,它包含着戏剧文学,舞台环境,戏剧情景与观众审美心理等多重戏剧因素。曹禺戏剧的魔力,是与曹禺戏剧艺术的独特氛围分不开的,对曹禺戏剧氛围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剧作家的审美追求,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透视剧作家对现代戏剧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交融的探索。同时,也可启示我们从戏剧舞台环境、戏剧表演戏剧交流过程中观众的审美心理等方面入手,把曹禺戏剧研究引向深入。
田本相先生在《曹禺传》中说:“我以为,自他写《雷雨》以来,他的《日出》《原野》都一直追求戏剧的神韵,味道,或者说是韵味,境界。”“在这方面不但体现着他的戏剧美的独特追求,而且积淀着传统艺术的审美文化心理。这些凝聚在他的审美个性之中,是很牢很牢的。《蜕变》是例外,《北京人》又回到他原来的审美个性追求的轨道上”①。我认为,曹禺的这种对神韵的诗意追求正是他精心营造的一种独特戏剧氛围的一个显著表现。曹禺戏剧的神韵就是一种近乎于诗歌艺术中追求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心荡神怡”的审美境界。
曹禺曾深有体会地谈到他为戏剧氛围所感染的体会。他在创作《日出》前,为契诃夫的平淡日常的生活中开掘出浓郁诗情所深深吸引,他说:“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柴霍甫(即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读毕了《三姊妹》,我合上眼,眼前展开那一幅秋天的忧郁,玛夏,哀林娜,阿尔加娜三个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里浮起湿润的忧愁,静静地听着窗外远远奏着欢乐的进行曲,那充满了欢欣的生命的愉快的军乐渐远渐微,也消失在空虚里,静默中。……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开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再想拜一个伟大的教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②曹禺正是为契诃夫的那种特有的戏剧氛围所感染,所陶醉,激发了他对一种新的艺术境界的向往,开始了《日出》创造的新尝试。
曹禺对戏剧氛围的追求是一以贯之,潜心神往的,“一个戏要和一个戏不一样。人物,背景,氛围都不能重复过去的东西。”③他把氛围与人物、背景看得同样重要。早在50年代就有人评论说:“奥尼尔和曹禺都受希腊悲剧的影响,都有一种对庄严氛围的爱好”,“《原野》好象是相信命运,又好象是喜欢一种氛围”④。曹禺的每一部戏剧都有他对不同艺术氛围的独特追求。然而,一个形成了独特艺术个性与美学风格的戏剧家,他的作品中是蕴含着某些共同审美倾向的。本文要探讨的便是曹禺早期戏剧(主要包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艺术氛围的审美追求中所呈现的共性特征。其中包括探讨戏剧氛围的组合形态,戏剧氛围的构造手段以及审美效应。
2
曹禺的戏剧具有浓烈诗意的抒情氛围。诗意的追求给曹禺的戏剧注入了无限的活力与蓬勃的生机。无论是具有鲜明现实主义特征的《日出》,还是具有明显的表现主义倾向的《原野》,诗意的抒情性同戏剧性的融合是它们共有的特征。曹禺凭着他对现实生活的诗意突入,对戏剧艺术的诗化处理,把“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戏剧与浪漫主义戏剧以及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戏剧作了有机的融汇,创造了一个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开放的现实主义戏剧审美体系(田本相先生称之为诗化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似乎也可借鉴胡风的一个现实主义美学概念称它为“体验的现实主义”)。他对戏剧的诗意追求,使他在民族的戏剧艺术传统与西方现代戏剧艺术的双向交流中,开通了渠道,发现了交合点。这一点田本相先生有精到的发现,并有以下精彩的议论:曹禺“他循着易卜生所拓开的近代戏剧潮流,寻找着使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东西,从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再回到希腊悲剧、莎士比亚,他看到,或者说领悟到世界戏剧发展的本质趋势。即如美国戏剧理论家约翰·加期纳年概括的:‘现代剧作家试图使现实与诗这两种可能的境界,都能够达到美的极致,或都力图使这两者能够浑然一致或互相选替。’易卜生的剧作追求‘写出诗意来’,契诃夫追求戏剧的‘情调’,他的剧作的‘内在戏剧性’,实际上是把诗意的抒情性与戏剧性融合起来。奥尼尔也强调戏剧的诗,他说:‘诗的想象力能照亮生活中最污秽的死胡同’。诗和现实的契合,是一种心灵的启示,是一种审美意识的点燃,或者说是一种审美思维的开拓。在这里,世界的潮流,时代的呼唤,生活的声音,在外来影响的启迪和深刻的领悟中,焕发起他革新的创造力,形成他的创新的戏剧观念。”⑤我们要进一步追寻的是曹禺如何在剧作中展现他诗意的追求,营构他戏剧的诗的抒情氛围的。
首先,他以一颗无限孤独悲凉的心情表现对人类的深深悲悯,他将这种上帝般的慈爱情怀与诗人的赤子之心渗透于戏剧的情景与戏剧形象之中,用一种贯注于戏剧过程之中的无比真切的潜在的情感力量,沟通自我、演员、观众的心灵,获取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效应。
曹禺每当谈及自己的创作,总是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心灵激动,似乎又回到了他戏剧的情境中。他的《雷雨·序》是一篇极为重要的自述,它不仅是我们透视《雷雨》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艺术感受与理性分析曹禺早期剧作的“总纲”。他谈及他创作《雷雨》时的心情时说: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
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在《雷雨》里,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的作祟,一种情感的发酵,是他对宇宙作的一种隐秘的理解。剧作家要呈现的是天地间的残忍与自然的冷酷,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宇宙残酷的井里作着越陷越深的可怜的挣扎。他把对宇宙人类生存的悲剧体验,诗化为一幕幕振奋人心的悲剧,透露的是他对人类的无限的悲凉感伤与无比的温爱怜惜的心情。他在1935年就表白他写《雷雨》是在写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要写的决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剧。他有意把故事的背景推到非常辽远的时候,叫观众如同听神话似的,并且有意的用了序幕和尾声,企望用巴赫的音乐,把观众带到远一点的过去境内,而又可以在尾声内回到一个更古老,更幽静的境界⑥。他早期的其他三部剧作,即《日出》、《原野》、《北京人》又何尝不是侵透了作者这种无限悲凉的心绪,又何尝不是他构制的程度不同的一个个富有诗意象征的人类悲剧的故事。
《日出》是一部最贴近现实的作品,一种更内在、更真挚动人的诗意的潜流在他剧作的主题、结构、背景与人物身上流淌着。他从光怪陆离的社会,看到无数梦魇一般可怖的人事,使他的灵魂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他说,我总是“妇人般地爱恋着热望着的人们,而所得的是无尽的残酷的失望”。无数失眠的夜晚,“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子里踱过来,拖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楞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动静。”“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⑦。他说:我挨过许多煎熬的夜晚,于是“我读《老子》,读《佛》,读《圣经》,我流着眼泪,赞美着那些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他们怀着悲哀驮负人间的酸辛,为这些不肖的子孙开辟大路”⑧。剧作家怀着一种近乎于绝决的情绪,发出了对这个黑暗宇宙与丑恶人类的恶毒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剧作最能让人感到的诗情氛围还是一种冥冥宇宙之中,人不能主宰自我,人性挣扎与人性沉沦中的悲哀,一群不肖子孙,冥顽不灵的动物无可挽救的走向堕落与毁灭。曹禺剧作的诗意渗透,使他的剧作主题深化到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境界,他超越了特定的时空背景,剧作的这种永久的诗情力量能叩响不同的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或观众的心弦。
曹禺剧作的诗情氛围还源于他对戏剧人物心灵世界的诗意揭示,在人物描写中的浓烈的情感的渗透。他的人物画廓中,他最用心思,最动情感,又最能“抓”人的形象,是一个个既美丽又悲哀的女性,蘩漪、陈白露、金子、愫芳,一个女人一个丰实的精神世界,她们灵魂的搏斗中又无不融入了作家诗情的激荡。蘩漪这个形象是一个极富有主观情调的诗化形象。她对周萍的紧追不舍,实际上是她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憧憬,是她对自然人性的狂热追求;她表现的种种暴烈的反抗是向命运的一种挑战,以一种近乎于“蛮性的遗留”的原初的自然人性来对抗人性扼杀的残酷。她的悲剧是人类意志向往自由,摆脱命运主宰而不能的一曲悲歌。她的对手不只是周朴园,周朴园仍然是一个悲剧的人物,蘩漪要挣脱的是一种束缚人类的自由意志,残害人类自然本性的天罗地网。由此来看,蘩漪不单纯是一个写实性形象,她是一个渗透了浪漫诗情,寄托了作者浓郁主观情感的诗化形象。“所以在雷雨的氛围里,周蘩漪最显得调和,她的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⑨。陈白露表现出一种更严酷的诗意的真实,一颗向善向美的纯洁的灵魂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后痛苦挣扎而又不能自拔,在希望与绝望的心灵分裂中作了与这丑恶世界的诀别。陈白露的悲剧是经历了心灵的炼狱而走向毁灭的悲剧,是对鬼域般现实人生的沉痛控诉,是寻找人生归宿与精神家园的诗的呼号。金子是荒凉原野世界中一股生命的活水,野性的美是她的外貌的诱惑所在,也是她的灵魂的魅力所在。尽管这个人物较少心灵的剧烈冲突,但她所显现的具有“原始野蛮”的蓬勃的生命力本身就是一首气韵生动、激动人心的抒情诗。那位在坟墓一般的封建没落家庭中寄生的愫方,有着哀静的外表,温厚的性格,她“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用她青春的生命孝顺着她那木乃伊一般的姨父曾皓,内心隐藏着对曾文清这位像耗子一般活着的废人欲爱而不能的苦情。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注入无限的怜惜和悲悯之情的同时,他又无不饱含着一腔愤懑之情,控诉着对善良人性的压抑与人性的摧残,作者最终不愿让他的人物与那古老的封建僵尸一同消亡,他怀着无限爱意,给愫方指示了一条求新生的路。愫方就象一首充满了浓郁感伤情调与哀静氛围的秋诗。曹禺剧作中的这几位女性人物,是曹禺戏剧中的诗的灵魂。剧作家在这诗的灵魂的展现中,精心铸塑的是她们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的精魂。作者从地位近乎怪戾乖张的行为中潜心揭示的是人物灵魂深处生命的激荡与自由意志的不屈追求。人们正是在这种人性美的诗意展现中,从她们的“不可爱处”看到了“可爱处”,从“不易领悟”的地方感受到一种“魅惑性”。这就是曹禺剧作的诗化力量。他的几位女主人公给他的戏剧带来了诱人的抒情的艺术氛围。
3
曹禺的早期戏剧具有一种神秘寓意的象征氛围。曹禺的早期剧作,首先给人的一种强烈感受便是那压抑、郁闷的氛围,一种紧张、燥动、焦虑的情绪。作者是把他“性情中郁热的氛围”,对宇宙的“一种隐秘的理解”都溶入他戏剧的氛围里。他是在自觉地追求与精心构造这种富有神秘寓意的象征氛围,他要把这种氛围作为一种戏剧的“魔力”,企望它能带领观众和他一起来体验宇宙人生的一幕幕悲剧。他在《雷雨·序》中谈到他不愿割弃“序幕”、“尾声”的意图时说,我“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着,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他们心里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象一场噩梦,死亡,惨痛如一只钳子似地夹住人的心灵,喘不出一口气来。”作者创作序幕和尾声的用心是想淡化恐怖、压抑氛围,但戏剧总体上依然给人以喘不过气来的郁闷、压抑的氛围的强烈感受。这种奇妙的氛围给了人们以审美的回味。
曹禺戏剧的这种压抑沉闷的象征氛围的表现,都分明地程度不同地表现在早期其他剧作中。下面我们从戏剧场景、情节、人物以及这些戏剧因素与观众心理的联系上来探究这种象征性氛围的表现以及它们所产生的戏剧审美效果。
艺术氛围的造成与戏剧场景的选择、描写直接相关,而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意识。曹禺早期戏剧的戏剧场景的选择与描写是具有共性可寻的。他的故事多是以家庭某个空间为背景的。他对这背景的陈述的描写最突出的是某种情调特征,在人物上台之前就显示出一种逼人的气氛。《雷雨》中周公馆客厅的陈设:褪色的家俱,一张旧相片,长年关着的窗户,黄色桌布上一些古香古色的小摆设,整本上突出的是这个空间的沉闷压抑感,它们与“雷雨”前沉闷的气氛十分合谐。《原野》中焦大星的家: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堂屋正中悬挂的满脸杀气的,沾满了油渍的焦阎王像,左门旁一张黑色的香案,上面供着狰狞可怖的菩萨,香炉里燃着将尽未尽的香——原野中这个孑立的鬼屋里一片恐怖的氛围,一种潜在的杀机在这里孕育。这个场面一开始就揪住了观众的心。《北京人》,曾家的小花厅:一切静幽幽的,右墙长条桌上一座古老的苏钟迟缓地迈着“滴滴答答”的步子,钟前放着祖传下来的一架金锦包裹的玉如意,条案前立一张红木方桌,有些旧损。左边一张紫檀木桌上,放着一盆佛手,几只鼻烟瓶,两三本古书。——透露出一个家运曾经兴旺过的大家庭的几分勉强的风雅。这些静态场景的陈设与描写,作者追求的是一种整体的情调与氛围,它能引起观众突破舞台的空间范畴产生自己的联想与判断。曹禺笔下的这些“家”都是一些没有生机,沉闷、压抑得可怕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成了戏剧中的人物悲剧故事的一部分,这些故事又赋予了这些场景以特有的象征性内含。
我们再看看曹禺对动态场景的描写所传达出的种种奇妙神秘的诱人氛围。《雷雨》第三幕,鲁贵家。周萍在雷电交加的夜晚,强行跳窗而入与四凤幽别。这时雷声轰轰,大雨倾泻,舞台渐暗。四凤推开窗户,场景转向窗外;外面黑黝黝的。忽然一片蓝森森的闪电,照见了蘩漪的惨白铁青的脸,露在窗台上面。她象个死尸,任着一条一条的雨水向散乱的头发上淋。她痉挛地不出声地笑,泪水流到眼角下,望着里面只顾拥抱的人们。这时自然界的电闪雷鸣与人物心理翻江倒海似的情感起伏交合了。电再闪时,“见她拉下窗下的护窗板,慢慢由外面关牢。雷声隆隆地响着,屋子整个黑下来。”在这样一种异常紧张可怖的氛围里,让观众看到了蘩漪由疯狂地爱变为疯狂的恨的这种近乎于雷雨的性格,可怕的报复性、破坏性与她悲愤而极的反抗糅合一起,强烈地震憾着观众的心灵。这个场景没有人物对话,只有雷鸣电闪,一幅阴森可怖的形象与人物简单的动作。它却以特有的戏剧氛围惊起了观众心中的阵阵“雷雨”。自然界的景象与人物性格、观众心理起伏构成了有机的整体氛围,使这场戏如此扣人心弦。
戏剧艺术氛围不仅限于场景的描写,它还与情节有直接关系。情节与场景构成一种舞台时空的立体交叉,每一种特定的时空关系下的戏剧情境,都可能带来一种特殊的氛围或情调。艺术氛围决不孤立地附丽某一形式范畴,而常常决定于情节与场景二者的有机联系。这种关系一方面体现着情节的时间运动,一方面又具有场景的空间意识。可以说,戏剧氛围既是空间范畴,又是时间范畴。它由时空和思维性的整体关系反映着艺术思维活动的对象世界。在一定的条件下,情节或场景也可以独自转化为艺术氛围。
曹禺在《雷雨·序》中透露了他戏剧情节的特征:“‘极端’和‘矛盾’是《雷雨》蒸热的氛围里,两种自然的基调。剧情的调整多半以它们为转移。”《雷雨》中矛盾交织如网,除了外在人物关系的矛盾外,还有人物心理行为的矛盾的扭结。剧作家所谓的“极端”,主要是指主人公蘩漪心理行为的矛盾的极端,“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⑩。她极端的行为正成了她性格的重要构成,又推动了戏剧情节发展,造成戏剧的特定氛围。以第一幕中“吃药”这场戏为例,周朴园要表现他的家长权威与尊严,逼迫蘩漪把药喝下:“蘩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蘩漪怒不可遏,丈夫并不是因为关心她要她喝药,而是如此冷酷自私无情,为了自己在孩子面前的尊严要她喝药以示“服从”;而她一直敷衍不喝,心里盘算着的正是不能当着周萍的面“服从”地喝下这碗药。到此双方行为将正面冲突推到一个“极端”,一个要服从,一个偏不服从,一种异常紧张的戏剧氛围笼罩着舞台,也牢牢揪住了观众的心。周朴园命令周萍:“去,去到母亲面前跪下,劝你的母亲。”当周萍正要按他父亲命令去做时,蘩漪发疯似地夺过碗来,把药一气喝下,向楼上跑去。这一剧烈的矛盾冲突,将外在人物冲突与蘩漪内心的冲突紧密交织。相比之下,蘩漪心灵的隐秘的冲突更叩人心弦,使台上台下弥漫着一场浓烈的紧张而压抑的氛围。它暗示着情节的发展,并由此让人们猜想预测着蘩漪这个不幸女人的未来的命运。她在周朴园面前是如此强硬,也可以说她没有在丈夫面前甘心失败过,但她陷在自制的情感的泥潭里是那般的弱软,那般的可怜。这个女人把心系在周萍身上,她肯定不能救出自己,她一直追寻的似乎只是一个梦。这场戏剧的冲突构成的情节场景,又是一种人物命运某种前兆性象征。在实在的凝固的情节造成的艺术氛围里,使时间得以延展,给观众造成一种审美心理上的滞留效果或带来感受的极大自由,这正是情节氛围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戏剧情节中的氛围,有时直接与特定情节进行中的某个特殊的动作发生奇妙的联系。曹禺戏剧十分注意从特定情节中的特定动作或场景制造戏剧氛围,感染他的观众。《原野》第三幕,仇虎与金子逃入黑林子后,那黑林子的肃杀诡谲与他惊惧不定的心理交织成一种异常恐怖的氛围。他与金子左冲右突,怎么也走不出这阴森的迷魂阵一般的黑林子。由旷野的深处又传来了辽远的凄厉的呼声,二人惊愕地回头,渐渐为呼声慑住:“回来!我的小孙孙!”“回——来呀!——黑——子!你——快——回——来!”焦氏瞎子没有出现,剧作家只让她为小孙子招魂的凄厉而悠长的呼唤,在黑林子里回荡,在剧场里回荡。这声音直接转化为一股强烈的神秘而庄严的戏剧氛围,在观众心理上久久滞留。这声响氛围给戏剧带来一种极为神奇的感染力。
曹禺在其他几部戏剧中也十分爱用声响行为渲染一种庄严、幽静或沉闷、抑郁的戏剧氛围。象《北京人》中,斜风细雨的深巷里时而传出的“硬面饽饽”的叫卖声,无不烘托出几分哀戚,几分凄凉。《雷雨》中的雷雨声,成了全剧不可分离的象征性情景。它序幕与尾声中响起的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更是增添了戏剧的一种庄严静穆的氛围。《日出》的结尾传来的夯声,使戏剧临终前浸润在一个象征的氛围里,它昭示人们告别黑暗与丑恶,去迎接日出与新生。尽管这声音与全剧氛围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它给全剧郁闷的情调加入了几分盎然的诗意。
“一切艺术都有待于达到音乐的境界”,“一切艺术向音乐靠拢”、“音响的神秘意义万岁”(11),音响审美效果成了一切象征主义艺术的共同审美追求。曹禺从中受到启发,并将音响艺术化为一种美的氛围的创造。他说:音响“有一定时间、长短、强弱、快慢,各种不同的韵味,远近”,“每一个声音必须顾到理性的根据,氛围和调和,以及对意义的点醒和着重”(12)。这“理性的根据”、“氛围的调和”与“对意义的点醒”正是他把声响作为一种象征氛围来表现的审美原则,是曹禺采纳象征主义艺术的一个成功探索。
戏剧艺术氛围是戏剧表演过程中的情感交流,它既是一种时空范畴,又是一种心理范畴。艺术氛围功能只能在特定的审美心理作用下方能实现。这就是要求戏剧家创作的时空舞台情景必须和欣赏者的审美心理逻辑相投合。如德国批评家赫尔德所说的那样,必须考虑时空活动与心理轨迹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剧作家应当按照他所追求的某种预期的规定效果的需要自觉处理时间与空间的活动。曹禺剧作中较普遍地刻画了具有象征性寓意的人物或景物形象,成功的象征性形象呈现出鲜活的“生命气息”,达到他象征的主观意兴与欣赏者心理逻辑的交合,构成了他戏剧艺术氛围的重要因素。象《北京人》中,他对象征性“北京人”的刻画,那个猿人的黑影在特定场景中在背景上的几次出现,不仅给这个写实性的戏剧增添了神秘、庄严的情调与象征的氛围,又与象耗子一样活着的现实生活中的“北京人”的形成映照,表明了作者的价值取向。这个被大胆的“北京猿人”形象找到了引起观众共鸣的心理契机,获得了一种饶有诗意的审美效果。而舞台上用作正面象征的两位现代北京人,即袁氏父女,似乎成了一个“北京人精神”的理念外化与意兴空壳,是舞台中的现实人物,却又缺少情感血肉,显得不实不虚,他们不能在与观众的心理交流中发生审美情感的契合。因此,不能形成一种象征的氛围。
《日出》中的方达生与没有出场的金八,似乎也是富有象征性兴寄的戏剧人物,作者对人物太观念化,也显得缺乏魅力。《雷雨》中的周冲,是作者创作前最先出现于心中的二个人物之一。这位象征“夏天里的春梦”的年轻人的出现,给周公馆黑暗沉闷的世界带进一些明媚的生机。但这个充满梦幻色彩的形象过于单纯透明,理念化色彩冲淡了人物应有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与形象的生动性。尽管作者在《雷雨·序》中作了近于偏爱的诠释,也不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因为作者的主观意兴缺少与观众心灵轨迹的对应。尽管周冲是一个象征性形象,却缺乏一种象征的艺术氛围的美感。曹禺戏剧氛围追求中的成败得失都是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寻的。
注释:
①《曹禺传》第277页-27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②⑦⑧《日出·跋》。
③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第207页。
④李南卓:《评曹禺的〈原野〉》,《文艺阵地》1985年6月第1卷第5期。
⑤田本相《曹禺传》第153页。
⑥《〈雷雨〉的写作》,《杂文》月刊1935年第2号。
⑨⑩《雷雨·序》。
(11)转引自廖星桥著《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第147、148页,北京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2)《曹禺文集》第1卷第46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