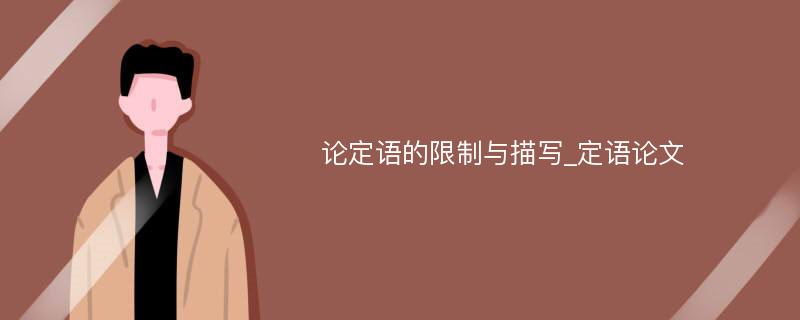
定语的限制性和描写性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限制性论文,定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朱德熙先生提出限制性定语和描写性定语的概念[1]后,限制性(区别性)和描写性已成现代汉语定语在语义上的基本分类,并被广泛用于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功能差异、定语排序、“的”字的功能、“的”字结构的称代规则等语法现象的描写和解释上。但究竟应该如何界定限制性和描写性,却至今没有达成充分的共识。由于概念不清,使用时名称相同,内涵却未必相同。对此虽有过一些专门的讨论[2-6],但有些问题依然使人困惑。这里我们仅就现代汉语定语的限制性和描写性谈一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限制性是否等同于分类性
关于定语的限制性,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限制性就是分类性,限制性定语的作用就在于给事物再分类。朱德熙先生认为:“根据定语和中心词之间的意义上的关系,可以把定语分为限制性定语和描写性定语两大类。限制性定语的作用是举出一种性质和特征作为分类的根据来给中心词所代表的事物分类。”[7]372陈玉洁也认为“区别性是为名词核心分类”[9],张敏则用“分类性”取代“限制性”[3]236,还有一些学者也持相同看法,如范继淹[8]、房玉清[9]205。
无论是说“限制性”,还是说“区别性”,这里都是指与描写性相对的概念。如果说描写性的实质在于没有或不重在区别性,那么限制性的实质就在于对事物的区别。对事物的区别是否等同于对事物的分类?按一般理解,给事物分类就是事物的范畴化,事物的范畴化具有社会规约性。所谓“社会规约性”,是说如何给事物分类以及可以分出怎样的类别,社会成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共识和习惯,符合这些共识和习惯的分类,就容易被接受,分类的结果就容易被认同为事物类别。否则,即使揭示了事物之间的差别或体现了事物之间的区别,看上去也未必像分类。
人们给事物分类倾向于选择那些界限比较清楚的属性作为分类的标准,因为只有标准明晰,分出的类别才清楚,才可以避免类与类之间纠缠不清的情况发生。因此,在现实中,界限越模糊、越有可能见仁见智的属性,充当分类标准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虽然这些属性也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区别。如果定语所表示的是这类属性,那么分类性就比较弱,看上去就不大像是一种分类,最明显的就是由状态形容词充当的定语。从词汇语义上看,状态形容词不仅表示某种属性,而且还表示这一属性所达到的量级,而属性的量级具有较大的弹性而缺乏清楚的界限。一般来说,事物是否具有某一属性,要比这一属性是否达到某一量级更容易取得一致的认识。就好比一块布是不是“红”的,很容易认定,但要认定一块布是不是“红红的”,要取得一致意见就相对难一些。状态形容词充当的定语,由于词义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虽然也具有区别性,但分类性就比较弱。如果将限制性等同于分类性,就容易将这类定语认定为描写性的,这恐怕就是人们往往认为这类定语更倾向于描写性的原因。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白白的衬衣”一定不会指黑色的或其他什么颜色的衬衣,甚至也区别于一般的白衬衣;“红红的苹果”也一定不会是绿苹果、黄苹果,甚至也区别于一般的红苹果。从这一点上看,状态形容词充当的定语虽然分类性不明显,但仍然具有区别事物的作用。这说明区别与分类并不等同,分类性弱的定语未必没有区别性。
人们给事物分类常常以事物内在的、稳定的属性为标准,这样分出的事物类别能够较好地体现事物之间的差异,因而容易被接受。如果定语表示的是这类特征,其分类性就容易得到认同,如:按颜色给花卉分类,分出“红花、黄花、白花、蓝花、紫花”等;按用途给车辆分类,分出“客车、货车”等;按材质给器物分类,分出“铁盒子、纸盒子、木头盒子、塑料盒子”。如果定语表示的是非内在的或非稳定的特征,虽然可以是区别性的,但其分类性就难以得到认同,甚至完全不像是在分类,如“我的书”“这本书”自然区别于“你的书”“他的书”“那本书”“别的书”,但要说这也都是给书分类,就难免有些牵强;“三斤黄瓜”自然不是“一斤黄瓜”“四斤黄瓜”,但要说这也是给黄瓜分类,这样的黄瓜类别就让人感到有些奇怪。所以,分类固然是重要的区别,但区别并不限于分类,区别性也不等于分类性,没有分类性的定语未必没有区别性。
人们对事物的区别依据的是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分类不同的是,分类一般依据的是事物的内在属性,而对事物的区别既可以依据事物的内在属性,也可以依据事物间的外在差异,只要能使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都算是有区别,就如同“这本书”不能算是对书的一种分类,却可以看作与其他书的一种区别。限制性的实质是区分和辨识,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将限制性定语的作用概括为“区别性”,这样既可以涵盖分类性,同时也可以说明“分类性”难以说明的限制性现象。
进一步说,限制性定语的功能在于区别,区别性即是对中心语所表事物的区分,既是对同类事物加以区分,必然会缩小中心语的外延,也就是限制性定中短语的外延一定小于中心语的外延。石定栩先生认为,限制性定语和非限制性定语的根本区别“在于限制性定语会缩小中心语所指事物的范围,而非限制性定语不会改变相关集合的范围”[6],我们同意这一看法。但对石定栩先生关于“汉语的所有定语都是限制性的”[6]这一主张,却难以认同,因为这既与汉语事实不符,汉语中存在“黑煤球、红盖头、白雪、圆球、钢锯条、年轻小伙子、飞机机翼”这类对中心语外延不起缩小作用的定语,也容易使人忽视“最贵的茅台酒”这类有限制性(茅台酒中最贵的那种)和非限制性(相比于其他酒,所有茅台酒都是最贵的)两种理解的歧义现象。
二、描写性是否就是内涵说明
如果说什么是定语的限制性,至今未能有一个清晰的且有充分共识的答案,那么对什么是定语的描写性,人们的看法就越发模糊不清。关于描写性定语,诸如“描写中心词所指的事物的状况或情况”“从性质、状态、特点、用途、质料、职业、人的穿着打扮等方面对中心语加以描写”“描写中心语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状态”“对中心语的性质、特点从不同方面进行描写”等,是最常见的属性描述。这类描述难以让人对描写性形成清晰的概念,结果导致同类定语在不同的分析者手里常常被赋予不同的性质。例如,同是表示性状、质料或用途的定语,在有的学者看来是描写性的[10]471,在有的学者看来却是限制性的[9]205,人们显然难以在这类界定的基础上展开相关现象的研究和讨论。
另有学者提出用外延性和内涵性来代替区别性和描写性,认为一般所说的限制性定语是从外延上对中心语加以限定,一般所说的描写性定语是从内涵上对中心语加以说明。[2]还有学者认为定语的区别性是为中心语分类,定语的描写性是对中心语的性质作出说明,并认为分类和描写并不矛盾,因而一个形容词定语往往既有区别性又有描写性。[如果我们是在语义层面而不是横跨语义、语用两个层面来讨论问题,那么后者所谓对中心语的性质作出说明,应该理解为是对充当中心语的类名之内涵作出的说明,而不应该是对一个类名在语境中的具体所指作出的说明。概括地说,这些学者认为限制性定语限定中心语的外延,描写性定语说明中心语的内涵。但这样看待限制性和描写性的区别未必妥当。
作为类名的名词是表示概念的,凡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内涵是对事物属性的反映,外延是对事物范围的反映。对概念内涵的说明有两种情况:一是增加新的内涵,一是描述已有内涵。
汉语定语中常见的一种内涵说明是增加新的内涵,由于内涵和外延之间有反比关系——内涵越多,外延越小,内涵越少,外延越大,那么这类内涵说明必然造成外延的缩小。例如“白纸”中的“白”增加了颜色方面的内涵,同时也就缩小了“纸”的外延,仅指“纸”中颜色为白的那一类。在对事物进行范畴化而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内涵的增加和外延的缩小是一个统一体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说内涵增加,外延缩小即是应有之义。如果我们以此为基础来界定限制性和描写性,自然会得出分类和描写并不矛盾的结论。但就讨论限制性和描写性是为了给定语分类这一点而言,这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就相当于说,所有区别性定语同时都是描写性的,所有描写性定语同时也都是区别性的,结果所有定语都一样,无类别可言。对内涵的说明是从内涵角度看的,对外延的限定是从外延角度说的,角度不同也就是分类标准不同,限制性和描写性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却用不同的标准来划分,这样分出来的类必然重叠甚至等同。当然,如果汉语里的定语确实都是限制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内涵说明和外延限定是统一的,我们倒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定语也都是描写性的,不过,若事实果真如此,限制性和描写性作为区分修饰语语义的对立范畴,对汉语来说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但汉语的事实并非如此,定语所表达的内涵说明并非都改变中心语的外延。
汉语定语中除了增加内涵的之外,还有另一种内涵说明,即仅对已有内涵进行描述而并不增加任何新的内涵,这种内涵说明不会改变概念的外延。例如“白霜”中的“白”只是对“霜”的固有属性进行描述,并没有增添新的内涵,“霜”本就是白色的,所以加上定语“白”并不会缩小“霜”的外延,“白霜”的外延与“霜”相等。“红盖头”“年轻的少妇”“坚硬的花岗岩”“飞机机翼”“鱼类的尾鳍”“隆起的穹顶”等与之相同。可见,内涵说明有的改变外延,有的不改变外延,如果笼而统之以内涵说明界定描写性,那么这两类都算是描写性的,这就抹杀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我们认为,既然内涵说明有改变外延和不改变外延的区别,既然定语的限制性可以从外延的角度来界定,既然对立范畴的划分应保持视角和标准的一致性,定语的描写性也应该从外延的角度而不应从内涵的角度来界定,即凡是不改变中心语外延的定语均是描写性的。
三、限制性和描写性是语义的还是语用的
定语的限制性和描写性曾长期被认为是语义层面的功能,近些年,有些学者提出:看待限制性和描写性应该区分语义层面和语用层面。[4-5]注意到这两种功能在不同层面的不同表现,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语义层面的定语功能在语境中受指称关系的影响而常常会发生变化,限制性的可能不再有区别功能而成为描写性的。例如,从语义层面看(即脱离语境),“出国留过学的老师”中的定语是限制性的,但在下面的语境中,定语“出国留过学的”却不起区别作用,是描写性的。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上课很认真,人也非常友善。一天课后,出国留过学的老师拿出他在国外的一些照片给我们看。
但有学者主张:描写性从内涵去修饰核心成分,告诉听话者“怎么样的”,而区别性强调所指的外延,告诉听话者“哪一个/些”。描写性是语义层面的功能,区别性则是语用层面的功能。[4]对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加以区分是值得肯定的,但将描写性和区别性分置于不同层面的看法,又使这一区分陷入交叉和混乱。
根据我们的观察,定语的区别性既有语义层面的,也有语用层面的,二者不应相混,也不应以彼代此。语义层面的区别性最基本的是以增加内涵为手段,通过增加内涵来缩小外延,以区分事物的类别。概念是对事物的抽象反映,无论增加多少内涵,也无论外延缩小多少,概念的这一根本属性都是不会改变的,通过定语限制而产生的新类名,依然是表示事物类别而不是表示事物个体的。“电脑”是类名,“笔记本电脑”依然是类名,“高端笔记本电脑”还是类名,“国产高端笔记本电脑”依然还是类名。如果要用提问方式来说明,那么语义层面的区别性是告诉听话人“哪一类/种”而不是告诉“哪一个/些”。语用层面的区别性则与指称密切相关,在语境的作用下,通过与特定个体的关联产生指别作用。“飞机机翼”的定语“飞机”在语义层面上是描写性的(飞机之外无所谓机翼),但在“我看到一架飞机,飞机机翼上有一颗红色的五角星”中,由于“飞机”表定指的个体,因而能对“机翼”一词的所指起指别作用,指别也是一种区别。如果要用提问方式来说明,那么语用层面的区别性是告诉听话人“哪一个/些”而不是告诉“哪一类/种”。可见,定语在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上都可以有区别性,虽然二者不尽相同。
同区别性一样,定语的描写性也是既有语义层面的,也有语用层面的。语义上描写性的基本特征是不改变概念的外延,语用上描写性的基本特征是不改变词语的具体所指。“年轻小伙子”中的“年轻”具有语义上的描写性,因为“小伙子”里不存在“不年轻”的类别;在“李霞到学校不久,这位年轻的教师便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中,定语“年轻”则具有语用上的描写性,有没有这个定语,“教师”的具体所指都是“李霞”。可见,定语在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上都可以有描写性,虽然二者不尽相同。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在语义层面上,还是在语用层面上,定语都有区别性和描写性两种功能。语义上的区别性(限制性)和描写性取决于是否对概念的外延有所改变,语用上的区别性(限制性)和描写性取决于是否对词语的具体所指有分辨作用。我们需要区分这两个层面,但又要避免造成功能错位,避免将语义功能误以为是语用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