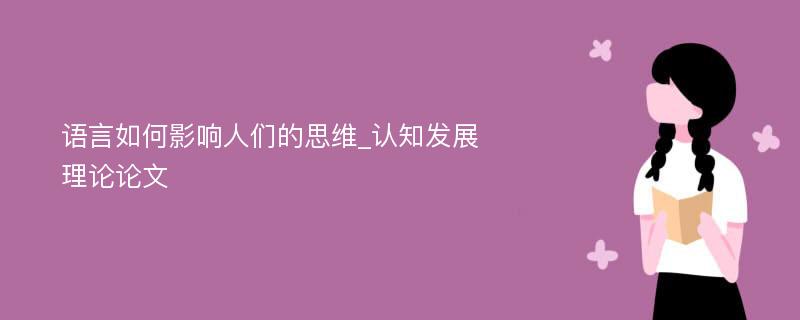
语言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9)05-0022-06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历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对研究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取向和认识。他们也许不会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但不同角度的探索和补充有助于人们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一直认为思维决定语言,语言仅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在二者的关系上,人们也一直认为语言居于完全被动的从属地位。其实,语言的起源与思维并非同时。从种系发展与个体发展看,语言发展中存在非思维阶段,思维发展中存在非语言阶段。但是语言和思维一经产生后却又常常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和制约。在很多情况下,语言和思维直接联系,但也确实存在语言与思维分离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在语言和思维这对矛盾中,思维起主导作用,语言能力发展不能先于认知能力发展,但认知能力本身还不足以解释语言发展,因为语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语言从属于思维,它决定不了思维,但却可能以它特有的方式影响和塑造人们的思维,这正是本文的观点。
语言影响思维的观点同维果斯基的工具理论一致。为说明人类的高级心理机能,维果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工具理论[1]。他认为,人有两种工具,一种是石刀、石斧乃至现代机器等物质工具,人运用物质工具进行劳动操作,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另一种工具是符号、词乃至语言等精神工具,人运用精神工具进行心理操作。动物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工具,所以动物心理永远只能停留在低级水平。人有了精神工具,所以心理功能就发生了质变,上升到高级阶段。精神工具越复杂,心理操作的内部技术也越高级。精神工具的使用不仅改造了人脑的结构和功能(人脑具有语言区),也使人的心理发生了质变。既然语言是工具,不同语言的工具功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必然影响到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脑结构和功能,必然会影响认知。此后,萨皮尔—沃尔夫提出的语言关联性假设也强调了语言在认知中的不可忽视的影响[2]。
联系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与之一致的观点。在主客思维中,过去一直广为人们接受的观点是,语言与思维可以分离,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或“物质外壳”。当代哲学对语言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其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尤为重要。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与思维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没有内容的形式和没有形式的内容都没有意义。语言和思维因而是一体的。维特根斯坦反对将语言视作思维的工具,而是将语词比拟为生活游戏中的“棋子”。他指出,如同象棋游戏中“车、马、卒”的意义取决于游戏者之间的“约定”,而不是某个游戏者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语词的“意义”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游戏者”共同参与协商、约定或建构的结果[3]。
社会建构论也重点论述了语言在建构思维中所起的作用。社会建构论者认为,建构是社会的建构,而建构的过程是通过语言完成的,因此社会建构论给予语言以充分的注意。社会建构论认为,所谓“现实”并非客观实在,而是社会以话语为媒介的建构物。话语是特定共同体中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呈现,表现为一整套的意义、隐喻、表征或陈述系统[4]。话语本身是同一文化中的“游戏者”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构成一种解释框架或概念背景,为“现实”提供定义和注解,以此实现对“现实”的建构[5]。因此,新的语言观认为,语言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划分经验的范畴和意义系统,并因此生成和建构了个体经验。语言具有“生成性”、“建构性”而不是“反映性”。因此,社会建构论将传统的现实与语言的关系加以倒置,视语言为第一性的存在。在它看来,语言不是对现实的表征,而是以其自身“构成(constitute)”现实。在这里我们并不是鼓吹相对主义,但这种观点对我们重新审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今,随着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日益深入,并从实证科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二者间颇为复杂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语言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被动,它对认知具有不可忽视的能动作用,这一点已得到实验研究的支持[6,7]。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资料分析语言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思维。
一、语言表达强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信息
我们已经知道,在空间语言表达上,不同语言间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空间认知。那么,它是以怎样的方式起作用的呢?很多人认为,语言表征上的差异会限制我们使用这种语言的内部表征。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需要进行非语言的计算加工才能明确特定语词的含义。如亲属词的使用,“A是B的妈妈的弟弟的妻子的父亲”,这种拐弯抹角的亲戚在不同语言中可能有不同称呼,而这些称呼语的使用可能有它特定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一个词的使用可能涉及到很多社会情景变量,而这种隐含关系不通过对文化的深入了解不能确切把握,像在社会知觉领域存在的原型匹配[8]现象也属此类。
同样,在空间定向上只存在一种参考框架的人们,在使用不同参考框架术语确定物体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时需要掌握不同的算法,即使用南北或左右等空间词表达事物间的空间关系时,两种表达间的转换遵守不同的规则。这样,对不同词应用的区分就强迫人们在认知加工上对之进行相应的区分,这种区分可能属于文化范畴也可能属于物质范畴。因此,不同语言中的不同的词,会强迫讲这种语言的人进行特定的计算加工。
另外,语言概念也会强迫人们以不同方式记忆所经历的事件。有些概念是可以进行内部转换的,而有些概念则不能。如你看到一个“三尺高的桌子”,几个月后你可以根据你所掌握的米尺关系对之进行换算,这是一个“一米高的桌子”。如果你所看到的是“男孩在树的左边”这样一个场景,而在一段时间后,你则不能将之转换成绝对方向术语来对之进行描述,除非你记得它们各自的绝对方向。如果开始就用“男孩在树的北边”来表达,则不会出现此问题。不同表达方式会带来信息缺失,这个简单的事实具有深远意义。如果语言根据绝对方位来表达事物的空间位置,则不利于经验者对事物间的关系进行组织,不能以个人经验对之进行描述,如前、后、左、右这些词的使用。否则,如果以“前、后、左、右”等词进行编码时,则不能记住事物的独立的绝对方向位置。要做到这一点,观察者必须同时记住自己的绝对方向位置,或者记住相关的场景中其它的主角的绝对方向位置。同样,对习惯使用不同空间语言的人来说,就会因为习惯的空间术语的不同而导致对所经验事物的空间位置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编码并贮存到记忆中。
无疑,在不同语言中类似的不可转换的例子有很多,英语语法要求我们注意数,而尤卡坦语(Yucatec)则不需要,因为它在语言表达中不需要复数标记。没有数的标记的表达方式,时间久了,我们将无法再获得有关数量的信息。同样的,英语中命名事物时主要看形状,而尤卡坦语中则注重材料[9]。如果抛开形状信息,只根据材料信息对事物进行分类,以后将无法保留事物的形状信息。
二、语义表征的差异可能影响到概念表征
语言是不是内在心理的外在表征形式,对语义表征的研究能否直接通达非语言的认知,外部表征会不会限制内部表征,内部表征会不会为了支持外部表征而进行调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会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关于语义表征和概念表征的关系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对之进行区分,另一些则认为应该区分二者。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们思维的内在心理表征不是语言形式的,也不是命题形式的,而是非语言的片断,这些非语言的片断足以支持外在的语言表征。如果我们把人们所思所想的内部表征,也就是我们进行思维的表征(记忆、推理、决策等等)定义为概念表征(CR,concept representation),把语言的意义编码表征定义为语义表征(SR,semantic representation),它们两者是重叠的吗?如果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对之进行区分。但是我们却经常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我们的思想而犯愁。我们是以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方式思考的吗?语言中广泛存在的差异使我们的语义表征必须脱离概念表征,以允许不同的语言把自己特有的性质放进去。显然,二者不是同一回事。
某些语言中语词的多样性和任意性告诉我们不同的语言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语义缺乏现象。像有些语言中的颜色词缺乏现象,以及空间表达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等。有些语言中没有真正的表达数的词语,有些语言中没有表达“逻辑”关系的连词,有些语言中没有“左、右”这样的词。不同语言中词汇的巨大的变异性,使我们无法在语义表征和概念表征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也许,任何语言中的语词缺乏都可以通过描述方式获得弥补,如用“天空样的颜色”来弥补颜色词的不足。但是人们是以解释的方式思考吗?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把所用的概念经过解释后进行思考,如当你运用“一百”这个概念时,会把它分解为“十个十”,把“姨妈”分解为“妈妈的妹妹”吗?一定要对之进行从头到尾的解释吗?显然不用。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语义沟”,且不同语言在其表达上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内在局限性。鉴于不同语言中广泛存在的差异,我们不得不在语义表征和概念表征的一致性与概念表征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之间进行抉择。而我们过去一贯的看法是概念表征具有普遍性。
三、抽象语言符号的使用促进高级认知的发展
珍特纳(Gentner,2002)在新近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关系语言对人的认知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那些较高级的关系结构[9]。罗恩斯坦(Loewenstein)和珍特纳通过实验方法证实了空间语言对空间关系匹配能力的影响[10][11]。他们在实验中要求孩子在另一个相应柜子里找到主试放置的某物体的位置。该柜子有上、中、下三个位置,主试让孩子看到他把“带星星的卡片”放到三个位置中的一个,然后要求孩子在另外一柜子里指出卡片的位置。实验条件是主试在放置卡片时加上说明放置位置的句子,在一种条件下,主试说的这个句子里有表达空间关系的"on、in、under"等词来说明放置的位置,如"I'm putting this on the box"。另一个条件下主试只是说"I'm putting it here"。然后要求被试到另一个相应的柜子里指出卡片放在哪里。结果发现,3岁孩子在两种条件下的表现有明显不同。当有明确的表示空间关系的词出现时,孩子表现较好。4岁的孩子在两种条件下的表现差异不大。但是,当任务难度有所增加时,4岁孩子在有明确的表示空间关系的词出现时,表现出了更好成绩。他们还发现用"top/middle/bottom"等词比用"on/in/under"等词有更好的效果,前者是一个关系系统,后者表达的是相对独立的位置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听到的关系语言有助于引导孩子对事件进行编码并且与空间位置关系进行匹配。而且,当几天后再把孩子带到图书馆(另外的环境中)要求他们“再玩这个游戏”时,关系语言的优势效应仍然存在。这表明语言经验能引导人们对事件进行不同的编码。
鲍森(Boysen,1995,1996)和他的同事曾经用猩猩做过一系列判断数量大小的实验[12][13]。实验中给猩猩呈现两种不同数量的小甜饼(一个和三个),猩猩指哪一堆小饼,就不给它吃哪一堆。对猩猩来说,最好的策略就是指数量少的那一堆。结果表明,这个策略猩猩很难学会,尽管它们都接受了关于数目大小的训练。然而,当情境发生改变,用数字代替甜饼时,猩猩就能够学会这个策略。显然,抽象符号的优势在于允许猩猩只对抽象水平的数量进行加工,而消除具体食物的丰富感觉特征。这有点像瑞特曼(Rattermann)和珍特纳的一个匹配任务中发现的现象,当分心物的知觉特征比较丰富时,孩子较难抵制分心物的作用。利用较抽象的物体能够使他们只对关键特征进行加工,而避免其它特征的干扰。
萨皮尔—沃尔夫认为语言的语法结构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维果斯基强调拥有语言允许说话者引导他们的心理加工。珍特纳认为特殊的关系术语和关系系统的学习给人们提供了增加其认知能力的表征资源。因此,在她看来语言既不是人们看世界的透镜,也不是引导人们认知的控制塔,而是一套建构和控制表征的工具,这与皮亚杰的观点有类似之处。过去人们检验萨皮尔—沃尔夫假设通常是在不同的语言间进行比较,认知工具观则允许人们在同一语言内对之进行检验。
四、语言为人们提供了整合各种信息的工具
斯伯克(Spelke,E.S.2002)通过一系列研究,认为人们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们掌握了语言这样一种可以把不同的知识进行整合的工具[14]。他认为动物和人都被赋予了核心知识系统,但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核心知识系统有它的局限性:第一,这些系统具有领域特殊性,每一种只表征出事物一个方面的特性;第二,这些系统具有任务特定性,不同的系统构建的表征只受到某一特定认知加工的指引;第三,这些系统相互间是独立的,每一系统内部的加工相对于其它的加工和表征而言是封闭的;第四,这些系统传递的表征是没有经过整合的。这些核心知识系统是人们从出生到成人一生都具有的,同样,动物也具有这些核心知识系统。人们之所以比动物更聪明,是因为人们拥有自然语言这一工具,它允许人们对具有上述缺陷的核心知识系统进行合并整合。
大量的实验表明,动物具有不亚于人类的空间认知能力。但是研究也表明,动物在某些空间认知能力上有不可超越的缺陷。比格勒(Biegler R.)和莫瑞斯(Morris,R.G.M,1993,1996)的研究表明,小白鼠能够找到房间里某个角落的食物(如,房间的东北角),或者找到房间里靠近某一参照物的食物(如,靠近白色圆桶的位置),但是却不能顺利找到“在圆桶东北角”的食物。小白鼠不能对“房间东北角”和“圆桶的”这两个信息进行合并,这是它们不能完成任务的主要原因[15][16]。类似的局限性,在程(Cheng,K.1986)等人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结果[17]。他们发现小白鼠只能根据房间的形状进行定向,而不会利用墙壁的明暗颜色进行定向,尽管小白鼠有对颜色的明暗进行辨别的能力。小白鼠对食物的位置的表征是“在靠近左面的长长的墙的角落里”而不是“在左边靠近白色墙的角落里”。研究者在2岁孩子身上同样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当要求孩子重新定向时,如果没有可利用的形状信息存在时(如在圆桶形的房间里),孩子也出现了定向失败。但是这种情况在成人身上则不会出现,研究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成人掌握了空间语言这一有力工具。斯伯克等人(Hermer-Vazquez,L.,Spelke,E.S.,and Katsnelson,A.,1999)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点[18]。他们认为,假如成人的定向能力是因为掌握了空间语言,那么当干扰被试产生空间语言时,他们的定向能力也会受到干扰。实验中,他们要求成人被试在完成空间定向任务的同时进行词复述任务,另一种条件是要求被试复述需要花费同样的注意和记忆资源的节奏复述任务。结果发现,在第一种条件下,被试表现与儿童和小白鼠的成绩没什么两样。这个结果表明,空间语言运用是人们能够更灵活地定向的主要原因。
语言如何起到这样的作用呢?研究者认为,语言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可合并性:一旦人掌握了词的意义和把词组合成句子的规则,他就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合并创造出新的意义表征。因此,语言使人们可以形成整体的表征,超越核心知识系统的上述缺陷。人和动物都具有“几何模块”,也有对颜色、事物的其它特性进行表征的模块,但是它们之间是独立的,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把这些来自不同系统的信息整合起来,如合并出“在靠近蓝色墙壁的角落里”的信息。
五、语言影响思维的其它可能机制
研究表明,语言影响思维可能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机制。
(1)知觉系统可以被改变或调整以适应语言的需要。如,学习一种语言使人们丧失对与该语言无关的音的辨别能力,同时也会根据需要增强对一些音的辨别能力。9个月大的婴儿能够对“松的”、“紧的”等各种空间关系进行辨别,但成人只根据语言的需要对一些空间关系做出区分。这种效应主要是基于人们的选择性注意最终导致知觉上的变化[19][20]。
(2)对事物的重新表征也会影响人们的思维。知觉调整能够在学习阶段影响类别的形成,但是开始的表征往往未被整合加工过,在随后人们进行的编码过程中,也会导致表征改变。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在某个特殊的领域随着经验增加,人们从新手到专家的转换,把信息重新编码到更高级的组块以规避短时记忆的瓶颈[21]。最常见的重新编码就是把它转化为语词编码。在不同语言中,知觉特征和维度以不同方式被组织起来,甚至于在那些被认为是客观的领域,如颜色、空间等。
(3)语言标签通过编码、加工过程影响认知。以“语法性”现象为例,人们为了有效地学习和记忆某个词的“性”,会对之进行符合其语法性的形象化记忆,从而使这种特征在记忆表征中更突出。例如,“太阳”这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雄性,人们会根据雄性物体的原型特征来构建太阳的表征,如“有力量,威胁”等。如果“太阳”这个词是雌性的,人们则可能倾向于把它表征为“温暖,滋养万物”等。还有一种解释是,为了解所学语法分类的意义,人们有意地去寻找具有同类语法性的物体间的相似性。如果意义和一致的相似性被发现,这些相似性就会被贮存(也可能那些与相似性有关的特征在记忆表征中占有更突出的地位)。这可以用来解释同类物体相似性的增强和对所观察物体描述上存在的偏见。这种机制得到新近一些实验支持,如比较导致相似性的增加(只要在比较项目间发现有意义的相似)[22][23]。
不同语言在不同事物的某些相似属性间建立起的对应关系,如在各种语言中广泛存在着一些词的比喻义、引申义的用法,和不同词之间的高频联系等,也会影响到人们认知。如我们前面研究所证明的汉、英语言以不同的空间语言表达时问,导致人们把空间的不同维度与时间类比;中国人由于“南下北上”的习惯用法,所导致的对地势高低的认知偏差等[5]。
六、结语
早期有关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没提供多少支持语言影响认知的证据,新近工作刚好相反,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发现了合适的探索途径。认知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把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置于一个新的视角。莱文森(Levinson,1996)指出,“认知科学的兴起使我们对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关系问题的观察产生了海量的变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的预设从经验主义转向理性主义;从本体论角度看,从唯心主义转向实在论。”由此可见,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上,认知科学的作用不容忽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的最终解决将有赖于认知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语言影响认知的研究也为心理学的民族化提供了动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特别是语言差异将影响人们的认知,这一点在国际交往中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