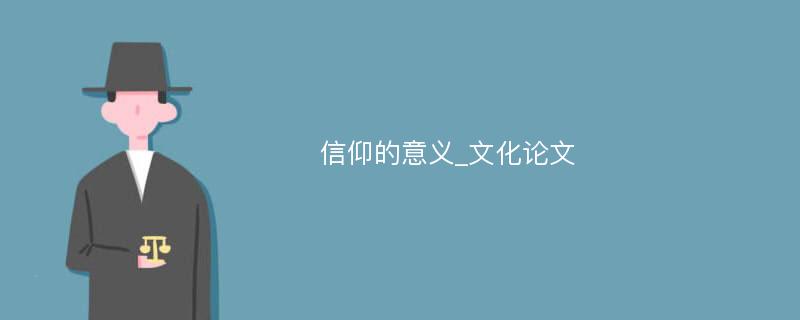
信仰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仰在现时代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意义,甚至成为一些人嘲讽和讥笑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很有必要揭示信仰在整个人生中的作用和地位。这首先需要我们自身具有坚实的信仰。
多少年来,宗教神学所揭示的信仰愈加理性化,离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生活愈来愈远;同时世俗性信仰也暴露出其摇摇欲坠的本质。真实地关切人生并引导人走向神性世界的信仰在哪里,这是人人面临的迫切问题。
信仰给生活提供了根基,这一点没有多少人反对。但是,应当信什么,怎样信,不是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认识。很多人虽然认识到信仰的必要性,却依恋世俗的享乐,迟迟不走向皈依之路。这种人当这样形容:既想拉着上帝的手,又想紧紧抓着撒旦的手。对他们来说,信仰只有能够获利才是正确的。
在信仰问题上争辩的结果往往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这在教会发展史和世俗历史进程中有数不胜数的例子。信仰如果导致这样的结局,恰恰证明了这信仰有虚无的成分。有些信仰就是虚无本身,是假信仰,虚无主义者所崇尚的信仰就是如此。20世纪人类痛苦的经历——奥斯维辛集中营——不正展示了这一切吗?
一、信仰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时代已经使我们失去生存下去的支撑,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自杀和玩世不恭。如果没有了根基,我们怎能忍受这苦难而沉重的生活呢?路在哪里,光明又在哪里?如何有意义地生活下去?信仰,只有信仰才是我们的路和光,才能为我们的生存提供支撑和意义。这条路并不是轻松的,它是非常艰难的,是一条窄而又窄的路。这需要我们的勇气。有人把这叫做“灵魂转向”(注:拉纳尔:《论今日信仰的可能性》,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46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从生存的现象事实和氛围出发,只能得出生活的无意义和荒谬,看到的是“生命的魔域”。必须清楚的是,事实本身不会提供意义,有的只是石头般的规律,令人不可抗拒。处于事实的包围中而不能自拔,这正是我们现时代人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为了摆脱事实的窒息,人往往产生一种疯狂,即荒谬的疯狂。在这种疯狂中,一切都无所谓了,一切都是可干的了。审美主义者甚至可从这种疯狂中看到“美的闪现”。对这种疯狂的赞赏和沉入,成为一种时尚。荒谬的疯狂的结果往往要走向其另一方面,走向高度机构化的强权的疯狂。
要摆脱无意义的生存和疯狂,只能超越事实性观照,走向另一种意义性的思维。在事实性的观照中,我们就物本身来思索其是什么,自然不能发现有何生存的意义了。意义性的思索乃是存在对人有什么意义,再进一步,就是询问整个生存对人有什么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我们必须区分存在物与存在本身(注:海德格尔:《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下卷)第930-93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事实性的思索是从存在物出发的,它用概念、理论界定存在物自身的规律——理性的法则,并没有对存在本身有何探究。存在是存在物之所以在那里的那个东西,已不能由存在物出发来思考。从这一点来看,人们往往局限于事实性——存在物的境域内,脱不开身,从而陷入荒谬的泥潭。对意义的##示存在的基本真理。存在的真理通过与事实性的抗争引导我们面向意义的真理。事实性真理具体地说,就是通常所称的理性的真理。我们常常处于理性的统辖下,“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管是否有人在思想上实现或没有实现过”(注: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见《哲学译丛》1963年第10期,第53页。)。这种真理“对于人、天使、天神都只是一个”(注: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见《哲学译丛》1963年第10期,第53页。),它“依赖于自明”(即事实性)(注: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见《哲学译丛》1963年第10期,第53页。),“在真理的面前,人或超人同样是无能为力的”(注: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见《哲学译丛》1963年第10期,第53页。)。面对理性真理,人是无助的。理性真理使人处于其绝对统治下,即使意识其荒谬,也必须服从。如何弃绝这种境地,正是每个人要严肃考虑的问题。从服从走向抗争,是需要勇气的。这勇气的力量源泉正是信仰。信仰为整个人生提供了根基,正是在对意义的询问中产生了信仰。信仰实际就是对存在意义的信奉,即对与存在的真理的关系的信奉。意义问题其实也就是信仰问题。只有存在的真理透射来,信仰才是可能的。这里我们经过了一个思维的轮回。可以看出信仰是反理性的,是对理性的真理的抗争。
意义性询问,就其对“我们是否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事实性真理?事实性真理不可超越吗?”这两个问题的追询而言,只引导我们实现了从事实性思维到意义性思维的转变,只是走向信仰的第一步。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可能的道路也多种多样。我们很可能偏离意义性追询的初衷,滑回理性真理的界域。在这种状况下,阐明信仰的具体含义及其实质内涵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离开了信仰的实质内容,意义性追询只会落空。
信仰最初的含义指对某种东西的信奉,随着宗教(谈论信仰不能不谈论宗教)的发展,信仰变为对绝对的信赖。通俗地讲,信仰就是指有信念。绝对如果从理性思维的观念来看,只是一种哲学范畴,并无信赖与不信赖的问题。从宗教的角度出发,那个绝对恰恰为生存提供了真正的支撑和意义。在那里,绝对没有概念或逻辑的意味,也不是一个对象,它是作为对生活的最终极的解释而体现的。对生活有无意义的回答并未产生对生活的真实的解释,自然也不能自动地引向信仰。信仰产生在哪里?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与对生活意义的追询一同才能导向确切的信仰。所以说,认识到那个绝对在信仰之先,而不是在信仰之后。甚至对生活有无意义的追询也依赖于那个绝对,真正的生活意义之有正是对那个绝对的肯定和信赖。追询是与绝对的展现融合为一体的。这个融合体唤醒了信仰。那个绝对我们就称为上帝。至此,信仰的内容依然是空洞的,具体的内容还需要建构。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上帝面前人是低微和无力的,我们对上帝要怀着敬畏。那生活的意义是上帝带来的,并非人单方面求索的产物。其次,我们要赞美上帝,并且这赞美还在信仰以先,如赫舍尔所说:“精神生活的秘密在于赞美的能力。称赞是爱的结果。它产生于信仰以前。我们先是歌颂然后才信仰。基本的问题不是信仰,而是感受与赞扬,是为信仰作好准备。”(注:赫舍尔:《人是谁?》,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16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在对生活的意义的追询中认识上帝再到自认卑微和赞美的基础上,我们才迈进信仰的领域。前面讲到生活的最终极的解释和信仰的建构,指的是人的自觉性的努力。在上帝面前自认卑微、服从和赞美,对上帝的归顺,只是信仰来自上帝的一个层面。要看到,上帝并不会替人做事,上帝只提供绝对的“阿基米德点”和能量,杠杆的撬动只能由每个具体的人自己来完成。上帝——意义的真理不能为具体的行动提供具体的指导。虽然说人的自由是上帝赋予的,但对自由的运用还在人自身,信仰的内容还是需要人自身去建构的。从事实性真理所显示出的生活的无意义,也能看出建构之必要:既然生活无意义,不能忍受无意义的人们不可能对生活强求意义,只能从对意义的追索中去建构意义。
二、信仰的具体内容
对生活的意义的询问是人的“终极关怀”,信仰作为对终极关怀的实质性回答,为生活提供了终极的基础。信仰与相信不同,它是无对象的。上帝并不作为一个信奉的对象出现在人的面前。信仰可分为“三种不同的层次:Deo credere,Deum credere,in Deum credere.(相信上帝、信任上帝、信赖上帝)。Deo credere意指:相信上帝所说的话为真……,譬如我们可以相信某一个人(是好人),然而不一定要信任他。Deum credere意指信任他是上帝。In Deum credere的意思则是:全心信赖地爱他、奔向他、紧紧依靠他,并与他结合在一起”(注:皮柏:《相信与信仰》,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528-52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所谓对上帝的信仰实际上所指的是在上帝中的有信念,是与上帝同在而皈依上帝。对象化的上帝往往成为一个崇拜的偶像,对这样一个上帝的信仰就滑回了无信仰,因为这只成为人的愿望的投射。信仰首先是爱,对上帝的信仰占第一位的是爱上帝。正如《圣经》上所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主上帝。”(注:《圣经·马太福音》22.37。)对上帝的爱是归顺性的、无条件的,人并不能企望从这爱中获得上帝的给予。爱生出了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承受现世的艰辛和苦难。我们不能说这种爱没有心理的因素,对这种爱我们也确确实实有一种心理体验,但它决不只是一种心理效应,不是所谓心理学所能包容的。爱与信仰是不能分出个先后的,它们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信仰即爱,爱即信仰。爱是上帝的恩典,是神性的闪光。爱上帝也就是相信上帝。
我们前面讲过,从现实的事实性出发,只会看到荒谬和无意义,生发出对整个宇宙的绝望,认识到处于深渊中。从深渊中如何走出?如何超越深渊?这均是单方面的人的力量所不及的,我们需要求救。舍斯托夫经常引用一句话,正体现了这一切:“De profundis ad te,Domine,clamavi.(主啊,我从深渊向你呼求!)”(注:舍斯托夫:《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第13-14页,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译文有改动。)信仰中正包含有这种求救意识。由爱上帝生发出求救意识,正是因为我们信任上帝。
信仰还在于承爱苦难和认可泪水的至上意义。对上帝的爱和向上帝的求救,使我们不重于世俗之利益的满足或所谓事业的成功,我们的眼光正好落在事实性思维所轻视的方面,落在苦难和千百年流之不尽的眼泪上,我们用“约伯的天平”(注: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称量一切。“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注: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翻开一部人类史,看到的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别无他物。那些成就和事业,只是理性所证明的,在“约伯的天平”上是轻之又轻的。千百年来,人们的眼泪流成了河,而理性却赞颂着“成功的辉煌”。为了理性法则的统治,泪水只成为成功路上的垫脚石,成为工具。流多少泪和血对理性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在信仰面前,眼泪才是真正珍贵的东西,显示出超越一切的意义。
信仰是绝望中的希望。在对苦难和泪水的意义的肯定中,我们摆脱了事实性的梦魇,有一丝光在我们心中闪现,这就是希望。在对现世的绝望中,在深渊中,通过对上帝的呼救,我们产生了对另一世界——神性世界的希望,产生了上帝拯救我们的希望。这希望是通过我们呼救而自上降临的,是上帝的恩典。希望不仅仅为我们指明通向神性世界之路,也为现世生活提供了保证。在希望中我们具有了活着的勇气,勇于抗争理性真理的法则,勇于承受苦难。希望使我们看到了那只“神秘的手”,它会擦干我们双颊上的泪珠,也使我们勇敢地伸出自己的手,相互擦干这苦涩的泪水。希望保证了我们不是站在流沙上,而是站在坚实的基座上。理性自认为杀死了上帝,在我们的希望中,上帝永远是活的。
信仰意味真正的人性之复归,真正的人的自由的发挥,真正的人的自我实现,也即真正的人道主义。那种不以信赖上帝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只会成为一种疯狂。成为“魔道主义”。人的一切:存在、人性和自由,从本原意义讲都是上帝的恩赐,也即上帝创造了人(注:《圣经·创世纪》1.26-1.27,2.7。),但上帝是以自己的形象造人的,并赋予人以他的灵,因此人与上帝是相似的。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人成为上帝的合作者,而非奴隶。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系乃是爱的联系,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信赖上帝——爱上帝,是人自觉的归顺,在归顺中人也获得了自由。上帝赐予的自由乃爱上帝的自由,而非滥用自由之自由。在信仰中,我们自然而然就接受了自由,并不需为自由而去抗争。在这一点来讲,这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在这种真正的自由中,人性、自我实现才被给予了源泉,才不会落空。正如弗兰克所说:“人在呼吁上帝、献身和服事于上帝时,自我第一次全面地实现了;只有与上帝结合在一起,人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本质,奥吉斯丁主教说:‘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上帝是人的灵魂的故乡故土……”(注:弗兰克:《上帝与人》,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19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信仰关涉人的整个一生。人不可能此时信仰,彼时不信仰。巴特说得好:“信仰关涉一种永远有效的决心。信仰并不是一种可以用其他意见来代替的意见。一个暂时的信仰者,根本不知道信仰为何物。信仰是一种始终不变的关系。信仰是关系上帝,关乎他曾为我们做过一次而永远有效的事。”(注:巴特:《论基督宗教信仰》,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492、5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信仰为人的整个一生提供了坚实的根基,从这方面看,人在信仰中灵魂是安宁的。当然这并不排除不信或不安之扰动,但这并不能动摇根基,而且这不信或不安也是为了信的探询导致的,并不指向对信仰的背叛,而是指向信仰的巩固。“只有信是应被看重的,如果我们有一点像芥子大的信,这足够使魔鬼遭受其失败”(注:巴特:《论基督宗教信仰》,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492、5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依赖神恩,信仰终生伴随我们。信仰者以信仰评判世界,而不是以世界评判信仰。信仰者使信仰深入、渗透生活的各个方面,信仰在生活中闪耀着其光彩。一个信仰者不可能过双重的生活:一时从信仰出发皈依神性世界,一时又以世俗利益背弃信仰。诱惑、世俗利益在信仰者眼中是不足为害的,它们在信仰面前均不攻自破。在信仰中不以世俗的成败为评价人的标准,而以对上帝的归顺为一切评价的出发点,所以从世俗利益的观点来看,信仰者似乎可以被称为失败者。但是,正因为在现世的失败,才获得了永恒的成功,永恒的荣光。信仰意味着关涉整个生活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针对一种人根本上改变了的意识,一种新的基本态度、一种另外的价值尺度,一种整个人类彻底的思维转向、整个个人的转向”(注:汉斯·昆:《做人与做基督徒》,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22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人充满信任地理解它并按它去生活”(注:汉斯·昆:《做人与做基督徒》,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22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信仰是一种决心,它意味着一种责任,也更是一种承认。我们皈向上帝的同时,就做出了一种抉择,采取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信仰就是宁采取信,而不采取不信;宁采取信赖,而不采取不信赖;宁采取知识,而不采取无知;信仰的意思是在信与不信、误信、迷信之间,作适当的抉择”(注:巴特:《论基督宗教信仰》,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492、5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我们从以我们的利益出发的生活中退出,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这样我们也就承担了义务和责任。我们不是逃避生活本身,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建构新的生活,也是从根本意义上去改造生活。所以说信仰者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隐士般的生活。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责任的承担,也说明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隐秘的和局限于私人小圈子,它是公开的,是公开的承认和担当。“信仰就是人类使自己与上帝发生关系,是一种应当有的关系。这种工作发生于退出对上帝的徘徊中立,在我们的生活和态度中退出,对于他规避的义务,退出私人的小圈子,而进入决定、负责和公开的生活。信仰如缺乏这种公开生活的倾向,信仰如规避这些困难,它本身便已成为不信、误信及迷信”(注:巴特:《论基督宗教信仰》,见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第492、50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既然有了信的决心,也便有宣称:“我信上帝!”的胆魂,必要时也毫不忧虑地迎向迫害,甚至为信仰受难而死。但是,信仰者决不应当用暴力强迫不信者去信,像官方机构化教会之所做所为。暴力败坏了信仰。那些用暴力强迫不信者的自称信仰者,他们的所谓信仰只能导向不信、误信和迷信。信仰之公开,不仅仅是公开的宣认,同时要从信仰出发对现世作出评价。在现世的不公和黑暗面前,不只是承受它所加诸自身的苦难,还要对其表示我信仰者之“不”,不同意、不服从。信仰者不是沉默者。
信仰从理性来看是任性的举动,它不以证明了的真理为借口。理性认为丢脸、愚蠢、不可能的东西,正是信仰真正依托之所在。德尔图良说出了问题的关键:“Crucifixus est Dei filius,non pudet quia pudendun est,et mortuus est Dei filius,prorsus credibile est quia ineptum est,et sepultus resurrexit,certum est quia impos-sibile est.(上帝之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并不因此耻辱而感羞愧;上帝之子死了,虽荒谬却因此可信。埋葬后又复活,虽不可能却因此而是肯定的。)”(注: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第3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信仰者不信赖理性,与理性做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如此,信仰者或可称为“以流血的头撞击绝对理性的铁门”(注: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中译序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的人们。在信仰者眼中,上界与地上绝不相同,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处于绝然对立的角度。不否弃世俗之城,便不能入上帝之城。常有人也表现了任性的勇气,但并没有抛弃对自己“事业”的期望,依然期待人们赞赏,这样他们就退回“必然状态”,还处于理性的奴役下。他们还没有伸出头来去撞横在眼前的“理性之墙”。
自贬是跨入信仰的一条必由之路。只有对自我能力、对现世的彻底绝望才能生出对上帝的希望。抛弃一切成就、一切赞扬,这就是自贬的举动。自贬就是自认无力救助,自认失败。
信仰是沉重的,在信仰中你要把整个世界的苦难都背在自己的身上。
这里探讨的只涉及信仰的“表层”,深入的讨论需要从罪出发,只有留待以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