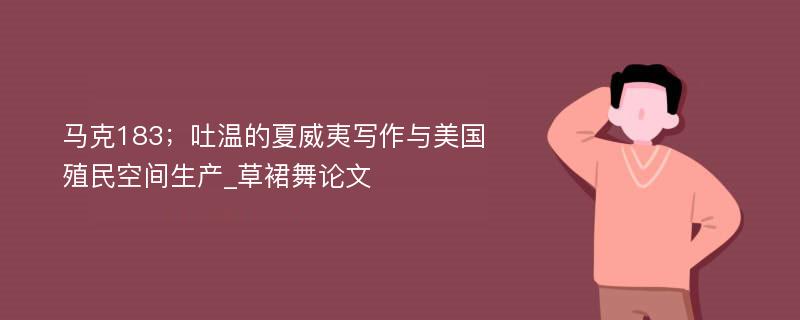
马克#183;吐温的夏威夷书写与美国殖民空间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夏威夷论文,美国论文,马克论文,吐温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通过生产空间”生产并再生产社会关系,缓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①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以国家领土边界为限可分为国家内部空间生产与国际化空间生产。列斐伏尔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领土边界稳定后的国家内部空间生产策略,尤其关注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都市化过程中的空间问题,但并未涉及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在领土范围形成时期以领土拓展和资源侵占为目的的殖民性空间生产过程。根据列斐伏尔所言,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具体过程是国家统治者、经济利益获得者和权力规划者将国家原有的自然和社会空间进行抽象化,将百姓的“生活空间”(lived space)转化成为资本主义者的“构想空间”(conceived space)。②本文将列氏理论置于国际视野中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在海外的殖民过程,指出这种殖民过程运用权力和知识改造他国原有的社会空间,将有利于本国发展的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与宗教思维方式植入他国,将他国人民的生活空间抽象化为遵循本国国家空间原则、为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所控制的构想空间,以便对他国的土地、资源、文化进行掠夺和殖民,这种空间生产方式可称为“殖民空间生产”。 内战给美国国内的制糖产业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黑奴解放运动导致南方蔗糖种植园劳动力严重匮乏,战乱使制糖器械和厂房遭到破坏和弃置,战前1,300家糖厂到1870年时只剩不到300家仍在运营③,种植园的数量和蔗糖产量大幅缩减,“原本种植繁茂甘蔗的良田现已变为令人忧虑的无尽荒地和沼泽”④。供应的严重短缺使得蔗糖产品价格迅速上涨,“白糖成为美国普通百姓餐桌上难得一见的调味品”⑤,人们只好用高粱糖浆、枫树糖浆和甜菜糖来弥补白糖的不足。为了满足国内对蔗糖的需求,北方各州派人来到夏威夷寻找新的糖产品供应地。美国人用技术逻辑和资本策略在夏威夷进行土地改革,大量建立甘蔗种植园,使得夏威夷糖产品出口在1861年至1865年期间从250万磅迅速飙升至1,530万磅。⑥与此同时,美国人将利润规则延伸至种植园空间之外的非生产性领域,规训夏威夷人的生活体验,操控他们的庆典活动,以保证种植园工人的工作效率、抑制庆典活动中的反抗性力量。另外,美国人削弱甚至消解夏威夷传统宗教庙宇和其他国家宗教场所的神圣性,构建并加强基督教教堂的神圣性,使美国在殖民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以此实现完全控制夏威夷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目标。 1866年3月,马克·吐温受托于《萨克拉门托联合报》(Sacramento Union)抵达夏威夷调查当地糖料种植园的发展状况,他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向国内发回25篇书信式报道⑦,回国后又以夏威夷经历为主题做了上百次巡回演讲,这些报道和演讲成为美国当时获悉夏威夷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吐温通过撰写报道和演讲的方式直接参与到美国在夏威夷的殖民空间生产过程中,帮助美国人掠夺、改造和建构夏威夷人的生活空间,将其转化为使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构想空间,这最终有助于美国兼并夏威夷领土、霸占夏威夷丰富的自然资源。 一、种植园空间的殖民化生产 在资本主义空间中,动态、多维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在国家权力和资本逻辑的操控下被抽象化为静态、二维的地图、蓝图、表格和数据,“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⑧,一切资源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来最大程度生产剩余价值。早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开始觊觎夏威夷丰富的物质资源,美国传教士鼓动夏威夷国王实施“大马赫里”(Great Mahele,1845-1855)土地改革,建设了大批的甘蔗种植园。他们用技术和资本策略在夏威夷进行殖民空间生产,用尺寸、面积、方位、利润等抽象属性对土地进行丈量和评价,改变原有的土地所有体制,掠夺夏威夷的土地,榨取夏威夷人的劳动,役使夏威夷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为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 在夏威夷期间吐温忽略了当地极富特色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他在发回美国的报道中详述当地甘蔗生产环境和蔗糖产品产量,将夏威夷人鲜活、生动的自然空间和生活空间抽象化为夏威夷蔗糖种植园的规模、产量、利润、生产工艺、劳动力、耕种方式等具体数据。吐温注意到科纳地区位于高海拔地区,有“充足的光照和丰沛的降雨”,随即赞叹这样的地理条件能够使“每英亩土地的平均糖产量为两吨”,远远超过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see Mark:210)。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国最大的蔗糖产地,南北战争使当地的蔗糖生产受到重挫。吐温将科纳地区与美国本土蔗糖产地相比较,用蔗糖产量的数据强调两地在生产能力上的巨大差距,刻意凸显夏威夷在蔗糖制造方面的独特优势,暗示夏威夷可以取代路易斯安那,成为美国新的糖产品供应地。在吐温看来,科纳地区的自然空间本身可以成为生产资料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能够让其他资本生产要素在种植园空间中有效运作,确保剩余价值的快速生产。 吐温进而指出富饶的科纳和夏威夷的其他地区还有很多“荒废的”(idle)和“空闲的”(unoccupied)的土地,夏威夷百姓将这些土地置于“门外”,不以任何方式进行“开发利用”(Mark:210)。吐温所指的是土地改革后仍归夏威夷百姓所有的少量土地,这些土地未被纳入美国人的种植园空间,逃离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不能为其生产剩余价值,因而被吐温视为“荒废的”与“空闲的”。吐温的措辞流露出对夏威夷土地资源的渴求和无法在这些土地上建设种植园的遗憾之情,更揭示了吐温的资本主义思维逻辑。将空间再现为空置的、未被占据的、未经开发的这种表述是资本主义空间占领的重要策略,隐喻性地剥夺了空间原有主人的所有权,使资本主义对空间资源的开发合理化。吐温认为这些土地对夏威夷人来说无足轻重,如同被弃置于“门外”的荒地,与夏威夷人的生活空间相隔绝。吐温没有意识到或是刻意忽略土地是夏威夷人重要的精神寄托,种植园的设立迫使夏威夷人民迁离世代生活的家族土地,这割裂了夏威夷人与土地之间原有的紧密关系,令土地失去了原有的厚重文化象征内涵,从具有灵性的民族生命之源抽象化为美国人获取最大经济收益的生产要素。在“夏威夷百姓将土地置于‘门外’”这句话中,吐温用主动语态暗示夏威夷百姓主动放弃与土地之间世代承袭的复杂关联,从而掩饰美国人在夏威夷土地改革和土地殖民化过程中起到的主导性作用。 除了土地,吐温将劳动力也抽象化为可计算、可操控的商品。吐温对比夏威夷种植园与美国南方种植园,精确计算二者的生产成本与利润。他指出前者的利润远远高于后者的原因除了夏威夷优越的地理条件,还要归功于夏威夷拥有廉价的劳动力,“雇佣每个工人的价钱为100美元每年——恰好与为一个黑奴提供住宿、衣服和医疗的费用相当——但是不需要支出500到1000美元购买劳动力的初始费用”(Mark:260)。内战对奴隶制的打击使美国失去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吐温对夏威夷劳动力的介绍似乎在向美国民众表明,夏威夷可以成为美国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地。吐温向美国人保证这些夏威夷劳工是驯服听话的,因为夏威夷政府协助种植园主制定多种严格法律对工人进行身体规训,“如果工人偷懒或旷工一天,他必须为此多工作两天。如果他变得难以管教、不服从命令,他会被责罚在礁石上工作一个季度,每天25美分工钱”(Mark:270)。抽象空间中需要构建符合空间规则的“抽象身体”,在吐温看来,夏威夷劳工必须放弃自己的自然生活节奏,严格遵守资本主义者的抽象时间表,被规训为有用的、守纪律的、理性的、标准化的、受到控制的抽象身体,成为空间生产实践中的经济生产资源而被资本家进行管理和利用,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劳力转化为资本家的利润。 夏威夷社会在吐温眼中如同华盛顿·欧文笔下令人昏昏欲睡的睡谷,人们“在树荫下悠闲垂钓,惬意地渡过整个夏天”(Mark:53),或者“坐在房子拐角处的阴凉里,懒洋洋地看着往来的行人和周遭的事物”(Mark:31)。吐温支持发展现代高速交通运输工具来改变夏威夷缓慢的生活节奏,以此促进美国与夏威夷之间“利润可观、毫无风险、成本甚微”(Mark:21)的贸易活动。吐温本人就是乘坐刚刚开通的“亚杰克斯号”(Ajex)蒸汽轮船抵达夏威夷的,他对这种现代蒸汽轮渡十分赞赏,因为它取代了旧式风力帆船,大大缩减了航行时间,使“海上航行时间能够以天和小时来计算”,避免了“浪费宝贵时间的可怕行为”(Mark:21)。列斐伏尔指出,理性的工业化技术损毁了人们的“循环时间”(cyclic time)观念,现代人打破自然时间周期和生物节奏来获得对时间本身的操控,“线性时间”(linear time)概念由此占据上风。⑨夏威夷人的时间观念遵循自然生物节奏,他们认为生命历程由诸多周而复始的循环周期构成,人的日常作息甚至生老病死都与自然界的昼夜交替和四季更迭紧密相连,人顺应自然节奏才能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处,这符合列斐伏尔所说的“循环时间”逻辑。而吐温推崇受科技和劳动支配的时间观念,他欣喜地意识到新式交通工具的应用使人员和资本在空间流通上的地理障碍得以加速消弭,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非生产性的时间消耗,他的思想正表现为列氏所提及的“线性时间”逻辑。虽然吐温将夏威夷社会描写成远离世俗纷扰的世外桃源,但他对效率、速度、利润、成本等方面的强调使我们相信吐温并非是忘忧不返的普通游客,他所肩负的政治使命使他从抽象、机械、冰冷的线性时间角度观察和评价夏威夷人生活和劳作的时间节奏,将线性时间观置于自然循环时间观之上。 蒸汽轮船使美国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夏威夷,他们不仅迅速用资本侵占夏威夷土地、建设种植园,而且他们带来的疾病导致夏威夷本土居民大量死亡,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人口结构。1778年库克船长发现夏威夷群岛时,这里人口至少有30万左右,但不断涌入的白人带来了诸多夏威夷人无法抵御的疾病,流感、天花、麻疹、水痘、麻风病、肺结核等疾病,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夏威夷人口死于非命,到了19世纪末美国兼并夏威夷时,这里的人口减少到不足四万人。⑩然而吐温却在演讲中指出,夏威夷人正以“令人欣喜的速度锐减”,他们“从生意场上急流勇退”(11),而快速轮渡会帮助美国人实现向夏威夷的“移民和永久定居”(Mark:21),美国人会取代夏威夷人成为这里的主人。在吐温看来,疾病让夏威夷人迅速从其领土上消失,乘坐现代交通工具而来的美国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夏威夷的新主人。在此,吐温非但没有对夏威夷人口数量的迅速减少表示出丝毫的同情,反而因为夏威夷人以死亡的方式将丰富的物质资源拱手相让而沾沾自喜。学者卡伦认为,吐温作为讽刺大师很有可能是在演讲中以反讽的语气谴责美国人给夏威夷社会带来的破坏(12),但笔者认为,结合吐温来访夏威夷的政治使命和他在发回国内的书信报道中表露出的对夏威夷资源的强烈渴求,吐温在此处暴露了他作为殖民主义者占领夏威夷的企图。而且就算吐温在演讲时的本意的确是用调侃的口吻讽刺美国人,那么他在实际演讲中也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他在演讲中流露出的浓烈殖民主义情绪使当时的美国听众相信吐温是在尽自己所能鼓动他们尽快前往夏威夷,正如一位美国听众在现场聆听了吐温于1873年在纽约史坦威艺术厅进行的一次演讲后写道,吐温“相信蔗糖,他用最强有力的言辞鼓励他的听众立刻到夏威夷去种植甘蔗”(13)。 二、庆典空间的殖民化生产 美国人不仅用资本主义逻辑和生产模式操控土地买卖、蔗糖生产、产品销售、效率管理等生产性领域,还通过规训夏威夷人的庆典活动来影响他们的生活体验,利润规则在种植园空间之外的非生产性领域中也获得统治性地位。列斐伏尔指出,节庆活动能够让人民暂时摆脱既有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和僵化的阶级关系,因为节庆的“非(日)常”特性可以消弭现代社会的生活异化,其中蕴藏的颠覆社会的革命能量可以促发批判日常生活与改造现代社会的革命实践。(14)列斐伏尔的节庆(festival)观点源于巴赫金对民间狂欢节(carnival)的认识,节庆和狂欢节在他们的理论范畴中都指涉不同于日常作息和一般场合的、具有庆祝性质的特殊活动。在夏威夷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列斐伏尔和巴赫金的节庆理论讨论范畴可拓展至范围更为宽广的“庆典”活动,不仅包括氛围欢欣愉悦的节日庆祝活动,还包括性质严肃的典礼仪式。夏威夷百姓参与的传统节日活动和夏威夷官方组织的典礼仪式能够延续和发扬夏威夷的传统民族文化,有助于削弱美国人在夏威夷的影响力。美国人意识到夏威夷的庆典活动阻碍了他们对夏威夷的操控,因此不遗余力对其进行压制,用体制化凝视将庆典中夏威夷人灵动的身体禁锢在狭小封闭的空间范围内,用严肃的身体牢笼让他们与周边世界的关系不断陌生化。 吐温描写了夏威夷传统周六节庆活动的盛大场面,“镇上所有的夏威夷人都停止工作……白人必须待在房间中,因为冲锋的男女骑手占据了每条街道,想要毫发无伤地穿过人群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下午,当地人聚集到小镇周边的开阔地,沉溺于他们传统的娱乐和消遣活动,在赌马场上输光一周的收入。那时有两三千名,有人说有五千名疯狂的骑手一起在原野上疾驰”(Mark:70)。周末节庆活动使夏威夷人暂时摆脱辛苦的劳作,从封闭的工作生活场所倾巢而出,涌入开阔的广场空间中充分享受身体的自由。他们挑战了白人以利润生产为目的的空间占有和控制方式,迫使白人放弃他们据为己有的场所,走进狭小的封闭空间中。夏威夷人用身体空间实践重构了被抽象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他们在欢庆活动中逃离了“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15),这样的传统节日正是巴赫金极力推崇的民间狂欢节。因为周末庆祝活动严重影响了夏威夷的生产和白人的利益,美国传教士和种植园主通过传教布道、施加政治压力等方式迫使当地政府设立法规将活动取缔。虽然吐温对周六节庆活动的消失表达了淡淡的惋惜,但他也更多地表示出了对这一举措的认同。 草裙舞是庆祝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但这一传统舞蹈在吐温男性目光的凝视下却成了“点燃男人欲望”的“淫荡舞蹈”,一群搔首弄姿的异教荡妇“发出最为奇异的猫儿叫春似的喊叫声”(Mark:168),充分展现了夏威夷当地女性的放浪不羁。吐温主观臆断草裙舞演员的肢体动作含义,曲解传统舞蹈的目的和文化象征意义。实际上,草裙舞演员用富有节奏的吟唱和律动的肢体语言在传承夏威夷的口头文学故事,空间中充满活力的身体释放出生命能量,消除了人对周边世界的恐惧和隔膜,促成了人与人、自然和神灵的沟通与交流,实现了巴赫金所说的“自由而亲昵的交往”(16)。吐温却将草裙舞视为纯粹以引诱异性为目的的表演,这与夏威夷美国传教士的观点不谋而合。传教士认为草裙舞演员暴露的着装和对性爱直言不讳的演唱内容低俗、野蛮,与基督教清教主义思想背道而驰,他们以此为由极力主张通过立法取缔草裙舞的公开表演。揭开虚伪的宗教面纱,传教士的真实意图是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传教士及其后代在土地改革中不仅在夏威夷政府谋得要职,而且成为坐拥万亩良田的种植园主,他们担心的是夏威夷人过于沉溺于观看或参与草裙舞表演而“滋生懒惰和恶习”,从而导致种植园劳动力的不足。(17)吐温已然向美国读者表明夏威夷种植园产品能够弥补国内的物质资源不足,夏威夷人也能成为内战后替代黑奴的遵规守矩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任何影响夏威夷人工作效率的因素必然也使吐温忧心忡忡。虽然夏威夷政府迫于传教士的压力,在1859年吐温抵达夏威夷之前就已颁布禁止草裙舞公开表演的禁令,但吐温对草裙舞的刻意曲解有助于在美国读者中丑化这一传统舞蹈形式,促使美国人继续向夏威夷政府施压以尽快推进法令的实施,从而为种植园和美国经济复苏提供足够的劳动力。 美国人不但竭力操控夏威夷的节日庆祝活动,还利用政治和宗教权力影响和改造夏威夷的传统典礼仪式。吐温详细描述了1866年夏威夷公主卡玛玛鲁(Kamamalu)的葬礼盛况。虽然夏威夷皇家禁止外国人观看典礼仪式,但吐温等美国人“非常好奇,想要看看这些围墙内发生的事情,看看那里正在进行的异教恶行”,所以他们多次违反禁令,乔装打扮闯入王宫,最终得以观看葬礼仪式上“野蛮的场景”(Mark:161-162)。吐温所言的“异教恶行”和“野蛮的场景”是指夏威夷皇室成员去世后,人们用草裙舞和彻夜痛哭等形式哀悼亡者。传教士到达夏威夷之前,除了上述悼亡形式,国家法律规范在人们服丧期间也会暂时失去效力,全国出现赌博、偷盗、纵火、淫乱等犯罪行为。吐温赞扬美国传教士到来后教化夏威夷民众用西方“文明的”殡葬仪式取代了“野蛮的”传统仪式,使这种无政府主义仪式得以销声匿迹(see Mark:131-132)。 改革夏威夷殡葬仪式具有进步意义,制止了特别时期非理性行为带来的秩序混乱,确保了国家法规的有序执行,但吐温和美国传教士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衡量夏威夷传统殡葬仪式,并用“野蛮/文明”的二元分类方式为夏威夷和西方哀悼形式贴上了标签。他们忽视夏威夷典礼仪式的传统文化象征意义,主张不加选择地废除包括草裙舞在内的所有哀悼形式。夏威夷人相信死亡是重要的“过渡仪式”(rite of passage),亡者正经历从世俗物质世界过渡到冥界的阈限阶段,此时普通民众需要参与到首领的葬礼中共同控制亡者体内危险的超自然力量,引导亡灵顺利完成过渡仪式。(18)规模盛大、形式多样的葬礼仪式让生者宣泄悲伤和紧张情绪,适应首领和亲人去世带来的重大变化,是夏威夷民族应对死亡带来的社会变动、维系民族稳定、增加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吐温和传教士不顾传统葬礼仪式的重大意义、执意将其取缔的深层原因其实出自美国人担心会失去对夏威夷整体社会的控制。 吐温引用美国学者贾夫斯(James Jarves)的词语“狂欢”(saturnalia)来描述夏威夷葬礼情形(see Mark:131),此词原意为古罗马每年年末举行的农神节,是民间纪念负责播种和收获的神灵的狂欢节。巴赫金认为农神节是最具狂欢性质的节日,它使人们脱离现有等级、道德价值、规范、禁令的“固定性、不变性和永恒性”(19)。我们可以推断,夏威夷葬礼仪式在美国人眼中如同古罗马狂欢节,因为正常的社会秩序和行为准则被打破,原有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别被消除,危险的反叛因素由此孕育而生,从而随时有可能脱离美国传教士的掌控而带来政治上的革命。因此,虽然大规模的葬礼仪式对于夏威夷本国政府来说具有正统官方典仪性质,但对于觊觎夏威夷政权和资源的美国人来说却是具有民间性质的反官方、反权威活动。吐温本人使用“国家狂欢”(national spree)来形容葬礼场面(see Mark:132),这表明他意识到了葬礼仪式涉及广阔的空间范围。周末节庆是在广场空间中有局限性的小范围活动,夏威夷盛大葬礼却是超越广场空间、几乎全民参与的全国性仪式。如果说对周末节庆的控制源于美国人对种植园工人工作效率的担忧,那么有理由相信,对葬礼仪式的操控则是出于美国人对夏威夷人民颠覆性反抗力量的恐惧,因此美国人必然竭力遏制夏威夷殡葬仪式中的狂欢性,剥夺其合法性,消除其“非(日)常”特性。 在美国人权力目光的长期凝视下,夏威夷葬礼仪式的规模和形式早已发生了巨大改变,皇家葬礼已经从全国范围缩小到仅在夏威夷王宫中的小块空间中进行的简单仪式。吐温在公主卡玛玛鲁葬礼上目睹的草裙舞和痛哭哀悼只是夏威夷传统殡葬仪式的暂时复兴,夏威夷皇家希冀以此恢复传统文化,遏制美国传教士在政府中的力量。在王宫有形宫墙的保护下,夏威夷的传统殡葬仪式得以恢复,王宫内外形成了互相竞争、互相冲突的异质权力空间,美国势力在夏威夷多年来苦心经营树立的权威遭受挑战。但位于王宫之外的吐温等人却无视夏威夷殡葬禁忌,执意打破有形的空间壁垒,用规训的眼光窥视夏威夷文化,试图铲除重新萌芽的传统仪式。随着美国人在夏威夷势力的日益强大,葬礼仪式终究没有逃脱消亡的命运,夏威夷民众不得不转而接纳西式葬礼形式来应对死亡给个体心灵和社会整体带来的动荡。 三、神圣空间的殖民化生产 柴德斯特等人指出,空间的“神圣性”(sacredness)并不是某一处所的固有属性,而是人们用权力控制、征服、挪用、剥夺、排斥的结果,是人为生产出来的产物。(20)因此,神圣空间是“竞逐空间”(contested space),不同群体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经济或宗教目的在神圣空间中进行权力角逐,争夺空间神圣性的阐释权和对空间本身的控制权与所有权。19世纪初期,夏威夷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西方各国宗教势力趁机涌入。(21)吐温抵达夏威夷时,美国传教士在这里已经建设起为数众多的基督教教堂,并在教堂物理空间占领的基础上,通过讲经、布道、组织群众聚会、举行宗教仪式、编纂并散发宣传材料等方式进行神圣空间的隐喻性生产。吐温在书信中多次提及夏威夷地区的教堂、庙宇等宗教场所,他褒赞美国基督教堂,向读者宣扬基督教的正统性,帮助构建并加强基督教教堂的神圣性,同时贬损夏威夷庙宇和其他国家所建的宗教场所,质疑夏威夷传统宗教和其他国家的宗教派系存在的合理性,削弱甚至消解夏威夷传统宗教庙宇和其他国家宗教场所的神圣性,竭力帮助美国人在殖民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夏威夷庙宇(Heiau)曾经是当地人举行祭祀仪式、祷告祈福的重要场所,在传统文化中具有至高神性,但1820年后逐渐被美国传教士建立的基督教教堂所取代,沦为被弃置荒野的断壁残垣。当吐温一行抵达夏威夷时,轮船伴随着六个教堂的悦耳钟声驶过狭窄的河道。他如此描写道:“浑厚低沉的钟声传到远方,越过山丘峡谷,而50年前那里还遍布着赤身裸体、粗鲁原始、喧声震天的野蛮人!在距离异教庙宇遗迹五英里范围内有六座基督教教堂,上个世纪那里还每天举行用人肉祭祀邪神的仪式。87年前,其中一个岛屿上一群凶残居民围攻绝望的库克船长,置其于死地,我们距离那里仅有一射之地。看,他们的后代进了教堂!看看传教士的功劳吧!”(Mark:26) 吐温在引文中将美国传教士建立的基督教教堂与夏威夷的传统宗教庙宇进行比照,用空间两分法把前者界定为正统宗教场所,而后者则是异教领地。吐温强调基督教教堂与夏威夷庙宇遗迹相距不远,是想用后者的破败衬托前者的繁盛,赞扬教堂对夏威夷庙宇的成功的空间取代。与此同时,吐温将空间场所与人的品性相关联,是在暗示在基督教教堂里祷告的教徒信仰正统、节制有礼、文明进步,而庙宇中秉信传统宗教的夏威夷人崇拜邪神、滥杀无辜、凶残野蛮。显然,吐温意在使读者相信,人们活动空间的变化标志着内心道德品性的改变,传教士的“功劳”在于他们让夏威夷人走出庙宇、走进教堂,使他们从野蛮人转变为文明人。吐温在文中提及的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是首位登陆夏威夷群岛的欧洲航海家,1779年在与当地人的冲突中死亡。虽然吐温在后来的信件中详细描写库克在夏威夷招摇撞骗、违背禁忌、亵渎神灵的种种行为,总结出是库克的不当行为导致了他与夏威夷人的冲突(see Mark:215-221),但笔者认为吐温在此处将库克的死归罪于夏威夷人的野蛮愚昧,目的是以此证明夏威夷人曾经的凶狠野蛮,突出传教士给夏威夷带来的改变,强调在夏威夷建设基督教教堂、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吐温在1873年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信中宣称,所有的夏威夷人都已皈依基督教,他们热衷教会活动,沉迷于圣经与赞美诗的学习。(22)但根据夏威夷计划与经济发展部统计员史密特提供的数据,从1825年至1870年,皈依基督教的夏威夷人从10人增至14,850人,仅占夏威夷全部人口的25.1%。(23)我们有理由推断,吐温夸大的表述体现了他向美国读者报告传教士卓越“功劳”的急切心情。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吐温的信件是大部分美国读者了解夏威夷情况的主要渠道,因此吐温的报道可使美国民众相信“野蛮的”夏威夷人已被教化为“文明的”基督教教徒,减轻国人对夏威夷人的排斥心理,为美国未来兼并夏威夷争取更多的国民支持。吐温虽强调众多夏威夷人已皈依基督教,但也多次暗示他们随时可能背弃基督,转向本族原始宗教。夏威夷议会主席如今“着装整洁大方、品德高尚、气质优雅”,是“欧洲王室的座上宾”,然而不久之前他曾经“如同婴儿一般赤身裸体,拿着矛枪和棍棒,带领一大群野蛮人与其他的蛮族搏斗,恣意屠杀”(Mark:108)。吐温刻意对比议会主席皈依基督教的前后状态,意在凸显基督教强大的教化作用,但同时也暗示从“野蛮”到“文明”仅有一步之遥,夏威夷人随时可能倒退回原始状态,他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民主政府和文明社会,夏威夷需要美国人的协同治理,这就将美国人殖民夏威夷的可能合理化了。 除了夏威夷传统庙宇,吐温在信中还数次提及英国人所建教堂。吐温对英国神职人员斯泰利(Thomas Staley)建立的夏威夷改革天主教堂(Hawaiian Reformed Catholic Church)大加批评,他否认该教堂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指出斯泰利的教堂不同于传统天主教、圣公会教和清教,缺乏存在的宗教理论基础,是“神奇的发明”(Mark:173)。在吐温看来,教堂内部空间布局拥挤简陋,装饰庸俗不堪,悬挂的宗教绘画“拙劣简陋”,刻有经文的华盖如同“淋浴棚”,可能用于盛装圣水的贝壳被吐温视作教堂向人索取钱财的用具,他认为这“不符合空间的神圣性”,“想到这样糟糕的环境就感到极其痛苦”(Mark:174)。吐温承认这段描述有失恭敬,心有愧疚,但随即表示他不会对此进行修改,因为很可能改得更糟(see Mark:175)。吐温明知行文掺杂主观臆断甚至有刻意丑化之嫌,但他即使心中不安,也不愿修正,这种与作家客观描写职业原则相悖的固执源于吐温希冀美国在殖民竞争中胜出的民族主义情绪。 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众多美国传教士在夏威夷政府中担任顾问和专家,参与国家各项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他们的力量远远超过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在夏威夷政府中的势力,几乎控制了夏威夷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1852年,美国传教士建议夏威夷皇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变君主制为共和制。夏威夷国王随后辞退政府中大部分美国人,邀请英国宗教人士斯泰利和其他一些英国人任政府要职,支持他们在夏威夷建立英式教堂。美国人认为夏威夷国王此举的目的是借英国人的力量震慑美国传教士,维持皇室的统治地位。因此笔者推断吐温不顾作家忠实描写的职业操守,尽其可能贬低斯泰利的教堂,使神圣的教堂空间尽失庄严,其意图是通过消解英式教堂的神圣性来削弱斯泰利在夏威夷的权力地位,进而排斥英国人在夏威夷的政治和宗教势力,增加美国人在夏威夷的影响力,帮助美国人实现对夏威夷的彻底掌控。 吐温认为夏威夷民众早已浸润在美国清教精神之中,无法接纳华而不实的英式教堂,甚至断言美国人不仅已经控制了夏威夷的宗教,而且岛上有利可图的农业、商业和贸易也都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夏威夷的政体实质上已经由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制。斯泰利的教堂受到如此局限,以至于教堂中仅有的三百座位容纳他的所有信徒也仍然绰绰有余(see Mark:173)。吐温使用的“局限”(circumscribe)一词具有强烈的空间感,表达了美国人的影响力已经渗透进夏威夷社会的各个方面,斯泰利的教堂只能偏安一隅,无法增加教堂的空间面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吐温在1866年写下上述文字时美国人还在同英国和法国竞争对夏威夷的控制权,美国在殖民竞争中并未胜出,而美国人所提议的政体改革也未实施,美国势力与夏威夷皇室之间仍在进行权力博弈。但吐温迫不及待地声明美国人已经掌权,夏威夷政体已转变为共和制,这足以显露吐温的殖民主义野心,他的目的是用夸大的事实震慑对夏威夷虎视眈眈的英国人,帮助美国人巩固在夏威夷的社会地位,推动传教士主导的夏威夷政体改革。 法国哲学家勒南曾经说过,“遗忘甚至是历史性的有意误记,是型塑国族的关键因素”(24)。南北战争成功废除了奴隶制,为了构建统一的美利坚民族、缓解在战争中暴露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美国转向夏威夷进行殖民空间生产,用资本主义利润原则规训夏威夷人的身体,榨取他们的劳力,控制他们的庆典活动,消解夏威夷传统宗教空间的神圣性,侵占夏威夷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将夏威夷人的生活空间抽象化为构想空间。 马克·吐温通过他的书写和言说以文学的方式推进了这一过程,这遵循了美国政治统治者、经济利益获得者和权力规划者的思维逻辑,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满足了美国读者的期待,为美国的民族性记忆缺失提供了合理化阐释。因此,当吐温于1866年7月从檀香山返回美国旧金山时,他发现夏威夷系列报道已使自己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转变为美国的主流作家之一。(25)尽管吐温对美国人时有批评,但他的真正用意并非谴责美国对夏威夷自然资源的随意取用和对夏威夷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恣意改造,而是借由美国人在夏威夷的行为讽刺美国国内的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每当美国人在夏威夷的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时,吐温必然义无反顾地站在美国人一边。虽然吐温于20世纪初期当选“美国反帝国主义联盟”副主席,公开反对美国等国的侵略行为,但吐温也坦承自己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曾经为美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擂鼓呐喊,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帝国主义者”(26)。在吐温等众多美国人的不懈努力下,美国最终在19世纪末兼并了夏威夷领土、霸占了夏威夷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建立“太平洋帝国”做好了准备。 ①See 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trans.Frank Bryant,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78,p.21. ②See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Donald Nicholson-Smith,Cambridge:Basil Blackwell,1991,p.53. ③See Mark Schmitz,"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uthern Cane Sugar Sector:1860-1930",in Agricultural History,vol.53,1(1979),p.272. ④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Cond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Cane Sugar Industry,Special Report 1,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77,p.19. ⑤Judith White McGuire,Diary of a Southern Refugee during the War,by a Lady of Virginia,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5,p.257. ⑥See Barry R.Rigby,"The Origins of American Expansion in Hawaii and Samoa,1865-1900",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0(1988),p.222. ⑦See Mark Twain,Mark Twain’s Letters from Hawaii,ed A.Grove Day,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5,p.vii.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⑧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收入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⑨See 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John Moore,vol.2,London:Verso,2002,p.48. ⑩See Haunani-Kay Trask,From a Native Daughter:Colonialism and Sovereignty in Hawaii,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99,p.6. (11)吐温在美国进行夏威夷主题巡回演讲时,会根据听众的不同调整演讲内容,所以他的演讲有多个不同版本,此段文字来自由弗瑞德·洛奇(Fred W.Lorch)整理的1869至1870年期间吐温在美国东北地区的演讲(see http://etext.virginia.edu/railton/onstage/savlect.html)。 (12)See James E.Caron,"The Blessings of Civilization:Mark Twain's Anti-Imperialism and the Annexation of the Hawaiian Islands",in Mark Twain Annual,vol.6,1(2008),pp.51-63. (13)Qtd.in David Zmijewski,"The Man in Both Comers:Mark Twain the Shadowboxing Imperialist",in The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40(2006),p.60. (14)See 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trans.John Moore,vol.1,London:Verso,1991,pp.200-207. (15)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玲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 (16)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第212页。 (17)See Noenoe K.Silv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nning the Hula",in The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34(2000),p.36. (18)索厄尔用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1960)和特纳(Victor Turner,1969)的过渡仪式范式来研究夏威夷人的殡葬风俗,过渡仪式分为分离、过渡、聚合三个阶段(see Teri L.Sowell,"Spiritual Remains:Hawaiian Funerary Rituals and the Legacy of Robert Hertz",in Le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Océanistes,124[Année 2007-1],p.4)。 (19)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20)See David Chidester and Edward T.Linenthal,"Introduction",in David Chidester and Edward T.Linenthal,eds.,American Sacred Spa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17. (21)关于夏威夷宗教体系的嬗变过程,详见Jennifer Fish Kashay,"From Kapus to Christianity:The Disestablishment of the Hawaiian Religion and Chiefly Appropriation of Calvinist Christianity",in The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vol.39,1(2008),pp.17-39。 (22)See Mark Twain,Mark Twains Letters,vol.5,Lin Salamo and Harriet Elinor Smith,ed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560. (23)See Robert C.Schmitt,"Religious Statistics of Hawaii,1825-1972",in Hawaiian Journal of History,vol.7,10 (1973),p.42. (24)Ernest Renan,"What is a Nation?",in Homi K.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London:Routledge,1990,p.11. (25)See Mark Twain,The Autobiography of Mark Twain,ed.Charles Neider,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59,p.157. (26)Everett Emerson,The Authentic Mark Twain:A Literary Biography of Samuel L.Clemen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4,p.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