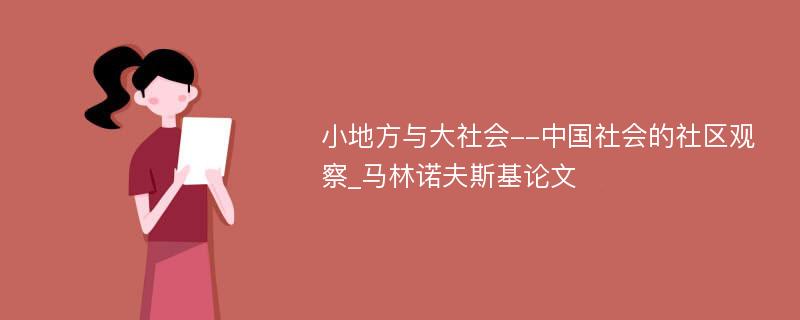
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地方论文,社会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描述了社区研究在中国引进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50年代以后关于“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这种对社区研究的批评意见,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力图从新的角度对汉人社区进行研究。实际上,社区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自身的重要价值。然而,小地方的研究与对大社会的理解,二者间的关系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以社区为视角观察中国社会,曾经被早期社会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当做方法论的立业之基。1935年,吴文藻先生曾说:“‘社区’一词是英文community的译名。这是和‘社会’相对而称的。我所要提出的新观点,即是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社会是描写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的。”[①a]
50年代以后,社区研究法被欧美汉学人类学界引以为方法论反思的对象。首先,一些学者对社区研究法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之后,一大批从事中国社会具体研究的人类学者又以新的角度对汉人社区进行不同的论述。他们所力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小地方的研究与大社会的理解之间到底有何关系?这个问题的提出,对于汉学人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对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来说,一如吴文藻先生所言,社区无疑是田野调查的可观察单位,但是这种单位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如何?怎样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小单位透视“复杂的”中国社会?则是他们历来无法回避并贯穿于本世纪汉学人类学(sinological anthropology)[②a]史的大问题。
社会整体观的兴起
本世纪20至40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在功能主义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方法论的革新时代,这个革新时代与“社区”概念的出现关系十分密切。在功能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提出来的本世纪20年代以前,人类学者沉浸于远古的历史之中。19世纪后期,欧美人类学者在受进化论的制约,广泛地收集第二手的人文类型素材,依据传教士和冒险家所写的没有被证实的游记,“猜测性地”构造宏观的世界文明史。20世纪初期,在德国文化传播论和美国历史具体论的相继出现,在表面上对进化论提出一个理论挑战,而在方法论上仍然没有摆脱旧有宏观人类历史的影响,保留对宏观的抽象历史的过分强调。直到20世纪,功能主义理论出现后,人类学的方法论才开始从宏观人类历史中分化出来,进入实地研究与社会理论化的时代。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被公认为是这一人类学方法转变的首倡者之一,他对以前的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方法论批判。他说:“在我看来,它们(进化论、文化传播论以及历史具体论)抑或在进化的阶段问题上绕圈子,抑或在这种或那种文化现象如何传播问题上索求来龙去脉……而对于界定和联想文化因素在文化事实中的运作没有赋以充分的重视。”[①b]为了克服这一方法论弱点,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类学者不应把物质文化、人类行为、信仰与理念分割开来进行分别的排列组合,而应把它们放在“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s)或所谓的“分立群域”(isolates)的整体中考察,展示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关系。马林诺夫斯基所讲的“文化事实”和“分立群域”,后来成为社会人类学社区研究法的基础,指的就是在一个方法论优先的整体分立社区,或“田野工作”(fieldwork)的社会空间单位。
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社会人类学者如摩尔根(Morgan)、波亚士(Boas)以及里弗斯(Rivers)已经开始田野作业,但当时的田野作业方法很不成熟,对大多数人类学者来说,研究的依据依然是生活在被调查社区的传教士的笔录。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田野工作地点没有加以“分立群域”的界定。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作业,与以往的作法形成相当鲜明的对照。他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特洛布里安德岛),与几乎所有社区成员成为熟人,对他们的活动规律和细节了解甚为深入,他的调查具有“直接观察”、重视民间生活和民间知识、亲自参与等特点。他认为通过在分立的小型社区的长期的直接参与观察,社会人类学者才可能对当地社会进行全面考察,并把当地社会的家庭、经济、法权、政治、巫术、宗教、技术等行为特质放在一个整体里加以分析,解释为什么社会形成一个难以切割的整体,避免像古典人类学家那样切割文化。
在这种理论思考前提下开创的社会人类学传统,十分重视对在时空上严格界定的单个社会中的人文生活的描写。马林诺夫斯基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划分为“文化”(即由各种用具、物品、社会团体、观念、技术、信仰、习惯等人类创造物所合成的整体)和“人的基本需求”(即人的新陈代谢、繁殖、舒适、安全、行动、生长、健康等需要)。他认为社会人类学者的使命,在于通过田野调查理解人的文化性、制度性的活动与人的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人类学者赖以理解这种关系的工具,是“功能”(function)的概念。所谓“功能”,指的是文化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方式,或满足机体需要的行动。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
诚然,这种功能主义方法论有它的理论局限性。但是,它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意义却是不可磨灭的。对于太平洋岛屿、非洲等地的“简单的”原始民族来说,社区调查法几乎成为“文化科学”(人类学)的唯一原则。
在20世纪以前,中国文化在人类学者眼中,被放在全球文明史中,作为“古代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史”的“残存”加以论述,它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科学意义,被进化的阶段论所抹杀。19世纪后期,荷兰人类学家兼汉学家德格鲁特(De Groot)在闽南地区的宗教调查,[②b]可以说已经具有“参与观察”的某些特征,但是其田野工作缺乏社区背景,而且解释框架仍是弗雷泽的进化论。直到本世纪初期,深受社会学派熏陶的法国汉学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解释中国文化时,还采用“上古史”的方法。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1925年,库尔伯(Daniel Kulp)在广东凤凰村的家族调查,在没有受过多少社会人类学的影响下,成为最早的汉人社区功能分析。[③b]不过,由于他只是“业余人类学家”,因此在人类学界所引起的关注十分有限。真正起着汉学人类学变革作用的,是一批受功能主义人类学影响的中国本土人类学家。在燕京学派的提倡者吴文藻的带动下,中国社会学者和社会人类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社区”和“功能派”展开大量的讨论。吴文藻本人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理论,提出对“社区”的系统化界说,主张“社区”是了解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单位,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关联而成的一个整体”,“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一个“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二者合并起来”的“社会体系”。[④b]在1934到1949年间,费孝通、林耀华等中国学者分别以英文发表一系列作品,均是在“社区论”和“功能论”的方法论前提下写成的,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⑤b]最典范地具有功能主义社区研究的色彩。
费孝通的社会人类学体系,不是单纯的“社区方法论”,而是结合了社区分析、比较研究法、应用人类学、社会结构论的复杂体系。不过,在方法论上,他强调以其1932年在燕京大学讲学的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Park)的“社区”(community)理论以及费氏的人类学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分立群域”概念为立家之本。在一本常被西方人类学家忽视的著作《乡土中国》(1947)一书中,费孝通说:“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空间的坐落,这就是社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写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工作是比较研究,在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表现出来的结构的形式不一样。”[①c]
《江村经济》(英文书名为《中国农民生活》)一书是费孝通以小型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实验性范例。这本书除了前言之外,包括15章,论及调查区域、中国人的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畜牧业、贸易、资金及中国土地问题,它涉及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把经济、社会关系、仪式等方面的素材,以功能的整体观加以联想、概括及分析。费氏所用的叙述框架,直接来自于马林诺夫斯基,表现出对文化器具(即各种用具、物品、社会团体、观念、技术、信仰、习惯等人类创造物所合成的整体)与人的基本需求的相关性的充分关注,并且以他的姐姐帮助农民建立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为例,探讨与技术引进相关的社会变迁动力。
他的这一表述,与当时中国其它人类学阵营仍然十分尊崇的进化论、传播论、历史具体主义形成很鲜明的对照。与其他人类学者不同,费孝通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结构与社会形式,而不是人类的历史、远古社会,他从事人类学研究不是为了从现时代可观察到的事实,推知远古社会的风俗和制度,而是为了以功能的角度解释中国社会的基质和社会变迁的动力。社区研究不是他运用的唯一方法,但是它是费氏切入中国社会的“时空坐落”,“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②c]
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写的“前言”中预言,费孝通的作品是社会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他为此举出三个理由:第一,费著将促使人类学从简单的“野蛮社会”(the savage)走向复杂的文明社会;第二,此书将开创本土人类学的发展途径;第三,《江村经济》注重探讨社会变迁,将会有益于人类学应用价值的推进。以社区为研究视角的《江村经济》的确成为汉学人类学的里程碑,因为它不仅成为一个时代社会人类学的描述文体范本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汉学人类学界对方法论的讨论。
“代表性”问题的提出
马林诺夫斯基在特洛布里安德岛的社区调查,无疑是人类学职业性实践的典范。他以具体的个案论证了社区民族志(community ethnography)对于理解传统人类学探究对象—简单的非西方族群—的作用。不过,当他说费孝通因为研究本土的“文明社会”及其变迁,而促成人类学研究取向的转变时,忽略了一个后来引起争议的问题(不过,对于这个问题,费孝通早已加以重视。在江村研究之后,他开展了“云南三村”社会经济模式比较研究,并在理论上对中国社会与发展进行超区域的论述):那就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与简单的“野蛮社会”有深刻差异的“复杂文明社会”进行社区分析,是否能体现中国社会的特点?换言之,社区研究针对的是小地方,在大型的文明社会中,小地方无疑也是大社会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们是不是可以被视为大社会的“缩影”(microcosm)?
对这个问题,社会人类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类学者从人类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肯定功能的社区分析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他们关注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社区在人类学描述(即“民族志”或“ethnography”)中的作用。因此,对他们来说,汉人(中国)社区研究只要能够提供符合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与描述方法标准,就是“成功”的研究。采用这种看法的人类学者,以利奇(Edmund Leach)为代表。
在《社会人类学》(1983)一书中,利奇上面提及的四本中国人类学家的英文著述,以功能主义民族志的标准加以一一评判,认为林耀华的著作运用的是小说,而不是人类学的描写手法,杨懋春的著作采用落后的民族学方法,把中国的社区描写成“原始部落”,缺乏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视角,许烺光对“西镇”的研究,类似社区调查,但是声称“代表整个中国”,因此也是失败的例子。他认为,在这四本作品中,最成功的是费著《江村经济》,因为它与别的描写方法(小说)形成明显的对照,避免了早期民族学的方法论缺陷,而且不声称是中国社会的“典型”。利奇说:“费著的优点在于他的功能主义风格。与社会人类学者的所有优秀作品一样,它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关系网络如何在一个单一的小型社区运作的细致研究。这种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自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它们也不是为了阐明某种一般的论点和预设的。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本身。虽然这种作品以小范围的人类活动为焦点,但是它们所能告诉我们的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其内容远比称为‘文化人类学导论’的普通教材丰富博大。”[①d]
虽然利奇一再说明人类学描述不应有任何“一般预设”,但是他在本质上是一个“普遍论者”(universalist),因而主张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意义,与“中国社会”的特征无关,而仅仅是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的泛论。这一看法,与费孝通的本意显然是违背的。在对利奇评论的回应中,费孝通多次提到,他的理想是“了解中国社会”,而不是发现人类行为与文化的一般规则。第二种评论针对汉人社区研究与“中国社会”的相关性而展开。这种评论与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的“社会结构”概念及其后来的变异有密切的关系。布朗本人也曾应吴文藻的邀约到燕京大学讲学,他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方法论,而在于理论方面,他是把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导师杜尔凯姆(Emily Durkheim)的社会理论引进社会人类学的学者。从费孝通本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功能的社区描写方法之外,“社会结构”的概念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与许多汉学人类学者一样,他的作品表现出一代本土人类学者对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旨趣。我们可以说,第二种评论更符合他的研究旨趣。
1962年,英国人类学家兼汉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马林诺夫斯基纪念讲座宣读一篇称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论文,对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前言中的预言作出热情的回应,并且对于汉学对社会人类学所能作出的具体贡献作出了明确的解说。弗里德曼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点共识是,中国社会的研究存在着把人类学从原始部落推向文明社会的潜能。但是,至于这种研究应该如何开展才可以达到这一目标,他与马林诺夫斯基不能形成共识。他认为,功能主义者在宣扬社会人类学社区调查法的有效性,是忘记了“有历史的文明社会”是中国社会与传统人类学研究对象不同之根本所在,在这样一个有历史的、有社会分化的文明大国,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和共时性(synchronical)剖析(即反历史倾向)不足以运用到中国的研究。
弗里德曼的批评是:马林诺夫斯基的以为,吴文藻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学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运用了小型社群研究法,而这种研究法在不同的村落社区反复实施,[②d]便可造成对整体中国社会的理解;实际上,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之所以如此看,是因为他们原来十分习惯原始部落的研究,一进入如此之大的中国社会,他们不免觉得无计可施,“为了方便”,不得不把无法驾驭的大中国分割为可以用传统社区方法分析的“村落”。弗里德曼主张,假使人类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没有充分了解,进行再多的社区调查也无法说明问题。社会人类学要出现一个“中国时代”,首先应该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法,走出社区,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较广的时间深度中,探讨社会运作的机制。一言以蔽之,弗里德曼认为,小地方的描写无以反映大社会,功能的整体分析无以表现有长远历史的文明大国的特点,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
在50至70年代,由于对社区方法的批评以及被广泛地意识到的田野调查机会的失去,主要的汉学人类学者从小型社群研究转向较为大型的社会史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弗里德曼本人利用史料、旧的社会调查资料、海外华人研究,构造出明清以后至民国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族组织的结构分析,并试图以这一侧面反映中国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学者施坚雅(G.Whlliam Skinner)几乎成为历史学家,他利用清史资料和经济区位的理论,对中国农村的区系和都市化进行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在理论上,他们的研究受新的社会科学概念的影响。但是,在方法论上,颇有回归历史具体主义时代的意味。
社区研究的新试验
弗里德曼对汉学人类学作出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指出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应注重探讨历史与现代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力图在这种探讨中提出适应于中国、与原始民族研究不同的方法论。毫无疑问,他提出的历史的、宏观的社会学方法,对于社区方法是一个补充。但是,他的论点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大问题是:为了体现中国社会中的历史与社会复杂性,我们是否一定要抛弃社区方法?换言之,社区方法是否像他说的那样,无法体现历史深度和国家—社会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考察弗里德曼以后汉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
在弗里德曼进行田野调查的时代,中国的社会空间坐落对西方学者是封闭的,因此他只能在新加坡的海外华人社区做实地研究,正如他本人在许多文论中承认的,他的理论和方法的提出与田野调查机会的缺乏有密切关系。但是,6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初步的变化。首先,英国人类学家沃德(Barbara Ward)在香港的渔村开发了田野地点,重新采用社区研究方法,对汉人社会的特点加以新的分析。稍迟,由于港台地区田野地点的开放,弗里德曼的学生裴达礼(Hugh Baker)在新界以他导师的模式研究村落宗族组织,另一个学生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在台北县的村落中研究汉人宗教,美国学者帕斯特奈克(Burton Pasternak)、马丁(Bmily Ahern)等在台湾验证和批评弗里德曼宗族模式。此外,美国人类学家葛伯拉(Bernard Garlin)、武雅士(Arthur Wolf)等先后在台湾进行村落调查。70年代中期,对中国的社区人类学调查也逐步发展起来。起先,一些人类学者不得已利用广东在六七十年代在港移民的访谈和短期访问,了解中国村落社区生活。1974年以后,长期的调查逐步成为可能。
60年代以来,在港台和大陆所做的社区调查,有的保留整体论民族志(holistic ethnography)的原则,但是大多表现出对新的实验旨趣。依照这些研究的主题,我们可以把社区人类学的新实验分为如下几类:
“范式”的社区验证
在传统上,社会人类学小型社区研究的发明,本来不是为了提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案例,而是为了通过个案的验证(case test)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流行观念加以评论和反思。马林诺夫斯基在太平洋岛民社区调查中,收集到关于文化和制度的综合性素材,但是并没有把这些素材处理成“代表”某个社会的独特性的文本(text)。相反,在其所著的七部关于特洛布里安德岛的民族志作品中,马林诺夫斯基反复地对不同的社会和行为理论进行反思。例如,在《原始社会的性生活》(1932)[①e]一书中,他对特洛布里安德岛民的性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密切关系加以考察,指出他们的冲动与情结受母权制的制约,不单是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动力”的反映论,因此当时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心理分析法不是普遍的真理。
弗里德曼提出社区研究法不足以概括“中国社会事实”,在很大意义上也是为了批评西方的社会理论范式,尤其是人类学界流行的“无国家的社会论”。[②e]但是,由于他过于追求“代表性”,因此没有看到社区法本身具有理论验证和反思的作用。在他的著作发表以后不久,不少学者为了思考他的宗族模式,回到社区研究的传统中,寻找论辩的证据。裴达礼、王斯福、马丁、帕斯特奈克等人在香港和台湾社区的调查均属此类,而最体现社区验证色彩的是帕斯特奈克的台湾两村调查和王斯福的台湾北部村落调查。
弗里德曼在他的两部作品中,以中国东南区为例,指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区域中的具体表现,造成宗族组织的发展。他认为,在中国东南区,宗族比其它地区发达,原因是该区是一个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陲地带”。带着弗里德曼的解释,帕斯特奈克于1964至1969年间两次在两个台湾南部社区调查,所发现的材料证明“边陲地带说”无法被验证。相反,他发现,单一宗族村和多元宗族村可以在不同场合存在,与中国东南的“边陲性”没有关系。王斯福的田野调查在表面上与宗教无关,但是实际上是为了通过一个社区实例反驳弗里德曼的说法。他在台北县一个山区村镇发现,弗里德曼所强调的那种单姓家族村并不存在,当地起社会组织作用的是地域仪式和家庭仪式。[③e]
模式交错的分析
在其它一些研究中,社区方法不足以反映大社会的看法也得到否证。上文提及的沃德在香港渔村的调查中指出,从一个单个的村落,可以探知汉人的传统社会认同或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所说的文化的“有意识模式”(theconscious model),是通过模仿上层的士绅意识形态、与邻村的交往、社区自我的定位而创设的。[①f]这意味着,通过社区调查,人类学者可以了解传统(历史)如何成为社会认同、不同的分立社会力量如何并存与互动、大传统如何与小传统糅合。70年代初,武雅士对村落中的汉人民间信仰的考察,说明中国社会的上层象征与民间象征可以在社区中得以透视。他发现,汉人社区中,民间信仰的体系是由神、祖先、鬼三类组成的,而在象征意义上,神代表“官”、祖先代表家族与社区、鬼代表“外人”和“下人”,这种神灵的分类体现中国农民经历的世界包含地方的、自上而下的和外来的社会力量。[②f]
在社区中发现不同观念、社会、象征的模式的并存,说明社区研究有潜力为阐明“复杂的中国社会”提供充分的素材。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社区研究需要摆脱功能主义的“分立群域”和文化整体论的框架,包容不同的社会力量,体现民间地方模式与官方超地方模式的交错。近年,在这一方面比较成功的试验是桑格瑞(P.Steven Sangren)的《一个汉人社区的历史与魔力》(1987)。[③f]与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其他汉学人类学者一样,桑格瑞无法在中国本土从事田野工作,他的调查对象是一个台湾的村镇。不过,在社区生活的描写中,他自觉地把所探讨的问题放置在“中国社会”中。他的书主要包含三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描写社区地方史和社会生活在超地方的“空间场域”(spatial context)中的地位,第二部分具体讨论地方性的民间仪式活动如何与大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联结,第三部分从中国传统宇宙观的角度解释汉人文化与行为的结构与实践。从而,桑格瑞的社区报告不仅是关于一个具体地点的社会生活,而且体现了中国社会中不同领域、观念模式、社会组织的交揉。
“社会缩影”的探讨
与“模式交错”并行不悖地,社区作为中国的“社会缩影”的方法论涵义也被重新提出。费里德曼问题和施坚雅的区系理论的提出,提醒汉学人类学界注意一个方法论的困境,那就是,社会人类学者所研究的小型社区一方面是大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说完整地“代表”中国现实,最多它们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迄今为止,这一论点仍然是不可反驳的。但是,不少学者已经逐步地在他们各自的试验中,通过社区窥视大社会。采用这种“窥视法”的学者对社区代表性的局限深有醒思,不过,在此前提之下,他们力图以充分的地方性描写,体现大社会的特征与动因。
如果我们可以把此类探讨称为“社会缩影”的探讨的话,那么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这种探讨的开创性作品,而后来的一些研究则以80年代出版的关于广东一村落的描写为代表。从1974年开始阿尼达·陈(Anita Chan)、安格尔(Jonathan Unger)、马德生(Richard Madsen)在香港对来自广东陈村的26位移民进行223次访谈。在当时中国尚未对外国人类学者开放田野调查地点的情况下,这一研究所收集的资料可算十分丰富。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资料本身,而是三位学者合著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民社区的现代史》(1984)[④f]以及马德生著《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与权力》(1984)。[⑤f]。
这两部著作利用同样的资料建构一个社区的社会生活史,虽然各具特色,但是探讨的是从社区中如何展示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中国人所经历的剧烈社会变革以及这些变革与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关联性。通过大量的访谈资料,陈村研究者成功地重构了一幅社会变貌与村落个人角色的图像,其叙述线路结合社区视角和社区中个人权力角色的生活史,所用的分析概念包括传统、话语、仪式、斗争等,两本作品均富有故事性。作者所讲述的故事,阐明古典中国对道德人和威严人的界说如何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被不同政治人物所运用,以及这种地方性的运用如何与全国性的政治权力模型相联系。在地方性生活史的描写中,作者从权力人格的角度,隐含了对近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解释,强调实用道德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持续影响,使《陈村》和《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明显地具有“中国社会缩影”的色彩。
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社区描写
考虑到中国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新的社区调查和描写的试验力图在“小地方”的社会场域中涵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此,上述的几种文本已经有意识地加以重视,大部分在80年代以后开展的研究更明确地体现对这一关系的强调。在社会史学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其对华北农村几个村落的研究中,提出了国家权力与区域—地方权力网络糅合的解释模式。在人类学界,波特(Jack Siu)[①g]的华南研究早已十分重视国家对农民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不过,1989年出版的,肖凤霞(Helen Siu)对珠江三角洲一个乡级社区的调查结果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社区研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
对于多数汉学家来说,社会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无法提供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力工具。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传统国家政权只渗透到县一级的行政地理单位,县以下的镇、乡、村主要是由民间社团和社会组织控制,是一种自治性的社区。肖凤霞在所著《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1989)一书,[②g]对这种传统汉学观提出批评。通过镇、乡、村社区的个案研究,她发现:在传统时代,中国的社区的确离中央权力机构的行政控制中心较远,且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不过,当时的国家培养一批地方精英分子,以意识形态和象征的等级制,把这些精英阶层吸收到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利用他们的网络控制民间社会和社区生活。本世纪以来,国家的行政力量不断地向下延伸,使社区成为“细胞化”(cellularized)的社会控制单位,把新的政治精英阶层改造成这些“行政细胞”的“管家”,造成社区国家化的倾向。从而,社区生活也成为类似国家运作的东西。
肖凤霞认为,这一观察对于汉学人类学的意义很大:在目前,进行汉学人类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应该结合弗里德曼的宗教模式、施坚雅的区系理论以及武雅士等人的民间象征分析,而如果我们要达到这种综合,就需要对联系着国家和地方社会的“代理人”(agents)加以重视,在社区和区域的场合中,分析他们的形成以及对社区建构的影响。
象征地方化的研究
与力图在社区中联结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者不同,一些人类学者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看社区。虽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是有国家的社会,但是十分强调国家象征被民间化的可能性。因而,对他们来说,社区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展示国家如何渗入地方,而在于体现地方的象征分立过程。类似的说法,在沃德的渔村社会认同研究中早已被包含在内。1981年出版的马丁所著《中国人的仪式与政治》一书,[③g]进一步地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不过,该书停留在文献研究上,并没有在具体社区实践这种理论。1992年,王斯福出版的《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一书,[④g]结合文献和他的社区调查资料对“象征地方化”加以探讨。与一般社区人类学调查报告不同,王著的叙述框架从“大传统”到“小传统”过渡,先阐述“中华帝国”的国家象征体系,然后进入他的田野调查素材,分析国家象征体系如何转变为具有不同意义的民间社区文化。
社区中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力量
7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版的汉学人类学研究论著,代表汉学人类学方法论的一个转型时代。概括上文的具体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代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在这一时代,社区方法得以复兴,五六十年代对小型社群研究的“代表性”的疑问得以澄清;第二,新兴的社区研究和描述文本,在克服了功能主义时代“分立社群”概念局限性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了学术界对社区的认识。这些论著的出版,共同回答了弗里德曼时代的问题,指出社区的分析可以体现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历史性”。同时,它们提醒我们社区研究如要包容中国社会的特点,就必须走出功能主义的“封闭性社区整体论”和“无历史”(ahistorical)的局限,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古代理念与社区现状、传统与现代加以综合考察。
这几点与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文本与理论的总体反思是一致的。就文本模式而论,近年一般人类学界对功能主义整体观民族志的批评已经充分地展开。马库思(George Marcus)和库思曼(Dick Cushman)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①h]中,概述了对七八十年代对功能主义民族志的9点批评,其中有3点适用于汉学人类学:
(1)在叙述结构方面,传统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totality),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科学或功能主义,所以往往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因此,这种民族志的写法是:先把文化或社会作横切面的切割,然后用功能关系的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
(2)因为以前的人类学者十分关心把社会—文化当成整体的研究对象,所以在他们所写成的民族志中被研究者个人的性格和特色总是被压制或消除,好像他们没有个人的个性而只有集体的共同特点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这种对被研究者的个性的压制,意在使研究显的科学和现实,而实际上减少了民族志的可信程度;
(3)虽然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是在时空上十分局限的社会中展开的,但是人类学者总是强调把具体的事例推向具有理论意义的结论,对具体事例的描述停留在它们所能代表某种“典型性”(typicality)上,而并不进入所研究的具体事例的细节。这种做法不仅使作者从现实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被研究的社区游离到理论的相关性之外,使民族志成为与作者和社区无关的论述。
汉学人类学的新著基本上避免了功能主义民族志的“全观性”、“民族性”以及“典型性”的局限,强调社会力量的多元特点、汉人文化的变异潜力以及社会现象在本土区位的直接意义。尤其是模式交错的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社区调研、象征地方化诸类探讨,均能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坐落中,表述社会的权力差异及其文化反映。
此外,受弗里德曼的影响,它们也能够注意到“历史”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独特地位。这一点是对功能主义民族志的重要补充。80年代初,沃尔夫(EricWolf)[②h]和费边(Johannes Fabian)[③h]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功能主义民族志建构了共时性的叙述框架,而这一框架的提出是以历史的忽略为代价的。“没有历史”的结构功能剖析,与进化论一样,导致文化偏见的产生,造成一种“欧洲以外的社会没有历史”的错觉。弗里德曼更早地注意到功能主义的这一缺陷,而在他之后汉学人类学者之所以能够给予中国历史一定程度上的关注,与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不过,这些新的试验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仍然留下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实际上,虽然这些研究都具有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文本形式。具体地说,虽然大部分的作品已对“历史”加以重视,但是其文本模式仍然保留共时性论的多数特点,从而使历时的视角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在这方面,《陈村》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但是,它叙述的“历史”实际上只有20年(1964—1984),并不具有充分的时间深度。桑格瑞和王斯福的作品,也重视历史,但把历史分别抽象化为“社区背景”和“古代的宇宙观”。此外,虽然大部分作品都已从过去的社区论著中吸取教训,试图包容更复杂、多元的社会力量与象征体系,但是,由于作者过于强调单一的社会联系机制,因此往往把丰富的社群类别、文化类别、社会经济类别归结为一元化的因素。
克服这两方面缺陷,汉学人类学者不仅需要对传统民族志的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造,而且需要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正如不少汉学人类学者已逐步地意识到的,一种既能够表述历史过程又能够展现(display)不同社会—文化力量的交错与互动的文本模式,在目前已成为中国社区研究的急需。在理论模式上,肖凤霞的人类学论点和杜赞奇的社会史观察是较为接近历史与权力多元化视角的。但是,从文本模式看,前者仍属以当代社会为主线的叙述方式,而后者则颇有横切的“断代史”的意味,两者均不足以体现汉人社区历史与社会—文化力量的交错与互动过程。一种替代的文本模式,就是社区史(community history)的叙述框架,不过它不应像进化论那样过于强调事物的起源,而应着重表现不同社会—文化力量如何在大社会中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关系变异、转型以及延生。
近半个世纪以前,费孝通就已指出社区研究与历史的相通性。他说:“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的有可作分析的对象。”[①i]
费先生指出,建构社区历史时资料十分关键,这一点是社区史叙述模式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叙述和解释框架也十分重要。由于社区史终将面对“变迁”的问题,因此它还需要一种宏观的历时性社会转变的理论作为“断代”的工具,而为了说有社会转变的特质,不连贯的(discoutinuous)社会变迁理论是必要的参照体系。
民族—国家理论的启示
牵涉到社区在社会中地位的变迁问题,目前最重要的人类学理论著作是尚未被汉学人类学者引用的吉尔耐(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983)[②i]一书。正如该书书名所标明的,此书的出发点不是“社区”,而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过,吉尔耐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的成长与工业化之后社会再生产方式(mod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的变迁密切相关,因而考察民族/国家务必从社会交往和传承如何从社区性转变为全民性(national)的过程入手。在传统社会,人的社会再生产是社区性的面对面式的人际关系训练,到了民族/国家时代,全民教育和普遍性知识成长起来,并取代了社区性的社会再生产方式。换言之,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是社区—国家分离的社会形态,转变为社区受国家和全民文化(national culture)的全面渗透。
吉尔耐对社区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地位变化的论述给我们一个启示:如果汉人社区的研究试图采用社区史的框架,就必须把大社会的变迁对社区地位的影响考虑在内。不过,由于吉尔耐的理论只限于“社会再生产方式”的变化。忽略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动,因此不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力量的多元性发展。而在这一方面,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85年,吉登斯出版在社会科学界引起广泛反响的《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③i]对现代社会转型进行独特的论述。该书以全球社会变迁的历程为叙述框架,阐明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人的理性化(韦伯)、社会分工的发展(杜尔凯姆)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所谓“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异,主要在于现代社会以民族—国家为特征,其突出表现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融合。造成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动因,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同时也包括其它三种力量的发展:以信息储存和行政网络为手段的人身监视力(surveillance)、军事暴力手段的国家化以及人类行为的工业主义。现代社会之所以与传统社会形成对照,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物质生产高度发达、信息和行政监视大幅度延伸、暴力手段为国家所垄断、工业主义渗透到社会各部分。
吉登斯把具体的社会转型过程分为三段:传统国家时代、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时代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时代。在传统国家(城邦、封建国家、继嗣帝国、中央化官僚帝国)时代,阶级分化十分明显,并表现在城乡之别,也就是说上层阶级居住在城市,下层阶级居住在乡村。城乡之别不仅体现出阶级差异,而且还表示传统国家行政力量涵盖面的局限性。在任何形式的传统国家中,政府对社会的行政控制被限制在城市之内,同时国家象征体系与宗教与一般人民的“民俗”保持相当大的距离,这便导致监视力的软弱。城乡之别与监视力的不发达证明,传统国家不是“权力集装器”(power-container),那就是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较松散,国家只有“边陲”(frontiers)而没有疆界(borders),也没有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权(大量的军事力量受军阀和民间力量操作)。在行为的规范方面,许多规矩只在贵族阶层有效,对一般人民毫无制约力。
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期,就是绝对主义国家。在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在十六、十七世纪出现,其首要的表现是大型帝国逐步蜕变为分立的国家。首先,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自然边陲”被确定为“疆界”,随之,“主权”(sovereignty)的观念也出现了,神异性的国王变成国家主权神圣性和分立性的代理人和象征,法律成为全民性的规范,直接界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裁制定。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发展为暴力的扩张提供条件,军队内部行政管理手段高度发达并为社会秩序控制提供可借用的体系,海军力量的成长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创造了必备的前提。
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它为后者提供了疆域概念和主权性。不过,现代民族—国家只是到19世纪初才在欧洲开始出现,其推动力在于行政力量、公民观(citizenship)以及全球化,而主要的基础是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的增长。所谓“配置性资源”指的就是物质资源,而“权威性资源”指的是行政力量的源泉。吉登斯认为,这两种资源是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机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导致物质资源的增长,而且还导致“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和个人行为取向的发展以及权威性资源的开发。进一步地,商品化使法律成为全民准则、税务成为国家控制工业的手段、劳动力成为“工作区位”(work-locales)的附属品、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一员。此外,传播媒体、交通、邮电等资源的开发,使国家更容易地渗透到社会中,强化其监视力。
正如吉登斯本人所承认的,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史模式只是一种为了理论说明而建构起来的“理想模式”,在不同民族的实践中可能出现地方性的变异。即便这一模式存在着“建构性”(constructiveness),对中国社会变迁史仍然具有一定说明意义。中国国家是从城邦国家转变为官僚—继嗣帝国,经历明清的绝对主义国家(此时期从具有世界影响的元帝国,转入严格限定边界的明清帝国),在本世纪初进入民族—国家的。这一转变同样地经历国家与社会分离(城乡分离)到国家与社会充分一体化的变迁。
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吉登斯并没有对社区与国家力量变迁史加以系统化的联想。但是,他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传统国家、经绝对主义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的考察,也隐含社区作为社会的主要单位所经历过的一系列地位变动。可以说,民族—国家的成长史是以社区内部的人民不断地被从地方性的制约“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的过程。[①j]
如果我们可以把明清以前称为传统国家、明清称为绝对主义国家、民国以来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地可以说中国社区的历程是以城乡—阶级分化为开端、经内外权力(绝对主义国家与西方世界体系)交错导致的“主权”和社区“全民化”过程、进入国家对社区监控全权化(totalitarianism)的。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过程之中,对汉人社区内部社会秩序、行动、互惠以及它们与外在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加以考察,可以建构一部有益于理解大社会及其变动的社区史。这部社区史仍然是试验之中的作品,但是它的大框架可以被视为国家—社会互动史的“折射”。吉登斯从宏观的世界史角度,阐明大社会从传统国家,经绝对主义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汉人社区史则可以反映如下过程:原有的较为自立的社区及其外联区位体系,经历绝对主义国家的行政区位制约,走向“全民”社区行政“细胞化”的历程。
当然,在重构这一社区历史的过程中,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是值得注意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成长史,最明确地表现出“单线性”(linear)演化的特点。这种单线性演化的全景,诚然值得我们当作变迁模式建构的线索。但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绵延性、历史在现实中的回归性,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历史的绵延性和回归性,给予汉人社区在现代场合中得以延生的空间,其具体表现就是所谓“传统的复兴”、“社区生活的回归”。近年的社会调查发现,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社区并没有在中国社会消失或完全被“细胞化”,并且其作用有愈演愈烈之倾向。因此,汉人社区史的叙述框架,尚需包容“倒逆时间”(reversed time)的观念,描写“从现代到过去”,“细胞化”以后的社区寻找它们原有的生存根源的“怀旧”(nostalgia)过程。
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汉人社区研究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发展:在20至40年代,受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社区”被当成一种方法论的单位加以研究,它的意义在于一种供人类学者借以窥视社会的“分立群域”,从事此种研究的学者相信,透过社区,可以了解中国整体社会结构,或至少了解其社会结构的基层;在50至60年代,“社区”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被提出来,这一问题的提出促使汉学人类学者重视社区以外的社会、国家以及历史;60年代以后,在前一阶段反思性讨论的提醒之下,社会人类学者回归到社区中展开田野工作,由于这些提醒的存在,他们已经能够较为开放地看待社区,认识到社区中多种文化模式的交错、社区的“缩影性”、社会权力多元化、文化地方化等现象。几十年来社区研究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演进线路,是“社区”作为方法论单位,向“社区”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进一步导致汉学人类学界避免用功能一体化的观点看社区,也就是避免把社区看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内在体系,从而促使人类学者在从事社区民族志研究的同时,注视与社区内部权力结构和功能一样重要的大场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在现存诸种新型社区研究试验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社区探讨强调在社区中展示地方性的文化—权力网络和超地方性的行政细胞网络的联接点,它一方面具有浓厚的人类学特色的“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反映大社会的结构与变动,因此是很有潜力的研究取向。但是,这种试验仍然没有充分吸收宏观社会理论,在解释和叙述框架方面尚有值得加深之处。一个可替代的模式,就是带有强烈“国家—社会”关怀的社区史叙述文体。这种文体不仅继承社区法的许多优点,而且可以作为大社会变迁和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的展示形式,对于社会理论的运用和反思也具有正面作用。当然,在社区史的研究中,除了上文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历史的框架之外,下列4个方面也应引起重视:
1.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异
社区内部结构分为两类,一是人民的空间和社会组织全貌,二是社区权力的分化秩序。社区空间和社会组织的布局,有的是以亲族(kinship)为轴心,有的是以地域(territoriality)关系为轴心,有的是以行业为轴心,有的是以行政空间为依据。把汉人社区分为都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我们可以发现,都市社区受行业和行政空间的制约较大,而农村社区则以亲族和地域的结合形态为主要形式。社区内部的权力分化,受一定的经济、社会、象征差异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社区上层人物以经济地位、在社区中被尊重的程度、受帝国官僚体制的间接承认程度等为策略,塑造自我的形象,造成一定的社区权力差异。随着民族—国家的成长,政府的官僚体制对社区事务渗入程度提高,造成社区内部正式政治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并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权力结构的分化状态。
2.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区域性变异
弗里德曼是较早提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区域性变异问题的学者,他从汉人宗族村落(lineage villages)分布情况为切入点,考察国家权力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社区组织的变异。他认为,在“边陲地区”,由于政府社会控制力的软弱,民间宗族组织得以发展。这个看法局限在宗族现象,其可应用性很值得怀疑。但是,弗里德曼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探究社区(村落)的试验,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参考。在不同区域中,国家力量与社会的互动所产生的模式应该是与国家、社会力量的消长为变异的核心内容,而这些变异可能导致社区结构的不同。在分析这些变异时,施坚雅的区系理论值得我们参考。不过,他的模式属于经济区位学的观察,较少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运用过程中,尚待进一步的修正。
3.民间模式和“社会缩影”的问题
目前对以社区生活为主体的“民间模式”有三种探讨,即沃德的“有意识模式”在社区中交错探讨,马德生的“社会缩影”探讨以及王斯福的帝国象征地方化探讨。在社区史的框架之内,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过程,不能避开文化—象征体系和“中华帝国”历史传统的地方性意义。社区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描写法,不过,它不应忽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在民间“自上而下”的重新阐释和意义改造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民间信仰与仪式行为与中国政治文化、古典“大传统”、国家崇拜(state cults)的关系,应引起社区研究者的注意。
4.文本模式的多样化
在功能主义的影响下,社区民族志文本一直以文化制度的分割性排列、整合为主线,强调表现社区的内部一体化和对外封闭性,而且十分排斥作者第一人称的使用、被研究者的“声音”(voices)的表述。社区史的模式不仅应打破“分立群域”的观念,而且还应包容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交流及人类学知识形成过程的描写。在文本体例方面,近20年兴起的“实验民族志”文本,较能重视以不同的叙述框架展示广泛的社会互动和人类学者的反思,它的一大趋势是在本土文化解释体系与外在于社区的政治经济关系之间,寻找联接点,这与包容国家与社会关系考察的社区史取向是一致的。
注释:
①a 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社会研究》1935(66)。
②a 或称“Chinese anthropology”,其意为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尤其是“汉人社会”进行研究。
①b Bronislaw Malinowski,1944,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Chapel Hill,pp.24-27.
②b 德格鲁特的主要出版物包括:1907,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E.J.Brill.
③b Danial Kulp,1925,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Familism,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
④b 吴文藻著“导言”,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⑤b Fei Hsiao-tung,1939,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ery Life in Yangtze Valley,Dotton.
①c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94—95页。
②c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①d Edmund Leach,1983,Social Anthropology,Fontana,p.127.
②d Maurice Freedman,1962,"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3:I:1-19.
①e Bronislaw Malinowski,1932,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Harcourt,Brace and World.
②e 例如,Evan-Pritchard对无中央集权的努尔人宗族列变制的分析,见:The N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
③e Burton Pasternak,1972,Kinship and Community in Two Chinese Villag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①f Barbara Ward,1965,"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in Michael Banton ed.,The Relevance of Models for Social Anthropology,Tavistock.
②f Arthur Wolf,1974,"Gods,ghosts,and ancestors",in Arthur Wolf 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③f Steven Sangren,1987,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f Anita Chan,Jonathan Unger,and Richard Madsen,1984,Chen Village: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CaliforniaUniversity Press.
⑤f Richard Madsen,1984,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①g Sulamith and Jack Potter,1990,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g Helen Siu,1989,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③g Emily Ahern,1981,Chinese Ritual an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④g Stephan Feuchtwang,1992,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Routledge.
①h Georg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1982,"Ethnographies as text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②h Eric Wolf,1982,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③h Johannes Fabian,1983,Time and the Other,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①i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94页。
②i Ernest Gellner,1983,Nations and Nationalism,Blackwell.
③i Anthony Giddens,1985,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Polity.
①j Anthony Giddens,1985,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Polity.
标签:马林诺夫斯基论文; 人类学论文; 费孝通论文; 弗里德曼论文; 功能主义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田野调查法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
